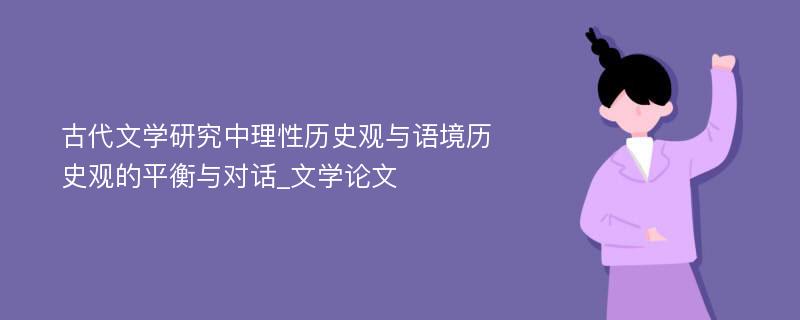
古代文学研究中理性史观和语境史观的平衡与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理性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所谓“文学”的历史,还是文学的“历史”?这一提问和思考,是基于哲学研究领域哲学与哲学史关系讨论而产生的类比联想。它涉及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理性重构与历史重构,以及背后折射的对待古代文学的理性史观和语境史观等问题。在此,结合近年来北京地区中古文学研究状况,做一粗略的分析和梳理,意在呼唤古代文学研究中理性史观和语境史观的平衡与对话。
韩东晖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一文指出:哲学史编纂和研究的重心究竟在其哲学特性还是历史特性,是哲学界深为关注也争议颇多的重要问题。对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的区分凸显了对待哲学的历史的两种态度和编纂哲学史的两种范式,其背后则是理解哲学的两种原则:理性主义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在方法论意义上,将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二分法转换为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两种理想形态,二者均面临如何澄清自身的思想语境和哲学观的问题,而这种反思会成为二者对话与沟通的契机。应保持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必要的平衡,既充分肯定哲学的历史性,又不能将哲学史编纂仅限于钩沉文本,阐明事实,推究因果,还要分析概念,重构论证,彰显意义。
这里所说的“保持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必要的平衡”,似乎也适用于古代文学研究,即在思考和研究有关古代文学的重大问题时,应把握好文学特性和历史特性并重的原则。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与文学史的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曾经有学者探讨和论述过“文学本位与历史本位的问题”(赵义山《历史本位与文学本位》,《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在学科建设的大潮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建立或组合新的学科方向——其中最突出的表征就是“某某与文学”论题的流行。这种“某某与文学”的论题,属于事物之间的关系研究。平心而论,这种研究,有助于了解文学,理解文学现象,但它本身与文学和文学现象仍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况且,在事物的关系研究中,不仅需要说明二者有无联系,还要说清楚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建立和形成的过程。而这一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我们好像仅仅满足于指出某某与文学存在着某种关系,如此而已。
二
文学与文学史的关系问题,虽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存在。
比如关于文学历史的自然状态及其逻辑展开,就牵涉到历史重构与理性重构问题。
以文学编年史而言,继1998年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问世并产生极大影响之后,曹道衡、刘跃进于2000年出版了《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著者试图突破以往文学史的编写模式,不以朝代为断限,而特别注意疏通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努力清晰地勾画出南北朝文学兴衰的轨迹。具体编录内容为:(1)对当时作家发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事件、哲学思潮、文学活动;(2)作家行迹,包括升迁贬谪、人物交往等;(3)作品系年。
对于编年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这种学理化追求,董乃斌曾做过专题研究,其《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兼评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一文(《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指出,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反思,呼唤一种新的大文学史观,从而将文学史写作推向新阶段,《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就是这一时期众多实践成果中的卓越代表。所谓“新的大文学史观”,即主张充分尊重各个时代人们的文学观,全面辩证地对待一切文学史现象,包括史料和文体,同时引入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深入探索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等等。
而过常宝的《建立在模式之外的陈述方式——评聂石樵教授著〈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一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也对文学史的建构方式和阐释模式发表了看法。该文肯定了聂著文学史建立在叙述习惯或叙述传统上的文学描述方式——在严密的历时性框架下,以作品而不是以作者为中心,书中往往以文体为理由,将同一作者的作品系于不同的章节。这一形式,首先当然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古代文体的嬗变,也是为了替文学史这一学科维持一个基本的连续性主题。但这一组织方式,在事实上冲击了另一种文学史观念,那就是人们一直孜孜以求的社会意义观念。文章认为,来自意识形态的意义模式,和传统的知人论世的诗教观念相结合,成为当今文学史编写中的一个最顽固的模式。只有削弱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知人论世的意义模式,文学事实才会凸显出来,文学史才能为我们提供文学事实,而不是所谓“意义”。
又比如关于文史结合、文学本位及其超越,就牵涉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文学的审美研究、文本的细读与文学的外部研究如何进入文学内部等问题。
2001年5月10日至11日,在上海召开了“新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会上葛兆光提出,古代文学的研究应该参照历史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对于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进行反思。现在所说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人们建构的一部我们理解的文学历史,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论文还在不断地描述、建构我们理解的文学史,其实文学史是不是这样很难说。如果我们改变一下研究方法,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文学史、文学作品怎样虚构了或者说构造了一个我们理解的传统。其实这个问题既涉及文学又涉及历史,历史真实的反思引起文学研究的变化。
三
什么是“文学”的历史?
2000年,郭英德的《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一文(《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在回顾新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之际,对9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所谓“私人化”倾向,即“小题大做”、“舍内求外”、“考据至上”、“制谱成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把反思的触角深入到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灵魂内部,“声讨古典研究者有如‘冷血动物’般的冷漠、顽固,并大声疾呼血性男儿的出现”。
应该说,该文指出的以上倾向的确是客观存在,但正如文章强调的那样,以上四种倾向在其“负”的一面之外,也还存在着其“正”的一面。问题是我们对待文学特性和历史特性时,把什么当作目的,把什么当作手段。
关于“文学”的历史及其内涵,我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学现象和观念的历史,即从历史的维度探讨文学的发生学机制。如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与当代文艺学理论的关系,就需要处理好理性史观和语境史观的平衡。在“新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王飙认为,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现在研究古典文学都是拿当代的文艺理论做指导,表现出所谓的当代意识,总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实际上古代文学中有很多概念术语:从义法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这些概念是从古代文学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可以运用当代的观点,吸取古代文论当中合理的成分,根据古代文学创作的实践,建立自己的理论,而不是以现代的艺术性、形象性来衡量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论。
二是文学家的历史,即从思想和心理的维度探讨文学家的思想世界、心灵世界与情感世界。近年来,从心理的维度探讨文学家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成果,而对文学家的思想世界的探讨,似乎相对显得薄弱了一些。
三是文学作品的历史、文体演变的历史,即从文本分析的维度探讨文学作品成立和演进的自身逻辑。如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特点及其实质,张少康的《刘勰的文学观念——兼论所谓杂文学观念》(《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刘勰能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特点,既看到文学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部分而具有普遍共性:“道之文”,同时看到它又和人类文化中其他部分,如哲学、历史、政治、伦理道德等根本不同。刘勰与六朝时许多文学批评家一样,清楚地看到了那种宽泛的“文”的观念是不科学的,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方式试图寻找和探讨文学艺术,也就是所谓纯文学的特征。所以,张少康对简单地肯定所谓“杂文学”观念,甚至把它说成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点持反对态度。
四是文学精神的历史展开,即从美学的维度展开文学的审美研究。袁行霈的《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曾经对其实质做过精辟的概括:抛弃那种先入为主的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式”的定性研究方法,回归到文学本位,将文学作为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总之,关于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理性重构与历史重构(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更多采用还原与重构的提法),可以说是近年来学界关心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往的讨论,集中在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还原与重构;现在人们认识到,面临纷繁复杂的学术环境和全球化浪潮,还原和重构不仅需要创新思维,更需要清晰和正确的研究理念。随着对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反思的深入展开,人们开始注意到本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学术思想的“对接”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在进行“对接”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即现代学术范式理念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独特性”之间的关系:既要充分认识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又要避免在具体的研究中,用这种“独特性”去取代现代公认的学术范式和理念。也就是说,来自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性”研究,还应该回到现代学术范畴中加以比较和判断。在我看来,后者尤其重要,所谓熔古铸今、贯通中外,其实质也就在此。
所以,今天的古代文学界仍然面临着廓清基本架构、厘清基本理念的严峻任务;而保持理性史观与语境史观的平衡和对话,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