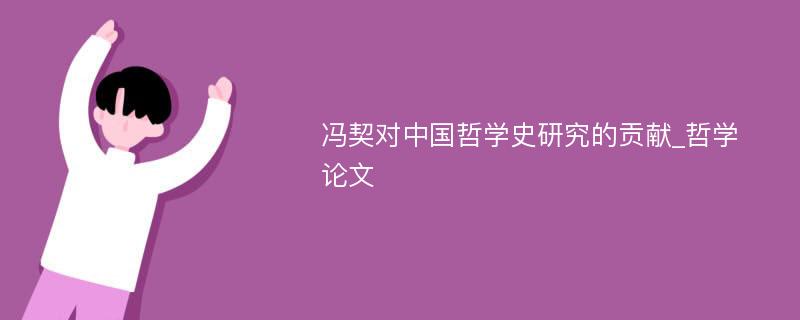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哲学论文,贡献论文,论冯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契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杰出代表之一。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逻辑结构的开发、基本精神的新思两个方面简要展示冯先生的理论贡献。
逻辑结构的开发
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对子”结构上,整个中国哲学史几乎被描绘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突出强调了哲学中的党性原则以及哲学与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联系。“文革”之后,不少学者逐步摆脱“左”的思维方式的限定,他们以黑格尔、列宁的辩证法和哲学史观为参照系统,开始关注和挖掘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构。冯契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对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开发中,冯契先生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以列宁提出的欧洲哲学史的圆圈为参照系统,全面总结了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螺旋结构。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是辩证逻辑的基本内容之一,它在西方哲学史上是由黑格尔和恩格斯作出较系统阐释的。冯契先生指出,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应该是统一的。他说:
“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要把握所考察对象的基本的历史线索,看它在历史上是怎样发生的,根据是什么;又是怎样发展的,经历了哪些阶段。而真正要把握基本的历史线索,就要清除掉外在形式和偶然的东西,以便对对象的本质的矛盾(即根据)进行具体分析,对每一发展阶段或环节都能从其典型形式上进行考察,而后综合起来,把握其逻辑的联系和发展的规律”。(《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历史方法的真正贯彻有赖于逻辑方法的运用,而逻辑方法以历史方法为基础,因此,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存在着内在的关联结构。用这样一种方法论原则考察中国哲学史,就会发现哲学史所体现的是人类认识的矛盾运动:“哲学家们所争论的问题就是矛盾,某个矛盾产生、发展、解决了,另一个新的矛盾又产生、经过发展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在循环往复中前进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就表现为黑格尔、列宁都说过的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形的曲线。”(第17页)那么,为什么人类的认识发展会出现螺旋形的曲线呢?冯契先生认为:
“这是因为客观现实是充满着矛盾的,而人们对这些矛盾的认识,往往是一些人考察了矛盾的这一方面而另一些人则考察了矛盾的那一方面,只有经过矛盾斗争才能达到比较正确、比较完整的认识。每一个矛盾的解决就表现为一个圆圈。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经过斗争、总结,又出现一个圆圈。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每经过一次矛盾斗争,认识就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同上)
人们对客观现实矛盾的认识总是处在从片面到比较全面的循环往复中,但这种循环决不是原地踏步,而是螺旋形的上升。人类的认识如此,作为人类一般认识史的全部哲学史也是如此,它表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形象地说像一个大圆圈,而这个大圆圈又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圆圈构成的。因此,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研究哲学史,关键的一点就是挖掘蕴涵其间的逻辑演化轨迹。
冯契先生选择了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举的欧洲哲学中的几个圆圈作为参照系统。列宁说:
哲学上的“圆圈”: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不!
古代: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儿对Gassendi(Spinoza?)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
冯契先生主要展开分析了从文艺复兴到近代的三个圆圈。冯先生认为,第一个圆圈是从笛卡儿、伽桑狄到斯宾诺莎。笛卡儿是唯理论、二元论、唯心论者,伽桑狄是唯物论的经验论者,而斯宾诺莎既是唯物论者,又是唯理论者,在某种程度上作了总结;第二个圆圈是从霍尔巴赫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到黑格尔。霍尔巴赫是机械唯物论者,贝克莱、休谟、康德是唯心论者,休谟、康德又是不可知论者,黑格尔既批判了霍尔巴赫,又批判了康德,提出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总结了前人的成果;第三个圆圈是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黑格尔是唯心论者,但有辩证法,费尔巴哈是唯物论者,却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既批判了黑格尔,又批判了费尔巴哈,建立了辩证唯物论。冯契先生认为,这三个圆圈正是列宁对欧洲近代哲学逻辑结构的研究,揭示了认识辩证运动中的感性和理性、绝对和相对、唯物论和辩证法三对主要范畴。虽然中国哲学有着自身的特点,但也有与西方哲学相通的地方,世界哲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些普遍规律,因此,列宁总结的欧洲哲学的圆圈可以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结构的参照系统。
正是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以列宁总结的欧洲哲学发展的圆圈为参照系统,冯契先生勾画出了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螺旋结构。
从总体上说,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圆圈,分别以荀子哲学、王夫之哲学、毛泽东哲学的诞生为标志。冯契先生在概括前两个圆圈时指出:
“中国古代哲学开始于原始的阴阳说,先秦时期争论‘天人’、‘名实’关系问题,由荀子作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仿佛回复到出发点,这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圆圈。秦汉以后,哲学上关于‘有无’、‘理气’、‘形神’、‘心物’等问题的争论,由王夫之作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在更高阶段上达到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完成了又一个圆圈”。(第18页)
从原始的阴阳说到荀子哲学是第一个大圆圈,从荀子哲学到王夫之哲学是第二个大圆圈,第三个大圆圈就是从王夫之哲学到毛泽东哲学,正象冯先生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小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所说的那样,“经过近代哲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当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历史观和认识论中的心物之辩作总结的时候,仿佛是在像荀子、王夫之复归。……这个‘仿佛复归’,实际上是实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哲学革命”。
冯契先生还重点对中国古代哲学两个大圆圈中的小圆圈进行了描述。第一个大圆圈包含着两个小圆圈:“前一个是原始的阴阳说经孔子、墨子到《老子》。”(第366页)原始的阴阳说主要是一种素朴的天道观,孔子重理性,墨子重经验,讲的是人道,老子着重讲天道,是对原始阴阳说的复归。“后一个是《管子》经孟子、庄子到荀子”(同上)。《管子》和孟子虽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但都是独断论,庄子则主要是相对论和怀疑论,其中还经过了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到荀子作了总结。在此之后,“哲学继续前进,荀子——《吕氏春秋》和韩非——《易传》,可说是总结阶段的一个小圆圈”(同上)。而在荀子到王夫之这个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第二个大圆圈中也包含了若干个小圆圈:“如‘或使’、‘莫为’之争,到王充完成一个小圆圈:‘形神’之辩,到范缜完成一个小圆圈;作为‘天人’之辩的一个侧面的‘力命’之争,到柳宗元、刘禹锡完成了一个小圆圈;‘有无(动静)’之辩,到张载完成了一个小圆圈;从张载到王夫之,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圆圈,这段时期围绕哲学的根本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归结为‘理气(道器)’之辩和‘心物(知行)’之辩,它们由王夫之作了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册,第1090—1091页)
可以看出,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逻辑结构的挖掘是比较深入的。但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出:第一,冯先生注重开发逻辑结构并不意味着他轻视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在冯先生看来,哲学史是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因此,研究认识的辩证运动离不开对思维与存在关系以及社会实践的研究。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世界哲学中是普遍存在的,但在不同民族哲学中的表现则是不尽一致的。研究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发展轨迹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冯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论著中所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第二,冯先生所借用的“圆圈”这一概念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所展示的是哲学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曲线轨迹。因此,冯先生所说的“圆圈”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既不是僵硬的,也不是外在的。他对“圆圈”轨迹的描述决不是为了整齐好玩,而是为了更加深刻地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应当指出,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开发,并不是自己头脑里的突发奇想,而与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整个方法论走向密切相关。70—80年代之交,人们开始逐步摆脱“左”的思维方式的羁绊,思想越来越活跃。中国哲学史界的一批学者在继续反思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同时开始深入挖掘列宁的哲学史定义,在运用历史唯物论和哲学基本问题研究哲学史的基础上充分估价唯物辩证法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意义,着重研究了中国哲学范畴史和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结构,并取得了突出成就。与当时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趋向相一致,冯契先生较早和较系统地勾画出中国哲学发展的螺旋结构,和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史家一起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冯契先生未对中国哲学发展第三个大圆圈中的小圆圈作出详尽的阐论,并非是改变了他的方法论初衷,而是出自对中国近代哲学实际的考虑,正像他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所说:“我为‘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取了不同的书名:一叫《逻辑发展》,一叫《革命进程》。这是因为,虽然两书都是运用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但所取视角稍有不同,选裁颇有些差别。在古代,我比较注重把握哲学家的体系,把它们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以揭示其中所包含的认识环节,前后联系起来考察其逻辑发展。在近代,由于现实经历着剧烈变革,思想家们一生变化较大,往往来不及形成严密的哲学体系。因此,我认为对近代哲学不要在体系上作苛求,而应该注重考察思想家们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独特贡献,看他们在当时提出了什么新观念来反对旧观念,从而推进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基本精神的新思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既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结论,也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切入点。长期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哲学着重讲做人,认识论不发达;长于伦理,忽视逻辑;停留于常识性的人生伦理上,缺乏思想的深度。可以说,这些对中国古代哲学特征的描述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一大批中国哲学研究的后来者。冯契先生从中国古代哲学的实际出发,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冯先生以广义认识论为理论原点,分别从认识论、逻辑学、自然观以及人的自由等方面,展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中国古代哲学特点的新思。
针对中国哲学认识论不发达的观点,冯契先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既然我们把哲学史作为认识史的精华来看待,如果说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不占重要地位,那么,何以见得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中的地位呢?遵循这样的思路,冯先生对何为认识论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厘定。冯先生指出,我们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回顾哲学史,可以看到,哲学史上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大体有四个: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但欧洲近代以来以实证论为主的哲学思潮把认识论狭义化了,在他们的理论视域里,前两个问题是有意义的问题,而后两个问题是形上学的问题,没有意义。从狭义化的认识论出发,就会觉得认识论在中国哲学中不占重要地位。冯契先生对狭义认识论对认识论范围的限定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指出,唯物史观的创立,给人如何由自在变成自为、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而实现真善美统一的理想这个既属历史观也属认识论的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所以,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不应把认识论局限于前两个问题。以广义认识论的观点为参照系统来回顾中国哲学,就会发现:
“在中国古代,从孔墨开始,就已在讨论感性和理论思维的关系了。而庄子已对‘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客观真理’提出种种责难。所以不能说中国人不关心前两个问题。……由于中国古代哲学(从先秦到鸦片战争以前)同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相比,曾经历了更长时期的持续发展,因而倒是较多和较长期地考察了上述后两个问题: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天人”之辩;‘天人’‘名实’之辩贯串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所以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上,显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第41—42页)。
冯契先生的观点显然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思路,广义认识论是研究哲学史的重要参照系统。从中国古代哲学来看,也关心前两个认识论问题,但更突出地考察了后两个认识论问题。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认识论不发达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正因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认识论相当发达,所以理应在作为人类认识史精华的世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针对中国哲学忽视逻辑、忽视自然的观点,冯契先生提出了另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明代以前,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的那么多发明和创造,是用什么逻辑、什么方法搞出来的呢?冯契先生指出,“中国哲学注重伦理,是公认的事实。中国人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在《墨辩》中有很高成就,后来却被冷淡了,所以确实不如欧洲人和印度人热心”(第43—44页)。但正像李约瑟所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337页)冯契先生欣赏并基本同意李约瑟的上述观点。在冯先生看来,谈到逻辑不能只考虑形式逻辑,也应当重视辩证逻辑。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指汉代以后—引者注)虽然在形式逻辑方面要逊色于欧洲和印度,但在辩证逻辑方面却优于他们。正如冯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如果古代哲学家已经提出某些辩证思维的原理,而当时的科学家已在运用它们作为科学方法,那就是有一定程度的自觉。……辩证逻辑在中国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有较大的成就,它虽然还是朴素的(缺乏近代科学的基础),但已经具有高级阶段的许多要素的萌芽,值得我们仔细地加以研究”。(第45页)
因此,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缺乏对形式逻辑的研究有一定的道理,但缺乏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并不等于缺乏逻辑,由于中国传统哲学较早和较深入地探讨了辩证逻辑,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逻辑思想也是很发达的。与此相关,中国传统哲学还较早的发展了辩证自然观,以气一元论为基础,认为气分为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就是道,即自然发展的规律。总之,“原子论思想和形式逻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弱点。但是中国人却比较早地发展了朴素的辩证逻辑和朴素的辩证自然观(气一元论),从而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法则这个认识论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考察,这却是一个优点”。(第47页)
在以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欧洲哲学中心主义者的眼里,“伦理型”的中国传统哲学只是一些常识性的道德教训,缺乏理论的深度。冯契先生指出,这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哲学的无知而产生的偏见。冯契先生从真善美相互统一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哲学在考察人的自由问题上的特征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观点。冯先生的总体看法是:
“中国传统哲学从人和自然的交互作用来探讨人的德性的形成过程,比较早地考察了伦理学上的自觉原则和美学上的意境理论,从而对理想人格如何培养这个认识论问题(这个问题也牵涉到真、善、美三者的关系),提出一些富于民族特色的合理见解”。(第54页)
冯契先生指出,关于人的自由问题,从认识论来看,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上,荀子、刘禹锡、王夫之的观点比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的观点更值得我们注意。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论者“不是把天人关系了解为‘无对’、‘复性’,而是朴素地把握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把人的自由看作是在人和自然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的,并从而引申出‘积善成德’(荀子语)、‘性日生而日成’(王夫之语)的命题”(第48—49页)。可以说,不论是荀子、刘禹锡还是王夫之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辩证的理解,他们一方面主张因任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主张治自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改造、征服自然,从而使人们在不断认识必然王国的基础上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冯契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真与善、认识论与伦理学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特点发源于孔子的“仁智统一”说(详见《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第89页)。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伦理学说与西方伦理学说相比,着重考察了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从而忽视了道德的自愿原则。冯契先生接着指出,人的自由不仅是真和善的问题,也是美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和伦理学的问题,也是美学问题。庄子“庖丁解牛”的寓言已经涉及到审美自由的问题,这种审美自由的思想与儒家的“言志说”相结合,就逐渐形成了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意境理论(关于抒情艺术的理论—引者注),深入地探讨了在艺术当中如何实现人的自由的问题。从真善美相互结合的角度认真审视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的自由的观点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问题的整合式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为当代中国哲学人类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迪。
综上所述,冯契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分析角度和结论,不仅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更切近中国古代哲学的原型或原貌;不仅表现了实事求是和披沙拣金的理论精神,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热忱。
标签: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认识论论文; 王夫之论文;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 哲学史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逻辑结构论文; 冯契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荀子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