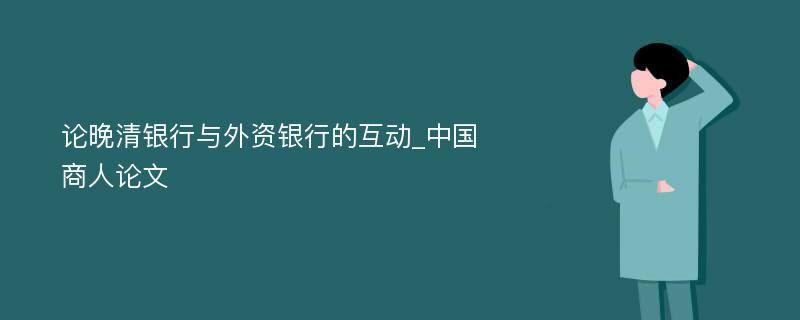
略论晚清钱庄与洋行关系的互动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钱庄论文,洋行论文,晚清论文,互动性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晚清,钱庄(注:本文所指的钱庄是指晚清中国商人开办的钱庄,外国商人在这一时期开办的钱庄不包含在内。)与洋行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两者相互融合,钱庄为洋行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钱庄借助洋行的势力扩大了自己的金融活动,实力不断壮大;另一方面,两者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不断冲突。目前,学术界对钱庄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如汪敬虞、张国辉、姚会元等先生在其相关论著中,对各通商口岸的钱庄、洋行的金融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涉及到钱庄与洋行的关系,并作了初步分析,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并厘清钱庄与洋行的关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晚清钱庄与洋行的经济互动:冲突与合作,共生与共存
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被迫对西方开放,中国传统的金融行业钱庄和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国洋行都适时地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钱庄方面看,它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种古老的金融机构。在鸦片战争前,它主要起着调拨资金的作用,适应了中国社会各省之间商业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商品的流通。鸦片战争,钱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量上,由于战乱、金融风潮的影响使钱庄的数量变更相当大,但总的来说,钱庄的资本是不断壮大的。在业务方面,由于钱庄实力的不断壮大,它的业务范围逐渐辐射外地。许多钱庄以开设分支机构或代办钱庄的方式,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外地。业务范围的扩大不仅促进了本国金融业向内地的扩展,而且加深了各钱庄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了其业务往来,加快了钱庄的发展。与此同时,钱庄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在鸦片战争前,钱庄主要经营货币的交换业务;鸦片战争后,它“摆脱了货币兑换业务,而集中在存款、放款、办理划汇、签发庄票等信贷活动上”。(注: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第33、68、80、51页。)钱庄在经营活动方面的种种变化,不能不影响到钱庄性质的变异,钱庄开始融入资本主义因素。
在钱庄不断发展的同时,洋行实力的发展更为迅速。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就已经有一些洋行在活动;鸦片战争后不久,洋行蜂拥而至,数量不断增加。道光二十年(1840年)还不足40家,“1872年不过343家,1882年增到440家,1892年已过579家,1902年比十年前增长一倍多达到1189家,到1910年则达到3239家”。(注:参见黄逸峰、姜铎等著《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7-289页。)在资金上洋行也有不同程度地增长,“50年代中期,上海美商的财产达到100万元”,而“到了80年代初期,上海外商的财产,包括土地、建筑、船只、货物、金银及其他财产在内,已达到5700万两之多”。(注: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7、477页。)这一时期,不管是小洋行还是大洋行在数量上不断得到增长,资金也不断地扩充。其突出地表现在经营范围的扩大上。早期的洋行大多靠卖鸦片起家,如怡和、旗昌、沙逊、宝顺、琼记。这一时期,由于洋行在华资本不十分雄厚,能力有限,它们只能以本国的工商资本家为依托,接受他们的委托,作为其在华的代理人。鸦片战争后,洋行的实力不断扩大。在金融业方面,国际汇兑业务掌握在大洋行手里,尽管19世纪50年代外国银行资本已开始进入中国,但势力远不如洋行大,直到6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洋行放弃了原来的汇兑业务,有的还把自己转为银行的股东。(注:参详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4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939、1940页。)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钱庄的业务几乎被外国洋行控制。洋行通过自己建立起来的商品收购网络和使用钱庄发行的庄票,深入内地对农产品和原料进行压价掠夺。为了方便自己的掠夺,便于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农产品,洋行还投资于交通运输行业和工业。1862年,美资旗昌洋行的大股东开办了旗昌轮船公司,经营上海——广州和长江两大航线。1872年英资太古洋行也设立了太古轮船公司,经营上海——香港航线和长江航线。在工业投资上,4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主要以船舶修造业为主,后又投资茶叶加工。总的看来,晚清洋行业务发展与变化是与其对华掠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洋行侵略一步步地加深,洋行经济实力发展壮大起来,进行掠夺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洋行的经营也逐渐成为一种掠夺型经济;另一方面,洋行业务的变化发展也促进了洋行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洋行的侵略与洋行业务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洋行初到中国时,在进出口贸易中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打开市场的,它只有得到钱庄的支持才有可能打开局面。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壤里的钱庄在商品服务流通领域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洋行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就不得不利用这条重要的商品倾销渠道。没有钱庄的支持特别是在银行还未出现于中国之前,仅凭洋行的力量是很难打开市场的。在鸦片战争后,英国输华商品总产值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例子。1843年英国输华商品总产值比1840年略有增长,但在1846-1849年间,其对华商品的总值不得不回落到1843年的水平;进入50年代,这种状况也没有很大的改观。以至1848年英国曼彻斯特工商协会的资产者呼吁“大家已经知道,距海岸不远的大城市里,钱庄和资本家的联合组织确已控制口岸市场,其势与进口商最为不利”。(注: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尽管这里含有一定程度的夸张和对中国钱庄以及商人的恶意攻击,但它的确反映了钱庄在中外贸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西方各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发展经济的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按照自己的要求和需要改造世界。钱庄在洋行蜂拥而至中国市场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针对性强的应对措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资产者的要求改造自己。钱庄发行的庄票,需要外商的承认和使用,只有这样,钱庄才能占领这个新出现的金融市场;钱庄的商业信贷也同样离不开这个市场。另外,钱庄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如了解中国市场、与中国商人联系密切和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等,使钱庄能够很容易地帮助洋行推销洋货和掠夺农产品。中国钱庄在利润的驱使下需要与洋行合作。对洋行来说,只要把钱庄稍加改造,就能使之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洋行可以利用钱庄同中国商人打交道,也可通过钱庄利用中国商人的资本为自己的商贸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另外,随着中外经济贸易的深入展开,钱庄不仅仅是要适应其环境,让自己能生存下去,而且更要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钱庄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与洋行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
当然,洋行与钱庄的合作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洋行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改造钱庄,而洋行与钱庄的经济利益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之间必然会出现摩擦与冲突。特别是随着洋行不断发展壮大,它对钱庄在金融行业的垄断越来越不满,尤其是外资银行发展壮大后,它们的摩擦与冲突越来越多。
二、买办:钱庄与洋行互动的中介
钱庄与洋行虽看似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机构或企业,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新与旧的冲突中,它们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大的相融性:
首先,钱庄为洋行进入中国市场、深入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钱庄在中外商人的联系与沟通上起了桥梁作用,为洋行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方便。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阶段,钱庄的桥梁作用也是不同的。起初,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贸易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换,洋行的商品并不能迅速地转化为资金。而钱庄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它接受中国商人的委托代售货物,这样一来可使洋行的商品迅速转化为资金,以方便洋行与中国商人的贸易。当然,这种交换方式是相当原始的,并不有利于双方贸易的展开。但是,在双方并不相互了解情况的前提下,钱庄代售货物,预付货款还是有利于促进双方贸易的,进而促进了中外商品流通。另外,鸦片战争后,外商大量进入通商口岸,随之带来了不同货币的兑换问题,钱庄为解决这一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洋行只有通过钱庄对其银两成色进行鉴定,来保证贸易活动的展开。还应该指出的是,钱庄票据的使用更加方便了外商与中国商人在贸易上的往来。由于外国商人初来乍到,他们对中国商人的信誉、资本状况、商品交易方式以及中国市场行情的变化都不是十分了解,特别是外商对华商的期票交易方式更加缺乏信任。在这样的条件下,以信誉著称的中国钱庄,向他们提供了庄票并以此作为信用工具。由于钱庄在中国商人中具有良好的信誉,而且对庄票的发行采取谨慎的态度,因而中国商人与外商在贸易中大量使用和接收钱庄发出的票据。随着中外贸易的进一步展开,钱庄自身制度的革新,引进近代的汇划制度,使它在中外贸易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上海“钱庄在1890年设立汇划总会,开始以公单方式计数,进行清算,事实上就是票据交换所的雏形”。(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3、14-15、496、496页。)这种方式不仅在上海汇划钱庄之间广泛进行,而且还出现钱业汇划总会接受其他非汇划钱庄甚至外资银行委托的代理清算现象,使得洋行开出的支票和华商手持的庄票能够很方便地在外商银行轧低冲销,大大简化了手续,有利于商品贸易。
钱庄为洋行开拓中国内地市场同样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在中外贸易发展过程中,货币金融业发展的程度与商品交易的广度、深度密切相关。只有在货币金融信用有力的支持下,进出口商品贸易才能有效、快速地展开,商品成交额和流通范围也会随之增加和扩大。而中国传统金融组织钱庄在商品流通中早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条件下,外商只有通过钱庄的力量才能开拓内地市场。在金融活动中,钱庄的作用就突出地表现着为进出口商人给予信用便利,以助于它深入内地推销洋货和搜罗生产原料。外商或洋行的买办深入内地搜集生产原料时,携带钱庄发行的庄票可以大大方便自己的活动。以镇江为例,1876年《英国领事报告》有这样的记载,“上海洋行把鸦片和匹头运给镇江的外商,并指望他们付款。镇江的外商按照买办自己认为能够销售的数量,尽快地把货物交给买办”;“如果买办不能在约定的时间付款,他就用目前暂时毋需付款的货物到钱庄去押借款项来支付”。(注: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第33、68、80、51页。)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洋行进行进出口贸易时,在资金方面钱庄也给洋行提供支持。在洋行进入中国的初期,由于资本较小,实力较弱,它们往往通过钱庄筹集资金,保证其贸易能够顺利展开。当时,“实力较差并和中国钱庄共同经营业务的洋行,情愿向中国钱庄借钱或由他们担保向其他中国商人借钱。中国的钱庄也放款给那些在伦敦并无分支机构或同各英—印银行缺少信贷关系的洋行,使之能够购买鸦片和支付大英轮船公司的运费”。(注:[英]勒费窝著,陈曾年、乐嘉书译《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华活动概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46、46页。)当然,这种现象只有在洋行刚进入中国社会时才可能出现。随着洋行实力的壮大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钱庄的金融霸主地位受到动摇,这种现象发生了戏剧化地倒转,不是洋行对钱庄的依赖,而是钱庄依赖洋行。
其次,钱庄与洋行在金融、商业上的合作,也使钱庄受益,并使之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钱庄最初设立时,资本还相当薄弱,规模并不大,它主要经营货币的兑换。而到1843年上海开埠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出口交易渐繁,金融流通的需要日增,于是钱庄营业逐渐发达;存款放款事项,亦较前繁多。如是年复一年,营业遂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拥资产者,皆知钱庄利益稳厚,竞相合股,纷纷组织。所以当时在南北市设立的钱庄极多”。(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3、14-15、496、496页。)可见,对外贸易的繁荣为钱庄的发展和繁荣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钱庄在同外资的互动过程中,其资本力量由弱到强地向前发展。但是有关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相对缺乏,没有留下直接的记载,我们只能从某一侧面来了解。例如,从上海各行业在19世纪60年代后近20年的时间内对公益事业的支助状况,可以探索出其中的奥秘。上海南北市钱业在同仁辅元堂的捐款由1867年的254千文增加到1882年的840千文,而60年代前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商船业由1867年的1526千文减少到1882年的487千文。(注: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第33、68、80、51页。)从这个剧烈的变化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不断入侵,钱庄也从其经济侵略中得到余惠,自身的力量也有所增长。
第三,钱庄与洋行双方人员相互渗透,加深了钱庄与洋行的合作。钱庄的老板和职员成为洋行的买办;同时,洋行的买办又投资钱庄成为钱庄的老板或股东。随着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钱庄与洋行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洋行买办开设钱庄,有力地支持了洋行商业贸易的展开,也为洋行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根据买办徐润的回忆,1859年他在宝顺洋行任职时,便已和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以支持他所经营的‘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注: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第33、68、80、51页。)其他的买办也有相同的情况,大买办唐廷枢担任买办后同样投资过钱庄。
当然,买办投资于钱庄,大多是被钱庄带来的巨额利润所吸引,同时也是为了自己所代理的商业贸易能够顺利地展开。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买办投资于钱庄业,客观上加深了洋行与钱庄的联系,支持了洋行、钱庄的发展。同时,洋行为了自身的发展,雇佣钱庄老板或职员作为自己的买办。上海泰记钱庄的老板杨坊后来就成了一个大买办;19世纪50年代“上海李百里洋行(Shaw,Beand & Co.)的买办,同时也是当时协丰钱庄(Ya-Foong Bank)的大股东”。(注:《华北捷报》1860年3月31日,第51页,转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第53页。)在这种情况下,洋行为钱庄提供商业上的便利既是可能的也是相当方便的。洋行通过钱庄把它们与华商的关系联系得更为紧密。
三、冲突和斗争:钱庄与洋行互动关系的一种常态
钱庄毕竟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一旦钱庄不能适应洋行发展的需要,或者有一种更现代的金融组织出现,两者间的冲突将会相当激烈,它们的合作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完全破裂。另外,洋行也有自身的经济利益,作为外国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它们为了尽可能地扩大其侵略利益的目的,不可能完全照顾、考虑到中国钱庄的利益,由于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它们与钱庄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首先,两者在金融业务上既竞争又冲突。鸦片战争后,那些在通商口岸的大洋行,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也是外国资本在中国金融活动中的急先锋。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它们一直掌握着国际汇兑业务,就是外资银行在五六十年代也无法与之竞争,更不用说中国钱庄了。这些大洋行不仅掌握着国际汇兑业务,而且还在中国进行商业放贷活动,并向清政府贷款以牟取厚利,“怡和洋行在1848年以‘略低于中国钱庄通行的’利率,贷给上海广东商人的金额达37万元”。(注:[英]勒费窝著,陈曾年、乐嘉书译《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华活动概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46、46页。)这些活动的展开,难免与钱庄的金融放贷展开竞争,至少可以肯定洋行的这些活动分流了钱庄的客户,抢占了钱庄的市场。
另外,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行逐渐从直接的金融活动领域退出,有的则把自己转为银行的股东。这些外资银行与洋行合作在金融风潮中一再打击钱庄牟取暴利。19世纪60年代,汉口金融市场上外国侵略者的疯狂投机活动,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这样一来,发生金融风潮的风险显得越来越大,而金融力量相对薄弱,在投机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或下风的中国钱庄,则是金融风潮的最大受害者。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多大变化,金融风潮依然频繁发生,外国金融资本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行市场投机,引发金融风潮,沉重地打击了中国金融业。
商业发达与否,同金融业繁荣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商业活动的展开与发展,都无法完全抛开金融业的支持,如果谁能垄断或控制了金融业,则当地商业的展开必须与其发生联系,它势必能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在各通商口岸,洋行不会甘心钱庄对金融业的垄断,洋行依靠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特权,通过种种手段打压中国钱庄,打破钱庄的金融垄断地位就已说明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洋行与钱庄为争夺金融垄断权的斗争必然会十分激烈。
其次,钱庄在维护自身经营自主权上与洋行发生矛盾。在钱庄与洋行的冲突中,钱庄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团结一致抵制洋行的不合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身的合理权利。在它们的冲突中,钱庄为了维护自身的金融信誉与洋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上海钱庄业中,长期保持着“认票不认人”的原则,但洋行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试图单方面破坏这一条规定,以至在1873年发生了顺发洋行止付票款事件。当时,顺发洋行存于买办的远期庄票被买办盗用,“持票人两人已向原出票庄照过,而顺发请止付。此事闻于会审衙门,判由顺发与两持票人各负捐失照三股分派。后闻道宪亦照会诸领事馆,欲将银票互交例议妥,以免日后有异言,而市面各钱庄皆为之不平,不肯开市再行出票,报论亦以破坏贸易常规为非是”。(注:《申报》1874年2月25日,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21页。)因为顺发案,上海钱庄停止发行庄票,直到1874年3月6日得到“西商公所议复仍照钱业旧制”(注:《申报》1874年3月7日,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22页。)的承诺才恢复出票。
钱庄在维护自身金融自主权方面也与洋行发生了利益冲突。洋行在中外贸易中一方面利用钱庄发行的庄票来加快和推广其在华贸易活动;另一方面又因钱庄实行的汇划制度和远期庄票的存在,在经济活动中深感不便,从而企图破坏钱庄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个惯例。1900年上海钱庄创立了庄票的“汇划”制度,规定“到期庄票,如遇钱业自行来收,即可当日解付同行之银,互相汇划;如遇洋银行来收,须解现钱,故再迟一天”。(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3、14-15、496、496页。)这项规定招致洋商银行和外商商会的强烈不满,他们邀请“前董袁聊清先生与谢纶辉先生出席与议”,而钱业领袖“袁、谢谓钱业议定章程,外人不得干预,其庄票收授与否,权操于洋商”。在钱庄据理力争的条件下,最后洋商不得不“照常收用”。(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3、14-15、496、496页。)洋行与钱庄关于汇划制度的争议并不仅仅只有这一次,在1903年外商又因反对庄票隔日付现,又与钱庄发生了冲突。1910年外国银行对中国钱庄发难,有“华商对此举反对甚力,竟有倡议凡不收10日期庄票之洋行,概不与之交易者”。(注:《申报》1910年8月23日,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549页。)总的看来,特别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钱庄与洋行的冲突日益增多,尽管这种冲突的形式主要是外商银行、洋行与中国钱庄之间、中国商人之间的矛盾,但实质上却是外国商人对钱庄在金融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的一种挑战,是一种经济利益的激烈争夺。虽然钱庄为洋行在中国倾销商品、资本输出提供了极大方便,但随着利益冲突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洋行势力的发展壮大,外国银行逐步进入了中国金融市场,洋行和外国银行为了同钱庄争夺金融控制权,使钱庄为它们的经济侵略服务,它们必须调整关系。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然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传统的工商行业,在外国资本主义疯狂入侵的条件下,往往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一种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打压下走向衰落,甚至退出历史舞台,曾经风光一时的票号就可以算一个例子;另一种则是在其排挤和打压下转变自己的职能,以图发展。汪敬虞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从入侵者这一方面而言,它对入侵道路上的障碍,固然要加以打击,但对能为它所用,受其操纵指使,以收更大的掠夺实效者,也不排斥对它们的扶植和利用。而无论打击、排挤和扶植、利用,它的目的都是要使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适应它的侵略需要。”(注: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7、477页。)可见,在钱庄与洋行的互动关系中,它们是既融合又冲突的对立统一。洋行与钱庄的冲突正是为了改造钱庄,排除其中不能适应甚至阻碍的因素;而两者之间相融合,恰好是钱庄自身经过改造能够适应洋行发展的需要;否则,钱庄也会和票号一样退出历史舞台。
总而言之,晚清钱庄与洋行的关系是既相互融合而又相互排斥。具体来说,在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它们两者以融合为主,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表现为排斥性越来越大,两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钱庄与洋行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转轨中的冲突和融合,从层次上讲,它们的互动关系体现为一种升级的状态;从内容上讲,它们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剧烈地放大;从社会影响上讲,它们的互动对社会变迁的作用越来越深刻。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钱庄和洋行的冲突与融合,是新旧冲突在经济领域里的突出反映,是衡量社会新陈代谢进程与程度的一把标尺。在社会激剧变迁中,新的依托旧的,旧的紧拉着新的,彼此联系,难舍难分,尽管新的充满生机,但却要蹒跚前进。尽管起初它们会以合作共处、相互促进的方式开展经济活动,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相互排斥、相互斗争,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在排斥、斗争中不能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就必定被淘汰。只有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变化,才可能生存、进化。这就是晚清社会转轨中钱庄与洋行互动关系的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