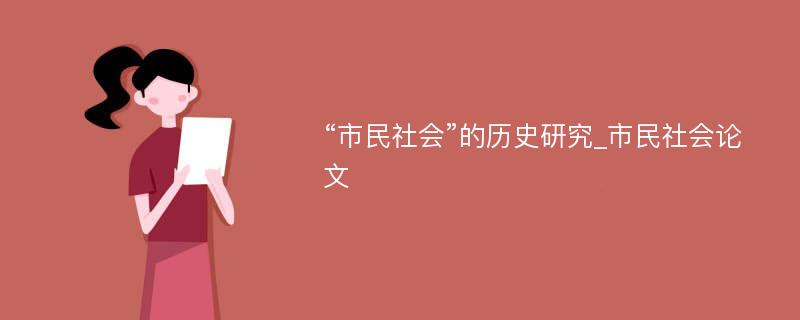
“市民社会”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民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是一个地道的西方式概念, 它在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指称与含义,因而对“市民社会”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作出厘清显得尤为必要。
一、在古希腊,城邦国家就是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最早大概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在《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使用了“Poltike Kornonia”(政治社会或政治共同体)的概念(注: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这一概念后来由西塞罗转译为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注:在拉丁文中,societas一词指协会、结社、结盟的意义,而civilis一词的含义则较复杂。首先, 它指市民的或城民的;其次它代表了一种法律和社会至上的思想;其三, civilis在拉丁文中还有重要的经济含义,它可以指私人权利;最后,它还是一个与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相关的术语。),一般指和野蛮社会相区别的文明社会。而现代英语和现代法语中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Societe Civile)一词便是由这个拉丁文词目演化而成。因此从词源学的角度有理由认为“市民社会”最初的含义乃指“政治共同体”。“Politike Kornonia”作为政治共同体讲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方面, 因为Politike是由“Polis”(城堡)一词转义而来,所以亚氏指称的市民社会或政治共同体乃指古希腊时期特有的城邦国家。城邦国家政治体制最具特色的是城邦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Polites),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 而不是以代议制的形式出现(注:关于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更详细的论述请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商务印书馆。)。但正如顾准所分析的,“直接民主制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才有可能。”(注: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第73页。)因而随着古希腊城邦国家的逐一衰落,亚氏的市民社会概念到古罗马时期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实体,不过市民社会“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注: Jean L Cohen,Andrew Arato,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Press of M.I.T,1992,pp84.)这一层含义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并成为市民社会在政治上自由、民主、平等的一种历史性的理论资源。托马斯·阿奎那、洛克等人不止一次地在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上溯到亚里士多德,这都反映了亚氏市民社会概念在政治学意义上的重要性。
二、中世纪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为市民社会的产生作了准备
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产生并非无因而起。实际上,所谓“黑暗时期”(dark age)的中世纪在政治与经济上为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产生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其一是政治上出现了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的有限分离。
随着罗马帝国的成形,共和体制的式微,人们逐渐认识到自己并非生活在一个理想的“政治结合”中;相反,人们日益感到是被“权力组织”统治着。这些观点,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对古典时代“政治共同体”的民主观构成了一种反动。
基督教(特别是早期的基督教)因为具有强烈的末世论(注:“末世论”是基督教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上帝会突然结束世界和历史,并在当日进行末日审判。详细讨论见布尔特曼等《生存神学与末世论》,三联书店,1996年版。)期待与平民意识,其反贵族政治的倾向相当浓厚。从这种心态出发,基督教一反古典时期推崇政治生活的倾向,拒绝赋予国家以道德上的价值认可,反而明确认定国家乃是一种压迫性的权力组织。作为对压迫性的抗衡,教会开始以神权为基础将自身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这就从客观上确立了这样的思想:社会并非完全根据其政治组织与特性来界定,从而表明社会成员同样可以被组合进另一个世界——教会世界中去,于是一种以权力抗衡权力的观点便出现了,这种观点对后期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教会当然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但教会组织成员的复杂性、广泛性、平民性却同旧日的政治社会有着明确的界线,因而在以政治领袖为权威的国家之外,一个隐性的社会组织开始出现,虽然这个社会还依附在神权的硬壳之中。
其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封建体制内部孕育了一批和新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市民”(bourgeois)。
大约从公元10至11世纪开始,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堡周围聚集了许多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向城堡的主人贩卖各种运自远方的物品和提供各种特殊服务,这样便在城堡之外形成了许多特定的商业郊区(suburbjum),出于安全考虑,这些地区又被围了起来, 便形成了新城堡(novur burgus),即外堡。居住在外堡的居民被称为“市民”(bourgeois,burgenses,Burger),这些人结成的共同体被称为communio或civitatis(注: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第44—45页。)。市民社会一词中civil便是由civitatis转义而成,英文中的commune(社团,共同体)则是由communio衍化而来。 Communio/civitatis是一个典型的自治城市,它是一个由商人、匠人、自由民、学徒、律师等在封建秩序的汪洋大海中以某些城堡或教堂为中心结成的工商业“特区”。在这个工商业特区中,商品经济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成了联结成员之间的纽带,而且随着这个社会的发育,一整套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化社会制度开始形成,具体体现为城市宪章(charters)、商人法(law merchant)以及行会制度(guild)的逐步确立。
在传统体制内部孕育的这两大新型基因,在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形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两大传统。
三、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认为市民社会是外在于国家的社会组织,政治自由是市民社会的主旨
中世纪为市民社会所做的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到了近代,被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发挥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洛克进一步区分了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概念,并将两者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传统观点认为社会组织应该由政治组织来予以领导,国家权力对社会而言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洛克并不这样认为。他的讨论是从人类史前所谓的“自然状态”开始的。他认为,人类建构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自然状态的不足,因为自然状态虽然平和、宁静,但缺少明确的法律,缺少按既定法律来裁决一切的公允的裁判,而且还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裁决,因而组建国家的目的就是构建立法、执法、权力这三重因素。但他又指出,构建这三重因素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弥补自然状态的不足,题中之义就是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只是社会组织自发建构并用来处理其内部事务的一个外在性的工具。这样,不仅社会与国家的界限得到了明确,两者的关系也被颠倒了过来。政治社会的权力不再来自神授,相反它只是来自民意。内在逻辑便是,如果国家不能代表民意,社会便有理由推翻国家。于是洛克便提出了社会先于、高于国家而存在的观点。这一观点开创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先河。
后继的孟德斯鸠则承袭了中世纪发展出来的以权力制衡权力的观点,并将其发展为三权分立的模式。孟德斯鸠不像洛克那样激进,他关注的重心不是政府在形式上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而是这个政府是否不被监督而转向专制主义。他认为国家是法律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市民社会则是捍卫法律的实体,而社会与国家又同时被归入宪法之内。国家与社会在立法、执法、行政权力中得以各司其职、相互监督是他的主旨。
无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内部有多少区别, 通过自然法(naturelaw)的基本精神来捍卫社会的自由、民主、人权是他们的共同旨趣。 他们一般都将社会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同义词使用, 而且这个社会一般指社会的政治活动,因而他们的市民社会理论更多的是确立了市民社会的政治传统。
四、黑格尔与马克思: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才是市民社会的本质
虽然洛克有不少关于财产权利的论述,卢梭浪漫型的自由主义也不乏对市民社会经济活动的说明,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更多的是透过政治来谈经济,因而对市民社会经济本性的透彻论述是从黑格尔才开始的。正如M.Riedel指出的,透过市民社会这一术语,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研究的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注:M.Riedel,The Concept of‘Civil Society and the Problem of its Historical Origin,in Z.A.Peleynski,ed.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pp3—4。)。这种转移是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这即是说,市场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成熟,都是促进黑格尔从经济的角度去考察市民社会的原因。黑格尔自己就曾说过:“我们没有两个不同的字眼来代表bourgeois(市民)和citoyen(公民)。”(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很明显,在他看来,同一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和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从本质上讲是有很大差别的。
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集中在其晚年著作《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而“法哲学”,“作为客观精神哲学只是对逻辑学的应用与补充。”(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因而对他的市民社会概念的背景理解之一就是对他的逻辑学中的“三一式”范畴的理解。
我们可以用下图来研究“市民社会”在其哲学大厦中的地位。
三一式范畴 正题 反题合题
存在 本质概念
逻辑学 个别 特殊普遍
感性 知性理性
家庭市民社会 国家
法哲学 直接的伦理精神 特殊的伦理精神 完成了的伦理精神
血缘关系 私人利益统一的归宿
很明显,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中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个分化了的特殊性的伦理范畴。它仅是一个反题,对于合题——国家而言,它只是一个知性(understanding)所了解的国家, 或外部的(external)国家(注:C.B.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46—70.)。作为私人利益而言,它是对血缘关系的否定,但是这种私人利益最终应该整合于国家之中。
为什么这样讲?还是让我们直接从其关于“市民社会”的具体论述中寻找答案。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各个社会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是在抽象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基于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和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既然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联合体,因此它是对家庭这样的血缘共同体的否定。这种否定,使得市民社会具有了一种普遍性(university)。但是由于独立个人之间缺乏必然的关联,有的只是外在的工具性的契约与利益关联,因而这种普遍性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市民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联还只是一个抽象的联结。这种关联性,黑格尔认为,它必将导致自然必然性与任性(caprice)。因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所具有的只是自然的意志,即以欲望和需求为基础的意志,同时这种意志之间只是以自然必然性为联结的纽带,而非自在自为的联结,所以黑格尔称市民社会是一个“私人需要的体系”,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所谓“私人需要的体系”,按时下的术语讲就是一个“全盘的市场社会”(full market society), 而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则是“占有性的个人主义者”(possessiveindividualist)(注:C.B.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46—70.)。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待价而沽,所有的自然成分(亲情、爱情、宗法关系)都被一并铲除。
很明显,对于这样一个以“自然必然性与任性”来联结的社会,如果没有外部强制性力量的整合,其瓦解是必然的。所以黑格尔进而指出,在这个抽象的普遍体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仍然是相互依赖的,所有成员之间的关联性是彼此如何满足别人欲望与需求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单个人的自利动机被“看不见的手”联结了起来,并由此达成了互相认可的公共契约(市场原则),这些契约便成了维持市场社会同一性的最后依据。
但是,黑格尔又认为,市民社会无法实施这一组公共契约,原因很简单,市民社会的经济本性中的一个内在特征就是“异化”(alienation),这种异化导致追求私利的特殊性本身是没有节制的,这样会最终导致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完全不同意洛克、卢梭或亚当·斯密所说的由普遍的自利动机形成的“看不见的手”最终可以导致公益与道德固有的合理性。相反,他认为在市民社会中道德沦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伦理精神在市民社会内部还只是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所以表现在伦理原则上的不自足性是不可以由自身来挽救的,只有依赖一个具体的普遍性原则的体现者——国家,才能救济这种异化状态。因为国家乃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它代表并反映普遍利益,因此只有国家才能有效救济市民社会的非正义缺陷,并将其所代表的特殊利益融合进一个代表着普遍利益的政治共同体中。
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并指出它在道德上的重大缺陷,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以为要由国家来纠正市民社会道德上的不自足性,也有合理之处;但在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上他却颠倒了。在他看来,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相反——国家高于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正如他所言:“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经济学中去寻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2页。)
这里需要首先澄清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究竟指的是什么?理论界长期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一提到市民社会就好像是专指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至少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马克思所指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应该有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的含义。从广义上讲,市民社会指的是商品经济的经济关系;从狭义上讲,它才特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同人类社会的特定发展时期相联系的,是以特殊的私人利益与普遍的公共利益的分离和对立作为自己的存在形式。正是这种分离促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产生和独立存在。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主要指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页。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可见, 只要存在着商品经济与私人利益,市民社会就一定存在,这就是广义上的市民社会。
但马克思又指出,私人利益与商品经济的出现在现实中并不必然表现出市民社会可以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比如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虽然也存在着商品经济,但市民社会还没有能够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而不独立的市民社会,在他看来,还只是市民社会的前身。因此马克思经常使用“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9页。)、 “中世纪的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86页。)、 “行会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4页。)来区别于后期的市民社会。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最终通过政治革命将市民社会和国家在现实中分离开了。法国大革命是这种政治革命的典型代表。“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因而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Solche B 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只是随同资产阶级(Bourgeoisie)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页。)这个真正的市民社会,就是所谓的“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6页。), “发达的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7页。)。 这样的市民社会,就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将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一般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特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民社会作出区分是有一定用意的。这种区分主要是针对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和斯密在内,将整个人类社会看成是市民社会的错误而言的。比如他说:“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看来,除了市民社会形式之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7页。 )不过,这种区分并不妨碍马克思在许多场合也从一般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一词。这段讨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只要存在着商品经济,市民社会就有了存在的基础;而只要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市民社会就有了将自己和国家分离开来的内部要求与外部环境。因而,市民社会的讨论和商品经济有着天然的关联。
对市民社会的概念作出这样的厘清之后,再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独特的历史贡献。这个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将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重新颠倒了过来。
虽然马克思也和黑格尔一样首先确立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但他却没有将这二者看成是永久的对立面,更没有试图用“绝对理念”来统摄一切。相反,马克思看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若干联系。
首先,马克思找到了市民与公民的真正关系。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是具有自我利益的人,现实的人;而作为政治国家成员的公民只是抽象的人,“寓言的人”。因此两者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后者无法离开前者而存在。简言之,“不是身为citoyen (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一分子)的人,才是本来的人, 真正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0页。)
其次,他指出,只有作为市民社会一分子的个人才是政治国家的自然基础。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成员的物质生产活动才是政治国家的全部活动和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因而从实质上讲,市民社会就是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社会的经济基础。
最后,他指出,对于社会形态的更替而言,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原动力。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来说是内容,而政治国家则是该时期市民社会的形式。因此恩格斯也说:“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35页。)
总之,马克思以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为起点系统地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并进而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与代表私人经济利益的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历史范畴。在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市民社会终于得以从政治国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在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其本质也显露无遗。随着阶级的消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也将消失,彼时,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市民社会也不复存在。
五、当代西方的研究视角:市民社会主要指文化共同体
本世纪以来,市民社会的讨论形成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由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发起。第二次是在80年代末, 以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柯亨、阿拉托等人为代表,形成了一套新的市民社会理论。
像马克思一样,葛兰西也将社会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部分。前者指国家或政治,后者指各种私人组织或民间社团。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将“市民社会”看成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能够被称为‘市民社会’……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注:葛兰西:《狱中札记》,四川人民出版社。)。这种区分标志着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个新的转向,即从经济领域的讨论转向了文化领域。
葛兰西之所以将市民社会不再看成是经济基础,而是将它看成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在当代西方,国家的的统治已经不仅仅是靠军队和暴力来维持,相反,它主要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文化渗透来取得其合法性地位的,因而国家与市民社会交锋的领域也相应地从经济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所以他认为市民社会和国家争夺的不再是经济自由权,而是所谓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因此葛兰西开了市民社会文化讨论的先河。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乃是指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它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其中私域(privacy sphere)指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公域(public sphere )则是指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私人有机体,它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沙龙、报纸书籍等。公共领域实际上就是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它为人们提供了讨论和争论各种公共利益的场所和讲坛(注:方朝晖:《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学说》,《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8月号。)。
由这个定义出发,他指出,对市民社会的私域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子系统已经受到了政府的大规模干预。由于这种干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得到了控制,经济危机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危机。相反,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主要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所谓合法性危机,主要是指在公域内人们日益远离政治讨论和政治事务,政治子系统日益失去其合法性基础而出现的危机。
他进而指出,导致这种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生活世界的“动机危机”。由于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子系统已经和国家耦合,因而以“文化、社会和人格”为基本要素的生活世界,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内容。但是,生活世界由于受到权力与金钱的渗透与控制,因而表现出作为文化解释性范式功能的弱化,大众失去了阐明社会生活意义与价值的文化背景,遂表现出以孤独、冷漠为特征的“动机危机”。简言之,即由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而引发的国家合法性危机(注: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总之,在哈贝马斯看来,市民社会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系统,这个系统的再生产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柯亨与阿拉托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由生活世界的机构或制度组成的。具体来说,它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由私人的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的领域(特别是自愿性的团体)、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注:Jean L.Cohen and Andrew Arato,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The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The MIT Press,1992, pp9.),其功能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含有经济与政治因素在内的广义的文化再生产功能。所以,他们主张采用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三分法。这种三分法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以国家为中心或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主张返回到以社会文化系统为中心的范式中去,通过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重建,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团结、公正的现代乌托邦理想。
六、小结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社会历史和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因此历史上的思想家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存在着种种差异。古典时代的思想家主要从文明社会的角度去界定市民社会,因而它一般指业已出现城市(城邦)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古典时代的这一思想以及中世纪对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的区分在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他们主要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及其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因而一般将市民社会看成是外在于国家的政治实体。黑格尔和马克思则开创了以经济特性研究市民社会的传统,他们主要是从私人的经济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及其政治与文化活动,因而他们倾向于将市民社会看成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社会组织。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文化矛盾的不断加深,现代西方思想家则主要是通过文化来界定市民社会及其经济、政治活动,因而他们的市民社会一般指称的是文化共同体。
尽管各派的看法存在着诸多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同点与契合点。综合多种观点,我们有理由将市民社会作如下定义:
市民社会是与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具有的明晰的私人产权及其利益并以契约关系相联结的,具有民主精神、法制意识和个体性、世俗性、多元性等文化品格的人群共同体。
从这个定义可知:
(1)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非商品经济不可能形成市民社会,因而只要有商品经济,市民社会就有存在的客观基础,区别只是在于发达程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市场经济,必定要建构市民社会,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
(2)市民社会的存在必须要有明晰的私人产权, 因此市民社会不包括公有制经济,市民社会只是与非公有制相联系的人群共同体。
(3)市民社会是一个契约型社会, 即社会成员的联结是以商品契约为纽带,而不是以血缘、地缘、宗教感情、道德观念为纽带的联合体。
(4)因为与商品经济相联系, 市民社会在价值层面上有整套与之相关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的要求。这些要求既区别于封建价值观念,在实现形式与手段上又区别于公有制的价值观。
(5)市民社会自身分立为公域与私域两个部分。在公域内, 它形成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或组织;在私域内,它遵循市场的基本规则进行私人性的生产、交换与分配活动。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法哲学原理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政治学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哲学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