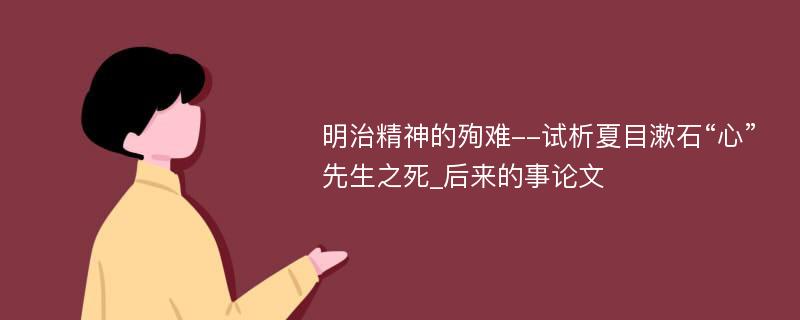
为“明治精神”而殉——夏目漱石《心》中“先生”之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之死论文,精神论文,夏目漱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夏目漱石后期“三部曲”的殿军之作《心》中,叙述者“我”与主人公“先生”是在海边纷攘的人群中首次相遇的,那时“先生”正陪着一位外国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后来,“先生”在与“我”闲聊时也不禁说道:“奇怪的是自己连同日本人也不大来往,却交上了这样一个外国人。”①
这真是个奇怪的开场,因为随着“我”与“先生”交往的深入,我发现“先生”并不喜欢出门,也少有应酬,过着与世无涉的寂寞生活。“他的学问和思想,除了同他关系密切的我之外,是不会有人知道从而对他深怀敬意的。我常常说这很可惜。先生并不以为然,只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到社会上讲话是办不到的。’”“先生”还曾语气深沉地说自己是个“没有资格为社会服务的人”(123-124),这些话让崇拜“先生”的“我”听后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
“先生”遁世和自弃的理由在他最后留给“我”的遗书中似乎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因为自幼被亲叔叔骗走遗产,“先生”痛彻地感到人不可信赖,并真心相信人性为恶,但他心中仍认为:“不管世人如何,我本人是高尚的。”可是,当“先生”发现自己与好友K同时爱上房东家的小姐时,竟不惜采用欺骗手法把K逼走,致使本来精神就高度紧张的K自杀身亡,这击碎了“先生”对自己的信念,如遗书中所言:“当我意识到,因为K,这种信念已毁之殆尽,自己也不过是个同叔叔一样的人时,我突然惶惶然了。一向厌恶别人的我,也终于厌恶起自己,动弹不得了。”(273)
因为厌恶社会,也厌恶自己,“先生”渐渐与周遭世界断了联系,与妻子静(即当年房东家小姐)一起靠旧日积蓄,过着看似平淡的家居生活,只是每月他会只身到K的墓前深深忏悔一番。然而,这近乎死水一潭的沉寂日子最终还是被打破了,当“先生”默默安置好妻子未来的生计,并给“我”写了封表白心意的长信后,他选择了自杀,而这样做的直接动因竟是:明治天皇的逝世。
虽说“先生”一直备感愧疚和绝望,但他于妻依然怀着爱与眷念,于“我”也还抱有希望,况且几十年来“先生”不问世事地活着,为何会因天皇逝世以及随后发生的乃木希典夫妇殉死事件而激动起来,竟决定以同样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在“先生”遗书的最末处,有一段令人大惑难解的话:“明治精神始于天皇,也终于天皇。受了明治精神影响最深的我们,就是以后活下去,也毕竟是不合时宜的。”(277)“明治精神”在此被颇为突兀地提了出来,而一直到整个故事随着“先生”之死戛然而止时,这一精神也没有得到任何详细解释。
漱石后期的作品渐少涉及社会具体事件,特别是小说《心》,如果不计人名、地点,这个故事可以移到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不过,作者终是用天皇逝世的事件,将主人公从“普世性”的云朵上降了下来,让人隐约感到那些对抽象人性的批判与模糊的“明治精神”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1868年4月6日,天皇率众臣以向天地神明起誓的形式,发布了新政府的五条誓文,即“‘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文武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俾人心不怠’;‘破旧习,基于天地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②誓文虽短,却如暗夜一声霹雳震动整个日本,江户末期社会的消沉气氛终被打破,志士仁人无不欢欣鼓舞。誓文中所包含的开国、进取、求知、平权的观念让漱石十分兴奋,正是它们构成了所谓“明治精神”的核心,而年轻有为的天皇本人,则成为这精神在尘世间人格化的象征。
在这种精神激励下,维新之初的十几年里,新政府在国内迅速建立起统一高效的国家机器,积极推进各项社会改革事业;在国际上则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推行大陆政策,不断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亲眼看着祖国迅速崛起,跻身列强,日本各阶层人士大有扬眉吐气之感。漱石也不例外,甚至到了明治43年(1910),漱石对日本社会颇多批评时,其《满韩漫游》中仍不忘特别记下自己在大连大和宾馆中偶遇一位英国老人的经历,当对方确定他是日本人后,“马上就开始恭维说:我40年前到过横滨,日本人有礼貌,亲切热情,确实是模范国民”③。可以想见,这英国佬当年踏上日本的土地时是何等趾高气扬,现在之所以谦恭,不过是因为日本强大了。
伴随着胜利的喜悦,与漱石心境相似的知识分子对“明治精神”开始寄予更多、更高的期望。但是,正如现代日本史学家坂本太郎所说,由于日本的现代化是由一个落后国家在短期内迅速完成的,所以难免有许多不均衡和不合理的地方。④在精神领域中,明治时代的思想“以四十年时间重现西洋历史上经历了三百年的活动”⑤;而在现实生活中,“一切的东西都像在遭到破坏,同时,一切的东西又都像在建设起来,真是大起大落的变动”⑥。几经这样的毁建沉浮,漱石笔下三四郎式的兴奋与不安中渐渐生出越来越多的焦虑与苦恼。
满含焦虑与苦恼的不安首先来自政治变革的冲击。与漱石心中的“明治精神”相悖,维新运动的第一要务并非“公论”、“会议”,而是要迅速建立起绝对主义王权。这样做有一定历史合理性,因为尽管“绝对主义王权的自身本质仍然是封建性的,但对于近代国家的出现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⑦,“以世界上最早出现近代社会和近代国家的欧洲为例就可以看出,不可能从处于分散、割据阶段的封建国家直接向近代国家过渡”⑧。所以,仓皇间被卷入急剧社会转型的日本如果不能迅速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就无法收束新旧各种力量,更不能有效地应对西方列强一次次扣关之举。
紧迫时势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核心出现,“躬自率先誓于天地神明之前”的明治天皇自然而然被推上维新运动的神坛。虽说历代天皇在日本百姓心中都是神族后裔,可相对于作为幕府将军囚犯的旧时天皇,明治天皇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没有沦为维新势力的傀儡,而且在积极介入权力时能够保持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受具体政策失败之累。“圣君明主”作为阿谀之辞能够送给每一位天皇,可这一位在臣民心中倒是当真的。于是,在新时代的造神运动中,五条誓文中像“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这样具有平权性质的誓文,便被高高悬置起来。
集权一旦形成,即便形势不再紧迫,独裁集团也难于自我感化,放弃权柄。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更是极端,他们无不铁腕当国,专制开道,通过高压手段摧垮任何反对力量。特别是新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暴力机关,除了防范列强入侵和旧势力复辟外,“所特别防范的却是新觉醒的、战斗的自由主义精神,那种精神在当时大有将初发端的民主主义倾向强行推广并贯彻到底之势。初期的陆军、警察队和官僚机构差不多完全由以前的武士或封建主的家臣构成,因而(除少数例外)对于一切自由主义的表现都抱有敌对的情绪”⑨。
虽然明治初期的自由民权运动还沿着“五条誓文”的精神继续发展,并且“通过这一运动,以前属于士族专有的维新精神终于渗透到了民众之中”⑩,但由于运动的主力军是未能与官僚统治集团分享利益的小商业、小地主阶层,其“理论指导者是未能和萨摩、长州均分官职禄位的土佐、肥前两藩的士族”(11),因此,运动很快以和局(而非失败)告终,明治政府“把官营企业和半官半民企业低价卖给民间,同时在权力上‘自上而下地’产生大资产阶级,使之与地主一起成为支撑自己权力的基础,然后发布宪法,开设国会,改为新的统治体制(波拿巴主义)”(12)。明治22年(1889)2月,《帝国宪法》正式颁布,权力的天平明显偏向君权,而次年发布的《教育敕语》则进一步强化了君权的专制性,其中“规定天皇是干涉和决定国民的道德观和社会观并且具有政治和道德(即代替欧洲的宗教)双重大权的存在”(13)。学问和信教的自由,尽管附有法律范围内的限制条件,应该说是受到宪法保障,“然而自从教育敕语发布之后,这种自由反而受到威胁”(14)。至此,较为开化的政治变革之路被彻底堵死。
在这场专制主义的造神运动中,漱石的态度十分复杂。漱石12岁便作有《正成论》一文,其中写道:“凡臣之道在于不仕二君,心如铁石,以身殉国,救君于危机之中。”(15)30多年后,已过不惑的漱石所作汉诗中仍有“幸生天子国,愿作太平民”(16)的诗句。但两者之间却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儒家教育的惯性使然,而在集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明治中后期,漱石还能发自内心地拥护天皇统治,并非他与众人一般见识,视天皇为神灵下凡,而是因为在那时的漱石心中,天皇身上依旧承载着他对以“五条誓文”为核心的“明治精神”的最后期望。因此,虽然漱石对社会屡有激烈批评,但他总愿意将“天皇”与“当局”分开;尽管现实的变革越来越背离五条誓文的根本精神,漱石却对那精神的人格化代表痴心不改,一直幻想着天皇终会出来纠正当局的错误,使“明治精神”重放光辉。
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化,政治上的变革不可避免地触及精神领域,在漱石那样的知识分子心中激起更大的不安。明治42年(1909),日本政坛元老大隈重信总结日本开国50年经验时,写道:“我日本以忠君爱国为特性,以集义直养为元气,政法教学工艺机器资之于欧美,含英咀华,辅长补短。是故,虽舍己从人,我有者,自若也。”(17)然而,在“求知识于世界”的誓文鼓励下,放眼世界的漱石对这种“和魂洋才”的提法却非常反感。在《我是猫》中,漱石借主人公苦沙弥先生之口狠狠地讽刺道:“大和魂是三角的呢?大和魂是四角的呢?大和魂像字面所示,就是一种魂,唯其是魂,所以永远是飘飘渺渺的。”(18)
通过对西方文明的深入学习,“洋魂”伴着“洋才”也悄悄渗入漱石的灵魂深处。明治25年(1892),漱石在《哲学杂志》上发表《关于文坛平等主义代表者惠特曼的诗》一文,当年《正成论》中“君臣父子”的思想以及后来写《中学改良策》(1892)时对西洋思想相当警惕的态度在此文中几乎不见踪迹。到了大正三年(1914),漱石赴学习院辅仁会作《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谈及何为自由时,他又言道:“为了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尊重,而且得到社会的允许,那么,也要承认别人的个性,尊重他们的倾向。”(19)这种观点与当时流行于英国的自由观十分相似,密尔就认为:“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20)
然而对“洋魂”的接受却并不顺利,它搅乱了漱石的心绪,常令他寝食难安。自明治27年(1894)始,漱石“就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在9月的日记中他曾记载自己觉得‘脑浆都在沸腾’”(21)。直到数年后,这种内心矛盾才趋平静,“洋魂”在漱石心中终于有了一席之地,而经过这番心灵磨折,“明治精神”的内涵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虽然这精神仍以“五条誓文”为核心,但他对它们的理解,已经不能完全放在旧传统的平台上进行了。这使得漱石及与他经历相似的知识分子在外在环境日趋恶劣之时,反而对“明治精神”寄予更多不切实际的期待。
但现实却是惨烈的。明治43年五月爆发了震惊日本的“大逆事件”,除四位暗杀天皇的策划者外,“与此事件毫无关系的幸德秋水等全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在同年六月受到搜捕。因是政府捏造的口实,所以审判是在极秘密中匆忙进行的,明治44年1月18日幸德等24人被宣判死刑,第二天其中的12人减为无期徒刑”(22)。对于此案,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感到愤懑难当,“石川啄木感叹那是个‘闭塞的时代’,永井荷风也在日记中写着,当他目睹大逆事件牺牲者的座车经过时,自己已不再是文学家了,只想玩弄文字偷生度日”(23)。然而漱石却表现得异常冷漠,之后作品也几乎和现实断了联系。但就在此事件前一年出版的小说《后来的事》中,漱石似有预感地特意安排不问世事的主人公代助阅读俄罗斯作家安德烈夫的小说《七个被绞死的人》,最后的行刑场面令代助不寒而栗,觉得“被逼着去死是极为残酷的事”(24)。如今,极为残酷的事就发生在身边,“明治精神”中那刚刚萌芽的“洋魂”很快就在凛冽的气候中枯萎了。
政治变革最终冲击到精神文化的最深处:言文之境。明治初年,激进的知识分子如前岛密、福泽谕吉和森有礼已提出削减汉字甚至废除汉字或干脆将日本公用语调整为简易英语的主张。之后,在二叶亭四迷、山田美妙以及自然主义派小说家和白桦派作家的努力下,用并未成形的“标准东京话语”来替换汉字文化的“言文一致”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场运动在柄谷行人看来,其“实质在于这里‘文’(汉字)的优越地位遭到了根本的颠覆,而且是在声音文字优越的思想指导下被颠覆的”。(25)
日本文化一千多年来一直是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氛围中生长的,本居宣长就曾指出:“日本人观察事物时已经到了只有通过汉文学的概念才能观察的程度,只是在《源氏物语》中还存在着自然地观察事物的视角。”(26)不过近代以来,中华帝国急剧衰落,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不仅在政治权力上,也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开始与中国断绝连带关系,因此,摆脱汉字文化圈,建立以本土的声音为中心的语言体系,不仅是一场文化运动,也是整个国家“脱亚入欧”的重要环节。
从漱石的小说《心》中,我们多少能感觉到这种转型所引发的巨大精神动荡。小说中K的身世简直与漱石一模一样,都是夹在不和的养父与生父之间,小小年纪就体会到强烈的无所归属感。其实,当时的“先生”以及同样夹在东西方之间的许多知识分子心中又何尝平静,“脱亚”并不容易,“入欧”更不简单,在新旧世界间,泛溢着何去何从的焦灼与烦恼。在现实中,年轻时的漱石也曾立志要通达英语,以之著文震惊西洋;对苦难的中国也生不出些许同情,反而“产生一种终于和残酷的中国人断绝了缘分的心情,不由得高兴起来”(27),可几经探索,漱石又不得不承认:“文学究竟是什么,除了基本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它的概念之外,没有救自己的道路。”(28)而这“自己的力量”,唯有从那浸透着浓浓汉意的自家传统中方能呼唤出来。
在大变动的时代里,漱石终是“无法割断那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对‘文’这个汉字文化圈的精神家园的依恋”,“这种依恋深深融入漱石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血液中,和另一方面希望国家强盛从而不得不接受西方文明的紧迫感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张力和精神断裂”(29)。到了明治45年(1912),漱石在病榻上仍不忘作几首汉诗,其中一首云:“大观天地趣,圆觉自然情。信手时挥洒,云烟笔底生。”(30)好一派佛道气象,仿佛作者还生活在江户时代,然而就在窗外,“言文一致”运动已经大获成功。看来,在漱石及其小说人物“先生”表面的平淡超脱之下,已经少了真正江户时代的从容不迫,就像湖上悠然的天鹅,在水下却不得不用力拨动着双掌。
更具颠覆性的不安姗姗来迟,那些如漱石般深受传统浸染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虽经一番心灵焦灼后或多或少地接纳了“洋魂”,但维新运动所要奔向的目标对他们来说仍然模糊不清。开始时当然是为了“强兵”,后来发现欲强兵,先得“富国”,可要富国,靠江户时期町人们小打小闹的那一套显然应付不来,于是政府牵头进行“殖产兴业”的工作,以使过去落后的产业迅速现代化、工业化。直到这时,从旧世界中走出的漱石那样的知识分子才意识到他们得面对一个新事物:资本主义!
伯曼在解释马克思用“魔法”一词形容资本主义社会释放生产力的能力时指出:在马克思诗性的描述中“也表达出了任何真正的惊奇感必然伴随的东西:一种恐惧感。因为这个令人惊叹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同时也是恶魔似的令人恐惧的,疯狂地不受控制的,前进时盲目地进行着威胁和破坏”(31)。面对着这个由钢铁机器构成的新世界,漱石同样体验到了恐惧。小说《三四郎》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刚到东京不久的三四郎目睹了一起火车轧人事故,貌似强壮的生命只在火车“轰隆”的一瞬间就粉碎了,事后当他向朋友讲述时,却吃惊地发现人们竟是那么平静与若无其事,话题很快转到其他琐事上。在这个渐渐被钢铁武装起来的都市里,生命宛若草木间的点点荧虫,显得毫不重要。
其实在漱石远渡重洋留学英伦期间,就已为伦敦人真实的生存状态悲叹连连:“散步伦敦街市,试一吐痰,吐出者为一漆黑团块,颇讶之。数百万市民呼吸此烟煤之尘埃,彼等肺脏日日受其污染。擤鼻吐痰时心绪甚恶。颇畏之。”(32)日本欲赶超的目标竟是这样,真是令人气馁。对西方文明的向往,是因为“洋魂”中那启蒙的光辉,可资本主义却与之大相径庭。好不容易接受了“洋魂”,真接触到实在的西方世界,又立即对它大大怀疑起来,这不能不使漱石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更为混乱、矛盾的境地。
痛苦还在加剧,像日本这种后起国家,为了追求速度,发展难免扭曲,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作为政府和商人资本的共同事业而实现的……首先,商人资本的积累成了初建立的明治政府的财政支柱,接着,在政府铺设了振兴实业政策的轨道以后,主要由政府的倡导来促进商人资本的发展”(33)。结果明治前期社会上出现了“政商”,后期则演变为“财阀”,“权力”和“钱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对此,明治时代的史论家山路爱山哀叹道:“世间不知何时又回复到旧时景象!过去,人们看到封建社会那种诸侯们领着持枪的侍卫挤满大道而横行阔步的情景便觉得很可笑,可是如今在他们的眼中,又映现出以黄金为城郭的新诸侯。现在,金钱的多少几乎是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唯一标准……如此下去,世界将逐渐变为财主的世界,政治家将逐渐变为财主的代理人。”(34)
这样一种社会令漱石分外厌恶,他无奈地看到,若想在其中活得好,就得奉行“三缺主义”,即“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35)。如上文所述,晚年的漱石曾到学习院辅仁会演讲,专门谈起密尔式的“自由”,不过密尔讲的“自由”是为限制“多数的暴虐”,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而漱石则是苦口婆心地劝导台下那些将会握有“权力”和“钱力”的“少数”今后要对“多数”宽容些。然而,这样的教育究竟有多大用呢?末了,在《心》中,漱石无可奈何地承认:“一见到钱,无论怎样的正人君子都会立刻变成坏人的。”(155)
在一个接一个不安的不断地冲击下,漱石那样的知识分子纷纷陷入从未有过的巨大心理危机中,对于国家的未来、个人独立、完满的精神世界,他们不再乐观,变得忧虑重重。三四郎式的那种充满朝气的冲动,在东京城里渐渐转化为K式的焦躁与紧张,然后,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人至而立、不惑,反而变得格外愤愤不平,就像漱石笔下的广田先生、苦沙弥先生、常井代助那样,对不公的世道猛烈地批评起来。
漱石35岁留学英国时,在日记里写下过这样的话:“据说日本是30年前觉醒了的。然则此乃闻警钟而急急跃起耳。此觉醒并非真觉醒,乃惊慌失措之举也,一味急于吸收西洋,以至于无暇消化矣。文学、政治、商业,无不皆然。若无真觉醒,日本无救矣。”(36)这种忧虑不但没有随着日后的改革减缓,反而与日俱增,在《后来的事》中,主人公代助十分激愤地骂道:“日本这个不向西方国家借钱就无法自立的国家,竟然要以一等大国自居,硬是要挤进一等大国中去。所以,它只好削足适履,限制各方面的深入发展,从面上铺开一等大国的规模。如此勉为其难的样子,更令人感到可悲,不啻是青蛙同牛逞强,你想想看,当然要撑破肚子啦。”(37)
可忧心忡忡的批判能够改变什么?最终代助不得不痛苦地承认:“骋目整个日本,能找到一寸见方的土地是沐浴在光明中的吗?真可谓暗无天日哪。我置身其间,一个人再怎么想有所作为,又何济于事呢?”(38)无奈的情绪越聚越浓,书里书外的人都发现自己不过是这乱糟糟社会中“多余的人”,除了消极避世,寻不到其他去处。于是,在《门》中,那对相依为命的夫妻宗助和阿米“日常除了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几乎不再意识到社会的存在……他们虽然住在城市,但却抱着寓居山野的心情”(39)。甚至当报纸上登出伊藤博文被刺的消息时,夫妻俩也只是淡淡地谈了几句,就把它放在了一边。
宗助和阿米虽然疏远人世,岑寂里夫妻二人还能够“紧紧抱合在一道,描绘出一个理想的圆来”(40)。可到了小说《心》里,“先生”连这点家庭的安慰也失去了,先是每天在酒精的麻醉中,后来又在书案边任书页翻转的茫然中,无力地排遣着自己的寂寞,便是爱妻也不能(也是不想让她)理解自己的痛苦。在遗书里,“先生”悲伤地叹道:“我非常孤独,常常觉得在这个处处隔绝的世界上,只住着我一个人。”(274)此时的“先生”已被逼到与K临死时一样“孑然一身,孤苦无依”的绝境。
在《心》的第二章“父母与我”中,当“我”乡下的父亲听到天皇逝世的消息后,精神立刻崩溃,病患之躯也随之垮掉,只因为普通农夫把天皇看成神,神且有死,和天皇同病者岂有活路。而在“先生”心中,真正重要的是附在明治天皇身上的那种“明治精神”,它承载着自己最为宝贵的希望与憧憬,只要明治天皇还活着,它们就有一线实现的可能,无论这希望多么渺茫。可明治天皇终是去了,“明治精神”亦随之而逝,再活着,对于“先生”而言已没了意义,于是,只剩下为“明治精神”殉死一途。
回到《心》中那个奇怪的开场,平日远离尘嚣的“先生”居然陪着位古怪的、他所不喜欢的外国人出现在海滨浴场纷攘的人群中,面对着一片阔大的蔚蓝色世界。这个场景似乎把明治时代的日本和“先生”那样特殊的知识分子都缩影其间:幕府两百多年闭关禁海的时代结束了,人们兴奋地拥向新天地,便是“先生”也不例外,实际上他比其他人更投入,也更了解众人所欲拥抱的世界。但在这嘈杂的人群里,“先生”却显得分外孤独,当明治的“太阳”落下时,沙滩上只留下他渐行渐远的身影,终于消失在黑暗中。
“先生”走了,漱石则继续在没了“明治精神”的世上苦苦探索着,他希望重新找到自我,并努力在“则天去私”的境界里攫取新的光明。然而,当《明暗》写到188回时,漱石却因胃溃疡复发而撒手人寰。旧的光明消失了,新的光明还没有找到,前途仍浸没在一片阴暗的雾霭之中……
注释:
①夏目漱石《哥儿·心》,胡毓文、董学昌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随文标注页码,不再另行做注。
②坂本太郎《日本史》,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62页。
③夏目漱石《满韩漫游》,王成译,选自《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4页。
④详见坂本太郎《日本史》,第405页。
⑤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⑥夏目漱石《三四郎》,第19页。
⑦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雷慧英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⑧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第103页。
⑨诺曼《日本维新史》,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0页。
⑩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27页。
(11)诺曼《日本维新史》,第173页。
(12)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第111页。
(13)远山茂树《日本近代史(第一卷)》,邹有恒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3页。
(14)远山茂树《日本近代史(第一卷)》,第93页。
(15)转引自张小玲《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16)夏目漱石《夏目漱石汉诗文集》,殷旭民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17)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序言”第5页。
(18)夏目漱石《我是猫》,尤炳圻、胡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19)夏目漱石《十夜之梦——夏目漱石随笔集》,李正伦、李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20)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4页。
(21)张小玲《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第138-139页。
(22)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林和生、李心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
(23)南博《日本人论》,邱琡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24)夏目漱石《后来的事》,吴树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43页。
(25)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41页。
(26)转引自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7页。
(27)夏目漱石《满韩漫游》,第240页。
(28)夏目漱石《十夜之梦——夏目漱石随笔集》,第121页。
(29)张小玲《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第22页。
(30)夏目漱石《夏目漱石汉诗文集》,第29页。
(31)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0页。
(32)夏目漱石《伦敦留学日记》,收入《梦十夜》,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7-258页。
(33)柴垣和夫《三井和三菱——日本资本主义与财阀》,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3页。
(34)柴垣和夫《三井和三菱——日本资本主义与财阀》,第77-78页。
(35)夏目漱石《我是猫》,第113页。
(36)夏目漱石《伦敦留学日记》,收入《梦中夜》,第279页。
(37)夏目漱石《后来的事》,第83页。
(38)夏目漱石《后来的事》,第84页。
(39)夏目漱石《门》,陈德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
(40)夏目漱石《门》,第1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