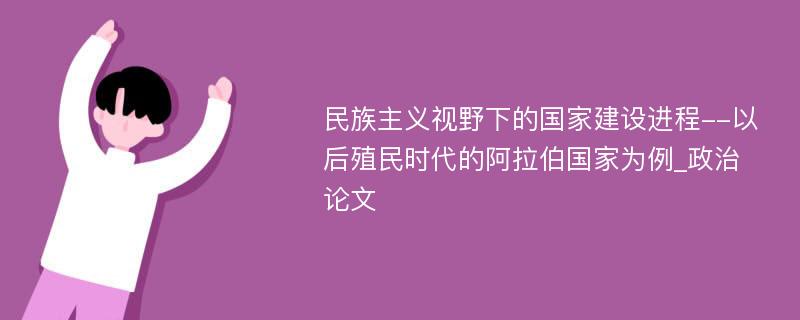
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国家建构过程——以后殖民时代的阿拉伯国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国家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为例论文,视角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发展政治学中,“国家建构”是指一个国家树立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向整个社会渗透国家权力、建立现代政治体系的过程。①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国家建构是其走向现代国家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而任何一种国家建构方式都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为行为根据的。不同国家所持政治理念的不同,决定了各自国家建构的进程和结果也会迥然有异,尤其是在国家建构的起始阶段更是如此。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菜单”中,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的“亲缘”最为密切,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往往是“塑造”政治发展框架的关键性力量。那么,民族主义是如何影响国家建构过程的?其最终结果又会怎样?本文拟以20世纪50-60年代获得民族解放后的阿拉伯国家②为例,对所提及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国家建构
从政治学角度看,如果说国家建构目标体现的是“谁得到什么”的问题,那么,国家建构过程就是一个“如何得到”的问题。由于国家建构是一个国家权力逐步巩固和向下渗透的过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道统”与“法统”两种路径各异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法。由于议题所限,本文主要考察阿拉伯世界的“道统”问题,即作为观念的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是如何做出反应的。③
后殖民时代,阿拉伯国家新生政权进行国家建构是必然的选择。④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法案的出台,仅仅是中东国家试图完全控制经济体系的先兆。这种控制是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的实施而最后完成的。埃及在1961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在1965年先后实施了工业企业、银行的国有化。其中的一些措施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改变和对社会公正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剥夺社会权力的资源,这一过程导致了传统富裕阶层的整体衰落。纳吉布对阿拉伯国家新生国家权力扩张的描述,为本文的分析、探讨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框架,但与纳吉布不同的是,本文主要考察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对国家建构的影响。笔者认为,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阶段,民族主义因其鲜明的反殖、反帝姿态而赢得了国民的广泛拥戴,并因此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在阿拉伯世界建立起新国家后,这种民族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民族主义,并使新生国家政治结构的构建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二、民族主义对国家建构进程的影响
阿拉伯国家新生的民族主义情感对国家政治体系的建构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
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壮大直接得益于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大力支持。在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滞后性,使得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发育较之西方国家都显得极不成熟,具体而言,就是缺乏具有明确政治纲领和利益取向的政治阶层。在此情况下,唯有体现全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奋斗目标(它的背后是一种政治力量),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可;也唯有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可,这种政治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民族主义正是具有这种双向功能的一种政治力量。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阶段,领导者们正是打出反殖、反帝的共同旗帜,才得以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反过来,正是由于得到广大人民的有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得以最终成功。在民族解放任务完成之后,如何保持广大民众对新生民族国家政权的支持,或者说,如何把基于反殖、反帝目标建立起来的民众支持,适时地转移到对新生政权政策纲领的支持上来,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尤其是在政治制度化滞后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新生民族主义政权往往都缺乏来自程序合法性的有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民众的直接支持就显得至关重要。
那么,阿拉伯国家新生政权究竟应该具有哪些特质,才能赢得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持呢?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新生民族主义政权主要体现为对原有政权精英主义价值观和金字塔式统治方式的彻底颠覆。而民粹主义(populism)正好是这样一种能够“真正”体现人民统治的政治价值观。何谓“民粹主义”?按照《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的定义,民粹主义实际是“对多种政治运动一种总的称呼。这些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其对整个人民,特别是对反对大商业组织和工会的普通公民,乃是一种号召力。对人民党主义(民粹主义)者来说,人民是政治美德的源泉,但他们却被异己的、强有力的和有害的敌人所困扰。此外,人民党主义还有下列特征:从中流砥柱人物和自由党中获取支持;政治上具有极端主义的语言和行为;把某种发生在逆时代主要发展趋势而动的反对方案似是而非地变为革命性的方案;一种引人注目的彗星似的跨入政治天堂的途径”。⑤另外,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所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也专门对民粹主义概念进行了界定。该书作者认为民粹主义至少有7种类型的政治现象。本文主要涉及其中的第四种类型,即“平民主义独裁”。“在这类情况下,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越过旧政客直接号召人民大众,给他们‘面包和马戏’的小恩小惠,而攫取非宪法权力。”⑥尽管学者们对民粹主义概念的具体理解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看,民粹主义政治具有利用“人民”作为政治号召,强调其政治权力来自大众的共性特征。可以说,民粹主义既是民族主义政治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逻辑延伸,也是民族主义政治哲学的集中体现。阿拉伯世界新生民族主义政权所奉行的,正是这样一种民粹主义政治哲学。
另外,从阿拉伯世界的现实看,阿拉伯世界的新生民族主义政权往往是一些军人政权,如埃及的纳赛尔、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伊拉克的萨达姆等领导人均是军人出身。从阶级背景看,这些领导者基本上都来自于社会中、下阶层。由于在利益认同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军人阶层不同于给定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类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处理内、外问题上容易患得患失。因此,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往往特别强调民族主义政权阶级基础的广泛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众性。从法理角度看,“人民”已经成为体现新生民族主义政权“政治正确性”的基本标志和实现其合法统治的权力来源。
这种民粹主义思想体现在政治制度领域,就是把原有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如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视为相互倾轧、政治分裂的代名词。在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眼里,这种代议制民主根本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直接民主取而代之。例如,卡扎菲认为:“议会制是解决民主问题的一种欺骗办法。议会本以代表人民而建,然而它的基础本身却是非民主的。因为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政权,而不是某种代表人民的政权。单单是议会的存在就表明人民没有参政。只有人民自己参与,而不是他们的代表参与,才有真正的民主。议会已成为人民行使权力的合法障碍,它不让民众参与政治,却代表他们独揽大权。”⑦他还指出:“议会已堕落为攫取人民革命政权的工具。今天,人民有权通过人民革命摧毁所谓的议会——独揽民主和权力,以及强奸民意的工具。人民有权响亮地宣布新的原则:‘不要人民代表’。”⑧对于政党在现代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卡扎菲同样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认为:“政党是建立在独断专权,即党员统治人民大众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政党愈多,争权愈烈。这种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的结果是,损害人民取得每一项成就,破坏造福于社会的每一项计划”;⑨“政党是现代的部落,是教派。一个政党统治下的社会,完全像一个部落或一个教派统治下的社会一样。……如果说部落政权和教派政权在政治上已经被拒绝和唾弃,那么,党派政权也应该被拒绝和唾弃。因为两者的行径一致,导致的结果也一样”。⑩
这种民粹主义思想的逻辑体现,就是废除各种既定的政治制度,而代之以各种群众性政治组织。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埃及的纳赛尔政权。1953年,纳赛尔领导新政权废除了埃及时存的所有政党。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有组织的声称代表全体人民意愿的群众性组织,如“解放阵线”(Liberation Rally,1953年)、“民族联盟”(National Union,1956年)、“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Arab Socialist Union,1961年)等。(11)在利比亚,所有其他政党和工会都被取缔,而代之以革命指挥委员会和仿照埃及建立的全民性组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对此类现象,以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而名扬天下的亨廷顿曾做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评价:“全国民族协会所以能吸引军人,就在于其成员具有广泛性,并且被认为是以动员和组织民众,达到军人认定是全民皆可受惠的国家发展目标。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非政治的建国模式’,这种模式体认不到任何社会固有的,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化中的社会里到处存在的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冲突,故而也就无从提供斡旋冲突及调节利益的方法。”(12)说到底,许多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奉行的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二)激进的“去制度化”行动
在国家建构过程中,阿拉伯国家新生民族主义政权首当其冲。国家建构就是对原有政治结构进行全面颠覆,这既是出于新生民族主义政权打破旧有国家机器和另起“炉灶”的一般性考虑,又是民族主义政治行为轨迹的特定结果。
首先,殖民政权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功利化运用,败坏了它在广大民众中的应有形象。政治制度化程度是表明一个国家政治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越高,该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就越高。就阿拉伯国家来说,它们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了现代民主制度(如议会、政党等)。但由于阿拉伯世界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得二战之前的阿拉伯国家政权(包括殖民政权和半殖民的封建政权)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对立和隔膜。在这些国家当中,基本上都是国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权贵阶层独享权力资源。例如,在1950年法鲁克王朝统治时期,埃及议会(即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前的最后一届议会)的319个席位中,大地主占了115席。这些地主拥有的土地都不少于100费丹(1费丹等于4200.833平方米),其中4/5的人拥有超过500费丹的土地。(13)这些权贵阶层作为这种落后且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自然要悉心维护当时统治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表达民意、保障实现个人权益的民主政治制度,一旦被移植到落后的殖民、半殖民国家,往往是“淮橘成枳”,非但没有成为社会不同阶层进行有效沟通和进而实现有效统治的手段,反而借民主政治之名,行独断专行之实,为不合理统治模式披上了现代化的合法外衣。有学者指出:“(阿拉伯)自由时期的主要领导者基本上包括了土地贵族、中心城市的商人和部族领导人。事实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在他们(与大众)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运转关系,也没有认识到公众的需要……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持住在政府中的位子和让个人获得好处。”(14)这种对民主制度进行庸俗化、工具化理解和实践的最终结果,是败坏了民主政治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应有形象。
在这种背景下,采取激进的“去制度化”措施,摈弃民主政治制度反倒成为一种深得人心的进步举措。无疑,阿拉伯国家新生民族主义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首先来自于反殖、反帝的历史功绩,因此它们要想在政治独立后继续维系这种政治合法性,就必须彻底否定殖民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框架和政治理念。此外,作为新生民族主义政权执政阶级基础的社会中、下层人民,他们对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十分厌恶。这就使“他们(阿拉伯军事领导人)提出了一种极端的现代化词藻来表明对少数权贵集中经济和政治特权的极度愤恨”。(15)在阿拉伯国家新生民族主义政权看来,殖民时代的民主制度仅仅是寄生在西方国家卵翼之下的政治附庸及装点门面的政治招牌,因此有必要把原有的政治秩序视为反动统治的象征而加以摈弃。于是,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政权把所奉行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应用到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中,便体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政治举措:废除象征着殖民和半殖民统治的“自由时期”(阿尔伯特·胡拉尼语)的政党和议会制度,而代之以直接民主。这是阿拉伯国家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纳赛尔对这一点进行过清楚的表述,他在1957年3月会见一位印度记者时说:“我能问一个问题吗?什么是民主?我们在1923到1953年间已经有过一个民主体系。但是这种民主给我们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我告诉你,地主和帕夏统治我们的人民。他们利用这种民主来更方便地服务于封建体系。你已经看到了,封建主把农民召集到一起,并驱赶他们去投票。农民们只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指令进行投票。……我想无论从社会还是经济上都能解放这些农民和工人,这样,他们可以说‘是’。我想在不影响农民和工人正常生活或每天获得面包的前提下,让他们说‘是’和‘不’,这就是我对自由和民主的基本观点。”(16)
其次,在阿拉伯国家新生民族主义政权的议事日程中,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排在较为靠后的位置。对这些政权来说,当它们经过浴血奋战把殖民者赶出国境后,新生的国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从一个较长的时段看,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想实现这一任务,就需要特别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相比之下,由于民主的发展往往是与个人获得充分自由紧密相连的,因而在民族主义政权的领导者看来,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之后。按照罗伯特·伊莫逊的说法,民主还应排在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的后面。(17)就此而言,在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诸事纷纭的情况下,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在中东,致力于发展自身的资源,连同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威胁的努力,使得国家安全、自卫和快速工业化等目标将不可避免地取代政治多元化和个人权利的目标。这样,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当地政权必须应对与贫困、文盲、健康、住房和快速城市化,以及渴望尽快赶上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在这种环境中,威权政权最好的选择是大力强调管理、监督和控制。”(18)于是,在处理政治制度化(或政治民主化)与发展经济(同时也包括巩固政权)的关系问题上,阿拉伯新生民族主义政权显然认为后者更为重要,更能给民众带来实际好处。纳赛尔就曾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生活自由和生活自由的保障,选举自由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而成为一个误导人民的骗局。”(19)
此外,对新生民族主义政权来说,通过强化政府权力、提高决策的效率和权威性来治理国家,是一种颇具诱惑力的政治选择。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包括实体性的和程序性的)的牵扯,国家的权力(在它背后是统治者的意志)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的。因此,几乎没有几个阿拉伯新生民族主义政权的领导人能够按捺住心中这种“去政治制度化”的冲动,他们倾向于把议会、政党、选举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视为可有可无的政治程序而加以摈弃。亨廷顿曾指出:“无论是带有改革性还是护卫性的军政府,在夺取权力后的第一个行动,通常是废除一切现存的政党。……与社会上的其他集团比起来,军队最倾向于认为党派不是建立共识的机制,而是分裂的祸根。他们的目标是没有政治的共同体和强迫命令的共识。”(20)“去政治制度化”行为,即废除政党、议会、选举制度等既定的政治组织和法律法规,既体现了民粹主义政治哲学,也是阿拉伯新生政权延伸自身权力、铲除旧政治势力的有效方式。
然而,政党的功能在于组织参与、综合不同利益、充当社会势力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在履行这些功能时,政党必然反映政治上的逻辑而非效率上的逻辑。因此,“现代化的倡导者和传统的卫道士一样,都时常反对和诋毁政党。他们试图在不建立能保证他们社会政治稳定的制度的情况下使他们的社会现代化。他们在牺牲政治的情况下追求现代化,到头来,他们对一种东西的追求却因对另一种东西的忽视而失败了”。(21)
(三)直接民主与“克里斯马”型统治
直接民主是一种古老而又颇具魅力的政治理想,它与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一道,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所能设想和实践的基本政治类型。何谓直接民主?刘军宁认为,直接民主是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重合,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失误,而不通过中介和代表”。(22)那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究竟孰优孰劣?囿于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的不同,不同的政治力量往往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就民族主义政治(尤其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而言,在政治哲学上的民粹主义政治观决定了其先天具有一种反精英主义倾向。在民族主义者看来,间接民主是一种少数人的统治,是一种假民主或民主的初级阶段。而只有直接民主制最能体现民族主义的政治理想。为实现这一目标,阿拉伯新生民族主义政权的领导人主张,应该把所有挡在人民与领袖之间的政治障碍都彻底清除掉,唯有如此才能保障人民意愿的充分表达。卡扎菲曾言:“人民大会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唯一途径”,“现在世界第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施直接民主的实际经验,民主问题终于在世界上得到了解决。现在只需民众努力奋斗,去消灭世界上盛行的各种假民主的专制统治形式——从议会、教派、部落、阶级,到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23)
然而,在政治实践中直接民主所要求的全民参与政治决策的做法根本无法实现,因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乃是科层制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繁复。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中,‘政治人’总是极少部分。不管直接民主理论者如何呼吁,他们却仍不过是极少部分‘政治人’中的极少数,一旦他们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他们必然要声称是在为其他人实行直接民主,这时他们就已经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实现‘间接’民主了。”(24)由此而言,在废除了代议制民主赖以运行的各种政治制度的情况下,直接民主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极少数政治精英的寡头统治。
在中东的民族主义政治中,民粹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废除各种政治制度的政治举措,必然导致直接民主和“克里斯马”型统治(25)的出现,因为直接民主与“克里斯马”型统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直接民主导致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对具有超凡魅力领袖的深切期待;而那些强化领袖个人作用的“克里斯马”统治,它们所要求的往往也是那种不受任何政治制度牵掣,声称权力直接来自人民的直接民主制。“克里斯马”型统治是一种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它往往出现在社会面临种种物质和精神危机的时期,民众渴望有救世主般的领袖人物出来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克里斯马”式人物的出现正好顺应了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要求,因而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克里斯马”型统治也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它的统治方式是情感性的,政治制度的废立、管理者的选拔完全取决于领袖个人的好恶,因此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而且,这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领导者个人魅力和超凡品质的基础之上的,如纳赛尔、卡扎菲、阿萨德、阿拉法特等都属于“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他们不仅在本国民众中具有极高威望,而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作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具有可以改变政治事件发展进程的潜在能力,能够以其个人创造力、理论思想和政治实践,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改变历史发展进程。(26)这种统治形式的出现是与中东社会特定的发展状况相契合的。
在阿拉伯世界中,传统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关系的地方性而使彼此隔离,这种状况不足以建立起一种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联系及政治组织。马克思对法国封建社会农民的分析同样契合中东的状况:“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7)落后的生产方式制约了民众参政的物质前提,同时又铸就了一种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和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这就使普通民众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对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深切期待,对领袖人物唯马首是瞻的盲目追随。这一特定的政治心理为“克里斯马”式领袖的出现提供了特定的文化背景。
二战以来,在席卷全球的“非殖民化”运动的历史大潮推动下,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如火如荼,从而有可能把在这一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推上政治的巅峰。他们因为在推翻人们深恶痛绝的旧政权或捍卫民族尊严过程中的杰出作用,而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信任,并由此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认可。彭树智先生曾指出,纳赛尔政府是独裁的权力主义政府,但是“革命领袖的形象,使政府的苛严程度似乎减轻了。他是以‘总统’而不是以‘铁腕人物’进行统治的”。(28)
三、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果
如前文所述,许多阿拉伯国家新生政权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因而受既定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价值追求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仍沿袭了争取民族解放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颠覆性做法(至少在政治发展方面是这样)。然而,从革命到执政毕竟意味着民族主义政权(尤其是民族主义的领导者)政治视野和政治利益的根本性变化。因此,从一个较长的时段看,新独立阶段所采取的一系列民族主义政策举措难以长久坚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变化,或者更直接地说,向威权政治(29)方向变化,构成了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这一发展趋势与民族主义的主张看似相悖,实则一脉相承。就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威权政治的产生乃是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果。具体地说,对阿拉伯世界的威权政治,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解读:
(一)民族主义运动的分化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威权主义倾向
民族主义作为指导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可以与不同的奋斗目标相结合,体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因此,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具有明确原则的意识形态,毋宁说像一条政治上的“变色龙”,能够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随时改变自己的颜色。在阿拉伯国家独立前,民族主义始终与反殖反帝、民族自决联系在一起。这一奋斗目标与这些国家所有阶层的政治诉求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保证了民族解放运动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政治运动奋进前行。然而,当这些国家真正赢得政治独立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民族主义领导人力图借助与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方式,以增加现行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但是,这种淡化阶级冲突、强化共同利益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其说是新时期民族主义政权的奋斗纲领,不如说是维护时下统治秩序的有效工具。梯比(Bassam Tibi)认为:“在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下,‘全民共识’不再是全体人民发自内心的想法的凝结,不再是能够立竿见影地进行政治动员的手段,而仅仅变成了一个空壳,一个它理应变成的粗糙而易碎的空壳。”(30)
这样,一度作为进步力量的民族主义,在后殖民时期已经转变成统治精英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识形态。这些曾经参加独立战争的统治者们试图占据殖民主义者腾出的特权位置。(31)事实上,在一个社会阶级分化日趋明显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宣传手段来弥合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973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提出了著名的“世界第三理论”,这一理论及其政治实践——“文化革命”——都涉及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和措施。然而,就在此后不久,政府便开始大规模抓捕那些反对革命和不完全认可新生政权的人们。(33)事实上,在获得政治独立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距离,几乎像他们的前任殖民上层一样远。民族主义和收回主权的华丽词藻,难以掩盖政权从异己的外国寡头集团手中转移到了异己的本国寡头集团手中这样一个事实。(33)例如,在伊拉克,阿拉伯复兴党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逐步沦为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不是提供思想启蒙,而是沦为政治控制工具。”(34)
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民族主义政权所奉行的是一种全能主义原则,即为了更好地巩固政权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由国家(政府)承担起社会正常运行的全部职责。而这种全能主义国家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首先要建立一个威权政体。“在经历了一个简短且十分含糊的时期后,国家巩固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重返殖民统治时的威权主义过程。”(35)具体地说,就是以政府职能扩张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权力扩张。而“国家膨胀的一个重大结果,就是权力集中在一个管理国家的小团体手中”。(36)这种具有威权主义倾向的国家总是试图控制整个社会。“当它(威权政体)面对社会内的有组织的团体,对一个威权政体来说,最理想的战略就是破坏那些不能控制的组织,重新改造和指挥那些能够控制得了的组织。”(37)国家权力向社会领域的不断渗透,使得社会和个人的权利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由此导致了威权政治的出现。至少就阿拉伯国家来说,“阿拉伯政治中精英—大众互动的运算方法是,国家把自己放到福利提供者的位置,以此来换取公众没有异议的服从”。(38)因此,依靠广大民众支持起家的民族主义政权,不管主观意志上如何想标新立异,创立一种有别于殖民主义和传统国家的全新统治模式,但最终往往是难脱窠臼,步入了威权国家的行列。
(二)民粹主义的开端导致威权政治的结果
前文已经提到,在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政权的主导思想是民粹主义。正如民族主义可以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盟一样,民粹主义也可以和任何事业或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但是民粹主义民主作为多元民主的敌人,它经常被看作一种隐性的威权主义”。(39)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民粹主义惯于在集体层面上使用“人民”的概念。它在抽象意义上颂扬人民民主的同时,却又在具体操作中忽略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毫无疑问,“如果社会或国家比个人更重要,如果他们自己的目标独立于个人的目标并超越个人目标的话,那么,只有那些为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目标而努力的个人才能被视为该社会的成员。”(40)这就使民粹主义民主呈现出一种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不宽容“性格”。
伊莫逊曾深入分析了这种民族主义民主是如何演变为民族主义独裁的:“运行中的民主制必须依靠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这两种潜在对立原则的有机混合。不论在什么时候,民族主义都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而集体原则很可能会以妨碍民族团结为由,而凌驾于个人和少数之上。……然而,谁能代表民族的意愿?民族的灵魂可以由构成民主简单多数的农民和工人来代表,但是他们的无知和缺乏经验,很可能使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而一个领袖或克里斯马式领导人可以取代民族的意愿。……主权的行使应该委托给那些能正确运用这项权力的人。这样,民族主义的民主最终转变为民族主义的独裁。”(41)
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民粹主义倾向于废除政党、议会等政治制度化产物,改而推行直接民主。但这种做法带来的政治后果让人始料未及。一般来说,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失去了进行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这样,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正像迪韦尔热所说的:“一个没有政党的政体必然是保守的政体。”(42)
亨廷顿对取消政党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曾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军人领袖陷于他们自己的主观偏好及价值观与其社会制度的客观需要二者之间的矛盾之中。所谓社会制度的客观需要通常指三个方面。首先,需要有政治制度能够反映现存的权力分配,并同时足以吸引和同化各种新生的社会势力,从而建立起一种独立于造成这些制度的那些社会势力的存在。第二,在那些军人掌权的国家,政治体系的官僚输出部门常常极为发达,相比之下,理应能表达和集中各种利益功能的输入却处在混乱和无组织的状态之中。第三,还需要有能够控制接班问题的政治制度,并使权力从一个领袖或领导集团移交给另一个领袖集团时,不至于诉诸政变、造反或别的流血手段。在现代发达的政体中,这三种功能大部分由政党来履行。由于军人领袖一般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政党。这就是他们难于创造出能履行这些功能的政治制度。”(43)
(三)从“克里斯马”型统治到现代官僚统治
从政治发展史的角度看,“克里斯马”型统治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统治形式,这一特征决定了它注定要朝着现代官僚统治的方向发展。
首先,“克里斯马”型统治几乎总是在社会政治秩序遭受破坏或被普遍质疑的危机环境中应运而生的,由此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模式。正所谓“乱世出英雄”,从民族解放到国家建设的主题转换,使众多阿拉伯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秩序动荡和价值迷茫。如何才能摆脱频繁的军事政变?如何应对以色列和西方的威胁和挑战?如何才能解决问题重重的国内事务?所有这些,都促使民众渴望能有一位兼具能力和品格的时代英雄来带领他们走出困境。这使得那些具有非凡魅力的政治强人很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时代主题的转换毕竟只是历史长河流淌过程中激起的一朵浪花,它虽然壮美但转瞬即逝。
其次,在这种政体中,政治制度发育的不完善,使得用以缓冲和沟通领导人与民众之间关系的政治机制相对缺乏。这样,“领袖与群众之间就存在着面对面的直接关系,用科恩豪泽的话来说就是:领袖可以任意动员群众,群众可以随时影响领袖”。(44)这种状况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时期或许十分必要,但一旦进入到国家建设时期,这种互动模式的弊端便开始日益显现,因为领袖与大众的这种关系具有明显的感性成分,它除了使社会政治秩序平添混乱外,还可能使领导人的政治决策显现某种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克里斯马”型统治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模式。
第三,只有终结“克里斯马”型统治,才能摆脱领导人的继承危机。“克里斯马”型统治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把政治体系全部维系在领导者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社会事务也都是以“克里斯马”式领导人为基础展开的。但是,“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45)这种政治决策模式或许有效一时,但这幢“政治大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代风云人物的领袖风范和个人魅力作为一笔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无法被后来者所继承的。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曾经寄托在几个非凡领袖身上的获得政治解救的近似千禧年运动的希望,现在不仅扩散到大量的显然不那么非凡的人物身上,而且这些希望本身也变得淡化。魅力领袖显然可以做到的对社会能量的巨大凝聚作用,随着这些魅力领袖的消失而消失了。”(46)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使然,纵然是一代领袖人物也难逃大限。这就使这种统治模式终究摆脱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巨大风险。“这样,从克里斯马式领导人向继任者的过渡往往伴随着一场灾难。因此,克里斯马型统治不可能依靠用另一个人来代替克里斯马式领导人的办法完成。”(47)
在韦伯看来,“克里斯马”式领导人的继承问题,实际上就是“魅力的平凡化”问题。总体上来说,伴随着魅力平凡化过程,“克里斯马”型统治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入平凡统治的形式:世袭制或官僚体制。(48)就阿拉伯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两种转换倾向同时存在:前者如叙利亚、伊拉克,后者如埃及、阿尔及利亚。由于继位者不可能与前任一样,完全凭借非凡魅力赢得民众的认可,因而继任者不得不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如埃及的萨达特上任后,以“虔诚总统”自居)来维持统治。但不管怎么说,在魅力平凡化过程中,继任者(不管是世袭的,还是官僚的)都需要借助制度化的机构来行使国家权力。而且实践也已经表明,新一代领导人的上台,已经成为推动中东政治现代化向前发展的最大希望。
四、小结
在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建构进程最终演化成了一种威权政治模式,这一结果可能是很多人所始料不及的。那么,这种民族主义主导的政治进程,为何容易滑向威权政治?我们知道,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民族主义的产生、壮大主要与反帝、反殖斗争密切相连,由此决定了那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外发凝聚型”的民族主义。这些独立后的国家,往往面临着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国家救亡与社会启蒙等多重任务的挑战。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从自身“特质”出发,更强调集体人权和民众的整体权益,因而具有明显的整体主义(表现为对内团结)和否定倾向(表现为对外排斥)特征。从对内层面看,民族主义更强调国家认同(主权为其最高体现)而不是个人认同(最高体现是人权);强调一元主义,而不是多元主义;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从对外层面看,民族主义更强调本土性和独特性而不是普适性和共通性;强调自足性和排他性,而不是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些特征与民主的基本价值都是背道而驰的。有学者指出,在获得政治独立后,“领导人不再从广大民众中寻求支持,而民众自身则必须适应领导人的独裁。并非是这种独裁一定是压迫性的,或不引人注意,而是大多数领导人自信凭个人的能力能够为民众作决定。从这一意义上说,民主信念在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意识形态中仅占非常小的部分。”(49)伊莫逊也指出,由于这种民族主义脱离了19世纪自由民族主义的民主前提,因而很容易变成建立集权统治的工具。(50)因此,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背后蕴藏的往往是一种非民主的政治成分。
总之,在民族主义主导下,阿拉伯国家从最初的民粹主义演化为威权主义,既是民族主义自身进化的逻辑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但从较长的历史时段看,威权政体仍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模式。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它可能走向集权政治,也可能走向民主政体。这取决于未来的民族主义将会与何种意识形态相结合。而唯有走公民民族主义(实际是公民国家主义)道路,才能保证国家政治进程不致偏离正轨。
注释:
①韩国学者李书勋(Su-Hoon Lee)认为:“国家建构指加强国家对社会的相对权力,或者扩展国家对社会的组织能力。”在他看来,“加强国家权力”和“扩展国家能力”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梯里(Tiny)则把“国家建构”等同于“消除或减少中心政治组织之外潜在或现实的竞争性权力焦点的过程”。至于国家建构的内容,李书勋把它归结为三方面的能力:获取(Extraction)、强制(Coercion)和赋予(Ineorporation)。Su-Hoon Lee,State-Building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Westview Press,Kyungnam Univerisity Press,1988,pp.25-31.我国知名学者李强也持有与之类似的观点。他结合韦伯(Max Weber)、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奥尔森(Mancttr Olson)的观点,把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合法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对税收的垄断、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李强:《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第78-79页。
②本文中的“阿拉伯国家”主要指阿拉伯世界中的世俗性国家,尤其是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
③由于“道统”与“法统”是互为表里的两个范畴,以民族主义观念作为分析重点,其最终仍可能会以物质性力量的形式表现出来。
④专门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哈利杜姆·哈桑·阿里-纳吉布(Khaldoun Hasan al-Naqeeb)为我们描绘了这些国家国家权力扩张的基本轨迹:第一步,这些新生政权(大部分是军人政权)在建立后试图马上控制整个国家。其主要是通过解散议会、废除选举和委派军人到各级政府任职等措施来完成的。第二步是破坏所有组织性的权力机构(如政党和政治组织),以便控制整个政治系统。第三步是在民众中扩展政府的权力(即控制劳工组织和其他职业组织),以便遏制这些组织潜在的“分裂性”。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就是认识到,要想有效垄断权力必须指向唯一还处在政府权力之外的领域,即基于土地所有权、资本和财富而产生的社会权力。Khaldoun Hasan al-Naqeeb,"Social Origins of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the Arab East",in Eric Davis and Nicolas Gavrielides(eds.),Statecraft in the Middle East:Oil,Historical Memory,and Popular Culture,Board of Regents of the State of Florida,1991,pp.64-65.
⑤〔英〕迈克尔·曼主编、袁亚愚等译:《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16-517页。
⑥〔英〕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主编,林勇军等译:《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⑦⑧⑨⑩〔利〕姆阿迈尔·卡扎菲著:《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9、10、16、19-20页。
(11)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econd Edition,Routledge,2000,p.150.
(1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72页。
(13)Eric Davis and Nicolas Gavrielides(eds.),Statecraft in the Middle East:Oil,Historical Memory,and Popular Culture,p.45.
(14)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64.
(15)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pp.69-70.
(16)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149.
(17)Rupert Emerson,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Boston:Beacon Press,1960,p.290.
(18)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240.
(19)Hilal Khashan,Arab at the Crossroads: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p.79.
(20)(21)〔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23、85-86页
(22)刘军宁等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7页。
(23)〔利〕姆阿迈尔·卡扎菲著:《绿皮书》,第37、38页。
(24)何包钢:《直接民主理论、直接民主诸形式和全民公决》,载刘军宁等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第23页。
(25)按照韦伯的政治学分类,统治类型分为法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克里斯马”型统治三种类型。其中的“克里斯马”型统治是介于法理型统治和传统型统治之间的一种政治统治形式。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页。
(26)王京烈:《动荡中东的多视角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4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
(28)彭树智:《纳赛尔与阿拉伯世界》,载《学术界》,1988年第5期。
(29)需要说明的是,威权(authoritarian)体系不同于集权主义(totalitarian)体系。由于威权统治缺乏仅仅通过官僚制手段就能控制或转变社会的强有力的制度,因而只有通过各种方法来遏制反对派。这些方法包括从恐怖无情的暴力手段(“大棒”)到经济利诱(“胡萝卜”);从利用个人、族裔或集团的联合到悉心建立的具有成员义务关系的联盟和职业协会。罗格·欧文认为威权政治有四个主要特征:第一,不能容忍在政治结构中存在有组织的团体;第二,倾向于把人民作为更大地区、族裔或宗教集体中的一员,而不是作为个人看待;第三,有意识地抑制阶级意识的发展;第四,使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控制。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35.
(30)(31)Bassam Tibi,Arab Nationalism:Between Islam and the Nation-State,S.T.Martin Press,Third Edition,1997,p.55,64.
(32)Lillian Craig Harris,Libya:Qndhafi's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State,Westview Press & Croom Helm,1986,p.18.
(33)〔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07-408页。
(34)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159.
(35)Christopher,Clapham,Third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Croom Helm Ltd.,London & Sydney,1985,p.68.
(36)Su-Hoon Lee,State-Building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Westview Press,Kyungnam Univerisity Press,1988,p.164.
(37)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32.
(38)Hilal Khashan,Arab at the Crossroads: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p.132.
(39)Andrew Heywood,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Macmillan Press Ltd.,1998,p.301.
(40)〔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36页。
(41)Rupert Emerson,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p.291.
(42)(43)〔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72、223-224页。
(44)(45)〔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82、17页。
(46)〔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8页。
(47)Roy R.Andersen,Robert F.Seibert,Jon G.Wagner,Politics and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Sources of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Second Edition,Prentice-Hall,Inc.,1987,p.210.
(48)〔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第180页。
(49)Christopher,Clapham,Third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p.64.
(50)Rupert Emerson,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p.213.
标签:政治论文; 阿拉伯民族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民粹主义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