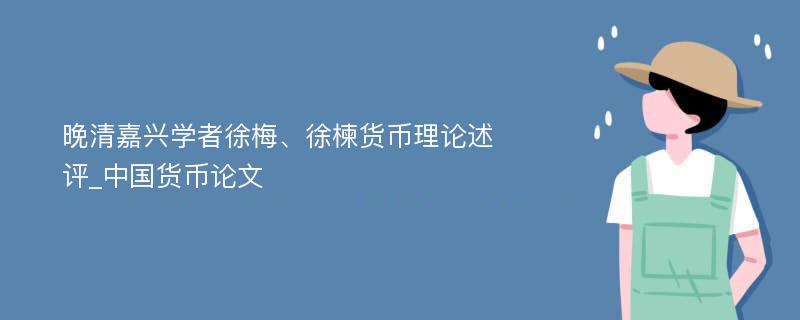
晚清嘉兴学者许楣、许梿的货币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嘉兴论文,晚清论文,述评论文,货币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81(2010)04-0005-06
许楣(1797-1870),字金门,号辛木,嘉兴海宁人,晚清著名学者;道光十三年(1833)中进士,官至户部主事;著有《真意斋随笔》、《真意斋诗存》、《真意斋文集》、《删订外科正宗》、《钞币论》等,其中以《钞币论》影响最大。许梿(1787-1862),字叔夏,号珊林,许楣之兄;也是在道光十三年中进士,历任知县、知府等职;著有《洗冤录详议》、《刑部比照加减成案》等。许梿为许楣的《钞币论》写了序言和若干按语,故该书可视为兄弟二人合作的成果。《钞币论》刊行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是许楣为批驳晚清名目主义货币理论家王鎏的《钱币刍言》而撰写的一部专论,几乎将中国传统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发展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主要论及了三大问题:货币的本质及价值、王鎏钞法的实质及危害、白银外流危机。
一、货币的本质及价值
和一切金属主义货币理论家一样,许楣、许梿对货币的本质及价值的认识基本上是错误的。他们忽视货币的特殊社会性,不知道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片面地认为货币的本质是固有价值较高的商品,金银等金属的固有价值较高,所以必然充当货币。由于不知道货币的真正本质和价值来源,所以他们把货币和商品的交换、金属货币和纸币的交换都视为普通的物物交换,把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纸币也视为商品纸,而不懂得纸币可以替代金属货币履行流通手段职能的道理。
许楣认为白银是最好的货币,这是由货币演进的历史和白银便于携带的物质属性决定的。他说:“以余考之,银之为币久矣,特未若今日之盛耳;上之用银亦久矣,特未以当赋耳。……魏、晋后金日少,银日多,而钱重难致远,势不得不趋于银。至明以银当赋,然后上下盛行。”[1]238也就是说,白银作为货币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进而强调说运用政府的强制力也不能剥夺白银的货币地位,“如欲尽废天下之银,是惟无银。有则虽废于上,必不能废于下也。”[1]238-239既然白银的货币地位不可剥夺,那么白银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许楣认为这是由白银数量的有限性决定的。他写道:“天下之物,惟有尽故贵,无尽故贱。淘沙以取金,金有尽而沙无尽也;凿石以出银,银有尽而石无尽也。天下之至无尽者莫如土,烧土以为甓,范其文一两,人必不以当金当银。造纸以为钞,印其文曰一贯,独可以当钱乎?且钞法之弊,非以钞之有尽也,正以钞无尽而钱有尽故也。”[1]241许楣的本意,是要借助纸币越多越贱的事实来否定王鎏鼓吹纸币是“不涸之财源”[1]238的谬论;但他的具体论述又超出了这一事实的适用范围,他试图用数量的多少来解释金银和其他商品的价值,认为数量有限的金银价值较高,所以能够充当货币,数量无限的商品价值极低,所以不能充当货币。这实际上是货币数量论的错误观点。
许梿则用一段按语对许楣的上述言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凡以他物为币,皆有轻重变易,惟金银独否……时代有变迁,而此二物之重,亘古不变。锱铢则以为少,百千万不以为多。至于钞,骤增百万即贱,骤增千万则愈贱矣。”[1]241他还指出:“多出数百千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之,多散数百千万之金银于天下,天下必不轻也。亦可见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之所能颠倒也。”[1]250-251显然,许梿对货币价值要比许楣的认识多一点合理的成分。他认为金银作为货币,其价值是稳定不变的,不会像纸币那样因数量增加而变化,并据此正确判断商品的价值不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
但是,许梿对货币价值的认识的主要内容是错误的。第一,他把金属货币(金银)、纸币都当作普通商品,并认为商品的价值“皆其所自定”,从而把金属货币的价值和纸币的“价值”混为一谈。其实,金属货币并不是普通商品,其价值和普通商品一样,都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人类社会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而不是由商品“自定”的自然属性;纸币本身并无“价值”,而只是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如果说纸币有价值的话,这种价值不过是它的购买力,也就是它在金属货币制度下替代金属货币履行的流通手段职能,而在金属货币制度崩溃以后,纸币的价值则是它所能购买到的单位商品的价值。第二,由于不知道商品价值的真正内涵,他误以为金银的价值是“亘古不变”的。其实,金银既然是商品,其价值就不是绝对不变的,也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发生一定的变化。第三,他不知道金银作为货币,其在流通中的价值不会因数量增加而变化,是因为它们具有贮藏手段职能,一旦其数量超出商品流通的货币需要,超出的部分就会自动退出流通领域;而在主要流通金属货币的条件下,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由于不具备贮藏手段的职能,当其数量超过商品流通的货币需要时,就不会退出流通领域,因而不断贬值。第四,他和许楣一样只指出了纸币越多就越贬值的一面,而未指出纸币越少就越升值的另一面。
总之,许楣、许梿对货币本质及价值的认识虽略有不同,但都是一种典型的货币拜物教思想,在哲学上都体现了客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念,因而在理论上几乎是完全错误的。不过,从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来看,他们对货币本质和价值的认识又是符合当时中国货币制度的实际情形的。当时,中国刚刚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尚未建立起近代意义上的银本位币制,白银虽然是中国主要的通货,但大多是原始的秤量货币,而不是近代的银铸币(当时流入中国的洋钱虽是银铸币,但被视为异端)。而且,许楣、许梿对货币本质和价值的认识,也是他们全面考察中国古代纸币流通的失败历史之后得出的结论。[1]236-238中国自北宋产生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以后,南宋、金、元、明数代政府都曾发行纸币,又都以引发通货膨胀、信用扫地而告终。这也为许楣、许梿形成金属主义的货币认识提供了客观依据。此外,尽管许楣、许梿对货币本质及价值的认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其目的是为了反对王鎏的滥发纸币主张,所以也就具有了历史的进步意义。
二、王鎏钞法的实质及危害
所谓钞法,就是废除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地位,发行不兑现纸币。这是王鎏《钱币刍言》所宣扬的名目主义货币理论的核心主张,也是许楣、许梿在《钞币论》中重点否定和批驳的对象。许楣指出:“钞以代钱之用,此著书者(指王鎏)之症结。”并说:“吾方论钞法之必不可行,则此(指王鎏所说的行钞‘大利’)皆不足论。”许梿则说:“盖以纸为必可代银,则事事见为利,以纸为必不可代银,则事事见为弊也。”[1]247-248这里的“钞以代钱”、纸“可代银”,都是指不兑现纸币,也是许楣、许梿所坚决否定的一种货币形态。他们还把这种货币形态称作“以纸代钱”,而把与之相反的可兑现纸币称作“以纸取钱”,并根据他们所抱有的金属主义货币观点,对王鎏钞法主张的理论实质和严重危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许楣说:“钞者,纸而已矣,以纸取钱,非以纸代钱也。以钱代钱,此宋、金、元沿流之弊,而非钞法之初意也。今有创议者(指王鎏)焉,取其弊法,奉为良法,而其为法也,则又宋、金、元弊法之所无有,而反以为宋、金、元良法之无有……夫以纸取钱,而至于负民之钱,此宋、金、元弊法之所有也。以纸代钱,而至欲尽易天下百姓之财,此宋、金、元弊法之所无有也。……夫纸之于银,其贵贱之相去也远矣,人之爱银与其爱纸,其相去也又远矣。千万之纸而易以一星之银,则笑而不与,千万之银而易以一束之纸,则欣然与之,岂其明于爱纸而昧于爱银也?不知爱银之甚于爱纸,而欲以其所甚贱,易其所甚贵,且欲以其贱而少者易其贵而多者,乃曰:如是则天下皆争以银来易钞。呜呼,吾不知其何以来易也!”[1]234-235又说:“宜其视金、银、铜举无足以敌纸者,而锐意行钞。夫天生五金,各有定品,银且不可以代金,而谓纸可以代钱乎?弗思耳矣!”[1]248可以看出,许楣主要是从货币的商品特性出发,来强调银和纸是两种固有价值相去甚远的商品,所以纸不可能取代白银的货币地位,进而批评王鎏“以纸代钱”的钞法根本行不通。这虽然是金属货币论者的观点,但是,在提出这种观点的同时,又正确地指出了王鎏钞法主张的理论实质是要滥发纸币搜刮民财以满足专制政府的财政需要,所以他的这种观点又具有维护人民利益的进步意义。更值得肯定的是,许楣不但正确地指出了王鎏钞法主张的理论实质,还和兄长许梿一起对王鎏为推行钞法而捏造的种种谎言和谬论进行了无情的驳斥和抨击,从而清楚地告诉人们,这些谎言和谬论其实不是王鎏所标榜的利国利民的“良法”,而是祸国害民的“弊法”。下面举其要者分述之。[1]242-260
王鎏说:“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布之于下,则遵国家之体统……”许楣驳斥说:“即尽收其银,又悉禁其票,绝天下之利源,而垄断于上,何体统之有?”
王鎏说:“民间多用钱票,会票,每遇钱庄歇闭,全归无用,行钞则绝钱庄之亏空……”许楣反驳说:“钱庄取富户什百千万之银,而其终悉化为纸,则为亏空。国家取百姓百千万亿之银,而其始即化为纸,独非亏空耶?”许梿则抨击说:“钱庄之失业,犹可言也,贫民抱空票而妇子愁叹,不可言矣!”
王鎏说:“国赋一皆收钞,则无火耗之加派……”许楣抨击说,这等于是国家用通货膨胀的手段于无形中向人民收税,“钞可当钱,则岂但无火耗之加派而已,造百万即千万,造千万,虽尽蠲天下之赋可矣,如不能何!”
王鎏说:“钞直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则去民心之诈伪……”许楣反驳说:“前代之钞直,未尝不一定也,商贾犹今之商贾也,然物重钞轻,史不绝书,非低昂而何?”许梿也指出:“今商贾用银一两只是以两,用钱一千是一千。银钱互易,乃见低昂,钞文一贯亦只是一贯,然能令商贾之必当千钱乎?”他们其实是否定了王鎏的国家权力决定货币价值的名目主义观点。
王鎏说:“天下有银若干,悉来以钞,则供器皿之鼓铸……”许楣批驳说:“恭俭之世,所不足非器皿也,安用以银为器皿,安用取百姓家百千万亿之银以为器皿哉!”
王鎏说:“富家间以土窖藏银,历久不用,一闻变法,悉出以钞,则去壅滞之恶习……”许楣反驳说:“西北窖银吾不知,东南则无矣。设果有之,则历久不用之银,彼方以不用为用,又何为而易钞?”许梿则补充说:“非特不易而已,又将其不窖者而窖之。盖以之取息于钱庄,则虑其没银而还钞,以之居货,则虑官吏之强以钞市也。”
王鎏说:“造钞约已足天下之用,则当停止,俟二三十年之后,再行添造,仍如旧式,不改法也。”对于王鎏这一虚伪的说法,许楣通过揭示历史上专制政府滥发纸币和财政赤字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作了精辟的批驳。他说:“宋、金、元之钞,未尝不欲足用而止也,而卒至增造无亿者,能足天下之用,而不能足国家之用故也。……势不得不于常赋之外,诛求于民,而行钞之世,则诛求之外,惟以增钞为事。然不增则国用不足,增之则天下之钞固以足用,而多出则钞轻而国用仍不足。”
王鎏说:“以钞与大钱发钱庄,即禁其私出会票钱票,如领钞及大钱满一万贯者,半年之后,核其换银若干,予以一分之利,止手银九千贯之数,又以一分之利予百姓,止收八千贯之数。”许楣一针见血地抨击说:“钞之罔民始此矣……禁票而行钞,则钱庄收存豪商大贾之银,皆不复与还银而直还钞……还钞,则累累之银,国家取其八,钱庄取其二,而豪商大贾,虽有百万之银,一朝悉化为纸,非罔民而何?”许梿则补充说:“行钞纸令一下,则富民火速以催还银,钱庄迁延以待还钞,必然之势。”
王鎏说:“使民以银易钞,及加以一分之利,以钞完纳粮税,又加以一分之利,使陡获二分之利也,谁不以银易钞。”许楣驳斥说:“徒令(富室)巨万之银,悉化为纸,谁肯以银以钞哉?”许梿也驳斥说:“完粮百两而获二分之利,不过少完银二十两耳,在富室所得亦甚微矣。设以此二十两易钞,则二分之利,亦化为纸。”
王鎏说:“凡钱粮关税,悉皆收钞,一贯以下悉征钱。”许楣认为这是劫贫济富的坏办法。他说:“贫民钱粮满贯者少,则利在大户,胥吏地保收贫民之钱易银买钞以输官,则利在胥吏地保。国家岁入什一分损其三,而贫民曾未得其一毫也。”许梿则进一步阐述说:“正使满贯,所获亦无几耳。议者(指王鎏)屡以二分之利为言,曾未计及此。”
王鎏说:“钞各分省,通衢大邑,设立官局,民以他省钞至者,验明换本省钞行用。”这显然会割裂全国货币的统一,也会严重阻碍市场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许楣直指其要害说:“是困天下之行旅也。”许梿则抨击说:“设立官局,则局中人皆为在官人役,其势如虎,民以他省钞至,不换则不可用,换则刁难勒索,控官所费愈大,不受其鱼肉不止矣。”
王鎏说:“行钞之初,官俸悉加一倍,本俸暂予以银,加俸悉给以钞”。王鎏批评说,这会造成“官有钞俸,将强民以必用”的后果,“其势必至于罢市”,还会使官乘机敲诈“富户”。所以,“钞之罔民自禁票始,钞之厉民自增俸始。”
王鎏说:“行钞之利,取之天地者也,故利无穷而君操其权。”许楣驳斥说:“君操其权,而民受其害……”
王鎏说:“百姓家有亿万之银,国家造钞以易之,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这是一种欺民之论,事实正好与之相反,所以许楣驳斥说,“是以钞为易银之本耳,何尝以银为用钞之本。”
王鎏说:“宋孝宗以金帛易楮币藏于内库,一时楮币重于黄金。”许楣反驳说:“金帛取之于民,楮币官所自有,孝宗何不以楮币易金帛,而以金帛易楮币?楮币重于黄金,民间何不宝藏楮币,而甘易金帛也?”许梿也反驳说:“楮币而至于收,不待辞费耳知其轻矣。”
王鎏还说:“论者谓金章宗时,以万贯老钞易一饼,妄言行钞则物价腾踊,不知物价之腾踊,原不关于行钞。汉董卓之乱,五十万钱易米一石,石季龙时,金一斤易米一斗,此皆因米极少,非关用钱与金之故。”这是王鎏为否认滥发纸币必然导致物价飞涨的事实而进行的诡辩。许楣洞悉这一点,所以他一分为二地反驳道:“谓行钞而物价腾踊,此论者不善立说之过。夫以万贯老钞易一饼,非饼之贵,乃老钞之贱耳。董、石之乱,则诚米贵而非钱与金之贱也。”
综上所述,许楣、许梿主要运用金属主义货币观点猛烈批判了王鎏名目主义钞法主张的理论实质和严重危害。他们所坚持的金属主义货币观点虽然和王鎏的名目主义钞法主张一样,都不是科学的货币理论,但由于他们运用这种货币观点正确揭示出后者的理论实质是帮助专制政府利用滥发纸币的伎俩掠夺民财,并对后者可能造成的种种恶果进行了酣畅淋漓的驳斥,所以其在实践层面上的意义与价值是积极的:既如实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商人阶层的利益诉求,又较好地顺应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许楣、许梿的金属主义货币观点在理论上也不是全然错误的,其中也含有少许合理的成分。
三、白银外流危机
这里所说的白银外流危机,特指鸦片战争前后以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铜)贱愈演愈烈为标志的货币金融危机。这一危机主要是由于英国对中国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而形成的,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而且严重侵蚀了清政府的财政来源和统治基础,进而引起了很多朝野人士的关注和讨论。许楣、许梿在《钞币论》中也对白银外流危机进行了深刻的议论,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根治白银外流危机,而是为了否定王鎏的钞法(发行不兑现纸币)主张。
白银外流的根源是鸦片贸易,所以王鎏主张“用钞”禁烟。他说:“海船载鸦片烟土,每岁私易中国银累千万以去,用钞则必将无所利而自止,则除鸦片之贻祸(白银亦不外流)……”许楣反驳说:“使用钞而果可废银,则鸦片之贻祸方大。何也?用钞而废银,则银为中国无用之物,载鸦片以易中国无用之物,中国之民,有不推以与之者乎?且鸦片之来,由于中国之民乐于吸食以自祸,而彼得贻之耳。不能禁乐祸之人,安能除贻祸之本。”许梿则概括其意说:“此所谓驱银出洋矣。”[1]243应当说,许楣、许梿在这里正确揭示了王鎏“用钞”禁烟观点的荒唐之处。因为禁烟成功与否,只和能否清除贩卖、吸食鸦片者有关,而和是否用钞无关;况且,在国家废银用钞的情况下,人民不敢私藏白银,而钞票又不断贬值,于是必定有不法之人大量走私白银出海牟利,结果白银反而会加速外流。不过,许楣、许梿为反驳王鎏“用钞”禁烟的谬论而认为“用钞”之后白银就是无用之物的观点,却与事实不符。
鸦片贸易导致了白银外流,白银外流又导致了银贵钱贱。王鎏既主张“用钞”禁烟,当然也就主张“用钞”来平抑银价。对于王鎏的这一观点,许楣主要运用他的“以银为币”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进行了坚决的抨击。他说:“(用银)至我朝乾隆、嘉庆之间盛极矣。……银之流布于天下者,已足天下之用,而民间地丁皆征钱,官为易银上库,无如亭林用银之害。向使无漏卮之耗,虽长此不废可也。至于今而数千年之蓄积,半耗于漏卮矣,而其势方未有所止。然而又欲用钞废银,则银不可废,钞更为厉民之阶。何者?漏卮岁数千万,国家税额亦数千万,民间以漏卮故,苦银日贵,而又欲以钞收银壅之于上,则银益骤贵。而山僻州县,昔之以银完粮者,亭林谓民至丰年卖其妻子,名曰人市,今幸官收其钱,易银上库。一旦征其纳钞,则民将负钱走通都大邑,易银以易钞,而后输官,吾恐人市之复兴也。”[1]240显然,许楣认为银贵钱贱的原因是白银外流,而不是以银为币,并且银的货币地位是不可“废”的,在这种情况下,“用钞废银”反而会推动银价暴涨,从而严重影响劳动人民的生计。
基于上述认识,许楣不但进一步运用他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断然否定了王鎏利用钞法平抑银价的观点,还通过正确区分“银贵钱贱”和“钱贱银贵”的不同,批评王鎏忽视了银贵钱贱的症结所在,而只是把银贵钱贱当作“行钞”的理由,所以根本于事无补。他说:“然则因其贵而以钞法平之,岂不可也?曰:奚可。银,银也;钞,纸也。然则以疏通钱法平之何如?……由钱贱而银贵者,以疏通钱法平之,由银贵而钱贱者,虽暂平犹当益贵也。钱贱银贵,银贵而钱贱,有以异乎?曰:异。泉府充溢,贯朽尘积,而银不加多,是谓钱贱而银贵。漏卮无极,以万以亿,而钱不加多,是谓银贵而钱贱。夫钱贱而银贵者,病止于钱,收之则瘳矣。银贵而钱贱者,银与钱交病。方收钱以瘳银,旋漏银以病钱,益之一,无裨于损之十。如蓄水然,均是瓮也,一溢一浅,挹其溢以注之浅,则平矣。均是瓮也,一漏一不漏,挹其不漏者以注之漏者,则几何其能平也?曰:此议者(指王鎏)所由欲行钞也,行钞而变其税法则平矣。曰:以钞易银,是犹以尘饭涂羹疗饥渴也。”[1]240-241许楣虽然正确地批评了王鎏利用钞法平抑银价观点的荒谬性,但是他也没能找到平抑银价的可靠办法,而只是郁闷地认为“事又有非变法所能尽”,所以“不能不叹息痛恨于漏卮之始也”。[1]241这种郁闷固然和腐朽的清政府无法制止鸦片贸易和白银外流的时代背景有关,但也是许楣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固有的缺陷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许楣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片面地把白银看作是最理想的货币,因而不容许对之进行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变革。正因为这一点,许楣才对当时的白银外流危机表现出无可奈何的郁闷情绪。其实,从理论上说,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钞法(发行不兑现纸币)的确是解决白银外流危机的好办法,这也为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实行不兑现的法币政策来解决白银外流危机的成功事例所证明。所以,平心而论,王鎏试图利用钞法来治理清政府面对的白银外流危机,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行不通,而且其钞法主张的具体内容错误多多,但他至少在理论上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许楣,则由于其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的羁绊和时代的局限,在谈论白银外流危机时,并没能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他不及王鎏的地方。
除了鸦片贸易之外,来自西方国家的银铸币——洋钱在中国的溢价流通,也是导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白银外流的原因之一,所以当时有人主张禁用洋钱。王鎏为了推销他的钞法主张,则宣传说“百姓便于行钞,洋钱不禁自废,则免外洋之耗蚀”。对于王鎏的这一观点,许楣、许梿也予以了驳斥。许楣说:“外洋之耗蚀,不在于洋钱之来,而在于纹银之去。使中国纹银不出洋,则洋钱亦银也,银入中国,何尝耗蚀。自嘉庆十年后,鸦片烟渐滋,外夷以鸦片易银,还以银铸洋钱入中国贸易,然后有耗蚀之患。近年鸦片银岁漏数千万……而新洋钱来者亦遂少,盖专以鸦片耗蚀纹银矣。而银已将尽,年岁间势必搜刮洋钱,洋钱将不禁自去。中国苦纹银之少,势必销熔洋钱,洋钱将不禁自罄。知洋钱之耗蚀纹银,而不知鸦片之并将耗蚀洋钱也,何待行钞以速之尽哉!”许梿则说:“洋钱乃外夷之制,谓非中国所应行使则可,谓钞之便于洋钱则不可。洋钱径不过寸余,身带二寸之囊,贮洋钱十枚有余,倘贮小钞十贯,每贯长必尺许,阔必五六寸,纸又极厚,就令折叠如洋钱之大,囊腹皤然矣。或谓十贯自有总钞,无须零析,此又不通之论。寻常日用,岂可从10贯起乎?”在此基础上,他又自问自答道:“若是则民间用钱票何也?曰:以票与现钱较,则票为便,且钱票长不过四寸,阔不过三寸,纸又极薄故也。然今之江、浙盛行洋钱之处,即不用钱票,则以票虚而洋钱实也。”[1]242
不难看出,许楣、许梿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鎏“行钞”可免洋钱之害的观点。许楣不过是在批评单纯主张禁用洋钱论者的基础上,强调为免洋钱之害而“行钞”是多此一举,而在反对洋钱在中国流通这一点上,他和王鎏并无不同。许梿也反对洋钱在中国流通,但又以洋钱便于携带、价值确实为理由来反对王鎏的“行钞”主张。这似乎是许梿只看到王鎏钞法设计上的缺陷而产生的误解,但归根到底是他受到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羁绊的结果。其实,只要把不兑现纸币设计得和可兑现的“钱票”一样精巧,并有效稳定它的购买力,它就不仅便于携带,还会比洋钱更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