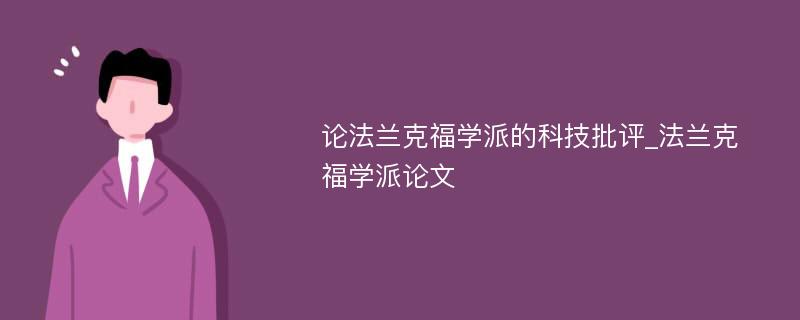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学派论文,科学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加速前进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高度发达的现代科学技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人类所面临的世界图景。更为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审视自然与社会的眼光,甚至重构了人们的整个思维结构。怎样看待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问题,已成为哲学家、社会学家们思考的中心,其立场的差异,形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的两大主潮——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活跃于20~6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人本主义代表之一),对科学技术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认真考察并弄清它生成的缘由及批判理路,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大有裨益的。
一、对作为意识形态之科学技术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论述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把科学技术定性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文中最先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1〕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就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研究,更确切地说,就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他是这样说的,“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了脱离群众而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2〕
法兰克福学派中,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论述最为详细,“实际上,关于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理论,由霍克海默提出,中经马尔库塞,最后到了哈贝马斯那里,才真正体系化了,才引起人们的重大注意。”〔3 〕哈贝马斯用两句话概括了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功能: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论文中明确指出,“技术和科学在今天具有双重职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他继而分析了这种趋势的后果,“我觉得,更为重要的倒是技术作为潜在的意识形态也侵入到了那些不过问政治的群众的意识中,并且还形成了一种合法的努力,这种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奇特效果就是:社会的自我脱离了交往行为的关联系统,脱离了以象征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而为一种科学的模型所代替,同样,在合理行为和适应行为范畴内人的自我物化替代了用文化对社会生活所作的一定自我理解。”〔4〕确实,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其社会职能得到了空前膨胀,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和文化取向,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受到冲击。
哈贝马斯还注意到,“技术统治论”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具体体现。基于这一认识,他把批判“技术统治论”当作批判科学技术的一个中心环节。立足于他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指出,“技术统治论”的危害性主要在于抹煞了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之间的区别,其实质是想用控制自然的方法来控制社会,而这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伤害人的交往行为,压抑人的本性。他说:“这种‘技术统治论’意识伤害了一种根植于我们文化存在的两大基本条件之一的,根植于语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植于由日常语言交往所决定的社会化和个人化形式的旨趣。这种旨趣可用于维护相互理解的主体交往,以及造就没有统治的交往,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使这种实际的旨趣淹没在扩充我们的技术控制权力的旨趣背后。所以,要对新的意识形态作出反思,就必须超越特殊的历史的阶级旨趣的层次,去披露超越正从事于自我构造过程的人类本身的基本旨趣。”〔5〕
很显然,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福祉,倒是为资本主义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提供了条件,科学技术担负起了促使发达工业社会“合法化”的力量源泉,它成功地把实践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哈贝马斯就此敏锐地指出,由于“社会制度的发展是由科学技术进步的逻辑决定的”,所以“正如马尔库塞提出的一个基本命题那样,当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6〕
二、对作为社会控制工具之科学技术的批判
既然科学技术已成了新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不再具有“中立性”,而成为一种控制工具,一种统治手段,全面地走向了反动,法兰克福学派由此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上普遍的统治和压迫形式:总体的技术控制。他们提出“工具合理性”、“工艺合理性”和“技术理性”等概念。基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已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7〕这一事实, 马尔库塞把“技术理性的政治内容”当作了分析发达工业社会的一种理论出发点。
所谓技术的合理性就是以技术进步作为一切合理活动的标准和模型,技术的进步及其理性的扩展,成了操纵大众意识、对人实施控制的有效工具。科学技术和社会操纵合为一体,形成一股强大的控制力量,人们保存自己的私人空间由于技术的进步而遭到侵占,自我深化的多样化过程在工业过程和机械反应的状态下被固定化、单一化,个人只能模仿世界,再也不能对社会提出抗议,技术控制造成的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思想。“合理的技术社会”实为“合理的极权社会”,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进步等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消了个人在创造财富和服务时作出决定的自由爱好和自主的需要。”〔8〕
于是,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在“技术合理性”这个貌似中立的伪装下发展起来的是新型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科学和技术的扩展同时也是社会控制和统治的扩展,科学技术“变成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并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9〕。 在这种条件下,更大的控制自然的能力变成更深的控制人的能力,“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在这个领域内,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它证明,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因此,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10〕
马尔库塞最后的结论就是,“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就是这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扩大的奴役。”〔11〕他悲哀地说,现在“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毫不奇怪,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地区,社会控制已经被潜化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也受到影响,拒绝‘随大流’的思想情绪显得是神经过敏和软弱无力的”〔12〕
技术控制并不诉诸暴力,它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缓缓、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13〕哈贝马斯对此有所警觉,他认为,科学技术力量,作为理性的产物,披上“合理”的外衣,掩饰着劳动和相互作用中的各种不合理和不合法因素,使现代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含糊起来,人们整体的生活实践在不知不觉中被工具性劳动取代了。1971年,哈贝马斯离开法兰克福大学,出任马克斯—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的所长(1971—1981年),研究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条件下的人类生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研究现代社会中因科技进步而出现的一系列涉及到社会伦理和心理生活的问题。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着重分析的是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和异化,在《启蒙辩证法》中,他们说:“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14〕阿多诺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的人与自然界的日益分离和对自然的支配,并不能推动人类的解放,因为这种进步的日益增长是以对社会和心灵压迫为代价的;同时,这也造成了人对自然的异化,世界被归结为它纯粹的量的方面,人变成抽象的物,简单地服从既定的社会秩序,而科技发展只是完成这种统治的工具。阿多诺最后愤然道:“科学与其说是人类进步的忠诚助手,毋宁说是包括了新的人类异化的种子。”〔15〕霍克海默也接着说:“看来,甚至正当技术知识扩大人的思想和活动的范围时,作为个体的人的自主性,他对日益发展的大众操纵机构进行抵抗的能力、想象力、独立的判断,似乎被剥削了,旨在启蒙的技术能力的进步伴随着非人化的过程。”〔16〕
三、对作为社会稳固剂之科学技术的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既然科学技术成了统治阶级的控制工具,那么它必定执行“麻痹批判意识、遏制社会质变”的反动功能,即是说,科学技术成了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无比强大的稳固剂。法兰克福学派指出,无产阶级不但“没有作为革命阶级而行动起来”,反而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
马尔库塞对此有深入的考察,其最有影响的著作《单向度的人》就在力图揭示,先进工业社会的技术使那些在以前的社会制度中发出不满或提出反抗的人们得到协调,从而消灭了斗争。马尔库塞首先指出,科学技术进步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同化起来,从而模糊了阶级界限。他说,现在工人和他的老板可以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他的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黑人也拥有高级轿车,他们还阅读同样的报纸。人人都在分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彼此好像都是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出来反抗?很显然,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创造出的“崭新”的生活方式,满足了那些可能会反抗的人的需要,从而促进了人们与现存制度的统一。而且,由于科技进步带来了物质丰富,人和物的关系颠倒了,人们把追求外在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生活的全部内容,好像就是为了满足物质欲望的商品而生活。“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17〕
其次,马尔库塞认为,表面上富裕的“消费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极端压迫”的社会。经济繁荣挽救并巩固了现制度,发达工业社会在财政上变得更加富裕,在生产上变得更有竞争力,同时却保持着压迫性。撕破罩在科学技术头上的那层温存脉脉的面纱,露出的是它的狰狞面目。他说:“技术的进步和高档商品的大量涌入产生和再产生了一个不费力的、快乐的、满足和舒适的世界图像,……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充满了失败、不幸和压抑。”〔18〕
最后,科学技术使人丧失了自我,批判和反抗的意识荡然无存。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没有成为解放的力量,反而消弭了人们的斗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恰恰正是革命潜力降低到了最低水平。他着重分析了在这种社会境况下人的处境,并对现代技术崇拜的状况和后果怀有恐惧,因为技术崇拜造成了一种根本不关心人的价值和需求的社会形式,“今天这一私人空间已被技术现实侵占和剥削,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占据个人的全部身心,工业心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19〕霍克海默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表示了同样的忧虑,“今天向乌托邦迈进的障碍首先是社会权力的强大机器同原子化了的群众之间的比重失调。”〔20〕
种种迹象表明,科学技术成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抑制大众反抗思想的最有效工具,故而,统治阶级对科学技术总是钟爱有加。“十分清楚,技术的进步和对技术进步的投资,是发达工业社会借以巩固其尚不稳定的现状的持续扩张的主要动力,这种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制度的每个部分。”〔21〕
四、对科学技术入侵文化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最后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的另一产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因为如果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也就不可能大规模地生产、复制、传播文化产品,也就不可能产生“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是以工业生产为显著标志的,它的物质前提与载体,如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都是现代科技的产物,“技术化”是文化工业的特征之一。
技术侵入文化,造成文化的人文意义和价值的丧失。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一般商品的生产已没有什么区别,“文化工业的技术,只不过用于标准化和系列生产,而放弃了对作品的逻辑与社会体系的区别。”〔22〕同时,技术也模糊了现实与艺术的差别,“生产技术越是密切地和完善地重复经验的对象,人们今天就越是容易产生错觉,认为外面的世界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情况的不断延长。”〔23〕很明显,科技进步与人类审美生活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文化工业产品由于在技术上的可复制性,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艺术作品的个人风格,一切作品皆沦为商品,它以技术作为后盾,泛滥成灾。
更为法兰克福学派警觉的,是文化工业也同样实行社会控制功能和对人的异化。阿多诺觉得个人和技术社会的协调已经达到如此规模,以致绝大多数人都按照僵化的先入为主的范畴来思想。就流行音乐来说,他认为社会的一般趋势,它的强力推行一律性,已经剥夺了许多个人使这样的音乐带有他们自己感情的能力。马尔库塞认为,富裕社会凭借大众传播媒介,如广播、电影、电视、广告等现代科技产物,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挤进人们的内心深处,消灭了从思想上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文化。所谓“文化工业”实际上就是技术理性与消费至上原则相结合的产物,他说:“现在,艺术远离社会、冒犯社会、指控社会的特征已被消除。艺术的异化已经成为同上演艺术的新型剧院和音乐厅建筑一样是以使用的观点来设计的……文化中心变成了商业中心、市政中心或政府中心的适当场所……现在差不多人人都可以随时获得优雅的艺术享受,只要扭动收音机的旋纽或者步入他所熟悉的杂货铺就能实现这一点,但在这种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却成了改造他们思想的文化机器的零件。”〔24〕
总之,科学技术产生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又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服务。文化工业关心的不是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批判职能,而是作品的经济效益或“上座率”,它不断地加强人们想要逃避的社会现存秩序,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稳定生产大量的“社会水泥”。
五、背景与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不是一个偶然或孤立的现象,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在20世纪,发达工业社会已被定义为技术的社会,技术已远非一般的工具现象,它首先是一种能改变一切生活领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其形式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技术问题就是西方的文明问题。”〔25〕显然,科学技术已上升为哲学的重要课题,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关捩点,如人所言:“在当代哲学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本主义哲学家、社会批判家不是从对科学技术——尤其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建造其哲学的。”〔26〕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则典型地代表了现代人本主义对科技理性的绝望与幻灭。马尔库塞曾提出深深的疑问:“西方文明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一方面是技术的高度进步,另一方面则是人性的倒退:非人化、残酷无情、作为审讯的‘正常’手段的严刑拷打复兴,原子能的破坏性的发展,生物圈的污染等等,这些问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27〕哈贝马斯也说出了自己的无奈,“生态问题,比起70年代早期鼓舞人心的预测来看,它将会在更长的时间内继续恶化,至于如何评判它们,我一时还感到无能为力。”〔28〕
法兰克福学派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看到的是技术理性的扩张,人的主体地位的退缩,统治阶级实行新的控制与统治,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彰显得使它的积极一面已无足轻重;科技文明的历史进程与人类精神的审美构想在深层的尖锐矛盾,已几乎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这一切决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态度。60、7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反科技运动,说明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批判代表了社会的一般潮流,并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科技进步对人心灵的挤压已使现代人焦头烂额,所以“在永无满足的驱动下享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所带来的福利的同时,又以最不堪入耳的诅咒式批判历数科学技术之罪状”,成了正在“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精神矛盾的现代人的活生生的心态之一”〔29〕。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人类对于科学技术而言,是否就犹如一个巫婆或术士无力驾驭自己呼唤出来的魔力呢?今天,整个世界面临着气候变暖、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核武器威胁等危机,这些还只是外在的;另一方面,现代人由于科技进步而带来的身心危机却是空前的,浮躁、烦畏、焦虑、不安等几乎成了现时代最流行的文明病。19世纪末,尼采在工业社会的前夜看到了上帝的死亡,他为此欢欣鼓舞,因为他相信人类正在从神的控制中挣脱出来,而成为超人。可是,就在掌握了技术的人类果真相信自我意志无往而不胜的时候,他们却陷入了另一种控制——人类亲手编织出的技术之网的控制之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虽然成功地解决了经济领域里的诸多问题,可在解决关于人的问题时却是日趋失败的,人类在工业体系中“正面临着失去他活生生的人的本性的危险”。因此,对于科学技术这个“雅努斯”(两面神),人们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对科学技术非常关注的,而且他们对技术进步采取的是一种乐观的态度,马克思称科学是“一本打开了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30〕,并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的力量”〔31〕。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站在全人类的整个历史的高度来看问题,毕竟,人类每迈出一步都依靠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今天,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科技兴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视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而要以西方为鉴,警惕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注释:
〔1〕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2〕马尔库塞:《否定:批判理论文集》,波士顿,1969年版, 第223页。
〔3〕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 重庆出版社,第242页。
〔4〕〔6〕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载《哲学译丛》,1978年第6斯。
〔5〕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波士顿,1970年第6期。
〔7〕〔9〕〔10〕〔12〕〔13〕〔17〕〔19〕〔2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18、142、10、 3、10、11、10页。
〔8〕〔11〕〔18〕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82、94页。
〔11〕〔22〕〔23〕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13、118页。
〔15〕马木·杰:《阿多诺》,(台)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0页。
〔16〕霍克海默:《理性的失色》前言,纽约,1974年。
〔20〕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法兰克福,1967年,第91页。
〔25〕塞雷佐埃:《美洲的技术哲学》,载《哲学译丛》,1978年第4期。
〔26〕李小兵:《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27〕麦基编:《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0页。
〔28〕包亚明主编:《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29〕高宣扬:《哈伯玛斯论》前言,(台)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