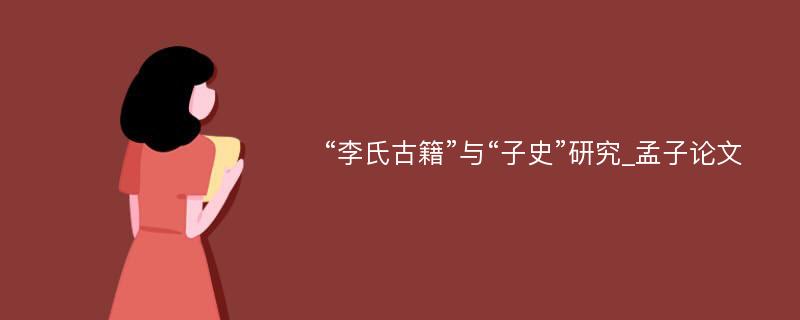
《礼》古记与子思之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思论文,之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3—0005—07
一 从所谓“《礼古经》”谈起
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艺文志》: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十七]篇。后氏,戴氏。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
《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
《明堂阴阳说》五篇。
……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学官。《礼古经》者,出於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①
所谓《礼古经》之说,即源于此。以上的点读,是有一些问题的,下文将有讨论。如学者们早已谈过,“礼古经”当点作“《礼》古经”,是《礼》经的古文本。② 钱玄先生曾详列《汉书》所记《礼》古经的来历,除《艺文志》外,又见于《刘歆传》、《鲁恭王传》、《河间献王传》等。③ 然而,钱先生以《礼》古经仅出于古淹中及孔壁④,恐失之过简。洪业先生纵考典籍所记,不仅认为淹中之地不可确考、孔壁出书事近子虚,而且《礼》古经迄东汉一代未见请立学官,故以《礼》古经“未尝尽亡于东汉,殆为‘今礼’学者所分辑于所传授之经记中耳。”⑤ 实际上,《礼》古经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正确认识《礼》古经问题,对于子思之学的考察有重要的意义。
《汉书·艺文志》记“《礼》古经五十六卷”,与“《经》十七篇”并存,事无可疑。至于《礼》古经的来源,则有不同的说法。《论衡·佚文》:“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闓(闻)弦歌之声,惧复封涂。”⑥ 《鲁恭王传》:“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⑦ 《河间献王传》:“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说传记,七十子之徒所论。”⑧ 孔壁说、河间献王说,加上《汉书·艺文志》的古淹中说,《礼》古经的来源说约有三种。目前所见的材料,尚不足以证诸说之伪;相反,根据近年考古发掘“古文”类简帛文献的情况,信其真却是有理由的。
在这些传统文献中,有两条值得注意,一是《汉书·艺文志》,一是《河间献王传》。
前已述及,上引《汉书·艺文志》是有不同的点读的。中华书局点校本:
《礼古经》者,出於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⑨
这是从宋人刘敞以“及孔氏”从上句读、改“学七十篇”为“与十七篇”。⑩ 以此为依据,清人黄以周进而改“及孔氏”为“及后氏”从下句读,即:(11) 《礼古经》者,出於鲁淹中,及后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进一步合于《汉书·艺文志》的描述及传统后氏传《礼》的说法。然而,据武英殿本,《汉书·艺文志》此节应读如下:
《礼》古经者,出於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12)
这是古书传本的原貌,是把《礼》古经与孔门之学联系起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河间献王传》也是如此:(13)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说传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明确指出河间献王所得先秦古文《礼》、《礼记》等皆“经说传记”,是孔子七十子弟子之作。这里,武英殿本《汉书·艺文志》的孔门之学说与《河间献王传》的“经说传记”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文体特征上,“经说传记”的文体,与我们在郭店楚墓所出及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战国楚竹书中所见的材料是相合的;在思想内容上,孔门之学与七十子之徒所论,也与我们在郭店与上博所见材料的内容相符。
按我们今天的理解,《礼》自然属于“经”、《礼记》属于“说、传、记”一类,但在实际上,古人在《礼》与《礼记》二名的使用上,还是颇为混乱的——不仅在内容上,《礼》经中混有记、说,《礼记》中杂有经文,而且在书名上,《礼》与《礼记》也见混用。
《孔子世家》:(14)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子。
这里的“《礼记》”说的就是《礼》的经,而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小戴《礼记》。郑玄也有称《礼》为《礼记》之例。《诗·召南·采蘩》郑笺:“《礼记》:‘主妇髲髢。’”(15) 所引文字实出于《礼·少牢馈食礼》而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小戴《礼记》。郭璞引《有司》经文也称“《礼记》”。《尔雅·释言》郭注:“《礼记》曰:‘厞用席。’”(16) 宋人未明于此,而以郭注为误:“云《礼记》者,误也。”(17) 《三礼通论》并有如下一节:(18)
《后汉书·卢植传》:“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时多回冗。……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此言刻熹平石经事。熹平石经于礼仅有《仪礼》,而这里称《礼记》。《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引《洛阳记》:“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则晋人所见也是名《礼记》。此《礼记》不是四十九篇之小戴《礼记》,而是指今之《仪礼》。
皆用《礼记》称《礼》经。所以,《孔子世家》所说的《礼记》就是《礼》、《后汉书》所称《礼记》也有指《礼》之例,都是没有问题的。
同样,用《礼》指称《礼记》的例子,也见于古书。如《礼记·问丧》引:“《礼》曰:童子不缌,唯当室缌”,《通典》卷七十二引《石渠议奏》:“经云:宗子孤为殇”,均非《礼》经之文,而是见于《礼记·丧服记》,但都被称作《礼》。(19) 沈文倬先生并考证其原因若干,兹录其一以见其义:(20)
(《礼》经)十七篇中四篇无“记”,但与有“记”之篇相对照,有些章节不像是经文,如《士相见礼》篇末的进言之法节、侍坐于君子之法节、称谓及执贽之容节,显属记文,因其篇无记字而被当作经文了。
也就是说,有关《礼》经的说、记,杂入经文之后,也见称其为《礼》经之例。这与武威汉简《仪礼》以传入经的现象颇为类似。(21)
如果说近年出土的战国楚墓竹简多与先秦的《礼》类文献有关,那么《礼》类经、传、说、记的这种文献特点,就是我们在考察时应该予以注意的方面。目前所知的战国楚墓竹简中,尚未见古文《礼》经的材料,但古文《礼》“记”的材料已经多有所出,《缁衣》一篇即有不同的本子。重读《汉书·艺文志》可以看见,《汉书·艺文志》在提到《礼》古“经”的同时,还提到“记”,所谓: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这里,《汉书·艺文志》并未明确百三十一篇“记”是古文还是今文。从前引《河间献王传》来看,献王所得《礼》“记”皆先秦古文。如此,即便这百三十一篇“记”是今文,也是去古未远的今文。所以,我们不妨循“《礼》古经”之例,称之“《礼》古记”,以与“《礼》古经”及近年出土的战国古文楚简相关联。应该看到,“《礼》古记”的重要性长期为“《礼》古经”问题所掩,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关注。今天讨论子思之学,“《礼》古记”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切入点。
二《礼》古记、《礼记》与《子思子》
从“《礼》古记”问题切入子思之学的考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李学勤先生通过对传世文献与近年所出考古文献的考证,指出“《中庸》一篇的确是子思的作品”,“《坊记》、《表记》、《缁衣》颇可能也出于子思,至多是其门人所辑成。”(22) 如所周知,《中庸》等四篇在传世文献中俱收入《礼记》(23),它们与《礼》古记的关系,也就不难推知了。从《礼》古记入手,也就是从先秦时期子思作品的流传、汉代以降传世文献中子思作品的来源的角度,来认识与考察子思的作品。
子思的作品,《汉志·诸子略》记有《子思》二十三篇,注:“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24) 《隋书·经籍志》记《子思子》七卷,(25) 《旧唐书·经籍志》作八卷,(26) 《新唐书·艺文志》复作七卷。(27)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思子》七卷,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顾实据此指其书北宋时尚存。(28) 梁人沈约云:
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29)
如果晁公武时《子思子》尚存,沈约所言《子思子》,当据亲见。当然,《缁衣》又有公孙尼子作品一说。(30) 《汉书·艺文志》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原注:“七十子之弟子”,列于《魏文侯》、《李克》之后,《孟子》、《孙卿子》之前。(31) 公孙尼子与子思子关系密切:传为公孙尼子所作的《乐记》,其“天高地下”一节即被朱熹认为是子思之作,所谓“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辞”(32);公孙尼子本人也被学者认为属于思、孟学派。(33)
《中庸》等四篇被收入今本《礼记》,而《缁衣》一篇目前至少已有两种不同的战国楚简本出土。郭店所出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本《缁衣》都没有今本《缁衣》的第一章,即“子言之曰”章。今本《缁衣》共24章,除首章始以“子言之曰”外,其余23章均始以“子曰”。孔颖达:“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曰’,余二十三章皆云‘子曰’,以篇首宜异故也。”(34) 认为首章应该用“子言之曰”区别于“子曰”。郭店《缁衣》出土之后,有学者根据简本无“子言之曰”,以孔疏为非。其实孔疏是正确的。“子言之曰”应该是《缁衣》辑入《礼记》时改编的痕迹。
《礼记》中,沈约认为出于《子思子》的四篇,除《中庸》外,《坊记》、《表记》、《缁衣》三篇文体基本相似。今本《礼记》中,《坊记》、《表记》、《缁衣》三篇的首章,皆以“子言之”开篇。《坊记》39章,首章始以“子言之”,其余38章皆始以“子云”(35);《表记》55章,除首章始以“子言之”之外,章首始以“子言之”者七见(36),孔颖达:“称‘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发端起义。事之头首,记者详之,故称‘子言之’。若于‘子言之’下,更广开其事,或曲说其理,则直称‘子曰’。今检上下体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37) 在这一组文献中,首章皆以“子言之”开篇,不应是偶然的巧合。《坊记》的首章言“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38),显然是全篇的总论。《表记》以“子言之”章发端起义,分全篇为数层,也基本上准确。
《缁衣》与《坊记》、《表记》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记皆属为君之道。所以,今本《缁衣》首章“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在内容上是与《缁衣》全篇的内容相合的。但此章本来并非《缁衣》之文。理由有三:第一,此章与《缁衣》全篇的体例不合。从郭店楚简《缁衣》来看,《缁衣》各章均始于孔子之说,终于《诗》、《书》的引证;今本《缁衣》也基本上如此。而此章仅有孔子之说,不引《诗》、《书》,不合全篇之例。第二,《缁衣》的篇名与《坊记》、《表记》不同,不是与全篇的篇义有关,而是取篇中文句的一词。这种情形,古书的通例通常是取全篇首句中的一词。今本《缁衣》的篇名,不出于首章的首句,而出于次章的首句,不合古书的通例。第三,简本《缁衣》在郭店楚简中是极完整的一篇,与上博所藏楚简《缁衣》基本相同,篇末记全篇章数“二十又三”,全篇无今本的“子言之”章。
按此章可能出于《表记》之文。前已述及,今本《表记》中“子言之”凡八见,多为发端起义,提要各层大义之文。如学者早已指出,这种体例未能通贯全篇:“今按‘后世虽有作者’一章,结前章‘凯弟君子’之义,非发端之辞,而称‘子言之曰’。‘君子不以辞尽人’一章,与前数章不相蒙,乃更端之辞,而称‘子曰’。”(39) 通读全篇可见,《表记》以“子言之”分层当为可信之说,但《表记》的分层确有错乱之处,应系早期传写错简所致。今本《缁衣》首章“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与《表记》论三代之道“赏爵、刑罚穷矣”(40) 诸论或有相关之处,可能原出于《表记》。《表记》各章所论,大多不引《诗》、《书》;郭店楚简《缁衣》,每章必引《诗》或《书》,而今本《缁衣》中不见于郭店简本的诸章,多亦不引《诗》、《书》,与《表记》的体例有相合之处,应是继续考察的思路。
此章不会出于《坊记》。《坊记》中,“子言之”仅一例,见于全篇之首,总括全篇大义。也许正因为如此,加之《表记》中的“子言之”章多有提纲挈领之义,这也许是《礼记》的编者在《缁衣》前依例加上一个“子言之”章的原因。
今本《缁衣》的此章一定是后加的。编加“子言之”章时,《缁衣》的篇名应该已经确定,否则编者当依《坊记》、《表记》之例为《缁衣》拟名“X记”,而不是取首句中的一词;而“子言之”章按例又必须编为首章,所以用以命名的“缁衣”章只能屈居次章。可见,孔颖达说《缁衣》“子言之”章“以篇首宜异故也”,不误。孔说“篇首宜异”,也合古书之例。《坊记》所见,即传世文献之例;郭店楚简《缁衣》23章,后22章皆始以“子曰”,独首章始以“夫子曰”别于“子曰”,系见于出土文献之例。(41)
孔疏“子言之”之说使我们相信,从文献特征来看,《坊记》、《表记》、《缁衣》是被当作相互关联的一组文献同时辑入《礼记》的。如果它们不属子思的作品,它们与子思之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文选》李善注引《子思子》见于《缁衣》(42),即是明证。《中庸》等四篇系被辑入《礼记》传世,战国楚墓出土了至少两本古文《缁衣》,可见《礼》古文“记”、《礼记》与《子思》的关系;从以上讨论可见,作为“《礼》古记”的《缁衣》,在被辑入《礼记》时,已经受到后人的改窜。
现在谈及《礼记》如果不加特别说明,通常指的是小戴《礼记》。然而,古人所谓《礼记》,往往包括了小戴《礼记》与大戴《礼记》。大、小戴《礼记》之说,见于郑玄《六艺论》:(43)
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隋志》以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俱来自《礼》古记: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经,合二百十四篇。戴圣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44)
这种小戴删大戴的说法,见于《经典释文·叙录》所引陈邵《周礼论序》等。《初学记》也有:
……后苍传于梁国戴德及德从子圣。乃删后氏《礼》为八十五篇,名大戴《礼》;圣又删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其后,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凡四十九篇,则今之《礼记》也。(45) 洪业先生《礼记引得序》已力辨其非(46),学者多从其说。(47) 然而,小戴删大戴说之所以流行,当有其原因。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此说符合大、小戴《礼记》文献来源复杂、历经编删、与篇数逾百的《礼》古记直接有关的史实。
大、小戴传所谓今文《礼》,这是否影响其与《礼》古记的关系呢?王国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
……献王所得《礼记》盖即《别录》之古文《记》。是大、小戴《记》,本出古文。《史记》以《五帝德》、《帝系姓》、《孔子弟子籍》为古文,亦其一证也。但其本不出孔氏而出于河间,后经大、小戴二氏而为今文家之学,后世遂鲜有知其本为古文者矣。(48)
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也认为大、小戴《礼记》是戴德、戴圣分辑《汉书·艺文志》所说的《礼古经》之《记》百三十篇而成:
郑康成《六艺论》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此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传而言。《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之数。……《记》本七十子之徒所作,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河间献王得之,大、小戴各传其学,郑氏《六艺论》言之当矣。(49)
钱氏之说因未说明大、小戴《礼记》中的复篇问题,所以每为学者所疑。徐复观先生对此已有明辨。(50) 李学勤先生举《经典释文·叙录》与《汉书·艺文志》所记《记》篇数的不同,说明:
《经典释文·叙录》引《别录》曾说古文《记》有二百四篇,《汉书·艺文志》为什么只作一百三十一篇?看来《汉书·艺文志》只是将大小戴《记》合计在一起,也没有仔细考虑其间复重的问题。因此,有学者怀疑《汉书·艺文志》何以未见二戴《礼记》,也就有了答案。(51)
也就是说,《汉书·艺文志》实际上还是著录了大、小戴《礼记》的,见于“《记》百三十一篇”。
从目前所见的考古材料来看,认为《礼记》出自《礼》古记是有理由的。现以今本《礼记》中与子思有关的几篇为例,看郭店楚墓所出古文儒家类说记与《礼记》相关的几个例子。今本《礼记·缁衣》与楚简本《缁衣》的问题,前文已有讨论。然《礼记·缁衣》又有:“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郭店楚简《尊德义》:“下之事上也,不从其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者。”除“令”、“命”相通与几个虚字而外,两者完全相同。又如,《中庸》:“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楚简《性自命出》:“修身近至仁。”两者关系紧密。《表记》:“情疏而貌亲。”楚简《忠信之道》有:“心疏而貌亲。”虽“心”、“情”二字不同,但郭店楚简与《表记》的思想、文字显然是一致的。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的一节,刘乐贤先生读作:“君子衽席之上,让而受幼(52);朝廷之位,让而处贱。”在《坊记》中,相关的文字作:“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两者虽有不同,但它们文字及意义之间的文献关联,也是不言而喻的,说明了楚简古文儒家说记类文献与今本《礼记》之间的关系。
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上博所藏战国楚简《诗论》的结构,有似《礼记·中庸》。(53) 其实不止是楚简《诗论》,郭店所出与上博所藏的战国楚简,不仅多有见于今本《礼记》的篇章与文字,而且多篇文字的内容与形式与今本《礼记》相合。陈来先生甚至建议称郭店楚简为“荆门礼记”。(54) 我们认为,就子思之学的考察而言,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在出土文献中见到传为子思的文字,而且在于我们可以见到子思之学的文献传流在先秦时期的文献形式。这种文献形式不仅解释了汉代以降传为子思作品的文献来源,而且展示了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各家儒学作品流传的形式与常例。也就是说,郭店楚墓竹简与上博所藏的战国楚竹书等,其中反映早期儒学内容的文字,“本为先秦儒家著作单篇”(55);换言之,先秦早期儒家的作品,战国时期多以目前所见出土楚简之类的单篇形式流传;后来题作《子思》或《子思子》的子思的作品,也不会例外。
三 子思之学的文献特征
子思之学的存在是有文献依据的。《韩非子·显学》: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56)
韩非子说“儒分为八”,“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各为其一,一方面可见子思之学是有影响的,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子思之学与孟子之学至少在韩非子时,尚未“统一”为一家之学。合论思、孟之学的内容与特点,早期的文献有《荀子·非十二子》,所谓:
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57)
至于这一段中有关思、孟之学的解释,其实还是颇有分歧的,当另文讨论。(58) 这里我们仅从学派研究的角度,认识一下子思之学与所谓思、孟学派的一些基本问题。
从韩、荀之说可见,子思之学的存在没有什么疑问。但应该如何从学派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呢?或者说,子思之学后来有没有发展成思、孟学派呢?
一家学说能否发展成为一个学派,要看它是否具备成为一个学派的基本条件,包括学派的创始人、学派的骨干成员、学派的追随者等。假如思、孟学派是存在的,那么其创派人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子思;孔子是学派的祖师。孟子显然不是创始人,而且从《韩非子》所论,孟氏之儒早先也不属于子思之儒;然而,如果把思、孟之学视作一个学派,那么孟子无疑是学派的领袖。思、孟学派的追随者不可胜数,问题是作为一个学派,思、孟学派有没有骨干成员?思、孟学派是唐、宋以来“道统”说的重要内容。然而,尧、舜以下,不论是下至程、朱、宋明理学还是黄宗羲、戴震、康有为等清儒(59),也不论其谱系之说如何圆融完备,子思、孟子之间的传承,还是阙失无人的;而孟子之后、宋儒之前,按道统说的说法,道统是不得其人而传的。换言之,思、孟学派的骨干成员,即便是在考述详备的道统说中,也是不得其人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思、孟之学能否成派,还是需要重新考虑的。
其实,思、孟学派的骨干成员并不是无迹可寻的。马王堆帛书《五行》传文所见的世子,被李学勤先生比作朱子《章句》本《大学》第六章所见述孔子之言的曾子。(60) 世子即世硕,系七十子弟子,李学勤先生考其年代为战国中期前半,即公元前450年之前,较之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要早半个世纪。(61) 从时代上看,世子正在思、孟之间。世子不仅解说马王堆帛书《五行》,而且也论人性。《论衡·本性》:
周人世硕(62) 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
如此,则[情]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性]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63)
世子《养性书》不传。但是,公孙尼子之说在传世文献中还是有迹可寻的。楚简所出《性自命出》或《性情论》,就是先秦儒家论性情的文献,“性自命出,命由天降”合于子思《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如前所述,公孙尼子说与子思之学有相近之处,被认为属思、孟学派。从这些材料来看,以世子与公孙尼子为思、孟学派的骨干成员,还是有理由的。也就是说,思、孟学派作为一个学派还是可以成立的。
既然思、孟学派成立,学派的主要学说,当见于《子思子》与《孟子》。《孟子》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于是,问题又回到《子思子》。如所周知,思、孟学派的论题目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战国楚墓所出多见子思之学的材料。在传世文献中,传为子思的著作,除《礼记》中的《中庸》等四篇外,又有宋汪晫所辑的《子思子全书》。《子思子全书》分内、外两编,共有九篇,《四库全书提要》:
《子思子全书》一卷,宋汪晫编。考晁公武《读书志》,载有《子思子》七卷,晫盖亦未见其本,故别作是书,凡九篇。内篇:《天命》第一,《鸢鱼》第二,《诚明》第三;外篇:《无忧》第四,《胡母豹》第五,《丧服》第六,《鲁缪公》第七,《任贤》第八,《过齐》第九。其割裂《中庸》,别立名目,与《曾子》载《孝经》、《大学》同。(64)
汪晫并辑《曾子全书》,上述《曾子》即指此而言。很清楚,四库馆臣对《子思子全书》是没有好感的,其主要原因是:汪氏所辑不仅割裂经籍、别立名目,而且不辨真伪,窜乱原文;在方法上,轻改旧文、真赝互见,有失先儒详慎之道;在体例上,编次踳驳、不著出典,有失辑录古书之体。(65)
汪晫所辑《子思子》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不论其主观动机为何,在客观上的技术原因,是因为汪晫是以宋人心目中的《子思子》作为蓝本,去纂辑复原先贤古书。我们认为,寻觅子思之学的遗文,一定要废弃长期以来我们心目中存有的传世古书的概念,以先秦古籍的概念,去寻觅先秦古书。《子思子》与《孟子》不同,不存在一个退而论集、与高弟子难疑答问、著书立说的过程。因此,《子思子》当以单篇传世,与“《礼》古记”的单篇有相似之处。明确这一点,我们可以避免不少弯路;这同时也是从“《礼》古记”的角度切入子思之学考察的重要原因。就子思之学而言,其文献形式,在传世文献中,可能会被收入《礼记》之类的经典,成为如《中庸》诸篇那样的典籍;在出土文献中,应该就是我们所见的郭店楚墓与上博所藏的战国楚简那样的古籍单篇。
在子思之学的考察中,《礼》古经与《礼》古记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指引着子思《中庸》诸篇的来源,而更重要的是它们告诉了我们子思之学传流的文献形式。“《礼》古经”不是《礼古经》,不是一部书的名称,而是一类书的名称;“《礼》古记”也是同样(不论它们是古文“记”还是今文“记”),它们是某一类书的名称。从前文的讨论可见,《礼》古经与《礼》古礼在称名与内容上,存在着相互混通的可能。郭店楚墓所出与上博所藏的战国简,多见这种“《礼》古记”类的单篇文献,其中多见子思之学。(66) 也就是说,如果子思有文字传世,不论是其亲撰还是弟子传录,最可能的就是以《礼》古记的形式流传;《礼》古记的文献特征即是子思之学的文献特征。
“《礼》古记”的文献特征,实际上是我们用晚后的名称去称说古书;“《礼》古记”类的文献,也是我们用晚后的名称去称说那些相关的战国楚墓竹简。子思之学之所以会是我们所谓的《礼》古记类的文献、与《礼》的记说相关,《中庸》诸篇之所以会被辑入《礼记》而不是其他经典传世,或许是因为中国古代“礼以体政”的传统。(67) 《荀子·大略》:“礼者,政之輓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68)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礼,政之舆也。”杜《注》:“政须礼而行。”(69) 昭公五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70),都与“礼以体政”的思想相关。桓公二年:“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杜注:“政以礼成。”(71) 《汉书·艺文志》记子思为鲁缪(穆)公师。《孟子·万章下》、《礼记·檀弓下》等均有记载证其事。郭店楚墓竹简也有《鲁穆公问子思》一篇。子思之学归诸《礼》类记说流传,是有理由的。
综上所述,《礼》古记的问题是先秦学术史上长期未得充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早期儒家文献的形式与传流以及近年出土的儒家类战国楚墓竹简,有着重大的意义。《礼》古记的重要性长期为《礼》古经所掩,但两者从形式到内容,在中国古代都有混淆之例,因此,不论是讨论《礼》古记还是古经,都应该结合《礼》古经或是古记进行考察。值得提出的是,《礼》古记问题也有着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文体,一种流行于战国时代的学术文体,即《礼》古记类学术文献的单篇。这种《礼》古记类先秦文献,近年在战国古墓中多有出土;从《礼》古记的文献特征去考察这类出土文献,我们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先秦学术古籍的知识,而且能够更加实事求是地认识此类文献的学术性质与内容。从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到,从《礼》古记类文献的角度去考察子思之学,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认识子思之学的传统方法与内容。此外,《礼》古记类文献有其本身的学术意义。《礼》古记的学术意义也许并不在于狭义的礼,而更在早期儒学的内容。这也许是先秦时期“礼以体政”的传统所至。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要在《礼》古记类文献中探寻子思之学遗存。
与其说本文是在讨论子思之学的内容,不如说是在考察子思之学的文献特点。认识到子思之学的文献特征,我们就可能会更自觉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战国楚墓所出的“《礼》古记”类的文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考古所出“《礼》古记”类文献中与子思之学相关的材料,既不追求、也不满足于在出土材料中发现子思的佚篇或佚文,同时也不轻易地给这些与子思之学有关的材料贴上具体标签——不论是学派的还是作者的,而是要认识到先秦学术流派产生与变迁的过程极为复杂,其文献的传流形式也是一样;认识到我们目前关于先秦学术的知识还很不够,仍然处于一个根据新近出土或公布的材料不断地学习、更新的过程。只有在主观上不把我们自己局限于一家一学之中,一切从文献材料的实际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对此一家一学获得真正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这是从“《礼》古记”的视角切入子思之学考察的方法论意义所在。
本文系“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济南、邹城,2007年)大会主题发言,也曾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演讲。作者感谢李学勤先生、杜维明先生、刘笑敢先生等国内外学者及香港中大的同学对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叶山(Robin D.S.Yates)先生曾对反映本文主要内容的一篇英文文稿提出过系统与精辟的批评。谨此鸣谢。
[收稿日期]2008-03-10
注释:
① 《汉书》卷三十,第171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
②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 钱玄:《三礼通论》,第7—8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 钱玄:《三礼通论》,第8页.
⑤ 洪业:《礼记引得序》,Index to Li Chi,Harvard-Yench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 No.27(Taipei: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1966 rep.),第xi-xiv页.
⑥ 王充:《论衡·佚文》,黄晖《论衡校释》本,第860—861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⑦ 《汉书》卷五十三,第2414页.
⑧ 《汉书》卷五十三,第2410页.
⑨ 《汉书》卷三十,第1710页.
⑩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三十引,第19页.上海同文图书馆1916年版.
(11) 黄以周:《礼书通故》,“礼书”,第8页下.光绪癸巳黄氏刊本(1893年).
(12) 《前汉害》卷三○,第164页下.清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
(13) 《汉书》卷五十三,第2410页.
(14)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15) 《毛诗正义》卷一一三,第16页中.《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6) 《尔雅注疏》卷三,第15页.《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7) 同上.
(18) 《三礼通论》,第5页.
(19) 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第3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 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第32页.
(21) 邢文:《楚简〈缁衣〉与先秦礼学》,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5-16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71-76页.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
(23) 《中庸》一书向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以英文出版物为例,最有代表性的即为杜维明先生与安乐哲、郝大维先生的阐释性论著:Tu Wei-Ming,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An Essay on Confucian religiousness(Albany:SUNY,1989); Roger T.Ames & David L.Hall,Focusing the Familiar:A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í Press,2001.
(24) 《汉书》卷三十,第1724页.
(25) 《隋书》卷三十四,第997页.
(26) 《旧唐书》卷四十七,第2024页.
(27) 《新唐书》卷五十九,第1510页.
(28)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第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子思与孟子年代并不相及,李学勤先生疑此为后人据《孔丛子·杂训》补入《子思子》,反映了《子思子》各篇著成年代不同,见《周易经传溯源》,第74页.
(29) 《隋书·音乐志》引,《隋书》卷十三,第38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合版本.
(30) 《经典释文》引刘瓛说.《初学记》卷二十一也有“公孙尼子作《缁衣》”一说.
(31) 《汉书》卷三十,第1724-1725页.
(32)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七,第225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3) 吴静安:《公孙尼子学说源流考》,《南京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34) 《礼记正义》卷五十五,第419页中.《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35) 《礼记正义》卷五十一,第390-395页.
(36)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第410-417页.
(37)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第410页中.
(38) 《礼记正义》卷五十一,第390页中.
(39)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五十一,第1297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40)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第414页上.
(41) 上博藏简本《缁衣》首章“子曰”前残,据郭店简文,也可补作“夫子曰”,见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74页;参见第201页对比图版.本节所论,请参见《楚简(缁衣)与先秦礼学》,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5-164页.
(42) 如《文选》卷五十一《四子讲德论》李善注引《子思子》:“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正则体修,心肃则身敬也.”
(43) 孔颖达:《礼记注疏·记序》引.《礼记注疏》记序,第4页上.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64年版.
(44) 《隋书》卷三十二,第117页中下.
(45) 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第3页下.古香斋本.董治安主编:《唐代四大类书》,第1763页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6) 《礼记引得序》,第xx-xxvii页.
(47) 钱玄:《三礼通论》,第36-39页.
(48)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第324-32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49) 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七,第142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50) 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两种: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第13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51) 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李学勤文集》,第43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52) 刘乐贤:《读郭店楚简礼记三则》,《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第362页.
(53) 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
(54) 陈来:《郭店简可称“荆门礼记”》,《人民政协报》1998年8月3日.
(55) 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李学勤文集》第435页.
(56) 《韩非子》卷十九,第1185页下,《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7) 《荀子·非十二子》,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三,第94-95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58) 邢文:《荀子的“天人之分”与思、孟“五行”——从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谈起》,“儒学全球论坛(2007):荀子思想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山东临沂,2007年8月5-8日.
(59) 姜广辉:《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儒学传统重新诠释论纲》,《中国哲学》第二十辑(2000年),第13-41页.
(60) 李学勤:《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见《李学勤文集》(上海:上海辞书,2005),第418-424页.
(61) 同上,第422页.
(62) 世硕,陈人;陈为楚灭,则世硕实为楚人;周人之说,乃传闻异辞,见李学勤:《李学勤文集》,第422页.
(63) 黄晖:《论衡校释》卷三,第132-133页.
(64) 《钦定四库全书·子思子全书提要》,第1页.《〈孔丛子〉、〈曾子全书〉、〈子思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诸子百家丛书》影印本.
(65) 同上.
(66) 李学勤先生指出,郭店简中《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一组作品,“当属子思一派,很可能即《汉志》著录的《子思子》,至少与之有关.”见《郭店楚简儒家典籍的性质与年代》,《李学勤文集》第425-429页.
(67)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第41页下.《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68) 《荀子·大略》,第492页.
(69)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四,第270页上.
(70)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三,第339页中.
(71)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第41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