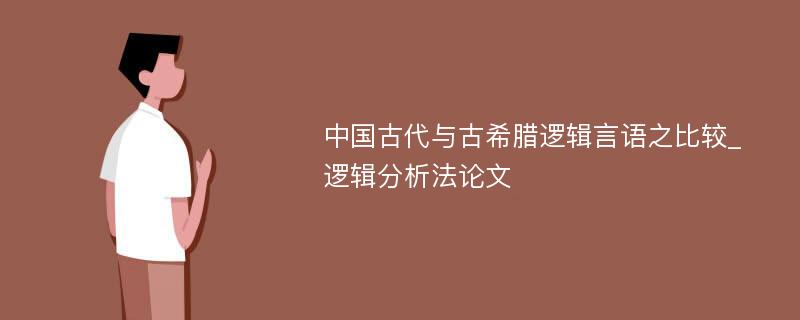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逻辑言说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论文,希腊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92;B81-091.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2)04-0070-07
古代中国逻辑言说的状态究竟怎样?此一问题是古代中国言说思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打算用比较的方式来考察这一问题,因为就此问题而言,比较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有着不可或缺的性质。
一、古代希腊的参照
考察古代希腊逻辑言说的状况可以按两部分进行。其一,逻辑言说的背景或环境;其二,在此背景或环境中生成起来的逻辑言说的特点与水平。
首先,在古代希腊文化中有一种修辞学传统。修辞学在古代希腊得到重视有若干相互关联的原因。第一,修辞学是希腊社会十分重要的教育内容,有无良好的修辞素养被认为是有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可以说是古代希腊修辞学发展的一般背景。第二,修辞学在古代希腊受青睐还有其特殊的背景。希腊,当然主要是指雅典的民主制度对演讲术或辩论术有着严格的要求。它要求那些欲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须具备良好的口才,以此可以有效地阐述自己的主张,并且有效地批驳对手的观点。由于政治一度成为古代希腊国家生活的核心,这就促使许多青年人对其趋之若骛,同时也就使得修辞学的训练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时尚。第三,修辞学的发展又是与一个专门的学派或职业群体密切相关的,这就是所谓的智者派,也称作诡辩论者。智者派当时广泛地传授演讲或辩论的技巧,他们甚至被许多具有政治雄心的青年人聘为家庭教师。
其次,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主要也是以逻辑的方式进行的。希腊思维的主流是对本质与属性问题的关心。对于本质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至巴门尼德,在他有关存在的学说中已经对本质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于属性问题的思考则是从柏拉图开始的,他有关上下行辩证法的理论已清楚地包含了有关属性的知识。而这种对于抽象问题的关注客观上为逻辑言说的介入和展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为逻辑言说也是抽象的,在抽象的思想与抽象的语言之间有一座天然的桥梁。例如“人是生物”、“语法是知识”这样两句话就既涉及对人与语法的本质及其属性关系的理解,同时又体现了作为主词的人和语法与作为宾词的生物和知识之间的语词逻辑关系。事实上,古代希腊逻辑言说的广泛应用与其思想的抽象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且,哲学对于逻辑言说的重视又成为逻辑言说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也可以说是古代希腊思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现象。
再次,自然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数学也即几何学,有一则著名的故事很难说明几何学在古代希腊的地位。这则故事说的是柏拉图曾在其学园的门口立了一张告示牌,上面赫然写着:“不懂几何学的人,不得溜进此门”。而几何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科学的逻辑言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所说的科学的逻辑言说主要是指证明与演绎方法。早在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的泰勒斯已探索性地使用了此类方法,其结果是证明了一些恒等三角形和相似三角形的定理。到公元前4世纪,这些方法已被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以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为例,其借助于证明和演绎的形式,竟能从五条公理、五条公设及二十三条定义出发,推出四百六十七条定理!如根据“彼此重合的东西是相等的”这一公理,可以推出“若两个三角形的两边和夹角对应相等,它们就全等”这一定理;根据“等量加等量,总量仍相等”、“等量减等量,余量仍相等”等公理,可以推出“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等”这一定理。古代希腊上述逻辑言说的环境实际上也就规定了古代希腊逻辑言说的内容与特征,换言之,正是这样一些活动左右或支配了古代希腊逻辑言说的样式。对这些关系,可进一步归结如下:第一,由社会或政治活动中演讲、辩论而来的论证形式;第二,由思想或哲学层面对本质、属性问题的关注而发展起来的抽象形式;第三,由数学即科学层面对推理、证明问题的思考而发展起来的演绎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希腊,第一类论辩环境及其论证形式对于逻辑言说来说是最基本的,但并非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后两类,即对本质、属性问题的关注而发展起来的抽象形式和对推理、证明问题的思考而发展起来的演绎形式,它们标志着古代希腊逻辑言说的特征及其水平,也标志着古代希腊逻辑言说与古代中国逻辑言说的深刻区别。
当然,要使逻辑言说规范化乃至科学化,则还有待于学者所作的专门研究,而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来完成的,其成果便是逻辑学。但须知道,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不仅是有关思维法则的学说,更是有关语词法则的学说。可以这样说,在相当程度上,亚里士多德对于思维的研究是通过语词这一中介形式来进行的。换言之,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思维转换成了语词形态。概念是由语词表现出来的,判断与推理则反映了语词之间的关系。不过,亚里士多德赋予希腊逻辑言说系统最重要的成就当是语词研究的分析化和语词研究的格式化。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将分析方法和格式要求广泛引入语词的研究和应用之中,最终使得古代希腊的逻辑言说具有了强烈的形式化特征或风格。这里分别粗略地考察一下亚里士多德关于上述第二和第三两类问题的研究成就。
先看第二类:对本质、属性问题的关注而发展起来的抽象形式。
古代希腊人喜爱对语词或概念作抽象本质的考察,而其最典型的方式也是最杰出的成就便是对概念下定义。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已分别对下定义的方法做过探讨,而亚里士多德对于定义的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揭示了定义的逻辑结构,这就是“属加种差”。亚里士多德将类视之为属,而将类所包含的子类或个体视之为种,不同子类或个体之间的差异也即是种差。定义的方法就是“把定义者置于属内,然后再加上种差”(《论辩篇》)。其次,“属加种差”这一逻辑结构虽然规定了定义的科学形式,但是它并没有就其中的内容作出深刻的理解。因此,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概念必须是关于事物或对象的本质规定,即所谓“定义是表明事物本质的语词”(《论辩篇》)。第三,在定义科学化的过程中还包括对定义规则的思考,具体如下:(1)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应当是吻合的,定义不可过宽,也不可过窄;(2)定义应当是清晰的,定义中不容许有含混不清的表述,也不容许有比喻性质的语词;(3)定义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4)除非必要,定义不应当是否定的;(5)由于定义在于揭示定义者的实质,而实质是唯一的,因此定义只能是一个。(注:阿·谢·阿赫曼诺夫:《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76、177页;又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定义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对于定义的思考已非常细腻,由此它成为古代希腊逻辑言说的一个重要标志或象征。
再看第三类:对推理、证明问题的思考而发展起来的演绎形式。
演绎形式对于科学活动中的逻辑言说至关重要。如前所见,早在公元前6世纪,泰勒斯已对演绎形式做过探索。不过,古代希腊演绎推理的最高成就是由亚里士多德取得的,而其最经典形式即是三段论。作为科学的逻辑言说,三段论中有这样一些要点:第一,在三段论的前提与结论的类属关系中,大前提应当是全称的,也即是周延的。因为唯有如此,它才能保证与特称性结论之间存在必然性的关系。无论是就思维而言,还是就话语而言,这一点都非常重要,因为它担保了逻辑推理的科学性质,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无类推理的可能。第二,中项的引入,这一点更为关键。亚里士多德这样讲:“除非设定一个中词存在,它以某种存在通过谓项与其他每一个词项相联系,否则我们便得不到任何三段论”。(《分析前篇》)中项或中词的地位何以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如果推理形式中没有中项,具体地说,也即没有中项与小项之间种属关系的确定,那么要从一个前提得出一个结论是困难的。因为我们无从知道前提与结论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推理关系。或者说,这种推理关系是否真实。中项或中词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三段论中,M(中项)与S(小项)是种属关系,而大前提中对M的性质有所确定。这样,通过M与S的种属关系,便可以在结论部分同样对S的性质有所确定(注:对此,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明的:“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中词揭示的。因为如果只设定一个前提,那就没有必然的根据,至少必须有两个。但当两个前提有一个中词时,条件就满足了。所以设定了这一词项,结论就是必然的”。《分析后篇》,Ⅱ,11,94a21-25。)。并且,中项的引入同样是防止无类推理的有效手段。
二、古代中国逻辑言说的环境
古代中国逻辑言说的环境与古代希腊逻辑言说的环境显然是不同的(这是就不同的文化而言,若以人类作为出发点,自有相同之处),此尝试归结如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中国没有非常突出的论辩环境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修辞传统。当然,这并不是说古代中国没有论辩与修辞,(注:此类例子尚且不少。如晏婴使楚即有“南橘北枳”之辩,孔子所说文、行、忠、信四教中的“文”亦有修辞之意。)而只是说在古代中国没有像古代希腊那样如此突出的论辩环境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修辞传统。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有所不同,逻辑言说的广泛基础主要不是“辩”,而是“说”。此“说”有二义:一为叙说之说,二为游说之说,两者且彼此关联。叙说每每为了游说,而游说又无法离开叙说。这种状况是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相应的。希腊文明是城邦民主制度,由此自然发展起了辩的形式;而中国文明则是国家君主制度,因此发展起来的只能是说的形式。但应当说,仅就对论证这类具体的逻辑言说的作用或意义而言,“辩”与“说”其实并无什么重要的差别。换言之,我们看到,无论是辩,还是说,都可以导致十分典型的论证形式。“辩”与“说”对逻辑言说的影响似乎主要是在后续的进程或内容中,具体的说,也即是在有关逻辑言说的规则的制定中。“辩”是一种双方的行为,而既是双方的行为,就自然需要制定出一些双方都共同遵守的规则,以此保证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说”则有所不同,其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行为,也就是“自说自话”,显然,这样一种行为或言说方式对规则的制定不会有迫切的需求。古代中国也有重视辩的,如后期墨家,故称墨辩。且既重视辩,便同样重视言说规则的制定。(注:如:“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小取》);又如“彼,不两可两不可也”(《经上》),“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经说上》)。)而重视言说规则的制定意味着由自发步入自觉,由自然步入必然。但总体而言,古代中国并未进入这种状态,墨家孤掌难鸣。
其次,古代中国哲人不象古代希腊哲人那样,对抽象与本质一类形而上的问题特别关心,而主要是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将哲学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基本上是魏晋以后的事情)。主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也即意味着主要是关注具体的现象或事实。表现在言说上,便是中国哲人多不使用那种抽象的概念(因为不在讨论抽象问题或不在抽象层面上讨论问题,所以也就没有在讨论的过程中使用相应的抽象概念也即手段或工具的必要与可能),而主要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事实或例证来阐述思想或解决问题(事实上,在具体的层面,这类具体的方法也确实要比抽象的方法来得有效)。关于这一点,国外学者也已注意到了。如中村元说:“中国人爱好以具体形式表达”“复杂多样性”,“这种以具体形式来表达复杂多样性的方式是通过用明喻和隐喻”;“既然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沉迷于抽象的思维和无视普遍性,那么他们并不试图用逻辑的精确来表达思想内容”。[1](P.143、145)又如德尔克·波德以为:“中国哲学,由于对类比的特殊强调,很少用具有严格的逻辑的论文形式写作,而是通过将一系列形象化的隐喻、寓言和轶事串在一起以阐述某些最重要的观念。其结果再一次使得中国哲学成为诗化而非逻辑的”。(注:转见陈汉生:《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说明一点,陈汉生此处引德尔克·波德之语本有商榷之意,与此有关之讨论,容本文在后面展开。)这里暂且不考虑有关中国古代言说非逻辑或不用逻辑这一判断的片面性,仅就喜好具体而非抽象形式以及其对逻辑言说的影响来看,以上见解应当说是正确的。逻辑言说有着明显的抽象特征。因此,具体色彩的浓厚、抽象性质的缺乏,这毫无疑问会影响到逻辑言说的水准或质量。
第三,与科学活动的关系。如前所见,古代希腊的科学或数学对逻辑言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其几何学知识的发展是逻辑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并直接导致了逻辑学的一个分支、与该学科密切相关的公理学的形式。然而,这并不意味或担保一切科学活动都对逻辑言说有积极作用。(注:这里固然涉及科学的划界问题,但此问题与本文无密切关系,故不必讨论。)事实上,只有那些与数学有关的理论科学活动才会直接影响到逻辑言说的产生。而绝大多数古代文明的这一活动主要是沿着技术或工艺的方向发展的,这一方向的活动基本与逻辑言说无关。古代中国也是如此,在这里,科学活动的基本特征在于对技术与经验的重视和强调。对此,看一下各类知识中那些代表性的著作便可一目了然。如手工制作方面的《考工记》,农业方面的《泛胜之书》、《齐民要术》,数学方面的《九章算术》,医学方面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所有这些著作几乎都凸现了一种经验品格,具体地说,也就是旨在为以后的相同活动提供一种经验意义的范本。(注:这当中,《黄帝内经》稍有区别,其包含有一定的逻辑思维与言说形式。但是,与古代希腊同类活动相比,它们并没有超出一般活动的层面,或者说,它们并没有提供某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贡献。此外,一些学者对其“逻辑”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也存有疑义。)应当看到,这样一种偏向经验技术的特征与方才所见的喜好具体事实的特征是相吻合的,即在思维方式上它们都定位于经验或现象的层面。无疑,经验方法与逻辑方法分属不同的路向,我们无法希求在经验的园囿里培植出逻辑言说的果实,尤其是像古代希腊那样,既能促进逻辑言说发展,又能成为逻辑言说象征的杰出果实。其实,科学活动中逻辑思维与言说的运用(也可以说是发现)乃是古代希腊人的一项专利。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古代希腊人独占这种言说方式的合法性。
其四,语言本身的问题。美国学者陈汉生(查德·汉森)认为:对于中国缺少逻辑言说的原因,主要不应该在思维方式中去寻找,而应该在语言构造中去寻找。他指出:“中国缺少这种抽象理论化的初始语法动机”,“来自语言的关于这类抽象或心灵思索的一般促动因素(语法结构和书写系统),在汉语中并不存在。没有理由让中国哲学家去发明这种对象”。[2](P.47、64)陈汉生不在乎思维方式对逻辑言说作用的看法似乎有些问题,不过他强调逻辑言说与语言本身的关系无疑是合理的。逻辑言说乃是言说或语言之一种,为此,对逻辑言说背景的考察,最终不得不追寻到语言本身,细说之,即是追寻语言的“祖宗三代”,追寻它的姓氏与血缘。诚然,人类语言之初,逻辑言说是不可能的,那时是一种自然语言。但是,至少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生活在各处的人类的活动已有所差别,并且已影响到思维。(注: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就曾对此问题作过仔细的考察;又刘志一的《科学技术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与拙著《中国思维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也分别就此问题有过讨论。)那么,这种差别是否有可能也影响到与思维分担表里的语言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注:如列维-斯特劳斯指出:“正如十八世纪《法国大百科全书》中‘名称’词条的作者正确注意到的那样,使用词的抽象程度的高低并不反映智力的强弱,而是由于一个民族社会中各个具体社团所强调和详细表达的兴趣不同”;“按照这一观点,一种包含有‘树’一词的语言,在概念的丰富性也不如那种缺少这个词但却包含有数十数百个个别物种与变种的词的语言”。《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页。)如结合思维特点对语言特点作一个大胆假设的话,很可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民族或古老文明表现在语言上的多样性现象乃是采集文化的结果。这是就语义而言。再从语形来看。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在语言吸纳或包容了文字以后,文字的特征可能就对日后的言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的文字受到腓尼基文字的影响而字母化,中国则仍然保留着象形文字。这两种文字对于逻辑言说的不同意义早已为人所知,字母文字在逻辑学、几何学中的优势是象形文字所无法企及的。
最后,语言或言说观念的影响。言说方式与言说观念应当是相濡以沫的。古代希腊逻辑言说的发展得益于希腊社会对于这一言说方式的需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这一言说方式的信赖和提倡,包括将其规则化或形式化。但是古代中国有所不同,其表现在:第一,古代中国的语词系统却不像古代希腊的语词系统那样注重词形和语法,而是注重词意和语用。在中国的言说系统中,意始终处于中心的地位,而词仅仅是一种表意的工具。古代中国人多不认为词形或语法对于表意有什么十分重要的作用。只要能够达意也即满足实用,词的形式是无关紧要的。这即是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第二,与此相关,众多的学派和学者还对言说表示出一种轻视甚至轻蔑。特别是儒家与道家这两个最大的学派,以及孔子与老子这两位最重要的学者。如孔子讲:“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仁者,其言也”。(《论语·颜渊》)又如老子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四十五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这些观点使得古代中国人认为,过分注重语言会危害到思想本身。第三,不仅如此,以儒道两家为代表,还对语言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易传》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经·系辞上》)对逻辑言说作最深入批评的是庄子,他从语言无法把握抽象的道、具体的物以及无法表达人的内心体验等诸多方面对逻辑言说给予了拷问。如关于道,“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庄子·知北游》)关于物:“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庄子·大宗师》)这些拷问对逻辑言说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注:对此,陈汉生的见解颇有意义:“哲学界在精神上接受了庄子对语言的批评:任意与变幻无常。对名的分析以及对构成名的知识的那些技巧的琢磨--包括对逻辑的研究--丧失了名誉”。《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第144页。)
三、古代中国逻辑言说的征貌
但如前所指出,那种认为古代中国没有逻辑思维与言说,或者古代中国人不用逻辑言说的观点是错误的。逻辑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逻辑言说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它们是思维与言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与文明外在要求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对达到一定阶段的思维或达到一定阶段的文明而言,逻辑思维与言说并不存在有与无的问题,而只存在因特殊语境和思境所导致的多与寡、高与下的问题。由此,对于古代中国逻辑思维与言说之判断与批评就应当是完整的,而非割裂的,或者说应将这一判断与批评置于一个科学的构架之下,以保证其客观性或合理性。
由阅读史籍可知,大致在西周时期,逻辑言说已开始生长起来。至春秋时期,作为逻辑言说的最基本形式--推断已经普遍地出现在各种文献中了。不过,古代中国的推断主要是侧重因果关系,而不像古代希腊那样注意事物属性。以《左传》为例,其中至少已有这样一些推断句型(注:申小龙在他的《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对《左传》的句型作了十分详尽的分析。):(1)具体或已然的因果推断句。如“故”型句:“邾人来讨,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2)一般或未然的因果推断句。如“必”型句:“我出师以围许,为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3)假设因果推断句。如“若”型句:“郑若伐许,而晋助之,楚丧地矣”。(4)条件因果推断句。如“而后”型句:“半济而后可击也”。之后到了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一种连锁类型的因果推理形式也已经被经常应用。如《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战国初年,逻辑言说的另一种形式--论证也被广泛发展起来。论证形式的出现涉及以下条件的成熟:第一,论证者也即思想者的普遍出现;第二,论题或论域的普遍设立;第三,良好的论证环境的形成;第四,思维自身的发展已为论证形式的产生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条件。广义的论证包括论证或证明、反驳或证伪这样两种具体形式。以《孟子》为例,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孟子论证其仁政理论的例子。又如孟子证伪陈相所谓“君子必种粟后食”的理论,经过一连串的追问,陈相始有“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的回答,于是孟子反驳道:“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又在春秋时期,分析,这样一种逻辑言说的形式也出现了。孙子有关作战地形的分析就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例证。“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孙子兵法·地形》)这是从地形或战役角度所作的分析;“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围地,有死地”,(《孙子兵法·九地》)这是从地理或战略角度所作的分析。这种分析的方式到战国时已相当细密,如商鞅一篇《垦令》将分析这一逻辑言说形式展现得极其充分。在《垦令》篇中,商鞅详细阐述了保证垦令实施的二十个方面,言说者完全借助于理性或逻辑的手段来展开其说服工作,使得统治者对影响垦荒的因素有了清晰和准确的了解。与此同时,这种言说形式还介入了比较,如:“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荀子·荣辱》)通过这一形式,言说者可以将比较双方的优劣利弊完整地呈示给他的听者或读者。在此基础上,概念的初始形态也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名”。不过,与古代希腊的概念系统相比,古代中国的概念系统有自己的特点,这体现在其首先注意的是名与实的关系,也即是概念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人们普遍认为概念(名)与现实(应)应当相符,如公孙龙讲:“夫名,实谓也。知此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可以说,名实关系成了中国概念系统所关心的最大问题。与此相关,古代中国的学者主要是关心概念的内涵而非属性,这样一个特点在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中得到清晰的表现。公孙龙讲:“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黄黑马不可致”;又讲:“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公孙龙子·白马论》)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孙龙关注的是概念内涵的差异性。马的内涵只是马,它是命形的。白马的内涵则不仅是马,它除了命形还要命色。而这样一个特点其实又是强调名实对应的特点的结果。
不过,古代中国的逻辑言说显然存在着一些缺点(如果仅以希腊作为参照,或许这些缺点未必一定存在,因为没有理由要求中国一定要达到希腊的高度。但是,当参照或比较不仅包括希腊,同时也包括印度时,存在这些缺点的可信度便增加了)。而这首先的一个即如前所见--是对形而上一类问题兴趣的缺乏。应当清楚,逻辑言说与抽象思维有着十分(至少是比较)密切的关系。换言之,抽象思维的状况会影响到逻辑言说的状况。从抽象思维主要寓居的一些领域,如哲学、宗教、科学、逻辑的情况来看,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和古代印度的确存在着一些差距。如古代希腊的哲学、古代印度的宗教,它们所关心的主要都是一些本质问题,或是关于自然的本质,或是关于人类的本质。但无论何种本质,都需借助抽象思维来把握,因为本质没有具体对应物。而正是这样一种关怀使得逻辑言说的能力提高了。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人由于局限于具体的事物和现象,因此抽象思维没有被充分发展起来,并因而又影响到逻辑思维与言说的发展。
关注具体现象,远离抽象本质,又体现了中国言说的这样一种精神,即注重语用。对此,陈汉生有正确的见解:中国古典时期是“以其有关语言和它的语义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语用(语言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显露出一种魅力”;可以认为“中国思想集中于语用的研究。因此比较而言,中国思想较少关心语义上的真假,而较多地关心语用上的可接受性”[2](P.72、74)。陈汉生的这一判断或评价是客观和真实的,例如孔子的“辞,达而已矣”的思想就正是此种精神的经典体现。但是,过分或仅仅满足于语用,对于逻辑言说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为语义或性质问题;其二为语法或形式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从逻辑与语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之所在:首先,定义形式的缺陷。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对定义问题有过接触,如《墨经》中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界定:“宇,弥异所也”;“久,弥异时也”。(《墨子·经上》)但应当指出的是,古代中国的这种定义形式具有明显的自然或自发性质,没有像古代希腊那样,给予定义以操作性的规则。而这从根本上说又是因对于种属关系认识的欠缺所造成的。事实上,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对于种属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他们已经注意到了概念范围大小与层位高低的区别,如《墨经》讲:“名:达、类、私”;(《墨子·经上》)荀子也有“大共名”与“大别名”(《荀子·正名》)之谓。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墨经》还是《荀子》,在讨论了概念的一般种属关系之后便止步不前了。他们并没有继续将种属问题与本质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讨论,并没有发现种属问题之于探讨事物本质的重要意义,因此,也并没有发现种属问题之于定义规范性的重大意义,结果只能与定义形式的发现失之交臂。其次,推理形式的缺陷。这里所说的推理依然是围绕种属也即类的问题来展开的,而其典型形式应是古代希腊的演绎或三段论方法。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同样接触到了类推的问题,如荀子讲:“以类行杂,以一行万”(《荀子·王制》)。古代中国的典籍中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演绎推理的雏形。(注:如《孟子·万章上》说:“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有学者认为,在这里大前提与结论都具备,但省去了小前提,即仲尼虽德若舜禹,却没有天子的推荐。又如《老子·六十五章》曰:“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也被认为具有三段论结构,即民智多则难治民(大前提),以智治国使民智多(小前提),所以以智治国则难治民,即所谓国之贼。)但正如学者们所普遍注意到的:中国的三段论并“没有定型化”[3](P.216);中国的推理形式“常常不完整不规范”[4]。其实,这样一种没有定型或不完整不规范的状况正是缺乏自觉意识的表现。它表明:古代中国的演绎推理或三段论严格地讲还并没有被形式化。演绎推理或三段论没有在中国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包括以下一些复杂原因:中国并不特别重视以性质为核心的直言命题或判断;中国在推理活动中并没有给予种属关系以足够的重视;由此导致,中国的逻辑学家或学派并没有对演绎方法给予专门的研究。而在自发状态下,就很难得到理想或有效的三段论推理形式。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印象:第一,古代中国有自己的逻辑言说系统,其中诸如论证、推断、分析都达到了应有的高度;第二,与古代希腊相比,古代中国在涉及抽象本质与类属关系(主要是哲学和科学)问题的逻辑言说方面暴露出不足;第三,同样与古代希腊相比,古代中国并没有对逻辑言说制定出有效的规则,这使得古代中国逻辑言说的形式化程度较低,也意味着自觉意识的相对薄弱;第四,古代中国逻辑言说的这些问题受制于更大的文化背景,其中也包括中国学者对于语言的特定观念,以及对逻辑言说的批评。
[收稿日期]2002-12-10
标签:逻辑分析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