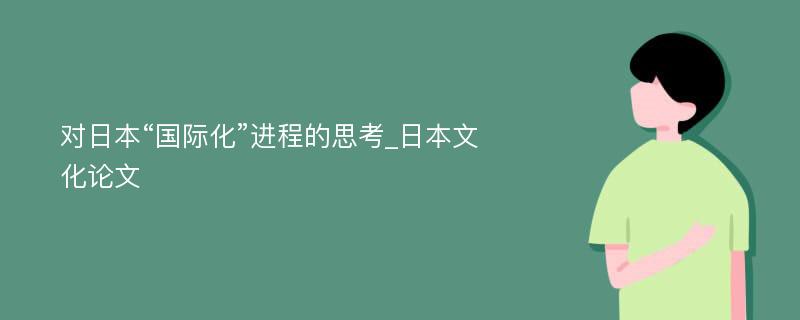
关于日本“国际化”历程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90年代,在日本呼唤得犹如春雷般响的“国际化”口号,有人称其为是日本的“第三次开国”(注:这是因将日本近现代史上的明治维新、战后改革称作“开国”而故称。)。如今,整个日本的“国际化”热潮似乎已成余响,其实则是从理论探讨到更加的实践化。日本的“国际化”热浪及其具体的实践,究竟给日本、世界,特别是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提供了哪些可资思考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笔者对日本“国际化”的研究起步较晚,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又局限在本人对日本文化和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范围,试图把日本“国际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加以探讨。也即从宏观的角度,以日本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及其特点为线索,通过宏观视野下的实证和比较来透视日本的“国际化”;从而,对照历史、纵横分析,阐释日本“国际化”的实质和问题,以及对正处在十字路口的日本“国际化”如何准确地选择和把握,从中获取若干有益的启示。拙论尚属肤浅或片面,恳请识者方家匡正。
日本“国际化”历程概略
目前,在日本“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中,有的往往把“国际化”与“近代化”、“现代化”混同起来。当然,它们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但“国际化”毕竟是指战后的一种新潮流。从日本说来,“国际化”既是一种思潮(观念),又是一种政策(手段)。因此,笔者拟从上述两个方面来概述其历程。
“国际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日本的“国际化”正逢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息时代到来,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为日本提供了机遇。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视、电脑、通讯卫星等现代化通讯手段日新月异,由此而迎来了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化时代。因此,偌大的地球也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有显著的增强,打破了国界的“经济圈”相继形成,以天然经济区为基础的“地区国家”也陆续崛起。面对世界经济的“区域化”、“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地处东亚一隅的日本,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就得抢占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故打出了“国际化”的旗号,从经济国际化着手,并为实现其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国际化”迈出了引人注目的步伐。
日本“国际化”进程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1)从经济领域首先开始的日本国际化。经过战后改革和获得政治独立的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上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10年时间出现了罕见的经济繁荣。由于经济发展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就需要实施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政策。1962年,池田勇人再次当选为自民党总裁时所发表的《十二人共同宣言》中,出现了“经济国际化”一词。但是,作为正式的官方文件出现“经济国际化”一词的,则在1967年3月的《经济发展计划——对(昭和)40年代的挑战》中(注:“经济国际化”一词,最早使用于1961年11月8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的“国内经济国际化”一文。),并作为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来贯彻实施的。2)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是从80年代才开始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的。这可见于1982年7月由日本政府经济企划厅编辑出版的《2000年的日本——具备国际化、高龄化、成熟化》报告书中,强调“必须以国际视野看待一切问题”[1-p85]。因此,在80年代就出现了名目繁多的,诸如“金融国际化”、“教育国际化”、“农业国际化”、“日元国际化”等等。这正是由于日本成为超级经济大国以后,能提供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以此为基础滋生的大国意识、民族优越感,以及统治阶层力求在国际舞台争取占有一席之地,争得对国际社会的发言权,作为实现“国际化”的物质的、社会的、政治的基础。与此相应的,伴随着全球国际格局趋向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化的变化以及日本商品向全世界渗透,逐渐形成了日本的“国际化”高潮。3)90年代后半期,由于日本经济不能摆脱滑坡和低迷状态,持续多年的“国际化”热潮有所减退。这除了经济发展的原因以外,不可忽视的是究竟如何进行“国际化”确实尚须深入细致的探索。可以说,目前日本的“国际化”并没有停顿,但处于十字路口,究竟迈向何方,这不仅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
关于日本“国际化”理论研究,当首推战后美国驻日本首任大使、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的对日本“国际化”所作的内容广泛、颇有见地的论述,以及哈米尔·别夫在其所著《作为意识形态的日本文化论》一书中,对日本国际化的定义所提出的十三条标准(注:13条标准即:1.欧洲在日本的影响,2.在日外国人,3.外国在日本的投资,4.贸易政策的自由化,5.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6.日本人的外语能力,7.与外国人的交际,8.对外国文化的理解,9.在日外籍教师的地位,10.归化问题,11.日本语教育,12.提高对日本文化的理解,13.日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日本(NHK)广播协会的主要负责人纳谷裕二、日本社会事业大学小林广教授于1989年10月在日本出版了大部著作《日本的国际化——与赖肖尔博士的对话》,这对日本“国际化”理论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在这以前,日本确实也已开始了有关“国际化”理论的研究。早在1974年成立的“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从1985年开始邀集了200余位学者,化了三年时间,完成大型的政策研究论著《90年代日本的课题》。这部论著被视为日本研究“国际化”问题的集大成之作。
日本的学术界或舆论界对于“国际化”解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说法。诸如:“通过对异文化的宽容,并积极贡献于世界,从而获得外国人的亲近感和信任”[2];“要相互容认环境、价值观、思考方法的差异,创造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能够相互信赖和理解的社会”[3];“不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日本国内,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人们共同生存,或是说,为此目的的努力”[4]等等。所有这些均能说明:日本国内对“国际化”的解释以及实施方法分别可从对外、对内两个方面来认识和实践的。因此,中国大陆有的学者把日本的“国际化”概括为“内在的国际化”和“外在的国际化”。所谓“内在的国际化”即指面对开放的世界,日本必须克服其“岛国意识”和封闭状态,也就是要进行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内部机制的革新,作出对外部世界瞬息变化的适应性反应;所谓“外在的国际化”,即是凭藉日本现在所具有的经济实力,通过其所拥有的巨额资本,以“开发援助”等手段,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树立日本人的“形象”,亦即面对变化的世界要显示出日本人的“创造性贡献”。[5-p185]
无论是“内在的国际化”抑或“外在的国际化”,其实只是“国际化”这块铜板的正反两个方面,是合为一体的。但在日本的政界和学术界,则有人认为当前的日本国际化是要体现在“外在的国际化”方面。如日本前外务大臣、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认为:现在的国际化是日本第三次开国。但这次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前两次是被迫的,而且是以引进为主,这次则是主动的,是以“拿出去”为主要特点。这次国际化要求日本人在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时,要由以物为中心转为以人、资本和知识为中心。也就是说,日本人将以资本的提供者和先进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的姿态活跃于世界舞台上[5-p185]。与大来佐武郎观点相似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倡导“战后政治总决算”和“国际国家”论时说:“过去,我们对吸收和消化外国文化,即对文化的‘吸收’过于热心,而对文化的‘传播’所作的努力却很不充实”;“日本越是要成为国际国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6-p263]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今日本高呼“国际化”,在主流派看来则是要以“外在的国际化”为主要倾向的。
纵观前述日本“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笔者认为:日本确实在迈向“国际化”历程中取得了不少成就,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如何处理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尚有观念和手段上的若干不足。这就需要其对自身以及对外关系的历史作一番回顾和反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由鉴于此,笔者拟以日本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特点及其选择为线索,对日本“国际化”历程作一回顾和展望,从中获取若干有益的思考。
日本文化时代性的新坐标
在日本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其固有文化所致。因此,竭力主张要挖掘日本所固有的、深层的文化[7]。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民族总是有她自己所固有的、独特的文化,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或否认这个民族由于吸收外来文化而发生的变化。
翻开日本文化史,远古的不说,自公元前后开始,日本通过朝鲜半岛或直接吸收中国文化。由于中国的铁器、青铜器和水稻种植的传入使日本由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此后,吸收了隋唐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于公元7世纪中叶进行了日本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的社会变革,以致迎来了奈良时代(710-784)的社会大发展和平安时代(794-1192)前半期的由唐风文化向国风(民族)文化的转变。这正如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说:“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化,对于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8-p14]16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向东方扩张,欧洲文化向日本的传播经历了南蛮学、兰学、洋学的不同阶段(注:日本直接接触欧洲文化始于1543年。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以葡萄牙语为媒介,吸收欧洲基督教和医学的,称“南蛮学”;1720年德川吉宗实行“洋书解禁”后,以荷兰语为媒介,吸收欧洲的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称“兰学”;1853年开港前后,以法、英、德语为媒介,吸收欧洲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称“洋学”。洋学也可作为包含南蛮学、兰学在内的总称,这相当于中国所称的“西学”。)。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大踏步地学习西方,由一向崇拜中国转向以西方为师。日本学习西方有成效,成为东方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加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能在战争废墟上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得益于吸收和引进了美国文化,在制度和观念诸方面效法美国,经过20来年的时间由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就日本文化在各个阶段的时代内容说来,正如不少学者所作过的概括:日本古代文化为“唐化”(中国化)、日本近代文化为“欧化”(西洋化)、日本现代文化为“美化”(美国化)。当然,这种概括并不完全准确,但大体上能说明日本文化演进的时代性特征。
那么,自8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国际化”论以后的日本文化,就其时代性而言又可作出何种概括呢?兹此,笔者将其与历史上不同阶段试作比较。
第一,就吸收外来文化的范围而言,在以往的历史上均是以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为主要吸收对象;而如今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并不以此为模式,而是面向世界,凡是对日本有用的都加以吸收。
第二,就接受外来文化的态度而言,无论是古代接受中国文化还是近代接受西方文化和战后接受美国文化,日本都处于强弱、高低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即有先进和落后的明显差距,故均采取被动的态度;而在提出“国际化”口号后,日本则在态度上有很大的改变,即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强,一改被动为主动,由被迫而改为自愿。
第三,就文化交流的方式而言,在“国际化”口号提出以前,主要是向对方引进的多,也就是“拿进来”的多;而如今则是“拿出去”的多,也即是以输出为主的。
最后,就文化交流的类型看,在提出“国际化”口号以前的各个时代,日本主要采取“接受”外国文化,如今则主要是将日本文化进行对外“传播”,这正如上文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说的那段话,它毫不掩饰地表露了日本人提出“国际化”所要追求的志向,即如何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
仅就以上四点似可说明,日本人所喋喋不休、一直挂在嘴上的“国际化”,显示了战后日本文化发展的时代性特征:一反历史传统,面向世界,积极主动,输出传播。因此,笔者有意将日本“国际化”口号的提出,作为日本文化发展时代性的新坐标。
日本文化民族性的展现
日本的“国际化”口号,除了反映出日本文化的时代性以外,同样也展现了日本文化的民族性。日本民族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吸收或接受外来文化,从不盲目地接受而是有所选择的,其选择的根据即按本国的需要,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结合,从而充分地展现其民族性。
早在公元7世纪的“大化革新”前后的200来年间,是日本吸收隋唐文化的高潮时期。“唐风弥漫奈良城”。但是,事实上日本并没有全面“唐化”(中国化)。如在官制方面,尽管是以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为蓝本实行了“二官八省”制,但唐朝的三省中的尚书省为最高的政务执行机关,而日本除了有类似于尚书省职能的太政官以外,还根据国内有神道教的传统,专门设立了与太政官并列的神祗官,专管神道的祭祀。
从公元6世纪起,中国将印度传来的佛教通过朝鲜半岛或由中国直接传到日本。在当初的2个多世纪里,中国所有的佛教宗派差不多先后传到了日本,形成了所谓“奈良六宗”、“平安八宗”的日本佛教宗派(注:从公元625年由高丽僧慧灌传入三论宗开始,相继传入了法相宗、华严宗及由鉴真传去的律宗、以及俱舍宗、成实宗两个小乘佛教宗派,统称“奈良六宗”。平安时代初期由从中国归国的学问僧最澄于805年在京都比睿山开创天台宗,816年空海在高野山建金刚峰寺,开创真言宗,与原奈良六宗,合称“平安八宗”。)。12世纪末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3),新兴的武士势力执掌政权。他们与贵族势力发生冲突,表现在佛教上即是旧佛教的衰落和新兴佛教的产生,诸如净土宗的兴盛和日本独有的日莲宗、时宗的应运而生,出现了日本佛教史上“诸宗竞起”的新景象,被称之为日本的“宗教改革时代”,故在平安末期那样,一时的盛观,确实不如镰仓初期那样兴旺[9-p6]。“传佛心印”的禅宗,是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在唐朝时已传入日本。由于禅宗主张依靠自我修炼,自力成佛,故它很适合于依靠脚踏实地的战斗开辟道路的武士阶级需要,成为他们对抗过去的贵族文化、创造武士新文化的武器。因此,日本的禅宗又表现出与中国禅宗的不同:中国的禅宗一向标榜“不立文字”,而日本的禅宗却由禅僧们掀起了专门舞文弄墨的汉诗文热潮,导致在日本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五山文学”的兴起(注:从镰仓末期至室町末期的汉文学,盛行于京都、镰仓,两地各以五座寺院为中心,仿中国禅林制度建立了地方最高禅宗寺院。1386年实行五山禅寺制改革,以京都南禅寺为最高寺院,其下分别确定受幕府保护的京都五山、镰仓五山,故有“五山十刹”之称。五山文学即由于五山禅僧从事诗文、典籍、经文的写作和注释而得名。),达到了日本史上汉诗文发展的新高峰。受禅宗影响而表现出的日本文化又突显其民族特色,诸如日本山水风景的水墨画所表现出的枯淡、简洁而意境深远的风格;庭园建筑充分注意与自然景观相结合而体现出淡雅情趣。被称为“日本人生活的综合艺术”的茶道,也是从禅宗思想中提炼出“茶禅一味”的意境,形成了贯穿于茶道之中的“和、敬、清、寂”思想(注:茶道是日本的综合生活艺术,贯穿于茶道中的“和、敬、静、寂”的含义是:普天众生平等互敬、超越一切个人的利益打算,潜心修性于寂静之中回复自我,以获取明天的生命力。)。显而易见,追求枯淡、典雅的风格是渗透在日本文化的深层之中,是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又正是日本吸收了禅宗所创造出来的日本文化风格。
在日本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儒学,自公元5世纪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天皇制国家的建立和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的道德规范方面起着作用。在江户时代(1603-1867),幕府统治者确定朱子学为“官学”。中国的儒学一直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而日本的儒学则在天皇、幕府将军并存的“双轨制”的幕(府)朝(廷)体制下,既为天皇服务也为幕府最高统治者——将军服务;强调伦理纲常的中国儒学,传到日本后被作了改造,把朱子学与日本的神道结合,提倡“儒神合一”,并把中国儒学的以“孝为首”改为把“忠”列在首位,作为“五伦之第一”来适应武士统治阶级的需要。然而,到了明治维新前后,儒学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如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认为,儒学是“造成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10-p148]。因此,他主张通过对儒学的批判来培植日本民族的自然科学观和政治主体意识。同时,由于当时人们对儒学的熟悉程度,故通过儒学来“嫁接”欧洲近代文化,亦即用儒学概念来解释欧洲近代文化中的若干名词,以利于接受和理解欧洲近代文化,以致进而出现了实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论的企业经营理论。明治维新以来,儒学仍然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指导性原理,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对于提高人的素质确实起着推进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处于战败国地位被迫接受了美国文化、议会内阁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但它并没有单纯地照搬而将其与渗透在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中的儒学相结合,形成了日本式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但是,若把儒学作为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原动力”,或推而广之将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视作“儒家资本主义模式”,显然是有失偏颇的。[11]
以上,仅就日本吸收唐朝文化以及佛教、儒学、茶道等方面来说明日本文化的民族性。关于日本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应该是从多角度、多层次来加以分析的,也可以由此作出各种不同的概括和归纳,似可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角度并侧重于观念文化的层次来考察当今日本国际化过程中日本文化民族性的展现。如果从文化史角度和观念文化的层次上来考察当今日本的“国际化”论,即是日本将由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吸收,开始扩展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日本文化的传播和创新。另外,对当今日本国内官民呼唤的“国际化”论的历史考察,还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末期的“开国论”、明治时代的“文明开化论”,以及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它们都是当今日本流行“国际化”论的源头。继之,20世纪2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和平环境中,日本国际活动家新渡户稻造等倡导了“国际协调论”,日本投降以后在“非军事化”、“民主化”过程中,曾任内阁文部大臣的教育家森户辰男等倡导的“和平国家论”,主张以建设“文化国家”为目标,重新进入国际社会。这些观点和主张都对当前的“国际化”论有着重要影响,成为由20世纪60年代出现、80年代盛行的日本“国际化”论的思想基础和历史前提。
日本文化特点的体认
日本文化随着时代的更替而发生着变化。但是,综观整个日本历史,日本文化的总体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或者称作为日本文化的核心。这也是日本民族文化真正区别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最根本的原质。那么,日本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
当代日本历史学家、文化史家石田一良教授认为,神道是日本文化的核心[12-p176]。日本神道早在稻作农耕的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就形成了雏形。神道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信仰,也是日本的民族宗教。它对外来思想信仰显示出自己的民族性格,具有对外思想信仰的包容和抗阻,经过诸多阶段迂回曲折地维系到现在。在日本的历史长河中,神道跟不同时代的宗教和思想结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神道。如:在古代与中国的原始儒教结合形成了古代日本的民族祖先教;继之,与中国的祗神教结合形成了两部神道和本地垂迹神道;到了近世,神道与中国的宋明理学结合形成了诸种儒家神道;神道与日本国学结合形成了古学神道;在近代,神道与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想结合形成了崇拜天皇的国家神道。因此,我们可以把神道演变过程中的原质与各个时代的宗教思想之间的关系,比喻为木偶与其所穿衣裳的关系,由此可视神道是“更换衣裳的木偶”[12-p12]。按照石田教授给神道用数学术语设定的函数公式:f(x)=y(f为神道的原质,x为各个时代的宗教状况,y是各个时代的神道的具体面貌),说明神道具有随机应变、变通自如的特性,日本人具有对异质文明的包容力。当然,我们不可忽视的,神道对日本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去年,时任首相的森喜朗抛出“日本神国论”,意欲把历史拉向后退的意图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与神道最有密切关系的是国学。从17世纪中叶开始为对抗儒学开始出现了强调日本固有文化独特性的“国学”[13-p351~398]。它始源于江户时代中期契冲的和歌研究,从和歌中求人间自然的叙情世界,把和歌从受佛教、阴阳道影响的解释中解放出来,企图正确地反映日本的古典精神。契冲的后继者荷田春满明确提出与朱子学对立的观点,因他出身于京都稻荷神社的神职家庭受到神道的影响很深,故把国学引向神道的道学方向发展。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对当时混乱的社会表示出反感,憧憬着一种理想的社会,即天皇统治之下政和邦宁的古代社会,并以和歌为媒介的神道作为通向古代社会的道路。到了宣扬皇国神国思想的平田笃胤时,又将本居宣长所提供的推崇古代和歌的神道运动迅速转变为社会运动。平田氏的“国体论”(注:平田骂胤(1776-1843)江户时代后期批判佛教、儒学,鼓吹皇国神国思想的国学家,撰写了《古史成文》、《古史传》、《古道大意》等著作,论证日本是神国、“万世一系”的国体,以及皇统是永不绝的。)成为明治维新“王政复古”的理论支柱。国学既是复古主义的封建意识形态又包含着反封建的进步因素,在幕末倒幕维新运动中表现得相当活跃;国学派的复古和排斥儒佛又是后来日本的排外主义、国粹主义思潮的渊源。
综观日本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吸收与排斥、适应与对抗并存的种种文化现象,似可得出结论:日本文化具有多样性、适应性和独自性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归结起来又表现在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法和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内聚和排外”的总特点,这是日本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成功和失败的关键性因素。
当然,日本迈向“国际化”的历程,我们可以部分地体认到日本文化的诸特点。日本“国际化”口号的提出,是在世界国际化的形势和环境中出现的。日本“国际化”论就是为了适应这一世界形势的需要,适应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作用的需要,适应日本由原来的文化输入国转变为文化输出国的需要。因此,日本提出的“国际化”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展开的。它由经济国际化起步,实行生产资本的国际化,通过跨国公司、跨国银行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同时,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开放国内市场,实行金融改革等藉以推进国际合作;在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向政治大国迈进,要挤占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要组建美、日、德三极体制的“世界新秩序”,要取得国际事务处理中的发言权等等。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的文化政策相应地发生了明显变化。近年来,扩大吸收外国留学生,到20世纪末计划招收10万留学生;在国内扩充日本研究的机构,加强日本研究队伍建设,并吸引和资助外国学者的赴日研究;在国外,资助设立日本研究机构和文化交流设施,旨在扩大日本文化的影响、宣传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从日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国际化”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的国际化是以日本为中心、以做大国为目标;日本国际化历程充满着以“自我为中心”作准则的利益判断,日本人高唱“国际化”论,说得尖锐一点,实质上是要把国际社会“日本化”。
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日本文化就其总体而言,确有值得世界各民族吸收和效法的优秀成分,同时也不能忽视它也有明显的劣质该清除。如果把孕育于岛国的日本文化与当前国际化大趋势对照起来就显得更加明显。这就给我们尤其是当代日本人提出了如何对待日本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日本人对“国际化”的准确选择和把握。
笔者认为,战后以来特别是从80年代“国际化”高潮之后,日本人在对待自身的文化时存在着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的倾向。例如,在日本学术界不少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日本深层文化,力图从古代的日本文化中去寻找当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对近代以来日本在世界上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的文化因素检讨得极其不够,且屡屡出现否认侵略罪责的谬论。他们总是害怕人们揭它的“疮疤”而退避甚远。这种态度无论从历史或现实角度考虑,不仅会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展开而且也会直接关系到日本对“国际化”道路的准确选择。
不可否认,80年代以来日本迈向“国际化”的历程,确实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991年9月的一份统计报告称:全球10大银行中,日本占有7家;全世界最大的100家银行中,日本占29家;全球保险公司前5名中,日本占有4家;全球的证券公司的前4名全属日本;全球100家大企业中,日本占有34家。这些足以说明日本人在高喊“国际化”口号下,确实在经济上获得了太过丰厚的实惠。同时,日本在对外的“开发援助、“无偿援助”、“低息贷款”等方面也作出过努力,这也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诚然,我们应该看到日本“国际化”的动向,既代表了日本的国家决策者的意向又反映了全社会民众的需要,它意味着全体国民的共识;这也是战后日本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归宿,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流。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日本的“国际化”障碍不小,而且这个障碍主要来自其自身。日本民族由于岛国的自然环境以及经历了近千年武士生活的感化,形成了全民族的“集团意识”,这正是日本民族至今保持着的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它无论是在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中均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日本民族的“集团意识”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过消极作用和带来不少负面影响。诸如效忠天皇、连续地发动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这同由“集团意识”滋生的“日本中心观”不无关系。如今,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依然十分强烈,在国际事务中总是试图以日本为中心,不太顾及他国利益。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的这一侧面,无疑对推进“国际化”进程会带来不少障碍。因此,日本要在“国际化”道路上继续迈进,就必须刻不容缓地对日本文化作出准确的继承和创新,认真反思和恰当调适,要继承日本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摒弃日本文化中的糟粕,充分地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创造出适应时代新潮流、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要本着平等自愿、特长互补、共同受益的原则,加深相互理解、增进彼此合作,在国际交往中消除民族隔阂,为追求人类共同富裕、丰富世界文化宝库而作出贡献。
日本“国际化”的进程,无疑对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同时对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对于日本积极推行“国际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应该予以肯定和称赞。我们似可“听其言、观其行”。日本地处东亚,与该地区的国家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和还没有还清的债。这就需要日本国家和民族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认真追究战争责任、肃清军国主义恶劣的思想影响。目前,在国际化的世界潮流中,日本正处于通向“国际化”的十字路口。如从日本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特点诸方面,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深入研究,无疑会利于准确地选择和把握迈向“国际化”的正确路径。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也应对日本“国际化”问题进行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这不仅能加深对日本“国际化”动向和实质的认识,而且也能推进本国在顺应世界历史新潮流,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自身现代化建设,共同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