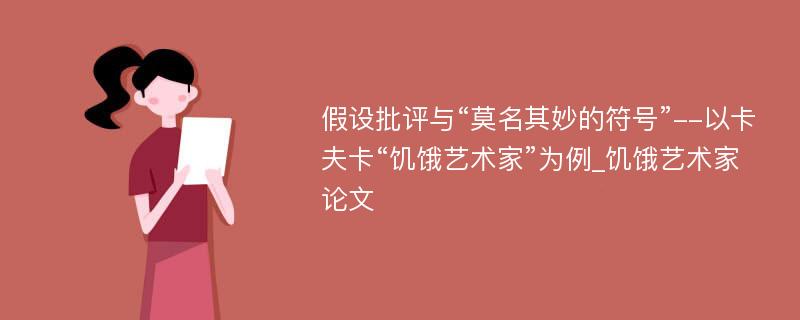
假设命题式批评与“难以解释的符号”——以卡夫卡《饥饿艺术家》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命题论文,饥饿论文,艺术家论文,符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假设命题式批评与“难以解释的符号”这两个名词,前者属于批评方法论,后者属于艺术本体论。作为相关性概念提出处于怎样的思考呢?
假设命题式批评是笔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过程中探索性命题,自然是以往任何理论流派中所没有的。其实,任何方法都是与特定本体相互对应,方法的运用与创新,来自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和把握。人类对于艺术的认识是不断深化没有止境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探索也就成为必要。“难以解释的符号”是希利斯·米勒在《解读叙事》中提出来的,是解构主义理论对于叙事艺术的理解和界定。“假设命题式批评”就是与这样的艺术界定和理解对应的。
希利斯·米勒在《解读叙事》第一章开篇即说:“不妨从我们目前文化传统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西方文化中两个毋庸置疑的经典文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1](p2)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希利斯·米勒独具慧眼,首先,在确认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典型代表的基础上,希利斯·米勒说:“它也证实了我的观点:以逻各斯为中心的文本都包含其自我削弱的反面论点,包含其自身解构的因素”。[1](p2-3)其次,是他发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极力推崇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并没有能够有力地证明理性的力量,恰恰相反,“《俄》剧是他的理论阐述体系里一位怪异的客人。亚里士多德力图使悲剧中的一切都合理地回归其位,就这点来说,对《俄》剧的引用非但未助他一臂之力,反而引入了一些无法征服的非理性因素”。[1](p4-5)《俄狄浦斯王》表明,俄狄浦斯王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解脱地陷于灾难的怪圈中,他的行动越是依据理性,陷入的就越深……。左右这一切的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呢?天神的动机根本让人无法捉摸,“最为缜密的思考和最为虔诚的服从都无助于揭示这些法则的真相”。[1](p14)希利斯·米勒进而说:“索福克勒斯与赫拉克利特看法一致:‘特尔斐之神既未解释也未隐藏,而是给出了一个符号’。[1](p14)《俄狄浦斯王》的全文可以看成这样一个符号。通常的叙事也可能是这样一个符号。或许,我们之所以需要讲故事,并不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是为了给出一个既未解释也未隐藏的符号。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和理解的东西,可以用一种既不完全澄明也不完全遮蔽的叙述来表达。我们传统中伟大的故事之主要功能,也许就在于提供一个最终难以解释的符号”。[1](p14)
希利斯·米勒就这样在解构亚里斯多德推崇理性的论述的同时,又从正面提出了自己关于叙事的看法,这段话含义丰厚深邃:既不完全澄明也不完全遮蔽是叙事艺术的一种存在形态;某一种艺术就存在于完全澄明和完全遮蔽之间;叙事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具有理性无力担当的功能;讲故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搞清楚某些事情,而是为了感受某些事情;“难以解释的符号”是优秀艺术的标志。
由于解构只能在具体对象中进行的,所以,任何解构理论,其实在解构的同时也连带着将它所解构的原来的理论痕迹透露了出来。笔者在思考文本存在方式问题时曾经有过一个发现:西方20世纪文论中,波兰现象学家英加登在《文学的艺术作品》和英美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都大同小异地提出了文学文本的层次结构问题;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则提出了相位的理论,从若干层面进入对文本的思考:中国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的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提出“先标六观”的思想,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从六个角度进行。这些理论依据不同哲学体系基础,或者从若干层次构成的结构,或者从诸多侧面来认识和把握文学作品,我梳理出如下几个层面。1、语辞所具有的语音和语义。除了弗莱的相位理论没有涉及到之外,其他前述理论家都注意到了文本层次结构是以语辞为起点的。2、句子和句子所组成的意群,是贮存文学性的重要地方,句子承载着最初的完整的意义,意义就是在由语辞构成的句子和句群中展开的。虚构的世界由之产生。3、已经形成的形象或者意象及其隐喻,其中已经具有了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意义。4、文学作品的客观世界。这是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西方人把这样虚构的、象征和象征系统称为诗的“神话”。其实,就是用语辞虚构出来的世界,一般指叙事性的小说世界。这是所有层次最终归结之所在。5、“形而上性质”(崇高的、悲剧性的、可怕的、神圣的)。虽然不是以阅读可能意识到的对象样式而直接出现的,但是也是生成文学性的因素。我认为,英加登的现象学文学批评理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有意义。茵伽登认为,在文学作品存在的结构中,语词声音和语义所构成的层次、意群层次、图式化外观层次都有其主要的目的和功能,那就是共同作用于客体的再现,积极地建构再现的客体性,再现客体这一层次的存在,是什么东西产生于客体层次,或客体层次指向什么东西呢?客体层次指涉的是一种“形而上质”。当然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形而上质,只有优秀的文学的艺术作品才具有形而上质。对这个层面的意识,涉及到我们对文学的完整理解。英加登还认为,从审美态度出发去意向文学的艺术作品,所构成的作品的最顶点的就是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性质的出现。既然是这样,那么,形而上质也必然产生文学性。这个文学性是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从这诸多层面来理解文学性,当我们在具有文学作品是有机整体的理解的时候,那么,我们所最终把握的文学性,其实就是英加登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所说的审美价值的“质的和谐”。在这样的发现基础上,我进而意识到,这是一个逻辑起点,可以为文学批评从“多层次的立体结构”来全面动态地认识“文学性”开拓了思路;文本多层次立体结构意味着划出了文本本体的边界,文学批评由此明确了批评指向何处;多种方法可以恰切地进入文本不同层次,并且在各层次间展开对话和交往,形成批评话语的间性。
“形而上质”层面是某些优秀文学作品的特性,对于这种特性,并非都一律可以用理性的逻辑的语言条分绺析地解释出来,事实是有的作品无法解释,《俄狄浦斯》就是这样的例证。被希利斯·米勒概括为“难以解释的符号”。
面对“难以解释的符号”这样的艺术作品,文学批评该怎样入手呢?我曾经试图对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作文本批评,但是,不论是采用人物心理分析方法、功能分析方法还是结构主义的叙事视角分析等怎样的批评方法,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似乎永远不能抵达这部作品的真正意味,无法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理解。这种感觉恰好证明了希利斯·米勒确认的“难以解释的符号”现象。
现在,一个“难以解释的符号”就在面前,如何对应着这种“难以解释”而努力做出解释呢?
我首先借鉴了德国现象学批评家瓦尔特·比梅尔对《饥饿艺术家》深刻独到的分析,比梅尔在《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中对《饥饿艺术家》做的是现象学研究,他采用了“解释”和“解说”两个步骤。在解释中,比梅尔“试图分析小说的内在联系,或者艺术作品的结构,以揭示出作品中的一切是如何必然地联系起来的”。[2](p7)比梅尔发现,这个故事的内在逻辑,就是不断地颠覆原来所追求的意义,直至饥饿艺术家彻底地颠覆了自己最初将饥饿艺术表演作为一门艺术的追求为止。在解释的基础上,比梅尔继而询问:在这个结构得到揭示之际,有什么东西启示出来呢?比梅尔接着解说到:“按照我的解说,这篇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自由理念的反常化”。也就是,小说的情节就是意义颠倒的过程及其辩证法。“作为置身于意义与荒谬之间的动物,人总是面临着沦于荒谬的危险”。[2](P2)也就是说,追求自由本来是人的理想,但是在现实中,人却迫不得已地不断地颠覆对自由的追求。
比梅尔确实做出了他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的结果就是进一步使我们确认了《饥饿艺术家》是一个“难以解释的符号”,因为,比梅尔的解释其实留下了很多漏洞。最为明显的漏洞就是,小说在回忆性基调中,以冷静和朴实的第三人称,叙述了饥饿艺术家的遭遇。比梅尔对于自由理念的颠倒过程的分析,是在饥饿表演是艺术似乎不证自明的前提下展开的。饥饿表演是艺术吗?其实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这是谁的逻辑?其实在逻辑起点上,比梅尔的分析就隐藏着被颠覆的危险和可能。
既然“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和理解的东西,可以用一种既不完全澄明也不完全遮蔽的叙述来表达。我们传统中伟大的故事之主要功能,也许就在于提供一个最终难以解释的符号”,希利斯·米勒这段话意味着小说不可以解释,任何解释都意味着可能被推翻,意味着还可以从其他方向来解释。各种解释共同构成对作品的理解。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采用假设命题式的方式来批评诸如《饥饿艺术家》这样的作品呢?。
所谓在假设性命题中重新提问,是基于已经通过直觉感觉到这个作品的不可解释,于是依据文本所叙述的虚拟情境及故事,假设几种命题,并用这些命题逐一地与文本的虚拟情境及故事对应地分析,由于不可解释,所以,分析的结果势必逻辑地发现其中的悖论,在这种悖论的展开中体悟审美意味,展示艺术价值产生的原因。
二、在假设性命题中显现的《饥饿艺术家》
对于《饥饿艺术家》这个个案,我提出的假设式命题是“饥饿表演是艺术”与“饥饿表演不是艺术”。
如果“饥饿表演是艺术”,那么会是怎样呢?关于艺术的定义虽然说法纷纭,但有几点是必须的。首先,从艺术创造者的主体来看,艺术家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艺术,艺术活动是自觉自愿的行为,其次,艺术品是艺术家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其中凝结着真善美,并且超越于任何功利性目的。第三,对于欣赏它的人来说,则是为了获得某种超越于物欲和外在功利的精神满足。用贺拉斯的话说,就是“甜美”和“有用”,精神上的愉悦和激动,在“甜美”中艺术达到了改变人的心境和精神的目的。
依此把握“饥饿表演是艺术”,我们发现,尽管饥饿艺术家的表演最初是自觉自愿的,是他自己选择了饥饿表演这样的艺术形式,但是,一旦他开始了自己的表演艺术,饥饿持续多长时间这样重要的事情却从来没有由他自己决定过,而持续多长时间变得不再重要的时候,他有权利决定了,却没有任何意义了。决定艺术质量的原则变成非艺术家的人来确定,这时,艺术家自觉自愿的性质被消解了。这样的表演能称作艺术吗?从艺术家作为创造的主体的角度来看,饥饿表演是艺术的命题势必受到质疑。
如果说饥饿表演是艺术,那么,艺术品是艺术家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是真善美的凝结物,超越于任何功利性目的。也就是说,艺术家必定能够创造出什么,这个“什么”是原来所没有的,比如,雕塑,作为艺术品,是用某一种物质创造而成的空间三维的物体存在于那里,例如罗丹创造的雕塑“思想者”。比如,绘画,是用线条和色块创作的空间二维物体存在于那里,例如徐悲鸿画的马。比如文学,是由语言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是以多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形态存在的,即便作品的制版被销毁了,只要有人能够通篇背诵下来,这个作品的多层次的立体结构依然存在,意味着作品还存在。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奥狄修斯》,以及托尔斯泰创作的《复活》等都是这样的艺术品。再比如舞蹈,舞蹈艺术家运用自己肢体,在空间中创造出一些符号,并且使这些符号在连续性表现时具有了意义,以此传达特定的情感……,总之,艺术家总是在有所为之后,创造出一个特定的实体……那么,饥饿表演的结果却没有物质的承担者。饥饿艺术家是无所为的。在他无所为的“不吃”中没有什么东西诞生。观赏者看什么呢?
如果饥饿表演是艺术,欣赏的人应该是为了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并且与表演者在对艺术的理解上达成基本的共识。从小说的叙述看,人们获得的仅仅是好奇心的满足,不论当初对饥饿艺术家感兴趣还是后来不感兴趣,都取决于好奇心。关于好奇心,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第36节中说过:“而自由空闲的好奇操劳于看,却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进入一种向着所见之事的存在,而仅此为了看。它贪新鹜奇,仅止为了从这一新奇重新跳到另一新奇上去。这种看之操心不是为了把捉,不是为了有所知地在真相中存在,而只是为了能放纵自己于世界。所以,好奇的特征恰恰是不逗留于切近的事物”。[3](P200)饥饿艺术家将忍受饥饿这样一种人类极限性的行为看作人生的极致,是一种美,当极限显示出美的时候,饥饿表演当然是艺术。饥饿表演者希望欣赏者欣赏的是他饥饿的极致状态及其美,而观赏者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对于饥饿表演者的极致之美却并不在意。所以,饥饿艺术家并没有能够在饥饿所达到的极限所产生的美这一点上与观众达成共识,并没有通过他的艺术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启示观赏者回归人类精神的家园……。
如果“饥饿表演不是艺术”,那又会怎样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同样也会面临一系列困境。首先是饥饿艺术家,最初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是非常执着和忠诚的。在他看来,饥饿表演是将人忍受饥饿的极致状态展示给人们看,而这种极致状态是值得欣赏的。他对于饥饿艺术也是极为忠诚的,“饥饿艺术家在饥饿表演期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点食不进的,你就是强迫他吃他都是不吃的。他的艺术的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当饥饿表演不再兴盛的时候,他坚持不改行,“主要是他对于饥饿表演这一行爱得发狂,岂肯放弃”。从饥饿艺术家的角度来看,他是相信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是艺术活动的。而且在饥饿表演兴盛的时代,他的表演确实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如果说,饥饿表演不是艺术,那么饥饿艺术家的多年追求和他的失落就无法解释。
从艺术品的角度看,由于饥饿表演没有什么承载物,是不符合艺术品的规定性的。但是,《饥饿艺术家》作为历史流传物,至今一直被人们所欣赏,而任何欣赏,其实都是在一定的前理解中层开的,在《饥饿艺术家》发表的当时,还没有行为艺术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则不同了,我们今天的读者是在对行为艺术的理解视野中阅读这篇小说的。所以,如果说由于饥饿表演没有什么承载物而否定其艺术性,就变得没有道理了。在今天看来,饥饿艺术可以归类于行为艺术。所谓的行为艺术,是为着某一种观念,在某一种行为过程中使这种观念得以传达,但这种观念不能被物化为某种固定的形式。行为艺术与其说是为了审美,毋宁说是为了“观念”,因此,行为艺术一般需要借助于媒体加以评论而得到表达。如果用行为艺术的界定来看,饥饿表演属于艺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分析表明,一个命题在历史性的解读过程中,其含义会发生变化,这无疑造成作品意义的含混。这种情形确实如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有一种文学史现象值得深思,即越是杰出越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与历史和社会的关系就越是复杂。它一方面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情境和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又是对这个时代的反思与批判,进而超越了这个时代”。[4](p248)《饥饿艺术家》产生出了一种力量,让饥饿表演所引出的问题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变成一个具有永恒意味的问题,并且不断地被置疑。
如果说“饥饿表演不是艺术”,对于观赏者也是背谬的。当年人们曾经对于饥饿表演的观赏趋之若骛,虽然如同前面提到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好奇心,但是,好奇心与饥饿表演者毕竟在“看”与“被看”之间形成了需求和给予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与艺术的创造与接受有所重合。并且在当年的观赏者中还有如同叙述者所叙述的“内行的人”,“内行的人”是理解饥饿表演者的,是从内心里潜在地认可这种表演是一种艺术的。如果我们将欣赏者的视角调整到文本之外,那么饥饿艺术家的表演无疑就是今天所谓的行为艺术,尽管是有欣赏者是带着好奇心来观看饥饿表演的,但是这种表演形式的变异性与陌生化无疑给欣赏这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无疑也是符合艺术理念的。行为艺术不是必须提供艺术品,重要的是在被观看的过程中,使得某种观念展示出来。
三、我们如何认识假设命题式批评
在对《饥饿艺术家》的假设式命题批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识这种批评方式的意义和性质。
第一,对应着叙事艺术是“难以解释的符号”的品质,假设命题式批评使“难以解释的符号”的难解过程化了,使之显得更加难以解释,艺术品谜一样的特征更加突显。这一点与我们采用结构语义学或者原型批评等其他方法分析作品的机制是不同的,那些批评方法对作品分析的结果是使作品内部的肌理更加清晰,或者使作品的意象由于置入历史文化的河道,使作品的意象得到了文化底蕴的解释。但是,在假设命题式批评中,比如,《饥饿艺术家》在饥饿表演是否是艺术的问题中,变的更加复杂,原来没有显现出来的悖论得到了彰显,既然饥饿表演是否为艺术都成了问题,那么,在这个基点上的一切判断和分析都随之成了问题。这只是我们设置的一对假设式提问,其实比如饥饿对于所有的人都是有吸引力的吗?饥饿的感觉对于饥饿艺术的关系等问题,都可以作为假设式问题被提出来。这篇小说具有潜在蕴涵的力量,可以承担得起各种假设。小说叙述到:“孩子呢,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学历和生活阅历,总是理解不了——他们懂得什么叫饥饿吗?”“试一试向谁讲讲饥饿艺术吧!一个人对饥饿没有亲身感受,别人就无法向他讲清楚饥饿艺术”。总之,假设式批评在浑然一体的难以解释的艺术品面前,虽说让艺术品的不可把握更为突显,但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品的文学意味却得到了挥发。“不可把握”这个效应本身就是假设式批评的结果,表明我们切近了艺术。
假设命题式批评使“难以解释的符号”的难解特性过程化,显得更加难以解释,像谜一样的艺术特征更加突显。这个效果符合文学批评的任务吗?
文学批评,用英加登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的看法,是属于“前审美”研究范围的。英加登说:“同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审美经验相比较,它的前审美研究似乎要简单得多,因为它专注于文学的艺术作品不依赖于审美经验的那些特性……对于文学的艺术作品这种前审美认识首先上一发现那些使它成为一部艺术作品的特性和要素,即在审美具体化中构成审美相关性质的基础的东西”[5](p242-243)对于这种东西,英加登称之为“艺术价值”。因为文学作品具有“艺术价值”,普通文学阅读才能产生“审美经验”。那么,假设命题式批评通过使“难以解释的符号”的难解过程化了,意味着展示了产生艺术效应的机制,而这正是文学批评所应当承担的“前审美”研究的任务。
第二,对于叙事性文本的批评,必然要面对作品中人物。假设命题式批评对于人物有独到的展开方式。在其他批评方式中,作品中人物命运展示出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特性。但是在假设命题式批评中,人物由于尴尬背谬被置于形而上意味之中,于是,读者对人物的艺术感悟不仅深切,而且始终与形而上的玄思相伴随。批评的过程也就成为了感悟玄思的过程。在《饥饿艺术家》的假设式批评中,我们所面对的饥饿表演者这个人物。他没有自己的名字,一开始就被不容置疑地确定为饥饿艺术家。这让他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我们都知道,“塑造人物最简单的方式是给人物命名。每一个‘称呼’都可以使人物变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和个性化”。[6](p245)如果没有名字,给予读者的阅读感受是主人公与他的身份合一了,人物就是饥饿艺术家,读者只能把人物作为先验的饥饿艺术家来看待,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被一个身份所取代了。当我们把主人公作为一个人感悟的时候,“他是非常孤独的人”的感觉油然而生:看守对他所谓的饥饿艺术不理解,夜班看守们故意远远地聚集在一个角落里打牌,以便给他留下一个便当让他稍稍吃点东西,这让他很苦恼,他感到不被理解的孤独;为了证明自己始终没有吃东西,他不断地唱歌,可是这竟被人们赞叹为技艺高超,“竟能一边唱歌,一边吃东西”;也有的看守很负责任,这让饥饿艺术家感到宽慰,“当天亮以后,他掏腰包让人给他们送来丰盛的早餐……也有人对此举不以为然。他们把这种早餐当作饥饿艺术家贿赂看守以利自己偷吃的手段”……饥饿艺术家是个彻底的孤独者,无论他怎样做,不被他人所理解是绝对的,从饥饿艺术被人们所瞩目,到饥饿艺术被人们所淡漠……他独自经历了这一切,而且无处言说。这一切都是所谓的饥饿表演引起的,尤其是他本人执着地将自己的表演看作是神圣的艺术所造成的,如果我们对这样的所谓的艺术加以置疑,那么,饥饿艺术家的行为将变得荒谬,他的孤独也随之丧失任何价值,悲剧性更加突显。无论饥饿表演是否是艺术,他都是悲剧性的人物。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饥饿艺术家的孤独,是他个人的还是人类性的,正因为他没有名字,饥饿艺术家就是他的名字,所以他的孤独和悲凉具有了人类性:我们人类创造了各种艺术,或者说在不断地探索各种新的艺术,但是人类在创造各种艺术的同时,那些艺术是否也在捉弄人类呢?或者进而说,是否有些人类艺术以艺术名目而践踏人类的尊严,成为人类的异己?这样的分析结果符合揭示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批评目的。
第三,由于假设式批评是以提出命题式的方式切入作品,所以,其实是在文学作品的形而上层面进入的,这恰好与艺术作品形而上的特性相吻合,便于在形而上层面上使文学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挥发。韦勒克和沃伦认为,形而上的层次是在小说“世界”之上的层次。“形而上的性质”,它是和“世界”紧密相关的,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或暗含在这个世界中的“调子”是同一个东西……[6](p254-255)“难以解释的符号”这一类作品,一般是具有形而上性质的。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具有形而上质这个层面,但是具有这个层面的作品一般是优秀之作。形而上质的作品具有难以解释的特点,作品就像一个符号。对于这种像一个符号似的作品,在哪个层次进入更适合于让文学性挥发出来呢?文学性,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概念。雅格布森说:“‘文学性’,即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因素”。[7](p305)不同的小说艺术作品,文学性所寄予的层次是有所区别的,有的小说作品,在小说“世界”的层面,文学性就基本完全挥发出来了,而《饥饿艺术家》这样的小说,仅仅知道了一个故事,了解了一个世界,文学性还远没有挥发出来,只有在感性地接受了这个小说的“世界”之后,进而感受和体悟那个无法言说的“滋味”,并且能够被那个“滋味”所震撼的时候,文学性才最大限度地实现了。通过假设式批评,让命题显示出背谬,背谬无法用理性的语言把握,使我们的阅读经过“世界”的层面,直逼形而上层面,然后在这个层面更感到困惑,希望洞察其中滋味的愿望更加强烈,直到悟出形而上的意味……饥饿艺术家让我们深思人类的状况和前景,巨大的悲剧感油然而生,并伴随着悲悯情怀……。康德说世界上永远都会有形而上学。因为,追问终极事物的形而上欲求是人这种具有高度智慧和自我意识的存在的本性。人类存在的意义,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万物的本原等形而上学问题,是超越时代和民族的,虽然不同时代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解答的重点有所不同,虽然不同民族的探究方式迥然异趣,但问题始终是存在的。形而上学不仅依存与哲学中,也依存在文学中。具有哲学意味的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是永恒的,但是对于艺术中形而上意味的把握却是比较有难度的,而假设式批评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显示和揭示文学作品的哲学意味。
标签:饥饿艺术家论文; 艺术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俄狄浦斯王论文; 卡夫卡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诗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