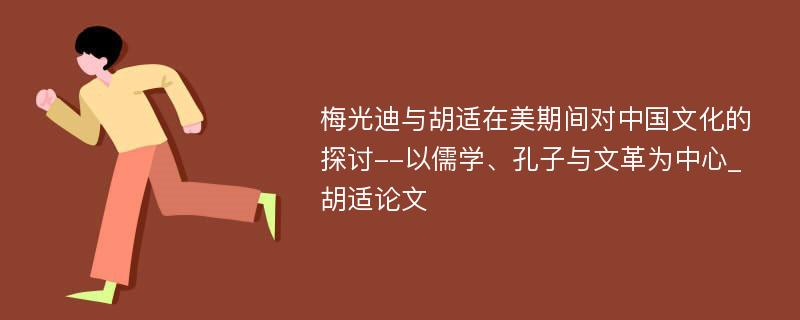
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以儒学、孔教和文学革命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文学革命论文,儒学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2年初,刚到美国不久的梅光迪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吾人生于今日之中国,学问之责独重:于国学则当洗尽二千年来之谬说;于欧学则当探其文化之原与所以致盛之由,能合中西于一,乃吾人第一快事。”① 其后,胡适于1914年初发表《非留学篇》,也阐发了与梅光迪非常相近的观点:“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需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② 梅、胡二人抱有共同志向,在留美期间围绕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本文主要使用当年梅、胡通信,从二人讨论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二人之间的思想互动,再现这一时期梅光迪和胡适思想发展的过程和特点。③
一、关于复兴古学
1909年,梅光迪、胡适二人经胡适的族人胡绍庭介绍在上海相识。此后,胡适于1910年考取庚款奖学金赴美留学。翌年,梅光迪也考取庚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怀着融合中西文化的志向,梅光迪和胡适一边积极地汲取西学,一边对中国文化进行思考。不过,相对西学,他们对中国文化显然更为熟悉和了解,思考和讨论的重点也自然放在中国文化上。当时,梅光迪远渡重洋,随身携带的是《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经义述闻》等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几十种,以至于父亲为此发出劝戒。④ 从目前保留下来的信件看,留学最初一两年,梅光迪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复兴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古学”,而胡适则予以积极的回应,提出自己相应的看法。
梅光迪认为:“孔子集群圣之大成,诸经多其手订,又为教育大家,故凡古人学术,吾辈皆推本孔子,亦何不可,且六经之教具在经书,非失传也。”⑤ 他高度评价孔子及其学说,“此老实古今中外第一人”,“孔子之学无所不有”。⑥ 关于后世儒学,梅光迪认为,汉宋诸儒扭曲了孔学的真精神⑦,而颜元、李塨的学说,则是“独得先圣精髓而与西人合”,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是“三代后绝无仅有之人物”,他们的礼教及民权思想,“皆孔孟嫡传”。⑧ 因此,梅光迪极力主张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古学救国”。⑨ 刚到美国,梅光迪就约胡适“回国后当开一经学研究会”,研究汉代至清代的儒家经典,“务使学而即用,不仅以注解讲说了事”。梅光迪设想将典礼作为学校的德育教科,实行演习,并推广到社会;冠、婚、丧、祭、乡饮酒、养老及学校制,也可以实践运用;射礼,可改为兵操剑术拳法。梅光迪认为,“此事若办到,吾恐欧美文明又差我一等耳”。⑩ 梅光迪强调在实践中复兴古学,而不仅仅局限于口头倡导,同时他还强调要有批判精神。从这两点出发,梅光迪不满当时影响较大的国粹派,批评他们“不脱汉宋儒者之范围,登几篇宋明遗民著作及几句说经说史之语,即谓之为《国粹学报》,以保存国粹自命矣。须知我辈保存国粹,口说固不可少,然尤在实行,而口说亦当洗去汉宋学说。”(11) 与对国粹派的批评相比,梅光迪对西化派的批评则更为尖锐。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尖锐地抨击留学生中不尊重祖国学术极端西化的人为“洋奴”(12)、“不学妄人”(13),认为他们与腐学究一样“足以亡中国”。(14) 在这一问题上,胡适和梅光迪的思想一致。胡适也反对极端西化,以留学生不懂祖国学术文化为耻,认为不研究祖国文字学术,不知本国历史文化风俗,数典忘祖,会导致无自尊心,更无法传输西方文明。(15)
胡适写给梅光迪的书信没有保存下来。他的观点,现在只能通过梅光迪信中保存下来的信息,参以其留学日记和其他资料加以考察。(16) 1911年9月26日,胡适致信梅光迪(从时间上判断,这封信应是对梅9月22日来信的回复)。(17) 梅光迪接到来信后,在9月30日的回信中引述了胡适的观点。胡适说:“吾国经籍譬犹理化之有实验场,今日外人试之而益验,足以坚吾辈信古之心,证吾辈复古之效为可喜。”可见,胡适赞同梅光迪的复古主张。在其后的信中也能反映类似的信息。1912年6月25日,梅光迪致函胡适说:“欲得真孔教,非推倒秦汉以来诸儒之腐说不可,此意又足下素表同情者。”“素表同情”一语可以体现出胡适对复兴古学的赞同态度。梅光迪在信中还直接称赞胡适为“热心复兴古学之士”。(18)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二人观点也很相近。如胡适在信中提到“礼即法”,梅光迪回应说“此言极确”,并加以发挥。(19) 在梅光迪1912年给胡适回信中还曾出现这样的话:“先秦诸子之学极有研究价值,吾辈归去后,当设会研究,刊行书报。此吾国学术上之大题目而无人提及。”(20) 这说明,二人当时讨论古学的范围不限于儒学。从现存资料看,二人并未在这一问题上展开讨论。从后来二人思想的发展看,胡适注重子学的地位和价值,而梅光迪则更强调儒学。(21)
胡适痛恨西方传教士贬低中国文化。(22) 一方面,他通过演讲积极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对美国传教士的傲慢、施恩于人的态度和武断、教条作出委婉的批评。(23) 胡适的这些做法得到梅光迪的赞扬。这在梅胡通信中有许多体现。在1913年初的一次考试前,梅光迪收到胡适关于孔教的演讲稿,“读毕豪气百倍,至名学讲堂,自觉彼讲师读书太少,以其不懂吾孔教也。又觉西洋人所著哲学史不足读,以其中无孔子学说,既有,亦皮毛也。足下所见,迪无间然,与拙作多有相合之处(此前梅光迪写有The Oriental Philosophy of Life——引者注)”。(24) 在考完试后的2月5日,他再致信胡适说:“读演讲孔教稿,倾倒之至。足下所见,与吾不约而同之点甚多。”(25) 1913年,梅光迪读了胡适在某教堂的演说后致函胡适,说:“足下某礼拜寺之演说,字字如从吾心坎中出来,彼教士稍以人类待吾者,当恍然悟矣。”他接着说:“天下最伤心之事,莫如蒙冤莫白,任人信口雌黄而无有为之辩护者。吾国旧文明、旧道德自谓无让人处,而彼辈乃谓为Heathen,是可忍孰不可忍,足下真爱国男儿!”(26) 与胡适一样,梅光迪认为传教士“不真解吾国文字、学术、风俗,徒有害无益”。(27)
在对儒学的基本态度和评价上,这一时期的胡适与梅光迪可谓同调,但在对待儒学的一些具体认识上,如对程朱理学、颜李学派的看法上,两人的观点却不相同。
梅光迪在高度评价孔子的同时,对汉宋儒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对胡适说:
迪观汉儒说经与人情物理多不合。如袁才子所谓如郑康成注礼,则天子之冕当重数十斤(想即《礼记·玉藻篇》),有是理乎?
至宋儒则更变本加厉矣。程、朱腐儒窃得孔子性近、孟子性善及《大学》正心诚意之说,遂日喧于口,号于众,以为圣学真传在此,不知孔子罕言性,孟子性善亦不过因时人问答偶一及之,本非重要学说;至《大学》正心诚意,始于致知格物,终于治国平天下。致知格物者,即礼乐兵农政治经济也(习斋先生解致知格物最痛快,最切实)。程朱则以静坐观心为正心诚意之学,其解格物为即物穷理,不知所穷者何理,虚无缥缈,举圣人之礼乐兵农政治经济皆不讲,于是圣人之学亡矣。儒者以空虚为学,皆变本加厉为无用之人矣;且其伪造三纲之说,以助专制之虐。而孔孟伦理政治学说,反对君主专制者,皆不敢道一字。种种程、朱之邪说,莫非以叛圣为归。故吾辈将来救国,以推倒汉宋学说为入手;不推倒汉宋学说,则孔孟真学说不出,而国必亡。(28)
梅光迪对宋儒的批评极为尖锐。他后来反复向胡适说明这一思想。他说:“程朱空谈性命,瞑目静坐,是真天下废物耳”(29),“宋儒出,倡为心性之学(心性为孔教之一部分而已),重于诵读讲章而轻于实用,又偏重三纲之说,于是人道益苦,而读书之人均为无用之人矣”,“孔教之不行于吾国,乃后世腐儒之咎,非孔子之咎”。(30) 梅光迪还对所谓的“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君要臣亡不得不亡,父要子死不得不死”等“君道臣节”的观念做了具体的批判,认为都不符合孔子儒学精神。(31) 在批评理学的同时,梅光迪高度赞扬颜元、李塨,认为他们二人“真能直接孔孟”,“以复古为学”。(32)
胡适也反对汉儒解经(33),同时赞扬先秦儒学中的积极因素。如他在文章中称颂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学说,并认为孟子是东方的孟德斯鸠。(34) 但他却反对梅光迪对理学的批评。在收到梅光迪1911年9月30日批评宋儒、褒扬颜李的来信后,他于10月4日写了一封两千言的长信,对梅光迪的观点加以反驳。(35) 这封信目前已看不到了,但其主要观点却在10月8日梅光迪的回信中保留下来。胡适认为“习斋言行皆甚鄙陋”,“读书甚少”,“《习斋年谱》之文俗不可耐”,而“朱注为千古第一伟著”,“程朱心性之学为世界哲学之一大派”,是“人类最高尚之智识”。梅光迪对这些观点在回信中逐一批评。(36) 从后来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胡适接受了梅光迪的观点。前文谈到,1912年底胡适曾做关于孔教的演讲,梅光迪读过演讲稿后,对胡适说:“足下论程朱极合吾意。孔子之学无所不有,程朱仅得修己一面,于政治伦理各方面似多误会。故自宋以后,民生国计日益凋弊,社会无生气,书生无用,实程朱之学陷之也。足下论阳明极透彻,论大同小康亦详尽,论孔子不论来世,谓其诚实,尤令吾叹赏。”(37)
客观地说,梅光迪对理学的尖锐批判和胡适对理学的热情赞扬各有道理,因为二人观察理学的角度不同。梅光迪关注的是理学的社会功能或意识形态作用,而胡适则强调理学的学术思想和人身修养的意义。从各自的思想看,二人对对方的思想都有所吸收;梅光迪对颜李学派的推崇,也影响了胡适。(38)
梅、胡二人对复兴古学的讨论,是他们继承和批判传统、为中国创造新文化的尝试。虽然二人对儒学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但主张对其进行改造则是一致的。不过,由于初到美国之时,二人对西方现代思想学术还没有系统、深刻的认识,兼以二人身处异邦而产生的强烈民族自尊心,“为祖国辩护”的防卫心态(39),以及因之而来的对祖国文化的强烈珍爱之情,更由于他们没有受到辛亥革命后普遍王权丧失而产生的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的直接冲击(40),他们还难以对儒学做出全面、深刻的审视与批评。梅光迪提倡对儒学加以分析,洗去其谬说,继承其精华,合中西于一,这是一个合理的思考。他对儒家三纲学说的批判,态度十分鲜明。但梅光迪在突破汉宋儒学后,却试图全面恢复以孔子为代表的“古学”,这样,他又陷入了原教旨主义般的对孔子儒学崇拜的误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没有超越他试图超越的国粹派。他的观点与国粹运动中的“真孔”论极为相似。(41)
二、关于孔教运动
进入民国之后,孔教运动在国内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与梅、胡讨论的复兴古学密切相关的问题。梅光迪对设立孔教的主张十分赞同,并从融合中西文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通过融合孔教和基督教以建立中国之宗教的主张。梅光迪认为,辛亥革命后,“吾国政治问题已解决,其次急欲待解决者即宗教问题”,而建立中国宗教的具体办法是“合孔教与基督教于一”,“在昌明真孔教,在昌明孔耶相同之说,一面使本国人消除仇视耶教之见,一面使外国人消除仇视孔教之见,两教合一,而后吾国宗教问题解决矣”。(42) 可见,梅光迪建立孔教的目的是要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建立新的信仰和精神支柱,同时还有以此消除中西隔阂、融合中西文化的考虑。
梅光迪对儒学的认识前一节已经讨论。关于基督教,梅光迪初到美国时曾一度反感轻视(43),但后来逐渐感受到其在道德塑造上的重要作用。1912年6月21日到24日,梅光迪参加了4天的基督教青年会大会,6月25日他对胡适说:“此去所得颇足自慰,其中人物虽未与之细谈,其会中组织虽未细究,然耶教之精神已能窥见一斑,胜读十年书矣。”“盖今后始知耶教之真可贵。始知耶教与孔教真是一家。于是迪向来崇拜孔教之心,今后更有以自信,于是今后提倡孔教之心更觉不容已。”基督教加强了梅光迪复兴儒学的信念,他想把儒学也改造成宗教,并希望与胡适共荷此任。(44) 他称赞倡导建立孔教会的陈焕章为“真豪杰之士,不愧为孔教功臣”。(45)
从梅光迪给胡适的信来看,胡适不完全赞同梅光迪的观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批评意见,而梅光迪接受了他的批评。1912年7月,梅光迪在读了胡适的回信和“北田日记”后(46),说:“吾子匡我甚是,然吾二人所见已无大异矣。”在梅光迪致胡适的信中还有这样的话:“惟陈君(陈焕章——引者注)亦以孔教为宗教,若以吾子之说绳之,亦有缺憾,尚望吾子有以告我。”(47) 两人间“无大异”说明二人主要观点一致或相近,而胡适对梅光迪有所匡正,又说明二人间观点存在差异。其后9月15日的信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信中,梅光迪再次赞扬“北田日记”有“极精到处”,虽表示“其间虽亦有与鄙见不同者”,不过,在梅看来,这一不同只是“细微之点”,不值得再争论。(48)
现在已看不到胡适的回信,“北田日记”亦早已佚失,所以无从得知其具体主张。但结合胡适这一时期的书信、日记和公开发表的文章,我们可以窥测胡适和梅光迪之间的异同。二人的共同点是赞同孔教运动。这一点可以从胡适在1914年5月发表在《中国学生月刊》上的《中国的孔教运动》一文中得到证明。在该文中,胡适使用大量的篇幅,通过对孔教运动的历史、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道德状况、孔教运动的领导人等方面,来论证孔教运动的正当性,反驳在美国流行的孔教运动是中国进步历史中的倒退的观点。(49) 梅、胡二人观点相异的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当时的文献中看出一些端倪。胡适反对简单地复古和简单地把儒教改造成宗教,而主张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在1913年胡适给信仰孔教的朋友许怡荪的信中,他表示不赞成许主张的侧重三礼、以孔子为宗教家、将冠婚丧祭等事复古以为孔教的宗教仪式的观点。(50) 与孔教运动的主张者不同,胡适对孔教运动做了很多的思考。在1914年1月23日日记中,胡适以孔教为题做了一篇札记。他写道:“今人多言宗教问题,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近来余颇为此事萦心。昨复许怡荪书,设问题若干,亦不能自行解决也,录之供后日研思。”胡适的问题是:立国究需宗教否?中国究需宗教否?如需有宗教,则以何教为宜?如复兴孔教,究竟何者是孔教?今日所谓复兴孔教者,将为二千五百年来之孔教欤?抑为革新之孔教欤?吾国古代之学说,如管子、墨子、荀子,独不可与孔孟并尊耶?如不当有孔教,则将何以易之?(51) 胡适的《中国的孔教运动》一文在明确表示赞同孔教运动的同时,也提出孔教运动还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运动,它仅仅是一个复兴孔教而不是改革孔教的运动。他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孔教运动应思考的问题。另外,关于引进基督教的问题,胡适认为中国引进基督教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目前中国接受基督教意味着另一场破坏传统的灾难(52),这与梅光迪提倡的两教合一的观点不尽相同。从当时二人的通信看,梅光迪后来对自己两教合一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修正和阐述,这似乎是受到了胡适的影响。1913年7月梅光迪在读到胡适在某教堂的讲稿后,大加赞扬,致信胡适,阐述了自己对基督教的看法。他认为宗教要因地制宜,要适合人民的习惯风俗,而不能使人民变易习惯风俗而迎合宗教。他说:“吾人吸收耶教之精神可,欲使吾人全弃其旧者而专奉耶教,使之喧客夺主,岂非做梦乎?”(53) 梅光迪表示反对教堂和教士,认为这些不能代表基督教,更反对把这些照搬到中国,因为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54) 他还向胡适详细阐述了他的合孔教耶教为一的主张,不是完全照搬基督教,而是要汲取基督教的精神。梅光迪在此虽然没有阐述基督教的精神是什么,但联系到当时他和胡适对基督教的观感,可以推知,基督教给中国学生的最大冲击是它在塑造道德方面的巨大力量。这也是梅光迪试图将注重内在超越、重修身、重伦理的儒家学说与之融合,为政治革命后的中国建立新道德规范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在汲取基督教精神这一点上,胡适和梅光迪又有许多相同之处。胡适到美国后,曾受到基督教的强烈影响。他认为基督教能“变化气质”,使人成为像程朱一样令人敬爱的人。他自己也几乎成为一个基督徒。(55) 胡适后来并没有成为基督徒,而且在1912年后,开始以理性的态度认识基督教中的迷信和许多教会的商业主义、愚昧、卑屈品质和“基督教”国家对弱小国家赤裸裸地使用暴力的倾向,并对此加以批评。但胡适并没有完全否定基督教,没有拒绝其文化特质,他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绝未丧失信念。他所要的是抽去基督教中的宗教因素,而接受其俗世价值。(56) 后来五四时期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也都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不同的是,与当时平视中西的梅光迪和胡适不同,新文化派更强调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并试图吸取基督教的精神来补充中国文化的不足罢了。(57)
除为中国人建立道德规范的思考外,梅光迪的孔教主张还有为西方世界提供道德规范的意图。梅光迪认为:“孔教兴则耶教自兴,且孔、耶教各有缺点,必互相比较,截长补短而后能美满无憾。将来孔、耶两教合一,通行世界,非徒吾国之福,亦各国之福也。”(58) 他曾对胡适说,西方政以贿成,无告之民多,杀人劫案多,卖淫业多,离婚案多,“彼物质文明固尚矣,其道德文明实有不如我处”。(59) 所以,梅光迪提出:“我辈决不能满意于所谓modernization civilization,必求远胜于此者,以增世界人类之福,故我辈急欲复兴孔教,使东西文明融化,而后世界文明可期,人道始有进化之望。”(60)
梅光迪批判西方现代文明与其“积极悲观”的认识论有关。梅光迪认为:“古今大人物为人类造福者皆悲观哲学家,皆积极悲观哲学家,彼皆不满意于其所处之世界,寻出种种缺点,诋之不遗余力,而立新说以改造之。”(61) 这一观点是他从西方文明进步史中总结出来的。他对胡适说:“西洋人见人生有种种痛苦,思所以排除之,故与专制战,与教会战,见有人生之疾病死之,遂专力于医学,见火山之爆裂,遂究地质,见天灾之流行,遂研天学及理化,此皆积极悲观,因有今日之进化。吾国数千年来见人生种种痛苦,归之于天,徒知叹息愁困而不思所以克之,此纯属消极悲观,所以无进化也。”(62) 梅光迪还认为:“世间一切事皆有美恶两方面,在观察之者如何。爱之者只见其美,憎之者只见其恶。如今之世界,在普通人视之如天国,在社会党、无政府党人视之如地狱。两面皆有真理,然迪实赞成悲观一派。”(63) 因此,梅光迪强调西方现代文明的消极面,欲以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融合的办法,来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
而胡适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留学美国期间,胡适除课堂学习之外,还积极投身美国社会;虽不间断地自修中国学术,但却更积极地汲取西方文化,对西方现代文明,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社会文化都极为赞赏。所以,在对待西方道德文明的问题上,胡适不赞成梅光迪的观点,曾予以规劝,批评梅光迪思想过激。(64)
孔教运动既是一个思想运动,也是一个政治运动。经过孔教运动的激荡,尤其是它的迅速失败,促使胡适和梅光迪对儒学做进一步的思考。孔教运动在国内政界遭到阻力,在思想界遭到强烈批评,中国是否需要宗教等胡适不能自行解决的疑问在实践中迎刃而解了。(65) 而帮助胡适完成这些思考的理论武器是实验主义。1915年后,接受了实验主义的胡适对儒学的态度,由试图对其改革使其在现代中国继续存在,改变为强调非儒学派的价值,把复兴非儒学派作为接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土壤。(66) 与胡适不同,梅光迪在接受了新人文主义后,强调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去发掘孔教的意义。不过,这时梅光迪心中的孔教也已不再是宗教之“教”了。(67)
三、关于文学革命
改良中国文学,可以说是胡适和梅光迪二人的共同愿望。还在1912年初,胡适在康奈尔大学酝酿改科时,梅光迪就去函支持:“足下之才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一国文学之进化,渐恃以他国文学之长,补己之不足。)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68) 梅光迪支持胡适并非偶然,因为他自己也“以创造新文学自期”(69),在革新文学问题上,二人可谓相知。正因为如此,胡适每有新见解,首先告诉梅光迪,而梅也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据胡适的说法,1916年2月到3月,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觉悟。他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70) 这是胡适后来提倡文学革命的基本理论。(71)
3月间,胡适写信把这一新见解陈说给梅光迪。梅甚为赞成,回信说:“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聩。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 etc)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俗俚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耳。”(72) 胡适得到梅光迪的赞同非常高兴。(73) 虽然此前二人关于白话入诗的问题曾发生过争论,但在这封信中,梅光迪表示坚决支持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而不愿再做争论。他说:“至于诗之文字问题,迪已不欲多辩。盖此种问题人持一说,在西洋虽有定议,在吾辈则其说方在萌芽,欲宗于一是,必待文学革命之后,今若与足下争,恐徒闹意见,真理终无从出耳。”(74) 可以说,对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梅光迪首先是一个支持者,然后才是一个批评者。二人的分歧是在共同主张文学革命的前提下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歧,尤其是在白话能否入诗的问题上的分歧。
还在1915年9月20日,胡适就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使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梅光迪表示反对,致函胡适说:“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改良,谓之革命,则不可也。”他认为:“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以其太易易也。”梅光迪也认为诗界需要革命,他说:“吾国近时诗界所以须革命者,在诗家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知效其形式,故其结果只有琢镂粉饰,不见有真诗,且此古人之形式为后人抄袭,陈陈相因,至今已腐烂不堪,其病不在古人之琢镂粉饰也。”梅光迪还表示自己的意见只是暂时之见,诗界革命如何下手,应该研究英法诗界革命家,比较华兹华斯或雨果的诗及18世纪的诗。(75)
胡适看到梅光迪的回信,认为梅光迪“移文之文字于诗,则不可。以其太易易也”的批评,是“未达吾诗界革命之意也”。(76) 为此,胡适又致信梅光迪,再论“诗界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之意,“略谓今日文学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词而已。今欲救此文胜之弊,宜从三事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觐庄书来用此语,谓Prose diction也。)时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弊也”。(77) 从胡适的回信看,梅光迪的质疑,引发了其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丰富了其具体主张。如将简单的“作诗如作文”,发展到三个方面。其中“须言之有物”,显然是对梅光迪“诗家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知道效法其形式”的回应和概括,或者说二人在这一问题上所见相同,而胡适将“作诗如作文”的绝对主张改为较具弹性的“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也是部分地接受了梅光迪的批评。可见,胡适对梅光迪的观点虽不完全赞同,但也有部分吸取。
1916年7月,因胡适批评任叔永的古诗,再次引发了不欲争论的梅光迪的批评。梅光迪说,文学革新应该洗去旧日腔调,去掉陈言,但“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他认为:“大抵新奇之物多生美(beauty)之暂时效用,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之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之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他还认为,按胡适的说法,村农伧父、非洲黑人和南洋土著都可以成为诗人、美术家。(78) 但在他看来,诗“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宣发,故其文字亦需最高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种种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故非白话所能为力者”。所以他虽承认“白话诗亦只可为诗之一种”,但却“非诗之正规”,且白话诗人“断不能为上乘”。(79) 这与胡适强调的“文学不应为少数人私产,而当能普及大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的文学观大有不同。(80) 梅光迪强调诗歌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而胡适则更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
梅光迪认为文学革命应先因后革。他对胡适说:“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尤须先精研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须先用美术以锻炼之,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者也(俗语白话固亦有可用者,惟须必经美术家之锻炼耳)。”他提出改革应该改革流弊,而与事之本体无关。他认为胡适的做法是“以暴易暴”,“直欲将吾国之文学尽行推翻”,不能称为改良。梅光迪在信的最后再次表示赞成胡适的文学革命,但反对胡适的激进,他说:“足下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81)
胡适在梅光迪的来信上做了眉批,对于其批评多不赞同,但也有肯定之处。如,对“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的批评,表示自己“并不作此说法”;而对俗语白话“鄙俚”的批评,则坚决反对。然而,对梅光迪所主张的谨慎,先精研本国文字后言改革的说法,他则表赞同,认为“此亦有理”;对于梅光迪主张的白话须经锻炼的说法,也表示“此亦有理”。但胡适不赞成“本体”和“流弊”的说法,认为“此言不通,无有意思”。(82)
1916年7月22日,胡适用白话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寄函梅光迪,又遭到梅的批评。梅批评胡“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并认为像胡适这样的革命思想在西方早已存在,如未来主义、印象主义、自由诗等新潮流等,这些思潮皆喜欢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获取名士头衔。他劝胡适不要向国内介绍这些思想。(83) 梅光迪进而反思了西方18世纪以来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欧美近百年食卢梭与Romantic movement之报,个人主义已趋极端,其流弊乃众流争长,毫无真伪美恶之别,而一般凡民尤任情使性,无克省与内修之功以为之防范,其势如失舵之舟,无登彼岸之望。”所以,各种思潮相继出现,“其结果也真伪无分,美恶相淆,入主出奴,互相诋毁,而于是怨气之积,恶感之结,一旦横决乃成战争,而人道更苦矣”。梅光迪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19世纪以来各种不良观念发展的自然结果,“今之欧战,其大因固在各国思想界之冲突,加以经济之学兴,人权之说倡,以人生之幸福只在外张而不在内修,而弱肉强食之说乘之而might makes right,乃为人生秘诀矣”。(84) 从这个意义上,梅光迪称新潮流为人问不祥之物,无革新之可言。
胡适不赞成梅光迪的观点,回信反驳,认为梅“不求真知卓见”。与梅光迪对现代思潮的反思批评不同,胡适对西方现代文化更为乐观,他认为,新潮流“其中大有人在,大有物在,非门外汉所能肆口诋毁者也”。(85) 在回信中,胡适还批评梅光迪“守旧”、“顽固”。为此,梅光迪在8月8日、19日致胡适信中,表白自己并非守旧,“主持破坏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观念,亦不让足下”,“之所以对于多数之‘新潮流’持怀疑态度者,正以为自视过高,不轻易附和他人之故。为自由之奴婢与为古人之奴婢,其下流盖相等。”(86)“弟之所以不轻附和‘新潮流’者,正以too skeptical,too independent,不喜欢奉人为宗匠耳。至于古人及旧思想,亦不过取其最高为吾良心与抉择力所许可者,非奴从也。”梅光迪还提出胡适过度崇拜进化论:“足下崇拜今世纪太甚是一大病根,以为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此弟所不谓然也。科学与社会上实用智识(如Politics,Economics)可以进化,至于美术、文艺、道德则否。”(87) 在这里,梅光迪和胡适的讨论涉及在近代中国影响巨大的进化论的评价,梅光迪完全否定文艺和道德的可进化性,固然不正确,但他看到文艺、道德与政治经济的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进化的观念去解释,又有其深刻的一面。因为,道德有其恒久不变的成分,而艺术更不能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之间,做出简单的高下之分。在近代中国,进化论一经引入就被迅速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不免有泛化和庸俗之处,如用进化的观念解释文学艺术,认为新的一定胜于旧的观点,曾被许多改革者所接受。五四时期激烈的新旧剧之争就是一个例子。梅光迪对文化变革中的新与旧的认识有其深刻性。他把这一思想引入文学革命的讨论,把文学革命的讨论发展为一般的文化变革问题的讨论,从而使得文学革命的讨论进一步深化。
在新与旧的问题上,梅胡二人虽有争论,但并非水火不容。在收到梅光迪的信后,胡适在回信中提出“但有是非,何问新旧”的观点,既突破新旧纠缠,也承认了梅光迪对新与旧的认识。“但有是非,何问新旧”一语,得到了梅光迪“正得我心”赞语。但梅仍忧虑当时的趋新之势,在回信中,又进一步向胡适阐述了他对“新”的认识。他说:“西方自卢梭之徒与尚情派文学潮流(Romantic movement)起,争新尚异,人自为说,其所欲得者不在真而在新,不在众人之所同,而在个人之所独,黠者乘而奋兴,巧立名目,号召徒众,以‘新’之一字标于天下,而天下乃靡然从风,不问其有真理与否也。”(88) 这说明,梅光迪并非反对新,其观点也不是胡适所批评的“耳食”之谈(89),而是反对为新而新,忽视“真”的“新”。(90)
梅光迪的文学观念,对西方18世纪以来西方文艺思潮的反思,以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的解释,都受到白璧德的影响。在白璧德看来,现代西方社会产生的问题,亦即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以来的种种变迁,有不少缺点,其中主要问题是人道主义的传布。白璧德将人道主义界定为一种对普遍人性过于肯定的自信态度。在卢梭所处的18世纪,人道主义已经含有多种涵义,因此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如浪漫主义、科学主义乃至情感自然主义、科学的人道主义等等。在白璧德看来,恰恰是过于自信,使人们忽略对自身人格的培养和要求。白璧德把卢梭当成主要批判对象,就是因为卢梭对人的能力做了高度肯定。(91) 梅光迪拥护变革,但同样担心人性中强烈的破坏性。(92) 因此,他强调在文学革命中对世界文化变革经验教训的借鉴和对传统的继承。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之所恃人生观在保守的进取,而尤欲吸取先哲旧思想中之最好者为一标准,用之辨别今人之‘新思想’。”(93) 他在另一封信中还说道:“因弟对于人生观言‘人学主义’,故对于文学则言Classicism(姑译为古文派可乎)。盖二者皆注重学问,皆不相信生知(original genius),皆深知人性非全善,必须用学问教育以补助之。皆深知奇才异能必须得古人之助而后能成完器。然此非谓为古人奴婢也。即以文学言,在取法古人之精神而加以个人独有之长。故文学大家无有不得古人之助而终能独立者也。”(94)
值得指出的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白璧德“重视意志,而以理智为其伙伴,这使他与当时主导性的哲学趋势,特别是受杜威影响的那些趋势有一种互相协调的基础”。(95) 梅光迪也认为实验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并不完全矛盾。他曾给胡适写信说,胡适主张的实际主义(实验主义——引者注)与自己所主张的人学主义(Humanism,即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引者注)“似多合处”。(96) 可以说,在文学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梅、胡二人切切偲偲,观点相反相成,相生相长。梅光迪对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形成、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胡适在晚年曾说,他当时对文学革命的观念是很模糊的,是梅光迪等人与他的辩论“愈辩则牵涉愈多,内容也愈复杂愈精湛”。(97) 越辩论问题越多是自然的,但内容愈复杂愈精湛,则不能不说是双方智慧和不同思想碰撞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光迪对胡适文学革命思想形成,显然不是“逼上梁山”式的负面影响所能概括的了。同样,在讨论的过程中,梅光迪的文学革命思想也逐渐成型。
1916年8月,梅光迪和胡适几乎同时提出各自的文学革命纲领。8日,梅光迪信致胡适,提出四条文学革命主张: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如今之南社诗人作诗,开口燕子、流莺、曲槛、东风等已毫无意义,徒成一种文字上之俗套(Literary Convention)而已,故不可不摈去之(以上为破坏的)。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曰添入新名词,如科学、法政诸新名字,为旧文学中所无者。四曰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价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然须慎之又慎耳(以上二三四为建设的,而以第二为最有效用,以第四为最轻,最少效用)。胡适将其记在日记中,认为第二条似是而非,表示要与梅光迪详细讨论。(98) 同月19日,胡适致函朱经农,提出自己的八条文学革命纲领: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方面)。(99)
这是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径和方法。两套纲领都主张对旧文学进行革命,但却有所区别。一是注重创造,大胆尝试,对文化变革取彻底的激进态度。一是在破坏的同时,注重经验传统,小心谨慎,寻求渐进的文学变革路径。
1917年,胡适将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加以详细论述,以《文学改良刍议》为题,发表在《新青年》和留美学生刊印的《留美学生季刊》上,并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同年秋,胡适回国,任教北京大学,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几乎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同时,梅光迪于1917年1月在《中国学生月刊》上发表《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梅光迪认为,在当前的文艺复兴时代,伏尔泰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习惯牢牢束缚我们,要摆脱他们需要力量和勇气。但是这样容易导致中庸的丧失,尤其在一个动荡狂躁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一时冲动的行为容易在卑微地模仿过去和反传统两个极端间摇摆。所以他提出:“我们这一代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寻找到一种方法,重新调整变动不居的情况,去收获新与旧融合的最佳成果。”他还提出:“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的观念,能够不仅与任一时代的精神相合,而且与一切时代的精神相合。我们必须了解与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然后才能应付目前与未来的生活。这样一来,历史便成为活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达到某种肯定的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价值标准,藉以判断真伪,与辨别基本与暂时性的事物。”(100) 侯健先生在评价梅光迪这一观点时说:“这是安诺德的文化论和白璧德的历史透视的注脚,而在精神上,却与六经皆史,孔子圣之时者,以及吾道一以贯之的主张,全合符节。”(101) 1920年,梅光迪回国。1922年初,他与友人创办《学衡》,对新文化运动大加挞伐。梅光迪对新文化的批评虽然是他在美国形成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但在新文化运动已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梅光迪的观点显得极端,甚至有情急而詈的成分,连他自己也承认,“余非好为苛论,实不得已耳”。(102) 对于这些批评,胡适认为是谩骂,并认为文学革命已经过了讨论期,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
儒学和文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变革中的重要议题。梅光迪和胡适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近代中国文化变革、思想革新大潮中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深深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变革与发展。
注释:
①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正月十七日),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以下简称《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② 胡适:《非留学篇》,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5页。
③ 对留学期间梅光迪、胡适二人关系的研究是在耿云志先生编辑出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后开展起来的,此前的研究多侧重五四时期梅光迪和《学衡》派对新文化的批评,虽涉及留学时期梅、胡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但基本上是根据胡适留学日记和胡著《逼上梁山》提供的资料进行的,很不全面。据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耿云志《胡适与梅光迪——从他们的争论看文学革命的时代意义》(《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运用了当时尚未发表的梅胡通信深入论证了文学革命还在最早时期就已显示出的时代意义;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也使用了胡、梅通信,在讨论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时,勾勒了二人留学时期的交往,内容虽短,但强调了二人思想的互动和一致的方面;罗志田《两个质疑留学的留学生——读梅光迪致胡适书信,1910—1913》(《昨天的和世界的——从文化到人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这一时期梅胡二人关于留学问题上的思想互动进行了探讨;此外,沈卫威《回眸“学衡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相关的章节,段怀清《胡适与梅光迪:分歧是怎样成为思想障碍的?》(《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18期,2003年9月)也对梅、胡关系做了研究。
④ 梅光迪的父亲不主张在美国花主要精力读十三经等书,他写信说:“身在数万里之外,求不急之学问,哪有此等闲功夫读书。”梅父还引用友人袁澄浦的话劝告梅光迪“专攻西学”,“中学俟回国后再研究亦不迟”。(《梅先生尊翁教子书》七月初五日,八月十三日),《文录》,第188、190页。
⑤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1年10月8日),《文录》,第113页。
⑥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3年2月16日),《文录》,第123页。
⑦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1年9月30日),《文录》,第138—139页。
⑧ 《梅光迪致胡适信》(辛亥十月初三日),《文录》,第119页。
⑨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1年10月8日),《文录》,第115页。
⑩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1年9月30日),《文录》,第139页。
(11)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1年9月30日),《文录》,第139页。
(12)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正月十九日),《文录》,第122页。
(13)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2月26日),《文录》,第124页。
(14)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1年9月30日),《文录》,第140页。
(15) 胡适:《非留学篇》(1914年1月),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9),第672—674页。
(16) 胡适这一时期日记保存下来的相关内容很少。1911年1月至10月,胡适有简单日记。1911年11月至1912年8月有短暂日记,即北田日记,但早已佚失。1913年1月至9月,只有4月间记了一条札记。10月到12月,18条札记。因此,梅函保留下来的信息弥足珍贵。
(17) 《胡适留学日记》(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8)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6月25日),《文录》,第132、134页。
(19)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1年9月30日),《文录》,第139页。
(20)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4月30日),《文录》,第130页。
(21) 如在孔教运动过程中,胡适就曾思考非儒学派是否可以与孔孟并尊的问题。在其后的《先秦名学史》中,胡适更是明确地提倡复活这些曾与儒家学派同时盛行的非儒学派,以接受西方科学和哲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6页)。而梅光迪则不同,在1916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梅光迪说,晚周诸子之时,学术思想自由极矣,然平心论之,其大多数皆无存立价值者也。梅光迪既反对学术思想的一尊,也反对绝对的自由,认为二者皆有流弊。见《文录》,第166页。
(22) 胡适后来说:“那些外国传教的人,回到他们本国去捐钱,到处演说我们中国怎样的野蛮不开化。他们钱虽捐到了,却养成一种贱视中国人的心理。这是我所最痛恨的。我因为痛恨这种单摘人家短处的教士,所以我在美国演说中国文化,也只提出我们的长处。”胡适:《美国的妇人》,《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79、480页。
(23) The Ideal Missionary February 2,1913.Cornell Papers.《胡适全集》第3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
(24)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3年2月16日),《文录》,第122—123页。在1915年1月名为“The Philosophy of Browning and Confucianism”的演讲中,胡适称儒学为“希望和努力的哲学”,并赞扬儒学的乐观主义精神。《胡适全集》第35卷,第129—134页。
(25) 《梅光迪致胡适信》(原信只署5日,从内容判断似应为1913年2月5日),《文录》,第145页。
(26)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3年7月1日),《文录》,第150页。
(27)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3年7月1日),《文录》,第150页。
(28)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1年9月30日),《文录》,第138、139页。
(29) 《梅光迪致胡适信》(辛亥十月初三日),《文录》,第119页。
(30)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6月25日),《文录》,第133页。
(31)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6月25日),《文录》,第133页。
(32)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1年10月8日),《文录》,第115页。
(33) 胡适在1911年4月13日日记中写道:“读《召南·邶风》。汉儒解经之谬,未有如《诗》笺之甚者矣。”《胡适留学日记》上,第28页。
(34) A Republic for China,The Cornell Era,1912 Jan,240-242.Coneu Papers.《胡适全集》第35卷,第2页。
(35) 在10月4日日记中,胡适记道:“得觐庄书,亦二千字,以一书报之,论宋儒之功,亦近二千言。”《胡适留学日记》上,第69页。胡适自幼受父亲影响,崇奉程朱理学,到美国后的1911年的6月,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会夏令会,在17日讨论会上听李佳白主讲《孔教之效果》。外国人讲孔教,胡适感觉是自己的羞耻。会后更有Dr.Beach对胡适等言“君等今日有大患,即无人研求旧学是也”。Dr.Beach并大称朱子之功,胡适闻之,深受刺激,感觉“如芒在背焉”(《胡适留学日记》上,第44页)。在此,胡适从世界哲学、人类智识的角度赞扬理学,反驳梅光迪,似乎引用了Beach的观点。
(36)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0年10月8日),《文录》,第113—116页。胡适在10月11日日记中也记录道:“得觐庄书,攻击我十月四日之书甚力。”《胡适留学日记》上,第70页。
(37)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3年2月16日),《文录》,第123页。
(38) 已有研究者看到这一点,如余英时先生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文中提出,梅光迪与胡适讨论儒学,对胡适十几年后热心提倡颜李学派产生影响。见《重寻胡适历程》,第262页。
(39) 据1912年10月14日胡适日记,胡适曾欲撰写著作《中国社会风俗真诠》,取外人所著论中国风俗制度之书,一一评论其言之得失,并认为这也是为祖国辩护之事。其后,胡适还于1914年1月专门作过《中国的婚俗》的演讲,专为中国婚俗辩护。梅光迪对这些做法非常赞同。他曾致函胡适说:“足下以西文撰述,为祖国辩护,为先民吐气,匪但私心之所窃喜,抑亦举国人士之所乐闻也。”[《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4月30日),《文录》,第130页]由此可见二人对中国文化的心态。
(40)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林毓生对1915年前胡适不否定儒家思想的解释。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页。
(41) 郑师渠认为晚清国粹派对孔子及其儒学的批判存在两个层次。一是以邓实、黄节、马叙伦等人为代表,重在批判历代君主借孔子实行思想专制,近乎真孔论;二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进而批评作为先秦学派儒家学说自身的弊端,矛头直指孔子本人。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42)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6月25日),《文录》,第133、134页。梅光迪对胡适说:“现今有两种腐儒:其一种并不读孔子之书,徒见耶教之盛于欧美,以为耶教果胜于孔教,于是主张废弃孔教,奉耶教为国教……其一种不出国门,略识吚唔呫哔之学,以为孔教在是,又妄自尊大,以为孔教以外皆邪教也。二者皆不识真孔教,皆为孔教之大蠹。尤可畏者,欧美人士目睹吾国社会现状,以为皆孔教所致,于是极力排挤之。”所以,梅光迪提出消除两教仇视,舍两教于一的观点[《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6月25日),《文录》,第134页]。胡适在这一问题上虽与梅光迪不完全相同,但他也尽力协调孔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孔教运动》一文中,胡适批评了那种视复兴孔教为对其他宗教尤其是在中国新兴的基督教的威胁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和没有理由的。胡适提出,如果基督教要完全影响中国,必须是移植一些基督教思想于儒教伦理的土壤中。改革和复兴孔教是为任何外国种子在中国本土播种进而培育而做的耕耘与施肥。胡适认为,至少基督教在中国需要竞争对手。他还认为,对基督教来说,改革的孔教在不远的将来是一个有用的摹仿之源,激励基督教调整它的一些信条以更好地适应东方的条件。见“The Confucianist Movement in China:A Historical Account and Criticis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Vol.9,No.7,May 12,1914,p.53。
(43) 梅光迪曾在与胡适的通信中批评基督教和圣经,认为:“吾国言修身之书,汗牛充栋,远过西人,独吾人多知而不能行,反令西人以道德教我,似若吾国许多道德之书,不如一部荒诞腐烂之《圣书》,殊可耻也。”《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正月十七日),《文录》,第121页。
(44)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6月25日),《文录》,第132页。
(45)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6月25日),《文录》,第135页。
(46) 从时间上判断,这封信是对梅光迪6月25日信的答复。胡适的“北田日记”中有许多关于宗教问题的思考。如梅光迪说:“北田日记拟留此数日再寄还。迪亦不以示他人,因此闻人不好看祖国文字,亦不喜研究此等宗教上之问题也。”《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7月8日),《文录》,第136页。
(47)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7月8日),《文录》,第136页。
(48)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9月15日),《文录》,第137页。
(49) “The Confucianist Movement in China:A Historical Account and Criticism,”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9,No.7,May 12,1914,pp.533-535.
(50) 胡适:《许怡荪传》,《胡适文存》第1集,第550、551页。
(51) 《胡适留学日记》上,第131—133页。
(52) “The Confucianist Movement in China:A Historical Account and Criticism,”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9,No.7,May 12,1914,pp.534-536.
(53)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3年7月1日),《文录》,第150页。
(54)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3年7月1日),《文录》,第150、151页。
(55) 《胡适留学日记》上,1911年6月18日,第44页;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
(56) 见周明之著、雷颐译《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四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胡适虽未奉行基督教,但对于基督教对人格的影响始终予以肯定,如他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1932年9月7日)一文中说,“基督教”对人格的影响,远非佛道两教所能梦见。见《胡适文存》第4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70页。
(57)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钱玄同和周作人等都曾高度赞扬过基督教的精神。如陈独秀说:“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我主张把耶酥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耶酥所教我们的人格、情感,是什么?(1)崇高的牺牲精神。(2)伟大的宽恕精神。(3)平等的博爱精神。”见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1920年2月1日),《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6—287页。钱玄同也说:“我承认基督是古代一个有伟大和高尚精神的人,他的根本教义——博爱、平等、牺牲——是不可磨灭的,而且是人人——尤其是现在的中国人——应该实行的。”见钱玄同《我对于耶教的意见》(1922年2月23日),《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58)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6月25日),《文录》,第133、134页。
(59)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3年2月16日),《文录》,第124页。
(60) 《梅光迪致胡适信》(日期不详,原信仅存“二日”字样),《文录》,第146页。
(61)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3年7月3日),《文录》,第154页。
(62)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3年7月3日),《文录》,第154页。
(63)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3年7月3日),《文录》,第154页。
(64) 梅光迪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得片甚喜。谆我之语,敢不拜赐。惟此邦(欧洲亦然)道德退化已为其本国有心人所公认,彼辈方在大声疾呼,冀醒迷梦,非迪过激也。”《梅光迪致胡适信》(日期不详,原信仅存“二日”字样),《文录》,第146页。
(65) 胡适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逻辑与哲学”中写道:“企图以宪法的形式确立儒教为国教,或是国家的道德教育制度的反动运动遭到了国会内外所有稍有思想的领导人的强烈反对,社会上在知识分子中稍有影响的期刊几乎没有哪种期刊不曾于最近几年发表关于非儒各派的哲学学说的文章。”胡适:《先秦名学史》,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
(66) 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逻辑与哲学”。
(67) 梅光迪在1916年对胡适说:“吾国文化乃人学主义的(humanistic),故重养成个人。吾国文化之目的,在养成君子(即西方之Gentleman and scholar or humanist)。养成君子之法,在克去人性中故有之私欲,而以教育学力发达其德慧智术,吾国今后文化之目的尚需在养成君子……故吾国之文化尚需为孔教之文化可断言也。”《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12月28日),《文录》,第175页。
(68)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正月十七日),《文录》,第120页。
(69)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3月19日),《文录》,第163页。梅光迪在1913年就对胡适说:“生平之大愿,在以文学改造社会”。见《梅光迪致胡适信》(1913年6月26日),《文录》,第148页。
(70) 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0页。胡适在1915年4月5日把这一思想写成札记:“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胡适留学日记》下,第287页。
(71)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受到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如他自己所言:“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响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胡适留学日记》上,自序,第8、9页。
(72)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3月19日),《文录》,第162页。
(73) 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01页。
(74)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3月19日),《文录》,第162页。
(75) 《梅光迪致胡适信》(原信仅署25日,从胡适回信日期判断,应为1916年1月),《文录》,第159、160页。
(76) 《胡适留学日记》下,第269页。
(77) 《胡适留学日记》下,第268页。
(78)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7月17日),《文录》,第164页。
(79)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8月8日),《文录》,第170、169页。
(80) 《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1916年7月13日追记),《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05页。
(81)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7月17日),《文录》,第165页。
(82) 见《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7月17日)及《胡适留学日记》下,第372—374页,胡适在日记中把这封信做了摘录,并加评语。
(83)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7月24日),《文录》,第167页。
(84)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7月24日),《文录》,第167、168页。
(85) 《胡适留学日记》下,第376页。
(86)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8月8日),《文录》,第169页。
(87)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8月19日),《文录》,第166页。
(88)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8月15日),《文录》,第173页。
(89) 《胡适留学日记》下,第385页。
(90)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12月28日),《文录》,第175、176页。
(91) 关于白壁德对卢梭的认识,参见王晴佳《白壁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7期,2002年6月,第63、64页。
(92) 参见“The Task of our Ceneration”,《梅光迪先生家书集》,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版,第190、191页。
(93)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10月5日),《文录》,第174页。
(94)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10月5日),《文录》,第175页。
(95) 见Thomas R.Nevin,Irving Babbitt:An Intellectual study(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4)。转引自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重寻胡适历程》,第265页。
(96)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10月5日),《文录》,第174页。
(97)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98) 《胡适留学日记》下,第395页。
(99) 《胡适留学日记》下,第391、392页。
(100) “The Task of our Generation”,《梅光迪先生家书集》,第190、192页。
(101) 侯健:《梅光迪与儒家思想》,见傅乐诗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65页。
(102)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文录”,第1页。
标签:胡适论文; 基督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梅光迪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读书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孔子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