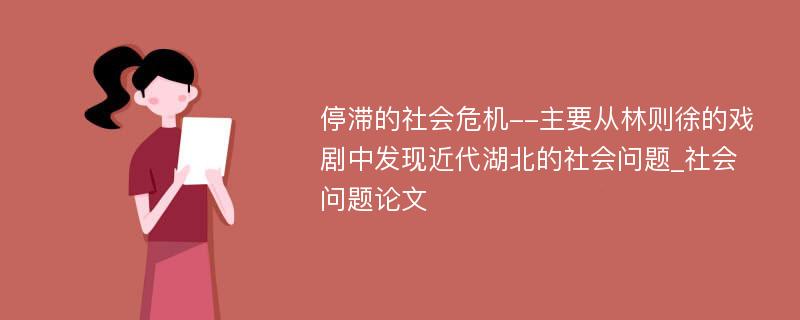
停滞社会的重重危机——主要从林则徐奏稿中发现前近代湖北的社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北论文,社会问题论文,近代论文,林则徐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1)02-0052-09
从19世纪开端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濒死阶段。由于一般历史研究往往重视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头,而轻视上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所以无论是以全中国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还是地方史志,对鸦片战争发生之前的数十年均着墨不多。近几年问世的各省通史,在古代和近代之间多数仍然留下了历史断层。
湖北地方史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19世纪初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失败之后,这里既没有发生重大历史事件,也没有产生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一切因循旧制,社会仿佛停滞了,地方史志对这一段留下了空白。幸好林则徐于道光十七年(1837)农历三月至翌年十月在武昌担任了近20个月的湖广总督,从他的有关奏稿中倒是能够了解一些当时湖北社会的严重危机。
一、吏治的因循窳败
第一,吏治因循守旧。从林则徐奏稿可以发现,他在近20个月的时间里,虽然身为总督,似乎位高权重,加上他信奉经世实学,以精明干练著称,却根本无力开创新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制度限制,二是“救弊”不暇,三是没有财力。
清王朝一贯执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政策,因此权力的分配和运作机制必然是内(朝廷)重外(地方)轻和上重下轻。州县亲民之官遇事须向督抚报告请示,经督抚允许才能处置。凡属“要政”,封疆之吏的督抚也一定要奏报朝廷,军事上每一个“讯”卡的添撤移动,民事上重要的狱讼案件,亦须经朝廷核准。如荆州旗营为改造和添置抬炮,需用银480两,还有修复溃毁堤防、修缮年久倾圯的城墙、书院、衙署,无论耗银上万两、数千两还是数百两,均须一一详细上奏,总督并不能擅定兴作。
从奏稿中可以看到林则徐的日常工作,除了例行的视察驻防军队、考核文武官员之外,耗时耗力量多的依次是检查督促防洪抢险、筑堤修城、查禁私盐;其次是关注、捕拿和审问境内各地出现的“面生之人”、“习邪教者”和藏有“邪书器械者”,即对“造反”的蛛丝马迹既惕且惧;最后一件事是忙于“禁烟”。总之,“救弊”耗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嘉庆道光年间,全省财政收入按定额应有200万两之数,但州县胥吏借口歉收(确有有权势的士绅、地主拒交和受灾农户拖欠,但更多的是浮收超收)大肆截留中饱,能交到官府的实际收入经常在130万两左右(而人民的实际负担,无疑在200万两以上)。各地都有官吏浮收中饱和虚报灾荒的事件,所以稍后胡林翼总结湖北过去数十年的钱粮弊端并下断语说:“数十万之正额,征收不满一半;数十年之积弊,浮动至于十倍。”(注:《胡文忠公遗集》卷23,“奏疏”23,同治六年刻本。)
在这130万两的实际收入中,解交北京和协济邻省的占70%-90%,本省留用的在13-39万两之间,通常是在25-30万两。用途包括官吏薪俸及养廉(10万余两,超过全省开支的1/3以上)、役食、驿站夫马、钱漕运费、祭礼、典礼、廪膳、考试、军政办公、赈济等,几乎全属人事开支和维持开门办事之需,完全谈不上地方兴作建设。在林则徐督鄂的1837-1838年,财政尚无亏欠,但已经捉襟见肘,修缮省会武昌城墙的经费无从开支,只能依靠汉岸盐商、江夏汉阳典商、一位江夏县的候补知县、一位咸宁的丁忧试用县丞共捐3.7万两,再加上林则徐本人及前任现任巡抚、藩司、臬司、盐道、粮道、武昌汉阳两知府共捐廉银9100两,一共4万余两才得以完成(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3-604页。)。而且由于财政支绌,省内常平仓因无钱购粮贮存,已较定额短少一百二三十万担。如在丰年按时价每20万担谷需银6.5万两计,等于缺银80余万两(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9-610页。)。由于朝廷和地方均限于财政枯竭,省、州、县“停办工程”已久,所谓“恤农”“通商”“惠工”,均停留于救灾、救弊,百废待兴而恢复旧观不暇,根本无力开创新局和兴办新的事业。林则徐如此,其他庸劣之辈更无足论。
第二,修补官员众多,故到其获实任时,多已疲老,遂难以振作,贪污渎职之事屡见不鲜。清代于各级各类官员例有定额,但由科举和军功而产生的官员源源不断,再加上所谓“捐纳”,即每遇战乱灾荒或京城、地方有建设工程时,朝廷就大开捐例,允许富人捐献金钱谷米,朝廷则赏以实授官职或候补的头衔身份。道光元年(1821年)任监察御史的麻城人袁铣,曾上疏力数捐官之多之滥,称“今襄阳知府实少林寺僧,宁波府道实邯郸响马,及保定知县、铁岭县丞出身不正……未经告发者,其人又不知几许”(注:张仲炘、杨承禧:《湖北通志》卷139,“人物志”17,“列传”7,湖北省长公署1921年刻本。)。地方官吏如此杂乱,势必造成仕风败坏、官场黑暗。
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看到的情况是,武职中两省世袭云骑尉一类,以候补名义在各营效力者达143员之多,等待守备之职,比例为14∶1,自道光元年至十七年,湖北仅得轮补7人。“未补之员,较历年已补之数,不啻相悬十倍,实属轮补无期。其中到标在先者,候补将及四十年尚未得缺。以定例十八岁随营扣至四十年之久,其人已在六旬左右”(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4-405页。)。如宜昌镇总兵珠尔杭阿,任该职过12年,年65岁以上,步履维艰,久不振作而诸事废弛。两省提镇,年逾六十、年力已衰者甚多;再加上身患疾病者、于士卒管教训练不力者、贪污渎职者,比比皆是,使得两湖营兵“技艺未能优娴,且浇薄成风,不耐劳苦,往往酗酒,吸食鸦片,并不恪守营规。其中老弱残废之兵,遇有差操,请人代替。其额缺者,既未能招募如数补充,而各将领衙署复以兵丁服役,恬不为怪。至各乡村塘汛碉堡倾圮,烟墩坍塌,平时并无守汛之兵”(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9-441页。)。营兵已基本丧失战斗力。故林则徐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七至九月校阅两湖47个标营之后,即奏请革职、勒休(强迫退休)和降职处分副将2员、游击3员、守备6员、千总11员、把总数十员(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5-470页。)。然而由于当时“营兵所支粮饷,仅敷糊口,不能赡家,每于操防之余兼习手艺,或作小贸藉资帮贴。遇值班时……私相互替,实为各营情事所有”(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0页。)。林则徐处分调换一批军官,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文职人员的情况大同小异。为数众多的候补人员往往为谋一实缺和临时差事而向上司行贿送礼,一旦占有官位即以权谋私。官员年老贪渎成为普遍现象。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时的湖北布政使张岳崧年逾六旬,有的知州、知县亦年过六十,或“身有痰疾”、“步履维艰”,或“两耳重听”,难以办公。这些人办事不力而生财有道,新任随州知州始至,即笑纳“吏以旧例进茶果银八百两”(注:张仲炘、杨承禧:《湖北通志》卷122,“职官志”16。)。宜昌府、黄州府、蕲州官吏均有“获私纵犯”、“勒报营私”的丑行。与施南知府对调的原襄阳知府阿尔彰阿,到任三月,管一府六县公事,上报详禀才四五件,被林则徐批评为“深居简出”、“偷安好逸”。林则徐和新任湖北巡抚周之琦三次奏报,勒休、降改和革职知州、知县、同知、外委、通详、吏目等19人,仍难有效地澄清湖北吏治。咸丰年间,胡林翼又曾“以吏治不清则乱源不塞,劾罢镇、道、守、丞以下数十人”(注:张仲炘、杨承禧:《湖北通志》卷121,“职官志”15。)。
掌管教育的府县学官同样老化。清代惯例,教授须以举人充任,教谕须以恩贡、拔贡、副榜等担任,训导须以岁贡生担任,一般需要“进学”(当上秀才)“二十年而后得”,故“居是职者类疲老,精气耗折尽,不复思自振拔”(注:喻文鏊:《红蕉山馆文钞》卷3《送仲弟之黄陂训导序》,红蕉山馆光绪三年刻。)。事实正是如此,王葆心曾记有“郢中九老”的故事,确凿地载明,嘉庆时,钟祥、潜江、安陆、天门、京山等府县的教授、教谕和训导共9人,年最长者91岁,最轻者62岁,平均年龄超过70岁(注:王葆心:《续汉口丛谈》,载台北湖北文献社《湖北文献》第97期,第56页。)。道光年间的情况仍然如此。
第三,胥吏和各种“书办”泛滥殃民。清代湖北州县,无论属“冲”、“繁”、“疲”、“难”四等中的哪一等,均有一大群“吃衙门饭”的帮凶走卒。除知县(大县还设有县丞、主簿、典史)、把总(率城守营兵勇数十至百来人不等)、教谕、训导、司官(即巡检司,各县有2-4员,率巡勇数十人)之外,知县衙门内有幕友、家丁,外有三班六房。幕友由知县延聘,分管刑名钱谷的俗称“黑笔师爷”,负责布告榜示的俗称“红笔师爷”,幕友“以浙江、福建人居多,因为操此业者世代相传,有其秘诀,县传授出许多徒弟”。家丁由知县自雇或由各处荐用,多者数十人,少亦有十余人。其中分管门房的(大门传达)、管签押房的(知县办公室)、跑上房的(直入知县内室)、管监审的、作随从护卫的等等。幕友、家丁以外,还有随任亲戚,亦必数人或十数人。县丞、主簿、典史、把总、巡检,亦有随从家丁。幕友由知县按年或季致送一定薪金,家丁则全无工食,均向百姓索要,遇有诉讼官司或人有所求,即为此辈生财之机。
此外还有包揽、征收钱粮(包括地丁、漕米、屯饷)的柜书和册书。这种职业世代相传,其缺可以出顶出卖,因为征收钱粮时可以浮收勒索,有利可图,岁末年终还可以到农户“打抽丰”要孝敬。由于册书掌有自明代相传下来的黄册,知道各户田地多少,应纳钱粮若干,所以粮差必须与之合作;遇有田地买卖,册书还可索取一笔高额的过户费。清末一县之中,有这种柜书册书数百人至上千人不等。当然柜书、册书、粮差有专职的,也有由书办、衙役、绅士(本人或指定代理)兼任的(注:吴端伟:《从黄安县的县衙谈起》,载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湖北文史资料》第33辑。)。
除了粮书(包括柜书和册书)之外,有些州县还有其他名目的书办。如蕲州有“礼书”,协助办理祭祀、县考等事;一般滨江濒湖之县有“工书”或“堤书”,负责摊派和征收修筑堤防之费。上述各种书办又按级别和管辖范围分别称为“户书”、“里书”、“县书”等名。林则徐曾上奏曰:“楚省粮书、工书等名目混称者多。凡在各乡分催钱漕、经手推收过户者,皆假借书吏名色哄惑乡农。其实则与局役相同,并非在内署科房办事。而人数甚众,大县竟以千计,实属骇人听闻。从前里书、册书之名,迭经奏明禁革,而若辈互为鬼蜮,总以里粮底册私相授受,故有官革私不革之谣。”(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8页。)可知当时在州县衙门之外,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冒牌书吏群体,他们虽非完全以“办公事”为生,而是自有产业,但却可以说是州县政权插进广大乡村的吸血管。这个群体在协助州县政权完成各种征收、摊派任务的同时,也通过种种欺诈手段,为自己分一杯羹,从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这就是几年后胡林翼批评的“以书差为政”的情形。
二、人民的沉重负担
对于佃农和半自耕农而言,田租为其最大负担。晚清湖北农村的田租,可交铜钱,按田地等次定租,上田每亩租钱1300文左右,中田1000文,下田600-900文;亦可交粮食,旱地交小麦,水田交稻谷,低者占产量的40%,高者竟达60%(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3、635页。)。晚清湖北农业由于技术落后,耕种粗放,旱地的小麦平均亩产不会超过100公斤,水田的稻谷平均亩产难以达到250公斤,故水旱田平均亩产仅150余公斤。按40%-50%的租率计算,每亩地需交租65-80公斤。一户五口之家的佃农倾全力可租种20亩水田旱地,产粮3250公斤,交租1300-1625公斤,剩余1625-1950公斤。而五口之家每年至少需要1500-1800公斤粮食,才能维持农业再生产的投入和全家人的衣食消费。所以如果稍有天灾人祸,佃农的起码生活就无法维持;遇有婚丧嫁娶、生病建房之类的事情,就得负债。
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负担,则主要表现为交纳给官府的赋税。这个问题需要从全省的财政收支状况和农民的实际负担两个方面考虑,才能全面了解。
在咸丰五年(1855年)实施征收厘金以前,湖北省的赋税分为地丁、漕粮、南粮、租课、耗羡、常关税6个部分。地丁是田赋与人口的综合税,全省合计应为1227900余两(注:张仲炘:杨承禧:《湖北通志》卷43,“经政志”2。)。漕米(包括运往京师仓的“正兑”、运往通州仓的“改兑”及另加17%-35%的“正耗”)19万石,南粮(运往荆州供驻防八旗及绿营之用)12万余石,两项共计31万石,折银43万两。租课是官田租给农民使用的税租,包括学田租和芦课租,学田租归书院,芦课租交官府,每年12000余两。耗羡是征收钱粮的手续费和杂费,包括“火耗”、“平余”,其在征收地丁、漕折时,在总额上分别加收10%和1.2%-2.5%。湖北的地丁和漕折共为171万余两,故耗羡为17.1万两,平余为3万余两。常关税包括武昌厂税33000两、荆州关税17687两。以上全部合计总数接近200万两。其中商业税收仅为5万余两,占200万两的2.5%,而农业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97.5%(注: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1年版,第55-62页。)。到1855年,对商人实行征收牙税(市场交税的中介费税)厘金之后,税收比例才发生变化。
前面说过,从表面的数字看,湖北人民的共同负担是130余万两,而实际负担是这个数字的3-5倍,其原因和真相有多种。
一是浮收,主要在地丁、漕粮两项。据胡林翼的了解和统计,在1858年以前的数十年间,北漕、南粮及水脚、运费、征收费等,每年的实际征收折银都在916900两以上,比官府实际收入的43万两高出48万余两(此中31万两作了官府行政管理费用,其余18万余两或者更多为各级官吏、册书、粮差、士绅、地主、保甲和户族首领层层瓜分中饱)。群众的漕粮、地丁负担至少是定额的2.3倍。
平均负担有两种算法。一种是把田赋按人数均分,如1840年田赋为2056241两,全省人口为3319.60万人,每人负担田赋0.06两(注: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1年版,第59页。)。浮收2.3倍后,每人负担为0.138两,那么五口之家的负担为0.69两。这种算法的缺陷是把城镇居民、商人的人数计算在内,因而实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因为清代自从“摊丁入亩”之后,农业税是按田亩征收的。第二种算法,是把田赋按耕地数均分。如1851年田赋为2305896两,同年耕地为61503127亩(注: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1年版,第59、24页。),则每亩负担为0.03749两。浮收2.3倍,为0.08623两。占地10亩的小农负担为0.8623两。占地30亩的中等农户负担为2.587两;占地百亩的大户负担则为8.623两。当然田地有水、旱、沃、瘠、荒、熟等多种档次(《清会典》记载,湖北所属民赋田每亩科粮六杪至二斗九升一合四勺八杪零不等),故无论按人平均还是按田地平均计算负担,都只能作参考。
《林则徐集(奏稿)》中记载的案例,具体生动地反映出群众的田赋负担。湖北产粮大县钟祥县屡有拖欠和抗粮不交事件,民人“金珍每年完银七钱八厘,陈瑞元每年完银一两四钱零,具尚无欠,惟(已革生员)胡作霖每年应完九钱五分二厘,欠至两年未完”。此三人均属中小农户,如按浮收完银,均在1.6两至3.2两之间。“捐纳千总职衔邬起泰,抗交钱粮八载,数至一百余两”。这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大户,每年额定钱粮就达10余两,不过仗势未交。由于浮收田赋负担不轻,故《清律》虽载以严厉处罚科条,如“贡监生员应纳银粮欠至十分以下,俱黜革,枷号两个月,杖一百”,“举人应纳钱粮欠至十分以下,问革为民,杖一百。在籍有顶戴人员与举人同”,不过“革后全完,仍准开复”。尽管悬有厉禁,人们还是拖欠抗阻,连士绅也不例外。从记载中可以知道,除邬起泰、胡作霖外,还有已革生员吴星纪、邱森烈、生员张恒修、武生夏荣春、捐贡王宇熙,均被牵连进了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一次交粮纠纷(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5-608页。)。
问题还在于,田赋并不能真正按田亩征收。有钱有势的士绅、地主时有拖欠、抗拒,更多的则是勾结胥吏、册书、保甲里正、宗族户首等,把负担转嫁到中小农户身上。湖北的漕钱交纳,历来是小(贫)户交折色(银或铜钱),大(富)户交本色(米)。可是书差只敢强迫小户多缴数倍的钱,而不敢多收大户的米,甚至让他们少交或拖欠。州县费用不足,就以小户之浮收款抵销。故胡林翼说:“侮鳏寡而畏强御者,今日之州县书差之于钱漕也。”(注:《胡文忠公遗集》卷60,“抚鄂书牍”2。)他还指出,有些地方的“刁绅劣监”,包揽完纳,所取于小户的,远比缴给官仓的为多,有如“蝗虫”,无耻地“为己求财”(注:《胡文忠公遗集》卷23,“奏疏”23,同治六年刻本。)。所以当时有田10亩的小农户,钱粮负担总在一二两银之数。佃户没有己业田地,不直接纳田赋,应由地主交纳,但“赋出于租”,地主不会贴本,早把田赋算进田租中。官府貌似体恤无业佃户,标榜“催赋不催租”,其实士绅地主仍然利用官府权威和纳赋的堂皇理由,向佃户收取高额田租。
按照1838年林则徐拟用6.50万两银子买10万石(每石约合126市斤)稻谷贮仓的数字,可知当年每石谷价为0.65两。耕种10亩田的小农户,即使只按最低的2.3倍的钱粮浮收,田赋亦须交谷(或卖谷折钱)167市斤左右。当然比起漕粮最重的江浙等省来,湖北的漕粮负担还只是其三四分之一。
二是各项杂税。以上所说田赋,是税收的大项(国税),其次还有州县和地方上的各种杂税。道光年间的杂税主要有“干鱼、麻、铁、湖课、线胶、门摊、酒醋、商租、地租、府钞、房租、街基、茶税、各府商税、长河、城濠、渔利等项”(注:张仲炘、杨承禧:《湖北通志》卷50,“经政志”2“田赋”。),城乡群众每户都要摊上几项。如沔阳对农户的自有房屋,包括湖区草房均征所谓“间架税”,“孤贫及屋舍倾圮者”亦不能免。杂项税费虽然数字不大,但对升斗小民和结庐而居的穷人而言,也是很重的负担。
三是银贵银贱。清代白银和铜钱通用,两者折算,银价最便宜时每两兑铜钱一串(1000文)。从19世纪30年代起,由于鸦片输入,白银外流,致使银价上涨。1838年,各省均是每银1两易制钱1600文。“1842年,武汉地区1两银子换制1626文,1845年后涨至2000文以上。以往卖米3斗,输1亩之课有余,是时卖米6斗,输1亩之课而不足”(注: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经济综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无论是佃农还是自耕农,交租交赋的负担无形增加一倍。
四是人民生活必需的米、盐均比邻省昂贵。清代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由于人口增加、水旱灾害、官仓补购、粮商囤积居奇和货币流通过多等多种因素,全国各地米价持续上涨。湖北由于人均耕地减少、自然灾害频繁,产米已经不能自给,不足部分主要依赖湖南、四川售运,故米价高于湖南、四川。即使在湖北农业丰收的年份,其米价亦比湖南高出2%;如遇湖北严重歉收,就会高出湖南19%-21%(注: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1年版,第55-56页。)。“道光末大水,斗米千钱”(注:张仲炘、杨承禧:《湖北通志》卷152,“人物”30。)。每天都要消费的食米如此之贵,不仅贫民小户有断炊之虞,中等之家亦会感到很大压力。
湖北食盐之贵,根源则是朝廷的政策所致。清代规定,淮南盐专销江苏、安徽、江西和两湖,其中两湖占60%的份额。道光年间,湖南定额为20余万引,湖北为50余万引,每引规定重量为400斤,故湖北每年应销淮南盐多达2.2亿余斤。而在湖北省内,施南(今恩施)一府六县和宜昌府属的鹤峰、长乐两州县准销川盐,湖北北部、中部、东部地区只能销淮南盐。由于淮南盐场是官府专营的老场,管理不善,质量差而成本高;再加上淮南盐行楚,需从扬州十二圩以木船逆江而上,时间长,运费高;尤其是清政府以盐课为国税收入之大宗,一再提价加课,于是造成“淮南盐课,楚省最重”的局面。
当时广东和湖南南部部分地区销粤盐,四川、贵州、湘西鄂西销川盐,陕西销潞盐,河南销淮北盐。而淮南盐课比潞盐、淮北盐课重4.8倍,比粤盐重5倍多,比川盐更重10倍以上。由于淮南盐成本高、运费贵、纳课重,盐商和官府为保证各自的收入,就提价出售,并把销盐情形作为考察楚省官吏政绩的内容之一。故尽管林则徐一再申说“各处盐课皆轻,而淮盐独重,各处盐本皆贱,而淮盐独贵;各处运盐皆顺流而下,而淮盐独逆流而上”等种种不合理情形,但由于他深知“淮盐销得一分,几足以抵川盐二十分之课”(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9-513页。),大利所在,朝廷必不肯改变,也只能对淮南盐的行销尽力保护。当时鄂西出售川盐,“每斤市价不过二十文,淮盐到彼则卖价约需两倍”(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5-586页。)。河南信阳地区售淮北盐,“每斤市价仅钱三十文,而紧连之应山等县,即系湖北口岸,应食淮南纲盐,其盐由汉口陆运而往,价值不止加倍”(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3页。)。
大米、食盐为人民生活所必需,感到困苦的虽然首先是升斗小民,但其更大的影响是会带动其他物价的上涨,米价和盐价只是一般物价上升的一个指标而已。
五是水患给人民生活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治水成为湖北的沉重负担。长江自四川进入湖北以后,从巴东至黄梅,流经18州县,自荆州以下筑堤,全长合旧制30万丈。汉水由陕西进入湖北以后,从郧阳到汉阳,流经13州县,自襄阳以下筑堤,共长17万丈。清中叶以后,人口激增,四川和汉水上游大多数地区只有开垦而无治理,水土严重流失,至中游泥沙沉积,河床增高而蓄洪之湖面缩小,每到夏秋两季,江、汉涨水,内渍外涝,一片泽国;而遇十天半月不雨,高凸之处又立现旱情。
清代湖北,对于州县之官,责之防洪之任甚重,如所管范围之内的堤防有溃决漫顶、造成损失者,无不给以革职、降职、撤换处分,故州县之官能任满期者不多。尽管这样,由于洪水势大,或者堤防不够坚实,守候时有松懈,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共30载,“溃漫之处,无岁无之”,“一处溃则处处之横流四溢,一年溃则年年之溃水长流”。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遇大水,适值林则徐督鄂。他竭尽心力,督率防堵,是年长江、汉水无一处溃漫,算是例外;但有沿河被淹之地、内湖渍水所淹之地和高处受旱之地,受灾农村仍遍及22个州县(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9-620页。)。
在洪水频繁为害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不仅承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为了抵御洪水,还要长年付出劳力和钱财,修堤筑坝。各有堤州县均又有一项名为“堤费”的征摊项目,不论丰歉,依钱粮派征。全省每年征收堤费无从知道确数,仅知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到道光十年(1830年)的10年民欠堤费共达327218两白银,平均每年欠下32721.8两(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7-418页。)。监利县境内的江堤最长,约为370余里,每年派征制钱7万串左右,由于拒交和拖欠,通常只能收到3万余串到4万余串(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1-423页。)。依照全省所欠只占40%计算,那么全省每年堤费应为8万余两白银。
在征收堤费的过程中,经手人如粮书、堤书、首士、户首等徇私舞弊、贪污中饱,对有钱有势的大户不敢征收,对小户则勒收重收,种种弊端,层出不穷;而且收取过后,管理使用时又存在诸多不公。如前述监利县额定年征堤费7万串左右,而道光十四年(1834年)交到堤工局的仅4万余串,原因就在大户拖欠和经办人员吞没;掌管堤费的堤工总局“薪饭等项已开销至一万四百余串之多”,还打算趁收成较好之年“酌情多派以防不足”,“总局之外分设乡局,加添首士多名”等等(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1-427页。)。可知当时无论办理何事,都会给不肖者带来贪污中饱的良机,而给贫苦小民增加负担。
为了灾后重建家园并抵御来年的洪水,湖北人民还要继续付出代价。据林则徐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农历四月的上奏中所说,从道光十七年农历十月至十八年农历三月,即在四个多月的冬春农闲中,湖北有近30个州县都曾进行疏浚河道、加筑堤防、兴建闸坝和御水城垣的工程。根据当时朝廷“一切河道工程,银数在五百两以上者,应奏明办理”的规定,林则徐逐一开出了下列州县的工程费用:天门县下中洲三区堤防用4700余两;钟祥县马家湾堤防2750两、万佛寺堤防4161两;潜江县护城土堤696两;安陆县和荆门州修复水毁城垣分别为24300余两和13700两;黄梅县堤防8481两;当阳县疏浚沮、漳二河用14484两;咸宁县堤防4600余两;蒲圻县堤防1211两;荆州府万城大堤共修52处,用土14600余方、石200余方,约费银1000两;公安县除用完额定堤费外,追加4400余千文(含银3000两);监利县修堤用土一百万方有零,“居民喜有成效,今岁咸愿加倍集费”(即1.4万串,合银近1万两);天门县彭市、岳家口、上下陶林等处又用1200余两;京山县6000两;还有襄阳县的老龙石堤、荆门州的沙洋大堤,系由府、州、县官员捐资修补(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4-555页。)。粗略统计,这次冬春的水利工程共用银10万两以上。其他各处的水利工程,虽然每处用银不超过500两,但因处数多,总数也逾万两。这笔开支的来源,部分为“官捐”和“商捐”,但大多数仍然依赖当地群众“额交”的堤费和追加。
在上述重重负担之下的劳苦大众,生活当然困苦不堪,挣扎在死亡线上者固然不少,处于饥饿线、贫困线以下者无疑更多。据林则徐的说法,当时“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日;若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0页。)。照此推算,五口之家要达到“可过”的水平,年需银90两;到“诸凡宽裕”的水平则年需银180两。当时丰年每石谷价0.65两,平年0.75两,歉年0.85两,那么专以种粮为生的五口之家农户,分别需要有年产5担谷(合630斤)的稻田24亩和48亩。这样的人家,应分属于中等以上的自耕农和大户;无业的佃农、雇农乃至一般的自耕农,都达不到林则徐所说的“可过”的标准。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中举的天门人刘淳,写过一篇《农病》的文章,描述农家除了普遍陷入“尽一岁之力所出,不足以给用”的贫困之外,还有说不完的折磨灾难。“郡县凡大役作,农夫荷畚锸而待命,朝往暮归,不避霜露雨雪寒暑之劳。长吏之所征输、吏役之所侵渔、里胥之所中饱,尽农天之膏血也。鞭挞之惨,农亲受之;狱讼之繁,追呼之扰,农习闻之;舆马送迎之费,筑堤修闸之派,农靡不与之。朝所蠲者,吏已征之;一钱之欠,百钱不足以偿之”。遇有大灾,农民更难逃劫数。刘淳亲历了1831年湖北的大水灾,亲见当时“农之冻馁死者日以百数,僵尸累累横路隅,无一工商医卜倡优胥吏仆从僧尼道人,触望皆识其为农”(注:刘淳:《农病》,《云中集》第1册,光绪癸未赐绮堂刻。)。
被重重负担压榨得一无所有的农民,再遇上水灾,侥幸未死者就成群结队地流亡。武汉和沙市是灾区难民的集中之地,每年从农历九月开始,武汉的官绅商民就要“筹捐收养江汉等处被水棚民。棚民者,皆江汉上游灾民,流入武汉,以芦棚栖止,沿江汉两岸,尔后习为常举,每秋冬后,棚民罔不充塞省市汉市矣”。“道光季年,荆江泛涨,邻县俱漂没,流民逃至郡城(荆州和沙市)者,络绎不绝。”这些流民有时会得到社会上的帮助,便亦有官绅以为流民“易聚难散”,唯恐酿成事端,不仅不倡捐廉发赈,反而设法驱赶,故文士心忏子的《续闻见录》曾说“易聚难散”、“所谓一言而戕千百命者是也”(注:王葆心:《续汉口丛谈》,载台北湖北文献社《湖北文献》第97期,第56页。)。
不甘就死的贫苦百姓只好自寻求生之路。拖欠堤工、抗交钱漕、贩私(盐)食私(盐)等等,不绝于书。沔阳“民贫多讼”、“萑苇之薮多盗”(注:张仲炘、杨承禧:《湖北通志》卷21,“舆地志”21。)。不仅是沔阳一州(县),还有德安、安陆、襄阳、荆州四府和一个荆门直隶州,偷盗、杀人、抢劫之事层出不穷,官府惊呼“江汉多盗”(注:张仲炘、杨承禧:《湖北通志》卷121,“职官志”15。)。此外,溺毙女婴、拐卖妇女儿童之风亦在上自荆门、下至监(利)沔(阳)的广大地区蔓延,且愈演愈烈(注:王葆心:《续汉口丛谈》,《湖北文献》第99期,第64页。)。19世纪中叶的湖北社会,已经处在严重的动荡不安之中。
三、私盐的普遍流行和烟毒泛滥
清政府规定,湖北是销售淮南盐的主要地区,其份额在苏(江苏)、皖(安徽)、赣(江西)、汉(汉口),销及湖南湖北)四岸中占40%(湖南占20%,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共占40%)。由于清政府视淮南盐课为利薮,不断增加淮南盐在湖北的销量,其方法是追加在两湖的盐纲“引”数和每引的重量。清初湖北额销淮南盐近40万引,每引200斤;雍正年间每引加至344斤;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后,每引加至400斤(同治朝更规定每引600斤)(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0页。),规定湖北额销50余万引(最高时达到70余万引),计达二三亿斤之多。
当时湖北人口为3000余万,因此每人每年需食用七八斤盐,才能销完五六十万引淮南盐。故绝大多数年份淮南盐有10%-20%积压在仓库,无法销售,官员为此屡受朝廷申斥,原因就在私盐的流行。
价格不合理是私盐流行的最根本原因。由于淮南盐成本高、运费贵,尤其是政府课税重,使得湖北境内的淮南盐比邻近的淮北盐、潞盐和川盐都贵,最低者高出20%-30%,一般高出50%,最甚者高出一倍。民间生计艰难,即使最安分者也力求能省一文则省一文,故私盐有广大的市场需求。因有差价可图,“贫民无不百计挑运,四出售私”(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0页。);甚至成群结队,组成团伙,形成运送、保护、窝藏、销售的勾结和分工;遇有小股缉私人员,则不惜以武力抗拒。
二是客观上存在着走私的便利条件。前已说到,湖北施南一府六县和宜昌府属部分州县准食川盐,销淮南盐和销川盐之地不仅地界毗邻,而且犬牙交错,在崇山峻岭中行陆路偷运,路路可通,防不胜防;更有长江水运,由四川顺流而下的船只夹带私盐已成为惯例。潞路行销陕西,有的就必须从湖北郧阳府的地方经过;襄阳又紧接河南,有丹水、汉水船只通行,故郧阳、襄阳一带,贩卖潞盐和淮北盐成风。“襄阳一属,名为淮盐引地,而民间率食潞私。溯查道光元年以来,该府阖属每有片引不销之年,即设法销售,亦总不及定额十分之一”(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2页。)。另外,淮南盐逆长江而上进入湖北时,“黄州武穴一带,为盐船入楚停泊要口,船户水手与岸上奸贩串通,走私日甚一日”(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2页。)。总之,当时湖北除了与湖南交界的南路以外,西路、北路、东路均有私盐浸灌,仅道光十七年(1837年)就查获私盐100多万斤,未被查获的估计更多。
三是官吏的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使禁私不可能有效彻底。“不肖员牟每视鹾务为利薮,骫法营私,无所不至”。如道光十八年春,宜昌镇左营外委率一班员弁,“获私纵犯”,即留下所获私盐自食和变卖,放走盐贩;黄州协都司拿获贩卖私盐船只后,不送县究办,而由营书私下勒收贿银(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2页。)。即使是按规定缉私,也是将所查获一半作赏,“一半充公,充公仅资各处开销经费,于国课似无裨益”(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3页。)。将私盐充公变卖,必然使官盐销售减少;而所获私盐不予变卖又无经费维持缉私部门和人员的开支。地方保护主义则表现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官员,在组织和带领沿乌江和长江下驶的船只运送铜铅等物品时,经常勾结船户,大量夹带私盐,有的一次多达数千斤。他们打起旗号,亮出领运官员的知府、知州、同知、知县的头衔,并借助下水船速,越卡拒验,成为私盐的大宗来源(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0-412页。)。
私盐给百姓的日用带来了少许便宜,但大量的减少了国课的收入,严重地腐蚀着官吏队伍。如果走私者形成团伙,更对社会的安定和官府的统治构成威胁。林则徐就说过:“民间匪类,大半出于盐枭,即如襄阳之捻匪、红胡,为害最甚,总因逼近豫省,以越贩潞私为事,遂至无恶不作。”(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3页。)林则徐基于官府的利益和立场,把造反作乱者视作“匪类”,自属错误,但造反作乱最初往往与走私有关,也是不争的事实。
林则徐在督鄂的20个月内,曾尽力缉禁私盐。他一再重申“犯无引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巡禁私盐,故纵者与犯人同罪”等律令,对贩私盐数量大,尤其是结成团伙武力抗拒的私贩予以重刑处分;处罚和参革骫法营私的员弁及缉私不力的镇守、都司、千总、把总十来人;还提出对“公然犯法食私”者,“在绅衿应革功名,在平民应受满杖”,“责令绅衿大户以及乡团牌保,互禁食私,犯者公同送究”,但对“挑卖私盐之穷民,许其改悔,投充肩贩,由各处官盐子店给票挑赴四乡,卖完缴价”(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3页。);又增设卡、巡,并将各处卡、巡人员酌量更易,立定章程,严禁贿纵;还规定对所获私盐变卖之款,“先按引盐课则,提交正款钱粮”,以“抵官销之缺”,剩余才作“给赏充费之用”。他甚至“按月按季核计各州县销(官)盐,分别功过”,将“短销”严重的黄安县知县撤职查办(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2页。),以儆戒各州县,促其力销官盐。
由于林则徐雷厉风行,办事认真,措施得力,上任月余各地即获私贩38起,抓盐贩86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共缴获私盐100余万斤。宜昌、襄阳等历年官盐片引不销之处,由于官为领运,或鼓励商贩行销,民间亦开始买食淮南盐。故此年两湖共销淮南盐733201引,比销盐最多的道光十六年(1836年)还多3000余引(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6页。)。但由于官盐和私盐存在价差,故“凡买食盐斤之人,无不背官向私”(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2页。);官吏的腐败亦难根治,私盐始终无法杜绝。故同年两湖所销官盐仍然比朝廷额定的779926引短少46725引。因“缺销不及一分,例应免议”(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5页。),即缺销之数不到额销数的1/10,没有因此受到处分。
19世纪初,以英国不法商人为主的鸦片贩子开始向中国偷运鸦片。到二三十年代,鸦片走私已相当猖獗,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家财政困窘,银贵钱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城乡吸毒人数迅速增加,百姓体质下降,且将来之不易的钱财耗于罪恶之中,中户变下户,下户变穷户,穷户成饿户,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衰朽。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英商走私的鸦片已沿着鄂茶商道源源进入湖北(注: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吸食者“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吏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流毒之深,几于口有同嗜”。而“地方官以为滔滔皆是,不免畏难苟安”(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7-598页。);尤其因为“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0页。),故对于朝廷本来就不够坚定一致的禁烟指示,视同赘设具文,烟毒日益泛滥。
林则徐高度重视鸦片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危害。邪片之害,首先在于败坏人心,“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吸烟败坏人心,一在“吸烟之辈陷溺已深,志气无不惰昏,今日安知来日”,即丧失进取心和责任感,只求昏昏然醉生梦死;二在“吸食者方且呼朋引类,以诱人上瘾为能,陷溺愈深,愈无忌惮”,且吸食者有“玩法之心”,以为“犯者太多,有不可胜诛之势”;而贩卖者则以利厚,“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为之”(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8-601页。)。其次是在经济上,既使吸食者自己耗尽钱财,陷入贫国境地,又使社会凋敝、百业不兴,进而必然使国家白银外溢,财政支绌。林则徐估计,吸食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需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0页。)。这笔钱几够小户人家半年之需。由于“商贾码头及通衢繁会之区,吸食者不可胜数”,故当时市面已明显受到影响。“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圜圚聚集之地……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他估算全国一年耗于邪片的银两“不止于万万两”。“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故而他郑重提醒朝廷:“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0-601页。)
林则徐督鄂期间,曾就禁烟问题上过三道奏折,表明了严禁吸食和贩卖鸦片的态度,并就贯彻实施的办法提出了详实具体的建议,体现出其思虑和计划的周密。
在具体措施上,林则徐建议:应该首先把烟枪收缴净尽;并由各省广出告示,勒令吸烟者于限定日期内赴官府自首,将所藏烟具、余烟全部呈缴,“出具改悔自新毫无藏匿甘结,加具族邻保结,立案报查。如日后再犯……加倍重办。”而对烟贩、开设烟馆者和制造烟具者加重罪名和处罚,于限期内投官自首、将烟土烟具全部缴呈者,准将原罪量减;限期之后被拿获者,应予“论死”(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9-570页。)。
鉴于以前迭次讨论禁烟而各方主张不一,林则徐在强调鸦片之害后一再呼吁,应该“(朝)中外(省)一心,誓除此害,不惑于姑息,不视为具文”,才能“雷厉风行”,不致“养痈贻患”。鉴于“衙门中吸食最多”且“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他主张“从此严起”,“文武属员有犯,该管上司于奉文三个月内查明举发者,均予免议。逾限失察者,分别议处。其本署戚友家丁……若不早令革除,又不肯据实举发……应将庇匿之员即行革职。本署书差有犯……逾限失察者,分别降调”。即严肃“失察处分”,迫使各级官吏“先严于所近”,管好下级和身边之人,作为示范;同时又要发动和依靠各级官员,举凡收缴烟枪烟土、关闭烟馆、拿获烟贩,均责成州县限期进行,如期完成者“均免从前失察处分”。林则徐把禁烟一事定为“核作州县功过之数”,不力者“立予撤参”,有成效者予以奖励。他还责成“地保牌头甲长”查缴烟土烟具,举报开烟馆之房主,包庇者“与正犯同罪”(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0-571页。)。在禁烟决心和行动上,不仅要求“中外一心”,也要求“上下一心”,共同进行。
鉴于下有“玩法之心”、上有“畏难苟安”之情,多年来对烟贩和开烟馆者“徒有论死之法”,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对吸烟者亦仅止于“由杖加徒”,人不畏法,林则徐主张以严刑峻法厉行禁烟。他说,“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邪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力挽颓风,非严蔑济”。他支持黄爵滋“准给一年限期,若一年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罪以死论”的建议,对烟贩和开烟馆者,虽分别原有“死罪”和“远戍”罪名,现“均应一体加重”,因为“吸食者果论死,则开馆与兴贩即加至斩决枭示亦不为过”。他相信“民情非不畏法,风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弛”。而以刑才能止刑,使人“怀刑畏罪,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期并无处死之人”;到时即使有“处死之人,而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胜计”(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0-601页。)。林则徐当时身在内地,未曾虑及外国烟贩的因素,但他认为“如果内地无人吸食,谅彼亦即不来”(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6页。)的看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林则徐在主张严刑峻法的同时,强调应给人悔过自新的机会,主张在执法的过程中体现出自首从宽、拿获从严,早改从宽、逾期从严的政策区别。“由宽而严,由轻而重”,最终达到永禁烟毒的目的。同时,为了体现“爱民如子”的态度,他还亲自收集研究戒烟药方,设官制断瘾丸,并捐出自己的廉银供配制丸药之用。在林则徐的示范影响下,民间医师也积极研制各种戒烟药。汉口和武昌药店配制的戒烟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不仅城市如此,乡村也同样。鄂东名医杨际泰,精心研制出效果显著的戒烟药,并毫无保留地把药方和制法传授他人,以表示对禁烟救人活动的支持。在短期内,即有“久患烟瘾”之人,“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6页。)。
林则徐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农历五月上奏《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以后,考虑到“定议尚需时日,恐民间以为久无消息,或且不必查办。此心稍放,即不可复收”,即与两湖巡抚钱宝琛、张岳崧商议,认为“目下吸食罪名虽未定议,而查拿总不可稍懈,收缴亦不可稍迟”,因而在未获朝廷明令的情况下,即成立了禁烟局,委派得力官员查访开馆兴贩之徒,并迅速逐一缉拿,缴获烟土、烟膏和烟具;同时遍张告示,剀切禁戒。禁烟局派员收缴民间的烟枪烟斗,并教育吸食者:“真心改悔,查无不实不尽者,禀请暂免治罪,并酌给药料,俾其服食除瘾,以观后效。”
在农历五月到八月的短暂时间内,湖北的禁烟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汉阳县拿获烟贩朱运升、何日昇等5人,另有邵锦璋等3名烟贩自首,邹阿三等2名广东烟贩闻风逃走。从船上、栈房,以及各种货箱、夹层床中起获多批烟土烟膏,连同自首烟贩所缴呈,共计“一万二千余两”。省城禁烟局到六月底,即“缴烟枪计一千二百六十四杆”,此后武昌、汉口两局又缴烟枪“七百余杆,省外各属所收亦已陆续禀报,尚无汇计”(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7页。)。到10月,湖北又缴获烟土烟膏1万余两,湖南则缴获烟土烟膏3万余两(注:姚薇元、萧致治:《鸦片战争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
1838年10月27日,湖北除将汉阳县查获的烟土烟膏1万余两“暂贮藩库”外,把其余烟土烟膏1万余两、烟枪1700余杆,由林则徐亲自验明,并会同湖北巡抚率部属赴校场(今武昌阅马场)当众销毁,并把残沥余膏拌以桐油烧透,“投入江心”(注: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大事记》,第2页。)。林则徐还对禁烟严格执法、多次拿获要犯的汉阳县知县郭觐辰叙功请奖,荐升知州。湖北的禁烟工作成为中国人民近代禁毒斗争的序幕。
总计林则徐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写有奏稿近20万言,他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全是报忧不报喜。当时湖北社会不仅停滞不前,而且百病丛生,也确实无喜可报。以林则徐之学识和务实,仍然救弊不暇,诸如整肃吏治、防洪抗灾、查禁私盐和严禁鸦片,也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开创性的建设工作,则一项也没有。近20个月当中,林则徐还共受三次处分,“降级留任”、“不准抵销”。贫穷、停滞、衰朽的社会难以治理,造成了林则徐的困境。林则徐离去后仅三年多,湖北就发生了钟人杰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又十年后,太平军进入湖北,官军毫无阻挡之力,各地贫苦农民则纷纷揭竿响应,这只能说是一个濒死社会最可能出现的局面。
标签:社会问题论文; 林则徐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道光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明治维新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