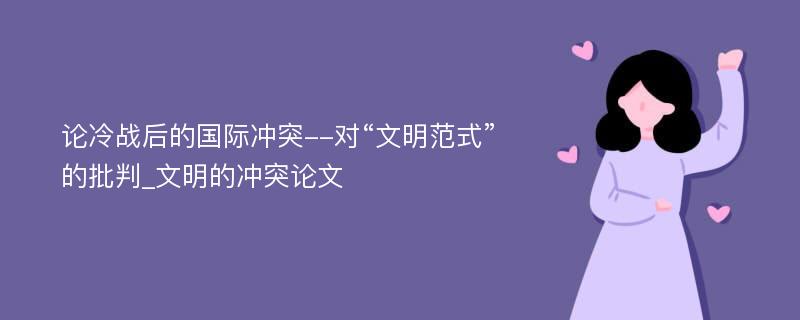
论冷战后国际冲突:对“文明范式”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战后论文,冲突论文,批评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世界进入了国家物质利益主导的多元冲突时代,文明冲突不是冷战后世界冲突的“范式”。因为当代文化传播已使文明的载体由地域性向社会群体弥散,而文化趋同又成为全球文明演进的基本态势,两者的共轭效应使文明冲突的国际性呈式微趋向;所谓文明的冲突只是表象,其背后是民族国家利益;冷战后国家利益更主要表现为经济物质形态方面,此即国家冲突可能的主因,同时文化等多元因素也会产生耦合作用,但世界战争则要以物质实力为后盾;所谓儒家——伊斯兰联盟与西方对抗说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一文中推出了一个引起国际学术界震动的理论,即今后“文明”将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主体,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战。在另一篇应答文章《若非文明,何也?》(If Not Civilizations,What?Foreign Affairs,Nov./Dec.1993)中,他进一步将其文明冲突论概括为“文明范式”(civilizational paradigm),并认为其“文明范式”将代替过去的“冷战范式”成为冷战后“指导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发展变化”的新模式。
冷战后国际冲突主要是不是文明的冲突?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此已经作了热烈的讨论,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本文拟在对亨廷顿所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评论的基础上,就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模式作进一步的建设性探讨。
文明是否国际冲突的主因?
尽管可以认定,文明或文化的因素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一个诱因,甚至说在冷战后这种因素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范围内有所上升,然而,文明的差异并非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文明范式”这一命题不能成立。对此可以从文明发展的两个基本动向进行分析。
首先,当代文明的载体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文明冲突的内容和含义已与历史上不同。历史上的各种文明从空间上看都比较封闭,文化载体是地理意义上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只能表现为君主国或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或者表现为亨廷顿所说的不同的亲族国家(kincountry)族群之间的冲突,这些都属于国际政治范畴的“地域性冲突”。然而,当今的文明冲突已经不仅仅表现为传统的地域性冲突,而且表现为“社会性冲突”,即社会结构——阶级、阶层、集团的冲突。因为当今世界文化传播的功能愈来愈强,不同文明之间的渗透在所难免,正象卡尔·多伊奇所说:“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差异,但他们之间却又有着不可避免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在某些方面,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今天这个日益缩小的地球上变得更加密切了”。①由于文化的传播和社会的流动,每一文明内部目前都不是铁板一块,都是受其他文明的辐射,都存在许多亚文化。这一现象即是文化的多元化,它成为当今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犹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超工业革命的锤击正在毫不夸张地将社会砸成碎片,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亚文化群爆炸”的过程之中。②文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文化的差异由传统的空间地理分布向现代的社会群体分布弥散。例如在美国,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有自由主义者,也有保守主义者,还有激进主义者;有恪守西方传统的,也有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和反传统的等等。而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也日趋明显。这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不具有相互内在联系,而且在历史上独立的种种特质,现在却结合在一起而且变得不可分割,为那些没产生这种认同的地区中无对应物的行为提供了所需的理由。这种情形的必然结果是,无论从行为的哪个方面看,各种标准从积极的到消极的不同文化中都会无处不在。③如果说不同文化之间会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冲突不完全发生于不同文明的地域之间(即整体文化的冲突),而也会涉及一个国家和地域内部(即亚文化的冲突);或者说文明的冲突不单是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越来越可能是东方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与东方和西方的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于是,文明和文化所引起的冲突越来越呈条条状,而非块块状,文明的冲突越来越不是一种国际政治问题,而是渗透到国内政治之中。而且,由于整体文化的冲突与亚文化的冲突犬牙交错,事实上是后者削弱前者,作为国际冲突的文明冲突的对象越来越模糊。总之,文明内部的文化多元化必然对国际上的文明冲突起到一个缓冲、牵制和消解的作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其次,从人类文化学的观点看,文明之间不仅冲突,而且融合,这是因为文化具有涵化和整合的功能。一个社会内部的文化多元化过程也就是全球范围的文化融合过程。文化多元化一方面是一种文明向外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另一种文明的涵化的过程,并且各种文化要素通过文化整合而融为一体。④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趋于一致性的“匀质”过程。佛朗西斯·福山在其引起较大反响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中提出,所有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均越来越相似,人类社会渐渐趋向“匀质化”。⑤虽然该书许多观点我们并不同意,但在这一点上福山却说出了真理。亨廷顿教授在其1971年的著作《变动不居:现代化、发展与政治》(The Change to Change:Modernization,Development and Politics)中也把现代化视为一个匀质的过程,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将朝着一个终极融合运动。但在《文明的冲突?》中,他却一反过去的看法,对匀质化、世俗化和理性化避而不谈,转而片面强调文化的异质性、排他性以及宗教化或反世俗化的倾向。实际上,文化的异质性与同质性、宗教化和世俗化两种状态都存在,而总的来看,世俗化是主流、文化趋同是历史总趋势。阿尔蒙德指出,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文化的日益世俗化,这已成为“普遍的趋势”⑥;而白鲁恂认为,随着文化世俗化的发展,文化的同质性将越来越多,最后会产生一种“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⑦詹姆斯·罗斯诺也指出,世界的相互依赖的增强带来了价值规范的共享,促使全球共同体对地域共同体的吸收,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在塑造着“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⑧。“全球文化”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对民族文化的一体化和民族认同产生消解作用,这正是迈克·费瑟斯通等“文化全球化”论者所关注的问题。⑨这种全球文化虽然还没有完全生成,但可以看到的是,人类所享有的共识是越来越多了。1992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最后协议以及1995年社会发展问题全球首脑会议都昭示着这一趋向。世界各国总的来说是对异文化抱有更加宽容和吸收的态度,而不是更加顽固和排斥的态度。虽然,某些国家仍会保留其某些传统文化特色,而全球文化的形成也并不抹煞文化的多元性,但每个国家每种文明都必须置身于这样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都必须对其他文明和文化作出适应,都必须在更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总之,尽管文明的冲突以某种形式仍会存在着,而且今后仍可能长期存在,但是,文化多元和文化趋同这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文明发展趋向的共轭效应,将大大削弱国际冲突的文明差异之诱因,作为国际政治层面上的文明冲突总体上呈式微态势,而不是所谓国际冲突的“最后阶段”。值得一提的是,亨廷顿在其答辩文章中以“美国完了?”为标题,对美国近30年来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忧心忡忡,视之为非西方化和非美国化的趋向,甚至放言如果美国变成了真正的文化多元并弥漫着文明的内部冲突,现在的美国将不复存在。果然如此吗?实际上,目前已无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完全自我封闭而保持自己文化的“纯洁”,任何一种现代文明本身都是复合型文化,这是文化传播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且这一趋向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它是文明进化的条件,正像汤因比所说:“在各种文明相互影响的辐射和反辐射之后,能得以保存下来的将是人类共同的伟大经验:由于受到来自其他文明的地方传统的冲击而使社会文化遗产的某些部分受到损害,但正因为如此而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公共生活——从而逃避了毁灭。”⑩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文化的多元化也有其积极作用。迪韦尔热认为,西方社会的多元化是其制度合法性的一个要素,李普塞也说,一个社会应达成冲突与一致的适当平衡,合法的冲突“有利于社会和组织的整合”(11)。美国不正是广泛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各种宝贵的财富才成为今天的美国吗?难道美国因此而国将不国了?从这里倒可看出,亨廷顿自己始终未弄清其“文明范式”究竟是一种国际冲突范式,还是国内冲突的范式。
国际冲突:表象与实质
把国际冲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并非一件新鲜的事。反观历史,早就有人这么说。且不提那些较小的冲突,即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曾被贴上了文明之战的标签。当时西方每一个国家都有一批学者力图把一次大战的爆发证明为由于敌对国家的民族哲学与文化的冲突,其中包括柏格森、桑塔亚那、乔舒亚·罗伊斯等知名学者。而且各战胜国政府也向所有参战的士兵颁发了一枚铜质奖章,上面刻着:“保卫文明的伟大战争。”对此罗伯特·宾克莱评论道:“本来是一场政治冲突,哲学家们却把它搞成一场宗教大分裂”(12)。
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场冲突本身真的就是文明的冲突,还是被说成是文明的冲突?是文明自然和必然地发生冲突,还是人为地制造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在指出以文明为分野的“亲族国家并发症候”(kin-country syndrome)时,说在海湾战争中侯赛因总统放弃阿拉伯民族主义,公开向伊斯兰教徒作出诉求,侯赛因及其支持者“意图把这场战争定位为文明间的战争。”问题是,意图把一场冲突定为文明的冲突就等于这场冲突真的就是文明的冲突吗?把在一场较大冲突中的敌我力量的暂时重新分化和组合现象归结为亲族国家并发症候是幼稚的想法,因为这种情况在没有亲族关系的国家中也会发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贯对共产主义的苏联十分仇视的丘吉尔也暂时捐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转而力排众议主张与苏联结盟,他的说法是:“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想我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句好话。”但一俟战争结束,他就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积极策划“冷战”策略。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许多。同盟关系既不以文明的差异为界限,也不意味着敌对的消失。
因此,在对国际冲突作出分析的时候,应当辨明究竟什么是冲突的实质,什么是表象;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什么是内容,什么是形式。我们不否认某些冲突的确可能具有文明的因素,但就大多数国际冲突而言,包括亨廷顿所指的那些“文明的冲突”,其实质主要不是文明的冲突,而只具有某种文明冲突的表象;文明的冲突也非国际冲突的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结果。
如果单从事物的表象看,任何冲突都可以解释为文明的冲突,因为任何冲突的双方都多多少少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冲突很容易被附会为是这种差异所引起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文明差异会引起冲突,而更多的文明差异并没有引起冲突呢?这从文明差异本身是得不到解释的。在文明冲突的背后必然有更为本质的内容,这就是国家利益。汉斯·摩根索断言:“只要这个世界在政治上由国家组成,国家利益在世界政治中就具有决定意义(13)。不管有多少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事实上各国的政治家都是这么行事的。政治家在考虑敌我关系时,是不大会以文明属性为出发点,而是以利害关系为基准。华盛顿总统早就说过,美国要以其正义所指引的“我国利益来选择和平或战争”,而“与欧洲进行友谊的结合或敌对的冲突都是不明智的”(14)。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的名言则是: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15)。另一方面,所谓“文明的冲突”,起因并非文明的差异,而是西方国家文化扩张主义政策的结果,说到底是一种政治冲突。这就是摩根索所说的“新民族主义”,即“民族世界大同主义”(nationalistic universalism)——主张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有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强加给所有其他民族(16)。亨廷顿所列举的“文明的冲突”基本上都属于借助于政治手段人为制造的冲突,是西方强国对外扩张政策在文化领域的表现,都是西方国家一手制造的,是单向的冲突。广大非西方国家从来没有试图把自己的文明输出到西方国家或向西方文明“挑战”,它们在所谓“文明的冲突”中始终处在被动的受压迫受攻击的状态。总之,并不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而只存在西方的文化侵略。
由上可以看出,与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相比,文明只是一个藉口和工具。在所谓“文明冲突”的表象背后是一以贯之的延绵数百年的西方国家的扩张政策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主体不是抽象的文明,而是具体的国家。
由于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有些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将走向衰落,进而提出了一些新的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在形形色色的替代物中,一类比民族国家的范畴小,如种族、部族、部落等,此即部族主义观点;另一类则比民族国家的范围大,如国际共同体、世界共同体等,此即世界主义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是似是而非的。
部族主义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衰落。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的解体以及国家内部的种族纷争,表面上看是民族国家的危机,而实际上是传统的帝国主义的危机。前苏联不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古老帝国在现代的翻版,它是靠着强大的政治力量把历史上曾经属于若干个国家的人群结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而当这种政治力量消失后,共同体也必然消解,但这种消解正是民族主义势不可挡的反映。民族国家的普遍趋势不仅通过帝国的解体表现出来,还通过因政治力量人为地把民族国家割裂而产生的政治共同体的重新合并表现出来,德国的统一便是显例。冷战后政治共同体的分化组合,是民族国家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不是部族主义的崛起。至于世界主义,虽然长远看似乎是一种发展的趋向,但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它并不能改变民族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的格局。亨廷顿对部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观点似都不以为然,而以文明作为国际行为的主体。文明较世界共同体小,但也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畴,通常是若干国家的族群。问题是,作为一种文明的若干国家能在国际事务中统一行动吗?或者即使是较之异文明的国家能更多地统一行动吗?这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根据的,即使有一些实例,也是偶然的和暂时的。相反,我们倒可以经常看到在同一文明之中的若干国家同室操戈,短兵相见,其冲突的暴虐程度并不比异文明冲突缓和。我们很难找到在国家以外的政治上铁板一块的文明,倒可以发现只要是文明超出了国家的界限,往往就四分五裂。一种文明非但难以成为国际冲突的主体,反而其内部经常孕育着冲突和战争。因此,国际冲突不必然以文明作为界限,却必须以国家作为主体。正象多伊奇所说:“民族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成为国际冲突媒介体的危险。(17)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明的冲突的确存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较之过去更为重要。只是,从全球政治的角度看,它不构成国际冲突的核心。
冷战后国际冲突的特点和动因
既然“文明范式”不能对国际冲突作出合理的解释,那么应如何分析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呢?对此首先要理清楚的是,冷战后与冷战期间甚至历史上更长一段时期相比,国际领域哪些方面没有变,而哪些方面变化了。换言之,要找出冷战后与以前的国际冲突有哪些一致的、联系的方面,又有哪些不同的、区别的方面。
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体,追求国家利益是国际冲突的原因和本质,应该说这一点无论在冷战后还是以前的时期都一样。所不同的是在同样都是追求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冷战期间更加注重的是国家利益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而在冷战后注重的则是国家利益的经济物质形态方面。
国家利益最重要的是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冷战期间,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国家利益以非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体,因此主要表现为东西冲突;而随着全球东西格局的瓦解,南北关系就变得更为重要了。但南北冲突之所以崭露头角,并非文明的缘故,而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减弱,经济物质因素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因此,这时的国家利益主要是民族主义与经济因素的结合体。冷战后经济因素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因素而主导国际关系,这已为很多人所察觉到,这里无庸赘述。
至于文化或文明因素,它只能依附于民族国家和经济政治因素,而不能主导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和经济。这正象多伊奇所说,民族的、宗教的、语言的、种族的或文化传统问题,或者民主和专制作为政府形式的差别,并不是根本性冲突的根源,因为“这种类型的许多冲突在任何两个特定国家之间并不能证明是永久的。相反,争端中的所有特定同盟和问题倒在经常变化,或变得不再重要,不再重现”(18)。国家从来不会以文明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相反,文明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亨廷顿自以为发现了别具一格的新范式,实际上是陷入汤因比早就批评过的窠臼,即对立双方的好战派都使用思想上特别能引起恐怖和敌意的词语,把对方说成十足的敌对国家,以此在本国国民中煽起狂热气氛,所谓宗教上对立的说法,“是极其肤浅和虚伪的”,“实际上都不过是相互竞争的地方国家之间敌对斗争的假面具而已”(19)。
那么,文明对于国际政治的作用是什么?简言之,它仅对国际冲突的进程和程度起到一个加剧或减缓的作用。当今世界由于变得更为复杂多样,冲突的形式也更为繁多,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也伴随着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冲突,实际上进入了“多元冲突”的时代。经济和政治的冲突与文明的冲突耦合,就较易引发战争,此即冲突的“多元耦合”效应。甚至,当其他各种因素相持不下的时候,文明因素作为天平上的一个小砝码,有时也会影响天平倾斜的方向。但这并非“文明范式”,因为文明因素不是冲突的主导力量,它只能通过契合经济政治因素而发生影响。如果说一定要概括出一种模式的话,不妨称为国家物质利益主导的多元冲突模式。
国家物质利益在当今世界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前面所讲的一些因素外,更深层地看,乃是人类社会日益发展和国际政治日趋世俗化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越是欠发展,越是在远古时代,越是未开化,人们的行为就越受超物质因素的制约,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偏见以及亲族、血缘关系越成为划分敌友的界限;而人类越是发展、越是世俗化,非物质因素的作用就越弱,物质利益就越成为判断敌友的标准。为文明献身,为宗教捐躯的人固然还存在,但与过去相比不是更多了,而是越来越少。不管是好是坏,这是客观事实。而物质利益并不以文明为转移。冷战后,作为国际政治主体的民族国家,不是以文明来为自己定位,而是要以物质利益关系来为自己定位。因此,未来的全球冲突,不将取决于文明的差异,而取决于各国物质经济利害关系的消长。
下一世纪将是世界各国进入激烈的经济实力竞争的世纪,民族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物质利益分配不平衡将成为冲突最为可能的源泉。从表面和暂时来看,由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在冷战刚结束一段时间里的凸现,南北关系似乎成为冲突的主题,但在可见的将来,南方国家无一可具有经济物质实力与西方或北方国家抗衡,也不足以发展这种实力。因此,尽管南北经济摩擦将长期持续下去,甚至引发一些局部的军事冲突,但全球性战争却不会在南北之间爆发;从更深层和较长远看,北方大国物质力量的角逐将是重大国际冲突的始作俑者,如果有下一场世界大战,最有可能的将是北方国家之战。
重大的全球冲突,历来都是争霸战争,而争霸必须以经济物质力量为后盾。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在现代世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基本上是连续几个占霸权地位的民族国家活动的结果。尽管这些经济政治结构反映了占支配地位国家的经济利益,但也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扩张提供了机会。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分布的变化以及经济活动主体利益的变化,从中得益的经济活动主体,努力通过改变贸易、货币和其他方面的国际经济活动以及控制国家经济的规则,以求改造旧结构和建立新结构,而上述变化中蒙受损失的经济活动主体,包括衰落的霸主在内,都抵制这种要求,或力图使结构变得对自己有利,这样“新兴的强国和没落的强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最后要么诉诸武力,要么进行和平调整,而后矛盾才会得到解决。”(20)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经济格局,人们会奇怪的发现,作为胜利者的同盟国一个个在经济上相对衰落下去了,而轴心国却一个一个地创造了“经济奇迹”。这种变化所引起的矛盾,由于冷战的意识形态的表象而长期被掩盖着,一时没有爆发出来。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矛盾将逐步增加,并可能最终突发。一方面,老的霸主如美国尽管经济力量相对衰落但却想保持昔日的威风,不得不力图扩展自己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利益,并由此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大国之间经济力量的角逐最可能引发大的国际冲突乃至世界大战。
不仅大规模全球冲突的原因根植于北方大国的经济利益之中,而且冲突胜负的结果也由经济实力所决定,正象保罗·肯尼迪精心研究所揭示的,某一大国在军事冲突中的胜利或另一大国的失败,从更深一层的背景来看,“取决于该国在实际冲突发生前几十年间,同其他领先国家比较而言的经济上的兴衰情况。”(21)而经济实力的消长正是一个国家长期追逐其经济利益过程的结果。如果某一大国不在这一过程中抑制强大的对手的实力膨胀,就等于坐以待毙。认识到这一点,各强国就会加紧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削弱其他大国的经济力量,这反过来又构成了冲突的原因。因此,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北方大国冲突的原因和结果相互助长。如果新的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话,这将是其最基本的成因。
儒家与伊斯兰会联合对抗西方吗?
亨廷顿的观点之所以引起东方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除了上述各点外,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文明范式”的主要结论是:儒家与伊斯兰文明必结盟对抗西方,“在可见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儒家国家之间”。
对于这个问题,来自各方的批评已很多,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撇开其他不谈,即使按照“文明范式”本身的逻辑,它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按照这一范式的因果关系,文明的冲突产生于文明的差异,而文明的差异在亨廷顿看来也是要区别对待的。例如若以基督教文明为标准,俄国就与西方不同,因此其有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但就东方和西方文明两分法而言,俄国是比较接近西方的,而儒家和伊斯兰则与西方文明大相径庭,两者的联合是西方的大敌。然而奇怪的是,儒家与伊斯兰这两者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吗?这两者为什么非但不产生文明的冲突,反而会走向联合呢?是什么力量促使这种联合呢?按照“文明范式”,这是得不到解释的。相反,既然以文明的亲疏关系为敌友的标准,那么其逻辑结果应该是西方国家自然而然地与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儒家,因为从文明的亲族关系来看,正象汤因比指出的那样,东正教国家与西方国家是“姐妹文明”(所以亨廷顿认为俄国不是西方的主要敌人),伊斯兰教国家则是西方的“表姐妹文明”(22)。而儒家不但与西方文明,同样也与伊斯兰文明均无任何亲缘关系,且当今的儒家文化已经吸收了不少西方文化,却很少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那么按照文明范式的逻辑,怎么会是儒家与伊斯兰国家联手反对西方文明呢?
进而言之,在设想文明间是否会发生冲突的时候,不能抽象地谈文明的冲突,而必须考虑相关文明的实际内涵,考虑每一文明所包含的基本要素、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以及这些内涵与冲突是否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文明的冲突不只取决于文明的差异,而且还要看特定文明的特性。用斯宾格勒和本尼迪克特的术语说,只有浮士德型的文明才具有冲突的性质,而日神型文明则具有和谐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伊斯兰国家与基督教国家会发生冲突,尚还有所根据。因为从经验层面看,历史和现实表明这种冲突始终存在,而从文化的层面看,伊斯兰教是非世俗宗教,具有较强的文化排他性。然而,儒家与伊斯兰则不可等量齐观。儒家文化本身是一种世俗文化,它有较强的包含性,并不排斥西方文明。尽管儒家文化与西方有价值观的分歧,但它对西方文化的涵化和吸收构成了鸦片战争后的一个重要趋势,而在近几年新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象日神型文明那样,儒家文明是爱好和平的一种文化类型。诚如很多中西贤哲所说,儒家文化是一个追求和谐的文化,它主静不主动,从来不会自己去和别的民族发生冲突。反观历史,重文轻武、崇尚和平,是儒家文明的基本要素,所以雷海宗教授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曾说“中国自东汉以降为无兵的文化”,而梁漱溟先生则进而指出中国历史上几乎为“无兵之国”,此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23)。林语堂则认为,中华民族不象基督徒自称“为牺牲而生存”,而只想安宁现世的生命,中国人“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他们痛恨战争,永远地痛恨战争,好百姓从来不在中国战争”(24)。马克斯·韦伯也特别注意到了儒家文化的这一特征,相信“儒教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25)。美国的汉学权威费正清同样也指出,“轻视兵士在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可与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或者日本的海上冒险和海盗制度相比拟的时期,致使中央政权靠海外掠夺而富强”,因此中国的武力问题基本上是为了维持国内秩序的“警察问题”。(26)池田大作进而断定,中国投入的战争都属“自卫战争”,“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27)英国汉学权威李约瑟依然认为中国官僚封建社会形成了一种尚文而不尚武的社会风气,并说“中国历史上尚文而不尚武的精神仍将继续保持下去,并预示着今后几个世纪中基本上和平发展的前景。”(28)可见,即使按照文明范式推论,所谓儒家——伊斯兰联合对抗西方说也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文明冲突这一模式本身就难以成立。
无庸讳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并没有成为一种理论“范式”,而是一种“神话”,它不仅无法解释当今世界一般的冲突,而且构成了冷战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冷战意识形态的继续。因为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消失后,社会主义作为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政治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而其中最为强大也最有前途的就是中国。另一方面,苏联的解体虽然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却使西方失去了一个主要的共同敌人,正象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1994年11月“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所说:美国40年的来的目标一直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但现在却失去了目标,美国没有了敌人。(29)这样,西方世界的凝聚力就大打折扣,美国则很难维持其冷战时期作为西方盟主的特权地位。这时为西方国家重新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哪怕是一个假想敌,以重建美国对西方的领导权,也就显得十分迫切了。由于冷战的意识形态毕竟不能适用新的国际形势了,如何找出一种新的“理论”,既能对遏制中国提供合理性,不露痕迹地为西方提供一个假想敌,又不致流于赤裸裸的意识形态纷争,避免有老调重弹之嫌呢?亨廷顿在这种情况下推出其文明冲突的神话,无疑是用心良苦的。如同乔治·凯南在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就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那篇署名为X的文章从而为西方遏制苏联的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一样,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又在同一份刊物上发表一篇把儒家——伊斯兰视为西方头号敌人的文章,其意识形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文明范式”被企图用以代替已经失灵的冷战策略,然而,如果说冷战策略还多多少少反映了二战以后世界格局的核心内容的话,那么,“文明范式”则根本没有抓住冷战后国际冲突的要害,而只能被视为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这种神话,如果象托马斯·库恩所说作为科学研究之中“必要的张力”存在,也许对激发人的思想还有某种价值,而若作为库恩所说的“范式”来分析日益纷杂的国际格局并用于指导外交实践,未免就显得是削足适履且荒诞不经了。因此,尽管“文明冲突”论可以一鸣惊人,但也只能昙花一现,沦为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只有从冷战后世界经济物质利益主导这一现实出发,才有助于建构一种国际战略的宏观分析模式。
注释:
①(17)(18)K.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5页,1页,175页。
②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2-293页。
③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④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英文原名:Cultural Anthropology),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48页及535-546页。
⑤F.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
⑥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2页。
⑦Lucian W.Pyc,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 Brown,1966,PP9-11,198-199.
⑧J.Rosenau,Turbulance in World Politics:A Theory of Changes and Continuit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419-420.
⑨M.Featherstonc,Global Culture:Nationalism,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London:Sage,1990.另参见M.Albrow & E.King,Globalization,Knowledge and Society,London:Sage,1990;R.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Sage,1992.
⑩(22)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4页,133页。
(11)S.M李普塞:《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8-10页。
(12)《R.C.宾克莱文选》,马克斯·费希编,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328页。转引自H.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商务印书馆,1993年。
(13)H.摩根索:《又一次“大辩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参见S.霍夫曼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4页。
(14)《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4-325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16)H.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17-419页。
(19)(27)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99-300页,290页。
(20)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0-111页。
(2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页。
(2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20和164页。
(24)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53-56页。
(25)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26)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50-51页。
(28)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三联书店,1987年,第32页。
(29)参见“1994年华盛顿‘中美关系研讨会’侧记”,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1期,第50页。
标签:文明的冲突论文; 亨廷顿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范式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美国史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