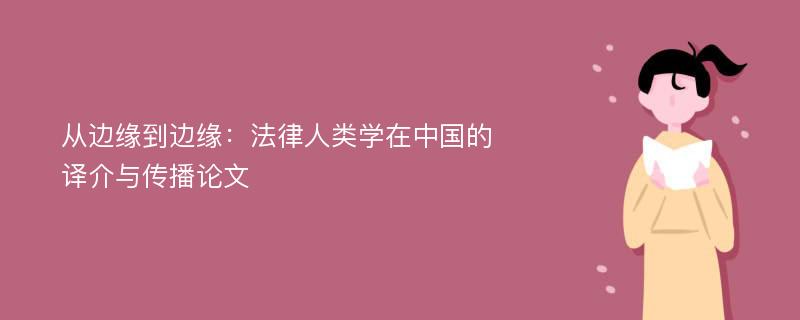
从边缘到边缘:法律人类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王伟臣*
内容摘要同样都是源自西方且有着百年历史的关于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为何法律人类学在中国仍表现出一副“新兴学科”的面貌?本文拟对法律人类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进行一番梳理。改革开放以后,重新获得启蒙的中国法学发现法律人类学的“只言片语”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案例支撑功能,所以开始碎片化地引入。1997年以后,随着几部译著的出版,略显神秘的法律人类学终于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各种“填补空白”的作品集中地出现。2010年以后,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互联网文献库的普及,导致外文文献获取难度大幅度降低,前沿、专题研究日渐成为主流。虽然法律人类学与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一同进入中国,但是在影响力上较后两者差距甚远。在西方就是一门“不太成功”的边缘学科,进入中国也就难以避免地继续被边缘化了。
关键词 法律人类学 霍贝尔 人类学 法律社会学 译介与传播
近年来,随着社科法学的影响不断扩大,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法律人类学得到了不少“曝光”机会。比如,侯猛、陈柏峰、刘思达等学者在关于社科法学的评述和讨论中都提到了法律人类学。① 参见侯猛:《法学研究的格局流变》,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前言第3页;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陈柏峰:《社科法学及其功用》,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刘思达等:《社科法学三人谈: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载《交大法学》2016年第1期。 但是在当代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法律人类学有没有资格和能力进入社科法学阵营是大大存疑的。因为无论是从研究的规模还是深度上看,当代中国的法律人类学都难以同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等“传统”的交叉学科/社科法学相比。② “社科法学已经形成规模的有三种研究进路: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法律认知科学。所谓形成规模,主要指的是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群体,具有一定数量的知识产出。”参见前引①,侯猛书,第3页。 同样都是源自西方且有着百年历史的关于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为何法律人类学在中国仍表现出一副“新兴学科”的面貌?究竟是移植之后的水土不服,还是西方法律人类学自身的原因?③ 在本文语境中,西方法律人类学主要指的是19世纪末近代学科体系建立之后,关于法律的人类学研究。 为此,本文拟对法律人类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进行一番梳理,并尽可能地将译介作品及其理论观点在国外的学术谱系中进行定位,同时着重考察不同译介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相承关系,以期能够解释此项研究在中国的遭遇。按照目的和规模,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碎片化地引入
同法律社会学一样,法律人类学向中国的知识传播肇始于民国时期,代表作当属瞿同祖于1947年完成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这本书一般被归类为“中国法制史”、④ 参见周会蕾:《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制史学史》,华东政法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孙国东:《功能主义“法律史解释”及其限度——评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11期。 “法律社会史”⑤ 参见杜月:《社会结构与儒家理想:瞿同祖法律与社会研究中的断裂》,载《社会》2012年第4期。 或者“中国法律思想史”⑥ 参见王志强:《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以研究对象和方法为线索》,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苏力:《在学术史中重读瞿同祖先生》,载《法学》2008年第12期。 等领域的作品。但是从研究范式与参考文献上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显然还受到了法律人类学的诸多影响,而这又与瞿同祖的求学经历和学术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瞿同祖曾回忆:“在燕京大学,我主要上社会学系和历史方面的课。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吴文藻……”⑦ 王健:《瞿同祖与法律社会史研究——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几年后,他又在吴文藻的指导下,获得了硕士学位。作为人类学中国化的奠基人,吴文藻在人类学研究方面最著名的学术观点或贡献就是借用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推进中国的社区研究。⑧ 参见祁庆富:《论吴文藻先生引进西方文化理论的贡献》,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此外,吴文藻在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还曾旁听过“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FranzBoas)及其女弟子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的课程,所以他对于美国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也并不陌生。
受此影响,作为吴门嫡系弟子的瞿同祖在求学期间就已经接触了人类学的经典作品,而后又追随导师的足迹于1944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交流访学。所以,《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所引用的为数不多的十余篇外文文献大都与人类学有关。它们包括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E.Westermarck)的《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⑨ E.Westermarck,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Macmillan,1912. 英国民俗学家哈特兰(E.S.Hartland)的《原始法律》、⑩ E.S.Hartland,Primitive Law,Methuen,1924.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罗维(R.H.Lowie)的《初民社会》、[11] R.H.Lowie,Primitive Society,Boni&Liveright,1920. 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以下简称为《犯罪习俗》)[12] B.Malinowski,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Kegan Paul,1932. 以及美国人类学家霍贝尔(E.A.Hoebel)的《科曼奇印第安人的政治组织与法律方式》等。[13] E.A.Hoebel,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Law-Ways of the Commanche Indians,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U.S.A.,No.54,1940. 而这其中最后两部作品更是意义非凡。马林诺夫斯基的《犯罪习俗》是近代法律人类学的开山之作,[14] Annelise Riles,Representing In-Between:Law,Anthropology,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Illinois Law Review,1994,p.603. 霍贝尔的博士论文《科曼奇印第安人的政治组织与法律方式》则使用当时法律人类学领域最为前沿的纠纷案例研究方法(troublecase method)。[15] 参见王伟臣:《法律人类学个案研究的历史困境与突破》,载《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那么,瞿同祖是如何接触到这两部作品的呢?据其回忆,1939年“去了云南大学,开了一门课讲中国法制史……又读了人类学家写的书,有马凌诺斯基的《蛮族社会之犯罪与习俗》……”。[16] 前引⑦,王健文。 “在云南大学阅读人类学”意味着,1940年左右,1932年版的《犯罪习俗》就已经传入中国了。霍贝尔的博士论文虽然完成于1934年,但是笔者有理由推测,瞿同祖应该是在1944年前往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到的。其实,在1944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还有一部作品对法律人类学影响远远超过了《科曼奇印第安人的政治组织与法律方式》,那就是1941年霍贝尔与法学家卡尔·卢埃林(KarlN.Llewellyn)合著的《夏安人的方式:原始法学中的冲突与判例法》(以下简称为《夏安人的方式》)。[17] Karl N.Llewellyn and E.Adamson Hoebel,The Cheyenne Way:Conflict and Case Law in Primitive Jurisprudence,University ofOklahoma Press,1941. 但遗憾的是,《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并没有引用这部作品。[18]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947年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甚至把霍贝尔的英文名错写成“Hobel”。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0页。 毕竟对瞿同祖而言,参考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只是为第一章的第四节“亲属复仇”和第五章“巫术与宗教”提供案例支撑。不过,马林诺夫斯基、霍贝尔等人的作品能够出现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脚注中本身就极有意义,它们标志着西方法律人类学向中国传播的开端。
笔者目前能够找到的第一篇专门介绍法律人类学研究的汉语作品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夏晓兰翻译的《人类学与法律》,收录于李亦园在1974年所编写的《文化人类学选读》中。[19]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律人类学的传播似乎并未中断。比如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在1974年所编的《文化人类学选读》中就刊载了由夏晓兰所翻译的《人类学与法律》。参见李亦园主编:《文化人类学选读》,台北食货出版社1974年版,第161-167页。 原作者为美国著名法律人类学家保罗·博安南(Paul Bohannan),原文收录于美国人类学家索尔·塔克斯(SolTax)于1964年主编的论文集《人类学的视野》中。[20] Paul Bohannan,“Anthropology and the law”,in Sol Taxed.,Horizons of Anthropology,Aldine Pub.Co,1964.
进入1980年代,大陆学术界开始大规模译介西方社会科学文献。西方法学的各个流派以及涉及法学的交叉研究几乎都参与其中。比如,据刘思达的观察,对西方法律社会学文献的翻译和研讨,“从对庞德、埃利希、韦伯、霍姆斯等经典理论家的介绍,到对布莱克(Donald Black)、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科特雷尔(Roger Cotterrell)、卢曼(Niklas Luhmann)等同时代的国际知名法律社会学家的关注,我国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基本上‘全盘西化’了”。[21] 刘思达:《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载苏力主编:《法律与社会科学》(第7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正是在此基础上,赵震江、季卫东、齐海滨发表于《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3期)的《论法律社会学的意义与研究框架》才能够全面地回顾了国外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史和主要流派。大概是因为对法律社会学的介绍已经比较丰富了,就在这一时期,有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推出了几篇关于法律人类学的译介文章。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再次刊登了一篇法律人类学的作品——朱晓阳的《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截至本文写作之时,在中国知网以“法律人类学”为主题的论文中,这篇论文以2678次的下载量高居榜首。比两年前高丙中、章邵增的论文多出了近1200次。那么,同样都是《中国社会科学》所刊登的关于法律人类学的论文,为何朱文在下载次数上超出两年前的文章近两倍?是不是因为朱文关于西方法律人类学的梳理更加全面、深入呢?恰恰相反,朱晓阳的论述完全跳出了由张冠梓所创立的“马林诺夫斯基与霍贝尔(原始法)——格卢克曼与博安南争论(规则与过程)——纳德、穆尔(法律多元主义)”的叙述范式,甚至和法律人类学的学术脉络没有太多的交集。当然,朱晓阳所谓的“语言混乱”与格卢克曼与博安南争论关切的都是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语言混乱’一直困扰着费孝通先生式的知识分子。这种困扰是因为舶来‘实证科学’教条与‘在地’的信念和知识之间无法‘视野融合’引起的”。这种“语言混乱”不仅仅是中国才有的独特性问题,它是全世界所有非西方文明的共同遭遇,比如格尔茨所讲述的“雷格瑞的麻烦”。[71] 参见前引[55],吉尔茨文,第84-86页。 于是,朱晓阳便从格尔茨的“整体论”入手,探索如何将其“注入‘法’的实践和法律构建中去”。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在梁治平的《法律的文化解释》与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之间建立了联络。这篇论文的目的并非在于传播法律人类学的知识理论,而在于试图与之对话并回应中国的本土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1987年第6期的《世界民族》杂志发表了由杨周云翻译的德国汉堡大学人类学家克劳斯·科赫(Klaus Friedrich Koch)的论文《法律与人类学》,原文曾收录于美国人类学家皮特·哈蒙德(Peter B.Hammond)主编的论文集《文化和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的入门读物》中。[26] Klaus Friedrich Koch,Law and Anthropology:Notes 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in Peter B.Hammond eds.,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Ethnology,Collier Macmillan Ltd,1975.这篇文章最早以“Law and Anthropology:Thoughts 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为名发表于Law and Society Review,Vol.4,1969,pp.11-27. 1965年左右,科赫曾与老师纳德一道对1964年以前的法律民族志的作品(主要以英语为主,也包括一小部分德语、法语、荷兰语)进行了系统的检索和整理。[27] 他们于1966年在《当代人类学》第7期上发表了相应成果——《法律的民族志:一个文献学回顾》。Laura Nader,Koch Klaus and Bruce Cox,The Ethnography of Law:A Bibliographic Survey,Current Anthropology,Vol.7,No.3,1966,pp.267294. 所以,科赫对于法律人类学历史的了解远在克雷齐尔之上。他的这篇文章不仅提到了经典作品,而且还着重介绍了二战以来人类学回归本土之后的“对当代社会的法律研究”。在科赫看来,法律人类学绝不同于原始(野蛮)法律的研究,“人类学家为法律界人士提供了有价值的从经验主义的分析中得到的实据”。因而,科赫也对霍贝尔的《原始人的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该书试图对法律体系所做的全面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
某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4×320 MW,其最高净水头502.7 m,输水系统水平总长度2 449 m,其中中平洞衬砌后直径为9.2 m,衬砌厚60 cm,静水头约300 m。中平洞存在长约40 m的V类围岩洞段,该洞段发育有f24、f20和f80三条较大断层。断层均为全风化构造角砾岩,围岩见高岭土化,地下水多呈渗滴~线流状,最大渗水量约5 L/min~6 L/min。断层外围岩裂隙发育,裂隙走向总体与断层垂直。该洞段地质平面展布图见图1。
一年后,林端在《中国论坛》(1988年第298期、第299期)上发表了论文《法律人类学简介》(以下简称为《简介》),后收录于1994年出版的论文集《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中。虽然在发表时间上稍晚于上述两篇译文,但无论是从篇幅字数,[28] 据笔者的手工统计,《法律与人类学》约7500字,《法律人类学评介》约8000字,而林文约17000字,比两篇译文的总和还要多。 还是从理论深度上看,这篇《简介》都堪称汉语学界关于西方法律人类学最早的、最全面系统的引介性文献。或者说,此文早已超出了“引介”的高度,其对于西方法律人类学的细致观察与真知灼见,时至今日都不过时。文章围绕着“法律是动态的文化现象”“与所谓高阶文化中法律体系的区别”“术语问题——两难”“何谓‘法律’”“法律的基础——相互性”“民风、风俗与法律”“法律的社会功能——法律人类学的出路”以及“法律多元主义与法律人类学任务”等问题展开讨论。在笔者看来,林文的最大贡献在于,它首次向国内读者介绍了“术语问题——两难”,即20世纪中叶格卢克曼与博安南关于西方法律与前工业社会法律共性及差异的分歧、西方法律范畴能否以及怎样研究前工业社会法律的争论。这场争论是20世纪法律人类学最为重要的学术事件,不仅反映了此项研究在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困境,而且还引发了研究范式的变革。[29] 关于这场争论的详情,参见王伟臣:《法律人类学的困境——格卢克曼与博安南之争》,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更重要的是,术语的翻译及使用具有普遍性意义,是西方社会科学本土化绕不开的问题。
但是这篇《简介》依然存在些许不足之处。虽然在参考文献中,林端列明了博安南、纳德、波斯皮斯尔、西蒙·罗伯茨(Simon Roberts)等英美学者的论著,但在正文讨论中他却只是参考了两份德文资料,即乌韦·韦塞尔(Uwe Wesel)在1985年的专著《国家社会之前的早期法律形式》[30] Uwe Wesel,Fruhformen des Rechts in Vorstaatlichen Gesellschaften,Suhrkamp,1985. 以及绍特(R.Schott)在1983年的论文《法律民族学》。[31] R.Schott,Rechtsethnologie,in Hans FischerHg.Ethnologie,eine Einführung,Dietrich Reimer Verlag,1983,SS.181-203. 作为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林端具有德国民族学的学术背景,参考德国学者的研究资料对法律人类学进行介绍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国际法律人类学界,德国民族学都还处于边缘地位,[32] [挪威]费雷德里克·巴特、[奥]安德烈·金格里希、[英]罗伯特·帕金、[美]西德尔·希尔弗曼:《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79页。 与之相关的,德国法律民族学[33] Hanser Peter,New Perspective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Law:A Short Report on the First German-French Symposium,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Unofficial Law,Vol.28:187(1989). 不仅难与英美法律人类学分庭抗礼,甚至在欧陆也远远落后于荷兰学派。[34] 参见王伟臣:《法律人类学的身份困境——英美与荷兰两条路径的对比》,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 此外,1988年的林端正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撰写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为来年的答辩做准备。那么,他为何要在学业、生活双重压力之下[35] 根据林端夫人吕爱华女士的说法,“一边摇着他的第一个儿子,一边写作论文,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参见吕爱华:《林端先生生平事略》,载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574,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7月17日。 耗费心力去撰写一篇并不能代表德国学术传统的引介性文章呢?答案就在于其1989年完成的硕士论文的题目即为《韦伯的社会学式的法律概念:一个法律人类学观点的分析》。[36] Duan Lin,Der soziologische rechtsbegriff Max Webers:Eine analyse aus rechtsethnologischer sicht,MA Arbeit,Uni Gottingen,1989(unpublished manuscript,on file with author). 《简介》与其硕士论文有着高度的关联性,简言之,林端试图通过法律人类学的视角来解读韦伯。6年后,他在博士论文中对韦伯学说的批判同样也引用了法律人类学的观点。[37] 关于林端对法律人类学译介以及法律人类学对林端的意义,参见王伟臣:《法律人类学的启蒙——评林端〈法律人类学简介〉》,载《法律书评》(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8-97页。
与此同时,张乃根在《法律科学》(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大陆学者关于法律人类学的第一篇专题论文《当代人类学法哲学评述》。文章开篇就阐明了写作目的:“新中国建立后,文化人类学曾长期遭禁锢,人类学法哲学更是鲜为人知。本文尝试对人类学法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当代英美人类学法哲学的研究领域及其启示作初步的评述。”不过,限于前期研究不够充分,这篇文章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不及林端的梳理。但是有一点作者倒是非常明确:“英美人类学家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法律,……法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这一论断要比后来很多介绍性论文动辄声称“法律人类学是法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要严谨得多。两年后,《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2期)刊登了么志龙的论文《通向文化之路——从历史法学派到法律人类学》。这篇文章视角非常独特,试图寻找历史法学派和法律人类学之间的理论勾连。可是,萨维尼和马林诺夫斯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此外,文章还分析了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的差异,并尝试阐明马林诺夫斯基、霍贝尔学说的理论前提,这种叙述视角较之张乃根的介绍有所进步,但碍于资料有限,讨论得不够深入。
山西省忻州市某水库1号输水隧洞位于水库灌溉取水口下游500 m与进库道路交叉处,为单孔正圆形型隧洞,长度为58 m,采用模筑混凝土工艺成型,内径2.2 m,洞壁厚度为400 mm,混凝土设计强度为C30W8。混凝土作为输水隧洞的主要材料,对于工程的使用功能和使用寿命来讲非常重要,其耐久性是工程设计最重要的技术指标,提高混凝土耐久性就是要通过技术措施提高隧洞混凝土抗裂、抗渗、抗碳化、抗碱反应的能力,使混凝土工程具有高抗裂性、高抗碳化性、高抗渗性、高抗侵蚀性,从而满足工程使用功能和要求。本文论述在施工中满足其要求所应采取的技术措施。
1992年8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严存生等人所翻译的霍贝尔的名著《原始人的法》。[38] [美]霍贝尔:《原始人的法》,严存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为给译著做“广告”,在出版的前一年,严存生在《法律科学》上专门撰文介绍霍贝尔的法人类学,内容和译著中的“译者前言”部分大致相同。参见严存生:《霍贝尔的法人类学》,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4期。 一年后,该书的另外一个译本,即周勇翻译的《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为什么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没有一部西方法律人类学的译著,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突然于一年之内出现了一本书的两个译本?《原始人的法》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在英美法律人类学界,霍贝尔是继马林诺夫斯基之后的第二代法律人类学家的领军人物,也是第一位专门从事法律研究的人类学家。他的代表作当属1941年与卢埃林合著的法律民族志《夏安人的方式》。在这部书中,两位作者进一步丰富了纠纷案例研究法,成为此后数10年法律人类学领域的标准方法。[39] 参见前引[15],王伟臣文。 这部作品也被称为“当代人类学法学研究之开端”。[40] P.H.Gulliver,Introduction for Case Studies of Law in Non-Western Societies,in Laura Nader ed.,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11. 此书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使用法律职能(Law-Jobs)的术语,而不是法律或法律制度,从而避免了关于法律究竟如何定义这种无休止没有意义的讨论”。[41] Laura Nader,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Law,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67,No.6,1965,p.10. 法律的定义是马林诺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需要处理的问题,而从《夏安人的方式》开始,法律人类学已经不再考虑法律的定义了。不过,在此书写作过程中,霍贝尔曾提议在结论部分像马林诺夫斯基一样阐述一个广义的法律定义,但是遭到了卢埃林的反对,这也是合作过程中为数不多的分歧之一。[42] William Twining,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3,p.178. 笔者猜测,这就为后来《原始人的法》为法律下定义埋下了伏笔。
20世纪50年代是法律人类学的黄金时代。格卢克曼、博安南、波斯皮斯尔纷纷学习霍贝尔发明的纠纷案例研究法,完成并出版了各自的经典作品。[43] 前 引 [24],Gluckman书;Paul Bohannan,Justice and Judgment among the Tiv,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Leopold J.Pospisil,Kapauku Papuans and TheirLaw,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1958. 作为前辈的霍贝尔此时已经成为美国犹他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长,不可能再只身前往印第安部落进行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了。所以,他就综合爱斯基摩人、伊富高人、科曼切人、凯欧瓦人、特罗布里恩德人和阿散蒂人的研究资料完成了《原始人的法》。这里面除了科曼切人之外,其他民族的资料都是来自其他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在此之前,一部严格意义的法律人类学的作品必须是经过田野调查而完成的法律民族志,比如《夏安人的方式》。除了政治人类学家琼·维森特(Joan Vincent)独辟蹊径地认为“《原始人的法》的出版标志着这一学科(法律人类学)真正确立”[44] Joan Vincent,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Visions,Traditions,and Trends,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0,p.307. 之外,法律人类学界并没有把这本书列入经典著作的行列。[45] Robert M.Hayden,Review:Rules,Processes,and Interpretations:Geertz,Comaroff,and Roberts,American Bar Foundation Research Journal,Vol.9,No.2,1984,pp.469470;Chris Fuller,Legal Anthropology,Legal Pluralism and Legal Thought,Anthropology Today,Vol.10,No.3,1994,p.9. 不过,《原始人的法》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模式——根据二手民族志材料进行理论分析,大大降低了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成本,从而标志着法律人类学不再是法律民族志的代名词。不过,与同时期格卢克曼等人的法律民族志相比,《原始人的法》的确是一部过时的作品。[46] 穆尔曾这样评价《原始人的法》:“在今天看来,我们会说这并不是一本很好的书。他所做的是比较了五六个社会,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章节。他将每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缩减成几项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都是从他们社会的秩序中体现出来的。而他没有告诉你他得出这些原则的方法,这就是一种个人的解释。那他怎么知道这些就是原则呢?根本没有办法来证明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张冠梓主编:《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既然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当时还要翻译这本书呢?首先,当时国内对于西方法律人类学的学术谱系并不了解;其次,《原始人的法》似乎可以回应当时法学界的一场争论。严存生版的“译者前言”开篇就提到:原始社会有没有法律?100多年来,这个很有魅力的问题一直在吸引着许多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的研究者。的确,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以上各个学科都有着重大意义。就法学而言,它涉及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等一系列法理学上的重大问题。前几年里,我国法学界围绕着法律的本质和基本属性而展开的讨论也涉及这个问题。应该说至今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不统一,各人有各人的回答。《原始人的法》这本书就是著名法人类学家埃德蒙斯·霍贝尔对此问题的一种回答。[47] 参见前引[38],霍贝尔书,译者前言第1页。
全面推进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需关注的问题及建议……………………………………………………… 胡四一(16.1)
原始社会有没有法律?霍贝尔的书名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可能就是严存生等人早在1986年就完成了译稿的原因。[48] 参见前引[38],霍贝尔书,译者前言第11页。巧合的是,《原始人的法》也在同一时期进入日本。1984年,两位译者千叶正士和中村美孚将书易名为《法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参见[美]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校者前言第1页。 可能为了进一步强调“原始法”的意义,他们还删去了原书的副标题“法律的动态比较研究”。[49] 有趣的是,在2012年的第2版中,《原始人的法》终于加上了副标题:法律的动态比较研究。大概是因为在2012年,中国法学界就不再关心原始社会空间有无法律的问题了。参见[美]霍贝尔:《原始人的法——法律的动态比较研究》,严存生等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但是霍贝尔笔下的特布罗利恩德人、科曼切人等“原始人”并非是几万年前原始社会的人,而是与霍贝尔、马林诺夫斯基处于同一时代(20世纪)的人。这些人所生活的社会,虽然经济、科技不够发达,但是同样也有着漫长的历史、复杂的政治组织与婚姻系统。可是在19世纪后半叶社会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下,第一代人类学家将他们称为“原始人”或“野蛮人”。进入20世纪以后,进化论对人类学的影响逐步减弱。20世纪40年代,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以文学生态学为基础提出了“新进化论”,但是霍贝尔的《原始人的法》与此毫无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原始人的法》从书名到内容实实在在是一部过时的作品。中译本《原始人的法》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它是西方法律人类学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译著,在影响力上远远超过此前所有的节译短文和介绍性文章,并很快成为汉语学界法律人类学的“经典名著”。尽管在西方法律人类学的发展脉络中,此书不够新颖,但毕竟视野宏大地把五个不同民族的习惯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在周勇版的“校者前言”中,我国民族法学的奠基人罗致平认为,此书对于中国民族法学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50] 参见前引[48],霍贝尔书,校者前言第10页。 这大概可以部分解释周勇翻译此书以及保留副标题的初衷。《原始人的法》与《初民的法律》本想抛砖引玉,但是却没有立刻获得回应,多年不见新的译著出现。此外,书名中“原始”与“初民”的字眼共同制造了一个误解:法律人类学被当成“原始法”或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代名词。
1993年,梁治平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4卷]上发表了一篇在中国当代法学史上颇具影响的论文《法律的文化解释》;一年后,全文收录于其主编的同名论文集中。文章开篇阐明宗旨:“本文要提出的是所谓的文化的解释。由这个标题,人们可能首先联想到人类学和解释学。的确,以下的讨论着重于人类学和解释学之处甚多。”[51]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页。 在梁治平看来,“语言就组织同时也限定了人们对于实在本身的理解”,为此他颇有洞察力地分析了格卢克曼与博安南的分歧,将其表述为“关于‘概念’和‘语言’的争论”。[52] 参见前引[51],梁治平文,第20-27页。 从引文来看,他主要参考的是纳德根据1966年法律人类学会议编纂的论文集《文化和社会中的法律》。[53] Laura Nader ed.,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Aldine Publish,1969. 除了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之外,梁治平还参考了露丝·本尼迪克特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也译作吉尔茨)等并未专门从事过法律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的学说。但是,在梁治平关于“法的概念”的讨论中,象征人类学家格尔茨却在法律人类学的语境中出现,因为他有一句名言——“法律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54] 参见前引[51],梁治平文,第53页。
1981年,考虑到格尔茨在整个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日益剧增的影响力,他成为继格卢克曼之后第二位获得耶鲁大学法学院斯托尔斯讲座(Storrs)邀请的人类学家。为了准备这次讲座,格尔茨首次使用阐释人类学的方法用于法律问题的分析,而后将讲演稿集结命名为《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与另外七篇论文共同组成了《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并于1983年出版。[55] 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act and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Basicbooks,1983.中文译本参见[美]克利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前引[51],梁治平主编书,第73-171页;[美]克利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正是因为这是一篇应景之作,同时也从未出版过法律民族志,所以,“格尔茨从来都没有被看作是一名法律人类学家,而且对于这一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似乎全然不知(对于70年代的作品都没有参考)……”。[56] 前引[45],RobertM.Hayden文,第475页。 他的“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也很快被戳中了要害:“讽刺的是,格尔茨作为‘地方性知识’以及文化间差异重要性的拥护者,却不加鉴别地采纳了‘法律’(law)这个单词所具有的标准的英语意义。到了这里,他整个理论都已经坍塌了”。[57] 前引[45],RobertM.Hayden文,第475页。 因此,在格尔茨的两部论文集共23篇论文中,这篇文章并非是出类拔萃之作。梁治平也敏锐地觉察到了些许异样,但是却解释为“与其以往精细入微的个案分析不同,吉尔兹在这篇文章里引人注目地采取了宏观研究策略”。[58] 参见前引[51],梁治平主编书,前言第9页。 因而,在《法律的文化解释》论文集中,梁治平特别收录了由邓正来翻译的《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这篇译文对中国法学产生了极大影响。1996年,苏力在其代表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运用吉尔茨关于‘任何法律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59]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序(赵晓力)。不过后来苏力又解释说:“我所使用的地方性知识受到吉尔兹的启发,但是有重大的不同。”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在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与“本土资源”之间建立勾连并一同成为反对法律移植的两大论据。[60] 参见何勤华等:《法律移植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而后由于苏力理论学说的广泛流行,格尔茨及其“地方性知识”在中国法学界也迅速走红,成为一种时髦的标签。
通过上文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不管是瞿同祖研究中国古代巫术与宗教,还是林端解读与批判韦伯,或者严存生回应法律起源与本质的争论,亦或梁治平阐述法律的文化解释,法律人类学与象征人类学可以为他们提供案例或理论支撑,所以他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碎片化的形式引入了法律人类学的“只言片语”。[61] 需要说明的是,1996年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了由石泰峰撰写的《跨越文明的误区——现代西方法律人类学》。可惜的是,笔者未能找到这本书。
3.利用好信息技术,发挥技术上的优势。当今是知识经济信息时代,任何活动都需要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开展。当然,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优化了经营管理程序,也能有效节约了管理的成本。企业需要结合信息技术,建立自身管理活动的信息技术机制。信息技术的强大功能,能够有效协调管理活动的各要素,通过应用信息技术,从而实现经济管理的成本最低。当然,利用信息技术来开展管理时,不仅是系统上的优化,而且通过对相关管理信息进行筛选,也能够让企业获得有效信息,进而服务于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
溧阳南山水库片区乡村旅游公路属于县域旅游公路,包括平横线、金溪路、金牛路、黄南线、X305、G233等公路组成,公路长度共计35 km(图2)。全线途经平桥、松岭、黄岗岭等多个村落。同时也串联起平桥石坝、青峰山庄、横涧幽兰园艺场等多个主要景点。沿线旅游资源类型丰富、价值较高,总体布局完善、功能明确,沿线可视景观优美、形式乡土自然,重要区域和景点配置服务设施完善。
二、第二阶段:填补空白式的介绍
20世纪初期,人类学受到了韦伯式的法律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法律与经济、政治、宗教等社会现象不同,不具有普遍性,只存在于发达文明的社会中。但是1926年出版的《犯罪习俗》却拓宽了法律的定义,认可了部落社会习惯规则的“法律”性质,为今后人类学家涉足法律研究奠定了基础,标志着现代法律人类学的诞生。不过,《犯罪习俗》对法律人类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它对于马林诺夫斯基本人的重要性。在学科创立模式上,文化人类学没有参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对西方本土资源的切割而专注于非西方社会(部落社会)的研究。所以,马林诺夫斯基其实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社会科学家,他关注的是特罗布里恩德社会的各个方面。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当地人最为特别的制度当属“库拉圈”的交换体系,以此为基础完成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才是他的代表作,被誉为“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65] 中译本由梁永佳、李绍明翻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出版。 在田野调查期间,尽管马林诺夫斯基记录了一些法律案例,但是直到获得皇家人类学会的讲座邀请之前,他并没有撰写一部法律民族志的打算。[66] 参见[英]布·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页。 所以,作为法律人类学经典的《犯罪习俗》其实是马林诺夫斯基在一个小时的演讲稿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一篇长论文。可是,就是这样一篇只有几万字的论文,从瞿同祖自1947年首次引述后,过了整整半个世纪才被译成中文。许章润的译本尽管用词准确、自然流畅,但法学集刊的影响力毕竟不如由出版社汇编成册的学术专著,所以,在知名度上远不及原江的译本。同时,由于在前期的译介作品中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人气”,所以,2002年《犯罪习俗》的出版所产生的效果甚至超过了10年前的《原始人的法》,仿佛宣告了一项全新的研究领域开始进入中国。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出现了数十篇关于西方法律人类学的介绍性论文。
4年后,汤浅道男等人为了庆祝千叶正士七十寿辰而出版的论文集《法人类学基础》,由徐晓光、周相卿翻译出版。论文集分为四个部分:“法人类学的成立与展开”“作为基础法学的法人类学”“固有法文化的各种样态”“多元法体制下的法文化”。每一部分都由数篇论文组成,比如“作为基础法学的法人类学”包括《法思想史与法律人类学》《法史学与法人类学》《比较法学与法人类学》《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法符号学与法人类学》《法人类学与法哲学》。这些论文每篇都短小精悍,以4000字左右的篇幅从不同侧面展示法律人类学的发展脉络、理论方法以及重要的学术成果。此书对于我们了解西方法律人类学在日本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法律人类学传播的角度来讲,它比千叶正士的《法律多元》更有意义。几年后,本书的译者徐晓光还专门发表论文《日本法人类学及民族法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对日本法律人类学以及民族法学的发展过程及研究水平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不过,可能是因为在香港地区出版的缘故,《法人类学基础》在内地学界影响很小。[64] 据笔者的梳理,似乎只有四篇文章引用过这本著作,包括张冠梓:《法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其流变》,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张永和:《法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及其他》,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吴大华:《论法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张文山:《关于法人类学若干问题的思考》,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与之相比,200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学者布·马林诺夫斯基著、原江翻译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以下简称《犯罪习俗》)却极大地促进了法律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
2.2 暴露方式及部位 暴露方式:锐器伤82名、占68.91%,黏膜暴露17名、占14.29%,皮肤暴露15名、占12.60%,其他5名、占4.20%;暴露部位:手指95名、占79.83%,手臂17名、占14.29%,眼7名、占5.88%。
其实在2000年左右,作为“法律人类学爱好者”的原江就已经译完了《犯罪习俗》。而在更早之前,《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秋季号)甚至已经刊登了由许章润翻译的《初民的法律与秩序(I)》——《犯罪习俗》的第一部分。随后,该集刊《1998年春季号》继续刊登了第二部分——《初民的犯罪与刑罚(II)》。换言之,1998年前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已经刊载了《犯罪习俗》的完整译本。为什么一本杂志仅仅通过33页的篇幅就能够刊登一部完整的学术著作?《犯罪习俗》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
1997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强世功等人翻译的日本著名法学家千叶正士的代表作《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以下简称为《法律多元》)。虽说此书是一部论文集,但是却贯穿了一个统一的主题。作者以非西方学者的身份自觉地从非西方立场对法律文化和法律多元进行理论建构,并且对流行的西方法理学进行批判,力图将其法律多元理论建立在本民族的经验之上,[62] [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强世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致谢和说明(梁治平)。 所以,自从被译成中文后,其思想和观点,尤其是所谓的“多元法律的三重二分法”对中国法学界一直有着较大影响。不过,学界似乎忽略了此书的法律人类学背景。按其弟子汤浅道男、小池正行、大塚滋的说法,千叶正士前半期主要是研究学区和神社祭祀,但是,“1965—1966年在霍贝尔、劳斯两教授所在的明尼苏达大学留学后,改变了方向。其问题就等于从世界看亚洲的日本,其方法被法人类学采用”。[63] [日]汤浅道男、小池正行、大塚滋:《法人类学基础》,徐晓光、周相卿译,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3页。
2003年,张冠梓在其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的论文《法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其流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近年来,无论是法哲学、法理学等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研究,都对法人类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与之不相适应的是,许多人对这门学科缺乏足够而准确的了解。”为了“向传统法学展示一个陌生的世界”,文章从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内涵、学术发展、研究特点等方面逐一进行了介绍。在关于法律人类学史的梳理中,文章不仅把此项研究向前追溯至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和以梅因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者,而且尽其所能地展示了20世纪以来法律人类学的发展脉络。除了马林诺夫斯基、霍贝尔(特别强调了《夏安人的方式》的重要意义)、博安南、波斯皮斯尔、穆尔、纳德这些前述译介作品中曾提到的人物之外,文章还列举了菲利普·格利弗(Philip Gulliver)、简·科利尔(Jane Collier)、萨莉·恩格尔·梅丽(Sally Engle Merry)、[67] 据笔者的考证,国内文献中第一次引用梅丽的作品应该是苏力于1993年发表的《法律规避与法律多元》。参见前引[59],苏力书《法律及其本土资源》,第45页。 卡罗尔·格林豪斯(Carol J.Greenhouse)等更为年轻的法律人类学家的学术观点。关于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文章介绍了法律多元主义、田野调查方法、案例研究法、跨文化的法律语言分析等特色的理论与方法。
根据西方学者西蒙(Simon,1994)的研究,增能理论的思想基础有七个方面,它们分别是:第一,新教革命;第二,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第三,杰斐逊式民主;第四,先验论;第五,乌托邦社区;第六,无政府主义;第七,泛公民权观念。[2]在综合了这七个方面的优秀思想的基础之后产生了增能理论。思想基础的兼容并蓄,使增能理论与陆九渊心学一样成为其所在时代的思想翘楚。
从理论上讲,此后的研究都应该以此为基础才能更进一步,但可惜的是,这一时期不少学者关于法律人类学的梳理都在这篇文章的叙述“范式”之中(均不及这篇文章完整)。比如,杨方泉的《法律人类学研究述评》(《学术研究》2003年第2期),[68]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尽管在发表时间上早几个月,但是在内容上完全被张冠梓的文章覆盖了。 徐亚文、孙国东的《为法治找寻沃土——法律人类学的历史、主题与启示》(《求索》2004年第3期),张永和的《法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及其他》(《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乔丽荣、仲崇建的《功能主义人类学派法律观的流变及其启示》(《理论月刊》2005年第5期)与《从博弈到认同——法人类学关于纠纷研究的旨趣、路径及其理论建构》(《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6期),吴大华的《论法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张文山的《关于法人类学若干问题的思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罗洪洋的《法人类学论纲——兼与法社会学比较》(《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董建辉、徐雅芬的《西方法律人类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常安的《试论法人类学的学科独立性问题——与法社会学相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大都千篇一律,乏善可陈,而这主要是由于参考文献高度雷同所造成的。它们主要参考的是“四大文献”:林端的《法律人类学简介》,纳德的论文集《文化和社会中的法律》(最早由梁治平引介)以及当时仅有的两部译著——《原始人的法》与《犯罪习俗》。
现阶段,慢性心力衰竭临床治疗的主要措施便是抗心衰,以此减少患者出现心血管危象的风险,提高患者的存活率。细胞生物学的快速发展,帮助人们进一步明确了慢性心力衰竭的主要诱发因素,即心肌能量代谢异常。健康人心肌代谢能量为葡萄糖、脂肪酸生物氧化产生的三磷酸腺苷,而慢性心衰患者心肌长期血氧不足,代谢较差,纠正临床症状,必须保证心肌代谢能量充足。磷酸肌酸钠经人体可以向三磷酸腺苷转化,补充患者心肌代谢能量[3]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心功能以及运动耐量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磷酸肌酸钠可以改善患者的心功能,提高患者的运动耐量,为病情抑制奠定较好的基础条件。
当然,在这一时期还是诞生了几篇可圈可点之作。也许是2002年以后法律人类学突然成为一门“显学”的缘故,受此影响,《中国社会科学》也试图“填补空白”,于2005年第5期发表了自创刊以来的第一篇关于法律人类学的论文——高丙中、章邵增的《以法律多元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在笔者看来,此文主要有三点贡献:第一,它以两千余字的篇幅着重介绍了霍贝尔的代表作《夏安人的方式》的诞生背景与学术地位,强调此书“所开创的纠纷处理的研究范式成为20世纪中期法律人类学研究的主流”;第二,它从当代法律人类学研究对象和兴趣的转移入手,首次讨论了“何谓人类学的法律研究”的判断标准,即必须基于“长期的民族志田野工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章依据西蒙·罗伯茨的观察[69] Simon Roberts,Do We Need an Anthropology of Law?RAIN,No.25,1978,pp.4- 7.中译文参见[英]西蒙·罗伯茨:《我们是否需要法律人类学?》,王伟臣译,载吴大华主编:《法律人类学论丛》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首次向国内学界展示了法律人类学的范式危机,尽管只是一笔带过,但却具有釜底抽薪的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项研究在过去的汉语文献中所展现出的“生机勃勃、意气风发”的形象。之所以能作出这些贡献,是因为此文参考了丰富的外文原始文献。就此而言,它还阐明了一个最基本的学术生产逻辑,只有基于原始文献,才可能在实质意义上推动国外社会科学的传播。
同年,赵旭东在《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西方法律人类学梳理的代表作《秩序、过程与文化——西方法律人类学的发展及其问题》。这篇文章依靠同样丰富的外文文献,试图为20世纪法律人类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寻找不同的主题——“秩序与原始法律”“规则与过程”“历史与权力”“文化、法律与现代性”,最后以“法律民族志”为题讨论了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值得一提的是,赵旭东是费孝通弟子中为数不多的专门从事法律研究的人类学家。就这一点来看,他在中国法律人类学界的角色有些类似于美国的霍贝尔。霍贝尔的导师博厄斯是美国人类学的奠基人,在博厄斯的一干弟子中,也只有霍贝尔专注于法律研究。无论是霍贝尔还是赵旭东,均在学术生涯的初期就敏锐地发现了本国人类学关于法律研究的不足。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赵旭东阅读了大量的外文原始文献,发表了近十篇(部)与法律人类学相关的研究成果。[70] 参见赵旭东:《部落社会中的政治、法律与仪式》,载《民俗研究》1999年第4期;赵旭东:《习俗、权威与纠纷解决的场域——河北一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赵旭东:《法律为何?——以文化建构反思为基础的法律人类学札记》,载《清华法律评论》2007年卷;赵旭东:《法律与文化——法律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赵旭东、何利利:《“争”出来的公正——对赣南一村落林权改革的法律人类学考察》,载《法律和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赵旭东:《启蒙、秩序与发展综合症:法律人类学的中国思考》,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赵旭东、张洁:《从异域到本土:中国法律人类学本土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载《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赵旭东:《作为文化的法律与法律人类学的问题回归》,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第一篇是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1期)的《法律人类学评介》,文章译自澳大利亚法学家马丁·克雷齐尔(Martin Krygier)所撰写的《人类学方法》,译者傅再明将题目翻译为《法律人类学评介》。这篇文章最初收录于1980年澳大利亚哲学家尤金·卡门卡(Eugene Kamenk)及其夫人爱丽丝·泰(Alice Erh-Soon Tay)合编的论文集《法律与社会控制》中。[22] Martin Krygier,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in Eugene Kamenka and Alice Erh-Soon Tayeds.,Law and Social Control:Ideas and ideologies,Edward Arnold,1980,pp.27-59. 克雷齐尔的这篇文章并非简述整个法律人类学的发展史,而只是简要地介绍了该领域关于纠纷和争议的各种理论。为此,他介绍了马林诺夫斯基、马克斯·格卢克曼(MaxGluckman)、保罗·博安南、利奥波德·波斯皮斯尔(Leopold Pospisil)、伊恩·哈姆内特(Ian Hamnett)等法律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并重点强调了《夏安人的方式》的历史地位。此外,克雷齐尔还提到了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等并未专门从事法律研究的人类学家,毕竟原文的名称“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本身强调的就是人类学的方法。换言之,克雷齐尔已经暗示了法律人类学的学科性质——人类学的一项分支研究,而并非人类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但是,不知是否是节译的缘故,这篇译文遗漏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劳拉·纳德(Laura Nader)、萨莉·福尔克·穆尔(Sally Falk Moore)为代表的第三代法律人类学家[23] 关于法律人类学家的代际划分,参见王伟臣:《法律人类学的认识论贡献》,载谢晖等主编:《民间法》(第18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413页。 的研究成果。此外,可能是因为版面,这篇译文只保留并翻译了两篇引注文献,一篇为格卢克曼的《北罗德西亚巴罗策人的司法程序》,[24] Max Gluckman,The Judicial Process among the Barotse of Northern Rhodesia,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5.克雷齐尔引用的是此书1967年第2版。 另一篇为霍贝尔的《原始人的法》。[25] E.A.Hoebel,The Law of Primitive Man:A Study in Comparative Legal Dynamic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这是《原始人的法》首次出现在汉语文献中。
2008年,明辉发表于《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4期)上的论文《穿行于法律与人类学之间——西方法律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趋势》,根据1988年在弗莱堡召开的第一届法德法律人类学研讨会的会议简报,首次向国内学界介绍了此项研究在欧陆的当代进展。此外,文章还列举了格林豪斯的《为正义而祈祷:美国市镇中的信任、秩序与共同体》、[72] Carol J.Greenhouse,Praying for Justice:Faith Order and Community in an American Town,Con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 梅丽的《获得正义与公平:美国工人阶级中的法律意识》[73] Sally Engle Merry,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以及约翰·康利(John Conley)与威廉·奥巴(William M.O’Barr)的《规则与关系:法律话语的民族志》[74] John M.Conley and William M.O’Barr,Rules versus Relationships:The Ethnography of Legal Discours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本书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语言与法律话语”系列丛书之一。康利和奥巴也是这套系列丛书的主编。中文书评请参见胡鸿保、张晓红:《语言、话语与法律人类学:从〈规则与关系——法律话语的民族志〉一书谈起》,载《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这三部关于美国本土法律制度的研究成果,从而展示了法律人类学的当代趋势,以此说明法律人类学已经不再是研究原始法律的代名词了。实际上,早在明辉的论文发表一年前,梅丽的这部作品就已经被翻译出版了。[75] [美]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郭星华、王晓蓓、王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郭星华、王晓蓓、王平三位译者将主标题“获得正义与公平”(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更名为“诉讼的话语”,理由在于,作者考察的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管辖下的塞伦和剑桥两个城镇及其初等法院的“法律话语、道德话语、治疗性话语以及三种话语的转换”。[76] 参见前引[75],梅丽书,译后记第291页。 所以,此书不仅是国内出版的第五部关于法律人类学的译著,也是继马林诺夫斯基的《犯罪习俗》之后第二部被译介到国内的、完全基于田野调查而完成的法律民族志。但是,如果翻开作者为中译本所做的“中文版序言”会发现通篇的关键词却是“法律社会学”。比如,“我认为,本书的中文译本将会对中国法社会学的发展有所贡献”,“我期望本书的翻译将会促进法社会学中比较研究和跨国研究的发展”。[77] 参见前引[75],梅丽书,中文版序言第3-5页。 但据笔者了解,梅丽曾于布兰迪斯大学获得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其在纽约大学的主要身份也是人类学教授,可是为什么梅丽要反复强调此书属于法律社会学的作品呢?是不是因为在与梅丽沟通的过程中,三位译者强调自己的法律社会学背景以及此部译著归入“法律与社会译丛”呢?[78] 需要说明的是,郭星华在2009年的一篇论文中把这本译著书归入法律人类学领域。参见张晓红、郭星华:《纠纷:从原始部落到现代都市——当代西方法律人类学视野下的纠纷研究》,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不过,从本书的原版自序中来判断,梅丽本人似乎并不在乎她的研究属于法律人类学还是法律社会学。但是这里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疑问,当法律人类学回归本土关注复杂的现代社会时,与传统的法律社会学还有什么区别?
另外,西南政法大学曾令健于2009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法人类学视野中的纠纷解决仪式》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这篇学位论文是作者于2008年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的《纠纷解决仪式的象征之维——评维克多·特纳的〈象征之林〉》的延续。象征人类学家特纳虽然身为格卢克曼的弟子,但是没有像老师一样继续借助霍贝尔发明的“纠纷案例研究法”来研究纠纷,而是去关注作为基本社会冲突(纠纷)调节手段的仪式。受此启发,曾令健尝试用“象征人类学的方法对审判仪式以及乡土社会中的纠纷解决仪式进行文化层面的阐释”。[79] 参见曾令健:《法人类学视野中的纠纷解决仪式》,西南政法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第五部分“结语:迈向象征主义的法人类学”甚至针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危机(可能作者也未能意识到)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回应。但可惜的是,作者后来并没有继续象征和仪式的研究。
2000年以后,通过近10年的“填补空白”式的传播,不仅展现了西方法律人类学的模糊轮廓,甚至揭示了法律人类学的范式危机以及回归复杂社会之后与法律社会学的重合问题。但是从整体上看,依然存在三个缺陷:首先,这段时期的译介作品鱼目混杂、良莠不齐,有着大量的重复;其次,对法律人类学历史的梳理仍停留于列举人物、作品、观点的程度,未能展示出不同学者、不同作品、不同观点之间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比如,很多文章都提到了从“规则中心”到“过程中心”的变化,但没有人分析过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再次,缺乏对某位代表学者或者某种学术观点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正如严存生在2011年解释为什么《原始人的法》能够被两个出版社三次刊印时所说的:“(法律人类学)这一学派对我国的法学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80] 参见前引[38],霍贝尔书,再版译者附言第1页。
2006年还出现了三篇专注西方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学位论文:李小妍的《霍贝尔的法人类学思想研论》、陈梦的《论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研究对法学的贡献》以及刘青山的《克里福德·格尔茨对法人类学的贡献》,这三篇论文均为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这三位硕士之所以会关注霍贝尔、马林诺夫斯基与克里福德·格尔茨,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只有这三位人类学家研究法律的著作(且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不能被归入法律人类学)被译为中文。这三篇论文与其说是关于法律人类学思想的研究,倒不如说是关于《原始人的法》《犯罪习俗》以及《地方性知识》的读书报告,对于三位人类学家研究法律的背景、动机、渊源、传承、学术地位都没有太多的涉及。更为遗憾的是,这三篇论文也未能展现出法律人类学与其导师谢晖教授所从事的民间法研究的关联。此外,还有一些似乎与“人类学”有关的法学论文,比如曹全来的《法律变革的文化阐释——人类学的法律理论》(《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和陈云生的《“宪法人类学”的创意与构想》(《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但从内容上看,他们只是借用了“人类学”的名称而已。
三、第三阶段:专题式研究
201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冠梓主编的《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此书的宗旨是:“通过甄选、介绍、评价世界学术史上的著名法律人类学家及其代表性著作,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法律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脉络,试图揭示法律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全貌,目的是为国内读者提供一本较为详尽、系统地了解国内外法律人类学的学者与著作的工具书,可望弥补目前国内缺乏相关著作的遗憾。”[81] 参见前引[46],张冠梓主编书,第428页。 所以,在挑选作品时,编者把握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共收录了30部经典著作,上至1748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下至1996年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凡是稍微涉及原始法律、法律与文化的作品都囊括在内。其实,如韦伯的《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都被列入这本选集是相当牵强的。而其中标准意义上的法律人类学作品似乎仅有马林诺夫斯基的《犯罪习俗》、霍贝尔的《原始人的法》、格卢克曼的《部落社会的政治、法律与仪式》、穆尔的《准自治领域的社会控制》、梅丽的《法律多元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部选集的甄选范围主要是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而截至2011年,被翻译成中文的法律人类学著作只有上文所提到的寥寥几部。因此,这部《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对于西方法律人类学史上绝大多数经典作品都没有涉及。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张冠梓于第二年推出了姊妹篇:《多向度的法:与当代法律人类学家对话》(以下简称为《多向度的法》)。如果说前一部作品基本上是本土化的,那么这部作品则完全是国际化的。此书主要是由编者在“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赴美访学期间采访一些著名法律人类学家的稿件组成的,另有少量稿件则系学友帮助”。[82] 参见张冠梓主编:《多向度的法——与当代法律人类学家对话》,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87页。 他们共采访了16位学者,其中除了瞿同祖、千叶正士等6位中日学者之外,其余10位都是欧美学界著名的法律人类学家,包括与格卢克曼、博安南齐名的第二代法律人类学家——波斯皮斯尔(受访时85岁,下同),第三代法律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学界双姝——穆尔(84岁)与纳德(78岁),第四代法律人类学家的中坚力量——劳伦斯·罗森(Lawrence Rosen)(67岁)、梅丽(64岁)、约翰·科马罗夫(Johan Comaroff)(63岁)与简·科马罗夫(Jean Comaroff)夫妇(62岁)、安妮·格蕾菲斯(Anne Griffiths)(55岁),第五代法律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万安黎(Annelise Riles)(42岁)以及曾担任法律人类学国际协会“法律多元研究会”主席的德国法律人类学家弗朗兹·冯·本达-贝克曼(Franz von Benda-Beckmann)(67岁)。如果把他们的学术作品、研究旨趣以及理论观点按照年龄进行排列,基本上可以呈现出自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法律人类学的发展路径。此外,和以往的译介作品不同的是,《多向度的法》采用对话的方式,由作者先提问题,然后分别给出答案。尽管这种方式可能没有达到中西方法律人类学对话的程度,但是对于中国学界深入了解法律人类学家研究问题的渊源以及他们的学术生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这种提问的方式巧妙地“引导”国外的法律人类学家围绕各自的研究和观点在同一逻辑层面进行阐述,胜似一次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83] 参见侯波波:《提供多元视角的法律人类学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7日。 此书的封底介绍中提到:“究竟何为法律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主要关注点是什么,方法上有何独到之处,最新研究进展又怎样,等等,迄今为止国内学界的介绍和研究或略显陈旧,或语焉不详,或支离破碎。”笔者认为,针对这些问题,此书给出了截至彼时最为深刻的回答。
就在此书出版的同时,三部法律人类学的译著相继问世。第一部是由彭艳崇翻译的劳伦斯·罗森的著述《法律与文化:一位法律人类学的邀请》(以下简称为《法律与文化》)。作为第四代法律人类学家,罗森在芝加哥大学读博期间深受格尔茨的影响,所以这部作品是为了展示“法律是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文化同样是法律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二者都形成了我们在普通原理基础上认识世界的范畴”。[84] 前引[82],张冠梓主编书,第322页。 罗森曾长期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研究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和伊斯兰法,曾出版过《现实的交易:穆斯林共同体社会关系的构建》、[85] Lawrence Rosen,Bargaining for Reality: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a Muslim Communi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司法人类学:穆斯林社会中作为文化的法律》、[86] Lawrence Rosen,The Anthropology of Justice:Law as Culture in Islamic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伊斯兰教的正义观:以伊斯兰法和社会为比较视野》[87] Lawrence Rosen,The Justice of Islam: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Islamic Law and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等(法律)民族志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讲,《法律与文化》之于罗森似乎相当于《原始人的法》之于霍贝尔,是一部功成名就之后的总结和反思之作。
第二部是由沈伟、张铮翻译的西蒙·罗伯茨的著述《秩序与争议——法律人类学导论》(以下简称为《秩序与争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同《法律与文化》一样,此书也不属于(法律)民族志,而是根据二手民族志材料所进行的理论分析,非常类似于《原始人的法》的创作模式。但是和前述霍贝尔、罗森不同,罗伯茨写作此书时年仅37岁,为何还不到40岁就开始反思和总结?笔者发现,罗伯茨写作此书的目的并非在于反思和总结,而是为他与约翰·科马罗夫合作的《规则和过程:非洲语境下纠纷的文化逻辑》[88] John L.Comaroff and Simon Roberts,Rules and Processes:The Cultural Logic of Dispute in an African contex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撰写一份详细的学术综述。所以,《秩序与争议》的最后一章并没有像《原始人的法》一样提出法律发展的历史规律,而是代之以学术综述——“文献中的主要理论和研究兴趣”。在笔者看来,罗伯茨对于法律人类学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最早对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的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第三部是由江照信等人翻译的万安黎的著述《担保论——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法律推理》(以下简称为《担保论》)。这本译著对于中国法律人类学的意义,可能远远超过了作者和译者的预料与想象。在此书被译介到国内之前,由于国内仅有《原始人的法》等少数译著,以致法律人类学被当成了关于原始法律、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专门研究。但是殊不知,早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就开始从非西方的简单社会转移至西方的复杂社会了。21世纪以后,法律人类学渐趋与政治人类学、法律社会学相融合,开始关注人权、知识产权等领域。而万安黎作为新一代法律人类学的旗手,更是将研究视野扩展至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掉期交易。所以,把此书同《原始人的法》一道归为法律人类学的著作显得颇为突兀。但这的确“是一本运用民族志学的方法研究金融体制和市场的法律著作”。[89] [美]万安黎:《担保论: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法律推理》,江照信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译后记(於兴中),第285页。 当然,如果从西方的学术语境来分析,《担保论》的意义在于,尝试摆脱法学的研究方法,彻底告别了法律人类学曾赖以为生的“纠纷研究”,为解决20世纪末困扰法律人类学研究的范式危机提供了绝佳范例。不过,这一点对中国学界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在过去的译介作品中几乎没有提到过范式危机的问题。
除了上述选集、译著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关于某位法律人类学家或者某个事件、学说的专门研究。2011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婉琳的专著《社会变迁中的法律——穆尔法人类学思想研究》。按照序言的说法,作者之所以选择穆尔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是随意之举。在其读博期间所修读的“法律人类学课程中,穆尔的三篇文章被指定为必须阅读的材料,同时,在课堂讨论中,穆尔的‘半自治社会领域理论’往往是同学们关注的理论热点”。[90] 参见李婉琳:《社会变迁中的法律——穆尔法人类学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张晓辉),第2页。 从年龄上讲,穆尔只比博安南小4岁,比波斯皮斯尔小1岁,但是在法律人类学的学术谱系却被归入前两者的晚辈,主要是因为穆尔早年并没有从事学术研究,39岁才在大学谋得一份助教的工作,后来因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论文才引起了比她小6岁的纳德的关注,并在后者的帮助下进入了当时由霍贝尔、格卢克曼、博安南等人所组成的法律人类学的“学术圈”。而后,40岁的穆尔厚积薄发,逐渐成为与纳德并肩的一代巨匠。当今在世的法律人类学家当中,除了纳德以外,应该没有人比浸淫欧美学界半个多世纪的穆尔更了解人类学的法律研究了。所以从知识传播的角度,以穆尔作为研究对象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伟臣的专著《法律人类学的困境——格卢克曼与博安南之争》。这本书的选题受到林端的启发,试图通过200余篇(部)英文文献的梳理,探寻这场争论的真相。全书共分为五章,其中前三章是按照事件的发生顺序对争论起因、经过、结束整个过程的梳理。第四章对这场争论的分歧进行剖析,将其剥离为三重困境:认识论困境,即怎样理解他者的法律;方法论困境,即怎样表达他者的法律;学科身份困境,即法律人类学究竟是交叉学科还是人类学的分支研究。第五章“结论”认为,这场争论通过对非西方法律的研究和讨论,实现了对西方自身法律的反思,打破了西方法律的高等性。虽然受到了法学的严重阻挠,但法律人类学为我们理解法律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其实,在这场法律人类学争论之外,还有其母学科——文化人类学的阐释学的“主位”和解释性的“客位”的争论,即人类学关于自己究竟属于人文学科还是自然学科的争论,而在这背后还有着20世纪中叶整个西方社会科学从实证主义到诠释学的知识论方式的过渡。所以在梳理的过程中,因能力所限,作者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2017年前后,关于格卢克曼的研究也实现了突破。刘顺峰在《民族研究》上连续发表了两篇专题论文,即《从社会情境分析到扩展案例分析——格拉克曼法律人类学方法论思想研究》(2016年第1期)与《法律人类学知识传统的建构——格拉克曼对法律概念与术语本体论问题的探究》(2017年第1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秋俊的专著《格拉克曼法律人类学思想研究》(格拉克曼即格卢克曼,译法不同而已)。格卢克曼是法律人类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巨擘,他不仅完善了霍贝尔和卢埃林发明的纠纷案例研究方法,而且还进一步发展成为“延伸个案研究法”。[91] 参见前引[15],王伟臣文。 格卢克曼与博安南的争论尽管被不少学者批评为“毫无必要又耗费精力的争论”,[92] 前引[69],Simon Roberts文,第4页。 但实际上却证明了法律人类学无法解决自我表述的问题,从而促成了此项研究由规则中心范式向过程主义范式的转移。这些观点和影响对于当下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93] 参见刘顺峰:《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法律人类学对中国法学的知识贡献》,载《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王秋俊:《格拉克曼法律人类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136页。
法拉利812 Superfast凭借着其明显的功率优势成为了六辆跑车中的性能怪兽。这是一辆集狂野与沉稳气质于一身的跑车,美中不足的是,座椅加热并没有在配置列表上出现。除此之外,如果再配上座椅通风功能,如果座椅能再柔软些,如果能再增加座椅电动调节的选项,那就再好不过了。
从整体上看,2010年以后,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互联网文献库的普及导致外文文献获取难度大幅度降低,前沿、专题研究日渐成为主流。这些作品的出现提升了学术期刊的审稿、发表要求,类似于十几年前的《法律人类学简介》的论文已经越来越少了。而“崭新的、直观可感的、系统真实的法律人类学”[94] 参见前引[82],张冠梓主编书,第322页。 的传播似乎才刚刚开始。
与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相比,法律人类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分析这些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中国法律人类学诞生和成长的历史进程,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法律人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对中国法学的影响。
四、传播的特点与影响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equation of the actuator is
在笔者看来,法律人类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主要有五个特点。第一,从空间上看,主要以北京和云贵两个地区为中心。北京主要指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两家单位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以及更为优质的学术资源;云贵主要指云南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等科研、出版机构,这与民族法学在中国的地理分布是吻合的。第二,从体系上看,缺乏规划性,传播的偶然性强。基本属于个体、自发型的传播,没有呈现出体系的特征,至今未出现成套的译丛或论丛。据了解,2011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曾推出“法律人类学译丛”计划,但是目前没有看到成果。第三,从数量上看,规模有限,未成气候。按照上文的梳理,法律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方式):译著、专著(专题研究)和论文。其中,译著仅有8部,数量之少以致《原始人的法》竟然被两个出版社重印了3遍,而(法律)民族志的作品仅有3部;专著仅有3部,且均为2010年以后出版;论文虽有100余篇,但仅及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的十分之一。第四,从论文的平台上看,主要以民族学类、综合社科类的刊物为主,法学类期刊不多,法学核心类期刊更少。从上文可以看出,仅有《法学家》《法商研究》《比较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等刊物曾参与传播,而民族学的权威期刊《民族研究》近2年来却刊登了3篇法律人类学的译介作品,由此说明,目前人类学界、民族学界更认可此项研究。第五,从人员上看,专职人员极少。很多人曾积极地参与传播,但此后再无后续成果。从事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较少,而持续从事法律人类学传播、译介工作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仅有张冠梓、赵旭东、王伟臣、刘顺峰等人。
传播的特点决定了传播的影响。虽然法律人类学曾与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一同进入中国,但是在影响力上较后两者差距甚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西方法律人类学的概念、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经典作品仍不甚了解。[95] 比如,邵六益在《法商研究》(2015年第2期)上发表的《社科法学的知识反思——以研究方法为核心》一文中提到:“无论是法律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学术化,法律人类学对人的知识的研究,还是法律经济学选取要素后的建模。”这里“对人的知识的研究”显然是对于法律人类学望文生义的理解,因为理论上看,一切学问都是“对人的知识的研究”。 首先,对英美法律人类学不了解。法律人类学的历史远超法律经济学,如果追溯到梅因时期,它比法律社会学也要悠久,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关于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古老”的一门学问,但是我们直到不久以前都仍然以为它是一门“崭新的交叉学科”。值得讽刺的是,这门“崭新的交叉学科”在20世纪末甚至遭遇了范式危机,险遭灭顶之灾。由于传播的偶然性,《原始人的法》这部过时的作品长期被冠之以“法律人类学经典名著”的头衔,导致学界普遍认为法律人类学就是研究原始社会、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代名词(但是又没有发生互动)。张冠梓在采访穆尔时曾表示:“她在法律人类学领域、在中国国内实在是一位大家都熟知的学者。”[96] 参见前引[82],张冠梓主编书,第167页。 但就是这样,穆尔还没有一部著作被译成中文。[97] 据悉,侯猛正在组织翻译穆尔主编的名作《法律与人类学:选读》。Sally Falk Moore,Law and Anthropology:A Reader,Wiley-Blackwell,2004. 除了一篇译文外,[98] [美]马克·古德尔:《法律中的生命:劳拉·纳德和法律人类学的未来》,王伟臣、周晓程译,载吴大华主编:《法律人类学论丛》(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55-465页。 纳德也没有任何作品被译成中文。再比如,不少汉语文章认为,法律人类学擅长法律多元研究或者鼓励多元纠纷解决机制(ADR),但其实法律人类学和这些学说、制度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比如,罗森就曾批评法律多元这个概念没有什么理论意义,[99] 参见前引[82],张冠梓主编书,第322页。 而纳德自始至终都在反对ADR,认为其是“借由人治而逃避根本问题”,[100] 参见前引[98],古德尔书,第463页。 所以,她呼吁还是应当由国家司法机关按照法律来审理。其次,除了徐晓光关于日本法律人类学、王伟臣关于荷兰法律人类学的介绍之外,目前国内对于英美之外法律人类学的了解更是一片空白。
第二,法律人类学对中国本土的法律实证研究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由于传播所限,西方法律人类学理论与中国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民间法研究未能产生对话。但有趣的是,由于不甚了解,反而促成了法律人类学的神秘化、时髦化。如今很多的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或是乡村法律实践的研究,都会加上一个副标题,比如“关于某某的法人类学考察”或者“以法律人类学为视角”,仿佛加上了“法律人类学”这五个字就是使用了不同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真正的法律人类学研究至少要经历一年的田野调查,这是一种成本极高的知识生产方式。除了朱晓阳等少数学者外,[101] 朱晓阳:《小村故事:罪过与惩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很少有人会使用人类学的方法——田野调查——进行法律研究,更不要说以中国的本土实践回应西方的理论方法了。
学生成绩考核评价是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课程考核要以过程性考核为主,重在考查学生在工作任务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教师要面向学生对课程主要项目开展实际操作、口头描述等形式,增加对学生完成项目的过程和结果的评价。过程性考核在总成绩中所占比例为70%。过程性考核包括学生完成项目的结果和质量、出勤情况以及在完成项目中体现出来的职业道德、思想品德水平、团队协作精神。
In Purang, heavy rain and hail often occurs in summer and autumn, then cause flood and mud-rock flow. Consequently, fields are covered, crops are washed away,ditches are blocked, and roads and bridges are destroyed.
第三,法律人类学对中国法学的影响很小,但是格尔茨的象征人类学对中国法学的影响却很大。如上文所述,格尔茨并没有专门从事法律研究,据其学生罗森的回忆,格尔茨“对法律没有特别的兴趣”。[102] 参见前引[82],张冠梓主编书,第315页。 格尔茨也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法律人类学家:“这样一种研究进路,不是法律的人类学家或法律人类学家的方法,而是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103] 参见前引[55],吉尔茨文,第89页。 尽管如此,20多年来,格尔茨在中国一直备受推崇,影响了梁治平、苏力、朱晓阳等一批学者。
侯猛曾分析过法学与人类学对话的困难,认为“法学与人类学光有形式上的对话是不够的,那只是各说各话,而真正的沟通和对话是知识上的合作”。[104] 朱晓阳、侯猛编著:《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页。 而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法学对于西方法学比较了解,相对而言,中国人类学对于西方法律人类学却不够了解。中国学术界似乎并没有接受西方法律人类学,所以也就很难产生中国法律人类学的自觉。
围绕型号产品的数字样机开展工作,不但要进行设计模拟装配,还要进行装配工艺仿真和工艺验证,利用虚拟装配技术暴露和解决在产品设计以及后续产品生产、装配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各方面的问题。
五、结语:超越边缘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曾敞开怀抱欢迎各类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但是在与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法律认知科学的竞争中,法律人类学最终败下阵来,根本原因在于,在西方的战场上,法律人类学也没有胜利过。
对于法律问题的研究而言,人类学其实并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使用的都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法学的研究方法。20世纪中叶,法律人类学出现了第一次研究高潮,霍贝尔、格卢克曼、博安南等代表学者的作品所使用的研究模型其实都是所谓的“个案(纠纷/冲突)研究”,它来自美国法学院的“案例研究法”。后来出现的“延伸个案”延伸的依然是冲突和纠纷。按照本达·贝克曼的观察,经典时代的法律人类学变成了对纠纷的专门研究。[105] Franz von Benda-Beckmann,Riding or Killing the Centaur?Reflections on the Identities of Legal Anthrop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in Context,Vol.4,No.2,2008,p.208. 难道只有纠纷和冲突才是法律问题吗?法律人类学长期受困于此。在母学科——文化人类学看来,法律人类学使用法学方法,并无甚新意。在法学看来,法律人类学研究“原始法律”,也没有特别之处。后来法律人类学回归本土,提出法律多元理论,大批法学研究者纷纷进入非国家法领域,所以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法律多元研究“确定无疑是法学界所创造的产物”。[106] Simon Roberts,Against Legal Pluralism:Some Reflect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Enlargement of the Legal Domain,42 J.Legal Pluralism&Unofficial L.95,1998,p.97.关于对法律多元中的人类学与法学的关系之评价,参见Francis G.Snyder,Anthropology,Dispute Processes and Law:A Critical Introduction,British Journal of Law&Society,Vol.8,1981,p.157;前 引 [45],Chris Fuller文,第10页;Sally Engle Merry,Anthropology,Law,and Transnational Process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1,1992,pp.357-379. 因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英国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的这一分支领域似乎已经失去兴趣了”。[107] 前引[69],Simon Roberts文,第4页。 虽然近年来法律人类学通过对各个部门法领域的渗透,正处于复兴之中,但是从整体上看,其不仅难以和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相提并论,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内也依附于政治人类学,在西方就是一门“不太成功”的边缘学科,进入中国也就难以避免地继续被边缘化了。
不过,边缘化的法律人类学依然有着可供借鉴之处,比如,“进入隐秘与获得整体”[108] 参见王启梁:《进入隐秘与获得整体:法律人类学的认识论》,载《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的研究视野,成本极高但却经常会有意外收获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法律人类学“不太成功”,并不代表人类学没有能力涉足法律领域,诸如象征、符号、仪式、结构主义等理论学说都可以用于法律研究,就好像格尔茨不是法律人类学家,不代表他的学说对于法律研究没有启发价值。恰好相反,几部影响极大的作品,如梁治平的《法律的文化解释》、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以及朱晓阳的《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都是受到了格尔茨阐释人类学的启发。为什么三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格尔茨那里汲取养料?在笔者看来,格尔茨是不是法律人类学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学界需要更全面、更深入系统地接受人类学的知识。诚如尤陈俊所言:“我觉得诸如对法律人类学学科问题进行出色梳理的高质量论文,在今天的中国法学界不是过剩,而恰恰是太为稀缺。”[109] 尤陈俊:《困境及其超越: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的法律人类学》,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1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 11年过去了,这番话依然振聋发聩。
Abstract:Legal anthropology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social studies of law including such tradi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s legal sociology and legal economics, but why does it appear to be an emerging research area in China?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try to review in this paper the process in which legal anthropology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spread in China. After the incep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ompted by the second wave of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legal academics in China began to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legal anthropology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ough it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was fragmented at that time.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several complete translated works in China since 1997, legal anthropology, which had appeared to be mysterious before, has eventually begun to attract wide scholarly attention, hence a surge of publications claimed to report so-called gap-filling researches. After 2010, due to the increased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wide availability of online database of academic literature which has made it much easier to get access to foreign research information, cutting-edge research on special issues is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Though entering China at the same time, legal anthropology cannot compare in influence with legal sociology and legal economic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legal anthropology is marginalized and it inevitably continues to be so treated in China.
Key words:legal anthropology;Hoebel;anthropology;legal sociology;translation&transmission
*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学科编辑:肖 威 责任编辑:刘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