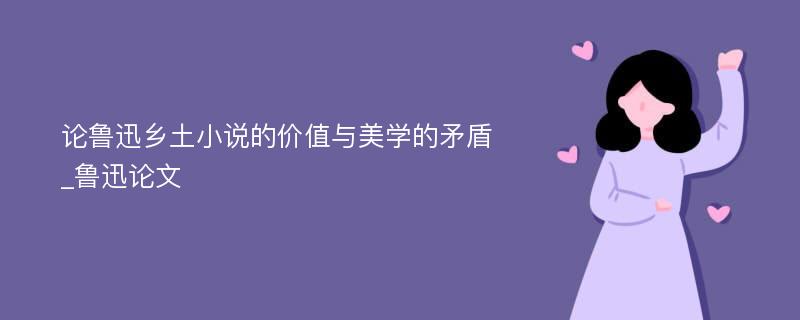
浅论鲁迅乡土小说中价值与审美的悖反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乡土论文,现象论文,价值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其实,在探究鲁迅思想时,如果离开了他对乡土中国的本质认识,就不能更好地解读他的小说;而如果不把他的小说首先作为乡土小说来读解,我们就不能理解鲁迅对乡土中国的深切认识。鲁迅乡土小说的意义是多重的,仅就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而言,鲁迅开创的现代乡土小说模式,是“五四”乡土小说及其后的重要乡土小说作家和流派的被模仿式;鲁迅开掘的现代乡土小说母题是可不断播撒拓展但难以超越的母题。 鲁迅之所以用“乡土”作为“载体”,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一个现代智识者充满着矛盾的思想与情感在特定文学形态上的反映。鲁迅既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五四”先驱者,同时又是与中国农民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地之子”,在直面乡土中国时,他的现代理性精神与关涉传统的文化感情始终处在难以弥合的紧张之中。一方面,那种改造农业社会国民劣根性的使命感迫使他从一个更高的哲学文化层次上来审视他笔下的芸芸众生,用冷峻尖刻的解剖刀去杀戮那一个个腐朽的魂灵,从而剥开封建文化那层迷人的面纱;另一方面,那种哀怜同情农民的大慈大悲的儒者之心又以一种传统的情感方式隐隐表现在他的乡土小说之中,其“深刻的眷恋”在表现出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精神时,又制约着对封建王权和奴性教育的统治思想更有力的批判。鲁迅对封建文化思想最猛烈的批判,根植于中西文化对照下的价值取向;对被损害者(亦即鲁迅“童年记忆”中的“乡土人”)倾注的怀旧式的同情,则是中国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根由所在,也与中国农业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暗通关系。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虽然有时能够成为有机的整体(也就是人们所一直强调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主题内涵),但更多的是两者冲突下形成的悖论。这使鲁迅的乡土小说呈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虽然不完全排斥情感内容但更具有积极主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理性之光的形上之作;其二是以《故乡》、《祝福》为代表的虽然不缺乏理性的烛光但更显消极被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情感形式的形下之作。 鲁迅是站在“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来书写乡土的,其全部乡土小说都渗透着对“乡土人”那种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变革的精神状态的真诚而强烈的痛心和批判态度。他笔下的“乡土人”,虽然大都出自“鲁镇”、“未庄”等乡野村镇,但其精神特征的普遍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其普遍性的获得,根源于鲁迅独有的文化气质与思想视域。李长之认为:“鲁迅不宜于写都市生活,他那性格上的坚韧,固执,多疑,文笔的凝练,老辣,简峭,都似乎更宜于写农村。写农村,恰恰发挥了他那常觉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凉,不特会感染了他自己,也感染了所有的读者。同时他自己的倔强、高傲,在愚蠢、卑怯的农民性之对照中,也无疑给人们以兴奋与鼓舞。”①李长之强调鲁迅的个性气质与其乡土小说创作之间的适宜性,并特别指出鲁迅与其笔下的“乡土人”在文化性格上的级差与悖反所带来的审美冲击力。李长之将鲁迅置于“农民”之上,使其居于“俯视”的位置。与之不同,周立波突出鲁迅的启蒙批判立场,他说:“鲁迅是直觉地感到了,半殖民地国家的国民性,带着浓厚的农民色彩,要雕塑我们民族的典型,农民气质,是他不可分离的部分。”②不论是李长之还是周立波,他们各自都看到了鲁迅极为重要的一面。正是切近鲁迅自身文化气质的启蒙诉求,使他的文化批判闪烁出具有穿透力的理性光芒。《阿Q正传》能够成为千古绝唱,正是鲁迅理性之光闪射得最清晰之时。他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冷峻地剖析一个中国人生命冲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的根源,从而从哲学的意义上来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做出全方位的价值判断。那种尖刻犀利的反讽,撕开了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最深层的幕纱,成为窥探几千年中国人心理的窗口。它不仅是鲁迅的具有积极主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理性之光的形上之作的代表作,而且也是本世纪最有思想深度的小说。 以《故乡》、《祝福》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虽然也有鲁迅无处不在的理性之光的烛照,但它们更其突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批判意识的复杂的文化情感。像《故乡》这样的乡土小说,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乡土小说,它更多的是流露出对闰土式农民自上而下的人道主义同情,它是在两个人物——闰土和杨二嫂的对比下(即农和商的比照下)完成对“地之子”哀怜的母题的。显然,那种传统的“重义轻利”的农业社会观念是制约知识分子审视社会的障碍,对“豆腐西施”杨二嫂的鄙视恰恰表现了作者对土地(这个“土地”是一个大的哲学文化范畴)的深刻眷恋。因此,与《阿Q正传》相比,《故乡》留下的仅仅是知识分子共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烛照,它的普泛意义并没有超越古典文人的“意境”追求。《祝福》也是在这一视域下描写人物的,它通过祥林嫂的一生遭际来完成对社会的抨击,但它的主题视阈仍未脱离那种自上而下的人道主义精神眼光。当然,这并非是说,这些作品就没有对封建文化进行猛烈的攻击,尤其是《祝福》,它是间接地对封建文化的四大绳索提出了更深的思考,但是比起《阿Q正传》来,这些作品则不能进行划时代的超越,直接进入更高层次的文化批判。《社戏》同样流露出深深的“乡恋”情感和怀乡意识,虽然这种美好的情感已被现实生活的黑暗所粉碎,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作家试图在自己心灵中所留下的那块情感的“净土”,那种没有等级的社会秩序,那种纯朴平和温馨的人际关系几近成为鲁迅的“童话世界”,这种美化带有充分的童贞浪漫色彩,虽为理想,但多少体现出鲁迅在“乡恋”之情中所表现出的对传统文化的不由自主的流连。然而,正是由于情感与理性冲突所造成的悖论,使《故乡》、《社戏》一类的小说未能达到《阿Q正传》的思想力度,其批判锋芒之削弱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的乡土小说作家之所以不能与鲁迅同日而语,也正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只能囿于《故乡》、《祝福》式的内涵表现,而达不到《阿Q正传》那样的思想力度。然而,决不能简单贬抑这种情感。如此复杂的文化情感,显然不止是鲁迅一个人的,而是他那一代人所共有的。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所举起的反封建大旗是指导新文学运动奋勇向前的一个目标和宗旨,它无疑拉开了中国新文化的序幕,开创了新的纪元,但倘若看不到这种每个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于每个中国人所存在着的隐性文化情感,也就不能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有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每个人都能在两种文化情感的包围中挣脱出来,遴选出最优的文化情感规范,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是一蹴而就了吗? 上述鲁迅乡土小说的两种形态,是从其理性精神与文化情感的偏向性而言的。当理性大于情感时,作者所呈现出的是那种对王权意识统治下的国民劣根性与农民式的奴性的毫不留情的积极抨击与尖刻嘲讽;然而当情感大于理性之时,那种“地之子”的乡愁以人道主义的情感方式悄悄冲淡了批判的锋芒而趋向于消极的悲悯。“疗救”的“呐喊”往往从激越慷慨的情调而滑向低回缠绵的哀婉音符。这就是说,不论哪一种形态,理性精神与文化情感都同时存在,它们在鲁迅意识结构中的碰撞与整合,使得鲁迅的乡土叙事鲜明地呈现出双声对话结构,即一种声音言说的是启蒙话语,另一种声音言说的是个人话语。这种双声对话结构存在于鲁迅的所有乡土小说中。显然,这种双声对话结构是就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和隐含作者的意识结构而言的,因而还不是鲁迅乡土小说内在精神结构的整体。全面考察鲁迅乡土小说的内在精神结构,尤其不能忽略“乡土人”的存在。鲁迅曾言,他从事文学活动的主旨就是要揭示“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③。但是,实际上鲁迅乡土小说的艺术世界本身却显示出了比这种理性表述复杂得多的内涵。在鲁迅乡土小说的文本内部,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与“堕落的上流社会”和“不幸的下层社会”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现实社会关系和精神情感关系。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就其与“上流社会”的关系而言,既厕身于其中,同时又是其叛逆者和批判者;就其与“下层社会”的关系而言,始终处在既趋近又逃避,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的尴尬状态。而处于社会下层的“乡土人”,他们也有自己合理的生活欲求,有自己的精神需要,有自己的心理现实和生存现实,他们既有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使他们很难接纳知识分子主人公和隐含作者所信奉和追求的那一套从西方“盗火”来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在后者感到前者“愚昧”、“麻木”、“冷漠”、“不觉悟”的同时,前者也感到后者对自己的真正需要的“无知”、“冷淡”、“隔膜”乃至“逃避”。因此,鲁迅乡土小说中的“乡土人”,就如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地位,拥有他们具有作为一个人所应该拥有的种种相对独立的感受、情感、心理及思维活动。虽然更多地处在沉默之中,但他们对现代智识者的反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现代智识者及其所认同的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内在蕴涵的批判。巴赫金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时说:“作者的观点、思想,在作品中不应该承担全面阐发所描绘世界的功能,它应该化为一个人的形象进入作品,作为众多其它意向中的一个意向,众多他人议论中的一种议论。”④在鲁迅的乡土叙事中,作为现代智识者的隐含作者,其思想、观点对于获得了独立地位的“乡土人”来说,就是一种“听不懂”的异质的“他人议论”,双方因此处在“自说自话”的“复调”状态之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乡土人”虽然与“上流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抹杀的阶级冲突,但并不构成鲁迅乡土叙事的主导面,架构起叙事空间的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正是鲁迅作为一个以文化批判与思想革命为己任的现代知识分子型作家所必然要做出的叙事选择。 “双声对话”透露的是自身的理性精神与文化情感之间的分裂与冲突,“复调”则已凸现出作为现代智识者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仅是“余”在上下社会阶层“两间”的“一卒”的尴尬的文化困境。这是现代智识者对自身文化处境的痛苦发现。而这种发现又加深了对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统治而造成的历史文化积淀的认识。当他清晰而透彻地审视这满目疮痍的古老精神文化世界时,无疑是带着万分的惊异和悲哀苍凉的情感来咀嚼人生的痛苦的。正因为鲁迅更深切的体味了封建文化精神对人的戕害——这种戕害足以造成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自戕力和自虐性,所以他的小说,尤其是乡土小说更具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然而,这种悲剧意识并不囿于古典的悲剧精神特征,它更具一种现代悲剧精神特征。 鲁迅的乡土小说是以内容的深广而闻名于世的,就其悲剧形态特征来说,受尼采的悲剧影响甚大,而且也很难以一种固定的悲剧模式来概括之。或许像《狂人日记》这样的象征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更多的是以狂放的酒神精神和佯谬的写作方法来宣泄作者胸中对封建礼教戕害人性、扼杀情感的忧愤之情。在几千年淤积的浓重封建雾霭下,鲁迅作为一名反封建的战士和先驱者,他要尽情地宣泄胸中郁积的块垒,一种狷狂的活泼之心激励着他勇猛地掀开那黑暗的铁屋子,放纵的情绪像决堤的洪水汹涌澎湃;而作者又不得不顾及到在这黑沉沉的大地上,作为一个清醒者的呐喊却不会被更多的蒙昧者所接受,鉴于封建氛围的压迫之甚,他又不得不采用将主人公打扮成病态的“狂人”,以“佯谬”的非逻辑方式来阐释深刻的主题和宣泄忧愤的情感。 不同的主题表现在鲁迅的笔下呈现出不同的悲剧观,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故乡》和《社戏》是两篇不同悲剧内涵的作品,前者表现出的是更接近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情绪,兵匪官绅的多重压迫,层层的盘剥非但使闰土式的农民没有痛不欲生的感受,而是使他们更加蒙昧麻木,作为人的堕落,精神的毁灭,其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鲁迅欲哭无声,欲罢不能,又找不到可以解脱的人生之路,高声呐喊也无济于事,《故乡》的色调因此是阴晦的,格调也因此是低沉的。在寻觅三十年前那英俊少年的面影而不得时,鲁迅那种“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壁障”的悲观情绪攫取了一颗寻找梦幻世界的心。倘使仅仅局限于反封建和阶级对立的主题发掘,而忽视了鲁迅那颗彻底悲哀的大心,那已凉透的心境,则是很难体味到这篇作品更深的艺术情感的。《祝福》、《离婚》等作品都是作者“苦闷的象征”,倘若硬以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去分析这类作品,则是很牵强的。显露在这类作品中的更多的是悲观主义色彩,在这样的作品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一位伟大先觉者的孤独感,真正理解“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空寂、阴冷、孤独、悲凉、忧愤和比死亡还要恐惧比恐惧还要动人心魄的悲剧情绪。相反,像《社戏》这样的作品则是一幅充满着日神精神的美丽图景,一切美丽和谐,平静而充满着温馨的画面,以及人类的真善美情感的显现,充分地表现出作者试图摆脱现世痛苦的悲剧心理,这种仅存于鲁迅作品中的艺术描写的逆反现象,正是鲁迅对于另一种悲剧心理经验的尝试。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言:“他主张面对梦幻世界而获得心灵恬静的精神状态,这梦幻世界乃是专为摆脱变化不定的生存设计出来的美丽形象的世界”⑤。这种“净化”的处理是抛弃了原始的艺术处理,它一方面意味着作者的思想呈起伏状态;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作者悲剧美学观念的变幻。 毫无疑问,在鲁迅乡土小说乃至所有鲁迅作品中,最能打动人的作品还是鲁迅糅合了两种悲剧精神的《阿Q正传》这部传世之作。鲁迅赋予阿Q这一形象的悲剧内涵完全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的,这就使小说具有“佯谬”、“反讽”、“调侃”的意味。一方面,阿Q的那种流氓无产者的狂放性格,那种具有原始倾向的性欲需求和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本能,被封建秩序的格局所压抑;另一方面,他又以一个病态的形象出现,时时超越封建秩序的约束而做出出格的事情来,这就构成了人物的双重悲剧因素。然而,从作者的悲剧视角来看,一方面,作者试图创造一幅“人类的虚妄、命运的机诈,甚至全部的人间喜剧,都像五光十色的迷人的图画”,通过人物表象世界的虚拟性创造,来达到摆脱现实生存变幻的痛苦。这种典型的日神精神支配着人物,也支配着作者走向悲剧艺术的升华。但不能忽略的是,作者在作品描写的表象背后又时时地隐伏着一种无可名状的酒神精神,使其有一种形而上深度的悲剧情绪。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这作为一个审美判断,鲁迅所赋予的内涵与尼采的相同之处,就在于“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也正是酒神精神的要义。”⑥鲁迅在创造阿Q这个不朽艺术形象时正是采用了与痛苦相嬉戏的酒神精神。鲁迅把这个有价值的生命痛心地粉饰成一个无价值的个体形象,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悲剧性;而全篇附于阿Q之身的“佯谬”、“调侃”笔调,正是艺术家“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和“情绪的总激发”及“情绪的总释放”⑦的酒神状态。作者试图用一种难以言喻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毁灭的情绪来阐释一种对人进行否定之否定的生命哲学批判。鲁迅的悲剧观一直是建立在对人与生命的肯定基础上的,他往往是通过否定的形式,在对人的劣根性进行扬弃的过程中来肯定人和生命之本体的。这种矛盾心理就决定了他在雕塑自己悲剧艺术形象时采用了那种“曲笔”,“曲笔”构成了小说酒神与日神精神的交融渗合。一种病态、变态的放纵意识和另一种清醒的摆脱现世痛苦的悲剧意识融合在这部小说中,成为作家主体和人物主体的有机和谐,这不能不说是小说艺术显示的难点,正是在这一点上,《阿Q正传》才更有其不同凡响的艺术造诣,才获得普遍的无愧于“世界文学艺术”称号的悲剧审美内容。 在鲁迅乡土小说的悲剧精神中,可以体会到一个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胸怀的哲人对于现世痛苦和“安命精神”的民族劣根心理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亦可看到鲁迅那种具有“超人”的悲剧精神——在咀嚼痛苦回味痛苦中把握生命把握民族把握人类的强力意志;它执著于人生,更具有酒神不回避人生痛苦的形而上的悲剧精神。站在“世界原始艺术家”的角度来反观人类的痛苦与毁灭,鲁迅的乡土小说呈现了“现实的苦难就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就化作了世界的喜剧。”⑧这种二度循环所达到的悲剧境界是对人生的最高肯定。 鲁迅具有浓郁悲剧精神的乡土小说寄寓了上述深邃的智慧和思想,其强烈的主体意识统摄笼罩着笔下的芸芸众生,使其在鸟瞰这个世界时能够高人一筹。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就在于他突破了一般作家所采用的与平民之间的等距离视角(也就是“平视视角”),而选择“超人”式的“俯视视角”。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在描述鲁迅小说时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形成了‘精神界之战士’(超人)的‘心声’直达‘朴素之民’这样一幅构图。这个‘二极结构’,在此后的鲁迅作为小说家的活动的全过程中也得到确认。现在审视一下他的全部作品,以此观点对照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我们仍可感觉到,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他的关心还是朝向同一个‘两极’”⑨。毫无疑问,鲁迅的小说是将改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大主观意念(主体意识)融化在一种古老、凝滞、僵化、悲凉的习俗和愚钝麻木灵魂的客观再现之中,使之形成一种强烈的“文化反差”,这种看似冷峻,实则炽热的内外反差情感,铸就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风范,它所包容的主客观两极,须得作者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一方面又得在具体的创作中尽力隐匿情感的外露。鲁迅的《祝福》、《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药》等传世之作,就是用“曲笔”来抒发自己那个高屋建瓴的哲学总命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倡导写实主义文学的主将鲁迅,在其自身创作中却往往没有采用纯客观的写实主义创作方法,而是汲取和杂糅了多种艺术表现方法。这就使得仅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批评框架去范围鲁迅小说创作时,难免显得尴尬和窘迫,牵强和穿凿。鲁迅的《狂人日记》绝非是现实主义的产品,他也并没想到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构架小说,而是杂以时髦的现代派创作手法,使之在对新流派的模仿中呈现出小说的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韵味。或许当时无论对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来说,中国的新小说家们是无所谓新和旧的,因为批判现实主义对他们来说,同样也是新鲜的。因此,鲁迅的第一篇乡土小说《狂人日记》充满了现代派超越时空的创作手法,但它十分完满精确地表述了作家所要进行的“呐喊”——诅咒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要求轰毁“铁屋子”的愤懑。然而,这就使得后来的许多形而上学的文学史批评家们十分难堪,他们竭力把《狂人日记》描述解释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范本,从而达到把鲁迅作为现实主义旗帜之目的。殊不知,这不仅仅是对文学史的亵渎,同时也是对鲁迅小说艺术多元性的抹杀。在《狂人日记》之后的《孔乙己》、《药》、《兄弟》、《明天》、《一件小事》、《风波》、《故乡》等作品中,虽然描写的笔法近乎于写实,但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小说淡化情节、淡化背景,突出和强化的是一种强烈的印象和意念。《阿Q正传》是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至今能够超越这部小说的尚不多见。然而,在反复品味这部小说之后,也很难用写实主义的客观描摹来解释作品。阿Q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提炼,这绝非是能用单一写实的方式方法即可抵达的,从中足可以看到那种夸张变形小说意念的透视,甚至那种荒诞意念和梦幻构织的民族病态的畸形的阴暗心理完全溢出了作为一个农民阿Q的性格内涵,小说的复义性多义性模糊性造成的阅读障碍和多解,致使它至今还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充分证明了鲁迅成为小说宗师所采取的兼容风度。很难想象,一个恪守一种创作方法的作家能够成为一流的文学大家,鲁迅创作至少在形式上超越了既定的规范,才使其内涵更深广辽远。 这种多样性的艺术探求,即使是在小说的叙事视角的选择和运用上也有所呈现。一般来说,鲁迅的乡土小说多采用现在和过去时态并存的视角,只有《社戏》是“童年视角”的再现。《故乡》、《祝福》等则是在不断的“闪回”镜头中展现人的变迁,这种交错时态似乎给现代“还乡”小说开辟了一个叙述方式(也是叙述视角)的范型。这影响了以后许多乡土小说的结构生成。当然,另一种进行时态的模式也成为鲁迅乡土小说得心应手的作法,像《药》、《阿Q正传》这样的进行时态,固然在结构艺术上显得呆板些(《药》的明暗双线结构则非视角构成因素),但它们主要是在哲学文化思想内涵上取胜,这种平实的稳态的叙述视角往往更适应小说的内容表达,尤其是漫长冷寂的中国穷乡僻壤里的“死水”般的生活,构成了小说外部形式无技巧的技巧,平实的风格正是与内容的对应。这种叙述视角所构成的乡土小说风格特征几乎成为一种不可解脱的“叙述情结”,一直延续仿照至今。本来,中国乡土小说自鲁迅始,就明显地显示出多种不同的艺术方法和艺术格调,它大大地开拓了乡土小说艺术延展的疆域。毫无疑问,鲁迅的这种大家风范影响了二三十年代的一些乡土小说的中坚作家,诸如王鲁彦、王统照这样的佼佼者。然而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近半年世纪的乡土小说史中,人们几乎放弃了表现型的艺术叙述形式,而沿着再现型的艺术叙述形式走向一个极端,导致了整个乡土小说艺术的断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寻根文学”的崛起才有所改变,应该说,“寻根文学”中表现主义艺术范式的弘扬,正是“鲁迅风”的“复归”。 作为一个乡土小说的伟大实践者,鲁迅为乡土小说提供的典范性作品不仅是深邃的哲学文化批判意识和叙述视角所形成的多元创作方法的生成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说所形成的“乡土”审美形态几乎成为以后乡土小说创作稳态的结构模式。无疑,20年代初,鲁迅和周作人在艺术主张上是很谐调的。只不过鲁迅并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对乡土文学理论进行过系统的阐释。然而他的创作正是应和了周作人“乡土艺术”的理论的。周作人在为刘大白《旧梦》作序时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而鲁迅在1934年给陈烟桥的信中也称:“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⑩正因为如此,鲁迅在创作乡土小说时就非常注意表现有个性的小说特征——地方色彩和风俗人情。这一点周作人在1923年2月的一篇《地方与文艺》的文章中就特别强调过,他认为文学的艺术生命就表现在它的三个特性中:“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11)。我以为,鲁迅的创作以此来概括则是非常合适的。正如上文所述,除了深邃的哲学文化批判意识(即对国民性的根本认识)外,就是周作人所倡导的个性,这个性也就是“五四”时期所表现的普泛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两个要素在“五四”及其后的许多作家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周作人所倡导的文学的地方性正是乡土文学的美学特征,可以说,鲁迅是第一个在自己的乡土小说中竭力表现这种美学特征的。他的小说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被溶化了的浓冽风土氛围。吴越农村的乡土气息不仅极有魅力地展示了人物的特定性格,同时给人的审美情趣也是韵味无穷的。《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祝福》等杰作中对绍兴古镇的景物、风习、摆设、服饰等的描绘不断给接受者以新奇满足的审美刺激,以致使一些评论家为之倾倒。张定璜在1925年1月的《现代评论》上著文称鲁迅的《呐喊》中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12) 总之,鲁迅的乡土小说的艺术风格之所以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作家,正是它们开创了风土人情的异域情调的疆域,赋予小说强烈的地方色彩。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下定义时认为:凡寓居他乡来回忆故乡、叙写乡愁者,无论他是用主观或者客观的方法,均可称之为乡土文学。但就他自己的乡土小说来看,使用的方法是多元的:第一,视角并不限于“回忆”;第二,表现方式是多元的;第三,风土人情和地方色彩成为固定风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小说的重要贡献多由乡土小说所体现,而乡土小说对20世纪的中国小说的贡献则在于它除了宏大的思想力度以外,就是它阈定了乡土小说以强烈的地方色彩和风土人情为这类小说根本的审美形态。 综上所述,我们在鲁迅乡土小说的创作中不难发现的是:两种文化价值在其中所形成的理念叙述的冲突,造成了作者对传统的“乡土中国”两种情感——“深刻的批判”与“深刻的眷恋”的混合;从而,也使其乡土小说创作的悲剧审美形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酒神的悲剧精神与柔美的田园牧歌相杂糅的表现形态交错出现。 注释: ①李长之:《鲁迅批判》,上海: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118页。 ②周立波:《谈阿Q》,《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278页。 ③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页。 ④[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7页。 ⑤[德]尼采:《悲剧的诞生》,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⑥周国平:《〈悲剧的诞生〉译序》,[德]尼采《悲剧的诞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⑦[德]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61页。 ⑧周国平:《〈悲剧的诞生〉译序》,[德]尼采《悲剧的诞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⑨[日]伊藤虎丸,《鲁迅早期的尼采观和明治文学》,《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⑩鲁迅:《致陈烟桥》,《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页。 (11)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龙集》(《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页。 (12)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1月。标签:鲁迅论文; 乡土小说论文; 乡土论文; 阿q正传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社戏论文; 孔乙己论文; 故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