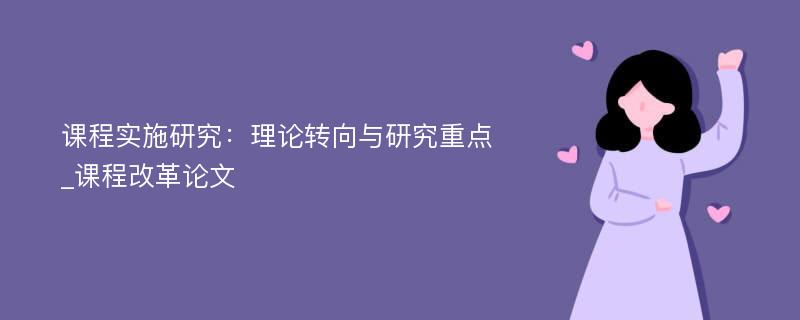
课程实施研究:理论转向与研究焦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课程论文,焦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1年至今,新课程改革已经实施了4年,从一些研究中发现,新课程的实施在取得很多成绩的同时,也遇到不少问题,我们也感受到现有的研究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关于课程实施的信息。因此本文试图从教育改革研究的理论转向入手,探讨课程实施研究在当前的焦点,以期发现对当前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有意义的启示。
一、教育改革研究的理论转向及其现实意义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教育改革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转向,就是从结构——功能观(structural-functional perspectives)向文化——个人观(cultural-individual perspectives)进行转变。[1] 当今世界上著名的课程改革研究专家,如富兰(M.Fullan)、范登堡(R.van den Berg)、哈格里乌斯(A.Hargreaves)、利思伍德(K.A.Leithwood)、霍尔(E.H.Hall)等等,大多从文化——个人观的角度来进行有关课程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结构——功能观是从组织结构和职位功能等角度来研究课程实施和领导的作用,认为人是具有理性的,能够发挥一定功能的动物,可以通过组织结构和管理使成员达成理想的表现。这种观点的核心在于相信变革和对变革的实施可以通过层级式的管理来实现,课程改革方案是否合理至为关键。因此持这种观点的研究倾向于探究课程开发方案的合理性以及控制、经济理性和权变的组织理论。时至今日,在我们的新课程改革当中,依旧可以看到这种观点的痕迹。一些专家学者相信,只要课程方案设计合理,课程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都是教师没有按照新课程的思想和策略进行教学所造成的,教师在他们眼里,是“好”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接受容器。一些教育管理者则热衷于下命令,相信学校严格的管理可以保证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
顾名思义,文化——个人的观点强调两个重点:一个是教育变革中个人的意义,包括他们的态度、信念、期望、情绪等等;一个是变革过程中以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主的组织文化对变革的影响。这种观点倾向于把教师看作是变革过程中能够自我引导的主动因素,而不是被动的受管理者,因此他们的动机和投入对于教育变革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观点也导向学校作为一个学习型组织的概念,在这种学习型组织中,教师对变革和专业学习的投入被看作是变革实施成功的关键因素。
也就是说,文化——个人观实际上是把教师看作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主动建构意义的主体。课程改革对于教师来说,不仅是一种客观事实,更重要的是,这种客观事实必须进入到教师的意义系统,成为一种主观事实,然后才能指导教师在复杂的改革环境中有所行动。
教育改革研究领域的这一转向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或者学者们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和教育改革的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回顾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其主要趋势就是越来越全面,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也越来越复杂。当前的改革趋向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革的结构—功能观对过去那种结构清晰、目标明确、构成简单的改革来讲是很有效的,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化、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等等的影响,教育改革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不确定,以至于富兰认为,混沌和复杂性成为描述教育改革的更恰当的词汇。[2] 由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没有任何改革的策略可以一成不变,也没有什么可以准确预测的结果,结构—功能观对此显然无能为力。
在这样改革的形势下,为了成功地实施这些改革,教师需要在理念和实践上发生根本的变化,教师对改革的主观意义构建因而显得十分重要。一些研究也发现,尽管教师对改革的解读与政策制订者并不一致,但是这种解读却深深地影响着教师的课程实施行为。[3] 同时,教师这种意义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支持性的文化环境。也就是说,文化——个人观对于新的教育改革可以提供有力的解释。
如果拿当今的新课程改革和以往的教学改革相比,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次改革不论是在教育理念,还是在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发生了全面的革新;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乃至文化都在向全球化、市场化迈进,知识经济也在社会发展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复杂的、规模宏大的改革和社会的变化使学校和教师面临着更富有挑战性也因而充满了机遇的教育情境。课程改革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行政命令或者简单的示范就可以得以实施,而需要通过教师在真正理解、认同课程改革的基础上主动地意义建构。
二、课程实施的研究焦点
与教育改革研究的理论转向相适应,对课程实施的研究日益关注以下焦点:教师对课程改革的认同感、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效能感、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情绪以及学校文化。
(一)教师对课程改革的认同感研究
教师认同感(teacher receptivity),也称作教师接受度,是指教师对课程改革所表现出来的正面态度和行为意向。[4] 尽管这种正面态度和行为意向并不能保证教师一定有正确的课程实施行为,但是有研究发现和教师在课程实施中的真实行为有着显著的正相关。
对教师认同感的研究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方兴未艾。澳大利亚的学者沃(R.F.Waugh)在这个方面是领军人物。他和另外一位学者庞奇(K.F.Punch)在对大量实证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出六个显著的、普遍的影响教师变革认同感的变量:1、对教育的基本倾向(attitude),也就是教师对教育基本问题的看法,例如对教育价值、学生特性等的看法;2、对变革的恐惧和不确定因素的避免程度;3、变革在实际操作中的实用性,如改革能否被清晰地交流、变革所强调的原则和教师实践中占优势地位的规则之间的配合程度等;4、在操作中所感知的对于变革的期望和信念,也就是教师在采用一个新的课程变革的时候所感知到的结果以及所带来的信念的变化,比如更有利于学生学习、更容易让教师把握教学的精髓等;5、对操作中学校支持的感知,也就是学校的领导是否在改革方面做出积极的支持;6、在变革中个人成本的评估,这种评估主要是指非金钱的成本和收益(non-monetary cost-benefit)之间的评估。[5] 这一研究成果成为他们以及其他学者以后研究的一个基础,很多调查问卷都是根据这六个因素进行编写。
在近年来,对认同感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个变化就是对认同感的研究模式进行了修正,以更好地解释教师对变革的态度。沃在2000年根据认同感研究的一些新发现,提出了一个新的教师认同感模式,包括四类共9个自变量:改革的特征,包括与先前系统的比较和在教室中的实用性;学校对改革的管理,包括降低改革忧虑、促进对改革的理解、参与性决策;改革对教师的价值,包括个人成本的评价、和其他教师的合作、教师发展的机会;改革对学生的价值,也就是新课程对学生发展的意义。[6] 这一新的模式显然扩大了教师认同感研究的范围。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在关注教师个人感受、信念对认同感认同的基础上,开始考虑一些学校组织结构变量,如工作组织、学校文化等与认同感的关系,沃的新模式当中已经包含了这样的因素。香港学者颜明仁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显示,教师对改革的认同感与学校文化存在互为动态的影响关系,而且两者的关系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校长扮演的角色、问责制度、新旧教师对改革建立共识等。[7]
(二)教师在改革中的效能感研究
教师效能感(teacher efficacy)研究应用于教育变革比认同感更久,自上个世纪70年代课程实施兴起以来就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般认为,教师效能感研究有两个起源:一个是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称作兰德-罗特理论(Rand-Rotter theory);另外一个是班杜拉(A.Bandura)的社会认知理论。前者强调教师对教学专业的效能感,也就是教学效能(teaching efficacy),后者则关注教师对自身的效能感,也就是个人效能感(personal efficacy)。后来一般学者在对教师效能感进行研究的时候,则把班杜拉所提出的“效能期望”和“结果期望”与教学效能和个人效能对应起来,前者指大家对于事情结果的预期,后者则指个人对自己能否达到一定结果的预期。[8]
如果说人们对教师认同感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影响教师认同感的因素的话,对效能感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其效果。兰德计划的研究发现,教师效能感是预测变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变量之一,它与变革目标的完成、教师发展、学生学习的改善、以及变革材料和变革方法的持续有着显著的正相关。[9] 其他研究者,如古斯基(T.R.Gusky)、劳思(J.A.Ross)、斯科沃泽(R.Schwarzer)和格林格拉斯(E.Greenglass)等后来的研究,也肯定并丰富了兰德研究结果。
不过,上述研究基本上是把教师效能感看作是教师的个体心理特征,近些年对教师效能感的研究,则有试图超越个体心理范围,把教师效能感与教师集体互动和学校组织环境联系起来的倾向。班杜拉新近出版的书籍也认为教师效能感不仅限于个体教师范畴,学校氛围、家长的支持、对群体的感知等都会影响教师效能。他还区分了七种教师效能:影响学校决策的效能、影响获得和利用学校资源的效能、教学效能、关于学科知识的效能、获得家长支持的效能、对社群参与的效能和生成开放的学校氛围的效能[10]。笔者刚刚完成的研究也发现,教师效能感对教师投入新课程改革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它不仅仅包括教师对自己能否改变学生学习状况的信念,还包括能否把握由新课程改革所带来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如和学生的关系、和同事的关系以及和家长的关系)的信念。不仅受到自我能力与新课程所要求的教学模式之间关系的影响,还与同事、领导等与自己的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11] 这些发现已经超越了关于效能感作为个人心理特征的讨论,把效能感置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下。
(三)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情绪研究
受上个世纪中期兴起的“认知主义”的影响,教育改革的发起者、促进者以及研究者,往往把教师在改革中的行为看作是一个完全理性的选择过程,而忽略了教师情绪这一非理性的因素在课程实施中的作用。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情绪在教学和教育变革中的重要意义。他们认识到,对教师来说,教学是一种情绪实践,其中涉及大量的情绪理解和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教师这个职业的特征决定了他会在自己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中注入了大量的情感,而改革不仅仅影响着教师的知识、能力和问题解决的方法,还往往改变了学校的关系网络,从而对教师情绪产生强烈的影响。[12]
赞白拉斯(M.Zembylas)将情绪的研究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并将过去20多年的教师情绪研究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从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主要致力于情绪在教学中的作用,情绪研究集中在教师压力和倦怠感的分析(stress and burnout)上;第二个时期则把政策、社会关系等问题对教师情绪的分析联系起来。[13]
有关教育变革的文献显示,变革可以给教师带来大量潜在的压力。概括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压力的种类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不确定和模糊感 变革可能带来新的角色期望、组织目标期望,而这些期望和教师本来所具有的期望有所冲突,从而让教师感受到未来难以确定,甚至觉得前进方向模糊不清。
2、无能感(Feeling of incompetence) 变革需要教师具有一些新的知能,并扮演新的角色。这对教师有关知识、能力以及控制造成挑战,此外,新技术、新标准等在变革中的运用也使教师感到落伍于时代。
3、无权感(sense of powerlessness) 变革威胁着一些教师对环境的影响能力,也因此挑战教师的专业自主和自我决定能力,尤其对一些有经验的教师而言可能情况更是如此。而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也会剥夺具有创造精神的教师的信心。
4、秩序和意义丧失感 改革通常会对教师已有的信念、价值、假设、归属等等提出挑战,而这些则是教师秩序和意义建构的主要因素。
5、工作沉重感 变革由于需要教师新的知识、转变观念等等,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因此大大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
课程改革中教师所感受到的负面情绪,往往是教师对课程改革进行抗拒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改革中的压力也并非全是负面影响。一些研究发现,学习和成长在不清晰的情境下,在充满问题、冲突以及挑战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改革所造成的非常规性要求教师进行实验、高度注意、解决问题,因而促使组织学习和成长。尤其上述压力处于比较温和的程度的时候,更会出现积极的效应。[14] 此外,有些变革本身也是为了减轻压力所开展的,教师也可以成为变革的发起者,而不是被动实施者,[15] 压力对他们来讲就是有意义的。
而加拿大学者安迪·哈格利乌斯(Andy Hargreaves)及其同事赖斯基(S.Lasky)、斯格米特(M.Schmidt)最近则对教学和教育变革中的教师情绪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组织结构、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教师的情绪问题,探讨了学校组织结构、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家长、教师与同事和领导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的情绪经历。哈格利乌斯并提出“情绪地理学(emotional geographies)”的概念,认为应从社会文化、道德、专业、物理和政治五个方面分析教师与他人的情绪互动,从而达致教师对他人之间的情绪理解。[16]
(四)对学校文化的研究
从对前面三个研究焦点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学者们日益关注学校文化对课程实施的影响。如果说,课程改革的实施状况如何依赖于教师的所思和所为,那么教师为什么会如此思考、如此作为,则必须到学校文化那里寻找原因,因为教师的任何教育行为,都无法脱离具体的情境来进行抽象的探讨。学校文化不仅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也是教师的生活与工作以及课程改革的意义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学校文化的关注,实际上是对课程实施的具体情境的关注。
尽管学校文化意义如此重大,文化这个概念却是人类所面临的最诡异的概念之一,我们都可以感触到它但是又都无法进行精确的描述。从大的方面来看,文化可以看作是全体的人生,是一切生活的总体,从小的方面来看,则可以看作是“一套普遍的生活方式或者规范”。本文无意在概念上进行深入考究,而采用一个相对比较狭隘也得到西方学者普遍认可的概念,就是把学校文化看作是学校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普遍的规范、价值和深层假定。
对于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学校文化氛围,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在三个主要的方面:1、构建分享的愿景(vision),塑造学校的灵魂;2、构建专业学习社区(learning community),提升学校文化的表现;3、构建支持性、开放性的学校环境,凸显学校文化建设目标。
在学校形成分享的愿景或者使命为很多学者所强调,因为学校的发展愿景以及使命中蕴涵着学校最深层的教育哲学或者教育信念,而这些是学校文化的灵魂。很多学者坚信,愿景在迅速变革时代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愿景或者使命对于变革的实施以及组织效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持续的愿景构建给予一个组织以方向和目的,并发挥深刻的激励效应,不仅可以提高领导者或者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变革的时代,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促进个体和集体学习发展的条件。共享愿景的构建有两个重要途径:一个是从个人愿景的构建开始,通过促进个人愿景的融合来形成共享的愿景,[17] 二是从集体的共同经验或者进取心出发,构建分享的愿景。[18]
最近有关成功组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发现了一个宽泛的名词——学习型组织——的实践意义。学习型组织的主要倡导者圣吉(P.Senge)及其同事指出学习型组织是其成员在共同目标指引下注重学习、传播、创新知识的组织,是具备高度凝聚力、旺盛生命力的组织。[19] 很多研究也发现,支持教师学习的组织文化、促进教师积极地对日常工作进行反思的文化、提高学校知识管理的文化,有利于教育改革的实施。这些文化形态的作用在于使教师保持开放的心态,能够从同事以及领导那里获得有用的知识,也能够从自我的实践中不断成长,这些都可以促进教师迅速适应变革,积极地参与变革,而不是趋向专业的保守立场。
很多研究都发现,在学校建立一个团结协作的专业性学习组织对于减缓改革对教师的压力、促进教师对改革的认同、提高教师改革的效能感以及对改革的关注水平有重要的作用,而这样一个专业性的学习组织需要一个开放的、支持性的学校氛围。这种氛围鼓励教师进行尝试和标新立异,并且对一时的失误给予原谅;这种氛围也使教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这种氛围使教师更愿意做改革的主人,积极投入到改革当中去,而不是做改革的被动适应者和受害者。
三、让课程实施成为充满意义的过程
仔细审视最近在课程实施研究领域所发生的理论转向以及转向后的研究焦点,我们不难发现,新近的研究特别关注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感知和情感,包括他们对课程改革所宣扬的价值的认同,对自我能力是否适应课程改革要求的看法,以及教师由课程实施所引发的情绪。在课程实施研究领域的转向以及研究焦点表明,在课程改革(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等)这个客观现实之外,我们更需要关注教师内在的主观现实。正如麦瑞丝(P.Marris)所指出的,任何变革“都不能被吸收,除非它的意义为大家所共享”。[20] 只有在社会系统能够为个体提供使其获得生活意义的理论、价值和相关技术框架的情况下,社会系统加在个体之上的力量才能获得理解,有效的课程实施过程,应该是一个教师对课程改革的意义建构过程。
对于“意义”的理解并没有什么答案,虽然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常用的词汇。通过对过往的哲学思想的检视,辛格(I.Singer)发现,对意义的理解有两个相反的哲学力量,一个是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一个则是荒谬主义者(absurdist)或虚无主义者(nihilist)。前者相信存在着可以被发现的生活的意义,就像所有的数学问题都有一个解一样。后者则相信,虽然人们好像按照一些意义在生活,但是一旦深究内心,他们发现生活的意义并不存在。对于这两派学者把生活的意义看作是一个存在某处的统一的、包揽一切答案的想法辛格并不赞同。他指出这个宇宙并不提供我们类似意义这样的东西,但是人和其他动物可以为我们自己创造生活的意义。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那么他的存在可能就有问题。而当人们思考意义或者价值问题的时候,是由于他们发现适合他们的生活是不确定的,或者他们期望探察充满意义的其他生活道路。生活的意义,究其实质,是特定物种对他所处的环境的创造性反应,这个反应以他者的有意义的生活为借鉴,也是对自己所需要或者所倾向的环境相一致的价值的创造。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优越就在于人类能够超越固定的意义,在对意义的反应上具有更多的创造性。[21]
从辛格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意义”的意义至少有两个属性:1、意义并不是存在某处让我们可以发现的东西,它起源于人的主动创造,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产物;2、意义和人生活的目的和价值相连。
如果用这两个属性来检验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不足之处。比如很多改革的推行者相信,他们可以把改革的意义通过“洗脑”的方法强加给教师。当前的很多课程实施的实践,比如教师培训、课程实施的强制推行,都是建立在这种盲目的信心的基础上。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很多类似行为在教师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就在于这些课程推行行动过多关注课程改革的客观意义,而很少关注课程改革的主观意义,相信改革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学校得以忠实地实施,而忽略了教师已有的经验、价值、能力和情绪等对课程改革方案的调适作用。要纠正这些偏差,我们就需要充分关注教师在新课程改革中的意义建构过程,充分关注教师工作乃至生活的目的和意义。
前面的研究焦点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是:教师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的意义构建,并不仅仅是个体心理作用的结果,也并不仅仅牵涉个人的目的和意义,而是和学校文化密不可分,在通过与他者交往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此,符号互动论给我们提供了思想基础。带着实用主义、人文主义色彩的符号互动论学说,是20世纪最为持久的社会理论思潮之一。这个领域最经典的著作要属布鲁默(H.Blumer)的《符号互动论》,他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符号互动论的三项核心假设:
“第一项假设:人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是根据事情对于他们所具有的意义来决定如何行事的……第二项假设:这些事情的意义来自于或者说生发于一个人与自己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第三项假设:人在应对自己所遭遇的事情时,会使用一套解释步骤,而这些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处理和调整的”。[22]
这段话表明,任何改革只有进入人的视野,并具有主体的意义,才是真正的存在,才会引发人真正的合目的的行动,而意义是在参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并随之进一步发展。因此,关注学校文化、关注教师与学生、同事、家长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我们也会明白,为什么在课程实施研究的理论转向中,学者们把文化和个人放在了一起。
对课程实施研究理论转向以及焦点的回顾,其意义不仅在于提醒我们在理论研究上要关注教师的个人意义以及学校文化,也在实践上给我们很多启发。其中一个启示就是新课程改革应该以教师为主体,让他们主动地投入其中并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进行新的成长,真正构建以教师为主体的改革力量,外界专家以及学校领导所起的作用只是激励和支持,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做的相反。第二个启示就是需要实现学校文化重建(reculturing),只有在这种开放的、富有支持性的文化环境中,教师才敢于改革,进而善于改革,而不是担心被当作“出头鸟”来打击。总而言之,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要让课程实施的过程对教师而言是一个充满意义的过程,让他们在一个身心愉快的环境中为自己认同的教育价值而奋斗,让他们有能力驾驭被改革复杂化的工作环境和关系,因而保持积极情绪和进取心。只有这样,新课程改革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