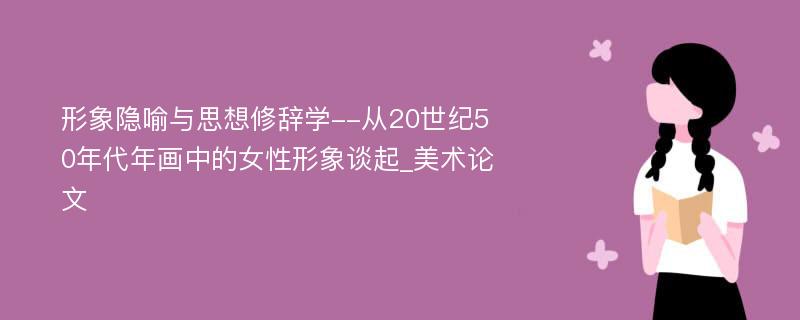
图像隐喻与意识形态修辞——从20世纪50年代月份牌年画中的女性形象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画论文,修辞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图像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1-0231-04
新中国的成立除了带来政治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外,也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从1949年开始,一套源于解放区美术的图像系统被推广至整个国家的视觉文化领域,并迅速取代旧图像而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表意系统之一,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美术的现实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其影响。这一图像系统更替的过程究竟出自何种动力?新的图像符号是如何克服旧的语义场从而确定它的隐喻意义?这种新的符号又将如何主导中国现代美术的走向?
这些都是解开中国美术发展史上许多宏观问题的枢纽所在,但当前的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对现象的微观描述,却没有看到事关整体发展的关键问题。鉴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以及作者有限的笔力,我们不妨先从一场几乎不为人知的争论谈起。
一、关于月份牌年画的争论始末
1958年的《美术》杂志总共刊载了十几篇关于新年画的文章,其中有5篇文章谈到了同一幅作品——月份牌画法的新年画《晚会新装图》,它们对该作品的评价如下:
1.第2期《年画座谈会》认为它“趣味不高”。
2.在第4期《群众喜欢什么样的年画》中,记者报道说:“解放军战士认为这是解放前的旧样子;工人说‘八级工也养不起她’……农民不爱看她。”
3.第6期的记者通讯中将其与《农村治虫小组》相比,认为虽然其发行量远大于后者,但“如果说《晚会新装图》是一幅给工农兵看的好画,是大成问题的”①。同期《谈谈年画出版工作》也谈到农民对这一作品的批评。
4.在第9期《从农民画看月份牌年画》中,认为此类作品“如其说是画新时代的新妇女生活,不如说是有的很庸俗,有的就是插白旗”。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对该作品的非议无关艺术技巧,而是针对人物形象和作品主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幅出自名画手金梅生的年画,即便从内容来看,也没有太多不妥:人物体态优美,面容秀丽。但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何以被指为像“旧社会‘名花’一样的女郎”[1]呢?这就要从新旧年画中女性形象的差异谈起。
女性图像在新旧年画中前后大概有这几种不同的样式:在桃花坞、武强、杨家埠等地的木版年画以及杨柳青的石版年画中,是体态娇弱的古装美人形象;到20世纪初,月份牌年画在上海因商业广告而盛行,这一图像除保留传统年画中女性的娇媚之外,又多渲染都市女性的性感、时髦、奢侈,采用了炭精擦笔和水彩画法,画面看起来透明、细腻、匀净,显得真实感十足;由解放区发展而来的新年画中女性形象则与前二者截然不同,单线平涂的画法使之相对于月份牌年画而言,画面略显粗糙,却与其内容更为契合,它表现的多是健康、活泼的农村少女,生产战线上的女模范,甚至是手持钢枪的巾帼英雄,当这一图像与不同的主题相结合的时候,它可以具有多种不同的隐喻意义,它可以隐喻恋爱自由、男女平等(《新娘子讲话》、《王贵与李香香》);也可以隐喻献身革命,勇于牺牲(《刘胡兰》、《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她”可以是一位健康朴素的农村姑娘(《好庄稼》);也可以是一位追求进步的年轻母亲(《妇女互助小组》、《考考妈妈》)。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上海的月份牌年画画家从1949年前后就开始主动改造思想,向解放区美术学习,但是奢靡、艳丽、摩登的画风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全蜕变,因此,在解放初期,烫发、浓妆的美人系上一条围裙便摇身变为“纺织厂女工”的情况比比皆是。到5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虽已有明显好转,但是月份牌年画与新年画相比,始终有所不同。《晚会新装图》之所以受到言辞激烈的批评,就是因为这一作品从构图到表现手法都与1949年以前的老月份牌年画如出一辙,而画面着力表现的女性美和其主题的相对模糊,都引起了1949年以后经历过多次政治思想教育的美术界领导和理论家高度的警惕,1958年1月,在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组织的年画座谈会上,就有人将此类月份牌年画与当时音乐界反对的“黄色歌曲”相提并论,称之为“粉色画片”[2]。
二、月份牌年画的现实处境
事实上,虽然月份牌年画在1949年以后努力向新美术靠拢,某些作品还在年画评选活动中获奖,但大多数作品却很难被官方艺术机构所接纳,更别说成为时代的主流艺术,这不仅仅由于其“消费主义”出身和不光彩的历史,更由于擦笔水彩画法本身所带有的甜俗浮华气息与50年代的革命浪漫情怀格格不入,新年画画法以木刻般铿锵有力的线条、响亮醒目的色彩成为新中国的视觉文化代表时,也就决定了月份牌年画处于被改造甚至被监督的地位。1958年第4期《美术》杂志上刊登了薄松年的《为月份牌年画说几句话》,文中提到:“‘美术’月刊从来没有介绍过一幅月份牌年画,好像这种形式应该摒弃于画坛之外似的,很多文艺干部轻视它,理论家不谈它,即便附带几句也是不加研究轻率地加以否定。”[3]薄松年的这篇文章写于1956年9月,在这之前,何溶曾有一篇题为《试谈年画的特点及其发展问题》的文章,作者直接指责新月份牌年画“不健康”,是在“散播低级的审美趣味”[4]。可见,很多时候,月份牌年画都被当作反面典型,即使是那些对月份牌年画没有任何偏见的理论家,仍然小心翼翼地与之保持着距离,如闻华在《关于月份牌年画和年画的特点问题》中,虽然对月份牌年画作出了中肯的正面评价,但其对月份牌画家却以“他们”相称[5]。
新年画工作的领导者对月份牌年画的态度是复杂的,首先,他们不可能对月份牌年画在民间的广大市场视而不见,仅1957年,上海画片出版社(专业发行月份牌年画的美术出版单位)就出版、发行了月份牌年画8千万份,1958年春节期间,全国公开发行了1亿4千万张年画中,其中月份牌年画占到了75%左右,其中的优秀作品,动辄印数就会高达几百万份。[6]如此巨大的发行量迫使文艺界的领导者必须正视这一被称为“庸俗的商业作风”统治下的美术领域,并设法将其改造成宣传自己的阵地。但另一个方面,月份牌年画所占据的巨大市场份额又令他们深感不安,在那个阶级划分成为普遍分类标准的年代,不同的艺术形式被划归到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中,既然“单线平涂”是最先进、最革命、最代表工农大众的艺术样式,怎么能在月份牌面前败下阵来呢?何况,解放初期的月份牌年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旧上海月份牌的气息,就《晚会新装图》来说,画家希望表现的是一个优美的妇女形象,但她同时又是一位革命事业的建设者,画家甚至在作品中加入了这样的说明:“晚会上,试新装,新装美观又大方,薄罗轻纱披两肩,红裾素裹增风光,借问姑娘为何笑,姓名新登光荣榜。”② 然而,对于已经在“思想觉悟上大大提高了”的人民群众来说,虽然画面是美的,但他们并不满意这幅新月份牌年画,认为她是“旧社会有钱人家的太太样子”[7];而新年画的领导者考虑更多的是:画面本身的“美”是达到宣传效果的基本条件,但是当这种“美”掩盖甚至损害了主题时,它是否就变成了一种庸俗的、有害的东西呢?
三、图像背后的意识形态之争
表面看来,月份牌年画所引发的问题仅仅与审美趣味有关,实际上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年画作者必须提供一种“政治上正确”的视觉样式,从而指导现实生活,这既关系着对旧艺术改造的导向问题,也涉及一种旧的图像符号如何在新语境下转义。
首先,政治形势要求创造新的图像隐喻,旧的图像如果不是被彻底摒弃,就必须被改造成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1949年,新中国成立,整个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都发生了转换,新中国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具有空前凝聚力的整体化社会,这一目标要求建立与其组织结构对应的表意系统。图像的隐喻是连接客体和意义的桥梁,当社会的意义框架因整体组织结构的变动而发生变化时,图像与其隐喻的变动便是必然的趋势,而审美风尚的流变则仅仅是以上变动的附属品而已。如庞迪曾经指出的那样:“关于组织的客观事实的形成是受到基本隐喻的指导的……隐喻既是情境的模式又为情境树立了模式。”[8]隐喻对历史实践又起到了样本或模式的作用,建国初期,最迫切的任务莫过于巩固新政权和建设新中国,因此,在美术作品中表现革命建设中的英雄人物或劳动人民形象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对月份牌年画来说,怎样才能紧跟这样的政治形势呢?蔡若虹在1951年就专门撰文指出:月份牌画家首先要学习“新的思想,新的作风”,辨别“在原有的题材范围之内,哪些是对人民有害的,哪些是对人民有益的或无害的”,而主题人物则应该更换为“一切从事生产劳动的妇女”[9]。从蔡若虹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图像实际上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视觉修辞方式,正如米切尔指出的那样:图像是一种“修辞”,艺术是一种“写作”[10](P1)。
一个新的社会权力机构在建立其表意系统时,意义生成的情况是复杂的。拿女性形象符号来说,在新年画出现之前,它在民间年画和月份牌年画中无疑有着约定俗成的隐喻意义,而新年画则赋予它一种新的隐喻,这样,无论从艺术表达还是艺术接受的角度看,符号的预先解释性与当前解释性产生了冲突,而这种冲突则“是由一个符号集体内不同倾向的社会意见的争论所决定的,也就是阶级斗争”[12](P365)。符号最终的意指取决于使用它的具体语境,如《晚会新装图》,虽然作者试图以“新中国劳动妇女的幸福”来解释画面的意义,但画中女性居室背景与人物姿态的“小资情调”,都使其图像的隐喻不同于新年画的要求,反而更接近于旧上海广告画的商业主题。从50年代美术作品的整体面貌来看,与新政权整体化价值体系相对应的图像符号系统已经基本建成。图像的隐喻作为多种价值体系斗争的结果,其最终被确定的价值观背后还隐藏着无数隐性的价值观,它们在被掩盖的同时仍不时显示出反抗主流价值观的张力。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月份牌年画中人物形象引起的争议,就像40年代在发生鲁艺桥儿沟的“马蒂斯之争”一样,实际上是所谓“工农大众的艺术”与“资产阶级没落艺术”的意识形态之争。
四、意义生成与“表达性现实”建构
一般来讲,新的图像系统确立的过程就是组织意义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新创造的图像符号接受社会行为者(包括评论家与一般观众)的质询,以此对组织事件——特别是那些旧的符号系统难以解释的新生活体验——进行解释,最后形成社会共识。在新的图像系统确立的过程中,意义得以生成、表达和被广泛接受,而图像的隐喻结构也在反复运用中逐渐被修正地更加规范,最终成为这一历史语境中固定的象征性图像符号。
可见,意义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参与,除了主管部门的协调控制外,还需要理论界对其进行宣传,以及群众认可该意义体系,这几个群体之间便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主管者无疑代表着权力结构的要求;理论界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原因,很容易受到官方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因专业背景而更注重艺术本体方面的问题;群众也并非被动地接受官方意识,而是有着主动意识主体,群众的意见是这一“命名”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既然“命名”的完成依赖于图像与接受者之间的相互质询,那么,只有通过权力机构之外一般群众的语言,或是以其他方式表明立场,才能认定这一“命名”的有效性。
但是,与新年画的画面一样,今天有记录的群众意见与理论文章无疑也是官方所建构的“表达性现实”的一部分,我们绝不能预先假定客观性现实和表达性现实的一致性。《美术》1958年第6期的记者通讯通篇都在批评《晚会新装图》,但却从侧面说明该作品在民间颇受欢迎,与“只印了2000张”的《农村治虫小组》相反,发行数达到“几十万份”[1]。作为中国美协直接领导的刊物,《美术》杂志一直在美术界发挥着理论阐述和舆论导向的作用,并以此参与国家政治文化的建设。在对《晚会新装图》的批评中,从未提到该作品受到欢迎的情况。代表官方立场的价值观以“群众意见”的形式被赋予先验的合法性,而这些由图像和话语共同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经过若干次重复强化后,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接受者的思维结构,最终成为他们主观性的思想。
1958年对月份牌年画的争论虽然没有出现在美术史中,实际上它却是新中国视觉符号系统建立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晚会新装图》最后的定论是“旧月份牌画形式的作品”,这既是对之前争论的一个总结,又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在表面上简化为“新”、“旧”形式的对立问题。对我们来说,则完全可以把1958年的争论看作新中国在构建它的表意系统过程中需解决的一个小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美术领域图像系统的转换是在国家整体政治框架下有计划、分层次地进行,其他的文化符号也同样经历着类似的调整与更新,这是整个国家的表意系统重新建构的过程,也是人们的信仰、情感等心理结构被重新塑造和整合的过程。
注释:
① 《晚会新装图》作于1957年,由郁风初稿,金梅生绘,该通讯中称作者是郁风和李慕白,其实当时郁风与李慕白合作的作品是《女工新装图》,两作品内容完全不同,从通讯中对作品的描述看来,当是金梅生所作《晚会新装图》无疑。
② 这一作品现存的版本中,有些没有这一文字说明,如59年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