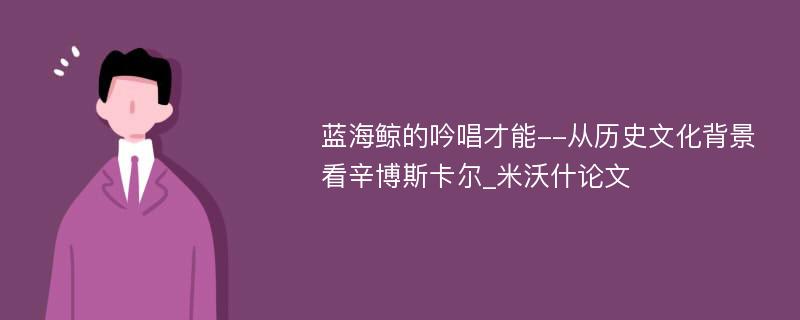
碧海掣鲸咏絮才——从历史、文化的背景看席姆博尔斯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碧海论文,斯卡论文,博尔论文,背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引
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界的泰斗季羡林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叫《留德十年》,其中写到二战前夕他在去德国火车上的情景:车一过红色苏联就到了波兰,上来的人明显地比苏联人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大多数人可以用英语与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交谈。这时走来一位十多岁的豆蔻少女,自然而大方地用英语与他谈笑风生……
差不多是过了一个甲子,与这位少女大约是同龄人而现在已是73岁的老太太的波兰诗人维斯瓦娃·席姆博尔斯卡(Wislawa Szymborska)获得了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消息传来,正在波兰南部山城扎科帕内一处作家休养地用午餐的席姆博尔斯卡先是告诉记者不要打扰她进餐,随后又告诉波兰电台的记者说:“恐怕从现在起的我有一段时间安静不下来了,而安静对我来说是最为珍贵的。”转而她又告诉在华沙的路透社记者说:“我为波兰文学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我已有几年被提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波兰像我这样的诗人还大有人在,只要提一提塔·鲁热维奇和兹·赫贝特就够了。”
与此同时,波兰克互希涅夫斯基总统的发言人则说,元首欣喜地获悉席姆博尔斯卡获奖的消息,全体波兰人民都怀有同样喜悦的心情。
而在席姆博尔斯卡的第二故乡克拉科夫,曾经在最近几十年的波兰历次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波兰影响最大的天主教杂志《普世周刊》(TygodnikPowszechny)主编耶·图罗维奇再一次走到世俗中来说:“她受之无愧,这证明她是我们最优秀的诗人。”
为何诗人这样珍视安宁?为何世俗政权和宗教政权的发言人都表示了这样的关心?
记得肖洛霍夫曾这样形象地描述哥萨克人的历史:
我们的土地不用犁儿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儿耕。
而对于波兰这个几百年来一直处于几大列强的狼吞虎夺之下的国家来说,他们的土地不仅用马蹄儿耕,还要用鲜血和眼泪来浇灌,所以在波兰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密茨凯维奇式或者叫文天祥、夏完淳式的诗人。又因为在历次民族斗争中,教会大多扮演了爱国者的角色,特别是在二战中,有三分之一的神职人员为反抗法西斯而死在希特勒的屠刀之下。所以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无论共产主义者下多大的决心,都没能取消教会的作用。最后也许是波兰从来没有宁静过,所以女诗人才这样珍视宁静!
那么波兰有怎样的一段历史,女诗人又怎样在历史中寻找宁静呢?
一、历史背景
大约在耶稣临世后不久,古老的奥德河和维斯瓦河流域居住着凡涅特人,这便是波兰人的祖先。以后近千年的时间里,东部斯拉夫人和西部的日耳曼人都曾用马蹄儿“耕种”过这个“中间地带”,到公元965年密什科一世完成了波兰同文同轨的事业。那时“基督教运动”在国际上轰轰烈烈,密什科在第二年便加入了“国际基运”。之后波兰是合久必分,到14世纪才又分久必合。在波兰辉煌的历史上,乌克兰、立陶宛都曾向华沙朝拜,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波兰被瓜分、奴役。17世纪外国列强插手波兰,沙皇俄国和瑞典王国的铁蹄再一次“耕种”了这块土地。而在1722年、1793年和1795年沙俄勾结普鲁士、奥地利三次最惨忍地将波兰瓜分。从此在波兰人的血液里,每时每刻都在流着对东边的俄国人和西边的日耳曼人的仇恨。多少年以后,那位出生于波兰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物理学家在回忆童年时说,她永远忘不了那时被迫屈辱地站在俄国督学面前,背出波兰的历任俄国统治者的名字。又多少年后,即便是在与俄罗斯人最友好的日子里,波兰著名哲学家沙夫也这样描述波兰人对俄国人的感觉:
波兰人对俄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过敏症”。……波兰的大部分古典文学和几乎全部浪漫主义诗歌都凝聚着对俄国压迫者的仇恨。……有一件事可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就是红军把波兰从纳粹手中解放了出来,这是可以用来改变波兰人态度的一张王牌,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伤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
东边如此,西边也是如此。铁血宰相俾斯麦在给他姐姐的信中曾说:“毒打波兰人,让他们失去生活的愿望。我本人倒也同情他们的处境,但是我们要想生存下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他们灭绝。”到了希特勒时代,这种欲望变本加厉。1939年,希特勒与苏联签订了《德苏友好协约》。希特勒死后,人们从他的秘室里发现,这个协约的后面还附有一个秘密协定,这就是当时轰动世界的“瓜分波兰协定”。
这一年席姆博尔斯卡年方二八,她已随父母从波兹南来到一个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城市——克拉科夫。在战争结束的这一年,她进了雅盖沃大学攻读波兰语言文学和社会学。也就是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她在克拉科夫的报纸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我在寻找词汇》。
这时斯大林的名声在波兰如雷灌耳。当时罗斯福与丘吉尔想在以原总理米科瓦伊奇克为代表的流亡政府的基础上建立新政府,而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坚持,应以由波兰工人党控制的波兰临时政府为基础建立新政府,结果斯大林胜利了,席姆博尔斯卡最初的一些诗篇就是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苦难,并以一个年轻姑娘的热情拥抱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1952年她出版了诗集《我们为此而活》(Dlatego zyjemy),里边都是一些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诗篇。多少年以后,198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曾这样评价她:
席氏的诗人生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我不喜欢她早期的作品,那里有斯大林的阴影,但后来的诗集一部好过一部。
这时波兰的六年计划(1950—1955)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由于工业发展速度过高,出现了农、轻、重的发展失衡,国内出现了要求改变和结束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方法的呼声。这期间斯大林去世了,席姆博尔斯卡已主编《文学生活》周刊的《诗歌》和《课外阅读》专栏。1954年她发表了《向自己提出的问题》(Pytania zadawane sobie),在这部诗集中,诗人的风格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那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热情大大降低了,代之以对生活的冷静观察和简约的描述。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波兰由于教会的影响最大,知识分子最受人民的尊重和西方文化非常普及而建立了最不“苏联模式化”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危机就在这里出现了。1956年6月在波兹南这个曾经是百年前暴发了反抗沙俄民族起义的城市,竟有20万人上街高喊“俄国佬滚出去”、“布尔什维克滚出去”、“我们要面包和自由”的口号。当局出动了近3个军和300辆坦克才将动乱镇压下去。到了10月,众望所归的哥穆尔卡回到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努力恢复法制,力求建立有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原话是“走建设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于是出现了被称为“波兰小稳定”的十年。
这时期席姆博尔斯卡的诗歌逐步走向成熟。也许这是波兰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安宁时刻,诗人的创作也到了一个旺盛时期,她先后出版了《呼唤雪人》(Wolanie do Yeti,1957)、《盐》(Sol,1962)、《一百个欣慰》(Sto pociech,1967)等诗集。在这些诗集中,诗人对人生进行了多方面的哲学思考。夕阳野草寻常物,鲜用皆为哲理诗,如《盐》中的《与石头对话》,就反映了人类处境的孤独和无奈。
哥穆尔卡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波兰的边界终于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在1956年至1965年的10年间,工业一直以每年9%以上的速度增长,丝毫不比西方国家落后。但哥穆尔卡与波兰人民的蜜月很快就度完了。1966年至1970年的工业增长为每年0.3%,同时政府与知识界和宗教界产生了冲突。早在1964年,《新文化》和《文化观察》被停刊,曾引起知识界的强烈不满,许多被查禁的作品不得不在国外出版。当时波兰只有3000多万人口,而国外侨民就有1000万,家家户户大约都有国外亲友,所以波兰与西方的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政府进一步把国内的知识分子反对派与国外的敌人相提并论。哥穆尔卡失去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
雪上加霜的是,政府与教会发生了严重冲突。同时又因中东局势紧张,波兰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引起波兰犹太人的强烈不满。这一切导致了1970年的12月危机,哥穆尔卡被迫接受“劝退”,波兰进入盖莱克时代。
盖莱克凭借西方的贷款,使波兰的经济再一次高速运转。但盖莱克再一次重演了哥穆尔卡的悲剧。没有几年外债压力越来越大,而经济增长却成了强弩之末。1978年10月16日,原波兰克拉科夫主教卡·沃伊蒂互当选为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由一位非意大利人担任教皇,波兰为之轰动,而约翰—保罗二世的波兰之行,其空前的盛况则使波兰政府的形象更加渺小了。于是当1980年政府决定再次提高肉类价格40—60%时,便出现了有80万人参加的全国性大罢工,团结工会成为合法组织,一个矮小的工人瓦文萨成了世界知名人物。军人出身的雅鲁泽尔斯基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政府总理,不久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实行了战时状态法。这是诗人相当不感兴趣的。这时期她曾写了一首《不再》的诗,其中前一节是这样的:
带着微笑和甜吻,我们
在星光下寻求谐音,
虽然我们不同,
只不过像两滴不同的水。
怪不得米沃什称她的诗为社会减震器,甚至是海边的窃窃细语。那么大的冲突,在她看来只不过是像两滴水,只要同意就可以结合在一起了。
的确,自70年代以来,席姆博尔斯卡的诗,政治在其中不过是个淡淡的影子,这期间她发表了《诗歌集》(1970),《各种可能情况》(1972),《诗选》(1973),《大数目字》(1976),《眼镜猴及其他诗》(1976)和《桥上的人们》(1986)。这些诗以千奇百怪的生活现象,表现了女诗人对人生意义的多方面的探索。如《大数目字》中的《罗得妻》一诗,借一个神话故事,表现了对人生的另一种看法。在这段时间里,席姆博尔斯卡虽然不问政治,但也表达了对波兰社会主义的不满。进入80年代以来,她经常为《普世周刊》写评论,有些评论新闻检查官甚至认为是不能发表的,这就说明诗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瑶台仙子。这一时期,席姆博尔斯卡的诗有时不得不在地下发表,这说明最不讲政治的诗人,也没有被政治家放过,也说明这个政府将不久人世了。
进入90年代,波兰又成了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国家。经过了1989年最困难的时刻之后,到1992年波兰的经济增长又成了东欧国家学习的榜样。但席姆博尔斯卡的丈夫死了,他是波兰著名的小说家,这是诗人最悲痛万分的事情。1993年她出了一本诗集《终了与新生》,其中有一首叫做《空房间里的猫》是这样开头的:
要死
我们并不能对一只猫
就像一只猫在空房间所做的那样。
《终了与新生》有许多个人化的东西,也许暗含着丈夫的死去和个人的新生,但也可以暗含着波兰的死去和新生。
二、文化背景
在近代500年的历史中,波兰为人类创造了光彩夺目的文化。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后人——包括牛顿、开普勒、康德、拉普拉斯、爱因斯坦、W.德西特、A.A.弗里德曼、G.勒梅特、G.伽莫夫、霍金在内——都不敢与之相提并论。单就是文学这一项,波兰可以说是东欧国家中的第一大国。本世纪内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人加上席姆博尔斯卡已是4人,东欧国家加在一起也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这个只有比两个上海的人口多一点的国家凭什么创造了如此光前裕后的文化?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从13世纪的《圣母颂》到前几年才当上波兰作协主席的伏·茹克罗夫斯基做一次细大不捐的描述。但自席姆博尔斯卡诞生之后出现的种种奇特现象——诸如女作家雄霸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兰文学,二战前后都出现了“真正的文学在外国”的说法,而女诗人却能在国内写出最优秀的诗篇——这一切对说明一个女诗人如何在战后波兰兄弟阋墙、汹汹攘攘的环境里,几乎是在不与任何人产生冲突的情况下能获得诺贝尔奖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好的注释。
且说在席姆博尔斯卡出生的1923年前后,可以震憾世界的波兰作家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莱蒙特相继去世了。这时波兰文坛上活跃着的是以东布罗夫斯卡为代表的女作家,她们的名气和声势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男性作家。这是世界文学史上极为少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在文化素质较高的国度的某一时代才有可能发生,但即便是英国的勃朗特姐妹和盖斯凯尔夫人时代,德、法的史达尔夫人时代,美国的狄更生时代,甚至中国的李易安与魏夫人时代,都不好说她们超过了当时的男性作家,只有在文化相当发达而社会相当民主、开放的古希腊的萨福时代,才出现过这种现象。而当时波兰的女性作家有佐·纳乌柯夫斯卡、海·博古舍夫斯卡、东布罗夫斯卡、戈雅维琴斯卡、玛·昆采维卓娃、万·华西列夫斯卡,怪不得早在1935年波兰评论家莱昂·皮温斯基就惊呼:“几年来男性作家的创作退居到次要地位了。”这时诗坛上如果不是还有一个杜维姆和一个描写科技文明的普日博希,那么波兰文坛就几乎是女人的世界了。应当说,在波兰有适合女作家成长的沃土,即便是在战后也出现了贝特日茨卡、纳伏罗斯卡、内波穆茨卡和奥斯特罗夫斯卡姐妹,当然更著名的是曾经当过波兰作协主席的哈·阿乌德尔斯卡。而席姆博尔斯卡的获奖便标志着波兰女性作家成就的一个高峰。
除了有女性的沃土之外,波兰的战前战后都有许多作家流亡国外。如30年代末华西列夫斯卡、布罗涅夫斯基、古尔斯卡、列昂·帕斯特尔纳克曾流亡苏联和其他欧亚地区,杜维姆和斯沃尼姆斯基则长期流亡欧美。波兰的流亡文学,自密茨凯维奇开始就是波兰文学重要的——有时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诗人在国内无法生存,于是许多人不得不跑到国外,而席姆博尔斯卡在国内可以顽强地生活着,并且写出了人类最优秀的诗篇。这可以解释女诗人的诗为什么多写生活中的琐事,有那么多个人化的东西,否则就无法避开国内那么复杂的斗争。
转眼之间波兰解放了,在40年代末期的几年里,作家们都忙着写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政府与作家之间似乎还没有出现太大的矛盾。1949年波兰作协在什切青召开大会,要求作家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社会主义生活中的阶级斗争:“表现阶级斗争的伟大场面,让英雄的今天和幸福的明天闪闪发光——这就是文艺的美好任务!”
但不满在增加。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在当时曾任驻华盛顿文化参赞,他认为波兰的文化政策是不可忍受的,于是便在1951年他调任法国一秘后,在法国要求政治避难,开始了他走向斯德哥尔摩的30年流亡生涯。在国内从1952年开始,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越来越多,而席姆博尔斯卡则开始了她的另一种诗人之路:她既没有像布罗涅夫斯基那样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也不象米沃什那样不停地揭露波兰生活中的虚伪,她似乎多少继承了先锋派诗人普日博希的唯美主义倾向,以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把生活中的细节诗化到群玉山头。
到了1956年,哥穆尔卡纠正了对右倾民族主义偏向的错误处理,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了清算,同时欧洲现代派作品也被一批一批地介绍到波兰,这时期大约相当于我国的1980年前后,新的刊物如《当代》和《直言》相继问世。说到《当代》,应当说这是波兰文学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围绕着《当代》有一批才调无伦、语妙天下的诗人,他们大多在二三十岁,他们学习的榜样中,还有几位三四十岁的兄长,如果把这些年轻的兄长也算在内,那么当代派就有两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席姆博尔斯卡在获奖后就曾只提到塔·鲁热维奇和兹·赫贝特。1921年出生的鲁热维奇可以说是当代派的兄长,而1924年出生的赫贝特则是地地道道的当代派。这个圈子里,其他的诗人还有1911年出生的米沃什,他虽然长年流亡国外,但一直是当代派的精神领袖;1922年出生的米·比亚沃舍夫斯基是最年长的当代派诗人;1923年出生的席姆博尔斯卡,对当代派有极大的影响,其他的都是30年代出生的诗人如塔·诺瓦克,耶·哈拉塞莫维奇、埃·布雷尔、博·德罗兹陀夫斯基、斯·格罗霍维亚克。这当中的领头雁是米沃什、鲁热维奇和席姆博尔斯卡,而赫贝特则是当代派中一员最勇猛的虎将,所以这几年鲁热维奇和赫贝特也是诺贝尔奖候选人的热门话题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鲁热维奇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在70年代之前发表完了,而赫贝特在70年代之后则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他对波兰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满意,包括像米沃什这样的作家,也“有很短的时期为一个出版社写作,这出版社为了政治目的着意歪曲了一些人物”。所以赫贝特未免走向了极端,因此在波兰“当代四杰”当中,米沃什与席姆博尔斯卡的获奖就非常自然了。
不过席姆博尔斯卡获奖的另一个文化背景是,当代派诗人的诗歌在冲破传统的教条主义约束的同时,由于没有老作家的声望和对斯大林心有余悸,大部分人不敢恃才傲物,眼高于顶。所以彼·昆策维奇在《当代》和《它的一代人》中曾这样评论说:“他们算是战后文化政策上最客气的一代、最能忍让的一代,也许是愤世嫉俗而又是被吓坏了的一代,是跪着造反的一代。”
席氏可以说是这一特色的典型代表。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和《呼唤雪人》中,她虽然把斯大林主义比做毫无温情的喜马拉雅山上的雪人,但绝大多数诗歌都是以美刺(gentle irony)的形式出现的。
60年代初期,哥穆尔卡曾亲自出马参加了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以消除作家对政府的不满。这时在波兰文艺界各种思想并存。而到了70年代,盖莱克的高速度很快出现危机,这时党的文化政策不是努力引导作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强制作家靠拢政治集团,大搞政治主义,这愈加引起了作家的不满。到1980年罢工风潮乘风而起,“团结工会派”的作家占有了波兰作协一半以上的数额,特别是团结工会派的天主教小说家什切潘斯基当选为作协主席之后,作协便成了反对政府的公开组织。
而这时席姆博尔斯卡却基本上可以遣身物外,虽然波兰检查机关有时查禁她的作品,但她超然物外的诗篇通过地下出版机构或国外的波兰文报纸发表后,就会很快地在读者当中流传。应当说,席姆博尔斯卡的婚姻对她的生活态度也有很大的影响,她先是和一位名叫亚当·沃迪克(Adam Wlodek)的诗人结婚,但两人离婚了,后来她与小说家科尔内尔·菲利波维奇(Kornel Filipowicz)结婚。菲氏是波兰当代一流的小说家,他的反映纳粹集中营生活的小说,至今仍然是描写被占领期间的不可或缺的作品。他的一篇名为《光明与黑暗》的小说,写维斯瓦河上游的一个农民带着全盲的儿子去看病,两年后仍然看不见,方知被诊所骗了。小说中的悲凉气氛可以使人想到我国作家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儿子在黑暗中描述的各种物体的形状,对应着中国瞎子所想象的油狼(游廊)。菲利波维奇的去世给诗人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波兰一著名文学杂志的主笔贝·契米尔(Beata chmiel)认为《终了与新生》中的有些诗篇是他读到的关于死亡的最动人的作品。
进入90年代以来,席姆博尔斯卡名声日上。1991年她获得了歌德文学奖,不过这时诗人仍然对生活没有“吃透”,所以她的获奖致辞就是《我珍视困惑》。就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两天,她获得了波兰笔会的诗歌奖。目前她住在克拉科夫市中心一套质朴的两间房子里。而获奖的这一天她正在波兰南部边陲小镇扎科帕内渡假。多年的习惯,养成了她不愿抛头露面的性格,她不喜欢大庭广众,而喜欢法国诗人布勒东式的个人主义。在她获奖后,米沃什从加利福尼亚打来电话,她对这位老大哥说:“我不是个公众人士。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写一篇获奖致辞。这需要我一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要讲些什么,但我会讲到你。”席姆博尔斯卡还对记者们说:她将隐居到一个比扎科帕内更偏僻的地方,一个连精明的记者也无法找到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她倒颇得中国古代山林高士之风,所谓“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正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些文人高士的必然写照,以此来说明席姆博尔斯卡在动荡不安的波兰社会中为什么会走一条既不同于热情赞美社会主义的东布罗夫斯卡,也不同于对一切都表示不满的赫贝特的中间道路,说明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席氏却能感动地走向斯德哥尔摩,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三、诗歌分析
应当说在席姆博尔斯卡获奖之前,不仅在我国文学界鲜为人知,就是在欧洲文学界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其名不扬。在我国大约只有林洪亮、张振辉、易丽君等几位50年代在波兰学习文学的留学生才熟悉这个名字(当然获奖后大家都熟悉了),在这一点上,她与莫扎特也有相似之处,作为为纯艺术而苦苦追求的艺术家,他们起初都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莫扎特因在银行的信笺上写曲子而被老板解雇,在尔后举行的一次音乐会上,开始听者寥寥,曲终之时,户限已穿。席氏大约也是如此。在英国伦敦郊区有一个叫做布丽达·沃尔克的女出版商,她曾出了一些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但席氏获奖时,她却在罗马尼亚,于是飞奔至伦敦重印席氏的诗歌集。她在飞机场惊喜地说:“我还不知道席姆博尔斯卡已被提名了呢?在我家里还有她500本《桥上的人们》正愁卖不出去呢?”但沃尔克这一天从美国接到的订单一次就是1200本。看来瑞典人在影响世界文化方面确有一根阿基米德的杠杆。
瑞典文学院在10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席姆博尔斯卡是诗坛上的莫扎特,公平地说是指她灵感的丰富和信手得来的妙有词致。她的诗具有美刺的恰到好处,使历史的和生命的内容在人类真实性中一点点地显现。
的确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这些评价都是在反复研读了她的诗歌之后所得出的中肯结论。波兰是一个诗的国度,而在20世纪表现得越发突出。所以米沃什在得知席氏获奖后说,这是“波兰20世纪诗歌的凯旋”,“在一个国家有两个诗人获得诺贝尔奖真是妙不可言”。波兰战后最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女诗人的朋友和邻居斯坦尼斯瓦夫·莱姆(Stanislaw Lom)则认为席氏非常有资格享此殊荣,“这说明波兰诗歌在散文作品之上。”那么席姆博尔斯卡的诗歌都描写了什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从最初的印象里,席姆博尔斯卡似乎是在写生活琐事,特别是一些个人化的东西。她自己曾经说过:“诗人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自负的;她倾向于相信自己并以此向读者叙说。”例如《车站》一诗中就写了许多生活中怪里怪气的小事:我没有到达N站,而你却不得不准时到来,一封没有发出的信却莫名其妙地给了你警告,后来,“一只不属于我的箱子”,丢失了。这些事情本来与我们没有关系,而我们却来到失乐园。给人的印象是人与人之间是冷漠的。
波兰作协被“团结工会”和平演变过去之后,在80年代末期曾出现6个“作协”并存的局面,如波兰文学家联合会、波兰作家联合会等。其中波兰作家联合会克拉科夫分会的主席彼查克维奇曾这样评价这位获奖朋友,说她精致、敏感,又有良好的幽默感。“在她的诗中有一种伤感和思乡情结,有一种对文明和价值危机的恐惧,但与其他诗人相比,席氏告诉读者,人们仍然可以高贵地活着。因此在她的诗中总在讲日常而普通的故事,照诗人看来,这些生命可以独立地活着。”在女诗人看来,生活中精神方面的东西比其它任何事情都重要,特别是比政治更重要。她的《博物馆》通过生活中这一常见的建筑物,说出了人生的短暂:
一顶皇冠荣耀过多少君王。
一双手套的生命比手更长。
一只皮鞋也早把右脚遗忘。
尽管如此,女诗人仍要顽强地活着,并且“跟衣裙的竞赛始终未停”。
通过普通的生活,席姆博尔斯卡在寻找一种真实。据说女诗人特别喜欢收集废旧的明信片,因为废旧的明信片没有伪装。在世界诗歌史上,诗人们为了追求真实,从屈原为香草美人而上下求索,到但丁为贝德丽采而苦苦煎熬,到济慈赞美希腊古瓮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到席姆博尔斯卡为废旧的明信片而刻意求真,也可以说是到了“无所不求其极”的地步,可以使人想到毛泽东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也就是说可以入诗的都入诗了。
不过席姆博尔斯卡并不是为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她常常通过千奇百怪的现象来探求人生的意义和哲理。这就是她诗歌的第二个内容,而且是最重要的内容。
在这个最重要的内容里,女诗人首先探讨的是人在社会中的意义。人类不仅受自然界的限制,还受到社会和历史文化的限制。像《也许》这首诗就表达了人的作为是有限的思想,因为“死”迟早会发生,也许是由于阴影,也许是由于艳阳天。因此人面对他的不幸时,总会感到一种无能为力,他总是有美好的幻想,而迎接他的只有痛苦和死亡。人的悲观主义在于提出问题而得不到解答,诗人便以她自己的幽默方式和彼查克维奇所说的伤感来寻找答案。
在探讨人生哲理的同时,席姆博尔斯卡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不能理解,人与周围世界的陌生感似乎是天然的。在这方面《与石头交谈》最为典型,“我”满腔热忱地想走进石头的宫殿,仅仅想得到一滴水,一片叶,但石头的回答却是冰冷的。诗人想着力描写的是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随着人生的延续而与日俱长。
在女诗人的哲理诗中,常常出现现实与历史的映照。在这里现代人和他们的祖先、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交替出现,从而探索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命运。诗人用象征的手法表现历史的进程,用神化了的历史来影射现实。诗人对历史有她独特的视角。时过境迁了,当女诗人重新审视希特勒幼年的照片时对这位小娃娃竟表现了一种母爱。按年龄,希特勒正好可以做席姆博尔斯卡的父亲,但历史改变了一切。《罗得妻》中的女主人翁是千百年来被人议论的话题,过去人们说她好奇才回头,有一本苏联人评述的《圣经》,说罗得的妻子不可能变为盐柱,因为人身上氯化钠的成分极少,因此《圣经》是不可信的,这是一种解释,但诗人却找到了另外的原因。席姆博尔斯卡认为历史上很少有秩序可言,总有人在那里瞎折腾,于是在《终了与新生》里:
时不时总有人
从下边的草丛里
挖起老掉牙的争论
特别是历史上的许多复杂问题不是靠思想而是靠利剑,不是靠艺术而是靠战术来解决的。这是每一个波兰人都有的体会。所以在《勃吕盖尔的两只猴》这首诗里,诗人表达了相当丰富的内容,波兰历史上曾经有太多这样的考试;女诗人那时正通过人生最艰难的选择;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两者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一种动物,因此猿猴的命运也是人类的命运……
席姆博尔斯卡的诗一般都有情节,在里边你可以读到一段故事、一条趣闻,但这些草木花鸟都有兽性,在外人看来可能是毫无意义的“晴空一鹤”,诗人便引诗情到碧霄。但这种碧霄上的诗意又是不易把握,不易琢磨的,甚至是流动的,变化的。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席姆博尔斯卡的诗一方面明白如语,另一方面却藏头露尾,指山说磨。
席姆博尔斯卡的诗,较少涉及妇女的内容。米契尔在1994年采访席氏时,女诗人坚持认为没有“女儿诗”这回事。“我认为把诗歌分为男人的诗歌和女人的诗歌是非常荒谬的,也许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母系时代,但现在没有一种事情不是同时涉及男人和女人,我们早离开绣楼闺房了。”看来尽管妇女文学在波兰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但席姆博尔斯卡的诗却不属于妇女文学。也许是因为女诗人更关心波兰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所以,她的诗歌才有一种“宇宙意识”,才有一种蓝天和大海式的宽广。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因此,表面上看席氏的诗作都是像郭璞的“翡翠戏兰苕”一类的“女儿诗”,实际上却是“碧海掣鲸”的力作。
瑞典文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特别提到席姆博尔斯卡是诗园中的莫扎特,我想这里边较深一点的含义是指两者在风格上的类似。莫扎特的音乐用中国古典诗论的语言来说就是“清丽”,也就是有一种秀美而极工的意思。席氏的秀美似乎已不必说,而她的极工则可用她自己下面的一段话来说明:
我写诗的时间越长,就越少想到有提出创作纲领的愿望和需要。我越来越觉得提出纲领只能束缚手脚,而且……为时尚早。我觉得自己就像只昆虫,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钻进了一个玻璃橱窗,而且被一颗大头针钉在了上面。
我只有一个座右铭——去攀登写作艺术难以企及的高度,不断地让思想超越现实。
的确,用莫扎特的“清丽”来形容席姆博尔斯卡的诗风是相当合适的。这里边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她非常喜欢法国古典诗歌,并且动手翻译了几本诗歌集。诗是不可翻译的,里边一定有诗人自己的创作,而这种创作又必须和原来的风格相同,这样法国古典诗歌的纯正、清秀之美也一定影响了她的创作。这使我们想到文章的开头曾提到季羡林先生说的,波兰人比苏联人有更高的文化,一般都会一两门外语。同时也使我们想到,波兰人会外语也是与他们艰难的历史有关的。
标签:米沃什论文; 波兰总统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文学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当代论文; 作家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