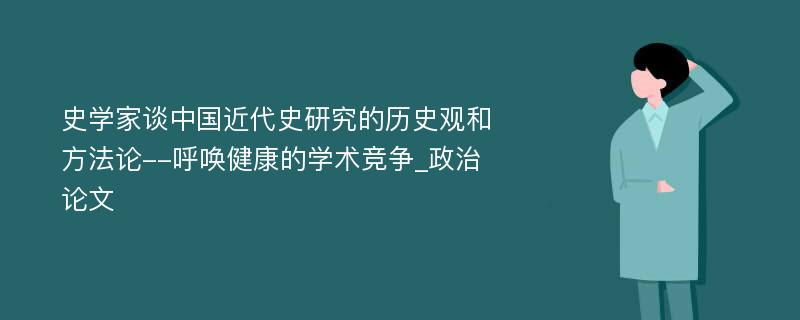
历史学家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呼唤健康的学术争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近现代史论文,历史观论文,历史学家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6月6日,北京市史学会和国家教委社科中心联合召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研讨会,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将部分与会同志的发言摘要刊登如下。
这十几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有很大进展,领域的扩展、问题的深化或是对过去某些简单化、片面化做法的纠正,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前进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其中也包括一些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不合乎历史真实的意见,我觉得这完全是正常的。但也有不正常的一面:因为有些看法并不是属于个别文章中的个别看法,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有倾向性的意见,而对这种意见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声音几乎没有。现在似乎是发表那样一些看法的园地很充分,机会很多,而另外一些不同的意见,还没有发表时,人家就宣判你没有合法的地位,是“左”的,是僵化的,是打棍子的。我觉得这样一种学术气氛不太正常。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空气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环境和学术环境要不要宽容、如何宽容的问题。有些文章在呼吁宽容的同时,对别人说话的权利是非常不宽容的。
这里我赞成另一篇文章的意见。文章说,政治上应当讲宽容,过去我们经常把学术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这是不对的,不能让批判成为一种政治审判,不能让批判与政治惩罚相联系,但决不能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消灭、取消批判本身。政治意义上的文化宽容意味着容忍某种现象存在,也容忍对这种现象的批判存在。宽容要结束的是那种病态的批判,而不是批判本身。如果以宽容的名义反对一切批判,这是一种有害的越位,宽容也意味着为批判松绑。在这里,作者使用了学术批判这个词,我觉得不如使用学术争鸣。不要一下子把问题提到政治上去,对于错误的或者你不同意的看法也不要这样,同时对于对某些意见的批评也不要这样。我发表意见时,尽管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希望你给我发表意见的权利,也尊重我发表意见的权利。
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可能就比较好办一些了。这几年来,在有些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带有体系性的意见。我觉得,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极力夸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传播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所起的作用,极力贬低或苛求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所起的意义。另一个是极力夸大某些封建主义代表人物的某些政治作用,而对改革者、革命者却非常苛求、苛刻。它实行的是两个标准,对革命者和改革者实行非常苛刻的标准,而对于封建统治者则是另外一个标准。比如,“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这个帽子至少已经戴在五六个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的头上。现在有一种“扬袁抑孙”的倾向,我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它说,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根源就是孙中山。而对袁世凯,作者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袁世凯的教育思想是前无古人的;袁世凯和他以后的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培养出了一大批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成长起来,与袁世凯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像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讨论,但也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
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说明一下。首先是理论指导是不是限制了对历史真实的认识的问题。尽管现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没有多少人,但是也有人公开讲,现在来谈马克思主义指导未免显得可笑;另外也有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是必要的。我觉得,至少可以这样说,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人,虽然未必能够把握历史的真实,但是,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就绝对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
第二,感情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有篇文章是这样说的:“解放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宣泄上,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就是说,我们老是对帝国主义进行感情宣泄,老是批评,结果我们不能科学认识它,淡化了我们的理性色彩。文章说,“过去讲的西方的殖民主义造成东方的普遍落后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资本主义向世界体系拓展打上了非正义的侵略的烙印,东方封建国家和落后地区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抵抗却涂上了正义的反侵略的金粉。”文章说,殖民主义对东方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唯一的一次良机。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讲到感情问题。我说,我们当然要追求历史的真实,但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是不是一定要心如死灰、心如槁木呢?恐怕不行。每个人都有感情,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进行揭露批判当然是一种感情。那么,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次良机,说不能批评它,批评就是感情宣泄,这也是一种感情。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感情,而在于这种感情对不对,符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第三,如何服务于现实的问题。我觉得,近年来有些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是不能接受的。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为现实服务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强调要稳定,没有稳定一切都不行。一些人为了为现实服务,就讲历史上的稳定,谁起来作乱,破坏了统治秩序就不好了。又如爱国主义,前几年港台报纸上有篇文章,说爱国主义重新提出来是北京的某些“左”派理论家用来对抗改革开放思想的一面旗帜,似乎强调爱国主义,就不要改革开放了,如果用宽容一点的态度来考虑,他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改革开放,似乎揭露了帝国主义就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了。我觉得,这也是两回事。今天我们与外国人谈判,当然不能说:干杯,打倒帝国主义;但是讲历史的时候,讲过去帝国主义曾经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灾难,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某些同志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至少犯了一个错误,犯了过去我们曾经犯过的简单地用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错误。
最后一个是创新问题。是不是新的都是对的,应该分析一下。比如,刚才讲的对袁世凯的评价,应该说是非常新的观点,但我觉得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科学的观点。所以,新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是两码事。科学从本质上讲要求创新,如果重复前人的东西,科学就没有前进。但创新实际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对前人的某种不科学认识的纠正来达到新的科学的认识,这是一种创新;另外一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进,往同一个方向前进,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有些人对老前辈范文澜同志历史著作的评价,话说得不公平,带着一种轻率的嘲弄、轻薄的口气评论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纠正了过去旧史学对历史的颠倒,现在有些人提出要重新认识。如果现在一定要再简单颠倒一次,这里的新与旧就很难说了。很显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范文澜等同志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未必都是真理,需要重新认识,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要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因为先辈的成果是我们研究的基础,纠正他们的错误也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往前走。
史学研究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会逐渐形成一种有系统性的看法呢?从研究方法来讲,有一个特点,就是把中国近代社会变成抽象的脱离周围环境的真空里的东西。现在有些人认为近代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仅仅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这就离开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民族独立,近代中国是一个不独立的国家;二是政治民主,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需要解决政治前提问题,否则,近代化就走不下去了。不仅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一定时候就需要解决政治前提,需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中国除了要有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反对封建之外,还要有民族独立。这里办一个工厂、那里办一个工厂,甚至搞一些资本主义的政治设施,都是可以的,都是在量的范围之内逐步向近代化前进。但是,如果上述两个前提不解决,近代化就化不下去了。现在很多人抛开了这个东西,因此,就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是错的、反对封建主义是错的这一类的观点。如果认为只要谁办过工厂或是发表过意见说要办厂就是好的,而不考虑大的政治前提,那么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者是该否定的,因为任何一个统治者,即使是最腐朽的,为了维持其统治,也会办几个工厂,搞点实业。所以我觉得,讨论历史观、方法论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史学研究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同时有一种健康的学术争鸣的气氛,就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标签:政治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袁世凯论文; 范文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