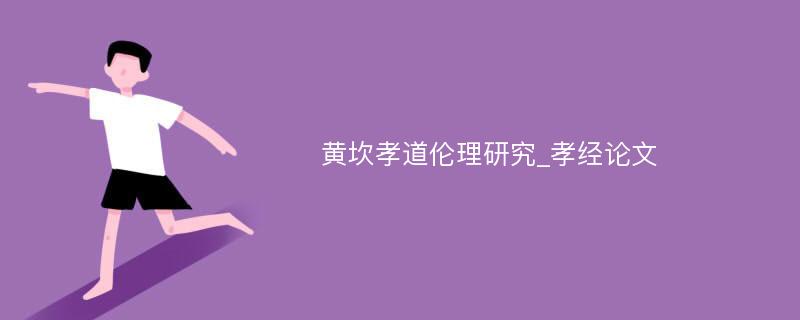
皇侃孝道伦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孝道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14)06-005-06 皇侃为南朝梁最为著名的经学家之一,所撰《论语义疏》最为后世所推重。皇侃本人不仅“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1](P680),又撰有《孝经义疏》。然而,至宋时《孝经义疏》于国内流佚。隋唐间《孝经义疏》虽曾传入日本,但也仅流传一时,最终也是难逃亡佚劫难。[2](P39-40)今可见者唯邢昺《孝经注疏》所援引的二十四条。①故对皇侃孝论的考察当以此二十四条与《论语义疏》中的相关阐释为文献依据。而目前大陆学术界鲜有学者对皇侃孝道伦理进行研究。皇侃论孝,颇为复杂,命题迭出。诸如,云:“孝悌者,实都不欲”、“本,谓孝悌”、“孝是仁之本”、“孝为体,以敬为先”、“孝是事亲之目”、“政者,以孝友为政耳”、“孝于其亲,乃能忠于君”、“人子为孝,皆以爱敬为体”,等等。基于此,本文拟对皇侃孝道伦理的本质、地位,及其行孝实践分而疏之。 一、孝的本质与地位 在魏晋南北朝时,“孝”不仅是儒道释三教论辩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推行教化的重要内容。据此看,皇侃对孝的本质与地位的阐述不仅是其思想体系建构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学术氛围。 (一)“孝是仁之本” 自孔子以来,儒家论孝往往将其与“仁”并举,践履仁道须以行孝为基础,如孔子云“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有子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因此,有学者认为:“儒家孝道思想的展开,本于孔子之‘仁’,而孝弟为实践仁道之本,盖爱人为仁,而孝弟为爱之基础。”[3](P22)此论符合事实,以“爱人”释“仁”,孝与仁相通。 皇侃对孝之本质的揭示符合上述理路,提出了“孝是仁之本”的命题。在疏释《论语》“其为人也孝悌”章时,皇侃云:“孝是仁之本,若以孝为本,则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举仁则余从可知也。故《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王弼曰:‘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4](P5)“孝是仁之本”,即以孝为仁的根本,行仁为行孝的衍生与发展。为何如此疏释?皇侃援引王弼注作出了说明。王弼以“自然亲爱为孝”乃是立足于道家“无为而自然”之道,意在于儒家名教中注入自然的因素,统合儒道。皇侃是否承续此意?就“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而言,“孝”“仁”并举,因此有必要先梳理皇侃“仁”义。皇侃认为“人禀天地五常之气以生曰性”[4](P79),“此五者(仁、义、礼、智、信)是人性之恒,不可暂舍,故谓五常也”[4](P31),“仁者,人之性也”[4](P6)。可见,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仁为人性中生而即有的五种不同品质之一,具有恒久不变的特征,即仁为人性本身所具有成分。皇侃又云:“仁者,恻隐之义。”[4](P101)“恻隐”即指仁性的特质,属于未发的状态,故为“五德之初”,其彰显则为“恻隐济物”、“恻隐济众”(疏释“樊迟问仁”章“爱人”)。可见,作为仁性内容的“恻隐”并不具有道德性,仅为生而即有的利己利他的自然心理机能,这种机能本身也具有自然向外彰显的特质。据此可知,皇侃论孝并不遵循王弼注,而是立足于生之谓性的角度,转化其“自然”义,即认为人生而即有自然亲爱的本性,这种本性的彰显就是“孝”。因此,皇侃论孝乃是基于血缘之爱。由血缘之爱推及人、推及物便为仁。仁与孝的本质是相通的,均具有利人惠他的特质。在现实生活中“事亲之孝”较“推而及物之仁”更自然、更直接,故孝可以作为仁的根本与基础。 如果上述的理解是准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征引宋儒程颐对“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的疏释与皇疏作一比较。程颐云:“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又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事……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P30)在程颐看来,爱有差等是现实生活的实情,血缘之爱必然是最为亲近之爱,故仁爱的扩展(行仁)以立足于血缘之爱的孝悌为基础,这与皇疏有相似之处;但是程颐的立论基础却和皇侃是截然不同的。程颐认为“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6](P207)。程颐对人性作出了“善”的价值判断,人性中先天存在的仁、义、理、智也必然是善的。因此,程颐所论的仁性不仅不是皇侃的自然气质之性,而且因其性善而具有了德性价值,孝悌只能为仁性的发用与彰显,与皇侃之论相去甚远。 皇侃所论“孝是仁之本”,一方面,从人性的潜质上说,孝、仁在本质上为一物;另一方面,则是从行孝与行仁的关系上说,行孝是行仁的根本或基础。 (二)“孝为百行之本” 皇侃从其人性论出发,认为孝、仁在本质是一致的,行孝为行仁的基础。这种论述与其生平笃守孝道,身体力行,对行孝及其行孝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存在密切关系。关于行孝在社会生活的地位,皇侃提出了“孝为百行之本”的命题。 在对《孝经》题疏时,皇侃云:“经者常也,法也。此经为教,任重道远,虽复时移代革,金石可消,而孝为事亲常行,存世不灭,是其常也。为百代规模,人生所资,是其法也。言孝之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经下经,老子有道德经。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经。”[2](P117)训“经”为“常”、为“法”,②虽非皇侃发明,但是将《孝经》与《周易》、《老子》并举,则或是皇侃的卓见。从学术史发展看,《易》为群经之首,肇自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承其续,[7](P57)后世学者多延续此论。皇侃此处,将《孝经》与《周易》并举,则是说明《孝经》的地位可与《周易》相当。值得注意的是,两汉以来存在《孝经》不断升格现象,至南北朝时,甚至出现王俭的《七志》以《孝经》取代《周易》居群经之首的现象。《孝经》以其世俗化倾向,普遍被世人广泛认可,被奉为行为的规范,甚至上升为一种强烈的信念,如皇侃般日诵《孝经》二十遍。如果说皇侃日诵《孝经》,并将其比拟为《观世音经》;那么此处的疏释又将其与《道德经》并举,这也反映了南朝三教流行的背景下三教经典均可以成为世人的行为规范与信念支撑。 就皇侃孝道的建构看,行孝为现实生活中行仁的基础。在皇侃思想中,仁性主生,居于“五德”之首;在现实生活中行仁则居于万行之首。作为行仁基础的孝行也必然成为了整个社会教化的根本与基础,故皇侃在疏释“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时,援引《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4](P5)是十分恰当的解释,即将行孝看作一切德教的根本。 皇侃疏释《孝经·广至德章》“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时,又云:“并结要道,至德两章。”[2](P129)现存皇疏甚简,唯此二句。如何理解此二句则出现了歧说。邢昺认为:“言乐易之君子,能顺民心而行教化,乃为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谁能顺民心如此其广大者乎?……此章于‘孰能’下加‘顺民’,‘如此’下加‘其大’者,与《表记》为异,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为并结《要道》、《至德》两章,或失经旨也。”[8](P54)而陈金木则云:“何以皇氏特以此广至德章引诗云之语,而曰‘并结要道,至德两章者’,其或如黄德麟氏所言‘孝经开宗明义章,以孝经为至德要道焉,而广要道章言孝遂言悌言乐,而终言礼。其下广至德章,亦承上章礼之敬而言’。故皇氏独以此章因诗为通贯广要道、至德两章也。”[2](P129)就邢昺立场看,乃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崇奉当时流行的孔安国注,对皇疏多有批评,甚至云其“辞多纰谬,理昧精研”。此处邢昺虽援引《表记》论说至德之君用乐易之道教化人民,堪为民之父母,但或与其立场有关,指责皇疏“或失经旨也”。而考察《孝经·广要道章》,知其内容乃是站在国君的立场上,通过论述教民亲爱、移风易俗、安上治民,说明《开宗明义章》中孔子所谓的“先王有至德要道”,而其后的《广至德章》又进一步阐发了上述德行。因此看,邢疏侧重于君主论说,而陈金木则联系《孝经》主旨疏解。二说各有侧重,虽无法确定何者更符合皇侃意旨,但此处皇侃论君主之孝,仍着眼于“孝”为遍及家庭伦常与国家治理的“至德要道”。也唯有如此重要的孝行,才能成为“百行之本”,《孝经》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了。 基于上述,皇侃提出“孝为百行之首”的命题,不仅应合了《孝经》在儒家经典中的升格现象,及顺应了三教合流的时代学术思潮;也着眼于孝行本身在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既然孝与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行孝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百行之首”的地位,那么如何行孝则成为了皇侃进一步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孝是事亲之目” 无论学术界对“孝”的起源、本质、涉及的对象等存在怎样的分歧,但无不承认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家庭、宗族之孝是一切孝道的核心与基础。皇侃十分注重阐发事亲之孝。 (一)无违为孝 “无违”为孝,见诸于《论语》“孟懿子问孝”章。皇侃疏释“无违”云:“言行孝者,每事须从,无所违逆也。”[4](P21)显然,皇侃将“每事须从,无所违逆”作为“无违”的内容。然而作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子如何能侍亲时“每事须从,无所违逆”?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无违”也的确很难行通。事实上,皇侃的阐释并不是停留于具体的实践操作上,而是注重从“孝子之心”出发。在疏释“其为人也孝悌”章时,皇侃云:“言孝悌之人,必以无违为心,以恭从为性。……然孝悌者,实都不欲。……故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悦,先意承旨。’”[4](P4-5)皇侃认为孝悌之人“实都不欲”。在事亲的过程中,若没有犯上的心欲必然在事亲时“无违”父母心愿,“恭从”父母的吩咐。如果“以无违为心,以恭从为性”,没有了犯亲的心欲;那么和颜悦色地侍奉父母,秉承父母意愿去行事,便成为了事亲的应然之理、当然之事。故皇侃云“此孝者不好,必无乱理,故云‘未之有也’”[4](P5)。 在疏释孔安国注:“孝子在丧哀慕,犹若父在,无所改于父之道也”时,皇侃又云:“本不论父政之善恶,自论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风政之恶,则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恶,则其家相、邑宰自行事,无关于孝子也。”[4](P13)如果联系皇侃在疏释苞氏注“先能事父兄,然后仁可成也”时,所援引的王弼注“自然亲爱为孝”理解上述引文的话则可知,皇侃将“自然亲爱”看作是心无欲的内容。“孝子之心”无欲,并非是说没有任何欲望,而是指其在事亲时以生而即有的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自然情感(孝子之心)为基础。由这种情感所支配的事亲行为,则必然是先天恭顺父母意愿的,符合亲子之间的“正理”。故皇侃以“冢宰自行政”、“家相、邑宰自行事”曲为孝子辩护。 总之,皇侃论事亲无违,是从孝子具有的自然情感出发,并不是着眼于具体的生活实践操作。 (二)以爱、敬为孝 上述“无违”侧重作为事亲的态度而论,至于如何进行“无违”行孝,皇侃则继承了以往儒家以爱、敬行孝的思想。 疏释《论语》“子游问孝”章时,皇侃云:“夫孝为体,以敬为先,以养为后。而当时皆多不孝,纵或一人有,唯知进于饮食,不知行敬。故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犬能为人守御,马能为人负重载人,皆是能养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犬马皆能有养’也。……养犬马则不须敬,若养亲而不敬,则与养犬马不殊别也。”[4](P22-23)皇疏基本吻合孔子的意旨。皇侃认为行孝之法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则是“敬”,其次方是“养”。如果不对父母持守敬爱,仅以物质赡养父母则和豢养犬马、喂养珍禽奇兽无二致,不可以称之为孝。可见,“敬”是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在行孝中是高于“养”的层次。事实上,皇侃的这种理解立足于孝子之心(即人生而即有的血缘情感),也包含人性中生而即有的利人惠他的特质不断地向外彰显与扩展的因素。 《孝经》也十分注重强调以爱、敬为孝的思想。如云:“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纪孝行章》),“生事爱敬。死事哀戚”(《丧亲章》),“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士章》)。然而,因皇侃疏释的亡佚,以无法看皇侃对上述言论的阐述,仅就皇疏其他言论作一窥测。在疏释《孝经·天子章》“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时,皇侃云:“爱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为爱心。温清搔摩,是为爱迹;肃肃悚悚,是为敬心,拜伏擎跪,是为敬迹。”[2](P120)爱与敬均是由人生而即有的自然情感而展现的。事实上,以“爱”、“敬”连用论孝,在曾子那里已经存在。诸如《大戴礼记·曾子立孝》云:“君子之孝,忠爱以敬,反是乱也。”而皇侃却在把握曾子以来的论孝大义的同时,又将爱、敬分而论之:爱是与日俱增的惜爱之情的展现,故人子无论是温夏还凉秋,均能侍奉父母,以尽其孝。敬则是内心恭敬之情的展现,故人子无论是行拜伏礼,还是行擎跪礼都是发自于内心,毕恭毕敬。皇侃此处阐释的文本乃是《天子章》,其意也甚明,理当是阐述由孝亲推至天子之孝。 如果说“以敬为先”的论述还仅侧重于行孝敬养之上,那么通过阐发《孝经》的大义,将“敬”与“爱”并举则丰富了行孝的内容。如果联系孔子“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语,与皇侃上述“温清搔摩”、“肃肃悚悚”、“拜伏擎跪”等敬爱孝行,则可知皇侃和孔子一样均主张以礼事亲,行孝必须依礼而践形,行孝即行礼。 (三)孝之终始 在疏释“曾子有疾召门人”章时,皇侃云:“孔子昔授《孝经》于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禀受,至死不忘,故疾病临终日,召己门徒弟子,令开衾视我手足毁伤与不,亦示父母全而生己,己亦全而归之也。先足后手,手近足远,示急从远而视也。”[4](P129-130)《孝经·开宗明义章》载孔子语:“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皇侃此段疏释仅援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句,此内容恰是对“孝之始”的阐述。在皇侃看来,“父母全而生己,己亦全而归之也”就是行孝。如果联系《礼记·祭义》“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可不敬乎”语,皇侃之论则更容易理解了。自己的血肉之躯来自父母,对身体的保全则是体现对父母的孝敬,以此为“孝之始”最为直接、最为恰当不过了。然而这种孝敬并非是仅停留在身体层面,而是需要进一步提升到精神层面。推而扩之,则涉及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行孝。故皇侃在疏释《孝经·开宗明义章》“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时,又云:“若生能行孝,没能扬名,则身有德举,乃能光荣其父母也。因引祭义曰:‘孝也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此则扬名荣亲也。”[2](P120)显然,这段疏释阐述了人子以“生而行孝”与“没能扬名”的行为,来“光荣其父母”。“扬名荣亲”成为了行孝的结果,为“孝之终”。如果联系《孝经》“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语,则知皇侃以“扬名荣亲”为孝之终,恰是说明达到了“扬名荣亲”,也使自己“立身”了。 然而,在《孝经》看来行孝立身作为德行并无终始,故其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庶人章》)皇侃疏释云:“无始有终谓改悟之善,恶祸何必及之。”[2](P125)如何理解皇侃此句疏释?邢昺疏云:“夫子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毕,于此总结之,则有五等。尊卑虽殊,至於奉亲,其道不别,故从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则无终始贵贱之异也。或有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盖是勉人行孝之辞也。”[8](P126)陈金木则云:“虽以孝道内蕴广大,塞乎天地,横乎四海,难备终始。因而勉人以虽无始,然能有改悟之善,亦可无祸;可谓别开蹊径,然于经义,称嫌不足。”[2](P126)实际上,邢疏与陈说理应源于《孝经·感应章》所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但是《感应章》此句在于说明孝道之广,凡有人处皆有孝道。《感应章》是就孝道存在的范围与行孝的普遍性而言。然而皇侃却云“无始有终”,非契合邢疏、陈说所释孝道广博之义。因皇疏前后文缺失,很难清晰考知皇疏的具体涵义。故愚以为,如果从皇侃疏释《论语》“子夏问孝章”所引沈峭注“今世万途,难以同对,互举一事,以训来问。来问之训,纵横异辙,则孝道之广,亦以明矣”[4](P24)看,皇侃认为孝道广博,随事可言,行孝入手不能拘于一处、一种形式,即便是最基础的“事亲”也是如此,故云“无始”。但恰恰是“无始”、不拘一格的行孝,可以达到改善迁过、全生、扬名,故可以说是“有终”。换句话说,皇侃认为遵循“无始有终”的行孝行为,有助于“无终始”的孝道推广。 (四)父子相隐 在疏释“叶公语孔子有直躬”章时,皇侃云:“叶公称己乡党中有直躬之人,欲自矜夸于孔子也。……言党中有人行直,其父盗羊,而子与失羊之主证明,道父之盗也。……孔子举所异者,言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应相隐。若隐惜则自不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尽矣。”[4](P232-233)皇侃阐述的重点在于孔子与叶公所论的“直”不同。叶公论的“直”是立足于理性法则之“直”,据事而判定是非。而皇侃则认为,孔子所举与之恰相反:父子相隐本源于父子与生俱有的自然天性,相隐属于人性的“自然至情”,而“自然至情”的展现则是“直”。孔子论“直”依据的是人的自然性情,其判定不符合理性法则左右下的事情是非。皇侃认为孔子的判定不仅不悖于社会教化,而且恰恰体现了父子之间具有“人伦大义”。在皇侃看来,父与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乃是基于先天即有的自然情感,这种情感的自然彰显是社会中最为合理的。维护父子真情,不仅有助于维系家庭的和谐,而且可以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导引社会风化。故皇侃又援引范宁注;“夫子所谓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故相隐乃可为直耳。今王法则,许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盖合先王之典章。”[4](P233)由此看来,叶公论“直”,将人伦与礼法完全对立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是维护了社会礼法,实际上则违背了社会礼法所建立的基础—人性,是不可取的。而皇侃认为孔子所谓的“直”是符合人性、人情,于人性而立法、容情于法,符合“先王之典章”。此种思想也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并列入法制。 皇侃的这种阐述并不是说面对“其父攘羊”,其子无所作为。皇侃在疏释苞氏注“见志者,见父母志有不从已谏之色,则又当恭敬,不敢违父母意而遂已之谏也”时,又云:“然夫谏之为义,义在爱惜。既在三事同,君亲宜一,若有不善,俱宜致谏。今就经记参差,有出没难解。案,《檀弓》云:‘事亲有隐无犯,事君有犯无隐。’则是隐亲之失,不谏亲之过,又谏君之失,不隐君之过,并为可疑。旧通云:君亲并谏,同见《孝经》,微进善言,俱陈记传。……父子真属,天性莫二,岂父有罪,子向他说也?故孔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故云‘有隐’也。而君臣既义合,有殊天然。若言君之过于政有益,则不得不言。……又父子天性,义主恭从,所以言无犯,是其本也。”[4](P65)皇侃认为,如同致谏君主一样,对待父亲之过也需要致谏。因此,皇侃对《礼记·檀弓》所云“事亲有隐无犯,事君有犯无隐”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这也是援引“君亲并谏”的“旧通”佐论自己观点的原因。一般而言,君亲“并宜微谏”,但若父亲犯了大过,子谏亲三次,若不见从则“号泣而随之”;而谏君主则不同,君主若是三谏不从则逃离于君主。为什么同样是致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皇侃认为父子关系天然自成,子恭从亲属于自然天性;而君臣虽然义合,但已非是天然即有的关系了。 综上所论,在皇侃看来,父子相隐并不是说儿子任凭父亲犯错,而不去进行任何纠误。恰恰是基于父子生而即有的亲情,父子相隐,融情于法,不仅符合孝之本义,而且与礼法建立的基础,及其社会教化的目的不相违背。 三、“以孝友为政” 在皇侃思想中,孝除了为“事亲之目”之外,还展现于社会政治生活中。拟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 (一)“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 皇侃疏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时,云:“孔子举所异者,言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4](P232)皇侃除了强调因父子间具有自然至情,而父子相隐,维护人伦大义外;也强调行孝悌是社会风政的重要内容。事实上,以孝悌作为社会治化的内容,早在皇侃之前便被统治者视为社会教化的法典。诸如汉宣帝于元平四年五月,下诏云:“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9](P251)甚至在汉代也出现父子一方犯罪,而告发的另一方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情况。诸如刘爽告发其父衡山王刘赐谋反,以“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9](P2156)。可见,从社会实践上看皇侃“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融情于法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皇侃之论则是试图从孝的本质与功用上为其思想的合理性作出阐述。 在疏释《论语》“或问孔子子奚不为政”章时,皇侃云:“善父母曰孝,善兄弟为友。……言人子在闺门,当极孝于父母,而极友于兄弟。若行此二事有政,即亦是为政也。……言施行孝友有政,家家皆正,则邦国自然得正。亦又何用为官位乃是为政乎?……行孝友有政道,即与为政同,更何所别复为政乎?”[4](P30)皇侃视行孝友之事为政,其因有二:其一,在儒家传统里,齐家是治国的前提,其中也蕴藉着为政的理念。如《大学》所谓:“治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人子在家庭中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此二事恰是修身与齐家的内容,进而可以为政,即以行孝友去推及到为政。其二,行孝、友二事与为官为政在义理上是相合的。这也是皇侃最为关注的内容。皇侃疏释《为政》章时云:“为政者,明人君为风俗政之法也。谓之‘为政’者,后卷云:‘政者,正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又郑注《周礼·司马》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4](P18)显然,皇侃赞同“政,正也”的观点,认为为政引导社会风化,“政所以正不正”。据此看,行孝友虽为整饬家庭事务,但可以使家庭和谐,符合有物有则之“正”,即如皇侃所谓“家家皆正”。以“家家皆正”推而广之,“邦国自然得正”。故皇侃云:“行孝友有政道,即与为政同,更何所别复为政乎?” 可见,皇侃孝论不是孤立地就孝论孝,而是将孝置于家庭伦理与社会治化中论述,将以行孝友看作社会治化的基本因素。 (二)“以孝事君则忠” “孝”“忠”并论在《论语》已有展现,如云:“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在《孝经》中则出现了四次论“忠”,即:“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明事其上”,“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 皇侃对《论语》与《孝经》的疏释也涉及到“以孝事君则忠”的问题。故择其要,作一疏解。在疏释“其为人也孝悌”章时,皇侃云:“言孝悌之人,必以无违为心,以恭从为性。若有欲犯其君亲之颜谏争者,有此人少也。然孝悌者,实都不欲。必无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亲有过,若任而不谏,必陷于不义。……夫孝者不好,心自是恭顺,而又有不孝者,亦有不好,是愿君亲之败。故孝与不孝,同有不好,而不孝者不好,必欲作乱;此孝者不好,必无乱理,故云‘未之有也’。”[4](P5)在皇侃看来,孝悌为仁之本,一切德行均以此为基础。而行孝者具有无违、无欲、恭从的品性,不仅对父母如是,推及到君主也是无欲、恭从,故很少会出现有意犯上的现象。但是皇侃又认为面对君亲之过,孝悌之人也需要微言上谏,进行规劝匡弼。而此种上谏行为并非是“犯上”,而是避免君亲陷于“不义”的行为中。与之相反,不孝之人即便表现出恭顺之貌,但其心有作乱之欲,其不好犯上恰“是愿君亲之败”。可见,当皇侃将孝悌视为忠君,不犯上作乱的基础时,即认同了移孝为忠的思想。这也与《孝经》所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开宗明义章》)一脉相承。行孝始于奉侍父母,推广于侍奉君王,最后扬名立身。这即所谓的“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忠孝并举,将家庭伦理与国家伦理相结合。 在疏释《孝经·天子章》“子曰”时,皇侃又云:“上陈天子极尊,下列庶人极卑,尊卑既异,恐嫌为孝之理有别,故以‘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贵贱有殊,而奉亲之道无二。”[2](P119-120)考之《孝经》,“子曰”一词共出现十五次,且或置于在章首,或次于介绍背景及向孔子提问之后。《天子章》首称“子曰”,而其后《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四章则不称“子曰”。此五章虽内容不同,但均是论孝,即所谓的“五等之孝”(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从内容上看,各章也具有一定的逻辑性。故皇侃认为“子曰”通冠五章,也是有道理的。五等之孝,因其对象不同,相应的行孝规范也不同。现存皇疏甚为简略,但可以辨析出皇侃立论基础在于将孝、忠合论,将家庭伦理与国家伦理相结合。 综上,在对《论语》、《孝经》的疏释中,皇侃从自然人性论出发揭示孝的本质,视孝为“仁之本”、“百行之本”、“事亲之目”、为政之基等,有效地揭示了孝的意义结构。身处南朝玄学流宕、三教盛行之时,皇侃对孝的疏释不仅皇侃反映出皇侃的儒学立场,也反映出儒家的孝、忠等纲常伦理依然是稳定政治秩序、弘扬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深入人心。 ①马国翰《玉函山房辑轶书》依邢疏辑得18条,陈金木则辑得24条,且对佚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辨。(参见氏著《皇侃之经学》,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117~123页)陈一风《孝经注疏》研究认为邢昺辑得22条。笔者将马国翰、陈金木辑文与邢疏进行对比后,认同陈说,故文中所引皇侃《孝经义疏》均取于陈氏所辑佚文。 ②释“经”为“常”,皇侃之前已有此说。如:《尚书·大禹谟》“宁失不经”,孔安国传注“经,常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政有经矣”,杜预注“经,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