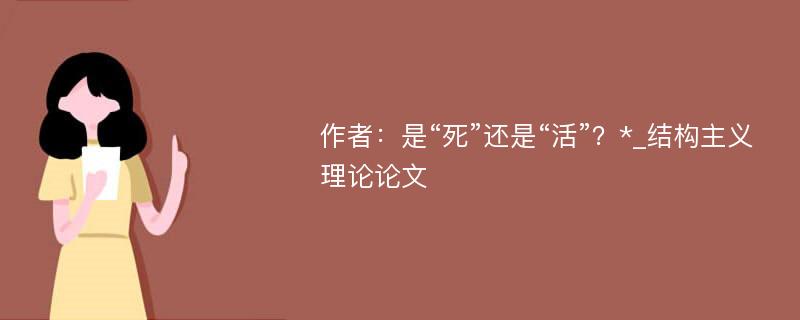
作者:是“死”去还是“活”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8年,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宣布了“作者之死”。[①]从此,理论界关于作者的“生”“死”问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首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背景进行考察,然后分析作者难以“死”去的原因,最后提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与产生的背景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代文论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根源。巴特本人认为,这个问题历经瓦莱里、普鲁斯特、超现实主义一直可追踪到马拉美。[②]但事实上,这些人即使与反作者论有关也关系不大。普鲁斯特尽管反对传统的传记式批评,却从未直言宣称作者之死;瓦莱里赞成作者对浪漫的灵感实行控制;而超现实主义则从未对批评理论有过明显的直接的影响。唯有马拉美可被看成一个先锋人物,因为他表现过作者隐退、作品自主的思想倾向。他说,一部诗集的结构一定自始至终有其内在的必要性贯穿其中。这样,契机与作者就都被排除在外了。他还认为诗歌中的某些对称来自一首诗中诗行间的关系及一卷诗中各首诗间的关系,并延伸于一卷诗之外,直奔其他诗人。[③]
按马拉美的说法,文本的意义该是来自于语言本身的力量,来自于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而无作者的主体干涉。这个思想已经显露了作者不在场的端倪。然而,批评家们认为,将马拉美作为“作者死去”的始作俑者尚不能成立,理由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历史必然性;而且马拉美仅仅是勾画一种文学理想,并非正式提出一种写作理论。
那么让我们另辟蹊径,寻找“作者之死”的来龙去脉吧。
1.“作者之死”与“上帝之死”
19世纪的“上帝之死”与20世纪的“作者之死”说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二者都隐含着一种对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权威的离叛。作者之于文本如同上帝之于世界。他是文本的起因,源泉和主人,文本一系列的意义最终都归结于他;文本的生成、意义、目的和合理性都只能在他身上找到。巴特本人也承认他的口号有着一种弑神的类似含义。他指出,“作者之死”的先声便是尼采《快乐的智慧》中那个疯子喊出的“上帝死了”。[④]他毫不掩饰地说出了作者——上帝这一类比的目的,声称“作者之死”给予了所谓反神学活动的自由,这个活动具有真正的革命性,因为拒绝将意义固定不变最终就是拒绝上帝及其三位一体——理性、科学、法律。[⑤]
尼采表达了他在上帝死去时的欢欣,并欢呼由此而来的自由和解放:
老朽的上帝一死,我们的心便洋溢着感激,惊讶,预感和期待。地平线仿佛终于重新开拓了,即使尚不明晰;我们的航船毕竟可以重新出航,冒着任何风险出航了,求知者的任何冒险又重得允许了,海洋,我们的海洋又重新敞开了,也许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开阔的海洋”。[⑥]
上帝一死,便有了新的希望。这新的霞光就“在一切价值的重估之中,在从一切伦理评价解放出来的自由之中,在一切历来被禁锢、被蔑视、被诅咒的事物的肯定和信仰之中”。[⑦]
一旦文本从作者手中解放出来,也便成了一片“开阔的海洋”。“作者之死”是走向拒绝将最终意义归结于文本的首要和必要的一步。将作者强加于文本就是将过时了的一元论强加于生机勃勃的多元世界,就是对上帝死后所开拓出来的差异共现,色彩纷呈的世界的禁锢。一旦文本冲破作者一统天下的桎梏,我们也突然发现它原来是“一个多维度的空间”。[⑧]各种意义在其中融合、冲突,展现出一个更为绚丽的世界。
显而易见,巴特的“作者之死”与尼采的“上帝之死”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这19世纪后期的撒旦似的反叛并不是引发巴特的“小小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唯一原因。
2.“作者之死”与“意图的迷误”
按照传统,作者的意图被认为是文本意义的基础,文学批评的目的也就仅限于挖出作者在文本中无所不在的意图(有时作者亲自出场道明意图,有时假人物之口说出初衷)。批评家的重要任务便是找出作品之中的作者。作者一旦找出,文本的解释也就大功告成,批评家于是胜利在握。为了找到作者,批评家瞪大了眼睛,审视作者的传记,由作家而作品,由作品而作家进行忙碌的实证,甚至由蛛丝马迹而生发,而附会,他们只是忘了文本本身这个文学批评中极为重要的东西。
这种“传记批评法”随着“新批评”的出现而受到了严重的挑战。1954年,新批评的主将比尔兹莱和维姆沙特发表了论文《意图的迷误》。他们认为文学作品在其文本的文字中已蕴含了所有理解它的必要信息,因而诉诸于作者的意图是与阐释不相干的,甚至会使人误入歧途。因此在文本阐释中排除作者是完全有道理的。
新批评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如韦勒克、兰色姆、瑞恰兹、燕卜荪等,也从理论上的论证和实践上的成功,为新批评推波助澜,从而使文艺学从传统的考据转到对文本的注意,树立了文本的主体形象,使作品及其形式“显豁而独秀”。
3.结构主义的影响与“作者之死”
结构主义于本世纪60年代兴盛于西方文坛。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总结了结构主义的三大特征:整体性、转换性、自身调整性。[⑨]其整体性结构即指任何事物的结构是按照组合规律有程序地构成的一个整体。语言学家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前者是社会现象,后者是个人行为。“言语”是“语言”系统中的部分,这个部分本身没有意义,只有把它放到总体中去考察才会显示其意义。《结构主义诗学》的作者卡勒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把诗的读解分为三种程式:首先是诗具有普遍性,读诗须读出诗的普遍性情趣,而不囿于诗中的作者个人成分;其次,诗具有整体性,诗人把缺乏完整性的日常语言进行加工,从而将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整体,读诗就得从整体观念出发,使整体与各部分得到正确的完整的阐释;第三,诗具有意念性,即诗往往有言外之意,象外之象,读诗就是要见出这种丰富的内蕴。[⑩]巴特在《论拉辛》中,运用结构主义的“二项对立”方法对拉辛的人物进行分析,认为拉辛的人物在整体结构中显示出差异,他们因地位、作用、性别、自由程度或家族的不同而显示出性格的两极组合,即正负两面的二项对立的性格结构模式。[(11)]
总之,结构主义重文本的整体性及内在的关联性,重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关联性,认为意义就在这种对整体的观照及二项对立中显现,而不是作者的赐予。他们不屑于传记索引式的批评,反对对作品进行社会、历史的评判,认为这些都是对文学的外缘研究,而不是对文学本身的因素作出审美判断。这个思想无疑对“作者之死”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4.读者中心理论与“作者之死”
如果说传统的观念是从作者身上挖掘作品的意义的话,那么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则从文本本身出发,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对作者中心进行了否定。而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阅读现象学、读者反应论及接受美学和更早一些出现的阐释学则以读者为中心去研究作品,认为作品的意义来自读者,从而从读者的角度动摇了作者——上帝传统的根基。
阅读现象学源于现象学,这一派别的代表之一是英伽登。他把海德格尔的“意向性”理论应用于文艺学,认为艺术品是纯粹的意向性对象,其属性只有通过读者的想象力补充完备,因此,艺术品成为自足体必须要有读者的参与。换句话说,作品的具体化,需要并依赖读者的阅读行为。
阐释学同样研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要了解整个文本的意义,必须要有对它的前理解(Vormeinung)。[(12)]前理解包括在理解之前阐释者的前拥有,前观点和前假定。例如我们在理解一部作品之前,就已经有了有关文学作品的知识,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观念,有对社会生活的印象、概念,有了进行作品阐释的较确定的方式方法,有对作品的初步看法和对其性质的假定(如假定某部作品表现了主人公精神的崇高,或表现了人文主义精神等)。基于这种前理解的阐释,就不是阐释者对文本的被动反映,而是一种积极、主动、创造性的参与。
接受美学更是专注于研究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过程中的一系列因素与规律,接受美学认为,作者是文艺信息的发送者,读者是信息的接受者,作品是信息的媒介,研究文艺就必须研究文艺信息流通的整个过程。接受美学的主将之一伊塞尔说:“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作品之中,等待阐释者去发现的神秘之物。”[(13)]尧斯与伊塞尔异曲同工,认为意义的来源有二:一是作品本身,二是读者赋予,作品中有很多空白与意义的不确定性,有待读者具体化,完整化,没有读者的这种实现过程,文本仍只是孤立的存在,如同藏之深山的玉石。说到底,读者的赋予是主要的,决定性的。读者反应论者费希则更取一种极端的态度。他把文本本身也看成是读者的产物,因为诸如格律形式,押韵方式等等都只是阐释策略的结果。
不管他们的论点有着何等程度的不同,上述各种理论流派都高扬读者的旗帜,突出读者在文本意义阐释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5.“作者之死”的政治意义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政治相关联。“作者之死”也反映了一种政治倾向。传统上的作者就意味着权威,这个权威地位在西方往往被白人男性和资产者占领着,而人口中的大多数却被拒之门外。“作者之死”,在某种意义,就意味着推翻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资产者的高高在上,意味着政治解放。传统作者权威一倒,就意味着“黑人文学”,“妇女文学”、“下层文学”的兴起。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之死”不正道出了各种受压迫者要求政治解放的心声吗?
6.“无意识”的挑战
在人们对无意识领域进行探索之前,总相信凡事都有一种直截了当的意图或动机,它构成了人类性格与行为间的简单关系。随着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复杂心理的发现,这一信念消失了。人们发现,在显露于外的口头或笔头表达的后面,隐藏着复杂的意图。换言之,表露于外的也许并不是真实的思想或意图,或不是全部的思想与意图。因此,言语的表述与作者的真实意图间就产生了不一致的现象,而这种不一致使得将文本看成是作者的真实声音的做法显得荒谬。于是,文本怎样,读者与批评家就怎样对待,而不把它看成是作者意图的证明,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上述六种或哲学或文学或社会的反权威的理论或思潮尽管各自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之点:都把作者排除在外,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为“作者之死”的前台声音构筑了背景。
二、作者:是死去还是活着?
从“作者之死”的提出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六种力量结成同盟,要判处作者的死刑,在这一片众声喧嚷中,巴特只是起了一个发言人的作用。作者一死,便没有了作者唯我独尊的霸气;就有了读者的“崭露头角”,就有了动力阅读,读者赋予作品的意义;就有了对文本本身的注意而不是传记实证考据法的阐释;就避免了对文本中的作者意图进行盲目的探究;就有了受压迫者的政治解放,精神解放,等等。
那么,作者之死就顺理成章,必死无疑了?
但有很多问题使得作者拒绝死亡的力量甚于判其死刑的力量。作者之死,其死也难。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作者在写作时的主体作用。
在《作者之死》一文中,巴特声称,作品是那种中性的、混成的、倾斜的空间,我们的主体就从这里滑掉了。他认为,在作品中说话的不是作者,而是语言,因此,作品再也不能称为有主体干预的“记载”、“再现”、“描写”。写作主体只是对业已存在的某种姿态的模仿,永远不能标新立异。他为此而用了“Scriptor”一词来代称author。按照巴特的说法,写作就是涂鸦者不带任何意图,毫无任何动机的文字堆砌。
我们诚然不能像考据学家那样把一切说成作者的意图,但我们却否定不了作者写作时的主体性,不能否认作者在文本中的存在。
这种主体性表现在作者对题材的选择和对素材的重新组织加工。
生活给作者提供了不可胜数的题材,然而,作者只选甲而不选乙,这便表现了他的侧重点和意向性。亨利·詹姆斯在写《一幅淑女的画像》之前,曾写信给朋友说,他要写一部小说,表现一个天真、单纯、充满热情和求知欲望的美国少女是怎样在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而又狡黠世故的旧大陆成了牺牲品的。如果我们在这部小说中读到了这一层,那怕是多种解读中的层面之一,我们就不能否认作者意图的存在。事实是,小说主人公阿切尔小姐确是这样一个人物。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任何头脑清醒的写作者,写作之前总要运思筹划,写作时总围绕着某个主旨,作品(不管是政论文还是文艺作品)至少在总体上体现了初衷,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不争的事实。“文以载道”和“文如其人”正说明了作者与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关系。至于由于文字本身的歧义性(因而也是丰富性)和时空的变易、审视者的不同等因素而造成了多种解读,这也是很自然的。正如造地运动造成了一座庐山,而观赏者能“横着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样,写作者的作品不变,而阅读者因角度不同却会见仁见智。而能使他们产生不同见解的客观存在就是文本,这一受作者的意志支配而生成的产品。
除了18世纪一些作者跑到前台自报家门,坦露心迹的小说以外,还有一种小说无疑深深地打上作者的烙印,使读者感到他/她的存在,那就是带自传性质的小说。以康拉德为例,他15岁表示了航海的愿望,17岁正式出海,几十年的航海经历是他日后写作航海小说的不竭泉源。若问,康拉德为何只写航海小说,而不写航空小说或打猎小说,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航海是他最熟悉的,是他的生活经历。小说世界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这种虚构决离不开生活,这是作品的最终源泉。那怕虚构的是天堂或地狱,神仙和魔鬼同样着人世装,说人世话,用人世的法律去量刑。而按“作者之死”论者的看法,康拉德写航空小说与写航海小说一样地可能,因为写作只是“语言说话,而无作者因素的介入。”
不仅在题材的选择上,在文本的组织上也可看到作者的存在。如果说是“语言在说话”的话,我们应立即加上:“但不是语言随便说话,而是按作者的意图说话”。
众所周知,客观事件按线性时间发生,然而在文本中,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作者往往对事件的发生作时间上的重新安排,因而就出现了“倒叙”、“从中间开始”等多种时间倒错现象。还有,叙事视角的选择能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作品中或褒或贬,或扬或抑等,种种效果,正是作者利用其自由,借视角控制帮助达到的。
文辞的选择,句式的长短,修辞的运用,久而久之,皆成风格。故谈起繁复冗长,我们会想到亨利·詹姆斯;而谈起精练简约,就想起海明威。真是论其文如见其人;甚至精神气质,皆入文中,故有中国诗圣杜甫的“沉郁顿挫”和诗仙李白的“骏发飘逸”。
文章是怎样凝注了作者的苦心,渗透了作者的经历和情感,连宣称“上帝死了”的尼采也满怀深情地承认:“每一字都深深来自我的人生经历。有些字充满了痛苦,很多字则是蘸着鲜血写出来的!”
其实作者的意图如何,是否承认有何意图,这更是一件社会的事。作者一旦署名发表了某部作品,就等于他与社会签了一项契约,社会就要求他承担有关道德、伦理、政治、法律宗教等的责任。这就不是“作者之死”论者的所谓文字的游戏了。福柯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他说,作者签名以使作品合法化,同时也是承担责任。[(14)]
还是让我们以实例为证吧。
1989年,英国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出版了他的《撒旦诗篇》,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场轰动。伊朗的宗教权威们认为该书是对伊斯兰教的侮辱和亵渎,要对作者处以死刑。拉什迪四处躲藏,后来由于伊朗出于外交考虑,方才免了这“作者之死”。其时,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们正在讨论“作者之死”这一命题,于是,在沙龙、在酒吧或是别的公开场合,人们都谈论着“作者之死”这个严肃的玩笑。[(15)]这件事也让人们清醒过来,重新思考问题。比如:作者身份真的涉及人命,这种事该怎么认识?批评家怎样面对写作引起的责任?史毕瓦克(Gayatri Spivak)的回答是:读《撒旦诗篇》回避不了关于作者的政治含义问题。[(16)]而德里达则一点也不坚持文本中的“作者虚无”之说,倒是认为“作者过多地存在,在文本中由作者将作者推上舞台。”[(17)]
最具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耶鲁大学解构主义的班头德·曼(Paul de Man),1987年底,《纽约时报》上刊出了一篇短文《在纳粹的文件中发现了耶鲁学者的文章》。这篇文章导致了人们对德·曼作为一位理论家,对他所倡导的解构运动和他将文章与作者分开的一贯主张的伦理意义进行质疑。
德·曼在他的理论生活中一贯否认作者的生平与对他(她)作品的解释有任何关联。在其理论前期,他采取了现象学的观点对待作者,认为自我在其超验主体的构成中没有任何传记性内容:没有个人履历,也没有经历的问题;后期他作为一个解构主义者,则反对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写作主体,不管是经验的还是超验的。
德·曼的纳粹丑闻既出,人们如梦初醒,不再把他对传记性的否认看成是无私的理论阐述,而是一种处心积虑的自我保护行为。以堂皇的理论外衣出现,他就可以暗渡陈仓,逃避他历史上的那个自我,甚至将其化为乌有。
德·曼想借语言逃遁,用心良苦,但最终又是语言背叛了他,欲盖弥彰。
德·曼的例子至少可以说明下面几个问题:一、写作并不是“此时此地”的事,写作行为一旦完成,就与作者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不是从此与作者了无瓜葛;二、传记性事实与作品关系密切,作者的生活背景是了解作者写作意图的重要来源;事实上,对德·曼及其理论的重新评价就是基于对他生平的重新发现之上的,而德·曼的辩护者也以德·曼的生活背景为根据为他鸣不平。这些都恰好说明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紧密关系。三、作者一旦在作品上署上名字,就意味着他将承担作品所产生的道德、法律、伦理等方面的责任。而社会也认定作者的这种责任;四、在“作者之死”的口号声里同时就响着“作者的复活”的声音。越是宣布“作者之死”,作者的概念越是显得生机勃勃。君不见,罗兰·巴特宣布了“作者之死”,而作为这一宣言的写作者的罗兰·巴特不正被引为权威而声名沸扬吗?巴特没有“死”去。作者也没有“死”去。
结语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本题目所提出的问题。作者是该死去还是活着呢?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不能作非此即彼的回答。首先我们应该对“作者之死”论的合理性作出客观的评价。这种理论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它使文学批评的注意力从传统的“作者中心”转到了对作品和读者的关注。它使批评从此不再是关于作者的传记和考据。作者也不是意义的唯一来源;它确立了文本为审美客体的地位。同时,从信息流通的全过程强调了读者在作品接受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它的致命缺点在于,在为作品和读者的登场鸣锣开道的时候,它采取了极端的态度,彻底否定了作者在作品中的存在,这样就否定了作者在创造作品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进而否定了作品风格的存在,否定了作者应承担的道德,伦理、法律、政治等责任;也否定了仍然存在的某种意义上的作者的权威作用(我们引用权威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就是作者权威作用的表现,甚至作者签名售书也是作者权威的表现:读者慕名而来,作者凭其名声促销)。只要我们不带偏见,承认事实,那么我们应该承认作者(包括由此而来的作者身份“authorship”)和权威(authority)的存在。当然,承认作者的存在并不等于承认作者——上帝的存在。
承认作者的存在,又承认它的“不在”,同时承认包括作者在内的多元存在,这才是研究作品发生和作品接受时应取的态度。
* 本文承蒙申丹教授和周小仪副教授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Roland Barthes,"The Death of the Author",in R.Barthes,Image-Music-Text,trans.S.Heath(Glasgow:Fontana/Colins,1977).
②Sean Burke,The Death & Return of the Author,(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2),p.8.
③Stephane Mallarme,"Crisis in Verse"in T.G.West trans.and ed.,Symbolism:An Anthology,(London,Methuen,1980),pp.1-12.
④See Friedrich Nietzsche,The Joyful Wisdom,trans.Thomas Common(Edinburgh:Foulis,1910),pp.167-9.
⑤Roland Barthes,op cit.,p.147.
⑥Stephane Mallarme,op.cit.,p.276.
⑦尼采:《瞧,这个人》,转引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67页。
⑧Friedrich Nietzsche,op.cit.,p.146.
⑨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2页。
⑩Jonathan Culler,Structuralist Poetic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5).
(11)Roland Barthes,On Racine,trans.Richard Howard(New York:Octagon Books,1977).
(12)参见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246—260页。又见Wilfred L.Guerin et al.,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P,1992),p.296.
(13)伊塞尔:《文本的召唤结构》,载瓦尔宁编:《接受美学》,236页。
(14)Maurice Biriotti and Nicola Miller,ed.,What is an Author?(Manchester,Manchester UP,1993),p.9.
(15) (16) (17)M.Biriotti et al.,op.cit.,pp.9,10,103-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