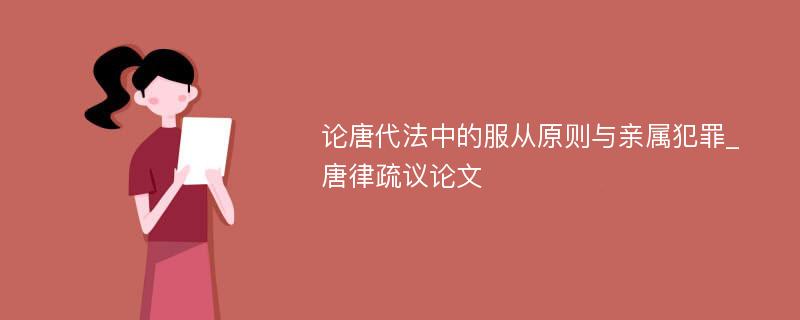
略论唐律中的服制原则与亲属相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律论文,属相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丧服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以为死者服丧的形式,规定亲属范围,指示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一项重要礼仪习俗。受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而完善起来的中国封建家族制度,以父系家族为基本形式,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为有服亲,亲属成员死后为其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丧服质地的粗细、服丧的期限及守丧礼仪的不同,将有服亲属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五服”制度。这种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丧服制度,既是以血缘纽带相联系的家族成员之间追悼亡者的礼仪习俗,又是衡量亲属间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基本标尺,更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所谓的法定亲属,基本上是以“五服”为标准的。魏晋以降数千年法律传承不绝的“准五服以制罪”原则,也是以这种丧服制度为基础的。(注:参见郑定:《中国古代的服制与刑罚》,《法律学习与研究》,第46页,北京,1987年第1期。)
“准五服以制罪”(注:《晋书·刑法志》称:《晋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原则是指以传统社会中的丧服制度(简称服制)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轻重的标准,又称服制原则。服制原则实质上是“同罪异罚”的原则在家族范围内的体现,即同样的犯罪仅因服制不同(实质上是因亲属间尊卑、长幼、亲疏不同)而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它在刑法方面的适用原则是: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依次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渐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亲属相奸,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注:参见郑定:《中国古代的服制与刑罚》,《法律学习与研究》,第47—48页,北京,1987年第1期。)
服制原则首次在晋律确立,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法律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起,是自汉代开“礼律融合”之先河以来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发展,它不仅体现了晋律“礼律并重”的特点,也是中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自西晋定律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就成为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充实与完善。至唐朝,服制原则在国家律典中得到充分而完备的体现,使唐律成为丧服法律化的最好范本。本文拟以《唐律疏议》为蓝本,分条析缕,疏理服制原则在唐律中的具体体现,以揭示丧服制度在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影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特征。
一、《唐律》中的亲等与五服亲等
(一)《唐律》中的亲等与五服亲等的异同
自西周以后的数千年中,中国丧服制度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各个时期关于具体的丧服礼仪、等级等,并非绝然一致。作为丧服经典著作的《仪礼·丧服》中的具体规则和标准,也非一成不变。比较《唐律疏议》与《仪礼·丧服》涉及亲等的内容,二者之间亲等就不完全一致:
第一,袒免亲。袒免亲是指本宗五世亲属,已经超出五服之外。(注:《礼记·大传》云:“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在《仪礼·丧服》中,仅经文一处提到“袒免”;“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归则已。”而《唐律疏议》则详细列举了袒免亲的范围:高祖之兄弟,曾祖之从兄弟,祖之再从兄弟,父之三从兄弟,身之四从兄弟,三从侄,再从侄孙。(注:《唐律疏议·户婚》“诸尝为袒免亲之妻”条。)
第二,缌麻亲。唐律载缌麻亲有四:曾祖之兄弟,祖之从兄弟,父之再从兄弟,身之三从兄弟。(注:《唐律疏议·名例》七之疏。)此与《仪礼·丧服》相同,不过后者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服丧对象。
第三,小功亲。唐律载小功亲有三:祖之兄弟,父之从兄弟,身之再从兄弟。(注:《唐律疏议·名例》七之疏。)此与《仪礼·丧服》同,不过后者不限此范围。
第四,大功亲。唐律仅身之从父兄弟。(注:《唐律疏议·名例》六之疏。)以上各同辈兄弟之直系尊属(非已之直系尊属)与己身之各服等,从各同辈兄弟与己身之服等。此与《仪礼·丧服》同,不过后者不限此范围。
第五,齐衰亲。唐律改“齐衰”为“期亲”。本来“齐衰”服叙包括民为君,并非亲属关系,而且法律上父母并列同论,不以斩衰、齐衰区分其尊卑,因此法律上以“期亲”代“齐衰”。“期亲”之本义,指夫为妻,父为子,不杖期亲属(己身之兄弟,与伯叔父、侄)。但法律上往往将曾祖父母(唐为齐衰五月)、高祖父母(唐为齐衰三月)与“期亲”同论。如《唐律疏议·名例》第52条:“诸称‘期亲’及称‘祖父母’者,曾、高同。”
第六,斩衰亲。唐律无“斩衰”之称,涉及斩衰之亲时,往往直接称呼亲属名称。原因在于:首先,由于丧服等级中“斩衰”包括臣为君,非亲属关系。其次,丧服上“斩衰”包括父为长子,但在法律上则极为重视尊长卑幼差别。父犯子与子犯父在定罪量刑上截然不同,况且法律上长子等同于诸子,已无特殊意义。再次,法律上犯母与犯父同论,父母并列,非“斩衰”所能包容。因此历代法律中均未出现过“斩衰”之称,而是直接称父、夫等。
《唐律疏议》中之所以出现具体的亲属称谓,而不是均以丧服等级替代,其原因一是由于某些服等涉及到非亲属关系的政治等级,如斩衰、齐衰中的臣为君、民为君服,故不用“斩衰”之名,“齐衰”改用“期亲”;二是由于法律上之亲等较礼制中之丧服更为注重现实中之亲属关系,因此在适用上凡不能以期亲、大功、小功、缌麻、袒免等一般服制称呼概括者,就以具体亲属称谓代替。
(二)服等不同但在法律上的效果相同的情形
1.父与母、祖父母与父母。在丧服等级上,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丧服是不同的。为父斩衰,为母齐衰三年(父在齐衰一年),为祖父母齐衰不杖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律中,子孙对父母、祖父母有犯,法律效果是相同的(注:参见郑定:《中国古代的服制与刑罚》,《法律学习与研究》,第46页,北京,1987年第1期。)。如《户婚律》:“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斗讼律》:“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
2.为曾祖父母、高祖父母服齐衰五月、三月,但法律中与期亲尊长同。如《名例律》:“诸称‘期亲’及称‘祖父母’者,曾、高同。疏议曰:称期亲者,《户婚律》:‘居期丧而嫁娶者,杖一百。’即居曾、高丧,并与期同。及称祖父母者,《户婚律》云:‘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徒三年。’即曾、高在,别籍异财,罪亦同。故云‘称期亲及称祖父母者,曾、高同。’”
3.为曾孙、玄孙服仅缌麻,但法律中与孙(大功)同。《名例律》:“称‘孙’者,曾、玄同。疏议曰:《斗讼律》:‘子孙违犯教令,徒二年。’即曾、玄违犯教令,亦徒二年。”但法律中注明“曾、玄孙者各依本服论”除外。
4.为外祖父母服小功,为夫之兄弟(即嫂叔)及兄弟妻(即妯娌)服小功,为外孙、妇孙服仅缌麻,但在法律中往往与大功亲同。如《名例律》:“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疏议曰:……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服虽轻,论情重。”
5.服制上男子出继为本生亲属降服,女子出嫁为本宗亲属降服,但法律中规定若与本生、本宗亲属相犯,各依本服,不得以出降依轻服处罚。《名例律》:“称‘袒免以上亲’者,各依本服论,不以尊压及出降。疏议曰:皇帝荫及袒免以上亲,《户婚律》:‘尝为袒免亲之妻而嫁娶者,杖一百。’假令皇家绝服旁期及妇人出嫁,若男子外继,皆降本服一等,若有犯及取荫,各依本服,不得以尊压及出降即依轻取之法。”也就是说,皇帝虽同于古之诸侯旁亲绝服,但皇帝袒免以上亲属仍可享受“议亲”的特权,犯罪可获得减免的特权。为人后之男子、已出嫁之女子虽为本生、本宗亲属降一等服,但如相互侵犯,仍依本服处罚。(注:参见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217页。)
6.长子与众子法律效果相同。而在服制上,父为长子斩衰、母为长子齐衰三年,为众子期。但法律中长子与众子同为期亲,法律中称“子”之处,即包括长子在内。
7.服制上为同居继父齐衰不杖期,为不同居继父(先同居后异居)齐衰三月,但法律中同居继父视同小功尊亲,不同居继父视同缌麻尊亲。《斗讼律》:“殴伤继父者(原注:谓曾经同居,今异者),与缌麻尊同;同居者,加一等(原注:余条继父准此)。疏议曰:同居者,虽著期服,终非本亲,犯者不同正服,止加缌麻尊一等。注云‘余条继父准此’,谓诸条准服尊卑相犯得罪,并准此例。”可见继父在法律中亲等降低是整部法律的基本准则之一。
服等不同而法律效果相同,有的提高,有的降低,其变化规律大致是:以卑犯尊时,提高直系尊亲的法律效果以加大对尊亲属的保护,同时也提高直系卑亲的法律效果以加大对卑亲属的处罚范围;因宗法原因造成服制变化与不同的,在法律效果上重新以血亲进行衡量,如出降、长子与众子;以义服(注:义服,指非因血缘、而是“因义而合”而成的服制关系,类似如法律拟制而成的亲属关系,如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养父母与养子女等。)而服者,一般降低其在法律上的效果,如继父。这反映了唐律突出血亲与尊卑差异,而弱化宗法影响的倾向。
(三)服等相同但因尊卑长幼而致法律上的效果不同
1.旁系亲属间服等相同但因尊卑而量刑不同。服制上,直系亲属之间尊卑之服不平等(如孙为祖父母齐衰不杖期,祖父母为孙仅大功),而旁系亲属尊卑之间制服同等(如侄为伯叔父母制服不杖期,伯叔父母为侄报服也是不杖期)。但法律上不仅区分直系尊卑,旁系也区分尊卑而量刑迥异,亲属之间相犯比照常人而言,凡卑犯尊者加重处罚,凡尊犯卑者则减轻处罚。如《贼盗律》:“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即尊长谋杀卑幼者,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徒下年);已伤者,减一等(流三千里);已杀者,依故杀法(绞)。”
2.同辈亲属因长幼而量刑不同。服制上同辈亲属之间除未成年者依殇服降等外,同辈成年亲属间服制相等,不因年龄长幼而有区别。但法律上凡同辈亲属均区分长幼而量刑不同,也就是说,不论是否成年,也不依殇服降等,只依本服并区分长幼,凡幼犯长量刑较常人加重,长犯幼则量刑较常人减轻。如《斗讼律》:凡弟妹殴期亲兄姊,徒二年半;殴伤,徒三年;骨折,流三千里;以刀刃伤,绞;殴死,斩。而兄姊殴弟妹伤及骨折或过失杀,皆不论罪;只有故意殴杀,徒三年;以刃故杀,流二千里。
《唐律》中的亲属对丧服亲等的变化,突出了血亲和尊卑长幼的差异、而弱化了宗法和以义制服的影响,对后世服制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唐律》中母与父同论,明初则服制上母与父同为斩衰亲;《唐律》中长子与众子同论,明初则长子与众子同为齐衰不杖期亲;《唐律》中未成年者不依殇服降等,明初则废止殇服。
二、《唐律》中纯因亲属身份而致罪的情形
某行为若在常人间进行本无犯罪可言,但若行为人与被行为人间具有一定亲属关系,则构成犯罪,这种纯因亲属身份而致罪者,我们称之为身份犯。英国著名历史法学家梅因曾说,从古至今的社会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古代社会本质上就是身份等级社会。中国古代社会也是典型的身份社会。在儒家的观念中,亲属为一体,亲族成员皆应“亲其亲”、“长其长”。亲属相犯有乖伦理,所受处罚理应异于常人。唐律就是一部典型的身份法、特权法。唐律受宗法伦理的影响,规定某种行为在凡人原本无非,但因其有亲属身份关系,而负刑事责任,所以,有无此种身份是决定犯罪成立与否的关键。身份在广义上包括行为人在法律上的一切特殊地位。所谓亲属身份,包括因血族及配偶的身份关系及其他身份关系(如男女、尊卑、老小、单丁、议、请、减、赎等)。
(一)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
《唐律·户婚》六:“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注:别籍异财不相须(注:“不相须”指“别籍”、“异财”可以各自单独成立,不必以另一行为存在为成立条件。)),下条准此。”律以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为犯罪,且为不孝,而入十恶(名例六—七)称祖父母父母在,曾、高在亦同。若子孙别立户籍或分异财产,二者有其一,即有籍别财同或籍同财异情形之一者,本罪使告成立,故注云不相须(疏)。此条是防止对尊属供养有阙,或有违承欢孝之道,礼所不许,律亦予禁止。(注:参阅《名例》六,《斗讼》四七。)
若是父祖命令子孙另立户籍,以及把子孙违法过继给别人当作后代的,该父祖要徒二年,而对子孙不予治罪。但父祖命令子孙分家财者不坐。(注:《户婚》六:“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子孙不坐。”)
父祖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之规定,唐律之后稍见放宽,如《元典章》户部门:“自后如祖父母、父母许令支析别籍者,听。”《大明律·户律·户役门》:“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但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清律与明律同,别增附注:“或奉遗命,不在此律”,“其父母许合分析者,听”。(注:《大清律辑注》户律,户役门。)
(二)父祖被囚而嫁娶
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户婚三一)。此系因尊长处于某一种状况下,所科以子孙之刑事责任。但受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盖祖父母、父母既被囚禁,锢身囵圄,子孙嫁娶者,名教不容(疏)。因嫁娶原为喜事,依礼有钟鼓琴瑟之乐,而父祖囚禁,骨肉亲切,子孙应同分忧苦,违之依父祖犯罪轻重而处罚之。若娶妾或嫁为妾者,准减三等(参阅户婚三0)。
若期亲尊长主婚,即以主婚为首,男女为从。若余亲主婚,因事在主婚,则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参阅户婚四六)。其男女被逼,或男十八以下,在室之女,并主婚独坐(参阅户婚四六)。注云: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即子孙奉命为亲,律不加罪(参阅户婚四六)。依令,父祖被囚,不得宴会(户婚三一疏)(注: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之《仪制令》。),凡违反本条之罪,其婚姻仍为有效,盖律无离异之明文也。
(三)父祖及夫被囚禁而作乐
唐律规定,若祖父母、父母及夫,犯罪被囚禁而子孙及妻妾作乐者,徒一年半(职制三一)。直系尊亲及夫,身处厄境,囚禁囵圄,为子孙及妻妾者,理宜分负忧危,乃竟而作乐,悖孝乖义,亏损名教,故治之以罪。
(四)父祖及夫被杀而私和
按照儒家的伦理要求,“父之仇不共戴天”,父祖及夫被杀,义不同天,作为人子,在父祖被杀的情形下,矢志复仇方合人子之道。不能复仇已经是孝道有亏,其有忘大痛之心,舍枕戈之义,与人私和更是不合天常伦理。所以,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大功以下,递减一等。受财重者,各准盗论(贼盗十三)。或竟有窥求财利而私和,自应予以处罚,籍维人伦。
虽不私和,知杀期以上亲,经三十日不告者,各减二等(贼盗十三);亦系基于血缘名分,期以上亲被杀,虽未私和,但经三十日不告者,律亦予处罚。
唐律以后宋刑统一仍唐之旧。(注:《宋刑统》贼盗“父祖夫为人杀”。)明律,则更为周详,清律因之。(注:《明律·刑律·贼盗门》:“凡祖父母、父母及夫,若家长为人所杀而子孙妻妾私和者,杖一百,徒三年。期亲尊长被杀而卑幼私和者,杖八十,徒二年。大功以下各递减一等。其卑幼被杀而尊长私和者,各减一等。若妻妾子孙及子孙之妇被杀而祖父母、父母,夫家私和者,杖八十,受财者,计赃准窃盗论,从重科断。”)
(五)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讳
传统伦理要求,“父为子天,有敬无犯”。对父祖的恭敬顺从,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方面,包括言语行为回避父祖的名号。唐律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徒一年(职制三一)。此系官称、府号,犯父祖讳,子孙冒荣居官之犯罪。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母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又府号者,谓省、台、府、寺之类。官称者,谓尚书、将军、卿、监之类。假若有人,父或祖名常,不得任太常之官(参阅名例二0疏)。果有此种情形之一者,为子孙者须回避之。并皆须自言,不得辄受。其有贪荣昧进,冒居此官(疏),即予处罚且免所居官;即因冒荣而迁任者并追所冒告身(名例二0)。又本罪所谓犯父祖名,并不包括高祖在内(参阅名例五二)。
(六)委亲之官
在儒家看来,“养”是孝道的最基本的要求。为人子孙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以孝养父祖为第一要务。在恪守孝道与个人利益、前途之间,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前者。唐律规定,父祖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自己出去做官、弃亲不顾者,徒一年(职三一),此系违犯孝道之犯罪。所谓老疾,指年八十以上或笃疾,依法合侍而现无人侍者,乃委置其亲而之任所而言(疏)。但移孝作忠,国而亡家,自古许为高义,故有正当理由,本罪非无例外:“即其有才业灼然,要藉躯使者,令带官侍,不拘此律。”(参阅名例二0疏及问答)委亲之官,除徒一年外,免所居官。
(七)同姓为婚
依唐律,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户婚三三)。同姓不婚之制,系同宗不婚之扩大形式,均为家族主义观念下之产物。此制可溯至周代,北魏时,法已有禁,至唐律,益加详备(注:戴炎辉:《唐律各论》第87页。)。礼记:“系之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同宗共婚即不得为婚,相婚者均罚之,(必要共犯),亦系典型的身份犯。惟同姓是否同宗,则难以确证,故律规定,仅同姓即予科罪,俾免滋疑,谅亦为同宗禁婚扩大至同姓不婚之立法理由之一。疏云:“古者,受姓命氏,因彰功德,邑居官爵,事非一绪,共有祖宗迁易,年代浸远,流源析本,罕能推详”。姓氏纷杂,历久而益繁,且古代有时“因官受姓名,能养马者,为司马。若掌仓有功,为仓氏。若封于唐,谓之唐氏,居于范邑,即为范氏。如此之类颇多,不可概举也。”(注:《释文》卷十四,释“受姓命氏条”。)在实际上,自有不少复杂情形,如鲁、卫、文王之昭;凡蒋、周公之胤,初虽同族,后各分封,并传国姓,以为宗本。若与姬姓为婚者,不在禁例……又如近代以来,特蒙赐姓,谱牒仍在,昭穆可知,令姓之与本枝,并不合共为婚媾。(疏)此为关于同宗异姓之特例,前段情形似因古代己属异姓,今则无从确证其系同宗,故律不禁止。后段情形,则事属近代,尚能知悉其系同宗,故律予禁止。(注:《释文》卷十四,释“鲁、卫、蒋、凡条”。)其有声同字别,音响不殊,男女辨姓,岂宜匹仇,若阳与杨之类。此为关于声同字别之姓氏等情形,唐律之周详,由此可见一斑。其有复姓之类,一字或同姓氏既殊,原非禁限。其为婚姻,并不违律。
娶妾是否亦禁同姓,唐代持严格态度。《唐令》中有如下问答:
问曰:“同姓为婚,各徒二年,未知同姓为妾,合得何罪?”
答曰:“贾妾不知其姓,则卜之(《礼记·曲礼》),取决耆龟,本妨同姓。同姓之人,即当同祖,为妻为妾,乱法不殊。户令云:“娶妾仍立婚契,即验妻妾俱名为婚,依准礼令,得罪无别。”(注: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之“户令”。)
母之同姓,除后周一度禁婚外,历代尚乏其例。唐律亦无明文,惟须受亲属为婚一定要件之限制。(注:《周书·武帝纪》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盖惟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买妾,虽曰异宗,犹为混杂。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妾。其己定未成者,即令改聘。”(建德六年六月丁卯诏)。)《唐律疏议·户婚》“同姓为婚”条后段规定,缌麻以上,以奸论。即同姓而系缌麻以上为婚者,各依杂律奸条(疏);亦即依杂律第二十三条至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处断,此为加重之规定,除同姓为婚外,并为亲属为婚。明清律亦如之。关于同姓或亲属不婚之立法理由,凡为家族主义观念所支配;不外为:避免妇女不育(不殖、不繁),以传宗接代。(注:《左传·喜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又“内宫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财相生疾。”(昭公元年)《国语·晋语》:“同姓不昏、惧不殖也。”《国语·郑语》:“夫和赏生物,同则不继……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亦为防淫佚,重厚别,以维家族伦常。
(八)卑幼私辄用财
按照唐律,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户婚十三)。家财本系同居尊长卑幼之公共共有,各有其应有份额,依现代法观点,家属之用家财,除构成民事问题外,如另无特殊事故,本不成立犯罪,但唐律基于家属一体及血缘名分观念,卑幼私辄用财,被认为侵犯家长权或尊长权之行为,且习俗上承认尊长对卑幼教令权,对家产的排他支配权。凡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则为犯罪行为,且视其情节之轻重,予以处罚。
(九)卑幼违背教令娶妻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户婚三九)。唐律不认承男女本人有绝对之婚姻自主权,须由祖父母、父母或期亲以上尊长主婚,主婚人或许先征询男女本人意见,但此不属于婚姻要件,主婚人如系大功以下之尊长时,则可由男女本人自由决定。但男子在外结婚,尊长后为定婚,为顾全事实,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予以处罚。所谓卑幼,谓子孙弟侄等。所谓尊长,谓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姊等。所谓在外,系指公私行诣之处。如卑幼非在外而自嫁娶,则依违反教令处断(参阅斗讼四七)。值得注意的是,犯本条之罪,止杖一百,律无离异之文,故已婚者,其婚姻为有效。
(十)詈祖父母、父母
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斗讼二八)。詈,诟詈也,即,子孙于祖父母,情有不顺,而辄詈者是也。父祖基于教命权,子孙自应顺从,若敢詈之,礼所不容,律之处罚亦重,惟遍查唐律,凡人间之相詈,并不为罪,然基于一定身份者则有之(参阅斗讼一一,二二)。子孙之于父祖,亦因身份关系,成立犯罪。并将此种伦理,推及于子孙之妻妾。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但须舅姑(公婆)告乃坐(斗讼二九)。其立法理由与夫同。
(十一)告言尊长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谓非缘坐之罪,及谋叛己上道,而故告者)(斗讼四四)。父为子天,有隐无犯,如有违失,理须谏诤,起敬起孝,无令陷罪,亦春秋父子相隐之义也。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罪入十恶(参阅名例七)。但有例外:基于君臣之大义,凡缘坐之罪及谋叛己上道者,子孙告亦无罪。即嫡继,慈母杀其父,及所养者,杀其本生,并听告(斗讼四四)。律重人伦,对于父祖以外之尊长,亦不得告言;违者,亦为犯罪。
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所告虽不合论,告之者,犹坐),即诬告重者,加所诬罪三等。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诬告重者,各加所诬罪一等(斗讼四五),
唐律重伦常,不独卑幼不得告言尊长,即一般亲属亦不得相告。律云:
诸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诬告重者,期亲减所诬罪二等,大功减一等,小功以下,以凡人论(斗讼四六)。
(十二)子孙违犯教令
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斗讼四七)。违犯教令者,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于事合宜,即须奉以周旋,子孙不得违犯。供养有阙,礼云:“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之类,家道堪供而故阙者,是为不孝。若教令违法,行即有愆,或家实贫穷,力不从心,有所不及,则不合有罪,本罪须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十三)缘坐
唐律所称“缘坐”,是指某人因与犯罪者有亲属关系而受处罚。因此也是纯因身份而致处罚之情形,与前列情形不同之处在于:该人无任何犯罪行为而受处罚。应缘坐之犯罪主要是重大犯罪,对缘坐之人的处罚主要有以下种类:
1.谋反及大逆(贼盗一):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之妻妾、祖孙、兄弟姊妹,并没官。伯叔父、兄弟子,皆流三千里。以上皆不限籍之同异。
2.谋叛已上道(包括亡命山泽而抗拒将吏者)(贼盗四):妻、子流二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
3.征讨告贼消息(擅兴九):妻、子流二千里。
4.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贼盗一二):妻、子流二千里。
5.造畜蛊毒(贼盗一五):同居家口流三千里。
但应缘坐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则不得缘坐:
第一,罪人之女已许嫁者(贼盗二):即有许婚之书及私约,或已纳聘财(户婚二六),虽未成,皆归其夫(疏)。换言之,不从本宗缘坐,而归其未婚夫完娶。须注意的是,谋反、大逆及造畜蛊毒,女子始缘坐;其他犯罪则否(名例五二)。
第二,出养、入道及聘妻未成者(贼盗二):出养者,从所养家坐,不从本生家缘坐;易言之,以因收养而成立之亲属关系为准,而定缘坐人之范围,若出继同堂,而出继人之本生父祖为正犯,则出继人于出继后,仍为正犯之兄弟之子或孙而缘坐。至出继同堂以外者,即不为本生父之兄弟之子或孙,自不在缘坐之限。入道者,谓为道士,女冠若骨尼(疏)。聘妻未成者,虽克吉日,男女未相见,并不追坐(疏)。
第三,婚姻、收养无效者(参阅户婚四五,户婚一0):婚姻因违律而无效者,虽针赦仍应离、正之;继养子孙违律者,有时亦应还正之。已离、已正之后,即不从男家或养家缘坐,固不待言。至于应缘坐之罪已发之后,始诉请者,亦因不发生亲属关系之故,不从男家或养家而缘坐。惟养子反逆,而收养须离、正者,则养父母亦应不缘坐,而缘坐其本生父母。又自正犯(所亲)应具之属性言之,道士及妇女,若部曲、奴婢等,犯反逆者,止坐其身(贼盗二)。
缘坐有时因某种情形或性质不同,在处罚上亦有例外,学者称之为缘坐者处罚上之特例。如缘坐中,以谋反、大逆之缘坐为重,情者、减者,亦不得享受殊遇(名例九,一0),又不准赎罪,应除名,配流如法(名例一)而造畜蛊毒之缘坐,虽会赦,亦流三千里(贼盗一五)缘坐人就谋叛以上罪,捕首正犯(缘坐人之所亲),亦同罪人(正犯)自首例(名例三七),缘坐人之祖父母、父母犯谋叛以上罪,而缘坐人捕告首者,则亦不予处罚,且罪人得同自首法(斗讼四四,名例三七)。反逆缘坐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名例一八)。
从唐律之缘坐之制看,缘坐亲属中处以死刑的仅父亲及16岁以上的儿子,是封建历代中亲属株连死刑范围最小者。因此,从亲属缘坐的犯罪种类及范围看,《唐律》是封建法律中之最宽平者,因此被后世封建律学家称《唐律》为“得古今之平”。
三、《唐律》中因亲属身份而致刑之加减的情形
可以说,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在于一个“别”字,即强调尊卑、亲疏、长幼、贵贱、上下、男女之别。唐律“一准乎礼”,维护家族和谐与伦常是唐律的核心任务,故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处罚,先须得明了行为人与被害人具有何种亲属关系,再依律加减其刑。某一行为,身份不同,罪与非罪迥异,罚轻罚重不同,犯罪情状万千,故加减处罚极为复杂,然而在一部《唐律》中,条分析缕,罪与非罪,应轻应重,错落有致,极为分明。某行为因亲属身份而致刑之加减,是指该行为在一般常人间也属犯罪,现因行为人与被害人间的特殊亲属关系而致与凡人不同之处罚。
在唐律中,亲属犯罪(含亲属相犯与亲属共犯)处罚的原则是:侵害人身犯,尊长犯卑幼,减轻直至勿论;卑幼犯尊长,则依次加重处罚;侵害财产犯,不罚或减轻。亲属相婚或相奸,原则上彼此同罚。亲属共犯侵害国家利益时,原则上只罚尊长,侵害个人(指被害人为凡人)利益时,原则上仍分首从罚之。仅就亲属间相犯,其一般原则是:亲属关系愈亲,尊长卑幼相犯之加减等数之差度愈悬殊。
(一)亲属间人身侵犯
亲属间人身侵犯,是指亲属间侵害生命、身体、名誉等的犯罪,可再分为殴伤杀与谋杀。
(1)亲属间相殴伤杀
因其比谋杀罪为轻,相殴伤杀加减等数的幅度更大,加减的因素也较多,因而加减法亦较为复杂。殴伤杀罪,主要有:
1.殴兄之妻,及殴夫之兄妹,各加凡人一等,若妄犯者,又加一等(斗讼三一)。
2.若殴夫之妾子,减凡人二等,殴妻之子,以凡人论(斗讼三一)。
3.妻之子殴伤父妾,加凡人二等,殴妻之子,以凡人论(斗讼三一)。
4.殴伤妻前夫之子者,减凡人一等,同居者,又减一等(斗讼三一)。
5.殴伤继父者(谓曾经同居,今异者),与缌麻尊同,同居者,加一等(斗讼三一)。
6.妻殴詈夫之期亲以下,缌麻以上尊长,各减夫犯一等(减罪轻者,加凡斗讼一等)。妾犯者,不减。(斗讼三一)。
7.尊长殴伤卑幼之妇,减凡人一等,妾又减一等(斗讼三一)。
至于祖父母、父母对子孙,殴杀徒一年半,刀杀徒二年,故杀各加一等,过失杀者,勿论。而子孙对祖父母、父母,詈者,绞,殴、伤、致死者,皆斩,过失杀流三千里,过失伤徒三年。于此可见亲属相犯加减幅度之大,轻重相差之悬殊。
就尊长卑幼之关系而言,尊长犯卑幼,不分尊与长。卑幼犯尊长,则区别尊与长,而异其效果。一般而言,尊长卑幼相犯,则逐级加减,相殴伤杀亦同。惟其加减等数,可分三种情形:
第一,相殴伤重者:尊长犯卑幼,缌麻减凡一等,小功、大功,递减一等;期亲尊长以上,不坐。幼犯长,缌麻加凡一等,小功、大功递加一等,期幼犯期长至折伤,加凡七等,刃伤以上,则处绞。
第二,殴伤(非伤重)者:尊长犯卑幼不坐;卑幼犯尊长,则逐级加重(不分手足,他物及故、斗),又詈期长杖一百,期尊加一等,父祖则绞。
第三,伤重致死者:其刑加减之刑幅轻小,即自缌麻至大功,尊长卑幼相殴致死,原则上只系斩与绞之差,如从父兄弟姊妹及从父兄弟之子孙,卑幼相殴杀,亦不致悬殊过大。
(2)亲属间谋杀
亲属间谋杀,原系殴杀的加重形态,因蓄意杀人,恶性重大,不但卑幼犯尊长,即使尊长犯卑幼,亦从殴杀罪加重处罚。故其加减等数的幅度较小,加减的因素较小,因而加减法亦较单纯,此以普通谋杀为其典型,但也有特殊谋杀。亲属谋杀罪,主要有:
1.诸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贼盗六)。
2.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贼盗六)。
3.即尊长谋卑幼者,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已伤者,减一等,已杀者,依故杀法(贼盗六)。
4.妻妾谋杀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贼盗八)。
亲属谋杀罪,父祖子孙相犯,其加减等数之刑幅亦最大。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大异于大功以下尊长。夫,夫之父祖,亦同期亲之例。谋杀罪重,尊长卑劝相犯,加减等数,不太悬殊。
亲属相犯之加减,除上述殴伤杀及谋杀罪外还有很多情形,如:继父子相殴伤杀(斗讼三二),残害死尸(贼盗一九),穿地得死人不更埋(贼盗三0)、子孙及妻与尊长及夫为戏(斗讼三七),死罪囚辞穷竟而囚之亲属杀者(断狱三)、尊长卑幼间以毒药药人(贼盗一六问答),所有憎恶而造厌魅(贼盗一七),亲属居丧嫁娶(户婚三0),亲属被杀而私和及不告(贼盗一三),亲属相告及诬告(斗讼四四至四六),投匿名书告亲属(斗讼五0),服卑违法(职制三0)等直接或间接之犯,均因亲属身份,而致刑有加减。
(二)亲属间财产犯罪
亲属间财产犯罪,即指亲属相互侵犯财物的行为,此比侵犯人身罪更为简单,又以同居与否分为二种情形:
1.同居之亲属: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不以窃盗论(贼盗四0),只科以轻刑,罪止杖一百(户婚一三)。其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杂律一),减三等,罪止徒一年半(户婚一三),同居卑幼,将人盗已家财物者,以私辄用财论加二等(贼盗四一)。卑幼将人强盗已家财物者,只依强者加二等之例,亦不为强盗(贼盗四一,职制五二)。
2.非同居之亲属:盗缌麻、小功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贼盗四0),疏曰:“缌麻以上相盗,皆据别居。惟卑幼于尊长家强盗,并不减罪,略、和诱所亲之怒婢,既以强、盗窃论(贼盗四六),故亦与上同。缌麻以上,自相恐喝者,犯尊长,以凡人论;犯卑幼,各依本法(贼盗三八),所谓依本法者,乃依亲属相盗法(贼盗四0),强盗亦同。杀缌麻以上亲之牛马者,与主自杀同,杀余畜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厩库一0),此乃减凡人罪,伤及误杀者,无罪,要之;亲属之相侵财,原则上减凡人犯,主要是基于他们有共财关系,故为之减轻。
(三)其他刑之加减
家族关系影响刑之加减,除上述亲属相犯之外,尚有亲属共犯,如亲属相婚(户婚三三、三四),亲属相奸(杂律二三至二五),异姓相养(户婚八)等,均有加减之情形。另外,还有刑法上的荫亲制度,也属刑之加减情形。
(1)因“荫亲”而致刑之减免
荫亲之制,是指本为犯罪之人,只因与某种人有亲属关系,遂得减轻其刑者,例如:
1.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小亲,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议者,原情议罪,称定刑之律,而不正决之)流罪以下,列减一等(名例八一议章)。
2.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流罪以下,减一等(名例九一请章)。
3.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名例一0一减章)。
4.应议、请、减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名例一一,赎章)。
(2)侵害特殊主体之亲属之加重
有些犯罪,虽不是发生在亲属间,但如果侵害对象为某种特殊主体之亲属,其处罚也较凡人加重。例如:
1.皇家袒免亲而殴之者,徒一年。伤者,徒二年。伤重者,加凡斗二等。缌麻以上,各递加一等。死者,斩(斗讼一四)。
2.殴本属府主、刺史、县令之祖父母、父母、妻、子者,徒一年,伤重者,加凡斗一等(斗讼一三)。
3.私贱殴主人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詈者,徒二年,过失杀者,减殴罪二等,伤者,又减一等(斗讼二二)。
4.殴主之缌麻亲,徒一年。伤重者,各加凡人一等。小功、大功、递加一等(加者,入于死),死者,皆斩(斗讼二二)。
(3)因亲属相隐而致刑之减免
“亲属相隐”,即藏匿犯罪亲属者依法可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如《名例律》规定,凡是大功以上亲属及某些虽大功以下但关系亲密者(外祖父母、外孙、孙妇、夫之兄弟、兄弟妻、同财共居者),有罪相互隐匿可不负刑事责任;凡小功、缌麻亲有罪相互隐匿,较凡人隐匿罪犯减三等处罚。但若所隐匿之罪犯所犯为“十恶”中之谋反、谋大逆、谋叛罪,则不得适用“亲属相隐”制。
(4)代为自首减免刑罚
《唐律疏议·名例》规定:即遣人代首,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犯罪人之一定亲属为首或亲属相告言,法律上视同自首而得减免刑。为首及相告言之效果则与相容隐人之身分关系而异,相容隐人若系同居亲属、大功以上之异居亲属、外祖父母、外孙、孙妇、夫之兄弟或兄弟妻,则原其罪;易言之,免除其刑;若系小功或缌麻亲,而为罪人首罪及告言,则仅减三等而已(疏)。这体现了亲属一体的观念。
除以上三大类情况外,唐律还有如下情况也属因身份而致刑之加减情形:得相容隐者代首之减罪(名例三七),征人同居亲属冒代者,减二等(擅兴五),亲属奸之加重(杂律二三至二五),私贱奸主之缌麻以上亲(杂律二六),告主之尊亲(斗讼四八),殴缌麻、小功亲、部曲奴婢(斗讼二三)等,莫不因亲属关系而直接或间接加减其刑。
关于加减的方法,名例律五十六条规定:诸称加者,就重次(名例五六);称减者,就轻次,惟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保例五六);加者,数满乃坐,又不得加至于死;本条加入死者,依本条(加入绞者,不加至斩。)(名例五六);其罪止有徒半年,若应加杖者,杖一百。应减者,以杖九十为次(名例五六)。
透过上述几个方面的资料,唐律中“服制原则”和亲属相犯的相关情形可略见一斑。鉴于唐律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突出地位,我们也可以透过唐律之一斑,来窥中国古代法律伦理性之全豹。这些关于亲属关系的法律条款、罪刑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属成员间关系的看法和要求。同时,透过这些直观的法律条文、明确的处罚规则,我们也可以依稀感觉到在这些充满伦理色彩的法律规范所蕴涵的深刻社会思想因素。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是一套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回旋而形成的体系完整、义理精深、风格特异的庞大法律系统,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主流思想为伦理根据、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体制。这种法律体制的存在和发展,包括其风格特征的形成,主要应该归因于中国数千年传承不辍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血缘家族家庭结构。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所依存的社会土壤的变化,传统法律中的“服制原则”、关于亲属关系的各种特殊规定,以及这些制度所蕴涵的一些传统思想因素,也势必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