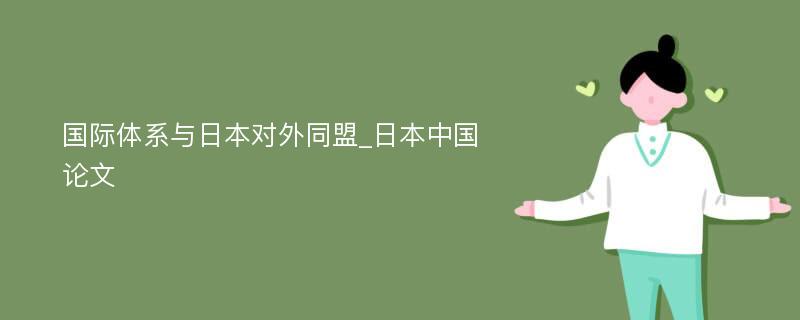
国际体系与日本对外结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同盟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由于对外结盟在日本外交历程中时间甚长、影响甚广,还是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笔者不揣浅薄,试图在前辈同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国际体系的角度对日本结盟问题略陈管见。
一、国际体系与同盟的一般关系
以国际体系为切入点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是“由外及内”的研究路径,它又称体系的解释方法,“是以体系总体上的特性为基础的”,强调“国家的行为,还有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强烈地受到国际环境所决定的限制和激励因素的影响。当国际体系发生变化时,激励因素和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注: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30页。)
何谓国际体系?乔治·莫德尔斯基认为,国际体系是由一系列客体构成,同时包括这些客体之间以及它们属性之间的关系。(注:George Modelski,Agraria and Industria:Two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eds.,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p.121—2.)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是国际主要力量配置构成及这种力量互动关系的组合体。(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ddison,Wesley Press,pp.71—2.)亚历山大·温特则认为,国际体系除了是固定的力量配置结构及其互动外,它还是观念的配置及其互动的结构。(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25页。)可见,国际体系是一种由国际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系统,其中力量配置和观念配置及其互动起着巨大的作用。那么,何谓同盟呢?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做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注:Arnold Wolfers,“Alliances”,in David L.Sills 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1968,pp.268—9.)。格伦·施奈德认为,同盟是“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的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明确地确认”(注:Glenn H.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pring 1990,Vol.44,No.1,p.104.)。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认为,“联盟是国家感到有共同的敌人或者共同的安全问题而进行的正式合作,这种合作一般是在特定的有限的时期以内”(注: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83页。)。斯蒂芬·沃尔特的界定是,“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做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注: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欧洲》1999年第5期。)。也有人认为同盟是“各国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同盟或联盟)进行合作,以增进它们的安全,防范可能构成威胁的行为体”(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72页。),或干脆认为同盟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为了具体的目的而合作的正式协定或条约(注:Wesb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New York:Gramercy Books,1996,p.39.)。可见,对于同盟的界定有严格和宽泛两种趋势,笔者倾向于严格界定这一概念:同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共同的安全利益,在一定时期、针对一定区域、针对一定对象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承诺。同盟与国际体系关系密切,甚至有人认为同盟就是“国际体系的特征”(注: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弗雷德·桑德曼:《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98页。)。
首先,国际体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没有任何守夜人为国家实现利益提供帮助,若想得到帮助,结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因此,有学者指出:“在一个自助的体系中,各国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要么保持中立要么加入同盟。”(注:同⑩,第576页。)于是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做出三种选择:其一,它们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它们可以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其三,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做出第一种选择时,它们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做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联盟政策。(注:参见汉斯·J.摩根索柱:《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5、236页。)事实上,同盟具有四种功能,其中第一种功能就是对外权力的增加。(注:Robert Osgood,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8,pp.21—2.)对外权力的增加与其他功能一样,都需要与国际体系联系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在国际关系史中,国家通过同盟增加权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必要帮助以求实现国家利益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由于任何国家都试图从国际体系中获得利益,因此通过结盟以使国际体系出现有利于己的状态,这也是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关于这一点,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以及构建同盟的当事国更喜欢称之为通过同盟来维持国际体系的均衡或稳定,这种均衡或稳定,在一定意义上无非就是有利于己的状态。笔者认为,一个国家是选择同盟还是其他的手段,是选择与强国结盟还是与弱国结盟,这与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国家可能决定通过结盟实现平衡,对威胁的认识将对是否做出这一决定产生极大的影响。”(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578页。)由于不同的位置和环境,使国家产生对威胁的不同认识,因此在选择是否结盟或与谁结盟时,国家在体系中的位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于处在国际体系重心位置、主导国际体系的国家而言,均衡是维持现有体系的均衡或稳定。因为国际体系是现有力量配置和观念配置及其互动的结果,在力量和观念上具有优势的国家无疑希望维持国际体系的均衡,这种体系状态下它们获益最多。因此,一方面,由于处于体系重心位置的国家握有更多的优势,更易于纵横捭阖,进行分而治之,即联合一些国家,打压另外一些国家;另一方面,它们更倾向于认为国际体系的强国或潜在的强国是对自己的威胁,这些强国或潜在的强国更可能破坏现存体系的均衡,它们无疑会被控制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国家冠以“破坏平衡者”。于是,处于国际体系重心位置的国家往往在潜在强国崛起期间或强国公然挑战其主导的国际体系期间,选择与相对较弱的国家建立同盟,以压制潜在强国崛起或强国过分强大。
对于处在国际体系边缘位置、非主导国际体系的国家而言,它们对威胁的认识不同于前者,其对威胁的认识往往是在前者创造的体系结构、制定的规则中进行判断,因此,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更倾向于认为是前者对自己构成了更大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它要么承认现有体系的状态,保持中立或迎合主导者,迎合主导者就有可能导致建立与强国的同盟,以求化解或减轻威胁,利用现有国际体系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要么挑战现有体系的状态,单独或联合行动,联合行动就意味着与其他挑战者建立同盟,以求建立国际体系新的均衡状态。而何时结盟,则需要根据国际体系变化所提供的时机见风使舵。
其三,同盟也间接塑造着国际体系。一是同盟通过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来塑造国际体系。权力的集中程度无疑对国际体系的结构产生影响,而同盟是最便捷的改变权力集中程度的手段之一。例如,冷战时以美国和苏联为首形成了两大同盟,尽管存在广大的第三世界,但国际体系的权力还是迅速在两大同盟的基础上进行集结,形成了两极结构的国际体系。二是同盟通过影响国际体系的规则来塑造国际体系。“因为国际秩序的形态因联盟的变化而变化。其结果是,形成公认的国际规则的原则——国家行为准则、公认的领土划分及其他权力——持续变化。关系一友好,既定的反对关系规则就立即被制定出来。一个新的对手与以前的朋友或中立国家站在一起,新的规则必然重建。”(注: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86页。)另外,人们对同盟与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也提出了看法。一些人认为,同盟的建立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危机意识,要么导致感到受威胁的国家与之单独对抗,要么促使感到受威胁的国家联合以构建另外的同盟与之对抗,战争几率增加,从而使国际体系不稳定。一些人则认为,同盟的建立可以阻止战争,从而维持体系的稳定。可见,尽管存在着不同观点,但对于同盟与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之间存在联系却是一种共识。
总之,同盟与国际体系关系密切。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之中,为了增进权力与安全,防范或减轻威胁,国家之间往往选择构建同盟。由于在国际体系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对于威胁的认识不同,从而对于何时构建同盟、与谁构建同盟、构建同盟以维持体系均衡或不均衡的意义也不同。体系边缘位置国家的同盟政策受体系重心位置国家的均势政策的巨大影响。
以上关于同盟与国际体系一般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展开对日本结盟的探讨。
二、边缘位置与日本对外结盟
如上所述,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与该国的结盟政策之间存在着联系。而日本恰恰是位置意识极其强烈的国家。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说,日本人“不断就日本的位置及其历史的立场而自问自答。所谓日本所看到的世界,几乎原原本本就是日本人考虑到的日本的位置”(注:加藤周一:《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6页。)。南博也认为:“自己和别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究竟被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日本人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注:南博:《日本的自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页。)笔者认为,从国际环境的角度来看,日本在位置上的特点在于国际体系和地缘上的双重边缘位置,这对其长期选择结盟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内。虽然在中世纪后期,日本试图建立自己的“小华夷秩序”,但就其本质而言,仍属于东亚传统国际体系。19世纪中后期,日本在西力东渐的压力下,实行维新,提出“脱亚入欧”,试图加入以欧美为核心的条约体系。20世纪中后期,日本战败投降、发展经济,又提出脱欧入亚、亲美入亚,注意发展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见,日本外交定位摇摆于东西方之间,于是产生了强烈的体系边缘意识。同时,日本是一个地处西北太平洋的狭长岛国,长期孤立的生存环境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孕育了日本的传统的危机意识。然而,若从更大的背景观察日本,人们会发现:日本西邻欧亚大陆,东望太平洋和北美大陆,因此从地缘位置来看,日本处在亚洲和北美的边缘,即处于两块大陆的边缘。
因此,日本的体系边缘位置在日本的地缘边缘位置的作用下得以强化,这种双重边缘位置赋予了日本独特的体验和认识,产生了日本的边缘位置意识。“历史上,日本的精英与作为学习对象的‘中心’文明(具体地说,即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相比,把自己定位在‘周边位置’……这是一种可称为‘本民族周边主义’的思维方法。”(注: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9页。)日本的这种边缘位置及其认识对其结盟外交产生了影响。
首先,基于双重边缘的位置,滋生出非常现实的机会主义,这与同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宜之计相吻合。结盟是国家获取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它不是一种原则,而是权宜之计。何时结盟、与谁结盟,这要求国家在利益冲突瞬息万变的国际事务中不断地权衡利弊,见风使舵。1992年,当美国记者问日本著名的战略家冈崎久彦日本外交政策有什么固定的原则时,他回答道:“我们两国的历史大不相同。贵国是建立在原则之上的,日本是建立在一个群岛之上”。(注: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可见,日本外交与它的所处的位置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日本的位置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体验,美国学者肯尼思·B.派尔认为:“日本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固定的原则”。“它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都很容易受到国际体系变化的巨大影响”,“一次次地随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而见风使舵”。“国际舞台上谁独占鳌头,日本就会出于自我利益而跟谁结盟:1902年到1922年追随英国,1936年到1945年追随德国,1952年起则紧跟美国”。(注:同上书,第266、267、269页。)
其次,基于双重边缘的位置,滋生出孤儿意识和团队精神,这与合作以共同对抗威胁的同盟同样吻合。作为国际体系普遍存在的现象,同盟的本质在于为了共同的安全利益而承诺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这表明国家在面临共同威胁时,有采取合作行动以化解威胁的可能。由于处于国际体系和地缘上的双重边缘位置,日本存在着强烈的国际孤儿意识,即认为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体系,这一方面表现为认为日本不属于亚洲,日本学者梅棹忠夫认为日本“虽然它在地理上和第二区的中国和印度同属于亚洲地区,单从本质上说,日本又表现了与这些国家的不同。日本在亚洲内部所表现出的特异性完全属于第一地区的特征”;“西部的边界线在东欧,东部的边界线则在朝鲜海峡”。(注:梅棹忠夫:《何谓日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8、105页。)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在融入西方时强烈的自卑感。大隈重信在1908年说:“我国虽然基于武力而跻身于世界一等强国之列,但在知识方面同欧美先进诸国相比仍因相差甚远而常怀劣势之感。”(注:内田满:《早稻田与现代美国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至今,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和美国均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感。
缺乏归属感的国际孤儿意识,总有不踏实的感觉,担心被抛弃。于是,强调群体意识、团队精神的就成为化解它的有效方式。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来源于自我和客我的不稳定的自我不踏实感,在日本人身上特别强烈”,“用什么来减弱、消除呢?第一,决定性不安,可以通过对集团的依存来减轻”。因此,“日本人往往是自己主动投入‘不能摆脱的集团’之中”。(注:南博:《日本的自我》,第8、11、12页。)于是在外交政策上,日本就体现为往往会通过寻找同盟者以摆脱孤儿意识和担心被抛弃意识,在同盟中寻求权力的增加和对自身的认同。然而,由于日本的结盟对象常为非本地区国家,其化解日本的孤儿意识和担心被抛弃意识的动机反而在事实上强化了日本在本地区的孤立,从而强化了日本的孤儿意识和担心被抛弃意识,结果导致日本不断走上看不到尽头的对外结盟之路。
其三,日本的双重边缘位置,使它产生易受到攻击的认识,而易受攻击的程度与是否结盟存在着联系。例如,托马斯·克里斯坦森和杰克·斯奈德认为,一国受攻击的可能性越大,越倾向于结盟并保卫受攻击的盟国。(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577页。)因为易受到攻击的程度越高,意味着它面对敌人时的脆弱性越强,这时选择结盟比单独行动无疑更安全或收益会更大。那么,哪些因素影响国家易受攻击的程度并且导致国家选择结盟呢?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地缘因素与权力分配在决定被威胁大国面对危险的入侵者时,是形成均势联盟还是推卸责任这一问题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注: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50页。)如上文所述,日本恰恰处于地缘及国际体系的双重边缘的位置,这无疑强化了日本易受攻击的认识。彼得·J.卡赞斯坦写道,日本“容易产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下被挟持的感觉,这在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中起着强有力的支配地位。……日本的外交政策选择‘出于一代又一代的、面临着内外各种压力的政治家们的集体信念,他们共同相信,世界是不安全的’。”(注: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易受攻击的认识和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促使日本不断增加自己的权力:在内政领域表现为追求富国强兵、科技兴国,在外交领域则选择了结盟。
三、体系重心与日本对外结盟
如果说,边缘位置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国际体系与日本结盟外交关系的一个方面,那么,对国际体系重心与日本结盟外交之间关系的分析,则将使我们看到该问题的另一方面。
首先,日本从未放弃摆脱边缘位置的努力,在外交上表现为追逐国际体系的重心,在国际体系重心的成员中选择结盟的对象,从中获取权力、安全与利益。19世纪的国际体系可称为英治下的体系,英国所在的欧洲是国际经济、政治的重心,当时的国际体系表现出明显的欧洲单一重心。尽管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逐渐崛起,并在经济实力上令许多欧洲强国相形见绌,但美国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军事力量以及美国新角色的定位等还需要时间,如美国在一战后未加入国联、回归孤立主义即为明证。因此,20世纪初叶至中叶的国际体系表现为由欧洲单一重心向欧美双重心转变的过渡期,一战和二战是这种过渡的代价。直至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美苏两极体制建立,欧美双重心的国际体系最终形成。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西欧、东亚重新崛起,欧美双重心的国际体系被一超多强的多重心国际体系所取代。有了对国际体系变迁的基本线索,我们就会注意到日本结盟对象国的依次变化,即由欧洲国家的英、俄、德到北美国家美国,日本结盟的曲线是在追随国际体系重心变迁的曲线。其中两点值得进一步解释,即为什么日本与同英国一样同是欧洲国家的俄、德结盟,以及冷战结束前后日本一度松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后又强化日美同盟?对此,笔者认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其原因有其共性,即国际体系处于过渡期时,日本的同盟外交处于判断和选择的震动之中:日本一度与英国一样同是欧洲国家的俄、德结盟,无疑是与欧洲单一重心动摇向欧美双重心过渡的剧烈而持久的震荡有关,而日美同盟由冷战前后的松动到随之的紧密,则与国际体系由欧美双重心向一超多强过渡、美国一超地位很快确立有关。
其次,作为先后处于国际体系重心位置、主导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的日本的两个主要结盟对象国——英国和美国,它们的东亚均势战略对日本结盟外交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英美势力进入东亚以后,面对着传统的地区大国中国、开始有所发展的日本以及随着领土扩张而成为东亚重要一员的俄国。鉴于三国的这种情况,英国最初选择以实力居中的中国来维系东亚的均势:在中国谋求利益的同时,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避免中日爆发大规模冲突或中国陷入混乱,以此在中俄之间从而在东亚建立脆弱的均势。
中日甲午战争后,这种脆弱的均势被日本打破,中日俄三国地位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开始取代中国成为本地区的大国;俄国由于利用三国干涉还辽而加强了对中国的影响力,其在东亚的优势也随之进一步提升;中国则成为中日俄三国中实力最弱的一方,最终被逐出东亚的均势圈。乔治·凯南在回顾英美该时期的东亚均势战略时写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力量有效地抵抗这些活动并防止俄国人统治另外那些地区。当时实际上唯一有可能取代俄国人在渤海湾势力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英国人认识到了这一点。”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认识到:“在那个地区保持俄国和日本之间的均势是可取的办法。”(注:乔治·凯南:《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35页。)这解释了英国与日本结成同盟、美国也在甲午战争前及战中支持日本的战略意图——维持东亚均势。于是,日本对国际体系重心位置的追逐与英美的东亚均势战略相呼应,日英同盟得以建立和保持。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日俄战争,削弱了俄国,在日俄两国间形成了一种均势。
然而,日本和俄国逐渐意识到两个互为邻居的大国在均势对峙中的恐惧和危害,开始调整两国关系,最终在1916年签订了具有同盟性质的秘密协定。日俄由均势对峙局面向和解合作局面的转化,促使英美列强的东亚均势战略开始重新调整。美国以侵害对华门户开放为由对日俄尤其是对在华不断扩张的日本施加压力。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度使均势战略的调整中断,因为英美法需要日本留在自己的协约国集团内以形成对德奥同盟国集团的均势。1917年11月,美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的“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84年、439页。)日英同盟、日美特殊关系得以维系。
中日俄三国经过一次大战,出现了三种发展的趋势:中国尽管持续衰落但开始重新觉醒;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实力大增;俄国在一战、内战及列强干涉中受到重创,与欧美世界渐行渐远。东亚三个主要国家间力量的变化终于导致以英美为主的欧美大国对东亚均势战略做出坚决的调整。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尤其是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之后,日本更可能建立自己的优势,与欧洲的情况一样,战争对远东力量格局的影响也是革命性的。到1918年,甚至欧洲战争还没有结束,威尔逊已经在准备,决心挑战日本的扩张。”(注: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80页。)
为了形成东亚新的均势,英国最终放弃了英日同盟,美国则把法国也拉进来,英美法一起在华盛顿会议上迫使日本接受对其海军力量的限制,并要求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非法侵占的领土及特权。如果从均势的角度看待华盛顿体系,这是在东亚地区国家中俄尚无法形成对日本的均势之前,英美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充当了抗衡日本的均势力量。
英美间接抗衡日本的东亚均势,压制了日本的扩张空间,日本开始放弃与处于国际体系重心位置国家的协调,逐渐走上了公开挑战既有国际体系的道路。于是,日本与另一个挑战者德国建立起轴心国同盟,力图建立自己主导的、东亚新的国际体系——“大东亚共荣圈”。在这种情况下,英美决定直接作为制衡日本的力量投入东亚,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英美与中国、苏联联合起来,以重建东亚的均势。
二战结束不久,以美苏两国为首迅速结成两大对立的同盟,由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的事实,日本被纳入美国的同盟网络之中。尽管历经冷战、冷战后,日美同盟也与时俱进。究其原因,美国需要日本制衡欧亚大陆强国的出现,而日本借日美同盟之力,重返国际社会并利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发展经济,逐步问鼎标志国际体系重心位置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可见,日本追逐国际体系重心位置的强烈意志与处于国际体系重心位置国家的东亚均势战略相互动,对日本的结盟外交也产生了巨大的塑造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