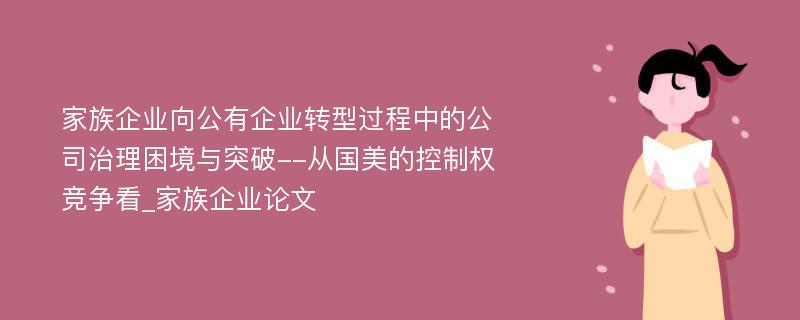
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过程中的公司治理困局及其突围——以国美控制权争夺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局论文,控制权论文,国美论文,公司治理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2-0098-10
2010年9月28日,备受瞩目的国美电器特别股东大会在香港如期举行。以陈晓为核心的国美管理层获得了多数股东支持,得以留任。黄光裕家族落败于大多数议案,但董事会增发权被取消,从而保住了股权暂时不被稀释。虽然国美的未来发展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控制权争夺已经在中国企业规范化发展道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下中国,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正尝试走向公众企业,其转型过程中均或多或少地遭遇了类似于国美的公司治理难题。本文试图以国美控制权争夺为视角,分析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过程中的公司治理困局,并尝试提出因应之策。
一、理论的迷思与现实的悖论:国美控制权之争的法理追问
自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A.A.Berle和经济学教授G.C.Means于1932年提出公司所有与公司控制相分离的经典命题以来,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就成为困扰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的双重难题。在公司控制权之争的漫长博弈中,西方国家逐渐构造了理性的制度体系,并且不断修改完善,使之日趋符合公司自治和公司监控竞争性平衡的时代要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代公司法律制度在我国的出现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在“言必称欧美”的话语体系和对西方公司法律制度亦步亦趋的模仿当中,我国的公司治理出现了偏差,走向了异化,控股股东滥用公司控制权有恃无恐,大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冲突司空见惯,上市公司被掏空的现象不时见诸报端。国美虽然是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和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但仍不失为一家典型的中国式家族企业。对于长期浸淫于中国家族文化的国美而言,其控制权争夺集中反映了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过程的公司治理难题,并至少在以下几个问题上需要引起人们的反思。
(一)公司是什么?
学界对公司本质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未有定论,先后形成了公司拟制说、公司否认说、公司实在说等诸多观点。但迄今为止,对公司本质的研究,最有说服力的学说莫过于公司契约理论或曰公司合同理论。1937年,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将企业的性质界定为“是生产要素的交易,确切地说是劳动与资本的长期的权威性的契约关系”①。科斯的学说开启了公司契约理论的大门,为理解企业的产生和边界做出了卓越贡献。根据公司契约理论的观点,公司的本质是一组“契约的联结”——一个在公司众多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的契约网络②。公司契约理论同时认为,现代公众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产生了严重的代理问题,公司治理的目标就在于降低代理成本。显然,公司契约理论对公司的所有和控制分离的认识始于A.A.Berle和G.C.Means的研究。在1932年《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通过考察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00家最大的公司,A.A.Berle和G.C.Means认为,“在公司制度中,产业财富的所有者仅仅剩下象征性的所有权,而权力、责任以及实物——这些东西过去一直是所有权不可或缺的部分——则正在让渡给一个手中握有控制权的独立的集团”,并得出了“控制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所有权”的结论③。为了控制代理成本,公司契约理论主张在内部给管理者激励契约,在外部则依靠经理人市场④。
然而,公司契约理论对于家族企业的解释力明显欠缺。所谓家族企业,按照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定义,是指企业创始人及其家族成员掌握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维持紧密的关系,且保留高层管理的重要决策权,特别是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高层人员的选拔等方面⑤。然而,所有与控制的分离在家族企业中体现得并不明显,困扰公众企业的高昂代理成本问题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并不突出。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家族企业特别重视血缘、亲缘和情缘,体现出一种非正式的契约安排与松散型的制度约束。面对公司是“扩大了的个人,还是缩小了的社会”⑥这一命题时,公众企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而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前者。至于公司契约理论为解决代理成本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对于家族企业并无太多适用性。首先,家族企业大都认为,经理人追求高于职位之上的更高目的,他们不是简单的自利经济主体,而是经常扮演着为组织和股东的利益服务的利他主义者⑦,这就是所谓的管家理论。在这样的价值预设下,家族企业普遍将经理人视为恪尽职守、可以信赖和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管家”,也就相应缺乏对其进行激励的动机。国美控制权争夺中,陈晓的行为被不少媒体和公众解读为“管家背叛了东家”,从而让陈晓背负了沉重的道德压力。虽然这一解读未必公允,但可以看作是传统家族文化在现代企业的一种典型映射。其次,公司经理人的偷懒与欺诈、懈怠与滥权是一个尚未攻克的全球性难题,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刚刚起步,远未成熟,将解决家族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希望寄托于职业经理人,无异于天方夜谭。
(二)公司归谁所有?
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属于股东所有,股东享有公司全部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股东至上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公司应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回报股东的利益诉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传统的公司法理念发起了挑战,认为公司是由平等的利益相关者所组成,股东只是其中一员,公司的目标应当是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⑧。与此同时,在理论界炙手可热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伦理支持。这两种理论对传统的公司法理念有所冲击,但并没有根本上动摇股东利益至上的这一公司法基本指针。
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理人革命”的兴起,“股东会中心主义”转向了“董事会中心主义”。为了降低股东大会的决策成本,股东大会交由董事会处分法人资本。董事会在保留法人产权的前提下,将日常经营权让渡给管理层。由此,企业管理的重心从老板转移到了经理层。职业经理人并非简单的高级打工者,而是对企业享有控制权,甚至还通过股票期权等形式变相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经理层的兴起使传统上以股东为中心的公司法制度设计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股东是公司当然所有者的地位出现了松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内部人控制”成为了公众公司新的隐患,于是出现了世界性的解雇经理人的高潮。尤其是随着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的轰然倒塌,公众对职业经理人的信任被彻底击碎。在此背景下,一场新的“股东革命”(又称“投资者革命”)应运而生。近十多年以来,机构投资者强势崛起,大型金融机构持有公众公司的股份比例日益提高,“股东法人化”现象方兴未艾,“股东会中心主义”出现了回归态势。各种机构投资者开始发布自己的公司治理宣言,如机构投资者理事会(CII)的《公司治理政策》、全美教师保险及年金协会(TIAA-CRER)的《公司治理的政策声明》、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CALPERS)的《公司治理核心原则与指引》等⑨,旨在重塑自己公司所有者的地位,抗衡职业经理人的控制权争夺行为。在英国,有一些公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机构股东的压力下辞职,这些CEO被戏称为“公司丛林中的国王的制造者和毁灭者”⑩。
(三)管理层为谁服务?
在回答管理层为谁服务问题上,信义义务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答案。信义义务理论将管理层视为公司的受信人,管理层对公司负有信托责任,即管理层对公司负有“最大诚信、忠诚、信任和正直的义务”(11)。管理层的这种信托义务是对股东全体而不是单个股东,但在某种“特别的事实关系”中,公司法并不排除管理层对个别股东负担信义义务,如管理层代表股东出售其股份,这个原则事实上已经为英国的司法判例所确立(12)。委托代理理论则将管理层视为“代理人”、“受托人”或“经理合伙人”,管理层与公司关系的法律调整适用代理法的一般原则。该理论承认“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理性的代理人会在获取预期收益的前提下通过偷工减料、偷懒、自我交易、扩大费用偏好等方式获取利益。为解决代理成本问题,委托代理理论主张采用适当的激励手段,以鼓励管理层为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服务(13)。
但是,管理层为公司和股东服务的理想图景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偏差。黄光裕在2008年11月被收审之后,授权魏秋立与王俊洲代为签署公司文件,事实上将公司控制权委托其行使。但在后来的国美控制权争夺中,此二人公然违反在“特别的事实关系”中形成的对大股东的信托义务,宣布“与管理层共进退”,加入陈晓阵营与黄光裕家族争夺国美控制权。值得注意的是,在国美与贝恩达成的最初协议中,有绑定陈晓、魏秋立、王俊洲必须在国美继续担任执行董事的条款,虽然该条款后来被香港联交所否决,但其充分暴露出管理层信托理念的缺失以及职业经理人道德底线的轰塌。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创始人是一面旗帜,是企业的灵魂。家族企业上市后,创始人对企业的控制不像过去那样百密而无一疏。一旦创始人离去或遭遇意外,控制权就会出现真空。在信托理念缺失和制度保障缺位的情况下,管理层往往存在“鸠占鹊巢”的冲动与偏好,而所谓的“受托人责任约束”只不过是“没有牙齿的法律”(14)而已。
(四)公司法的边界何在?
2010年5月11日,在国美周年股东大会上,黄光裕夫妇以大股东的身份否决了对贝恩三名非执行董事的任命。但令人诧异的是,国美董事会以“投票结果没有真正反映大部分普通股东的意愿,不能代表管理层及董事会的意志”为由,旋即否决了股东大会的决议,贝恩任命的三名非执行董事很快入主国美董事会。我们不禁要追问:公司治理是否属于纯粹的意思自治空间,公司章程是否能够改变公司法的基本法理,公司控制权之争是否需要政府干预?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公司法边界的厘清。
按照公司契约理论,公司是利益相关者通过合同自治达成的一系列合同的联结,公司法必须放弃强制性色彩,遵循合同自治原则,进而成为一部任意性法律。当然,鉴于订立合同所需的成本(15)以及合同必然的不完备性(16),公司合同理论也认同公司法可以以标准合同或缺省规则的形式存在(17)。然而,公司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外部性,客观上需要政府的干预(18)。政府的合理干预有助于纠正公司的不当行为,增强公司运营的确定性,促进公司的运营效率。但政府的干预一定要保持在“需要干预”的界限内,否则,“治疗可能比疾病更糟”(19)。在英美法的公司法架构下,董事会经由股东大会的概括授权,其职权已经极度膨胀,股东大会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董事会的约束力,这样的权利布局固然与“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观念相契合,但其对股东权利的隐性威胁值得警惕。一个应然的公司法边界,应当是强制性规范、缺省性规范与授权性规范的合理搭配,各种规范之间既能形成有效的竞争,又能促进市场机制、自律机制、法律机制之间的适时替代与良性互动,确保公司治理机制的规范弹性与应有活力。我国的家族企业在选择到境外上市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量股东大会与管理层的权利义务配置,科学划定上述三种规范的合理边界,不能盲目与国际惯例接轨。
二、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的路径依赖及其进化的可能与局限
尽管家族企业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但在生命周期上却存在着“富不过三代”的延续规律。根据国际权威调查机构麦肯锡的一项统计,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其中大约只有30%的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够传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数量还不足总量的13%。在我国,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更为短暂,能够成功转型为公众企业的更是凤毛麟角。是家族企业不适应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还是家族企业存在内在的路径依赖?本文拟通过比较家族企业与公众企业公司治理的异同来寻求答案。
(一)家族企业与公众企业公司治理之比较:基于法社会学的视角
国美控制权之争是在资本市场法律规则的框架下进行的,这可以看作是资本文明的一个标志性样本。但没有人会否认,国美控制权之争已经远远超越了法律文本的范畴,夹杂着复杂的商业伦理与价值评判,权谋、利益、情感、背叛等系列看点撕裂了控股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温情面纱,公司治理法律规则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社会与经济含义。因此,本文试图走出狭隘的公司法视角,引入更为宽广的法社会学视角对家族企业与公众企业的公司治理进行比较。
首先,家族企业依附于熟人社会,而公众企业依附于陌生人社会。上个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其著名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中国人生活范围狭窄、封闭且缺乏社会流动性,人们大多在某一地方“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进而形成了人与人相互熟悉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20)。熟人社会为家族企业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土壤,使之具有了鲜明的家文化特征,即特别强调血缘关系。家族企业的典型组织架构是以企业创始人为核心的一种环状“差序”结构,即创始人作为企业的精神领袖居于所有管理层级的中心,围绕这一权力核心形成一个紧密管理层,然后再联结一个更大范围的亲友圈。如国美在2006年整体上市之前,黄光裕家族持有70%以上股权,其家族成员在公司中担任要职,管理层均由其亲信组成。国美上市之后,尽管从多方面进行去家族化的努力,但其家族管制色彩依然十分强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社会阶层迅速分化,社会变迁明显加快,以伦理和人治为特征的熟人社会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一个依赖市场、契约、制度和规则而生存的“陌生人社会”正在形成之中,“从身份到契约”正在从理想变为现实。公众公司迎合了这种发展趋势,其股权高度分散,公司治理机构较为健全,是现代公司的典型形态,代表着公司的发展趋势。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的社会依然呈现出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市民社会还不够成熟,公民意识尚有待塑造,因此,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预示着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将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其次,家族企业注重商道伦理,而公众企业注重法律规则。在本次国美控制权争夺事件中,陈晓被置于道德的审判台,“背叛”、“不忠”等词汇成为民间对他的主要评价。忠信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在商业经营中演变成为儒商伦理道德。所谓儒商,是指具备君子风范、维护人的尊严和体现高尚道德教化的商业管理人员,其所进行的公司管理是在履行一种道德性的经济功能,担当着社会领袖的角色与化身(21)。儒商伦理道德为近代中国的家族企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今仍在东南亚创造举世震惊的华人经济奇迹。其实,家族企业所注重的商道伦理,也已经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关注。当概念法学面临困境、实证法学陷于迷惘,完善的法典和周详的判例无法规制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时,人们不得不反思东方的道德伦理在未来社会法律生活中的作用(22)。家族企业素来将职业经理人视为“管家”,其首要品德就是忠诚。在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的过程中,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操守如何界定,是忠于企业创始人家族还是忠于全体股东,如何权衡创始人、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是摆在中国职业经理人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公众企业则更加注重法律规则对其公司治理的调整作用。鉴于公众公司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社会的重要影响,立法机关、监管部门以及交易所总会制定各种规范性文件来规制公众公司的行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备完备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成为内地企业到境外上市的首选之地。当然,“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23),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并不意味着成为了遵纪守法的“企业公民”。国美在从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的过程中,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和设计,其中有两步值得关注:一是选择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二是在香港联交所借壳上市,均有法律规避色彩。“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规避法律的行为同样是商道伦理所谴责的对象。在国美取得上市资格后,黄光裕为了一己之私,多次套现,致使国美电器股价大跌,投资者损失惨重。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黄光裕又采取了操纵股价、非法经营等违法手段,直至锒铛入狱。这些事件表明,中国的家族企业在资本市场运作过程中,法律意识淡薄,社会责任理念缺失。在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合理借鉴传统商道伦理中的有益养分,坚守资本市场的法治规则,理应成为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的价值选择。
再次,家族企业是关系契约的联结,体现出契约的不完备性,而公众企业是个别契约的联结,体现出法律的不完备性。1980年,美国学者麦克尼尔出版了《新社会契约论》一书,另辟蹊径地将社会关系作为契约法的基石。他把契约分为两种形态,即个别契约与关系契约。个别契约意味着“除了物品的单纯交换外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关系”(24),只涉及很少的一部分人格、人身,关系相当松散,甚至可以不需要存在人身信任关系。而关系契约的各方存在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要求彼此信任、理解并相互支持。家族企业作为典型的人合企业,对人身信赖关系有着特别的要求,家族成员对企业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较为突出,与关系契约的法理旨趣相契合。公众企业属于典型的资合企业,是资本的聚集,不太关注股东之间的人身信任关系,可视为个别契约的联结。
完备契约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假设。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完备契约意味着,一切与交易相关联的、当前和未来状态下的权利和义务,都可以被一个完备契约所覆盖,并且可以无成本地被一个对交易各方持中立态度的第三方(如法院)所完美执行(25)。然而,契约总是不完备的,格雷斯曼与哈特将其原因概括为三点: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契约不可能预见一切;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契约条款不可能无所不包;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与不完全,契约的当事人或契约的仲裁者不可能证实一切(26)。正如前文所述,家族企业体现出一种非正式的契约安排与松散型的制度约束,契约的不完备性在家族企业中表现较为突出。契约的不完备性在公众公司中体现的亦很明显,如公司章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备的开放式契约,但公众公司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则是法律的不完备性。不完备法律理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斯托教授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许成钢教授于2001年提出的,其核心观点是,法律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阻吓过度与阻吓不足的问题,所以法律是不完备的。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被动式执法经常是不够的,需要引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主动式执法机构即监管者,进而改进阻吓失灵(27)。由于公众公司股权的分散性,其股东动辄成千上万,所以公众公司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其风吹草动容易引起诸多的利益变动,历来是法律规制的重点。然而,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生活,规制失灵时有发生,我国上市公司失信行为的层出不穷即为例证。我们有必要借鉴不完备法律理论,全面审思公众公司的法律规制制度,重塑立法机关、法院、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之间的执法权力格局。
(二)路径依赖、制度变迁与家族企业的进化
通过与公众企业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家族企业形成了一整套自足的制度体系。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中,这套制度体系已经内化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并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然而,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在道德与资本的博弈中,家族企业出现了某种不适,其制度供给尚有待改善。具体来说,熟人社会习惯用“人情”与“关系”来代替“契约”与“竞争”规则,从而弱化了法治的功能与制度的刚性,不利于家族企业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也淡化了竞争机制对家族企业的激励作用。商道伦理虽然是法律规则的重要补充,但是不能成为法律规则的替代机制,家族企业的现代转型应当首先学会并适应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关系契约将家族企业笼罩在爱恨纠结的人情网络当中,视企业为单纯的营利工具,而不认同其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这也为“富不过三代”的家族企业提供了一个经典注脚。总之,依附于熟人社会、束缚于商道伦理、沉溺于关系契约,构成了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的路径依赖,严重制约着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与结构转型,并使家族企业被锁定在特定的“均衡”状态当中而难以自拔。
家族企业欲要实现向公众企业的转型,必须摆脱路径依赖的影响。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摆脱路径依赖的可能路径包括科斯谈判、削减租金和塑造公共意识等(28)。然而,这些路径对于中国的家族企业有多大的适用性,尚未可知。其实,推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无非存在两种方式,即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与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迁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企业等为主体、自下而上进行的一种制度变迁类型,是一种渐进的、不断分摊改革成本的演进过程(29)。基于家族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政府并不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强制性地要求家族企业向公众企业转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家族企业转型中无所作为。事实上,政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来打破熟人社会、通过依法治国让法律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规则等均有助于家族企业的进化。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和陌生人社会的形成,家族企业有望在市场规则的诱致下从“建构理性主义”走向“演进理性主义”。然而,这一进化过程似乎并不乐观。家族所有和控制的历史惯性、以血缘为纽带的差序格局、敏感而脆弱的代际传承都制约着家族企业的进化,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从“采邑”到“宗法”的过程(30),不可能过渡到真正的公众企业。
三、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过程中的公司治理难题及其克服
迄今为止,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但就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过程中的公司治理而言,研究论著尚不多见,能够提出富有洞见的观点的著述更是寥若晨星。国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个案,其集中映射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背后的社会玄机以及英美公司法律制度设计的漏洞,值得深入挖掘与洞察。公司治理、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家族”观念与公众企业性质的冲突等等都需要进行研究探讨。
(一)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过程中的公司治理难题
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过程中,无疑,存在公司治理难题。
其一,企业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的分离所带来的控股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在转变为公众企业之前,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几乎合二为一,经理人被视为是忠于家族的管家,他们会牢记企业的使命,珍惜其雇员和股东,为其所在家族和集体组织尽职尽责。然而,家族企业在走向公众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分权制衡的权力架构。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股权的分散,企业管理的专业化及其对资本市场的日趋依赖,客观上造成了公司控制权向董事会和经理人阶层的转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无论美国还是欧洲,资本密集和技术先进型的企业都为经理人资本主义所控制(31)。欧美公司法为了顺应这一潮流,纷纷因势利导,通过变法来强化经理人的职权,如美国特拉华州在19世纪后期就逐渐将公司自治权力由公司股东转移到公司经理人手中(32)。《美国模范商事公司法》第8.01条第2项明确规定,公司的全部权力由董事会行使或由董事会授权他人行使。德国1937年的《股份法》正式废除了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大大削减了股东大会的权限,同时强化了董事会的经营权限及其对股东大会的独立性。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职业经理人遂成为公司的“帝王”。
掌握了公司控制权的职业经理人,并不满足于控制权本身的权利内容,而且还谋求控制权之外的利益形态,如控制权的溢价。除此之外,职业经理人还存在严重的懈怠与道德风险行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使控制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冲突真实地呈现出来。1972年的水门事件引发了民众对公众公司职业经理人道德风险的警惕,再加上美国泛滥成灾的职业经理人财务犯罪,美国开始推行独立董事制度,这一做法迅速风靡全球。然而,控制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冲突并没有因此化解,2001年安然公司因财务欺诈而破产再一次将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暴露无遗,这直接导致了《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简称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出台。可以预见,不管法律的设计多么精巧,只要公众公司的所有与控制保持着分离,控制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冲突都将难以避免,这几乎是每一个公众公司面临的“戈尔迪死结”,欲转型的家族企业对此应该有充分的心理预期。
其二,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概括授权问题。股东大会是权力机关,董事会是执行机关,这几乎成为公司法教科书上金科玉律般的定论。然而,法律文本与实践运作总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上,在盛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英美国家,股东大会对公司的掌控能力已经相当虚弱,董事会已经演变为元老院式的任命和监督机构。家族企业转变为公众企业初期,管理层多由家族成员担任,为了管理的方便,大股东往往会采取概括授权的方式,赋予管理层极大的职权。如在2006年,当时持有国美电器约70%股权的黄光裕,授予了国美电器董事会的权力包括:可以随时任命董事,而不必受制于股东大会设置的董事人数限制;国美电器董事会可以各种方式增发、回购股份,包括供股、发行可转换债券、实施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以及回购已发行股份等权力。董事会权力的过大和滥用,最直接的后果往往是董事会只为大股东服务,而置中小股东的权益于不顾。在后来的国美控制权之争中,陈晓正是利用了这一概括授权将大股东逼入了死胡同,黄光裕可谓是陷入了自己设定的圈套。在概括授权问题上,董事的选任和股权激励的推行颇值得我们反思。
鉴于董事在现代公司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合理的董事选任机制就成为优化公司治理的重要环节。大陆法系国家多将董事的选任作为股东大会的一项基本职权,并且公司法对股东选任董事权力的规定属于权力分配的核心结构性条款,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一般不能由公司章程限制或剥夺。根据我国《公司法》第38条和第100条的规定,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是股东大会的法定职权。应当说,将选任董事的权利交由股东大会并赋予其规范的强制性,是很有必要的。股东大会对董事的选任是一种重要的控制权安排,对不称职董事具有威慑作用,而且具有督导与遏制管理层的潜在功能。然而,英美法系公司法对董事选任的制度设计却迥然有别于大陆法系。在英国,公司法并没有规定董事必须由股东大会选举。美国的公司立法虽然不否认股东选任董事的权利,但大都允许公司章程设立分类董事会条款,这实质上是对股东选任董事权利的限制。所谓分类董事会,又称交错选举的董事会,是指公司章程将董事会成员的任期分批交错安排,由于全部董事任期不相同,所以每一次股东年会都只有部分董事任期届满,股东年会只能改选这部分董事。分类董事会条款的初衷是抵御敌意收购,但在实践中却严重影响了股东对董事的选任。对此,有学者不无忧虑地评论说:“领教了分类董事会强大反收购力量的股东,开始在机构投资者的带领下投票反对新置分类董事会,也开始投票支持废除现存的分类董事会。但是,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股东的这种积极行动均是徒劳”(33)。在国美控制权争夺中,国美董事会直接推翻股东大会的决议,任命贝恩推荐的三名董事,其做法甚至超越了英美公司法的制度框架,其合理性、合法性均有待商榷。我们认为,股东对董事的选任权不容抹杀,这是股东民主的基本要求。当这种权利不能确保的时候,实有司法介入之必要。
2009年7月,国美推出了庞大的股权激励计划,包括国美董事局主席陈晓在内的国美管理层和公司其他员工共105人将获得总计约7.3亿港元的股权激励。这被陈晓阵营解读为“国美走向职业经理人时代的关键一步”,但在黄光裕家族看来,股权激励是“慷股东之慨,变相收买人心”。国美推出的股权激励之所以引起这样大的争论,并不在于家族上市企业能否实施股权激励,而在于股权激励作出的程序与方式。由于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按照基本法理,董事会至多可以提出股权激励的计划草案,然后提交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如我国证监会于2005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37条就将股权激励的最终决定权赋予了股东大会。虽然国美内部有概括授权,但也应当充分尊重股东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在国美控制权争夺中,持有国美1/3以上股权的黄光裕完全被排斥在股权激励的决议之外,不能不说这次股权激励存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二)家族企业如何走出“被锁定的均衡”:分析与建议
家族企业是一种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甚至被冠以“古典企业”的名号。打破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过程中的公司治理困局,走出被熟人社会、商道伦理和关系契约锁定的均衡,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其一,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并强化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约束。虽然国美控制权争夺反映出了职业经理人与控制股东的深层利益冲突,甚至让一些家族企业创始人发出了“养虎为患”的感叹,但不能因噎废食,就此阻却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育。从长远看来,家族企业的转型离不开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推动,企业所有与企业控制的相对分离更是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首当其冲就是要塑造职业经理人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准则,通过文化激励与声誉激励等形式提升其道德修养水准。中国是一个被道德教化上千年的国度,一些传统道德观念深深扎根于文化土壤,可谓是根深蒂固。倘若能够对其因势利导,则对于提升职业经理人的道德素养不无助益。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道德与法律应当并行不悖,职业经理人的自我约束与自我调节(34)与法律的强制性节制应当同时发挥作用。我国《公司法》已经明确了职业经理人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还需要完善相关制度配套,以使信托责任约束能够真正落实。
其二,规范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并合理厘定管理层的权利边界。由于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发展相对滞后,股东民主的理念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中小股东的利益保障机制尚需完善,所以滥觞于欧美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并不适合中国。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主要是通过公司章程来进行,所以公司章程不再是“橡皮图章”,而是控制权争夺的重要工具。现行《公司法》将董事的选任、股份的回购、注册资本的增加或减少、公司债券的发行、财务预算的审批、公司章程的修改等职权赋予了股东大会,这是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公司章程不得对此进行改变,而只能在这些法定职权之外进行授权。家族企业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知,否则有可能重演国美控制权之争的乱象。我国的现行立法对管理层的权利边界厘定不够清晰,如CEO的法律地位不明朗,没有授予管理层必要的公司索取权,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其三,打破与公众企业不符的观念误区,对家族企业进行一场“思想革命”。我国是一个家族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家,家族企业与伦理规范以及意识形态均有紧密的关系,其与传统文化的依存度之高世所罕见,这也是我国的家族企业与西方的家族企业的一个重要区别。传统的一些文化观念给家族企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严重影响着其向公众企业的转型。家族企业要想走向公众企业,必须打破这些思想观念的桎梏,树立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建立三权制衡的制度框架,清晰界定产权,完善决策机制等。只有跳出传统观念的藩篱,家族企业才有可能实现蜕变、迎来新生。
注释:
①[美]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18页。
②Michael C.Jensen & William H.Meckling,“Theory of the Fim:Management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3 J.FIN.ECON.305,309(1976),pp.310-311.
③[美]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8页、129页。
④Henry N.Butler,“The Contractual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11 Geo.Mason U.L.Rev.99(Summer 1989).
⑤[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重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页。
⑥[英]伊凡·亚历山大:《真正的资本主义》,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⑦Davis J,Schoorman R,Donaldson L,“Towards a Stewardship Theory of Managemen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22),pp.20-47.
⑧Margaret M.Blair and Lynn A.Stout,“A Team Production Theory of Corporate Law”,Virginia Law Review,March 1999,pp.247-327.
⑨倪建林:《公司治理结构:法律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⑩[加]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与运作》,林华伟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11)Bryan A.Garner Editor in Chief,Black’s Law Dictionary,West Group Published,Seventh edition,1999,p.523.
(12)Paul L.Davies,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Thomson,Sweet & Maxwell,Seventh Editon,London,2003,p.374.
(13)Jensen.Michael C.and William H.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October 1976.
(14)Roberta Romano,“Answering the Wrong Questions:The Tenuous Case for Mandatory Corporate Law”,Columbia Law Review,Nov.1989,p.1602.
(15)Klein,“Transaction Cost Determinants of Unfair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7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Proc.,1980,p.356.
(16)Sanford Grossman and Oliver Hart,“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94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pp.691-719.
(17)Robert C.Clark,“Contrat,Elites,and Traditions in the Making of Corporate Law”,Columbia Law Review,Nov.1989,pp.1703-1708
(18)[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19)[加]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与运作》,林华伟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页。
(20)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1)唐任伍:《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22)刘殿葵:《公司经理人法律问题研究——对懈怠与滥权规制的法律本土化分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部分。
(23)[美]H· 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8页。
(24)[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25)Kenneth J.Arrow and Gerard Debreu,“Existence of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Econometrica,1954(22).
(26)Sanford J.Grossman,Oliver D.Hart,“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4,No.4,1996.
(27)[美]卡塔琳娜·皮斯托、许成钢:《不完备法律—— 一种概念和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场监管中的应用》,汪辉敏译,载吴敬琏主编《比较》,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3辑、2003年第4辑。
(28)邓峰:《公司法中的路径依赖》,《中外法学》2008年第1期。
(29)[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0-122页。
(30)Max Boisot and Jhon Child,“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41,1996,pp.600-628.
(31)朱弈锟:《公司控制权配置论——制度与效率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32)Michael W.Ott,Delaware Strikes Back,“Newcastle Partners and the Fight for State Corporate Autonomy”,Indiana Law Journal,2007,82,p.163.
(33)Lucian Arye Bebchuk,John C.Coates Ⅳ & Guhan Subramanian,“The Powerful Antitakeover Force of Staggered Boards:Theory,Evidence and Policy”,54 Stan.L.Rev,887(2002).
(34)Tamar Frankel,“F.Hodge O’neal Corporate and Securities Law Symposium:Mutual Funds,Hedge Funds,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the Scope and Jurisprudence of the Investment Management Regulation”,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2005,83,p.956.
标签:家族企业论文; 公司治理理论论文; 中国职业经理人论文; 企业控制权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公司法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董事会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