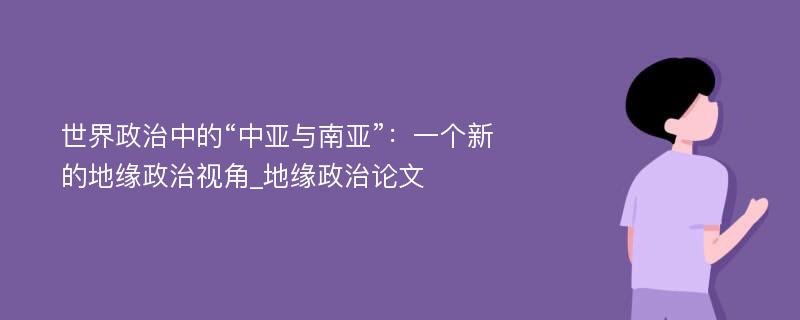
世界政治中的“中南亚”:新的地缘政治图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南亚论文,政治论文,图景论文,地缘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冷战的结束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安全整体态势这一论断,已经少有争议,但关于后冷战时代安全秩序的特征,仍见仁见智,十多年过后依旧争论不休。“新的世界失序”、“新的不确定性”于是成为学者们概括后冷战世界安全态势的常用语。或许是有感于难以在整体上对后冷战时代的安全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分析框架,以巴里·布赞为典型代表的一批学者,便转而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地区安全层面上,并提出了地区安全复合理论,① 因为“地区作为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舞台,作为学者们探究当代安全事务的分析层次,有其自身特性”。② 实际上,以地区为分析单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麦金德、斯皮克曼等地缘政治理论家就有过这方面的经典论述。而国务家们也遵从地缘的逻辑,从实力的对比变化出发,反复阐释政治地理的时代意义,并渴望借此揭示国家关系的空间逻辑。基于这种观念,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苏联解体开启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大变更过程,促使各主要大国“必须根据实力的新现实调整……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了在地缘政治方面有活力和有能力引起国际力量分布发生潜在重要变化的欧亚国家,并弄清它们各自的政治精英的基本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谋求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造成的后果。③ 基于这样的学理逻辑,本文旨在以中国为中心,围绕冷战后实力中心的动态变化这一主线,着力审视中国国土西部的地缘战略态势,并尝试从整体观念出发,把传统意义上的中亚地区和南亚地区合并为一个聚合体,即“中南亚”,④ 以揭示其所蕴含的巨大的国际政治张力。显然,“中南亚”作为战略整体所释放出来的国际政治张力,要比中亚或南亚这样的单一地缘政治区域所释放出来的张力大得多,也深远得多,而这正是当今中国需要认真予以战略思考和谋划的大趋势。为此,文章从三个方面对“中南亚”进行学理建构和战略解读,以阐释其重要性。首先,从地缘战略思想传统出发,论说“心脏地带”、“边缘地带”和“中南亚”之间的承接关系,并指出从“心脏地带”到“中南亚”是地缘战略思想观念变革的结果。其次,从大历史视角出发,着力论说主要大国在进行“大角逐”时,无不是从整体观念出发来统筹中亚和南亚事务的。正是大国权势政治的逻辑,决定了当前将中亚和南亚视为战略聚合体即“中南亚”的必要性。再次,从区域安全研究出发,勾画“中南亚”的地缘属性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的战略选择。
一、从“心脏地带”到“中南亚”:地缘战略思想观念的变革
现代政治地理学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曾经写道:“伟大的政治家从来都不缺乏对地理的感觉……当我们说到健全的政治本能时,我们通常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地理基础作出正确的评价。”⑤
在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中,近代英国地理学鼻祖哈尔福德·麦金德及其名篇《历史的地理枢纽》影响深远。根据麦金德的阐释,欧亚大陆的腹地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全球影响力的专门地缘政治区域——“枢纽地区”。⑥ 为此,麦金德特别指出,历史上枢纽地区的游牧民族曾经经由中亚地区给包括西欧在内的内新月国家造成巨大的历史压力,即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扩张。但及至1919年麦金德出版其名著《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一书时,“枢纽地区”这一术语被“心脏地带”所取代。⑦ 重要的并不仅仅是这一国际政治中耳熟能详的术语上的发展,关键在于麦金德已将自己视作一位政治家来论述这个心脏地带,特别是要借此谋求把“地理学作为能对治国和战略起帮助作用的东西”,⑧ 而不是早先的地理学家的身份。正是这种角色的换位,使麦金德把东欧置于远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重要的地位,这充分反映在他那广为引证的三段论之中:“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⑨ 实际上,20世纪前期,东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治的地理中心,欧洲列强就是在这里争夺地区霸权,进而争夺世界霸权的。对于麦金德的这一重大理论修正,当代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理论家杰弗里·帕克做了这样的解读:“1904年的枢纽现在发展成为在两个方面都扩展了的心脏地带,其一是中亚山岳地带,尽管河流的泻水大多数通往海洋,但(中亚地区)却几乎不可能进入海洋;另一个更重要的地区是包括黑海和巴尔干在内、从易北河到亚得里亚海这一广阔的东欧区域。”⑩
作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地缘政治理论家之一,麦金德的理论贡献在于其全球战略眼界,以及由此得出的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历史对抗这一世界政治规律。(11) 而几乎在同时,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以一种挑战和严重质疑的方式,进一步修正了麦金德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边缘地带”理论。实际上,斯皮克曼把麦金德理论中的内新月地带涵盖的地区扩大了,它囊括了包括巴尔干—黑海地峡在内的整个欧洲西部大陆、亚洲中部山地和整个中国,并将之命名为“边缘地带”(Rimland)。斯皮克曼认为,这一区域是海权和陆权发生冲突时的一个巨大缓冲区,它面向陆海两个方向,在陆海同时发挥作用,并且从陆海两面保卫自己。由此,斯皮克曼提出了自己的推论:“谁统治边缘地带,谁就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12) 在这里,“边缘地带”取代了东欧地区,成为地缘战略的关键区域。(13)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心脏地带仍然不失地理上的重要性,只是现在即便控制了心脏地带,也不像麦金德所设想的那样,会因此而控制整个世界。对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美国人威廉·富兰克林在《美国战略选择与欧亚边缘地带》一文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很明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采取的国家战略,在骨子里所代表的也就是斯皮克曼所提倡的‘边缘地带’战略观念,是以围堵(遏制)麦金德所谓心脏地区的向外扩张为主要目标,而其手段则为增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欧亚边缘地带。”(14)
毫无疑问,1991年苏联的解体开启了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的重大变更进程,“至少从那时起,地处心脏地带、独自行动的强权,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几乎构不成威胁,更不用说对作为整体的欧亚大陆了。”(15) 而这一事态最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在于开启了“后哥伦布时代”,也就是说,与哥伦布时代欧亚大陆的西部(主要是西欧)是世界政治的地理中心截然相反,冷战后欧亚大陆的东部成为世界政治的地理中心,这不仅仅是因为该地区无可比拟的人口优势和商业重要性,还在于它正在成为主要大国权势斗争的核心区域。而这一核心区的西部边界,则处于从哈萨克斯坦到巴基斯坦与中国的交界处。(16) 基于这样的逻辑,把中亚和南亚视为一个战略聚合体,即21世纪世界政治中心——欧亚大陆东部地区的西部外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特别是对当今中国而言,作为亚太地区的新兴大国,在冷战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地区安全层面上,国土西部的中亚和南亚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中亚和南亚,尽管作为相对独立的地缘战略区域各自具有十分鲜明的特性,但“9·11”事件后,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感知其日渐加深的地缘依存关系。把中亚和南亚合二为一作整体的战略考察,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无疑意义重大。因为这样一幅地缘战略图景,有助于清晰地描绘崛起的中国东西两端所面对的主要地缘战略棋手,无论是强大的海权国家,还是强大的陆权国家,抑或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挑战的非国家行为体(如极端势力)。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的“中南亚”作为专门的地缘政治区域,包括了狭义的中亚,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5个国家,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7国,以及位于伊朗高原上的伊朗,总共13个国家。毫无疑问,“中南亚”战略地位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主要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进程,而正在发生的这一转移进程至少涵括了如下重要事态: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21世纪初发生的“9·11”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军进驻中亚和阿富汗,它们与印度的世纪性崛起一道,共同催生了亚洲大陆新的地缘政治图谱。其中,“中南亚”这一广大区域所蕴含的国际政治张力,不仅直接关乎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还关乎主要大国权势斗争的走向,因而格外具有战略意义。
二、角逐“中南亚”:权势政治的内在逻辑
就国际政治的宏大历史图景而言,最能说明“中南亚”战略价值的,当数19世纪后半期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围绕该地区进行的“大角逐”。当19世纪最强大的海权国家大英帝国直接统治印度、强大的陆权国家沙皇俄国于1876年宣布废除浩罕汗国并于1885年抵达阿富汗边境后,陆海权对抗便在中亚和南亚这一广阔的区域展开。显然,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沙皇俄国,其战略构想均没有局限于中亚或南亚的单一区域,而是将之作为整体来加以考察。当俄国征服了中亚并推进到阿富汗边境时,前沙皇将军斯涅萨列夫用一段古老的谚语对这一战略成果做了最好的阐释:“谁统治了赫拉特(Herat),谁就能主宰喀布尔;谁统治了喀布尔,谁就能主宰印度。”(17) 同样,在大英帝国眼里,中亚与南亚密不可分。南亚曾被描述为辽阔的中亚细亚的腹地。历史上,印度河流域就不同于因有险阻屏障而相对封闭的恒河流域,其西部洞开的门户——喀喇昆仑山的一些山口,使英国得以经由阿富汗而在中亚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同时也使得南亚自身的安全与中亚、特别是阿富汗密不可分。而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征服者,如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铁木尔、巴布尔等,无不是经由这些山口进军南亚次大陆的。对此,一位学者做了这样形象的比喻:“中亚可以比作一个水库,它的水源来自暗流,水库里的水不时地、而且说不清什么时候会溢出,以致泛滥到它的邻近地区。”(18) 而英国外交官寇松则更为直白,他认为,“阿富汗、里海以南地区、波斯湾……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棋盘的赌注是世界。”(19)
19世纪末,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俄国的亚洲战略开始从中亚向远东地区进行重大转移。(20) 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署标志着英俄之间出现了缓和的局面。两次世界大战中,主要实力中心的较量都远离了这一地区。及至冷战期间,从大英帝国手中接下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另一个海权国家美国,主要基于乔治·凯南的地缘战略思想,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全面推行对苏遏制政策。(21) 当然,与大英帝国主要关注英属印度的安全有所不同,美国看重中亚的重要性主要源自这样一种历史推论:“就俄国向中亚地区的挺进来说,那就是波斯的边境”,(22) 即苏联试图谋取波斯湾的出海口。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所谓“北层”构想(23) 以及卡特主义,充分说明了中亚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素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其中,1979年发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堪称冷战时代的陆海权大交锋,而这场大交锋就其实质而言,无疑是19世纪英俄“大角逐”的历史延续,即最强大的海权国家与试图冲破海上环形包围圈的俄国陆权之间的冲突,而这成为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基本态势之一。(24)
1991年苏联的解体开启了新一轮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进程。冷战后,中亚由于与中东/南亚地区地理上的邻近,自主地增强了其地缘战略价值,以及地区国家(伊朗、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和区外大国(美国)的中亚敏感性。可以说,冷战后填补中亚“权力真空”的过程,也就是苏联解体引发的主要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进程,而这一进程最富有意义的变化表现在两大方面:其一是“基地”组织这类非国家行为体对该地区弱国的控制而引发的新型地区安全威胁;其二是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参与其中而引发的地缘震动。就美国来说,参与欧亚大陆的权势斗争是霸权逻辑的必然结果。对此,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强调指出:“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在广阔的欧亚中部高原以南有一个政治上混乱,但能源丰富的地区,它对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国家,以及最南部地区那个人口众多、有意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来说,都有潜在重大意义。”(25) 他将阿富汗以及中亚等国构成的地区称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认为这一地区在地缘战略上对美国有着重要意义。尽管美国因相距太远而无法在欧亚大陆的这一部分成为主导力量,但美国又太强大而不能不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26)
毫无疑问,在冷战后这场新的“大角逐”中,除了主权国家行为体——大国之间的博弈外,最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化当数詹姆斯·罗西瑙所说的“游离于主权国家之外的行为体”(sovereignty free actors)的显著影响力,(27) 像“基地”恐怖主义组织这类行为体,由于具备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包括施加伤害的能力,因而不仅能对国际体系中的弱国、不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进程施加重要影响,而且还有能力利用强大的主权国家在冷战后暴露出来的新的脆弱性而对其施加伤害。在这方面,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与阿富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性质的塔利班政权的结合,直接催生了2001年“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的“9·11”恐怖袭击事件。“9·11”事件后,当今最强大的主权国家美国与最具动员和破坏能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基地”组织在“中南亚”直接交锋,结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角逐”的呈现方式和内涵,而且赋予了其时代特色:一方面,新的“大角逐”在多元行为体之间展开;另一方面,在这场角逐中,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中亚和南亚地区成为战略整体。结果,“中南亚”作为单一地缘战略区域因为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而显得尤为鲜明。
通过发动阿富汗战争,以及赋予南亚国家巴基斯坦以“非北约盟国”的地位,美国对“中南亚”事务的影响不再主要依靠投资和技术优势,也不再相当间接地通过地区国家来确保其地缘战略利益。美国实际上具备了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手段直接影响地区事态,以及监视俄罗斯、中国、印度政策发展变化的极佳机会。(18) 在阿富汗反恐战争行动结束后,美国军事力量的继续存在使地区安全问题具有新的内涵。也就是说,美国因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作为首要安全问题的核心地位,成为其他国家不得不认真研究和应对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权势斗争将冲淡非传统安全的影响力,地缘政治仍将从根本上塑造地区事态和主要角力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大国权势政治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将中亚和南亚视为战略聚合体即“中南亚”的必要性。
三、21世纪“中南亚”的地缘政治图景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无论是从地缘战略思想观念还是从大国权势政治出发,“中南亚”作为单一地缘战略区域均有其合理性,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南亚”的地缘属性也更加鲜活,其对于中国的意义更加深远。
地理上,最适宜勾画“中南亚”图景的当数绵延1200余公里的兴都库什山脉。首先,它与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一起,形成了一道拱形的天然屏障,将“中南亚”与欧亚大陆的东部分隔开来;其次,它又像一座桥梁,向北可以直达费尔干纳盆地和里海北岸,进而直抵俄罗斯与东欧平原;向西南逐渐沉降,将通往伊朗和两河流域的大道展现出来。
在这样一幅图景中,就地缘属性而言,“中南亚”地区显然不是中亚和南亚的简单叠加。众所周知,中亚由于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其地缘战略上的弱点一目了然:地理上明显偏僻和封闭,特别是远离海洋;而南亚作为相对独立的次区域体系,其与亚太地区的互动明显迟缓和不协调。相反,作为战略聚合体的“中南亚”,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之间,是典型的“中间地带”,或者借用科恩的话说,是“门户区”,(29) 它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一直延伸到印度洋,故而不仅能够深刻影响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政治事态,而且还因为直达印度洋而拥有振兴经济不可或缺的世界主要大市场。
当然,“中南亚”作为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它位于欧亚大陆发达的西部(中欧、西欧国家)和欧亚大陆快速发展的东部(主要涵盖了中国和东盟以及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借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它“不再处于‘现代化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之间,而是处于‘两个欧洲’之间的一个奇怪的中间地带”。(30)
这个“奇怪的中间地带”,就如同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高级顾问托马斯·巴尼特所系统论说的,属于“未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空隙区”。(31) 处在该区域的基本都是弱国或“失败国家”,它们是对美国和世界安全造成威胁的主要来源。当然,“空隙区”有可能成批次缩小,而这意味着某地区的大批国家将差不多同时被融入核心区(该区域中基本都是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的国家),类似于过去十年中北约和欧盟同时吸收大批中东欧国家的模式。巴尼特的这一理论解读,实际上从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揭示了这样一种战略趋势:美国及其西欧盟国一旦成功地消化了中东欧国家,其下一个战略步骤或者说其施加的战略压力必然是欧亚大陆“中间地带”的“中南亚”地区,而且是从外向里压缩。冷战后,无论是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还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展开的反恐战争行动,均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在这一进程中,借用一位研究者的说法,美国主要是采取大促进者战略(grand facilitator)——美国有能力通过维持全球和地区均势,将其自身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主要目标结合起来,以维护其国家利益。(32) 可见,“中南亚”的形塑,离不开美国和西方的战略扩张与驱动。而这种战略趋势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尽管目前还没有很好地显现出来,但其后果之巨大是毋庸置疑的。
与美国的巨大促进作用相反,前苏联衣钵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没能充分展现其作为地缘战略棋手的作用,尽管“中南亚”是其阻止欧亚大陆外围势力(美国)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向核心地区渗透(33) 的重要方向之一。这是因为,虽然俄罗斯几百年以来的外交史是一部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舞台中心的历史,(34) 但今天的俄罗斯显得有点黯然失色、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它不再掌握自己在国际上的命运,而成为他国外交政策的对象。”(35) 所以,尽管冷战时期曾一度出现过莫斯科—喀布尔—德里“轴心”,冷战后的俄罗斯也提出了“近邻”外交的概念,大力倡导所谓的“欧亚合作”,但俄罗斯首要的战略目标是回归西方,特别是融入欧洲,故其在“中南亚”更多是采取一种守势。
如前所述,“中南亚”尽管在地域上主要包括两大块,即中亚和南亚,但其内部整合的前景仍相当诱人。这是因为中亚丰富的油气和矿物资源与南亚紧靠出海口形成了紧密的互补。(36) 然而,就目前来说,“中南亚”地区内部的整合主要表现为基于危机的合作,(37) 这就决定了印度这个新兴的地区大国的作用仍然有限,尽管从理论上讲其理应影响巨大。相反,这种危机导向的合作凸显了阿富汗的重要性。2005年10月1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演讲时指出:“一个安全繁荣的阿富汗能使中亚稳定,并将中亚与南亚联系在一起,这是未来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38) 2006年1月,美国国务院成立中亚南亚局,赖斯就此发表讲话称,美国正在把中亚、南亚视为重要聚合的地区。(39) 分管中亚南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包润石则称,作此调整的原因除了文化与历史上的联系外,更主要的是21世纪的现实,如反恐战争、能源输出线路、经济合作与民主机会等将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40)
在这样的一幅图景中,中国又该如何定位自己的作用、制定相应的战略呢?毫无疑问,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多元的,包括国家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诉求、地缘政治角力、经济利益以及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与威望。显然,这样一个多元的战略目标不仅会因为具体情势的变化而出现轻重缓急排序上的变更,而且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实力中心动态转移进程的影响。其中特别需要清晰地认识到:冷战时期,美国将其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欧洲和东亚,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威慑,即威慑苏联和中国;到了21世纪,美国不仅在这两个地区仍然有军事存在,而且还成功地在这两大区域的“中间地带”实现了军事存在。而在这种军事存在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新秩序,有可能使中国陷入某种战略困境,即东西受压的困境。特别是当中国发展和拥有了“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从而使得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后,美国在“中南亚”地区牵制中国不失为一项战略选择。可见,美国整合“中南亚”,不仅基于地区事态的发展变化,还基于整个亚太地区事态的发展变化。换言之,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基本战略取向在于通过对日安全保证、对华接触、对印战略对话和整合“中南亚”,即通过进驻、接触和再保证,防止或至少是延缓其他国家反对美国霸权领导和制衡美国。(41)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应制定和推行什么样的战略,以确保积极稳妥地实现上述多元目标呢?
首先,我们需要扩展战略视野,像美国那样,将传统意义上的中亚和南亚地区视为新的聚合区,即“中南亚”,并在此基础上反复估算主要力量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利益追求上作出精准的战略排序。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东部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缘经济优势,连同全球化带来的诸多便利条件,争取成长为能够对“中南亚”地区国家产生巨大吸引力的中心,为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公益,真正形成互补关系。第三,要充分认识并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实际上,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中亚五国在内的“中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均积极参与到上海合作组织之中,这不仅为我们通过多边机制规范国家行为、塑造战略预期、发展合作关系、缓解安全两难提供了机会,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合“中南亚”的大好平台。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它使中国获得了一项与美国大体相同的权势优势,即在区域范围内通过多边机制对力量进行制度化运作,从而赢得认可与追随。(42)
21世纪是一个需要新的战略思维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关于国家主权、怎样看待其他大国以及对外政策目的的新思维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新计划和新安排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随着“中国因素”的影响持续增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相互认知上的落差、行为的摩擦、利益的碰撞和舆论的交锋会趋于激烈。为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审视“中南亚”,细致辨识其中的对华因素,从而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变得越来越重要。
注释:
① Barry Buzan,Ole Waiver 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Colo.and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 Barry Buzan and Ole Wa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②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eds.,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P.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p.6—7.
③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④ 关于“中南亚”这一概念,笔者在写作过程中与《外交评论》执行主编陈志瑞教授进行过多次交流,并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笔者之所以决定在文中使用这样一个地缘概念,目的在于对中亚和南亚做整体的战略认知。当然,笔者愿意就此接受任何学术上的质疑和批评。
⑤ Francis P.Sempa,Geopolitics: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21st Century,New Brunswick,NL: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2,pp.103—104.
⑥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⑦ Halford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A Study in the Politics.of Reconstruction,London:Constable,1919.
⑧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13、62页。
⑨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p.194.
⑩ Geoffrey Parker,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5,p.32.
(11) 见Gerry Kearns,Geopolitics and Empire:The Legacy of Halford Mackind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51—161; Klaus Dodds,Geopolitic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21—125.
(12)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8页。
(13) 同上书,第74页。
(14) 转引自方永刚、康复全:《大国逐鹿——新地缘政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15) C.Dale Walton,Geopolitics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ultipolarity and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6.
(16) Ibid.,p.6.
(17) Milan Hauner,“Russian and Soviet Strategic Behavior in Asia”,in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eds.,Dominoes and Bandwagons: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55.
(18) F.H.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1870—1898年)》(第十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77页。
(19)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67—168页。
(20) John Chay and Thomas E.Ross,eds.,Buffer States in World Polities,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1986,p.257.
(21) John Agnew,Geopolitics: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115.
(22) [美]亨利·霍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49页。
(23) 所谓“北层国家”构想,是指在中东的北层构建起一个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在内的、而伊朗可能稍后加入的中东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的在于沿着苏联南部边界对其进行遏制。见Henry A.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527.
(24) Nicholas John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Inc.,1942,pp.182—183.
(25)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41—47页。
(26) 同上书,第197页。
(27) 这方面的论述见James Rosenau,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28) Scott Peterson,“Central Asia:The New Front in the Terror War?”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Vol.10,July 2002,p.7.
(29) 科恩认为,所谓“门户区”,意指能够促进其他地区联系和交往的区域,如东欧和中欧地区。见Saul B.Cohen,“Geopolitics in the New World Era:A New Perspective on an Old Discipline”,in George J.Demko and William B.Wood,eds.,Reordering the World: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21st Century,Boulder,Colo.:Westview,1994,p.28.
(30) 《我们的安全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季刊,第88卷,1992年秋季号,第60页。转引自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125—126页。
(31) 巴尼特在《五角大楼的新地图》和《行动蓝图: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两书中,把空隙区分为四个部分:a.包含北非、中东、中亚以及西南亚的伊斯兰世界;b.亚太边缘部分;c.包含加勒比海、中美洲以及南美洲安第斯地区的拉美地区;d.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见[美]托马斯·巴尼特:《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王长斌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特别见第四章;Thomas P.M.Barnett,Blueprint for Action:A Future Worth Creating,New York:Berkley Books,2005.
(32) Alberto R.Coll,“America as the Grand Facilitator”,Foreign Policy,No.87,Summer 1992.
(33) 参见宋德星:《中亚地缘战略态势的五大特征》,《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2期,第5页;宋德星:《地缘政治、民主转型与俄罗斯外交政策》,《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4期。
(34) Cyril E.Black,“The Pattern of Russian Objectives”,in Ivo J.Lederer,ed.,Russian Foreign Policy Essay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pp.3-38.
(35) [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36) Ambrish Dhaka,South Asia and Central Asia:Geopolitical Dynamics,Jaipur:Mangal Deep Publications,2005,especially chapter 5,pp.142—194.
(37) Ibid.,p.177.
(38) Secretary Condoleezza Rice,“Remarks at Eurasian National University”,Astana,Kazakhstan,October 13,2005,http://merln.ndu.edu/archivepdf/centasia/State/54913.pdf.
(39) Secretary Condoleezza Rice,“Remark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s Inaugural Newsmaker Breakfast”,Fairmont Hotel,Washington,DC,January 5,2006,http://www.trackpads.com/forum/us-statedepartment/450898-remarks-state-department-correspondents-associations-inaugural-newsmaker-brea.html.
(40) Ambassador Richard A.Boucher,“Pursuing Peace,Freedom and Prosperity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Remarks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Washington,DC,February 16,2005,http://merln.ndu.edu/archivepdf/india/State/61317.pdf.
(41) 宋德星、李高峰:《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缘政治考量》,《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4期,第18页。
(42)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见宋德星:《国际关系中的力量运用:侧重于中国方面的分析》,《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第66—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