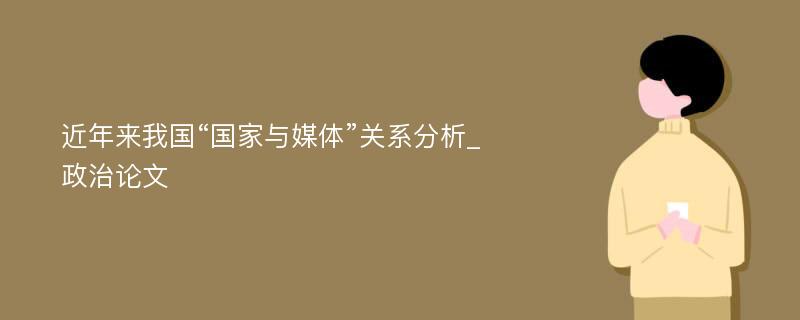
近年来中国“国家与媒体”关系研究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关系论文,媒体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新闻媒体属国家所有,因此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国家与媒体”关系是政治权力与国家公共部门、与国家事业单位或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一种管理关系。然而,新闻媒体却具有不同于其他公共部门和一般企事业单位的特殊性,它直接联系公共权威、市场利益和受众需求,是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直接冲突的场所,最为敏感地体现着政治控制与社会自主性的辩证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中国的“国家—媒体”关系置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大框架内,对近年来关于这一关系的研究进行综合评析。
一、主要研究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媒体”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一是宣传管理与市场力量的矛盾;二是传媒体制与媒体行为的变化;三是宣传控制与媒体生产过程的互动。经验研究上,主要关注市场化所解放出来的经济力量与党的宣传控制这一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1]。理论方面,主要关注在“命令型新闻体制”[2] 未受触动的情况下,政党与媒体的相互关系何以重建等问题[3] 45。相关文献主要探讨了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1.市场力量对宣传控制的有限渗透。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变化,使媒体获得了比以往更宽松的报道空间。然而,学者们一般认为,不能简单地认识市场改革对新闻控制的影响,不应夸大市场力量对国家控制的制约能力。李金铨指出,媒体结构和内容覆盖的变化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控制,但在政府干预下,市场化媒介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同时,政治控制与经济开放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导致了政治控制的循环和媒体改革的反复[4]。赵月枝也指出,在媒体转型过程中,系统内部各种力量的紧张冲突主要体现于政党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互动;公众能获取大量娱乐、微观经济和商业信息,但他们获取政治信息的权利却难以充分实现[5]。何舟对《深圳特区报》的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政治与市场力量之间的“拉锯战”在新闻过程的不同层面有不同体现,就新闻从业者个人、广告操作和竞争机制而言,市场力量明显占据优势;就报道内容、新闻过程和管理领域而言,政治控制依然保持强势,但市场力量也在不断渗透[6]。
2.政治控制的自主适应策略——媒体管理的制度化发展。改革给社会与经济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政治体制也不能不采取相应策略,以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朱迪·鲍罗姆运用米歇尔斯的官僚制理论,分析了中国新闻管理的制度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建立了从中央到省、市级的新闻出版管理系统、信息办公室系统等政府机构,从而在加强新闻管理常规化和可预测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鲍罗姆认为,既然对媒体的政治和行政控制机制更趋严格,那么,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媒体结构的多元化就很难具有政治意义[7]。但是,有关媒体管理制度的改革是否真正使中国的宣传控制机制走上制度化和常规化轨道,并因此加强了政党国家的控制能力呢?对此,学者们存有不同看法,下文相关阐述表明了这一点。
3.市场化带来媒体结构和媒体内容的多元化。关于媒体结构和媒体内容的讨论,研究者主要强调变化所带来的多元化格局。莱恩·怀特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海媒体改革的研究表明,媒体在组织、人事、财政和内容等四个方面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多元化变革[2]。丹尼尔·林奇在研究“政治思想工作”时指出,信息传播的多元格局增加了政党国家信息控制的难度;但是,媒体内容的变化主要是增加了娱乐内容,而不是严肃的政治论争,因而媒体内容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要体现在非政治的社会文化领域[8]。吴国光指出,中国的媒体结构逐步多元化,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形成了“一个大脑,多个嘴巴”的格局[3] 45-67。麦康勉则从传媒所有制的多样化角度,分析了中国传媒体制有限的多元化,而传媒内容上的多样化主要体现为“软性新闻”的盛行和“舆论监督”内容的增强[9]。虽然媒体结构的多元化主要发生在“社会”而非“政治”部门,内容上的自由化主要集中于大众文化而没有触及政治领域,但媒体结构的多元化效益最终会向政治领域溢出,而媒体内容的多样化同样标志着国家权力的重要变化。
4.市场力量加强了媒体行为的趋利性和不确定性。尽管政治控制仍然强有力,但市场偏好对于媒体行为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利益驱动对于媒体行为的腐蚀;另一方面就媒体生产过程而言,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报道空间的拓展,在赋予从业者较多自由的同时,也加强了其行为的非常规性和不确定性。陆晔指出,由于改革打破了一些成规,新的游戏规则尚未确立,因而在媒体的微观行动过程中,从业者个人凭经验而获取的自主把握能力、人情关系等非制度化、非正式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10]。潘忠党分析了新闻组织及新闻实践与指令型新闻体制的互动过程,并指出中国的新闻改革实践主要表现为一种“临场发挥的行为”(improvised activities),这种临场行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11]。他所强调的这种高度不确定的临场行为,与前述朱迪所讨论的制度化控制所体现的确定性恰成对照。
5.舆论监督。有关舆论监督的研究,主要从国家与媒体的不平衡关系出发,一方面强调媒介自律;另一方面则强调,政治控制不仅限定了舆论监督空间,而且由于政治控制范围内的舆论监督成为政治、行政甚至司法性权力,有碍媒体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其一,厘清中国传媒体制中舆论监督的含义。学者们一般将舆论监督看做媒体的一项社会功能,而不是一种强制性权力。对于舆论监督应否包括非批评性的评价和建议这一问题,仍存争议。① 其二,舆论监督个案和总体状况的分析。如孙旭培关于“跨地区监督”的分析,齐爱军关于舆论监督的三种话语形态的分析,景跃进关于舆论监督的内部行政性和单向性分析,孙五三关于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治理过程的分析。② 其三,探索现有制度中舆论监督的规范与改进途径,如童兵对海南新闻舆论监督中心的调查分析。
6.市场化是否催生新闻专业主义。市场所提供的利益诱惑的确增强了媒体行为的趋利性,但这并不代表媒体行为的全部。在诱人的经济利益和严格的宣传控制面前,仍有媒体努力表现出自身作为社会公器的价值。李金铨认为,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具有“解放”的作用[12]。吴国光通过研究《人民日报》社论的拟定过程指出,政治控制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矛盾在增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一般社论的形成过程已由“填注”式(pouring)转变为“鸟笼”式(birdcage),甚至还常常会“放风筝”,新闻专业主义的诉求比以往得到更多满足[13]。陆晔和潘忠党认为,中国新闻改革中的专业主义在实践中是一种“碎片和局域的呈现”,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并不以意识形态抗衡为主要特征[14]。
7.传媒体制变迁。潘忠党关于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研究指出,中国新闻改革不在于创造新体制,而是为了使现存体制能够容纳相对多元的“非常规”活动,并使之更趋制度化和更可预测[11]。陈怀林将传媒体制从高到低区分为三个层次——宏观管理制度、采编运作制度和经营分配制度,并指出制度创新有一个从底层到高层的先后次序。陈怀林还强调中国传媒制度变迁的地区差异性,并从创新的收益—成本比率分析差异原因,指出广告资源的分布具有决定作用。由于京、沪、粤三地广告资源居全国最前列,因而三地制度创新的发生概率最高[15]。
二、主要理论与方法论
上述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对中国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化的关注,涉及多个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在宏观上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个体与结构、传统与现代的两分范式,多数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强调两极之间的协调与互动。表现在中观方法论层次上,则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分析、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概念、体制转型理论和结构化理论等。
1.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与市场的矛盾。作为媒介研究的一种批判性分析路径,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过程对媒体和政治的影响。李金铨比较了政治经济学的两种分析路径:自由多元主义主要批判国家政权,是“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激进马克思主义集中批判资本,是“政治的政治经济学”[4]。李金铨关于政治对媒体的“控制循环”、何舟关于政治与市场力量的“拉锯战”、吴国光关于“一个大脑,多个嘴巴”的媒体结构、潘忠党关于媒体行为的“临场发挥”、赵月枝关于政党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矛盾等相关分析,均可在较宽泛的意义上看作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的国家与媒体关系。
2.体制转型理论——“传统—现代”范式。体制转型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南欧和拉美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它是“传统—现代”发展模式的理论表现,最初,媒体角色在这一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16]。林奇对中国“政治思想工作”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憾。他在政治转型的框架内探讨了中国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前景,强调公共传播中媒体的作用[8]。学者们不断反思体制转型理论,认为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应以特定社会为基础,自由民主模式未必是普适性的发展目标。赵月枝即强调,西方模式的“出版自由”不过是“编辑自由的出版市场”,在这一出版市场中,媒体所有者的财产权与公众的言论自由权同样重要。因此,不管西方自由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如何,它作为一种规范性理想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在中国政治传播的民主化过程中,必须同时考虑政治控制和市场自由两个方面的局限性,寻求自由模式以外的替代发展模式[5]。潘忠党关于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研究指出,体制转型理论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新闻改革实践。这一理论预设了改革的目标,强调体制转型前后质的差别。而中国的新闻改革在已有体制框架内进行有限改造,这种“体制改革”并不是制度创新意义上的“体制转轨”[11]。
3.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国家—社会”范式。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中,研究者对于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问题上的解释力存有明显分歧。比如,李金铨、林奇、迪特莫等人对中国的公共领域问题就持有悲观态度。李金铨认为,中国国有媒体角色中“公”(public)是指“公开”,而非英美意义上的“公共”,后者意味着公民参与理性讨论。因而,在中国情境中使用公共领域概念不够可靠[17]。林奇将改革后的信息传播状况称为“普力夺公共领域”,政党国家的控制尽管受到某些制约,但信息传播混乱无序。这种普力夺公共领域是混乱、非制度化和非政治的[8]。罗威·迪特莫认为,中国的公共领域依赖政权庇护,由于其内部缺乏坚固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组织领导,这种受庇护的公共领域在强力压制下很容易瓦解[18]。另一些学者如麦康勉则认为,虽然市场化改革并未形成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但却为公共领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与商业化之前的传媒相比,商业化所带来的传媒体制与内容的多元化、传播技术更新与全球化发展等,为开放和理性的公共领域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他认为,以公共领域概念研究中国社会,可能会促使人们思考并努力实现某些重要的社会价值[9]。
4.结构化理论——“结构—行动者”范式。“结构”与“个体”两者孰重孰轻,是社会理论的一个争论焦点。在这一问题上,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宏观结构的决定作用,行动者的能动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结构化理论”,主张结合对宏观结构的制度分析和对微观行为的策略分析,强调行动者的微观行为在制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19]。如果说吴国光关于“一个大脑,多个嘴巴”的分析,重点强调市场化以后媒介结构在宏观层面上的本质变化,那么陆晔、潘忠党、陈怀林等人则在肯定既有媒体结构制约作用的同时,强调行动者微观行为的重要性。陈怀林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制度变迁的研究,分析了不同层次的传媒制度创新的具体过程,其边际调整的渐进特点及其所导致的制度变革的“上下合谋”,恰好在方法论上验证了新闻实践中的微观机制对于宏观制度结构的重要建构作用[15]。潘忠党的研究肯定了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启发意义,他以新闻实践中行动者与制度结构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建构,来解释新闻改革所引发的制度变迁。媒体的“临场发挥”行为,体现着行动者的能动性,对现有制度结构不仅时有突破,而且新闻体制对于某些“非常规”实践的接纳,也使体制本身不断被重构。通过描述个体微观行为导致体制宏观变化的过程,在理论上构筑起“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结构的整合。
三、“国家—媒体”关系研究展望
现有研究就中国媒体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概括。但已有研究所揭示的宣传管理与新闻生产过程的关系模式,除陈怀林对传媒制度变迁的分析以外,大都没有区分或没有充分强调媒体之间的差异性。市场化改革以来,政治控制依旧是决定性的。不同地区的媒体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类型的媒体相对于政治控制的独立程度却并不相同。分析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媒体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解中国的国家与媒体关系是有益的。
就新闻媒体的类型差异而言,其差异主要来自媒体的内部要素,如市场化程度、采编部门的不同理念和操作技巧、从业者与宏观制度结构的互动策略、媒体组织领导人及采编人员与地方甚至中央领导层的联系等等。对类型差异性的分析,有助于从新闻生产的微观机制考察新闻体制的运作过程及改革前景。就新闻媒体的地区差异而言,其生成原因更多来自组织外部要素,如国家权力结构、地方党委和宣传部门的管理过程、地方社会的发展状况及文化传统等。对地区差异的分析,有利于揭示传媒体制的宏观结构特点,有助于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政治控制因素如何影响新闻报道的差异格局。
陈怀林对中国传媒体制变迁的地区差异性所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准确概括了经济动力对于传媒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一经济学分析却没有触及宏观层面的制度变革,甚至也无法有效解释中观层面上较敏感的那些制度变革。具体而言,首先出现于上海的恢复广告经营的制度创新,属于底层的传媒经营制度,“收益—成本”分析的解释是周延的。但是,对首先出现于上海、北京、广州的采编制度的创新而言,这一分析路径的有效性则是有条件的。从陈怀林的分析来看,三地采编制度的创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自行扩版;二为批评性的特色报纸和电视栏目[15]。经济制度的创新首先出现于上海和广州,以批评性报道为特色的报纸则首先出现于广州和北京。上海传媒的底层制度创新不仅早于其他地区,而且在京、沪、粤三地也属领先。但是,在中层制度层面关于批评性报道的采编制度创新,却没有在上海随之展开,上海在这一方面的制度创新落后于同属经济发达地区的广州和北京。从批评报道制度创新的总体情况看,在广告资源最为丰富的京、沪、粤三地,唯有上海的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一致,陈怀林的“收益—成本”分析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可见,经济因素是决定传媒体制变迁的重要变量,却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经济因素以外,还有其他变量,如政治因素、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传媒体制下,媒体的批评性报道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新闻专业主义的问题,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如何应对政治控制的问题。因此,解释传媒表现的地区差异性,有必要引入政治结构的相关要素进行政治学分析,从而与现有研究一道形成对于传媒体制变迁的多层面剖析。③
注释:
①参见童兵《传媒监督与执法公正》,《新闻传播》1999年第4期;陈力丹、郭镇之《关于舆论监督的访谈》,《现代传播》2000年第4期。
②孙旭培《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载于展江《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版;齐爱军《新时期舆论监督的三种话语形态》,《当代传播》2002年第12期;景跃进《如何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焦点访谈〉的实践与新闻改革的思考》,《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孙五三《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市场转型期媒介的政治—社会运作机制》,载《新闻与传播评论》,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见邵春霞《新闻生态:宣传控制、市场驱动和专业约束的矛盾互动》,《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45页;以及《局部性传媒公共领域的呈现——以报纸的批评性报道为分析对象》,《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标签:政治论文; 舆论监督论文; 公共领域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