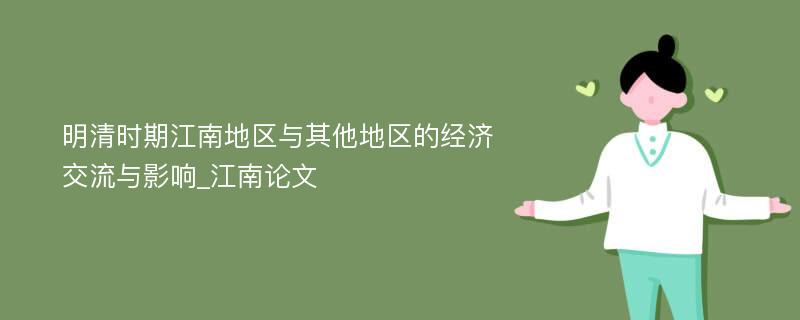
明清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地区论文,明清论文,区域论文,与其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10-0094-10
明清时期,随着各地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流通及对外交流的逐渐增多,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明清江南地区丝、棉专业种植区的出现,商品流通的繁荣,大量工商业市镇的崛起,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等等,与这一总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密不可分。这也使得江南经济得以和闽粤、湖广及华北、西北、东北等不同地区进行跨区域的经济交流,从而将江南区域市场纳入全国市场体系之中。这一时期,江南与其他区域经济交流的基本格局是,江南地区输出棉花、生丝、丝棉纺织品等农业、手工业品,从其它地区输入粮食、果品、肥料、颜料、木材等农林产品。在这总体经济交流格局大致类似的背后,江南与不同经济区域间的市场联系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与其它区域经济交流中所体现的各不相同、而又相对突出的特殊性,进而探讨江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互动关系以及江南经济对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
一、江南与闽粤地区——建筑于地区分工基础上的经济交流
明代,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的趋势。福建及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蚕桑业也有相当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其蚕桑业的发展尚不能满足其丝织业的需求。明时,广东所出的粤缎、粤纱、福建泉州的倭缎、漳州府的漳纱、漳缎等享誉海内外,其所用蚕丝原料则多来自于江南地区。粤纱虽“金陵、苏、杭皆不及。然亦用吴蚕丝,方得光华不退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于天下,缎次之”(注: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土,亦见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漳缎“丝则取诸浙西,苎则取之江右,棉则取之上海”(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050“泉州府风俗考”;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八,纪遗上。)。每年闽粤客商都要在江南地区大量购丝,“(乾隆时)闽省客商赴浙江湖州一带买丝,用银三四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至于广商买丝银两动至百万,少亦不下八九十万两。此外苏杭二处走广商人贩入广省尚不知凡几”(注:陈学文:《湖州府经济史料类纂》,第63页。)。
福建地区曾是中国棉花种植推广最早的地区之一,但其所产并不能满足其纺织所需。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均有大量棉花南运。太仓州鹤王镇所产木棉尤为客商看重。“木棉产鹤王市者,尤柔韧而加白,每朵有朱砂斑一点,离市十里外即无。闽广人贩归,题市必曰‘太仓鹤王镇棉花’”,“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为邑首产”,“远商海舶捆载而去,民以殷富”(注: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土,亦见嘉庆《直隶太仓州志》。)。
江南地区大量生丝、棉花的输入,推动了闽粤地区丝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其纺织所需有了原料的保证。这里,江南丝、棉等生产资料的南运,已远远超出了自然资源互补的性质,而是建之于江南及闽粤两地手工业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这是明清时期江南与闽粤地区经济交流中的显著特点之一(注:详细数据参阅张海英《明清江南与闽粤地区的经济交流》,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在棉花、生丝等生产资料大量南运的同时,江南地区质地精良的丝棉纺织品等生活资料也大量南运闽粤地区。明清闽粤地区的丝棉纺织品的消费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江南地区。“冬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与棉花皆为正货”(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上海法华乡所产紫花布“专行闽省,本色者各省行之”(注:民国《法华乡志》卷三,土产。)。江苏太仓州双凤乡所产“赤沙塘布纫而密”,为闽粤商贾竞贩(注:[清]佚名:《双凤乡》(抄本),“土产”,引乾隆《支溪小志》;按今赤沙塘属常熟支塘镇。)。福建连江县直到民国年间的新兴机织布兴起前,百姓衣着用布主要来自江南“苏布”。
江南地区大量的生丝及丝织品,也成为明清广州转口外贸的重要货物来源,这对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的崛起意义重大。清前期,每年从广州出口的商品中,茶叶、生丝及丝织品占广州口岸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4-255页。),其中的丝与丝织品主要产自江浙地区。江南丝织品的大量供应极大地支持了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广东地区外贸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江南丝棉纺织业的繁荣。这种区域市场流通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在明清时期江南与闽粤地区经济交流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与此同时,闽粤地区大宗的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业产品也有不少进入江南市场。“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注:王世懋:《闽部疏》。)。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江浙沿海海运贸易趋向繁荣,其商船所贩运货物种类之多,体现了区域市场交流的不断深入。浙江平湖县的乍浦港,“自闽、广来者则有松、杉、楠、靛青、兰、茉莉、桔、柚、佛手、柑、龙眼、荔枝、橄榄、糖,自浙东来者则有竹、木炭、铁、鱼、盐”,出港物品以布匹、丝绸为大宗(注:乾隆《乍浦志》卷一,城市。)。
江南与闽粤地区频繁的商品流通,刺激了闽粤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其经济作物种植大面积增加,也使这些地区出现了米粮供应不足、需仰赖他省的现象。当时江南地区粮食市场上,便有相当一部分输入闽粤地区,以供其经济作物种植区农民生活之需。“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岁虽频浸,而米价不腾”(注:[清]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载《清经世文编》卷四十四。)。江南粮食市场大量商品粮的输入,保证了经济作物种植区农民的粮食供应。
总体而言,明清时期江南与闽粤地区的经济交流,是建之于地区分工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交流,其表现为江南棉花、生丝等生产资料的南运对广东丝棉纺织业的支持;福建蓝靛等染料对江南染织业的供给;江南丝棉纺织品与闽粤果品、糖霜等农产品的相互交流以及江南粮食市场上大量商品粮的输入,对闽粤地区以果木、烟草及蚕桑业为主的农业商品化发展的支持等方面。清政府广州独口通商政策曾一度带来了广东地区外贸发展的高潮,江南丝棉织品的大量南运供应成为广东对外贸易发展的强有力后盾,同时,广东外贸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刺激了江南丝棉纺织业的繁荣。这种区域市场流通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在明清时期江南与闽粤地区经济交流中尤具有独特的意义。
二、江南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联系——全国最大商品粮基地的形成
明代,长江中上游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以至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
在江南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商品贸易中,米粮输入占据相当成份。一般而言,若非大灾歉收之年,明代江南地区尚不需要大规模的外粮输入,通过江南地区内部的区域调剂,能够基本保证本区粮食所需(注:参阅张海英《清代江南地区的粮食市场及其商品粮流向》,载《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6期。)。从方志及大量的清代奏折记载来看,大规模的米粮输入江南地区,主要是在清代。米粮供应区主要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安徽、江西、两湖及四川地区,其中尤以两湖地区为多。沿江东下之米,大多聚集苏郡的枫桥,再由此转销上海、福建。苏州的枫桥成为当时江南地区最大的米粮转运中心。从李煦奏折中可以看出,清代江南地区与两湖地区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上游地区输入江南地区米粮的早晚或多寡,直接影响着江南地区的米价波动(注:《李煦奏折》第42、122、203页。),“来船稍阻,入市稍稀,则人情惶惶,米价顿长数倍”(注:《清穆宗实录》卷三一四、卷五七。)。而且,江南地区对外来粮食的这种依赖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江苏省各府县产米不敷民食,向赖湖广等省商贾贩运”(注:《清穆宗实录》卷三一四、卷五七。)。
长江中上游地区米粮的大量输入,既对江南地区粮食市场的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又使江南丝棉纺织品农户的粮食来源有了保证,促进了江南地区丝棉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多种经营的发展,江南地区大量的丝棉纺织品也因此而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各地。清代,汉口市场上诸种高级棉织品如毛蓝、京青、洋青等多来自苏州和松江地区;丝织品种如贡缎、广缎、洋缎、羽毛缎等,多来自南京、苏杭、湖州等地。乾嘉年间,汉口镇内的江南及宁波帮约60-70家,交易货物以棉花、海产物、米、帽子、绸缎为主,年交易额约3000-3500万两,占总交易额(14950-16000万两)的21.88%-23.41%,与在汉口的潮帮、广东帮及香港帮(年交易额为3500万两)并驾齐驱(注:据吴量恺《清代经济史研究》数据统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0、89页。)。江南商品在两湖地区市场的影响可见一斑。
大规模的米粮流通,也带来了两湖地区商品市场的繁荣。以汉口而言,汉口作为当时内地货物之一大集散市场,各种生业,无不可行。俗称“八大行”者为其中最盛之商业,年交易额达9670-10070万两。其中粮、棉、油三项交易几近占总交易额的70%(注:据吴量恺《清代经济史研究》数据统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0、89页。)。清代汉口的繁荣与其数量庞大的粮食运转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在两湖地区输往江南的商品中,除大宗的粮食外,还有大量的木竹。清代,江南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其造船业、造纸业、刻书及木器家具等也堪称一流。同时大量市镇的兴起而带动的建筑行业的大规模发展、以及绵长的海岸线上海塘的修筑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木竹。而江南地区内部所产木竹远远不能供其所需,每年都要从福建、贵州、江西及至长江中上游地区输入大量的木竹,形成了一个需要量相当可观的木竹市场(注:详细数据参阅张海英《清代江南与两湖地区的经济联系》。载《江汉论坛》2002年第1期。)。
清代江南与长江中上游两湖等地大规模的粮食、丝棉织品及木竹等大宗商品的流通,反映了同时期全国性商品市场网络体系的发展与成熟,其对两地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就江南地区而言,大量商品粮的输入,保证了江南丝棉经济作物种植区农民的日常生活及粮食的各类生产资料性消费,促进了江南丝棉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多种经营的发展;与此同时,它也丰富活跃了江南地区的粮食市场。必须看到,沿江而下的大量商品粮,并非全部由江南地区内部消费,还有相当部分藉此中转沿运河北上山东、直隶地区,或南运福建等地。粮食市场的活跃推动了江南与闽粤、华北等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加强了国内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各不同经济区区域性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对上游地区特别是两湖地区来说,大量商品粮的输出,也同样刺激了该地区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清代全国最大的稻米产区。清代两湖米价始终保持平稳趋势,使得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粮食、商品流通得以维持和加强。江南地区做为两湖地区商品粮的长期固定的消费大户,其市场流入量占两湖粮食外流总量的3/4有余,这对促进两湖地区以稻米为主的商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其成为清代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基地,功不可没。
另外,在江南与两湖地区的经济交流中,清代两湖地区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对江南棉布传统市场的影响值得关注。从方志资料来看,两湖棉布主要销向是西北秦晋、西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及东部闽西、赣南地区。这一销售格局对江南地区棉纺业的影响则是,直接扼制了江南棉布在中西部市场的销售空间。笔者曾撰文指出,虽然从明代开始,江南地区就成为全国主要的棉纺织品生产基地,但始终缺少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发展为后盾,其产品缺乏为其自身开拓市场的能力,在生产效率上并无太大的优势可言,再加上长途贩运的费用,其产品在同外省区产品的竞争中,并无绝对的取胜把握。因此,清代江南棉布在远距离区域市场的销售额急剧下跌。在全国其他地区棉纺业相继兴起的情况下,江南棉布难以继续保持其空间范围的市场优势(注:参阅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1期。)。清代,华北等棉纺业的兴起已使江南棉布失去了大部分的北方市场,而两湖地区棉纺业的发展则使江南棉布在中部、西南地区的市场上受到排斥。但对两湖地区而言,它反映了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使得该地区的总体经济势力随之提高。这对江南经济而言,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随着清代全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提高,江南与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层开。
三、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官方市场强有力的支持
明清时期,江南与西北地区的贸易往来中,官方贸易(如边境贸易、茶马互市)和边防驻军对江南丝、棉织品的需求等官方市场是一重要的内容。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交流,也是明清南北经贸联系的重要渠道,它对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地理位置、气候的关系,明代,西北地区是江南丝棉织品的一大用户。其时民间所需布匹基本仰赖内地提供。除关中供应部分外,其余绝大部分从江南地区购买贩运。据叶梦珠《阅世编》载,明时松江府所产木棉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注: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褚华《木棉谱》亦载,“关陕及山右诸省设局于邑收之(松江标布)”。可见资本雄厚的晋陕布商,是江南棉布业的重要客户。
但是,同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有所不同,明清两代江南在同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官方市场的主导作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明代九边戍军的需求量不容忽视。正如藤井宏所指出的,“明代在华北诸省的北部、长城沿线一带,横贯着一条作为巨大消费地的军政地带,从全国各地以租税的形式收取上来的白银都挥霍在这里了。与此相应的,华中、华南的物资也以这一地带为目标被源源不断地运来了”(注:[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二章,《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从而形成了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军事消费群体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注:详细数据参阅张海英《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兼论“官方市场”对江南经济的影响》,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当时九边所需各类物资中,以粮、棉等日用必需品为大宗。边军所需的大量棉织品大多从内地贩运而来。棉布不仅用来为边军制作冬衣御寒,还常常折为军饷和战功奖赏品发给士兵,故而需求量非常大。据严中平先生估计,明代政府及军队所需棉布和丝织品的供应,约在1500-2000万匹之间,明中叶以后除少量征收本色外,百分之八九十是从市场购买的。军用之中又以九边需量最大,再加上互市的需要,数量至少在五六百万匹几至一千万匹(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二章,《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当时所需棉织品一部分取之关中泾阳、朝邑、大荔等县,另外绝大部分则从江南地区贩运。因此,明代江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经济联系中,江南棉布的大量输边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江南绸缎也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内容。明政府与边境各少数民族贸易中的互市缎,大多购自江南地区。每年西北“宣、大、延、绥、甘肃遣官赍银数万两,买互市缎”(注:光绪《苏州府志》卷七十,“名宦”引顾炎武“寇公墓志”。)。江南丝织品还曾一度是各地呈办织造的重要内容之一。山西潞安“每岁织造之令一至,比户惊慌,本地无丝可买,远走江浙买办湖丝。打线染色,改机挑花,雇工募匠,其难其慎”(注:乾隆《潞安府志》卷三四;陈学文:《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第64页。)。这一官方市场也成为江南丝织品形成全国性市场的重要因素。
清代,官方所需的大量棉布仍有许多来自江南,虽然这中间并非是全部运往西北地区,但这种官方市场仍然存在,象军需品、官方的茶马互市等等。李煦奏折中有许多即为向康熙帝汇报在江南地区采买各类布匹事宜。山东临清是松江梭布的最大集散地,朝廷委派官员去江南实地采买者,需借道临清北上,而各路商贩自行贩运北边销售者,有相当数量棉布购自临清市场(注: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清代,江南丝绸更成为清政府与西北边境少数民族贸易的主产品,其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绝对的优势。据林永匡、王熹的研究,以数量言之,乾隆时在90%以上,嘉庆和道光前期在85%以上,道光后期到咸丰三年贸易结束在90%以上。
官方市场及边境贸易带来了西北地区商品流通的繁荣及西北商人的活跃。当时边防所需的大量棉布多由晋商从江南地区贩运而来,也使得晋陕地区的众多商人因之致富,为其日后进入全国市场奠定了基础。边境贸易也还增加了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带来了边境城镇的繁荣。“张家口本荒徼,初立市场,每年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自湖广。因广召商贩贸易,号民市。兼收其税,充诸将吏廪犒需。时真有胡越一家气象”(注: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107页。)。宣府原是一个荒寂的小城,明朝成为“九边”重镇,是军队屯集、驻守的据点,后来又与鞑靼部的俺答建立了“封贡互市”关系,因而商业也跟着发展兴旺起来。“先年宣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五五,引万历《宣府镇志》,宣化府风俗考。)
应该看到,就明代西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而言,无论其商品交流的品种,还是其购买力,都还远未达到与江南地区有如上规模商品流通的程度。在这“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的背后,是庞大的官方市场的强有力的支持,因而其商品市场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清代,随着周边环境的逐步稳定,驻边军队大量减少,边境贸易便急剧衰落。“及大军既撤,仅留守戌官军,食口既少,则所需不繁,货价大减。……商贾为之色沮,落魄失业者,比比皆然”(注: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107页。)。另一方面,由这种官方市场所带来的农业、手工业品的商品化,有其自身的两重性。就江南地区而言,庞大的官方市场确也刺激了明清江南地区棉花种植与棉布纺织的商品化,政府需求实际上成为织户棉织品最可靠的市场保证。但这种市场容量带有很大的虚假性,从长远的角度看,它又给江南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惰性,使其无需锐意进取,扼制了江南手工业技术更新的积极性与必要性,削弱了其自身拓展市场的能力。松江地区具有长达几百年的棉纺织业发展的历史,却总是在低水平条件下的重复性简单再生产,在生产技术上始终没有出现质的飞跃,与这一官方市场现象不无关联。
丝绸贸易则有所不同。清政府每年在江南采办的贸易绸缎的数额十分可观,在客观上刺激了江南丝织业的发展。丝织品作为消费层次较高的产品,对原材料、生产工艺、花色品种等方面本身要求比较高,而江南地区悠久的丝织业发展历史,使江南丝织品在技术要求方面均能领先于同时期的全国其他地区,及至清代,其产品也能够达到质优价廉,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很强的竞争力。其产品的销售市场也没有像棉织品那样,受到其它地区丝织业发展的挤压与冲击。另外,贸易绸缎对质量品种式样色彩图案都有一定的要求,带动了边疆地区蚕丝和织造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尽管这种丝绸贸易被清政府所垄断,限制和阻碍了两地民间丝绸贸易的发展,但其客观上仍为江南丝织品提供了市场保证。
四、江南与北方地区——总体经济水平提高基础上的经济交流
华北平原地处黄河下游,是我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明代以后,随着政府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华北地区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集市,在数量、种类和集市功能的增加等方面都较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了由集市——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市场组成的市场网络(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卷一,导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尤其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其陆路交通是唯一可与同时期江南水乡交通网络相媲美的地区。这一切均提高了华北地区的经济势力,为明清时期华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奠定了基础。
江南与北方地区的经济交流中,明清两代南北方棉花、棉布市场的变化及清代北方大量豆麦等粮食作物输入江南地区的现象引人注目。
棉花市场方面,明中后期,华北地区棉花种植大规模发展。但由于当时纺织技术优势仍在江南地区,因此,华北地区大量棉花南运,以供江南地区纺织所需。而华北地区所需的棉布则主要来自江南,临清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清代,随着河北、山东等地棉纺织业的兴起,这两地的棉花基本上要供应其本地区的纺织业所需。这时每年虽有部分“北花”南运,但其地域内涵已发生变化,这时的“北花”主要指河南棉(注:参阅张海英《明清江南与华北地区的经济交流》,载《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2期。)。
随着棉花流通格局的变化,棉布的流通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代乾嘉年间,华北地区已形成不少有较大输出能力的商品布集中产区,从而由明代的棉布输入区变为棉布输出区。到清中后期,华北、西北等地的棉布市场已基本上为山东、直隶、河南三省棉布所占领,江南棉布被排挤在外。至此,明代江南棉布大规模运销华北的盛况已不复存在,仅在东北地区尚有一席之地(注: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黑龙江省“布来自奉天,皆南货,亦有贩京货者”。洋布兴起前,宝山高桥所产棉布,“由沙船运往牛庄、营口”(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一,市镇。)。江苏崇明所产小布,“运销青口者为青庄布,四十匹为捆;运销牛庄洋河者为关庄布,岁销约五万匹”(注:民国《崇明县志》卷四,地理志,物产。)。
江南与北方地区棉花、棉布销售格局在明清两代的变化,表面上是“北花南运”与“南布北销”格局的变化,实际上则体现了两地商品流通、经济交流的相互影响。就南北方纺织业的发展比较而言,明代北方棉花的种植尚处于原料供应阶段,反映了江南手工业纺织技术在当时全国经济中的领先优势;随着大量江南棉纺织品的输入,先进的纺织技术也随之传入,清代北方棉纺业的技术水平也随之提高。因此,清代“北棉南运”、“南布北运”的减少也就成为必然。棉花、棉布市场在明清两代的不同发展,反映了区域经济交流中,各区域分工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江南区域经济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同步发展的影响力。
清代,北方大量豆麦等粮食作物运往江南地区,是南北方经济交流的又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大量粮食的跨区域销售,反映了北方地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粮食种植结构的变化、高产作物的引进而带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土地负载能力的提高,成为区域经济交流与发展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
大豆在明代即是山东输往江南的主要商品,清代进一步发展。当时谷物贸易经由陆、海两线进行,山东豆麦南下多经运河,东北粮食南下多从海路。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以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山东、东北等地与江南的贸易大为增加。《清实录》中的大量有关粮运奏折表明,清代江南市场对北方粮食已有相当的容量,北方豆麦杂粮已成为江南粮食市场的重要内容。“关东每岁有商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曰‘沙船’,其大可容二千石。其人皆习于海,其来也,则载豆麦杂粟,一岁二三运以为常,而其去也,则仅易布帛棉花诸货物”(注:晏斯盛:《上制府论布商易米书》,《清经世文编》卷四七,户政二二,漕运中。)。清后期,“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注:包世臣:《中衙一勺》卷上,《海运漕议》,载《安吴四种》卷一。)。
豆麦南运成为沿河各关口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据许檀研究,运河各关粮食在关税总额中的比例大致为:乾隆七年至乾隆十三年,临清关为60.7%,淮安关为62.3%,扬州关为32.7%,浒墅关为50.5%。乾隆八年,在淮安关过境粮食、梨枣棉烟饼油(北货)、绸布姜茶及各项杂项(南货)的比例分别为62.3%、7.0%、25.3%;乾隆十年分别为61.9%、11.1%和16.2%(注: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日本学者香坂昌纪认为,乾隆前期,淮安关豆税约占60%,梨刺占17%,合计北货超过70%,南货不超过23%(注:[日]香坂昌纪:《清代中期の浙西にぉけゐ食粮问题》,《东洋史研究》第49卷第2号;《清代中期の杭州と商品流通北新关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50卷第1号。)。由此可见,北粮南运的规模已超过了南货北运的规模,说明清代江南对北方粮食需求的增加,而北方对南方丝棉等手工业品的需求量却下降,从中也反映出清代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其经济势力的提高。
北船南运的粮食系列中,众多的大豆及食用油输往江南地区,表明江南地区消费群体的庞大,这与其大量城镇蓬勃发展、城居人口急剧增加不无关联。而其中大量米粮豆麦用于酿酒、豆饼用于施肥等生产资料性消费尤值得注意,它反映了清代江南高投入以求高效益的农业生产模式的需求。清代江南地区,一方面是人口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可供开垦的土地已近极限,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成为江南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人力、物力投入,已成为当时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重要手段。随着农业用肥的普遍增加和需要高投入的经济作物种植的日益扩大,江南本地的传统肥料已不能满足生产的需求,因此,华北、东北等地的大豆及豆饼的大量输入,便成为江南农业高投入、高产出发展的重要支柱。大量粮食的生产资料性消费,反映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及多种经营的发展需求。
清代江南同华北、东北等地的交流,折射出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提高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交流的一些共同性特点:一方面,随着全国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江南地区部分商品的销售市场受到一定的挤压,最典型的莫过于江南棉织品市场在各地空间范围内的萎缩,明代时江南手工业品独树一帜的销售局面被打破。“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注:[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的盛况不再。另一方面,也正得益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清代各地商品市场的容量大增。以江南棉布而言,虽然其在空间范围内的销售区域有所萎缩,但其销售总量并未减少,清代江南棉纺业仍在继续发展,并且对各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继续起着推动作用。由此观之,江南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
五、江南与江西——过境贸易的繁荣
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宋代,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明初,江西在十三布政使司中税粮额高居首位,人口也仅次于浙江,其它如茶叶、纸张、苎麻、兰靛、木竹、油料以及制瓷、造纸、木竹加工等手工业也都在全国占重要地位(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365-366页。)。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其境内商人的活跃和同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奠定了基础。
江西地邻江南地区,因其地利之便,明清时期江南与江西的经济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就商品流通的总体格局而言,基本上仍是江南输出丝棉纺织品等手工业品,而江西则输出稻米、豆麦、瓷器、夏布、纸、木材、烟叶、桐油、茶油、靛青等农副产品,两地在经济上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但是,江西四面环山,只有赣北鄱阳湖与长江相通,故而江西的总体交通条件并无优势。在明清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特别是清乾隆二十二年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江南地区及至全国各地的大量商品便经大庾岭商道输往广东出口,出现了过境贸易的繁荣。江南地区大量的丝棉纺织品以过境转运的形式进入江西境内,对江西的过境贸易带来了很大影响。对此,位于赣江——大庾岭商道上的赣关关税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注:赣州地处江西南部,位于赣南地区上犹江、章水、桃江、贡水、平江五大水系汇聚赣江的交汇处。明正德年间始设钞关,主要抽取江西——广东、江西——福建地区往来商税。五口通商以前,赣江——大庾岭商道是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故而富商大贾“挟重赀以邀厚利,走番舶而通百蛮,必先经赣关”。见乾隆《赣州府志》卷二,关隘。)。
明代赣关的关税收入在全国各钞关中名列前茅。万历八年(1580),赣关税收占全国关税总收入的17.1%,仅次于运河沿线的临清关和杭州北新关,位居第三;万历二十七年(1599),赣关税收占全国总数的14.07%,位于临清关之后,与河西务关、浒墅关不相上下(注:两地经济交流的具体数据参阅张海英《明清时期江南与江西地区的经济联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这期间赣关的税收比九江关要高出许多,反映出大庾岭商路在明代的地位相当重要。明后期,赣关税收在全国关税收入中地位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庾岭商道的衰落。从同时期其它各关如临清关、浒墅关、九江关、北新关等处的关税收入份额日益接近来看,说明同时期全国范围内总体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均有提高,故而带来了全国性商税的普遍增加,往日某一税关的“一花独放”现象不复存在。
清代,全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从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实行广州独口通商政策到道光二十年(1842)五口通商的八十余年间,是大庾岭商道及赣关贸易发展的最高峰时期,也是江南商品途经赣关进入广东的高峰时期。清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中,出口商品主要以丝、丝绸、茶叶、瓷器、土布为大宗,丝、丝绸和土布等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而从江西过境转运输出的江南茶叶、丝棉织品占据相当比重。此外,还有部分湖丝流入江西内地如会昌、安远一带,成为当地葛布(主要以湖丝和本地葛丝合织而成)的主要原料(注:乾隆《赣州府志》卷二,物产。)。
转运贸易的繁荣刺激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一些位于交通要道上的山区小镇因此而繁荣兴旺。如广信府的铅山县,本来只是一个位于武夷山的山区县,但其地处信江中游,是江南钱塘江水系与信江——鄱阳湖——长江航线和赣江——大庾岭商道的连接纽带,也是江南产品进入福建、福建商品进入江西的重要通道,其转运贸易色彩非常浓厚。在明中叶的铅山市场上,几乎可以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其货自四方来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之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洲青、芜湖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之孝感布、临江布、信江布、定陶布、福建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韦坊生布、漆布、大刷竞、小刷竞、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籽花、棉带、褐子衣、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缎、衢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注:万历《铅书》卷一,食货。)。铅山成为全国各地的商品的集散地,其转运贸易的繁荣于此可见一斑。
大量江南商品途经江西南下,促进了江西过境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其沿途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明清时期江西因转运贸易而兴起的七大商业城镇,有五个位于鄱阳湖-赣江-大庾岭商路上(九江、吴城、樟树、赣州、大庾),两个位于信江-鄱阳湖商路上(铅山、玉山)。随着五口通商,长江沿岸城市的开放,大庾岭商路地位不断下降,江南茶叶、湖丝基本上改从上海出口。咸丰后,江西本省所产的瓷、纸、夏布和苎麻等土物产也多转赴九江、汉口等沿江开放城市销售,大庾岭商路不再是外贸转口的唯一出路(注: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七,经政略。)。因此,清同治后,赣关基本上无过境的大宗货物流通,商品种类也大为减少。
赣南地处江西腹里,南负梅岭,岭滩河险,水陆条件并非上佳,大庾岭商路作为清代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外贸大通道,从经济学角度讲,是非经济的。其沿途发展而起的一些城镇主要得益于过境转运贸易的发达。象位于大庾岭商道上的樟树、吴城等镇,在其兴盛前“既无传统手工业技艺,也无特殊的资源可供某一产品在本地得以充分的发展”(注:梁洪生:《吴城神庙系统与行业控制》,载《江西历史研究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它是清政府海禁政策特定环境下刺激起来的繁盛商埠。因此大庾岭商路的繁荣也是清政府限制海外贸易尤其是实行一口通商的结果,它不单纯是清代商品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和体现。如同政府官方市场也曾带来了明清江南与西北地区商品流通的繁荣一样,明清江西与江南地区密切的市场联系也带有浓厚的官方政策痕迹。清代江西地区过境贸易的繁荣更多的是政府经济政策影响的结果。
六、结语
总体而言,明清时期,江南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仔细考察明清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市场流通状况,可以看出,江南商品流通的触角遍及全国各地。其丝织品的输出,“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抵五岭、湖湘、豫章、南浙、七闽,溯淮、泗,道汝、洛”(注: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食货志。);棉织品也同样是“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对”(注:[清]钦善:《松问》,《清经世文编》卷二八,户政三,养民。)。可以说,江南地区商品流通的繁荣、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同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以及其产品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清代各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各地区的总体经济势力也随之提高。就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而言,无论是闽粤地区果木、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和蚕丝纺织业的发展、出口贸易的繁荣,还是两湖等地最大商品粮基地的形成,江西过境贸易的繁荣、华北、西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和东北地区的开发等,无不与江南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反映了封建农业、手工业较为发达成熟,并处在稳步扩大国内市场的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商品化过程。江南在同各区域的经济交流中,互相开拓市场,共同促进商业的发展,活跃了各地的商品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体现了江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密切的互动关系,也从中反映了江南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龙头作用。从明清江南与各区域的经济交流来看,江南经济的发展仍有相当大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