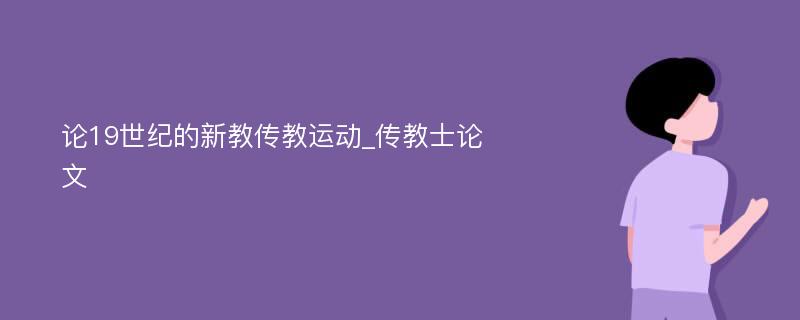
论十九世纪新教传教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被欧美史学界称为“新教扩张的世纪”。在此世纪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各国差会纷纷投入海外传教的大潮,导致新教在教派数量、信徒人数、组织机构以及地域等方面的显著扩张,进而引起基督教文化与非基督教诸文化大规模的再度接触与冲撞,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鉴于国内此方面研究欠缺,本文欲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其作一宏观考察。
一
种种迹象表明,19世纪西方社会文化背景对传教事业并非十分有利。18世纪的启蒙思想仍在发挥影响。启蒙思想家高扬理性的大旗,用理性法庭来审判与检验一切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保守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基本原则遭到批判与冲击,到19世纪,已被驳得体无完肤,只剩下道德一项了。现在“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忽视宗教在指导思想和行为方面的作用了”(注:John Dillenberger,
Protestant
ChristianityInterpreted Through It
Development, Macmillan
PublishingCompany, New York,1988,p.146.)。同时,发端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有助于形成一种漠视宗教的氛围。尤其在19世纪后半期,地质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生物科学的长足进展,打开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问题魔盒,如传统基督教世界观的可信性,《圣经》中叙述的世界与人类起源的可信度等,都受到了普遍的怀疑。而科学方法的成功表明人类已经找到了发现真理的方法,宗教对真理的特权被人们置于脑后了。与此同时,西方各国政教分离的趋势日趋明朗。1791年《美国宪法权利法案》修正案第一条即规定,禁止确立任何宗教为国教;1830年英国改革对国教安立甘宗的特权也作了种种限制;在欧洲大陆,这一趋向受到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改革及其东征的推动,不仅为法国政教最终分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废除了德国等长期遵循的“教随国定”原则。
这些迹象表明,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浪潮得到了加强,“宗教”与“俗界”分裂了,信仰生活变成了一种与政界、商界无关的事;在宗教生活内部,教会人士与普通信众开始脱离,“许多牧师整天赌博、狩猎、酗酒,毫不掩饰他们对周围奄奄待毙的人们漠不关心”(注:斯威特:《美国历史上的卫斯理宗》,纽约1933年版,第39页。)。世俗社会正式出现了。反映在灵性生活上,便是各教派都处于死气沉沉的状态,“引领教外人士入教的工作极少开展。下层阶级处于灵性贫乏的状态。群众的娱乐活动鄙俗不堪,文盲到处可见……酗酒之风盛行”(注: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4页。)。据此,有学者断言,19 世纪是基督教势力在西方大衰落的时代,新教教会的生命力与影响受到了严重削弱,甚至是完全衰竭了(注:John Dillenberger,Protestant ChristianityInterpreted Through
It
Development,Macmillan PublishingCompany,New York,1988,p.147.)。
另一方面,兴盛于18世纪的虔诚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在19世纪仍有持续的影响与进一步发展。对于笃信上帝者而言,浪漫主义反映了一种不忍背离传统信仰的心态,一种与传统上帝难以割舍的情绪。大多数浪漫文学都表现出对传统精神家园的渴望与回归,受此思潮影响的人,都是生活于现时,却心怀中古。而虔诚主义者们的生活,则为那些不愿抛弃传教的人树立了敬虔圣洁生活的榜样。虔诚主义的核心人物是斯彭内尔(P.J.Spener,1635~1705),他提倡读《圣经》,反对死守信条;追求内心虔诚与圣洁生活,注重行善。该派思想与实践在18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流传甚广,对英国也有影响。其最有名的团体是1722年成立的摩拉维亚兄弟会,该会极力宣扬自己的灵性生活,鼓吹宗教热忱,并自视为“世上的盐”,要将一种“心的宗教”传播到整个基督教世界。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宗教生活的复苏。
因此,19世纪新教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西方社会正远离传统,这是物质与技术力量进步的自然反映与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人们还难以彻底割舍传统的纽带,还希望有圣洁的生活。那个时代需要一种直接向内心信仰的召唤,以激发出活跃的灵性热情。18世纪30~40年代卫斯理兄弟在英国、爱德华兹和怀特菲尔德在北美发起的福音奋兴运动代表了这种努力。他们不断地巡回布道,宣扬一种洗心革面使人重生的转变,强调悔改归正,在积极为他人服务中体现宗教生活,切实打动了人们的心弦。英、美随之出现了数百个奋兴团体,最著名的是“牛津圣社”,它稍后发展为卫斯理宗。卫斯理等人的活动彻底改变了英国人尤其是中、下层阶级的宗教状况,重新激发了人们的宗教热情,对美国的影响甚至更大、更持久,以至出现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奋兴运动也得到了其他新教教派的积极反响。19世纪时,英国自由派信众增加一倍以上,由不足100万增至200万。1910年, 其教堂的信众座位已达8788285个;当时英国国教教堂有7236427个座位。1849~1899年间, 卫斯理宗增加了34万信徒(注:克莱顿·罗伯兹等著:《英国史》,下册,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53页。)。故有史家说, 奋兴运动“与工业革命一样有力地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注:克莱顿·罗伯兹等著:《英国史》,下册,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658页。)。
奋兴运动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人们宗教热情的空前高涨,同时也产生了一批新的宗教团体。这就使得新的、旧的新教团体在19世纪面临着如何竞争会徒与维持其忠诚等问题。灵性奋兴毕竟只是一种精神激励,它的对立面是日益强大的世俗社会,当国内灵性激发的工作达到极限后,宗教热情就难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退。为不使信徒重陷世俗社会的泥沼,对外传教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可以说,传教运动是新教各派面对世俗化社会的一种应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各教派为维系国内信徒的宗教热情而采取的一项必然措施。美国学者妮尔丝在考察美国传教运动后,也认为“海外的传教运动也就是让宗教狂热一直能在美国持续下去”的手段(注:P.C.妮尔丝:《美国传教士对美国对华政策之影响》,载李本京主编:《美国基督教会对东亚之影响》,正中书局1991年版,第 9页。)。当传教事业展开后,其成功与否常常成为人们判断一教派是否健康发展的标准,当时英国人普遍认为,“一个生机勃勃、圣洁、有责任心的教会必然是一个传教士不断扩张的教会”(注:Robert A.Bickers and Rosemary Seton ed.,Missionary Encounters:Sourcesand Issues,Curzon Press,1996,p.14.),这种观念影响着人们对效忠教派的选择。只有看到此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19世纪有如此之众的新教团体在自筹资金的情况下纷纷投入海外传教的大潮。
除上述因素外,19世纪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成功也为传教运动的广泛展开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率和异常丰富的工业产品,为扩大国外市场,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以英、美为首的新教国家不惜仰其船坚炮利的优势,打开亚、非、拉地区诸国的大门,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这为传教士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其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国民生产总值急剧增加。以英国为例,1851年,其国民生产总额为五亿二千三百万镑,至1870年达九亿一千六百万镑。1800~1850年间,英国个人收入增加了85%。在19世纪中期,英国个人平均所得达32.6镑,同时期法国人均收入为21.1镑,德国为13.3镑(注:克莱顿·罗伯兹等著:《英国史》,下册,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00页,第652页。)。正是有了这种坚实的经济基础,英国人才能响应差会的号召,每人每年捐献一镑资助传教事业。最后,工业革命为西方带来的普遍而持久的繁荣,强化了其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并在19世纪末发展为文化帝国主义。欧美人普遍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种族优越、宗教优越,力图建立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因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他们贬低、藐视一切异己的非欧洲民族与文化,视欧洲之外为蛮荒野性之地,非欧洲人为蛮种,尚处于“蒙昧”与“野蛮”阶段,需要他们去实施“文明开化”,并将之视为“白人的负担”或“上帝赋予的使命”。这种傲慢、自命不凡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是19世纪欧洲民族性的基本特征,也是传教运动的动力之一。当然,当传教士本着这种思想去实施其传教之职时,必然引起剧烈的文化冲突。
二
新教大规模传教运动的开端被公认为是1792年出版的一份小册子,名为《论基督徒有使用各种方法归化异教徒的义务》,作者是新教近代传教运动先驱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1761~1834), 他在此书中针对新教各派不注重传教的现象呼吁,基督徒应按照《新约》中的要求,“使一切国家实现基督教化”,并认为这是当代基督徒应尽的义务。在他的影响下,各教派的福音派人士开始关注传教,形成了新的传教神学,认为一切基督徒都有参与改变世界各民族宗教信仰的义务,基督所说的上帝之“道”是对全人类说的,闻道者应当是使之达于异教徒之耳的媒介,福音不是欧洲人的私有财产,应与世人分享。这样,在新教教会中出现了一种将福音传遍全人类的新的普遍冲动。当时广为流传的一首赞美诗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从格陵兰的冰山/到印度的珊瑚滩/还有非洲那滚动金色沙泥的/阳光灿烂的喷泉/从无数古老的河流/到数不尽的繁盛平原/都在向我们召唤/让他们的土地摆脱错误的锁链……。”(注:John Dillenberger, Protestant ChristianityInterpreted Through It Development,
Macmillan
PublishingCompany,New York,1988,p.153.)新的传教运动是面向整个世界,正如新教布道家威兰德在1824年一次布道会上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国土是整个世界,我们的目标是使整个人类发生一次全面的道德革命。”(注: John Dillenberger,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terpretedThrough It Development,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New York,1988,p.154.)
在新的传教神学的影响下,欧美各国新教教派纷纷建立了各自的差会。英国第一个海外传教组织是“浸礼宗广传福音会”,1793年由威廉·凯里建立。两年后,由公理会发起组建了一个跨教派性的“伦敦传教会”,这是新教最有影响的差会之一。1796年, 苏格兰传教会建立。 1799年“国教会传教会”也告成立,这是19世纪传教范围最广、输送传教士最多的差会。此外,本时期建立的差会还有“卫斯理宗美以美传教会”、“高教安立甘宗广传福音会”、“格拉斯哥差会”等。美国在新教传教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英国,其组建差会稍晚。第一个规模较大的差会是1810年成立的“美部会”,其1812年派遣5 名传教士去印度被视为美国参与海外传教事业之始。其后,相继出现了“美国圣经会”、“联合基督徒传教会”、“浸礼宗印度与外方广传福音会”等组织。在19世纪后期,随着传教活动的扩大,美国出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志愿传教团”,它以“在这一代就使世界福音化”为座右铭,为传教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欧洲大陆较著名的组织有:巴塞尔福音传教会(1815年)、丹麦传教会(1821年)、巴黎福音传教会(1824年)、莱比锡路德宗福音传教会(1836年)、德国北方传教会(1836年)等。芬兰、挪威、瑞典等新教国家也相继组建了一些差会。
19世纪到底有多少新教差会,目前尚无精确的数字,但我们可稍作推断。1836年时,英国只有10个差会,至1888年达100余个。1888 年春,世界新教差会在伦敦举行一百周年纪念会,共有193个差会的1579 名代表参加。其中来自英国的有53个差会、1316名代表;来自大陆、殖民地及美国的差会共85个、263名代表。由此推知,19 世纪末新教差会当不下数百个(注:Robert A. Bickers and Rosemary Seton ed.,Missionary Encounters:Sources and Issues,Curzon Press,1996,p.11.)。当然,在整个19 世纪, 英美始终是传教运动的主力,如1900年,新教传教士共13600人,其中英国5900人,美国4100名, 两国共占3/4(注:唐逸主编:《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传教事业是一项耗费人力与物力的昂贵事业。在传教运动初期,差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内信徒的捐献,当时多数教派都号召,每个信徒每年捐1镑资助传教。随着传教范围的扩大, 通过此方式得来的资金显然不能满足要求,必须开拓新的资金来源。各教派从30年代起,开展了各种寻求社会各阶层广泛资助的活动,并建立起各自的国内宣传与筹集资金的差会附属团体。各差会一般均在伦敦设总都,在全国各地设立代理机构或地方性的传教协会。其主要活动,一是散发各种宗教书刊,报道海外传教消息,宣扬传教事业。从40年代起,各差会发行的各种书刊急剧增长,如1898年,国教会传教会散发的各种杂志每月达216000份,季刊、小册子尚不在内;至1899年, 其发布的各种书刊已达 750 万份(注:Proceedings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London,1895,p.37.)。二是招募人员(主要是妇女、儿童)从事挨门挨门的捐款工作。三是组织各种巡回演讲、布道与集会活动,激发民众对传教士的资助。如国教会传教会在1874年就组织了5000次布道、 4000 次集会(注:Robert A.Bickers and Rosemary Seton ed.,MissionaryEncounters:Sources and Issues,Curzon Press,1996,p.24.);在19世纪末,其伦敦总部每年大约要组织2000次集会和演讲,而分会安排的活动则达8500次以上(注:"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tHome",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r,n.s.7 (April 1882),p.194.)。再如高教安立甘宗广传福音会,在1898 年也组织了 136 次集会、 671场演讲(注:Robert A.Bickers and Rosemary Seton ed.,Missionary Encounters:Sources and Issues,Curzon Press,1996,p.25.)。这些讲演由差会干事、教区牧师、代理传教士或归国休假的传教士进行。一名从印度回国度假的传教士A.H.拉什在1875年为国教会传教会进行了三个月的巡回演讲,他不断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面对人群布道,听众达3万人以上(注:Lash deputation diary,1874—1875,p.41.转引自前揭 R.A.Bickers & R.Seton 主编书,pp.24~25.)。其四,在地方上建立各种资助团体。19世纪40年代,由地方传教协会组织的各种捐募活动,每年一度的传教庆祝会、传教布道、公共集会、和散发书刊等活动即已布满了全英国。到80~90年代,几乎所有教派都成立了妇女协会、青年协会、俗人协会、青年教士协会、儿童协会这样的地方性资助团体。不少教派还发动妇女组成工作组,如1888年成立的“赤道东非工作组”。其工作是从事针线活和制衣,产品义卖,所得用以资助某一差会。总之,至19世纪后期,国内资助传教的工作已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
上述谋求各阶层广泛资助的活动极见成效。在1895年,英国各地方性团体为国教会传教会举行义卖所得达21555镑,占其总收入的14.5 %,从捐献箱中所得为31704镑,占21.3%(注: Proceedings of the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London,1895,p.27.)。 在1860~1884年间,安立甘宗用于传教的资金达1010万镑, 年均 42万余镑 (注:Official Yearbook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London,1886,pp.xvi—xix.)。到1899年,英国传教经费已达160万镑,占国民消费总额的0.01 %(注: B.R.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Cambridge,1988,p.83.)。 尽管19世纪后期,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多的财团加入了资助传教的行列,但普通人的捐献一直是传教资金最重要的来源。正如当时英国国教差会秘书芬恩所说:“那些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而自愿提供帮助的捐款者是我们在人力上必须依赖的。 ”( 注:Robert A.Bickers and Rosemary Seton ed.,Missionary Encounters:Sources and Issues,Curzon Press,1996,p.17.)
三
19世纪新教传教运动较之以往的传教事业具有一些截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同样体现了其民间性质。
首先,相对而言,它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属于自主传教。众所周知,天主教近代传教活动一直得到西班牙、葡萄牙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而东正教则受到沙俄政府的庇护。但在新教国家,由于受到政教分离趋势的影响,国外差会并未受到政府的经济资助,亦就没有受到随之而来的国家对传教活动的干预与控制。从传教方针与策略的制订、差会的组建、传教士的培训,到传教经费的筹集,都是由各新教教派自行规化的。在国外,传教士的活动与政府的利益也不是全然相容的。东印度公司曾阻止传教士入印传教。在中国,19世纪英国官方文件表明,绝大多数英国官员根本不指望“通过传教士的影响”来促进女王政府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反,他们认为传教士是顺利发展中英贸易的障碍,用克拉伦顿勋爵的话来说,这些传教士是一些“需要提防自己的人”,此即警告他们少惹是非,以免给政府带来麻烦(注:(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4页。)。再从传教士方面来看, 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毕竟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则是忏虔的基督徒,一心传教,对政治持不过问、不参与的态度,相当部分的传教士如中华内地会的成员甚至拒绝利用“传教宽容条约”赋予的种种治外法权。传教士与政府的合作一般仅限于传教初期,当时不少传教士针对东方国家的锁国政策,曾积极鼓吹武力,但正如费正清所说,一旦门户洞开后,“传教士就只当传教士了”(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页。)。因此,从根本上讲, 新教传教运动只是一场民间组织的运动,其本身并不代表任何政府意图。
其次,传教运动的民间性质也体现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上。传教运动并不是新教各派的单个行为,而是一场全国性的民众运动,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该运动。从传教士的出身看,既有出身贵胄的上层人士,也有来自社会底层的贫贱百姓。大卫·李文斯顿“由纺织工人转变为传教士”、威廉·凯里原为鞋匠、斯都德出身贵族,但皆为传教士精英。美国传教士大多也来自小城镇和穷乡僻壤。再以差会经费来源看,有个人捐赠的,也有学校、工厂、财团集体性资助的。农村对传教运动同样热心,在19世纪英国广大农村,几乎到处都有募捐者在活动甚至竞争。实际上,每个乡村堂区都会因这个或那个差会的传教士请求而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捐款活动(注:Robert A.Bickersand Rosemary Seton ed.,Missionary Encounters: Sources andIssues,Curzon Press,1996,p.22.)。英国各差会的刊物记载了各种资助款项,依其不同来源可分为三类:偏僻乡村、北部工业区和富庶的南方城郊,连城市贫民窟也提供了相当捐款。据1900年广传福音会的一份统计资料,在城市住宅区,花1镑组织费用可捐得14镑14先令, 在工业区可得9镑,在相对贫困的农村也能捐到6镑10先令(注:Robert A.Bickers and Rosemary Seton ed., Missionary Encounters:Sources and Issues,Curzon Press,1996,pp.23—24.)。英国当时有13650个堂区,其中10441个(占76.5%)资助过“国教会传教会”与“高教会安立甘广传福音会”,其余3029个堂区虽未资助这两个差会,却是“大学中非传教团”、“中华内地会”及某些特殊差会的坚强后盾(注:Proceedings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London,1895,p.16.)。
美国学生传教运动领袖穆德说:“在许多人头脑中都有一种印象,传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妇女从事的运动。”(注:J.R.Mott,The Home Ministry and Modern Missions:A Plea for Leadershipin World Evangelisation,London,1905,p.73.)他说这段话的目的是号召更多的男性投入传教事业,但也道出了这一事实:妇女在传教运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1868~1912年间,美国各大宗派均成立有女子海外差会,共派出女传教士200万(注:Charles H. Lippyand Peter W.Williams,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ReligiousExperiences—Study of Traditions and Movements, New York,1988,p.1446.)。妇女所占比重也逐年增加,如1898年,美国在华医药传教士共111人,其中男68人,女43人(注: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92页。)。1900年,在华新教士共1800人, 其中女710人,所占比重达39%强(注: Marshal Broomhalled.,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China Inland Mission,London,1901,pp.316—323.)。1880年美国国外传教人员中,女子占57%,至1883年达到60 % (注: Charles H. Lippy and Peter W.Williams,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Religious Experiences—Study ofTraditions and Movements,New York,1988,p.1446.)。 在国内主持资助差会的工作中,妇女所起作用更大,几乎所有差会都依赖女性进行捐款工作。到19世纪后期,各差会都建有自己的妇女协会。她们不仅自己充当挨门挨户的募捐人,也是组织捐款工作的干将。英国国教差会的一官员评论说:“在绝大多数教区,甚至是那些妇女并无正式职务的地方,她们正在为那些在册教士而忙碌工作,而作为募捐人,妇女实际上有一片净土。”(注:Georgia A.Gollock,"The Contribution ofWomen to Home Work of C.M.S.", reprint from the ChurchMissionary Review,December,1912,p.5.)在各差会的资助性团体中,妇女成员占有绝对优势。“拾穗者协会”(Gleaner's Union )是英国国教差会最重要的资助团体,它使该差会收入从1880年的228 000 镑增至1900年的405000镑。其7万成员绝大多数为女性,在1128名干事中,970人为妇女,占85.9%。国教差会所属的另一团体青年协会,85%的成员为女性;其医药传教附属团中,妇女所占比重也达75%(注:RobertA.Bickers and Rosemary Seton ed., Missionary Encounters:Sources and Issues,Curzon Press, 1996,p.33.)。可见,妇女对传教运动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无法替代的。正因如此,在19世纪末,英美新教各派大多提高了妇女在教会中的地位,出现了女执事、女牧师。在当时妇女普遍没有社会地位的情况下,她们的广泛参与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事实本身即证明了传教运动的民众性质。
保罗·科恩对近代西方人来华动机曾有一段评论,他说:“19世纪,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外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4页。)这一评论虽然美化了传教士的目的, 但与商人及外交官相比,传教士的活动的确带有更浓厚的人道色彩,他们在殖民地国家广泛开展各种人道主义活动,如建医院、学校、医生护士培训中心、将土著语言简化为文字、翻译《圣经》、译介西学、推行公共卫生事业与较高的农业技术,开展各种社会工作等。以传教士在华医疗卫生事业为例,1877年共计建有医院16所、诊所24处;1889年,在华40个新教差会中有21个从事医疗活动,共有61所医院、44处诊所,一年诊治病人达348439名(注:Kwang—Ching Liu,American Missionaries inChina,Harvard Univ.Press,1966,pp.104—105.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305页。)。传教医生增长较快,1881年为34人,1887年60人,1890年达100人(注:前揭Kwang—Ching Liu书,第103页。)。20世纪初,医疗事业有了更大发展,并成为一项专门事业。医院和药房在不足20年里增加了165%。1907年,医院增至166所 (注:WorldChristian Encyclopedia,New York,1982,p.233.)。1914年共有医院265 所、诊所386处(注:Paul A.Varg:Missionaries,Chinese andDiplomats:American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 195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p.92.)。新教在华教育事业发展同样迅速。1875年,新教传教士共建学校350所(注: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 页。)。至1906年,已设有小学2000余所,高等专业学校400所, 其中大学12所。新教学校的学生,1877年约为6000人,1890年16 836人,至1906年达57 683人(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7页。)。办学经费主要由国外差会承担,如大学,差会在20 世纪初负担其费用的63%,有些差会要负担数所学校的费用(如伦敦传教会与英国圣公会均各负担6所)(注: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此外,传教士还广泛投入赈灾、济贫、预防麻风病、盲哑人教育等各项社会福利事业。这些活动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教士的形象,有助于增强殖民地人民对基督教的认同感,但其耗资甚巨,显系仅追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政府所不为的。
四
如何评价新教传教运动及传教士的行为,这在国内外史学界历来是一个争讼不休的问题。国外新教学者多半是颂誉多于诋毁,强调其积极影响的一面,认为传教运动给殖民地国家带去了近代西方文明,传教士是文明的传播者,美国基督教扩张史专家赖德烈甚至认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绝对重要性”(注:K.S.Latourette,Anno Domini,New york,1940,p.169.)。国内学者则大多强调其侵略性的一面,视传教为“殖民扩张的工具”、传教士为“文化侵略者”。两种评论皆失之偏颇。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新教传教运动的性质未作全面认识。笔者以为,从传教运动的发生、经费来源及其种种特征来看,它在主观上是一场民间运动,但因其所发生的背景,又使它在客观上具有殖民主义的特征。作为运动主角的传教士也因而具有了“文明传播者”与“文化侵略者”的双重身份。运动的双重性质使得基督教文化在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接受度的同时,必然更多地是遭到排拒。下面我们即以此为出发点,对传教运动的影响作一简扼评述。
传教运动最直接、最重大的后果无疑是导致了基督教文化与其他非基督教文化大规模的接触,进而引起其他文化不同程度的变迁。这首先表现在信仰层次上。在国内民众广泛支持及传教士的努力下,新教信仰得到了广泛传播,在太平洋诸岛、东印度群岛、印度、缅甸、中国、日本、朝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及拉美等地均获得较大成功,并不断向未皈依之地推进。信徒人数增加较快:新教于1859年传入日本,1913年时,信徒达102790人;印度1815年仅有数千信徒,1914年达100万人(注: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vol.2,Harper & Row,Publishers Inc.1975,p.1330,p.1317.);1807年新教入华, 1840年信徒不足100人,1893年为55093人,1898年80000人, 1900年为10万人,1905年升至178251人,1915年达268625人(注:T.K.Thomas ed.,Christianity in Asia—North—East Asia,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Singapore),1979,pp.13—19.)。在东印度群岛,1914年仅荷兰辖区就有50 万新教徒(注: K.S.Latourette, A HistoryofChristianity,vol.2,Harper & Row,Publishers Inc.1975,p.1321.)。若从地区分布看,1900年的形势是:新教徒共计154457050人,其中东亚 504647人,南亚4 002 940人,非洲2 246 410人,拉美1 694 790人,大洋洲2 707 668人,前苏联2 002 000人,亚、非、拉、大洋四洲共13 158 455人,占全世界新教徒总数的9.3%(注: 《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牛津1982年版,转引自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4页。)。这表明,在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民众中,已有相当部分从其本民族文化信仰体系中游离出来,皈依了新教,接受了基督教文化。
传教运动对亚、非、拉各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同样深刻。19世纪的基督教已成为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载体。它的广泛传播给古老的亚、非、拉农耕文明注入了新的血液,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为后进民族提供了文化竞争与文化选择之机。在美洲印第安人与爱斯基摩人中,当地宗教与基督教因素相结合,对部落习俗作了新的神学阐释,促进了原始部落的现代化进程。“在近代初期的日本,基督教信仰被公认为是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它能为一种近代的市民社会提供精神基础。”(注:T.K.Thomas ed.,Christianity in Asia—North—East Asia,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Singapore),1979,p.45)在印尼,基督教促动了穆斯林改革,使伊斯兰教成为既尊重个人价值、又承认个人社会义务的宗教。在中国,至少新教传教士开办的西式学校、近代医疗与传播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启动因素。实际上,中国近代史上一切经济的(如洋务运动)、政治的(如戊戌变法)、思想文化的变革均与传教士的活动密切相关。由于各殖民国家与地区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各自文化系统的完备性不一,因而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层次也就不一样。但无论是抗拒抑或接纳,无疑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可以说,传教运动程度不同,方式不一地促动或直接启动了亚、非、拉农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传教运动带来的更多是文化冲突与灾难。作为一场由民间组织与发动的文化传播活动,它本应导致基督教文化与其他文化系统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进而加深相互了解与融合。但在这方面,基督教恰恰遭到了非基督教文化普遍的抵制与对抗。中国、日本、印度等地都有“教案”或类似“教案”的事件发生,非洲广为流传的“圣经换土地”故事亦反映出非洲人对传教运动的强烈不满。表现在信众上,就是新教徒的绝对少数,就其所占总人口比例而言,1900年非洲为2.8%(注:《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牛津1982年版, 转引自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 页。);1914 日本为0.5%(注: 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vol.2,Harper & Row,Publishers Inc.1975,p.1330.);1921年印度为 1.5 %(注:Arthur Mayhew,Christianity and the Governmentof India,London,Faber & Gwyer Limited,1929,p.216.);中国从未超过1‰。这些数字无异于宣布了旨在“使世界基督教化”的新教传教运动的失败。
基督教之所以受到如此普遍的抵制,除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诠释与吸收本身存在着种种障碍外,还有两个根本性的原因。一是19世纪西方诸国的殖民扩张与帝国扩张,造成了基督教文化与亚、非、拉文化在势能与性质上的巨大差异,致使平等的文化交流局面难以形成,也就消除了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文化交流系指跨国界的单纯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的交流,当这种交流伴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时,就变成了一种侵略。新教传教运动正是发生在殖民扩张这一背景下,也就改变了其民间性质,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文化输出行为。二是传教运动本身亦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霸权主义倾向。这并非指个别传教士在殖民活动中充当了种种不光彩的角色,而是指他们的言行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精神”。19世纪西方人最深厚的精神气质是欧洲中心主义,传教士也浸染了这种毒素。“让世界基督教化”这一目标本身即含有以基督教文化为标准改造其他文化的意图。传教士们真诚地认为,基督教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应为一切民族所效仿。因而他们根本篾视与排拒其他一切文化,拒不承认其合理因素,必欲彻底根除而后快。这种文化观念上的偏己心态及他们在传教区的作为,都有力地证明,他们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而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宗教或文化乃是每个社会依其特殊历史经验所发展出的产物,每一地区的民情风俗均有其适用与合理性,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文化。传教士无限夸大基督教文化的适用度,极力贬低其他文化的价值,犯了双重错误,亦就难以避免文化冲突与灾难。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交流甚至彼此融合是必要的、可能的,但必须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19世纪新教传教运动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