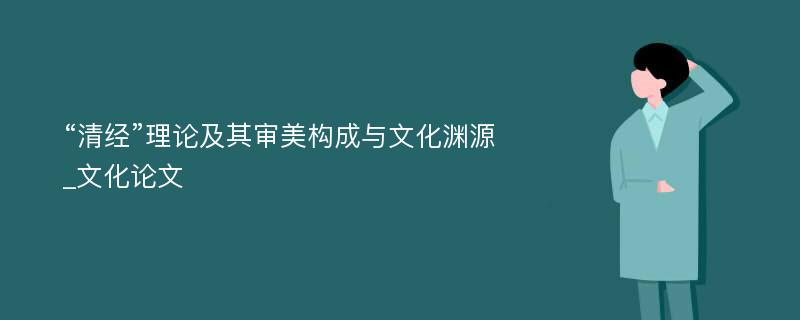
“清静”说及其审美构成态势与文化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静论文,态势论文,根源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美学史上,“清静”一直被看作为一种审美构成境域和最高审美诉求,所谓“诗以清为主”(宋咸熙:《耐冷谈》卷三)、“诗家清境最难”(贺贻孙《诗筏》)。正因为“清”之境域难以构成,因此,才成为历代美学家极力推崇的一种审美构成和审美意趣域。
一
“清静”之“清”的含义是纯净、寂静、明白、廉洁、单纯、点验等,像清楚、清醒、清净、清白、清醇、清淡、清高、清廉等等。“静”“静”是与动相对应的,是指安定、没有声息等,像安静、沉静、平静、清净、静穆等等。构成“清静”境域的心态与途径则是道家所标举的自然而然、清净无为,回归到最初的纯粹构成本源“道”,保持“清静”自然之心,没有一点人世尘埃的污染,悠闲超脱而清净高洁。从而才能在“无常”的世界中求得“常清静”,构成虚静之境域。就其原初的美学意义来看,所谓“清静”,就是“虚静”。作为一种无功利、超功利的纯粹的审美构成境域,“清静”说最早是由老子提出来的。老子主“静”。他认为“静为躁君”,“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在老子看来,“静”是“根”,是“命”,是生命的纯粹的原初构成域。他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1] (十五章)又说:“致虚极,守静笃。”基于这种思想,他指出,只有达成“虚极”“静笃”,才是真正还原到生命的原初,也就是还原到纯粹构成本源“道”。正由于“虚”、“静”是“根”,是“命”,是生命的纯粹的原初构成,所以他认为“清静为天下正”,并在其书中多处提到“静”。如:“重为轻根,静为躁君。”[1] (二十六章)他认为,在“归根”“复命”中,必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保持无欲无为的心态,才能达到“静胜躁,寒胜热”的境域。以“静”胜,“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1] (三十七章)。为什么呢?他形象地比喻道,“牝常(恒)以静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1] (二十三章)。这种“归根”和“复命”式的“静”,究竟是怎样的审美构成态呢?老子对此进行了追问。他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1] (十章)这里所谓的“营魄抱一”“专气致柔”“涤除玄鉴”的描述,深刻而又具象地揭示了“清静”这种绝对纯净的审美构成境域像“玄鉴”一样纤尘不染的特点。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清静”思想,提出著名的“心斋”说。他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可见,所谓“心斋”,就是指的一种纯而又纯的审美构成态。只有达成这种构成态,才可以全性,才可能明察,才可以使意志处于绝对的自由,才可以排除外物、内情的干扰,这时来“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2] (《人间世》),才会感到四堵皆空,视有若无,才能进入大道和至美境域。在老子“清静”说的基础之上,庄子把“虚静”从本体论层面进一步扩大到人的精神境域,成就在他所设计的理想人格上:“真人”与“至人”是其理想人格境域的完美统一。由“清”与“静”所构成的“清静”境域既是道家哲人所追求的一种原初纯粹境域,又是中国传统文艺审美创作的审美诉求和构成境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清静”境域的构筑不仅是文艺审美创作的美学追求,而且展现了文艺审美创作主体的人生境界、人格修养的原初构成境域。所以说,“清静”也就是“虚静”。中国传统文艺审美创作原初的构成态势就是“清静”。这正好与道家哲人的“虚静”观殊途同归。
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所谓“清静”,一是指审美创作主体原初构思心态的“清静”,二是指作品意境构成境域的“清静”。道家虚静观在中国传统文艺审美创作中体现为以下三种境域:
(一)收心去欲
在道家哲人和中国文艺理论家看来,“体道”与审美活动进行的关键一步是“清静”心境的构筑,因此首先必须收心去欲,回归原初的“清静”,而收心去欲则是回归原初的“清静”的前提条件。所以,中国传统文艺审美创作极为强调去欲以静心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面,古代许多哲人都深切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把审美体验时“心”的虚静作为审美境域构成的首要条件。
在中国美学,“清静”或谓“虚静”,意谓“澄心端思”,澄怀净化,忘知虚中,就是进入一种无视无听、寂寞无为的构成境域。苏轼《送参寥师》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走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仿,此语当更清。”处静方能观动、虚心才能纳物,虚静之境,在杳冥寂寞中,“离形去知”、“无视无听”、“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2] (《大宗师》),清代词人况周颐云:“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怅触于万不得已,既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晃、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3]“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此即老子所谓“致虚极”;“乃至万缘俱寂”,此即老子所谓“守静笃”。在中国古代美学家看来,只有通过这样致虚守静,达成离形去知、空明澄澈的“清静”构成态,在这样的构成态中,审美者才能放逐思虑、息机冥怀,进入心灵“忽莹然开朗如满月”、丰富情思不能自己地无端自来的佳境,于是审美意念便自然从中生发:“吾苍茫独立于寂寞无人之区,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沈冥杳霭中来。吾于是乎有词。”[3] 由此可见,去欲是静心的前提,只有守静才能寡欲,寡欲方能清心,因为清心而消除种种心理屏障,使自己的心呈现出以虚静为体的“道”,从而使艺术家的生命力得到自由解放,在审美创作中出神入化,运用自如,使玲珑澄澈的心灵突破“物”与“我”的界限,和幽深远阔的宇宙意识与生命情调相互契合,进入“应会感神”的境域。因此我们说,收心去欲是中国传统文艺审美创作中回归“清静”之心所达到的第一层境域。
(二)物我两忘
庄子在《齐物论》中多次提到“物化”,或“物忘”,这是一种主客两忘的境界。物我两忘是由“去欲”的“清静之心”消除了种种障碍,使生命力得到自由解放,从而泯灭了物我界限,是主体与客体反复移情互渗过程中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与道同化的境界。
“物我两忘”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审美创作构思中构成“清静”境域必经的途径,它从更深层次体现了艺术家自我的精神与物之精神相结合的程度。“物我两忘”既是一位艺术家在文艺审美创作必须体验的艺术经历,也是一位艺术家自身心态构筑所需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但要作到“忘”并非易事,它需要一种功夫,需要一种锤炼,它是以“清静为体”之心“应会感神”,与物契合构成的结果,非一般人所能达到,如果一位艺术创造者在对万物进行观照时没有泯灭物我界限,仍有个中分别,就无法纯净自己的精神,无法完成自我超越,最终无法进入最高审美境域——“大美”、“大音”。“物我两忘”可以说是“清静之心”通向“大美”、“大音”境域的构成态势,也是虚静之心所体验到的第二层境域。
(三)“大美”、“大音”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2] (《知北游》)。庄子认为,所谓“大美”即“天地之美”、“天道”之“美”,也就是说,“大美”即“道”。“大美”既是各种美的本源又是各种美的归结,它是最高的、统帅一切的美,又是构成众“美”的原初本原!在中国文艺审美创作领域,“大美”即可等同于老子所追求的“大音”境域,可以说,“大音”是中国音乐艺术特有的“清静之美”。
所谓“大音希声”,最美妙的音乐是无法用听觉来直接感触的,它必须用“心”、“道”去感悟;反过来说,能用听觉就直接把握而无须心灵沟通的音乐也绝不是最美妙的音乐;道家“大音希声”的真谛在于超越听觉感受,摆脱听觉束缚,直接用“心”悟“道”,用“心”听“音”。
首先,在文艺审美创作中的心理状态方面,中国传统文艺美学要求“心”静,静而能体“道”,静而能构成“美”,静便能构成“大美”。不过,真正构成“大美”的关键还在于“心”的构成态势——有一颗“清静之心”;“心静”而能“神静”,“神静”才能进入“虚静”的境域,通过这样的构成途径才能构成“大美”。
其次,在艺术意境的审美诉求方面,中国传统文艺审美创作追求“虚、远、逸、静”美学追求,这种美学追求也充分葆有道家道教“虚静”观的特色。中国传统文艺审美创作中的“虚、远、逸、静”是文艺创作以技而进乎道的结果,它以道家道教之“道”,以“大美”为其精神构成态势,以“虚、远、逸、静”为其最终构成域。
最后,在艺术家的人生境界和人格修养方面,道家“清静”观更为中国传统艺术家提供了理想的心态构筑境域。
总上可见,中国道家和中国传统文艺审美创作虽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范畴,但它们尚自然、崇清净的审美意趣却共同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自身特点。两者虽然有不同的出发点,前者是宗教,后者是文艺,但是最后都归结于人之心,要求在人心上做功夫,强调“内省性”,以敞亮本心,还原自然的心性,以“清静”为最原初的构成势态,这是对两种不同思想文化归趋的总结和概括。
二
就美学意义而言,“清静”之“清”,或谓“清”之域突出地呈现出一种的构成态势。据载,清代诗人殳梅生曾以诗稿请张云璈作序,其友人问殳诗品格如何,张称许之,说:“清才。”友人问:“如斯而已乎?”张云璈回答说:“子何视清才之易耶?古今来言诗者曰清奇,曰清雄,曰清警,曰清丽,曰清腴,等而上之曰清厚,等而下之曰清浅,厚固清之极致,而浅亦清之见端也,要不离清以为功。非是虽才气纵横,令人不复寻其端绪,则亦如刘舍人所云采滥辞诡,心理愈翳者矣。大都造诣所极,平奇浓淡,人心不同如其面,有未可执一例以相推,而先以清立其基,虽李杜复起,吾言当不易也。”(《殳梅生诗序》,《简松草堂文集》卷五)认为“清厚”之境是“清”域“之极致”,作诗应“先以清立其基”。后来李联琇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指出:“诗之境象无穷,而其功候有八,不容躐等以进。八者:由清而赡而沈而亮而超而肆而敛而淡也。至于淡,则士反其宅,水归其壑,仍似初境之清,而精深华妙,有指与物化、不以心稽之乐,非初境所能仿佛。东坡《和陶》其庶几乎?顾学诗唯清最难,有集高盈尺而诗尚未清者。未清而遽求赡,则杂鞣而已矣。甫清而即造淡,则枯寂而已矣。”[4] (卷二八《杂识》)在这里,他将诗歌的审美境界划分为八等,“清”既是最初的原发生之境域,又是最高之构成境域;只有由“清”之境缘构,循序渐进才能构成“淡”“静”之境,这种“淡”“静”之境,或谓“清静”之境域,看“似初境之清”,但却“精深华妙,有指与物化、不以心稽之乐,非初境所能仿佛”,乃是更高的审美构成境域。这种视“清”为原发生域和最高的构成境域之“淡”、之“静”,经过升华,在更高的层次上又复归于“清”,或谓“清静”境域,体现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即天道生生不已,周流不居,美也是如此,既生气流荡,生生不穷,处于永不停息的创造和革新之中,同时又周匝无垠,是一个完整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有机整体,圆融无碍、周而复始。最能体现中国美学天道生生不已,周流不息的这种基本精神的,是禅宗青原惟信禅师所提出著名的“三般见解”,他说:“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兑知识,有个人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5] (《五灯会元》卷十七)青原惟信在这里所表述的是禅体验中三个必不可少的过程,既是转迷人悟的三个阶段,也是由生命(真我、真心、本来面目)被遗忘到生命觉醒的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又周流圆融,回环反复。众所周知,禅宗所标举的参禅悟道,就是要根除妄心(分别心)而领悟和把握圆满具足的真心(直觉心),见到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把被遗忘的生命唤醒。在禅宗看来,由于人们后天形成的妄心(分别心)作怪,由于本身圆满具足的生命与真心被遗忘,因而用一种“连眼”来看待宇宙万物,以致所看见的事物只能是事物色相,这种色相是虚幻不实的。只有换眼易珠,把生命与真心唤醒,用一双“迷眼”来看待宇宙万物,才能见出事物本来圆洁自在的面目与法性,虽然这事物的本来面目是“性空无相”的,然而它毕竟是不生不灭而真实存在的。因此,同样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但开悟前后的两种心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开悟前乃是生命,即真我、真心、本来面目被遗忘的心境,开悟后则是生命,即真我、真心、本来面目已觉醒的心境。青原推信正是用悟道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与悟道后“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来比况开悟前后的心境。同时,我们从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禅宗“禅”境界缘发构成中往复回旋、逐层展开的缘构历程。是真心一一妄心一一真心的首尾相衔、开阖尽变、周转不息、往复回环,圆圈似的参悟解脱过程。而“禅”之境则在这原发的时间,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相互交媾中生成。正如百丈怀海所云“一切色是佛色,一切声是佛声”,这个完全疏离于具体时空背景的个体化的山水其实只是观者参悟的心相。这一直观的心相,保留了所有感性的细节,却不是自然的简单模写,它是心与物象的缘发构成,具有美学上的重要意义。
正由于“清”,或谓“清静”之域的构成性使然,所以“清”,或谓“清静”之域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它可以和更多的词结合起来,以构成新的意象系列。如魏晋时期《宋书》、《梁书》、《世说新语》等史册典籍中表征人为官品行端方,奉公守法的有“清正”、“清公”、“清廉”、“清恬”、“清谨”、“清约”、“清严”;表征为人超尘拔俗,不同凡流,如“清傲”、“清真”、“清退”、“清慎”、“清静”、“清正”、“清节”、“清和”、“清望”等;表征人的风神气韵之美好,如“清令”、“清雅”、“清畅”、“清俊”等;表征艺术的清真天然之美,如“清工”、“清新”、“清约”、“风清骨俊”、“清典可味”等。
“风骨”,基本含义就是“风清骨峻”,由此形成一群以“清”为骨干的派生概念,如清典、清铄、清采、清允、轻清、清省、清要、清新、清切、清英、清和、清气、清辩、清绮、清越、清靡、清畅、清通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常用“清”来评诗,如《文心雕龙·才略》称曹丕“乐府清越”,《文心雕龙·时序》称“简文勃兴,渊乎清峻”,《文心雕龙·声律》称“诗人综韵,率多清切”。除《文心雕龙·才略》篇外,“清”字用得最多的是《文心雕龙·明诗》:论作家则“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论作品则“张衡《怨篇》,清典可味”;至论诗体,首倡“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清丽居宗”,确立了五言诗的风格理想。曹丕论诗赋的审美特征曾独标“丽”字,陆机附以“清”而成“清丽”,以为文章美的共同标准,刘勰这里又将它从“文章”中剥离出来,独归于诗,遂使清在诗中的地位得以确立。稍后钟嵘在《诗品》中十七次用“清”字,构成的词有“清刚”、“清远”、“清捷”、“清拔”、“清靡”、“清浅”、“清雅”、“清便”、“清怨”、“清上”、“清润”,与刘勰相映成趣,共同表征了南朝诗学以清为主导的审美倾向。
三
“清静”,或谓“清静”境域的这种构成性与开放性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它和地域的、社会的与文化的作用分不开。仅就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其中老子提出“道”论与其“得一而清”、清静无为的虚静淡泊、返朴归真的人生理想,就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所谓“道”论,是先秦时代的中国哲人,特别是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哲人提出的一种思想。“道”先于自然万物,为自然万物纯构成的本源,是“道”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含义。老子说,有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它先天而存在。无声无形,杳冥空洞,永远不依靠外在的力量,自身不停地循环运行,可以称之为天下万物的母体。我不知道它的名称,把它叫做“道”,再勉强给它起名叫做“大”。道之所以被命名为“大”,是因为其无边无涯。道不止于大,又能不分昼夜的运行不息,故又可谓之“逝”。其愈逝愈远,无法穷尽其源,故又可谓之“远”。但虽远至六合之外,无穷无尽,却始终未尝离“道”,仍然依“道”不断发生构成,故又可谓“反”。“反”表明境域的构成绝不依靠任何现有的存在者。这是老子对“道”这种构成域的全面描述,它构成天地万物,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作为万物构成本原的道,它生成宇宙自身所固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张祥龙指出:“对……老庄而言,这最终的根源都不是任何一种‘什么’或现成的东西,而是最根本的纯境域构成。”“老庄的‘道’也同样不是任何一种能被现成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湍流’,总在造成新的可能,开出新的道路。”[6] 换言之,“道”是一切生命的总源泉总生机,万物发生构成于“道”,又内含着“道”而得其生命之常。所以老子以最崇敬的心情讴歌大道,他赞叹说:道不可见,但却不亏不盈,永无穷尽。它是那样渊深啊,好似万物的宗主,它不露锋芒,超脱纠纷,含蓄着光耀,混同于垢尘。是那样的无形无象啊,似亡而实存。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产生的,但却知道它出现在上帝之先。正是基于此,所以老子指出,“道”是生命能量的总体与万物的本原,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莫过于“道”,它就是大自然的造化之力。最终,老子将万物自然与宇宙人生纯粹构成境域“还原”到“道”。
在老子看来,作为万物发生构成本原的“道”,不能说它有,因为所谓境域就是在终极处的发生构成,所有的现成存在性都不能达到本源境域。“道”不是现成的物,无形无象;又不能说它无,不能说它可以独立于万事万物而“生出”万事万物,因为它缘于有而成就有,所以老子指出“有”与“无”“同出而异名”以构成异彩纷呈的动态世界。所以“道”体是无,“道”用是有,“道”是无与有的统一,两者同出而异名。他说:无,是天地的原始;有,是万物的根本。所以应当从无形无象处去认识道的微妙,应当从有形象处去认识万物的终极构成境域。所以说,作为大道本体的“无”,也就是“道”,是宇宙最原始的构成境域,此原始之构成境域并非绝对的空无,它朦朦胧胧、浑然一体,其中包孕着生成天地万物的基因,这就是“精”。西汉时期的道家学者曾经比喻说,老子之“道”就像一个鸿卵一样。鸿卵看上去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头又没有尾,既没有翅又没有腿,可是包孕着鸿的一切;“道”看上去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天又没有地,既没有人又没有物,可是却包孕着天地人物的一切。老子说:“道”这个东西,没有固定的形体。它是那样的惚恍啊,惚恍之中却有形象。它是那样的恍惚啊,恍惚之中却有实物。它是那样的深远暗昧啊,深远暗昧中却涵着极细微的精气。这极微的精气,非常具体,非常真实。从古至今,它的名字不能废去。根据它,才能发现万物的源起。我何以知道万物最初生成的状况呢?基础就在于此。也就是说,“道”这种东西虽然恍惚不清,好象什么也没有,但实际上有“形”、有“象”、有“精”。这个“精”就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因。正因为内蕴着构成天地万物的基因,所以“道”才可以生成天地万物来。当然,这个生成宇宙万物之“道”并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事物,而是纯粹境域之“道”,它超越了人类一切感官的知觉作用,这就是老子说的“不可致诘”(即不可思议)。有了“精”这个基因,老子就可以设想道生成天地万物的程序了。道,看起来什么也没有,所以可称为无。说它是无,那只是相对于天地万物而言的,而不是说它不存在。它是一种无形无象、无分无界、朦胧不清、浑然一体的东西。正因其无分无界,浑然一体,所以可称其为“一”。这样一来,“一”就从“无”中生发了出来。老子把这个过程称为“道生一”。这个“一”,指出是阴阳未分之前混沌一体的宇宙。它与“无”字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体现了“道”的这种纯境域性。这个混沌未分的宇宙,“其中有精”,在自我的构成之中,逐渐生成为阴阳二气,老子把这个过程称为“一生二”。“二”就是阴阳。阴阳间的对话交流,犹如强大的动力,激活并构成了宇宙间的“精”,从而生成天地,生成了人类,他们与道并存,老子把这个过程称为“二生三”,所谓“三”,即指天、地、人三才。宇宙间有了这三种东西,万物得以发生构成,即通过阴阳运动生成新的统一体后,生化出世界万物,老子把这个构成式称为“三生万物”。在对道生化天地万物的构成式做了描述之后,老子总结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明确指出,天地万物皆内涵阴阳,阴阳二气又在冲和之气中相构相成,相互召唤,万物亦在冲和之气中氤氲摩荡、化生化合。从无形无象最原始的境域的道,生化构成气态宇宙,生化构成固态天地,乃至形形色色的物体;其发生构成的根本缘在便是阴阳两种元素的相激相荡。在整个宇宙发生构成生成的各个层次上,阴阳间的交流对话是万物生成、生命构成的活力,“道”则是先于任何现成状态的最本源构成、通达万有的终结本源,其构成与最“边缘”境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老子把它形容为“玄妙之门”。
概括而言,作为天地万物原构成境域的道,具有三大特征:第一,从哲学发生构成论的角度上看,老子的道非常强调一个“生”字,指出道乃是生成万物的总根源,道具有能生而又不被生的永恒不息动力。这种重生的观念,深刻的影响了道家和道教,成为道家、道教学说的核心学说之一。如《庄子·大宗师》曰:“(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管子·形势解》曰:“道者,扶持众物,使行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淮南子·原道训》亦说:“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象而弗宰。……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而后死,莫之能怨。”后来的道教正是遵循老子的教诲,高扬重生的理念,成为老子学说忠诚的宏扬者;第二,从哲学发生构成论的角度,老子的道论突出一个“通”字,指出宇宙万物相互依存,“自身的缘构发生”的境域就是道,万物最终构成于道,道虽然无形无象,却是万物存在的普遍根据,因为它无所不在,无所不通。《庄子·渔夫》曰:“道者,万物之所由也。”[2] 扬雄说:“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扬子·法言》)王弼亦曰:“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王弼《论语释疑》)道教《灵宝天尊说大通经》云:“大道无象,故内摄于有。真性无为,故外不生其心。如自然,广无边际,对境忘境,不沉于六贼之魔。居尘出尘,不落万缘之化。致静不动,致和不迁,慧照十方,虚变无为。”一切物象皆有滞而成,道通而无滞,故可以为物象之本,它不是“迹”,而是所以“迹”;它“无象”“无为”,故可以“摄有”,可以称为“虚变”、“无为”。总之,在道家哲人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纯粹构成境域,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发生构成的,都从“道”那里构成自己的形体和性能,所以它们的本性和“道”是一致的,它们的行为都以“道”的自身缘构为构成式。那么,“道”的构成式是什么?是自然,亦即自然而然,他说:“域中有四大,而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 (二十五章)老子的这句话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在于突出“自然”,其二在于规范域内。在道家哲人看来,大化流衍,旁通弥贯,但是追究其终结构成境域,则只能是“道”本身。“道”本身是有无相生、动静相成、阴阳相合的发生构成,是永恒的实在和无限的生命本体。它融化在天地万物的构成存在、生化流行之中,规定着社会和人生的一切发生构成;大化迁易,莫不是“道”的造化伟力所致。万物万化,只是一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天地自然的原构成境域,主宰着一切存在事态的构成与存在,道虽无形、无名、惟恍惟惚、虚无空廓,而存在事态的最终构成却来自于它,天下一切事理情尽皆由此而生。而作为天地万物的纯粹构成境域的“道”,其构成态势则表征为“清”。老子云:“天得一以清。”(章)“天”[1] (三十九章)即自然,“一”即“道”;这就是说,天(或谓自然)还原为最原初的纯构成境域,则呈现为明澈清纯的态势。老子云:“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1] (十五章)这里,老子又将清与静相连,是指人的心灵空虚澄明,这是一个转义,乃从“道”的存在状态(虚静无为)推演而来,“清静”蕴含着用自然之自在本性来规范人生理想的道家旨趣。可以说,“清静”就是自然之自在本性,也就是“静”。老子说:“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1] (四十五章)王弼注云:“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故惟清静,乃得如上诸大也。”所谓“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辩”等诸“大”都是人生的终极期待,而要实现这些“大”则必须以“清静”为最原初的构成势态。这样,“清静”就被赋予了一种形而上的本原性意义。
收稿日期:2006—0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