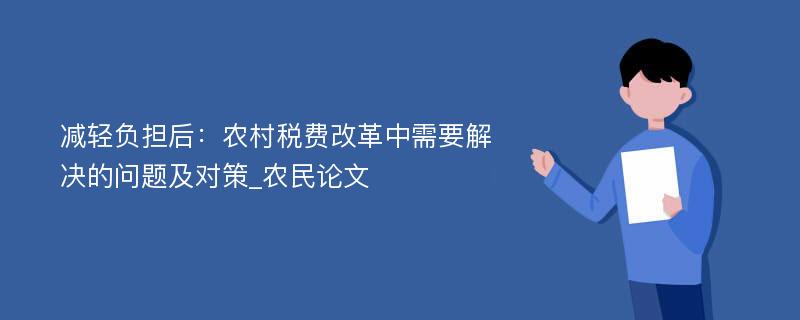
减负之后:农村税费改革有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农村税费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自2000年在安徽全省和其他省市的一些县推开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农民负担得到减轻。我们最近在安徽省和其他一些省市的试点地区,调查农户,和相关部门座谈,感到农村税费改革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据安徽省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改革后全省农民总税负为37.6亿元,比改革前同口径负担49.3亿元减少11.7亿元,减幅为23.6%。如果加上所取消的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民税负减少31%;农民人均现金负担由109.4元减少到75.5元,人均减少33.9元。同时省里还取消各种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和达标项目50种,初步堵住了农民称之为“无底洞”的“三乱”,减负效果明显。
从地区看,安徽池州市改革前农民总体负担为14357万元,改革后负担为9203万元,减负5154万元,亩均减负44元,人均减负39元。全市共清理了不合理、不合法的涉农收费77项。池州属下的青阳县通过改革使农民的总体负担从原来的2942万元减少到1873万元,减负1069万元,减负幅度达到36.3%,亩均减负41元,人均减负44元。目前亩均负担73元,人均负担77元。
安徽陆安地区的舒城县,农民除教育投资外的现金负担从改革前的7762.4万元减少到6800.4万元,总体减负962万元(不包含村公积金),人均负担减少10.96元,减负幅度12%。如果包括所减少的教育集资,全县农民负担总体减少2962万元,人均减少幅度为30%。舒城城关镇税费改革前人均负担104.52元,亩均负担188.55元,改革后人均负担56.53元,亩均负担100.35元,人均减负47.99元,亩均减负85.19元,减负幅度同为45.91%。减负幅度最大的舒中村甚至达到50%。
从江苏沭阳县的情况来看,改革前全县农民合同内负担(不包括屠宰税和“两工”)16083.23万元,合同外负担13188.88万元,合同内外总体负担29272.11万元;改革后全县农民合同内负担(不包括“两工”)11526.89万元,合同内负担比改革前减少4556.34万元,减负28.33%,人均合同内负担从112.66元减至80.74元,减负31.92元,减负幅度28.33%;人均合同外负担从205.04元减至80.74元,减少124.3元,减负幅度60.62%。沭阳县潼阳镇改革前合同内外总体负担是841.03万元,改革使农民减少了421.42万元的负担,减负率为50.11%;人均合同内外负担从192.58元减少到96.08元,减少了96.5元,减负率50.11%。沭阳县马厂镇将农民的总体负担从改革前的1209.03万元减少到目前的477.63万元,合同内外减负率总体上为60.49%。
湖北、宁夏等省区所反映的基本情况与安徽,江苏相仿,农民减负幅度一般在30%以上。
从上述总体情况来看,农民负担确实得到了大幅度减轻。我们所访问的农户也承认这一事实。可以说,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深得民心的重大举措。改革后农民缴纳税收的积极性提高,出现大量农民主动纳税的现象,也有效降低了税收征收成本。
二、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可说是继建国初农村土地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后的第三次农村革命,问题复杂,牵涉面大,无法一蹴而就,因此需要跟踪试点的进展,针对发生的问题,及时研讨对策。在调查中,我们听取了相关部门的反映和一些农户的意见,感觉存在如下问题有待解决:
1.县乡财政的收支矛盾趋于尖锐化。
首先是收入缺口较大。安徽池州青阳县,改革使全县农民负担减少1069万元,体现为政府收入相应减少(其中乡镇级减少764万元,村级减少305万元),同时得到省级转移支付564万元(其中乡镇级437万元,村级127万元),扣除后仍然有505万元的缺口(其中乡镇级缺口327万元,村级缺口178万元),造成乡村两级运行困难;舒城城关镇,镇村收入改革前为471.24万元,改革后可用财力只有193.7万元,缺口277.54万元。加上县财政给予的转移支付90.3万元,缺口仍然有187.24万元。
其次,在收入出现缺口的同时,农村原来依靠“三提五统”支持的事业,如乡镇道路建设、优抚、五保户赡养、计划生育、民兵训练等基本上都转移到乡镇政府的预算开支中,增加了财政的困难。
乡镇财政收支矛盾加剧的压力,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传导到原已十分困难的县财政,成为影响基层政权运转的因素,也有可能成为推动农民负担反弹的重要因素。基层干部的反映,主要集中在要求上级政府给予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这样一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推广,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通过转移支付手段给予基层政府资金支持方面,将面临很大的压力。看来这已成为2001年扩大试点不得不暂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2.基础教育投入存在缺口。
为了解决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在试点地区,乡镇学校教师工资从2001年起陆续转为直接由县财政通过教师工资专户统一进行(县乡间体制一般同时调整)。这有效解决了教师工资的拖欠问题,但并未解决基础教育投入不足问题,同时由于税费改革取消了教育附加和集资、规范了学生收费,从而使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更加明显。一方面在上级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原缺口不小,加剧了县财政的困难,影响县级政权其他职能的履行;另一方面教师未来工资标准提高的负担也很有可能累加在县财政,所以县财政未来的困难可能需要得到更大的重视。还有不少地方,上划到县财政的教师工资只包括省级以上政府认可的工资部分,如国家统一规定的固定工资、活工资、教龄津贴和其他津贴,一些原来地方规定或认可的相关费用或补贴(如教师误餐补贴、交通费、班主任工资补贴、“开放县补贴”等等)仍然由所在乡镇负责。安徽青阳县这类由乡镇负责的教师补贴人均153元,舒城县的相关人均补贴在80-88元。这些开支实际上在改革前已经相对固化,难以调减,仍然成为乡镇财政的负担,但财力来源却因为现在没有了“三提五统”和教育集资等,缺口立刻呈现,如青阳县丁桥镇税费改革前有相当于农民纯收入1.5%的教育经费来源,一年在该镇约15万元规模,现在没有了着落。
中小学校危房改造资金,在税费改革的试点地区,现一般要求由县财政直接负担,上级政府的相关援助只是采取一次性补贴的方式且数额较小,主要用于中小学布局调整,也可以相机从事中小学危房改造。显然上级政府这种额度不足、多功能用途的专项补助难以顾及全面情况。安徽省目前已暂停中小学布局调整,集中资金用于危房改造,仍然捉襟见肘。实际上中小学危房改造的支出现状,基本上是由县、乡,甚至村共同负责。安徽县级无可奈何的说法是:“谁的孩子谁来抱”,即指望不了县里。乡里有的学校实在困难,连桌椅都配不了,只好想出“学生入学自己买桌椅,所有权归自己”的招儿。江苏省原则上要求由县级政府独家负责,沭阳县由于上级在转移支付中基本上填补了改革取消的向农民教育集资的资金缺口(改革前向农民的教育集资规模为6058万元,改革后通过转移支付所得到的资金支持为6250万元),所以县财政在负担压力不大的情况下承诺包揽全县所有的中小学危房改造费用,然而从实际调查情况来看仍然没有完全到位,例如该县潼阳镇扎埠村小学2001年的危房改造费用仍然由村委会负责(2001年的危房改造费用已经支出7000元,估计还需要近2万元的资金)。
如果乡村小学的硬件建设和维护得不到有效保证,我国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度必然会受到影响,并且危房改造人命关天,“危房要倒,只好反弹(农民负担)”,这也是基层工作的同志反映比较强烈的一条。
3.村级公共职能的运转经费不足,“一事一议”难以操作。
税费改革以后,村级公共经费主要依靠“两税”附加,实行乡管村用,同时也切断了村级经贸通过扩张收费来弥补的口子,有助于减轻农民负担。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村级经费开支严重不足。池州市2000年有260个村运转经费在2万元以下,约占村总数的27%;3万元以下的村近400个,约占40%。按照测算,当地保持正常运转的最低经费标准为村均3万元,这样,约有2/5的村难以维持正常运转。陆安地区舒城县为了解决村级资金困难,对山区14个乡镇“两税”附加不足3万元的村由县财政直接补助到位,对16个丘陵等类乡镇“两税”附加不足3万元的村由县财政和乡财政分别负担不足部分的补助(比例是六四开)。为此,县财政直接负担了408万元的村级专项补助资金,16个乡的配套补助总额也达到129万元。江苏省为了解决村级资金困难规定农业税的10%返还村级用于维持运转。湖北宜昌五峰县最低的一个村年经费仅1900元,县向省财政厅借钱维持基层政权职能运转。这些举措说明,为数不少的村级公共职能难以维持正常运转而不得不和上级政府“分羹”。在我们所调查的试点改革地区,各级政府也一直在寻求解决村级经费困难的有效之策,包括压缩村级干部人员编制(如鼓励村干部兼职村民小组长等等)、实行报刊杂志订阅经费控制(安徽基本上是限制在村均500-800元以内,江苏沭阳限制在2000元以下)。看来这些措施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村级运转经费的困难。在上级政府财力支持不到位的地区,村级经费困难可能会掉头引发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行为。
按制度规定,村级“一事一议”主要用于乡村道路建设维护、乡村水利设施等等的村级公用事业,原则上是“有事则议,无事不议”。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在现实操作中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有事难议”。这也是公共选择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乡村议事的决策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决策成本虽然小,但可能造成公共偏好的扭曲,甚至成为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手段;如果需要经过全体一致或大多数人的同意,决策成本会明显增加,议而难决的概率增大,跨村、乡的项目尤其困难。二是“一事一议”的乡村民主制度可能会扭曲,即各地名义上的最高人均“一事一议”负担(安徽基本上是人均15元,江苏沭阳是人均20元)可能会成为变相的人头税,成为固定负担。这是在乡村缺乏有效民主条件下公共决策由上级政府变相垄断的反映。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地区为了防止“一事一议”成为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契机,所以干脆取消(如舒城县城关镇);有的干部觉得与其成为变相的人头税还不如适当增加“两税”附加比例,以增强乡村可用资金,在民主的监督下来保证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总体看来,“一事一议”在现阶段操作难度大,在标准很低的情况下,还往往流于“有事不议、有事难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如何改进还需要仔细斟酌。
4.农业税改革产生了新的税负不均,影响种田积极性。
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和屠宰税、大幅度减少农民负担的同时,适当提高了农业税税率(各地基本上稳定在7%左右,如安徽税率是6.96%,江苏沭阳是7%)。从调查中看,改革前的“三提五统”基本上类似人头税,农民的负担大体上是“人田各半”,所以农村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摊丁人亩”的倾向。这就使“离土离乡”、“离土不离乡”的那些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负担较轻,安徽青阳县测算,改革后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实际人均负担明显下降,只有18元/年,比总体的农民人均负担低2/3以上。而“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特别是种田大户的负担加重,即所谓“多种地、多负担、多吃亏”。一个极端一些的例子是:湖北五峰县一刘姓种田大户,原为人口大户,后子女皆进城打工,山地无人接,全归入刘本人名下,在提高农业税税率后,其负担增加达3倍之多。这在客观上又鼓励了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内在地推动了农民的“抛荒”现象,如安徽青阳县目前的土地“抛荒”已经达到1.2万亩,当地和安徽不少地方反映,农民举家外出的情况增加。当然,土地“抛荒”在税费改革前已经存在,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效益比较的结果),但也不能否认改革所产生的新的负担差异所造成的推动因素,而且改革后又正好赶上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这使得在农业税实行“代金制”的条件下,农民因粮食折价低产生的负担增加,按照青阳县干部的说法,农民以前100斤粮食就能缴纳57元的农业税,现在退出保护价范围的早稻则需要168斤才可以完成57元的农业税任务,最好的晚稻100斤现也只卖得54元,仍低了3元。农民想不种早稻,又苦于找不着替代物,不少人试种瓜、菜,却卖不掉。在土地大量“抛荒”的情况下,我们现时又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既不利于充分利用宝贵的可耕地资源减轻农民负担,也难以有效提高农业用地的使用效益。
农业特产税目前是要求“据实征收”的,但由于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产品品种变化也大,尽管在征收中也建立了台帐,但因征管工作量大、征收成本高,往往力不能及,难以真正掌握相关信息,实现据实征收。从安徽的情况来看,农业特产税征收环节由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征收改为只在生产环节征收,并提高了税率(即生产环节税率由8%提高到13%,取消销售环节征收)。湖北等地对茶农也有这种情况。这实际上是将负担直接集中在农民身上,因为销售环节是属于流通领域的事情。这样,农民的负担反而增加,显然不利于减轻山区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5.乡村债务负担沉重,化解难度大。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改革后显露出来的乡村债务较大,化解难度也大。安徽青阳县辖19个乡镇(目前缩减为15个乡镇),178个行政村,乡村两级债务总计29792万元,其中乡级债务22006万元,村级债务7786万元,平均每个乡级债务1158.21万元(按17个乡镇计算),村级平均43.74万元。全县每年本级财政收入中可用财力不到6000万元,显然没有上级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是无法走出债务深坑的。
舒城县在110个消债试点村清查债权1871万元,债务3248.12万元,净债务为1377.12万元,村均净债务12.52万元。目前,已通过种种措施消除了1194.94万元债务,占110个村债务总额的37%,还有63%的债务没有消除。由于债权不能得到有效清偿,所以债务的偿还就显得困难重重,而且债务的清偿越到后来越难,因为可用于清偿的手段已经使尽。舒城消除村级债务的基本经验是:通过“挤水”消除债务,即通过清理消除债务中的不实或虚假成分,挤干债务水分;通过降息减债,即比照银行同期利率,适当降低以前年度债务利息率来减少债务;清欠还债,即通过清理农户以前年度欠缴的税费(尾欠)来清偿债务;筹资还债,即对确实是村集体兴办的公益事业债务,以“一事一议”的方式,向群众筹资,偿还债务(不过,规定最高不得超过人均15元);节支还债,即从“两税”附加和上级补助中节约出一部分资金偿还债务;变现还债,即利用村级闲置资产变现偿还债务;补助还债,由上级政府和部门(主要是乡镇)从财政收入和专项资金中给予补助,减轻村级债务;增收还债,即发挥本地的区位优势,盘活集体资产、发展集体经济等等措施来偿还债务。
江苏省沭阳县潼阳镇的镇、村两级债务总计1161.49万元,其中乡镇负债803.83万元。村级净债务357.66万元,村均15.55万元,乡村中小学负债65.14万元。所采取的化解债务措施除和上述相同的方式外,还可以用“两工”抵销债务,也采取村内三角债相互抵销的办法进行(如该镇岔流村主要是通过债务债权抵销的办法消除债务)。
从调查地区的债务清偿情况来看,基层干部确实是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不过,一方面由于债务总量大,债务消除进程越来越慢,也越来越难,另一方面随着债务消除难度的加大,一些地方干部消除债务的方式也容易有过激的举措。比如村内债务和村内债权的相互抵消,在具体执行中存在着过多的强制性因素。被访问到的相关农户基本上都存在着不满情绪。农户之所以进行债务债权的更迭除强制性因素外,还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村委员会所欠村民的债务如果不进行债权更迭是不会得到较快偿还的,甚至会血本无归。这样一来对村委会拥有债权的村民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有的地方(如江苏沭阳县潼阳镇)还存在着用“工票”(实际上类似村民做公益性劳动工日的证据,只不过形式规范而已)抵消所欠村民公益劳动债务的情况,而且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些票据还不得抵消村民日后的“两工”负担(不过,县政府干部认为这是下级没有很好理解政策的问题,以后要纠正)。这样一来可能会产生村民“两工”以外的工役负担问题,否则村民手持的大量“工票”难以化解(仅潼阳镇岔流村村民就持有2.9万元的“工票”)。
村级债务中的“外债”(即欠财政周转金、银行和农业开发贷款等方面的债务)是最难消化的,因为必须由村级集体筹措实实在在的资金来偿还。调查显示,大部分地区的村级“外债”基本上没有清偿。安徽省已经就这些债务的推迟偿还或豁免和相关方面进行协商(有的据说已经达成了协议),显然乡、村级债务的消除不仅仅是乡村和地方政府的事情,需要通盘考虑。
6.逐步取消“两工”虽然有助于减轻农民负担,但也造成了诸多不便和新的矛盾。
《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规定:要在3年内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工”取消后,村内兴办水利、修路架桥等集体公益事业要采取“一事一议”的原则由村民民主决定(多数规则)。除遇到特大防洪、抢险、抗旱等紧急任务,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临时动用农村劳动力外,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无偿动用农村劳动力。这种方式,在改革试点地区基本上是相似的。
过度摊派和征用农村劳动力确实是加重农民负担的重要原因,因此逐步取消“两工”有助于减轻农民负担。基层干部的反映是:一方面,认为“两工”负担确实需要逐步减轻,但全部取消会造成诸多不便,比如防汛,如果平常不加以细致维护防洪设施,等到特大紧急情况来临的时候将会付出更多,而平常的维护工日如果采取有偿劳动的话,发生的费用可能在财政难以承付的时候还会回归到农民身上。况且,就现在的农村市场化发展水平来看,农村最闲置的是劳动力,最紧缺的是资金。如果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话,取消“两工”无疑会增加农民的资金负担,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徒增转换费用,所以适当保留和规范使用“两工”应是可以研究的。另一方面,认为如果取消“两工”,政府应该相应增加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防汛和公路建设等等方面的费用,在基层财政难以应付的时候,需要考虑上级政府的资金援助,因为事情总是要办的。还有的干部认为,现行农业开发项目,甚至包括目前仍然进行的国债转贷资金项目,总是要求相应的地方配套资金,有时候基层难以满足这些配套需求,但项目确是地方所需要的,也是农民拥护的,所以适当征用农村义务工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生态林建设,利国又利民,在项目资金不足的时候,当地政府组织一些义务工进行配套是合理的,农民也是有积极性的,但这是否应该算在规定的“两工”限制范畴呢?如果这些举措受到限制,本来可以办的事情就没有操作的可能性啦!所以如何对待“两工”,还值得商榷。
7.农税征收出现法规空当,农业四税征收力量不足。
湖北、安徽等地基层同志都反映,2001年5月份颁布的《税收征管法》,只是对非农税收征管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和明确了强制性处置措施,农业四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说要“另行规定”,而不再象过去的条文那样“比照执行”了,但直到目前也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造成了农税征管中的法规空挡、催缴通知书无法发、滞纳金无法收、碰到抗税的,无强制执行依据,无可奈何。基层工作同志迫切希望能够尽快出台相关征管法,使农业税收的征收有法可依。
调查地区的干部普遍反映农业四税征收难度大,而征收力量薄弱。一些乡镇农税征收人员和财政所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人员编制在一般3-4人,征收力量严重不足,影响了农业税收的及时足额入库。如青阳县,隶属于财政系统的农税征收人员只有65人,需要完成2300万元的征收任务,而税务局则有85人左右,征收大约1650万元的税收任务。相对来说,农业税征收难度较大,配备的人员明显不足,在征收旺季只能临时雇佣其他人员,也影响征收质量。所以,基层的反映是迫切需要加大相关方面的征收力量和配备相应的设施。
8.耕地占用形成的税收负担可能会不合理地转嫁给农民。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和道路建设的迅猛增加,许多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及时进行相应的土地用途更换手续,造成“农转非”用地的原农业税负担无法消除,反而累加到耕地农民身上,成为推动农民负担反弹的一个客观因素,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安徽池州市现有7万多亩非农占地(大多用于修国道、省道),由于前边的耕地占用税无法完税,因而现在无法核减农业税,造成“有税无地”难题。据当地同志说,省里是要求财政厅落实耕地占用税完税事宜的,但修路多用贷款,相关单位不肯承担这块税负,财政厅也没办法。另有些占地涉及的企业,曾应允交税,但企业已经倒闭,无法征收了。
9.五保户供养也难解决。
农村社会保障问题近年来已经表现出愈益明显的矛盾,五保户供养的难度本来就在加大,但原“五统”中是有与五保户供养相对应的项目的,因而在概念上说是有“专项资金来源”的。一旦取消“五统”,乡、村有限财力中保工资、保运转的事项缺口就会把五保户供养的问题挤到后边,更难解决了。
三、一些看法和建议
通过调查,我们有如下一些初步看法:
1.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基层政府行为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依靠下禁令、硬性压低负担水平,恐不是长久之计,需要在稳定农民负担的同时相应考虑一些更全面、更深刻、更着眼于大局的综合配套性措施,在体制、财力分配、农村社会变革等方面多管齐下,以求内在地减轻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同时使政府体系运作合理化。本文前面所列出的有待解决的问题,其实已经使与之针对性的对策考虑呼之欲出,关键是应使针对性对策协同于总体性、治本性的大思路之中。
2.在减轻、稳定农民负担的同时维持基层政权组织正常运转,原来隐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寄希望于基层政权实行精简并使其职能合理化,办事效率提高。从目前情况来看,“精兵简政,转换职能”作为解决问题的良策,似迫切需要涉及政府框架调整的新思路。我国五级政府的行政架构设置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而且政府仍然存在着包揽过多的问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方面降低行政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也无疑会加重公众的负担。可否考虑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试行精简政府级次,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比如可以将乡级政府转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以求大量精简非必要的乡级机构和人员。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可以逐步通过撤乡并镇、裁减人员等过渡性措施分步到位。国外政府,包括大国,一般都是三级政府,我国目前地区(市)与县级政府基本上不存在财政分配转移关系,也可以考虑逐步精简合并,或者是过渡到各自均对省级政府“说话”的状态(浙江目前就是如此),然后再考虑把地级(含地级市)明确定位为省的派出机构。这样,我国政府级次能够得到有效精简,职责也较易廓清,有利于减少行政运转经费,减轻企业和农民的负担。
3.在没有取得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性突破之前,还是要妥善解决减负与维持行政运转的关系问题,否则农民的负担即使暂时减轻也难免会反弹。建议在税费改革扩大试点时,以上、下限方式给予下级政府一定的弹性空间,最好不要搞减负幅度的“一刀切”。同在安徽,南部山区改革前原农民负担远低于北部平原,青阳县原只占农民纯收入的1.9%;湖北宜昌山区,原农民负担也不到纯收入的5%,明显低于江汉平原,按一律的幅度要求减负,不符合因地制宜的原则。因此,在改进操作方案时,可加入区别对待的内容。
4.政府公共性职能需要在政府间适当搭配。比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全局性“公共产品”,不应该完全让基层政府负责,应该考虑中央政府提高在这些方面的出资力度。以教育为例,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使教育服务均等化,是全国性的事情,因此中央政府有相关职责,而一些欠发达地区光靠现有财力显然难以完成义务教育的任务,应该考虑适度加大在这方面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力度。另外,如果暂时难以全面实现这一目标,是否可考虑中小学教师工资参照本地区工资水准实行按区分类发放,而不是全国统一的标准,否则会加剧欠发达地区财政压力,加重农民负担,也不利于农村教师队伍的必要精简。这方面也可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范围内的机动权力。
5.进一步研究和消除农村税费改革中产生的新的负担不均情况,十分重要。可能存在一种远景,即借鉴市场经济的国际经验,在进一步的税费改革中,将农业税纳入城市、农村区域一律的增值税范畴,同时明确集体土地的地租形式,使之归位;近期则可通过适当提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的货币负担来减少不均。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通过适当途径配套解决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通问题既有利于缓解负担不均,也能够提高耕地的使用效率。
6.乡镇、村级债务的消化需要多种途径综合配套。建议各级政府下大力气首先摸底,不轻率行事,不能采取有损政府形象的过激措施。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乡、村两级债务可能相当大(中新网曾经报道,我国乡镇债务总量在2000-2200亿元,平均每个乡镇在400万元左右;另有一说,我国乡、村两级债务约在3700亿元左右)。各地摸清楚实际情况后需根据本地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中央级对此则应作出必要的规范和指导。
7.农业四税征收管理的“法规空当”急需填补。政府有关部门对此事还应举一反三,在今后改革和工作中有必要防止类似“脱节”与“真空”情况出现。“有税无地”问题,目前也决非基层能够解决,建议中央和省级对此种情况作出协调处理。
8.“一事一议”和“两工”问题的处理界限,看来还需要实事求是,给予基层一定的弹性区间。五保户供养、农村合作医疗等有关社会保障体系的事项,应鼓励农村基层继续试验和探索。
标签:农民论文; 税费改革论文; 农村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政府债务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三农论文; 农业税论文; 经济论文; 债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