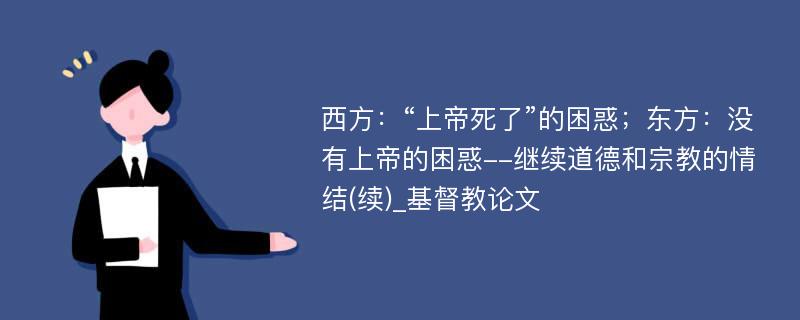
西方:“上帝死了”的困惑;东方:没有上帝的迷茫——续伦理性与宗教的情结(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帝论文,死了论文,伦理论文,情结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了解西方为了认识自己
我们在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会发现基督教在其中的深远影响和中心地位,有的学者不无夸张地将西方文化归结为一种“基督文化”。基督的信仰是一种与时代同步的理性化神学,亦即康德所张扬的“理性限定下的”神学,理性突破基督教教会律条的高墙,筛选出基督教观念中的思想精华,成为“对近代以来全部西方文化内涵的总体描述”。我认为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它通过宗教的信仰和律条所沿袭下来的神学传统,而在于由它融合、开启,又经过人类的体验、思索和筛选而成的一整套文化观念。基督教本身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说明,经过耶稣对犹太教的反叛,路德对罗马教的反叛这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基督教的信仰日益趋向于一种与时代同步的理性神学。
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从认识发展来说,沿着休谟--康德--叔本华出现的所谓非理性主义思潮的逆反,完全是合乎逻辑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潮,走向了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至康德,黑格尔所形成的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传统的反面。“西方的二十世纪,是一个非理性的长予刺杀了信仰的世纪”。非理性主义对于理性主义来说是一种反叛意识,它的直接现实化的理论品格,决定了它对西方社会和人们道德生活的观念影响的直接性和广泛性,形成了对基督教信仰的强大冲击力,与此同时,宗教生活的地位在二十世纪开始下降。而二十世纪是人类陷入最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时代。这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的社会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文化危机”。西方人在反省、寻找摆脱这场文化危机的出路中,宗教--文化论者更简捷地让基督教从神秘中抽象出来的元素重新归于神秘。从中找到新的起点,获得新的力量,“又能顽强地滚动那块西西弗的巨石”,他们在前人对理性和自由意识讴歌光沈响绝之后,以一种更极端的非现实性与基督教精神的终极指向相融和汇入非信仰的神学的潮流。“他们的上帝是死了,因此他们自己成了上帝,”就是说,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已经死亡,但那种靠个人内心去体验的信仰却还没有死亡。西方现代文化的源泉同样来自那贯穿于整个基督教文化的双重的选择之中,理性与宗教在西方文化中是一个神秘的情结,借用弗罗伊德的术语叫“恋母情结”。但基督精神不是“原欲”构成的“本我”,而相当于“由良心主宰的超我”而文化则相当于“自我”,这种不论不类的比附未必恰当,只是为了引起思辩的联想而已。
以上结论,作为一个参照系,用来反观各国基督教的状况,这样,才能为本文找到一个“现实意义。”的立足点。
中国“革命派”心目中的宗教是与“迷信”划等号的,或者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中不加思索地接受过来的关于宗教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宗教特别是对于基督教有精辟的科学的论述,我们当然要学习运用。“宗教鸦片说”在马克思以前的德国人中就有歌德、海涅、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诗人就曾有如是提法。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摆脱了中世纪神权意识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观点,所以它是祛除中世纪宗教蒙昧的启蒙思想的口号。马克思继承启蒙思想家的这一观点。但这一句话决不能概括马克思的宗教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于1843-1844年1月)曾说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一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列宁的《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全集》第二卷)这篇文章中引用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并把它誉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列宁把马克思这句话的真理性推向了极端。从此以后,有些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工作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顺便把这句话认作为集中揭示宗教本质并作为制定宗教政策的指针。其实,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对“宗教的批判”的结论性的断语,是从宗教的社会功能着眼而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人民的麻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文化背景及现实社会的实际,脱离社会功能而无限地扩大这句话的内涵和规律性,就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宗教是那些尚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自我意识,是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异化,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但是,宗教信仰所反映的内容并不是什么超出经验之外,不可捉摸的虚幻的东西,也不是信仰者个人内在的观念或感情,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在客观力量,这种外在客观力量当然应包括宗教的行为、活动,宗教的组织和制度,体现为宗教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活动,又逐渐规范化为宗教的组织和制度,因此,宗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存在于社会之中。宗教教义、教规的设立,强化了宗教的社会性,把广大信仰者纳入共同的组织,规范了他们的行为和信仰,影响以至决定了他们的整个社会生活。这就是使宗教在现实社会中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
但是历史证明,在苏联、东欧和亚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只承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种社会功能,否定宗教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作用。所以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受到排斥、歧视,宗教活动受到限制,或者说只看到宗教的消极的社会功能而忽视或不承认其积极的社会功能,或者把宗教当作政治的附庸和进行斗争的工具。
俄罗斯、南斯拉夫,巴尔干诸国都是信奉东正教⑧的国家。特别是俄国,基督教自中世纪由希腊传教士从拜占廷传入,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约有信徒2500-5000万,有教区教士十一万余人,一八九零年有697个修道院,共有四十九万六千余俄亩土地,教会除本身所取得的收入外,国家还要供给巨额补助。在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的革命者把教会当作反动势力对待,认定东正教是“为俄国专制制度效劳的”(吉特林诺夫《为俄国专制制度效劳的东正教》,列宁格勒,1924)是“处于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保护之下,并为其服务的”(〔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册中译本第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苏联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们预言:“基督教的消失,象一切宗教的消失一样,也是必然的”。(同上书)应该说俄罗斯东正教会及其上层神职人员,在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扮演着反动势力的角色是历史的结论,但俄国广大的基督教徒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投入反动营垒,也应该是历史的事实。
由于“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前,东正教教会的立场,始终是千方百计地彻底支持专制政体和剥削制度”,(同上书)所以,“一九一八--一九三九年东正教受到共产党政权严重迫害”⑨也是历史积累的必然后果。但苏联十月革命并没有消灭东正教,相反,在一七二一年被沙皇彼德大帝撤消的莫斯科牧首区,在十月革命后得以恢复。可是一九二二到一九四二年的二十年间,俄罗斯东正教被大大地削弱了,教会的活动和教徒的宗教生活几乎被迫停止,一九四三年以后,斯大林改变宗教政策,俄罗斯正教再度勃兴,新牧首选出,神学学校成立,成千处教会恢复活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正教会再次受到迫害”。⑩
这里要强调的是宗教在十月革命的俄国的社会功能不全起“麻醉人民”的作用,更不要说反革命的作用了。否则俄国的共产党人不会在十月革命后恢复莫斯科牧首区,斯大林也不会在一九四三年“突然改变宗教政策”。更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莫斯科牧首积极进行国际活动,尤其是参与苏联政府支持下的和平运动。一九四八年东正教各首脑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庆祝俄罗斯正教会自主五百周年,采取了激烈的反西方立场,这是明显地在发挥进步的社会功能了,一九六一年莫斯科牧首区参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反西方的立场有所改变,仍是“效忠”苏联政府的。同时政府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活动自由的政策放宽了。这证明宗教还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否则便无法解释,在现代社会的分化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与宗教教会组织、教徒的宗教生活出现了各自遵循着本身的准则发展的趋势,俄罗斯正教再次勃兴,而且有了鲜明的自主意识。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并非是唯一的社会功能,还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或西欧诸国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中找到例证。
德国神学家、牧师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纳粹德国更加疯狂推行专制暴政,许多正直的不愿与纳粹合作的人纷纷流亡国外,此时身在美国的朋霍费尔却毅然只身返回德国,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假如我此时不分担我的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与战后德国基督教生活的重建。”一九四三年八月,一直在国内从事地下反纳粹活动的朋霍费尔与他的妹妹、妹夫一同被关进了特别集中营。他入狱后,一些朋友想营救他出狱,被他坚决地制止了。因为他不能因自己而牵累他人的生命安全。朋霍费尔对上帝的信仰的崇高精神在反纳粹的行为中具体体现出来。他坚信,反抗暴政不仅是基督徒的权利,更是对上帝的软弱尽其本分。所以,他的反纳粹活动具有民族主义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他对上帝的正义的忠诚,远远高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在盟军解放佛洛森堡集中营的前一天,朋霍费尔被纳粹处死,他就义时非常从容。“朋霍费尔的生与死乃是二十世纪的苦难历史中基督教精神的光辉见证,作为本世纪最杰出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他的神学思想本身如何,属于神学探讨的问题,作为一位普通的基督徒,他的人生实践则得到各派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举世敬佩。”(默默《参与上帝的痛苦》、《读书》1989年第2期。)
还有巴特(Barth karl 1886-1968),瑞士基督教神学家,1937年希特勒上台后,巴特从一开始就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福音教会内部支持纳粹党的“德国基督教”派。1934年他同马丁、尼穆勒等其他反纳粹宗教界人士共同发起巴门会议,通过巴门宣言。巴特拒绝无条件地宣誓对希特勒忠诚。因而不得不离开波恩,赴瑞士巴塞尔任神学教授,继续反对纳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瑞士军队服务。战争结束后,他一方面谴责近代膨胀起来的德国军国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主张同战败后的德国友好,冷战期间,他反对搞反共十字军一类的活动,主张和平,要除掉东西方之间的铁幕,反对把苏联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反对使用核弹。参加巴门会议的宗教领袖人物都反对德国纳粹,如果按照流行的历史公式;“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的精神鸦片”,俄国十月革命前期和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并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的基督教所起的作用也并非如此。因此,宗教的社会功能,特别是作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文化习俗”或“社会伦理”的基督教更不是用“鸦片”二字所能概括得了。从文化的视角看,所谓的文化价值或文化意义的最基本的内核就是人性或自由。人类的全部文化活动,符号形式或思维方式的演变过程,归根结蒂就是一个塑造人性、创造自由的历史进程,只有人性才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程”的实质性的标志,宗教首先是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符号形式和思维方式,因而宗教便是人性的“一个扇面”,是人类走向自由的“一个阶段”(参见卡西尔Cassier:《人论》第68、228页)所以宗教对人性和自由的塑造和发展有一种不可否定的积极的功能。是否可以说,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都是适应于个体或群体的某些基本需要而形成的。按照文化功能派的创使人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观点来说,它们的主要文化功能即在于,将人类情感中,精神上,人格里的积极因素予以传统化,神圣化,从而既使个人心理获得平衡,又使社会生活得以巩固。他说:“凡有文化便必有宗教……尽管文化对于宗教的需要完全是派生的,间接的,但归根到底宗教是根据人类的基本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文化方式”。(马林诺夫斯基《文化》Culture Typewritten Manuseript,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第108页,笔者未见原书,转引自张志刚《在宗教与文化的交汇点上》)宗教是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的绝大多数信念与仪式都跟人的生命过程息息相关,是社会生活最主动的文化现实,苏联与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在他们当政的几代人中间,几乎没有认真探讨宗教与文化二者之间的极为重要的关系。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化,瓦解的历史有相当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就文化原因方面说,他们无视历史文化中的基督教的传统,低估了基督文化的社会功能,即低估了基督教在他们的社会里作为“文化传统”或“文化习俗”的社会功能,他们一向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层次军事、政治问题,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建立在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或文化习俗这一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他们双眼紧盯的政治思想、阶级斗争、理智文化等在整个历史画面上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其实,在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真正对平民百姓和社会传统影响最大的还是宗教活动。当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家致力于改造社会秩序,实现现代化时,普通百姓事实上还是在中世纪的宗教氛围里生活着的,这并非普通平民百姓“落后”、“愚昧”,只能说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过程是决不容忽视的,任何低估处于西方文化之前夜的那段以基督教文化为特征的历史,这意味着他们的事业的失败,不管他们是如何百分之百地掌握真理,代表正义、进步和历史的发展方向,因为不仅近代文化所必需的精神力量,甚至包括近代文化的先驱者们都是这段历史孕育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也离不开这段历史的孕育。某些肤浅的革命家把宗教视为反动的意识形态或敌对势力,既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不利,也损害了宗教维护社会安定的积极性,一般的宗教对现实政治都持有疏离感,保持一定距离,如对暴力、不管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持否定反感的态度而视之为恶。这并非说他们没有真理、正义的标准,宗教教义中的善与恶的价值标准与现实政治中的善与恶的价值标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又不是完全一致或者说什么时候都一致。宗教的善与恶的价值判断是建立在对终极关切意义上追求上,而现实政治家的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往往是建立在非常实际的现实功利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宗教价值观与革命家价值观不一致的地方。宗教以向善为慈悲,是应该肯定的。宗教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正义事业的认同、支持需要革命家们的耐心等待和诚挚关怀。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分子以及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某些反动势力确实存在的,但并非是宗教本身的“罪过”。作为人类深层次的精神活动,不管是原始宗教还是现代宗教,就它本身来说,并不能与迷信等同。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俄国及东欧诸国不同,没有产生象基督教那种形态的宗教。中国文化既非宗教型的也非哲学型的,而是血缘伦理型的。中国人坚执着有限的世俗人伦秩序,漠视个人生命终极价值的追求,没有对超验世界的神性困惑,中国宗教(道教与佛教)没有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截然两分,中国人的作为“天人合一”(儒道两家推崇的已成为民族的人理状态模式)中最高存在者的天道是理性与存在,价值与现实合一的实用理性,天道与人同处在一个等级的现实存在物,并非是高出于现实人生的另一种不同质的绝对存在,这种实用理性的思维模式,只让人们满足现世生活的享乐,倾心于人伦关系的和谐,这就从根本上继绝了指向未来的终极理想和绝对价值,用无限的理想来支撑有限的存在的必要性。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是圣人道德,是为统治者和上层文化人享用的修身齐家和治国安邦的理论与方法,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修养人格的人生伦理哲学,而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泛神论是以“道”取代神后,将精神生活的超越性不是支付给神学的彼岸世界而是在此岸,在现世的物质世界中幻化出寄寓人生理想的精神家园--逍遥游世界,是以历史退化观彻底否定文化存在的虚无主义的人生精神救疗法。由道家衍生出来的道教,主张的“白日飞升”是俗人凡胎的成仙作祖,进入天界,更是以形体长生不死的神仙方术来表达对现实人生的绝对肯定的意向。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汉魏六朝至唐代而与道、儒合流,以世俗化伦理消融原有追求超验价值的宗旨,转变为不否定今生现世而又得瞬间超越的中国文化之一种。漠视对个人生命终极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化从古到今的一种独特的东方文化心态,中国文化的这种宗教的心态,由于不存在对超世的天启的企盼和对上帝的崇拜,所以有一种宗教饥渴,这种宗教饥渴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往往靠迷信来填补,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起义都曾利用普通平民百姓的这种宗教饥渴的文化心态。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神化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就是最精致最巧妙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代中国人的宗教饥渴。改革开放以来,泛滥不止的命相、风水、《周易》、修庙热,也是群众一种宗教饥渴的表现。
资产阶级学者、宗教社会学专家韦伯(Maxweber)通过从整体上反省世界文化现象从而认识到:现代社会“理性化”除去了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之后,并非说要消灭宗教,他认为宗教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说:“那些神秘的、宗教的力量,以及基于它们而形成的有关责任的伦理观念,在过去历来就对行为有着至关重要、促进生成的影响。(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58年,第25页)韦伯的话值得我们作为思考中国文化建设的参考系,应该认真贯彻中国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的条款,让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挥其社会功能。
责任编辑注:本文上篇发表于复印报刊资料本专题1995年第1期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