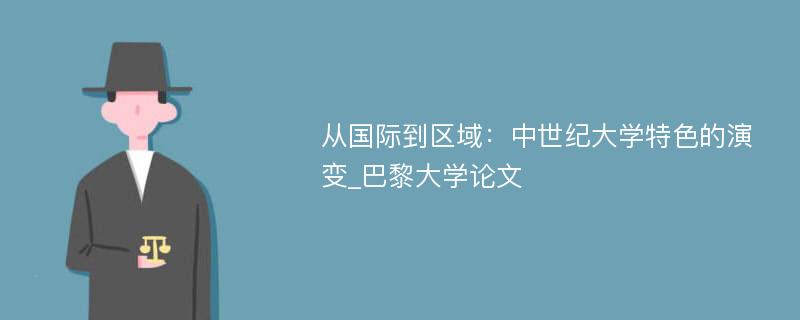
从国际性到地域性:中世纪大学特征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性论文,国际性论文,特征论文,纪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00(2015)08-066-06 西罗马帝国覆亡之后,基督教作为“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1](400),实际上担负起了欧洲文明从头做起的重任。此后几个世纪中,欧洲世界逐步完成了对基督教会的集体皈依,基督教会成为统一欧洲的重要力量。在宗教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统治模式下,欧洲形成了一个政治、思想、文化趋同发展的基督教世界。在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影响下,作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环境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的中世纪大学,在其发展初期表现出鲜明的国际化色彩。后来受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欧洲国家的民族意识开始苏醒,世俗王权在与教会争权的过程中逐渐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与干预,大学的国际化色彩淡化,逐渐成为地域性的组织。中世纪大学在地域特征上的嬗变,是其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体现。 一、国际性:中世纪大学发展初期的显著特征 大学先天具有世界性格。“大学”的拉丁文是“universitas”,与宇宙“umverse”有相同的词根,含有无所不包和普遍主义的蕴意。中世纪大学发展初期,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秉持统一的学术标准,开设基本相同的课程,并相互承认学位,“在一个上帝管制的世界里,学者不属于哪一个具体的国家或民族……(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学术共同体世界的公民”[2](70)。欧洲中世纪大学具有鲜明的国际化色彩。 (一)人员构成的国际性 在欧洲中世纪大学发展初期,构成大学组织成员的教师和学生往往来自欧洲乃至其他洲的各个地区,生员构成具有广泛的国际背景。据统计,13至16世纪在巴黎大学执教和攻读的知名学生中,有153名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200名德国人,56名荷兰人,109名意大利人,44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41名斯堪的纳维亚人,41名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希腊人,甚至还有一批来自亚洲的学者。[3](215)博洛尼亚大学不仅招收意大利的学生,还招收一大批来自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波兰、匈牙利的学子。学生构成的广泛性缘于中世纪大学宽松的入学规定。当时的大学,对于入学几乎不作国籍、社会地位、智力和语言等方面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入学考试。“除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不言而喻要接受洗礼之外,唯一的入学标准似乎就是道德品质:这是一种每个人在原则上都能达到的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包括合法出生的证明,但实际上只需要一个人相信自己是合法出生的就行了。”[4](187)甚至对于那些不需要获得学位的学生而言,即使这样的证明也是不必要的。如此宽松的入学条件,使得进入大学并成为一名大学生变成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不同地域的学生和学者以共同的语言、宗教为维系,以追求共同的知识与真理为动力,在中世纪大学中汇集、交流和共同生活。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等大学也如此成为该时期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集散地和著名的学术中心、国际中心。 中世纪大学人员构成的国际化与当时欧洲市政生活的复兴和学术风气的浓厚有密切关系。在意大利等地区,教会势力对世俗生活的干预相对较弱,继承古罗马市政制度和法治传统的城市在法治的框架下自由运行。为扩大税收来源,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大帝曾于1158年颁布《安全居住法》,使得外籍学者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合法居住权和特权,这大大促进了经济和教育活动的繁荣。同时,在一些学者的带动下,巴黎、博洛尼亚等城市的学术风气异常浓郁,杰出的学者如阿贝拉尔(Abelard)、爱那里乌斯(Irnerius)、格拉提安(Gratian)、康斯坦丁(Constantine)等人以其丰富的学识、杰出的人格和卓越的演讲吸引着大批学者不远万里前来拜师求学。因此,凯姆普沙尔(Kempshall)说:“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是一部逐渐机构化的历史,但它的开始阶段却是非计划的个人行为。”[5](203-209)可见杰出学者的个人魅力对中世纪大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二)民族团的兴起 民族团,英文作nation,它是中世纪大学国际性特征的重要表征。由于构成中世纪大学组织成员的学生和教师来自欧洲的各个民族和地区,他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以外籍人员的身份与本地人员及其他民族地区成员和平相处、共同生活。基于共同的出生地、民族、语言、文化、利益等因素,外籍人员以地缘为纽带,结合形成了中世纪大学内部重要的组织结构——民族团。中世纪盛极一时的博洛尼亚大学有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学生组成的14个民族团和来自以南地区的3个民族团:巴黎大学有法兰西、皮卡第、诺曼底、英德等四个民族团,其中的英德民族团成员主要来自东欧、北欧、苏格兰等地区。[6](133)由于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师大多来自本地,享有市民特权,所以博洛尼亚民族团由学生单独构成;而巴黎大学民族团的核心成员则是其基础部的教师,他们除自己作为民族团成员外还会介绍与其来自相同地区、在高级学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加入,但条件是这些学生要保证担任两年基础部的教学工作。所以,巴黎大学基础学部的教师大多具有双重身份——基础学部的教师和高级学部的学生。民族团组成人员身份的不同也带来了两所大学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特色,前者为典型的“学生大学”,后者为典型的“先生大学”。 中世纪大学的民族团是一个带有自卫和互助性质的行会组织。它们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来自异国他乡的学生(其处境类似于今日所说的“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从而保障中世纪大学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各地学生,不断彰显其国际化色彩。 (三)学术制度的开放性:游学与大学间的人员流动 欧洲中世纪大学以开放性的姿态接纳来自欧洲各地的成员,除了民族团作为外来成员的组织机构外,还有一项重要学术制度显示出其国际化的色彩,那就是中世纪大学著名的游学制度。游学制度源自中世纪市民对旅行的热衷。“中世纪的人喜欢旅行。他们不在乎道路稀少,在只能靠步行或骑马、乘船或坐马车的情况下也依然乐此不疲……旅行者像一支无所不在的大军挤满了欧洲中世纪的道路。”[4](307)中世纪大学充分尊重了时人的这种爱好,允许学者和学生的自由流动。游学“是一种学生和教师为了学习目的在欧洲一国或者多国进行的旅行”[4](308)。游学的兴起得益于中世纪大学开放性的制度设计,比如所有大学都有相同的授课科目、课程、教学方式、学位授予,如入学要求宽松并学位互认等。游学作为中世纪大学一道独特风景逐渐成为传统,并演化为如今西方教育中的一项特殊的学习、交流方式。 除了游学制度外,中世纪大学在校际和国际的人员流动也十分频繁。比如学者彼得·伦巴德曾先后在博洛尼亚、兰斯和巴黎等地求过学;作家彼得先在图尔和巴黎学习哲学,后于1160年左右前往博洛尼亚学习法律,后又回巴黎学习神学,最后在英国完成学业;[7](59)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追随阿贝拉尔学习长达12年之后,又师从米兰的米伦和康彻的威廉,后又成为伯纳德的学生,又追随其他教师学习数学和修辞学,可以说终其一生都处于不断的游学和迁移之中。[8](101-103)在人员流动的过程中,大学的办学模式被传播和模仿,一些新大学得以建立。比如博洛尼亚的学生在迁移的过程中建立了帕都亚(Padua)大学和锡耶纳(Sienna)大学。而在法国和英国,法学被博洛尼亚人布拉森丁(Placetin)引入蒙彼利埃大学,罗马法被另一位博洛尼亚人瓦卡瑞乌斯(Vacarius)引入到了牛津大学。[9](153) 二、地域性:晚期的中世纪大学 1378年,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事件,使欧洲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教会和教皇的权威日益下降,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被打破;另一方面,随着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日益加强,民族国家和地方政权不断兴起和壮大,他们开始和教会一同介入到大学中,并不断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和影响。在此背景下,中世纪大学的国际化色彩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其发展的民族化和地区化趋势。 (一)大学数量的扩张和分布的区域化 中世纪大学发展中后期,其数量不断扩张。从大学产生至1378年“大分裂”之前,将近300年的时间,欧洲实际存在并运转的大学约为30所。而在随后的2个世纪中,新增大学近40所。尤其是1451至1500年间,欧洲新增大学多达22所。据统计,至16世纪末,整个欧洲大学的实际数量已接近70所。[3](195)伴随着数量的扩张,中世纪大学在分布上也明显与之前不同,出现了区域化的特征。在中世纪大学发展初期,大学主要集中在意大利、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三大区域,即所谓的地中海文化圈内。晚期的中世纪大学在分布上突破了地中海文化圈逐步向欧洲中部地区转移。新建的大学遍及整个欧洲,除英格兰地区外,几乎欧洲所有地方都有新建大学的出现如伊比利亚半岛上有7所大学,法国有8所,德国有14所,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和匈牙利有9所,意大利则有8所。[3](195)新增大学吸引了大量学生和学者的加入,欧洲高等教育在知识和学术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欧洲大学在地理分布上的扩大无疑给欧洲学子带来了福音,他们不必再跋山涉水到异地他乡求学,而选择在家乡或邻近地区就近接受高等教育。因而,新大学较之前招收了更多的本地区或本国的学生。与此同时,新大学之间的交往也明显减少,“大学形成初期的那种来自不同区域的学者不受拘束在各大学之间自由漫游、讲学,为了追求学术和探索真理,自由往返于不同地区的现象已不多见”[3](121)。相对于发展初期,中世纪大学的国际化色彩已明显减弱,新大学至少在生源构成上已无法与汇集四方学子的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相媲美,而仅把服务对象局限在本地区。中世纪大学进入了由国际性机构向区域性机构蜕变的过程。 (二)大学设置形态的多样化 中世纪大学从诞生后长期为基督教会控制。而随着新大学的剧增,晚期的中世纪大学在设置形态上日益突破单一的教会型模式,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首先是世俗型大学不断增加。这类大学有些是由世俗王权或地方当局直接创办,有些则是由原来的教会大学经过改造或改编而成。世俗型大学受到了国王或地方当局的捐赠和庇护,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和干涉。世俗王权往往通过颁发特许状或法人资格、为大学制定法规或法律等手段来改革大学内部的组织形式,限制大学的某些特权。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曾在1598年至1600年间试图为巴黎大学制定新的章程,进行教育改革,推行世俗化教育。许多欧洲大陆国家明确制定各种保护本国大学的法令或条例,如禁止本国学生到别国留学、某些职位须由特定大学的毕业生担任等。[10](96)其次,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教会型大学也发生了分化,新教教派开始与天主教派争夺大学的控制权。所以,这一时期的教会型大学大致可以分为天主教教会创办的、新教各教派创办的及面向所有教派开放的等三种类型。各类教会型大学虽然设置主体不同,但是教育目标基本相同,都是着眼于培养为本教派服务的神职人员,因而只接收信仰本教派教义的学生和学者,传授本教派教义。路德派创办的大学在中欧和东欧一带影响较大;面对新教的挑战,天主教派的大学在其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重大改革;一些宽容型的教会大学,如奥尔良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帕都亚大学等则向所有教派的入学者开放,允许各教派教义在学校中传播。 (三)民族团的式微 随着晚期中世纪大学地方化色彩逐渐浓厚,民族团在大学中逐渐出现了式微之势。民族团的兴起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异地学生通过强化来自相同地区“地理联系”的方式增加安全感的心理相关,而晚期的中世纪大学除古老的巴黎、博洛尼亚之外,几乎遍布欧洲全境,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上大学,不需再借助组织寻求庇护。民族团存在的基础逐步消解。1538年,奥尔良大学的10个民族团被勒令减少至4个。161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下令取消法国大学中由民族团组成的大学评议会。即便是那些仍然存在的民族团,学生在大学中的管理权及发挥的作用也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创办于14世纪中期的布拉格大学,按照其学校规章有4个民族团。在民族团内,按规定学生和教师共同享有相同的权利。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组织权利常常向教师方面倾斜。布拉格大学的评议会成员由每个民族团推举2人共计8人组成,而8人中,教师常常占据多数甚至全部席位。1391年,评议会全部由教师构成的状况得到认可,布拉格大学逐渐由“教师与学生的行会组织”演变为“教师的行会组织”。[6](555)此外,欧洲大部分大学中的民族团不仅数目大量减少,而且多数名存实亡,基本丧失了以往选举学部长、聘任教师和拥有司法裁判等权利。 民族团的式微反映了晚期中世纪大学内部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事实上,多数新建大学从建立之日起便采纳了巴黎大学的管理方式,由教师负责大学的教学和其他行政事务,学生多被排除在学校事务管理之外。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逐步取代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型”大学,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大学模式。同时,学部和学院在大学管理中的职能也明显超过民族团,成为大学中最重要的组织管理机构。民族团的式微,标志着中世纪欧洲大学丧失了其最初的国际性特征。 (四)教学与服务的民族化和世俗化 这一时期,欧洲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和教学突破了统一模式,民族国家和地方的利益被纳入到学科及教学的目标之内。英国、德国甚至法国的大学已不再遵循巴黎大学的摹本,而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上更多地考虑到本民族的需求和特色。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在课程中除保留神学教育内容之外,将课程的重心转移到造就未来学者和绅士阶层的“自由教育”。在教学方面,统一的拉丁语逐步被希腊语、希伯莱语等民族语言取代。在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意大利南部,早在1400至1500年间就有大学率先使用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在教学内容上,大量与社会生活相关、直接服务于民族国家发展的实用世俗学科被引入。由于民族国家对法律及诉讼人才的需求,法学科目被广泛增设。德国大学的法学部新设置了国际法、宪法、外交法、商法和交通法等科目。在一些大学,法学及法学家的优越地位甚至超过了神学和神学博士。随着大学的民族化和世俗化,中世纪大学所带有的普遍主义特征不复存在,大学由国际性组织逐渐沦为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地方性机构。 三、中世纪大学从国际性到地域性嬗变的原因 中世纪大学从国际性到地域性的嬗变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社会在宗教、文化与政治等方面的变革密切相关。 (一)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洗礼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无疑是对社会变革起巨大作用的伟大事件。文艺复兴所主张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及其所宣扬的人的理性取代神性等观念,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对天主教神学构成巨大冲击。从此,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经院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教皇的权威逐渐衰落,欧洲基督教世界维持统一的宗教基础开始动摇。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之下,宗教改革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罗马教会,要求通过改革建立适应于民族国家发展的“民族教会”。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封建统治的瓦解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解体。 作为“教会的侍女或附庸”的中世纪大学,在欧洲社会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冲击和洗礼。首先,随着宗教战争在欧洲的爆发,大学被不可避免地卷入宗教纷争,宗派间的对立和冲突隔断了学生和教师在不同地域之间流动和游学的步伐,许多大学的生源急剧减少。其次,由于失去了教会的庇护,一些大学的特权被取消,地产和资产被世俗政权强行没收,由教会资助的教师职位被取消,教师的薪俸一再被削减或拖欠,许多大学因陷入财政危机而无法正常运行,大学的声誉不如从前,对域外学生的吸引力迅速下降。再者,宗教信仰的混乱使得大学无所适从,许多大学在宗派争斗与“教权和王权”之战中陷入矛盾的漩涡,动辄得咎,大学传授知识和探索真理的使命难以为继。总之,宗教和文化环境的变迁日益消解着大学的国际化色彩,推动欧洲大学在指导思想、组织管理、课程与教学内容等方面向着多样化和地域化的方向发展。大学的宗教色彩逐渐减淡,世俗化气息不断浓厚,“大学以往所具有的世界性和国际性已不存在,却普遍地带有地方的性质”。[4](85) (二)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兴起 虽然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基督教的维系下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然而各世俗王权在政治上却长期处于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状态。广大民众在对基督教顶礼膜拜的同时,还将民族情感投射于封建领主或生长于斯的地方集团。因此,占据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主导观念除了普世主义外,还有地方主义。随着教皇权威的衰落和西方“基督教大世界”的解体,被宗教压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迅速被唤醒,“基督教大世界”的普世主义逐渐被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观念取而代之,以世俗王权为核心、以统一民族为支柱的独立主权国家迅速兴起。基督教对欧洲社会的统治逐渐为民族国家政权所取代。 与欧洲社会的民族国家化相适应,中世纪大学日益脱离基督教会的掌控并受到世俗王权的干预和控制。大学逐渐被纳入到民族国家发展的框架之内,其服务于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使命逐渐让位于服务民族国家、满足地方需求的使命。世俗政权开始要求大学像政府官员一样效忠于国家和地方,并将大学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利益捆绑起来。那些由地方政权直接创办的新大学理所当然地服务于新政权的利益,而一些传统大学如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等也开始屈从于国家政权的控制。1409年,为了确保本地学者对大学的绝对控制,在地方君主的干预下,大批德国教师和学生离开了布拉格大学。这一事件被著名学者科班视为大学失去超国家特征,日益被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渗透的典型案例。[4](118)大学发展初期所具有的普世主义和国际化色彩也开始为区域化、民族化和世俗化特征所替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由国际性组织嬗变为区域性机构的直接原因。 (三)大学自身的变革 在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兴起的大背景下,晚期中世纪大学自身也开始寻求变革,不断调整自己以满足变化的地方社会需求。在大学内部,经院哲学逐步走向衰败,而与世俗生活联系更为紧密的法学、医学、商学等实用学科不断受到重视,早期中世纪大学中神学一支独大的态势逐渐被一种知识价值相对平均化的趋向所取代。这种趋向推动着大学中实用课程的兴起。牛津大学曾出现一些专门从事实用科目教学的教师,他们向学生讲授章程、遗嘱和书信的起草、财产转让、记账、法庭实践、文章的设计和应用等实用课程,受到许多城市自由居民的青睐,一些学生甚至放弃文科课程而转修这类实用课程。[9](224-225)同时,大学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地方社会事务,其突出的表现是学位获得者在政府公职中的比例明显增长。早期中世纪大学的毕业生大多选择从事学术职业或教会职业,政府提供给学位获得者的职位也十分有限。1450年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学位获得者在政府公职中所占比例明显增长,政府尤其是各省创建的最高法院纷纷为获得授课证书者和博士提供俸禄优厚的职位,许多大学毕业生也将进入国家公共职位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晋升,甚至一些大学教师除了在大学教书以外,还充当一些城市公社、大领主等的司法裁判和咨询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社会事务活动。[11](119-121)大学教师在此过程中不仅获得了经济收入和社会声誉,甚至还取得了近似于国家官员的级别和地位。 晚期中世纪大学自身的变革无疑极大地拉近了大学与其所在世俗社会的距离,大学将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精神信仰与世俗社会的精神信仰融合在了一起。这一世俗化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不可能摆脱与地方世俗政权的种种纠葛和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大学影响世俗生活和参与地方事务的不断加深,晚期中世纪大学的地方化、区域化色彩不断彰显,地方性大学纷纷崛起,并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标签:巴黎大学论文; 大学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中世纪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博洛尼亚大学论文; 地域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