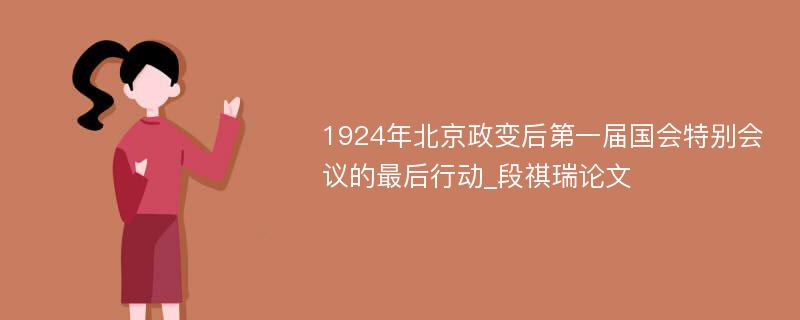
第一届国会的最后一幕——1924年北京政变后的国会非常会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会论文,一幕论文,第一届论文,北京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随着贿选总统曹锟的下台,那个受贿而选曹锟,久已为国人所不齿的第一届国会也走入了它的末路,而那二百余位当年拒绝受贿而选的国会议员(以下称“拒贿议员”),仍企图维持“法统”,以“国会非常会议”的名义继续活动,上演了民国第一届国会的最后一幕(注:虽然此后(1926年5-6月间)部分贿选议员乘段祺瑞下台,直奉重新联合之机,在北京成立议员通讯处,谋国会复活,但终因吴佩孚、张作霖不予支持而未果(参见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99页)。故此“国会非常会议”实可称第一届国会之最后一幕。)。
一、国会非常会议的建立
北京政变发生后,在上海的拒贿议员褚辅成、田桐等三十余人10月27日集会讨论时局,并发出通电,提出对去岁之贿选分子应予惩处[1]。在天津的拒贿议员四十余人11月2日集会,焦易堂提出“淘汰贿选分子,维持国会”的主张,得到与会者多数赞成,但具体如何进行,会议表示“尚须征求各方意见”[2]。10日,又电邀在沪拒贿议员北上,在沪议员即日开会议决“陆续北上”,并提出:立即驱除贿选分子,在津设立“反对贿选议员办事处”以为联络机关”[3]。在沪拒贿议员还分别致函“各处护法同志”,请迅即北上,积极进行[4]。
经过津沪两地拒贿议员的筹划联络,至11月中旬,聚集到北京的拒贿议员已达一百多人。11月22日,在北京的拒贿议员假太平湖饭店召开会议,到会者127人。会议决定成立“国会非常会议”,并以“国会反对贿选议员二百七十九人”的名义发表宣言。宣言称:“去岁曹锟贿选窃位,同人坚持正义,自维力薄,未克制止。曾以戡乱讨贼之任付诸国人及各方将领。乃者浙奉兴师,举国响应,期月之间,元恶就逮。当此民意机关绝续之交,同人自觉代表国民之职责益为重大,特于本日在北京成立国会非常会议,期存大法于一缕,共策国事之进行。俟政制完成,民意有托,同人即解除责任,以谢国人。”[5]显然,这些拒贿议员认为其去岁拒贿有功,且是今日推倒曹锟之变的发动者,正义在手,代表人民,欲以此为资本,取代“猪仔国会”而成为合法的民意机关。
11月25日,非常会议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大纲共11条,其主要内容为:“本会议由未参加十二年十月五日非法大总统选举会之国会议员组织之”;“本会议制定一切临时法规并议决关于政治重要事件”;“本会议设行政委员执行一切事务”,行政委员“由各省议员互选一人充之”;会议不设议长,开会时“由行政委员依次充任”会议主席[6]。此大纲表明,国会非常会议将本身定位为临时性的立法机关和政治咨议机构,而对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制约机制。
根据《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的规定,在12月10日的大会上,各省议员推举出各省的行政委员,组成行政委员会[7]。在12月29日的大会上,非常会议又通过了《行政委员会办事规则》和《秘书厅组织规则》。前者规定:行政委员会依非常会议组织大纲,监督、指挥秘书厅的工作;行政委员会开会时,依省区之顺序轮推一人为主席[8]。后者规定:秘书厅由总务、记录、会计、庶务四科组成[9]。其设置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机制表明非常会议的临时性和非正规性。
二、目标与结果
北京政变后,曹锟被囚,国会也停止了活动。继而检查厅开始检举、拘捕受贿议员,还在观望局势的“猪仔议员”四处逃匿,国会不解而散。取代“猪仔国会”而为此非常时期之立法机关和民意机关,是国会非常会议的主要目标。非常会议代表在会见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时称,“当此政变之际,非有民意机关不足以维持一切”,并提出须由国会非常会议来制定《临时执政府组织法》和将来的《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使执政府的行动“尚有轨范”[10]。拒贿议员王绍鏊会见《大公报》记者时指出:临时执政府“苟无一较能代表民意之机关以为之监督,或将仍蹈民六以后之覆辙”,需有国会非常会议“对于现政府监督而辅导之,使彼获循政治之轨道”[11]。
但当国会非常会议要实现为自己设立的这些目标时,则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之时,政局已趋明朗。段祺瑞在各方实力派的拥戴下,出任临时执政,组成临时执政府,控制了国家中央权力。国会非常会议欲以合法的地位开展活动,实现设定的目标,必须得到执政府的认可,否则无从谈起。对于这一点,拒贿议员们是非常清楚的,在11月22日非常会议成立大会上,即推定童杭时、王家襄等六人为代表,翌日即去“谒见”段祺瑞等人,“接洽一切”[12]。
段祺瑞十多年来,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由约法而来的这个国会一直持敌视态度,此次出山之际,宣称“法统已坏,无可因袭”[13],并欲以善后会议协调各方,稳定自己的统治,绝不希望有一个什么“非常会议”来“监督”、“辅导”自己,“轨范”执政府的行动。但仓促之间,恐一时尚无如何应付非常会议的办法和准备,当非常会议代表来访时,段委托许世英代为接见,并对代表们表示,他本人对国会非常会议“毫无成见”,但须考虑协商后,再与代表们见面答复[14]。三日之后,未见段祺瑞的答复,非常会议代表再次谒段,段委托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代见。这次,代表们对非常会议的目标和任务的设定显然发生了变化,不再提制定《临时执政府组织法》,而称非常会议只是“临时过渡之一种代表民意机关”,其任务仅在“草定国民会议之组织法……提出一种宪法草案于国民会议而止”,并强调非常会议“为纯粹辅助临时政府之机关,决不提弹劾案及质问案等等,请转达执政放心”[15]。
虽如此,段祺瑞仍不能接受非常会议的存在,而提出由拒贿议员组织一个国宪起草委员会,“重制宪法”,而“停止非常会议”[16]。拒贿议员听到这个消息后,“多不欲邃然易一名称”[17]。在12月10日的非常会议上,王用宾称:“现在政府对于非常会议,颇不愿其成立,而对于吾辈拒贿议员,似又不能不应付,拟将吾辈任为国宪起草委员以安置之”,但这个国宪起草委员会既“出之于政府任命,待将来宪草完竣时,仍不免有钦定宪法之嫌”。焦易堂也主张“努力进行非常会议,实行代表民意机关之职权,不必另组国宪起草委员会”。这种意见占优势,故由吕复等十九位议员提出的,不须政府任命,而由拒贿议员自行组织一国宪起草委员会的提案亦被否决。会议决定,“非常会议仍积极进行”[18]。段祺瑞以国宪起草委员会取代非常会议的企图未能实现。
12月13日,非常会议再次派代表王用宾、沈钧儒等6人往见段祺瑞。段先使梁鸿志出见,“谈论不得要领,段旋出接谈”。针对议员代表关于“分子有罪,机关无罪”,国会问题留待将来由国民会议解决之说,段称:此次政治变动“系纯粹革命,约法、国会应同时消灭……命令即日可下”,“曹锟公布宪法,早已革约法之命而消灭之;予乃为革曹命而消灭其宪法。要之,约法与国会皆已消灭”。对于段的这种逻辑,非常会议代表无言以对,只得辞出而去发15日召开“紧急大会”的通告[19]。
原来,就在13日当天,执政府已拟就三道命令:一、撤消曹锟所公布之宪法;二、《临时约法》失其效力;三、解散国会。段拟待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后发表[20]。“三道要令”的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与此命运攸关的非常会议更是激烈反对。在15日的会议上,各位议员纷纷发言,指责执政府的命令。有议员指出:如否认约法,解散国会,“中华民国四字即不能用,更不能继续民国十三年之年号……国际地位极为危险”[21]。16日,非常会议继续开会讨论此事,王用宾、范熙壬等议员“态度极为激昂,谓取消国会命令果下,则彼等立即通电,不承认执政府”;一些议员表示,拥护约法,坚持到底[22]。会议决定发表护法宣言,推定王用宾等15人立即起草[23]。
鉴于非常会议及其他方面的激烈反对,“接近合肥之重要分子”,以“兹事体大,不可不再四研究”相告,段乃于15日晚召集会议,“讨论约法、国会应否及早下令取消问题”。会议开至深夜4时,多数意见主张,此问题“俟召集国民会议后,交付解决”,段遂将此三道命令“搁起”[24]。
解散国会令虽“搁起”,但段仍坚持不允许非常会议的存在,遂提出由拒贿议员组织一“建设委员会”(注:此“建设委员会”后改称“建设讨论会”,又改称“建设会议”。),而放弃“国会非常会议”的名义[25]。这一方案虽仍受到非常会议的抵制,但段仍“令法制院起草条例”,准备提交国务会议通过[26]。段祺瑞的计划是,待善后会议闭幕后,设立临时参政院,作为代替国会的临时立法机关,并于1925年4月13日公布了《临时参政院条例》[27]。4月21日善后会议闭幕,4月25日,段即下令取消国会参众两院,并称,对于未参加贿选之前国会议员,将“特设机关,俾抒抱负之处”[28]。当日,警察厅即查封、接收了参议院;下午,非常会议预定在参议院开会,但“警察在门首阻止入内,未能成会”[29]。4月26日晚,部分拒贿议员在某饭店秘密集议,认为建设会议为“敷衍、安插之闲赘机关”,“不名誉”,并“相戒拒绝加入”[30]。段祺瑞则派其亲信分子曾毓隽、李思浩、姚震等人分头向拒贿议员疏通,说明政府解散国会为不得已,对于建设会议“实非常重视,希望拒贿同人咸加入,共谋国是”[31]。
5月4日,《建设会议条例》公布,规定:其成员“由临时执政聘任参众两院不参加贿选之议员充之”,职责为“讨论建设大计,拟订方案,备临时政府之抉择”[32]。关于非常会议对此的反映,《晨报》5月8日的报道称:“大部分拒贿议员均允加入”,段祺瑞已发出聘函多份,“是故非常会议业由政府顺利结束”[33]。但建设会议却迟迟未能成立(注:段祺瑞计划在善后会议后设立的几个机关,在1925年下半年陆续建立,如临时参政院、国民代表会议筹备处、宪法起草委员会、国政商榷会,乃至军事善后委员会、财政善后委员会等,惟独未见到建设会议的任何消息(至1925年底),有待进一步检阅资料。),《大公报》的报道称:半因少数拒贿议员“尚有待于疏通”,半由于正副议长的人选难以确定,“不得不略迟缓云”[34]。实际情况如何?稍后《大公报》报道了“一态度比较光明之拒贿议员”的分析:拒贿议员中,已有六七十人得到京内外各种官职或政治地位;余下200人中,有四五十人因党派关系,不可能与政府合作;还有一部分根本反对解散国会,拒绝加入此会议,“更有愤而出京以示决绝者”。如此,有可能与现政府合作加入建设会议者,“不到百人”,而这些人拘于此前“非全体一致,不许部分人先行加入”的决议,对于政府的疏通表面接受,实际上未便贸然行动,而“语人以尚未决定”。其结论是:“建设会议恐仍无完成之望”[35]。笔者以为,从个人品质而言,拒贿议员中多廉洁耿正之士,慎重名节,不会轻易接受段的收买笼络;在政治立场方面,拒贿议员中,国民党人及与国民党人立场接近的分子占相当部分,且几均为国会内的中坚分子,此时国民党与段已公开对立,而与共产党共同推动的国民会议运动,正在各地蓬勃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虽能解散国会,禁止非常会议,但以建设会议笼络拒贿议员的企图却难望实现。
国会非常会议在其后的五卅运动中,曾于6月5日发表通电,谴责列强“蔑视公理人权,断然出此残杀之横行”,表示“愿□国全体人民,一致主张公道,共作后盾”[36]。此后,则再未见到有关非常会议的消息。
三、失败的原因与存在的意义
国会非常会议之所以归于无声息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此时的国会本身已完全失掉了当初所具有的地位和威信。
1924-1925年之交,既非1913年国会初开之日,亦非1917年南迁广州“护法”之时。第一届国会自开幕至此,已逾十余载,其间历经曲折的变迁,已由万众景仰地位尊崇的民意机关、立法圣地,演变为军阀手中的政治工具。特别是1923年的贿选丑剧之后,国会和议员已成为万人唾骂的“猪仔国会”和“猪仔议员”,为世人所不齿。虽有部分议员拒贿、拒选,但这样的议员毕竟人少势弱,既无力阻止贿选的发生,也很难能使国会在人们心目中的堕落形象有些许之改变。而且这届国会“屡次藉端自延其寿命”,早已超过了其应有的任期,“颇见恶于国人”[37]。北京政变发生后不久,即有团体致电冯玉祥称:“惟民国之乱,无耻议员实为祸本”,要求拘捕受贿议员,解散国会[38]。亦有团体通电认为,“国会议员早失代表资格,须立时解散”[39]。《晨报》的一则报道称,就“国民心理”而言,“此十三年之寿命无疆老厌物,断无可以存在之理”[40]。国会整体既已如此,“非常议会”亦难以得到国人的认可和接受。
再者,这一时期蓬勃展开的国民会议运动,也对出现这样的结局有一定的影响。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倡议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军阀政权。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的邀请北上,行前发表《北上宣言》,明确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41](vol.11,p.297)。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济南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市的各界人民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表示拥护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各地还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海外华侨也函电支持,形成了有工农群众、知识界、教职员、学生、工商业者及新闻记者、律师等各界人士参加的大规模的国民会议运动,并且于1925年3月1日至4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各界民众把解决国是的希望寄托于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会议,已无心再理睬这个已根本不能代表人民的旧国会。
此外,非常国会也得不到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首先,缔造民国,曾为建立国会、维护国会而进行过努力和斗争的孙中山,即对国会不再表示支持。经过十几年的斗争与探索,孙中山不但认识到军阀“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而且对宪法、国会,这些他原先为之奋斗的目标,认识也有很大变化。1924年初,当一些国民党籍国会议员准备继续利用国会和法律进行斗争时,孙中山指出:“法律之在今日,已成军阀攘窃之资。非本革命精神从事于建设,殆无摧毁廓清之望。”[41](vol.9,p.18),在广州大本营军政会议上,当有人提出孙中山应复大总统位,继续护法事业时,孙中山当即表示反对:“现在护法可算终了,护法各议已不宜援用。因数年采吾人护法之结果,曹、吴辈毁法之徒,反假拥法之名恢复国会。北京国会恢复后,议员丑态贻笑中外,.实违反全国民意。……今日应以革命精神创造国家,为中华民国开一新纪元。”[41](vol.9,p.10)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孙中山北上之际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国会非常会议很希望得到孙中山的支持。12月初,孙中山北上到津之际,非常会议专门派人赴津迎接,拟“于欢迎之便详达组织非常会议之意”,争取孙中山的支持。但因孙中山身体的原因,“未能切实接洽”,非常会议特请彭养光、王用宾、张继等几位国民党籍议员留津,“就近与中山协商”[42]。但当12月19日,非常会议请王用宾“报告孙文对非常会议之态度时”,王则称:“中山先生之真正态度如何,不敢操切代言。惟以中山先生平时言论证之,亦可知其态度之斑”[43]。其语意不明,恐怕是因为没有得到孙中山的明确支持。
段祺瑞对非常会议的态度已如前述。被几方政治势力拥戴出山而为临时执政的段祺瑞控制着北京政权,他的极力阻挠是非常会议难以逾越的障碍。
非常会议内部的分歧与涣散也是其失败的一个原因。拒贿议员内部在是否应建立非常会议,以及对执政府应采取何种态度问题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章士钊、林长民、汤漪、乌泽声等均为拒贿议员的中坚人物,但都反对成立非常会议。章士钊出任执政府的司法总长,认为国会中受贿而选的议员占了大多数,“实不如爽爽快快,请执政府下令解散”[44]。林长民先是主张对国会进行“彻底的改造”,解散现国会,召集新国会[45];非常会议成立后,又称对其“首先反对”[46]。林长民、汤漪、乌泽声等不愿加入非常会议,“而另唱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之说”,使拒贿议员形成“分道扬镶之两派也”[47]。《大公报》的一篇报道分析,拒贿议员中,“与当局接近……不愿加入非常会议者”,约有二三十人[48]。这些人对非常会议的活动及效果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非常会议组织的涣散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国会议员向来散漫,虽然议事规则昭然有示,但开会时缺席、迟到、中途逃会等现象一直甚为普遍。在非常会议这一组织松散的特殊的会议形式下,对于其成员更是缺乏任何有约束力的要求。非常会议名义上由279人组成,但由于各种原因,出席会议的人数仅有一次超过一半。笔者根据《大公报》、《申报》、《晨报》、《民国日报》等4种报刊的有关报道统计,非常会议共开会二十余次,其中有人数记载的12次,其出席情况如下:
开会时间出席人数
1924年11月22日127人
1924年11月25日150人
1924年12月10日93人
1924年12月11日100余人
1924年12月15日87人
1924年12月17日60余人
1924年12月26日80人
1925年1月19日 60余人
1925年2月10日 70余人
1925年2月19日 53人
1925年2月25日 90余人
1925年4月22日 70余人
平均出席人数 89人④
注释:④关于1924年12月10日会议的出席人数,一种记载称:“计签到者共九十三名”。(《昨日拒贿议员之大会》,《大公报》1924年12月12日);另一记载称:“到会者一百六十余人”(《非常会议决移参院》,《晨报》1924年12月11日)。笔者取前说。“余人”均以5人计。
非常会议的平均出席人数,不足全部拒贿议员人数的1/3,表明拒贿议员内部涣散和分歧的严重,加之其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松散和非正规性,也都对非常会议活动的开展带采不利的影响。
国会非常会议从成立到无形消失,纷纷扰扰,有半年之多,虽未能实现设定的目标而归于失败,但亦具有某些积极的意义。
首先,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军阀政治起了某些制约作用。北京政变后,由段祺瑞任执政的临时执政府仍是一个与民主共和政治相去甚远的军阀政府。作为民意机关监督、制约这一临时政府,是非常会议为自己设定的主要职责。虽然非常会议为争得临时政府对其地位的承认,曾对这一职责有所掩饰,且实际也并未能进行任何有效的制约,但在某些问题上,非常会议还是发挥了一些影响。如前一节所述,主要是由于非常会议的激烈反对,段祺瑞被迫将撤销约法与国会命令的发表延迟了4个多月,对段祺瑞毁弃约法,恣意妄为的军阀政治不能不说是有力的抵制。
非常会议对段祺瑞解决“金佛郎案”中有损国家权益的行为也进行抵制和斗争。非常会议成立后曾发表宣言称:段的临时政府“系暂时的事实政府”,不能缔结条约与解决外交悬案,如金佛郎案[49]。待1925年春,金佛郎案的谈判在加紧进行。4月1日,非常会议再次通过宣言,谴责临时政府以金佛郎案损害国家权益,表示非常会议对此案“誓持反对态度”。金佛郎案签字后,非常会议仍于5月1日通电反对[50]。
此外,非常会议对段祺瑞的临时政府的军阀政权性质给予了揭露和抨击。如拒贿议员阎秉真等32人向非常会议提交了“重新组织临时政府”的提案,提案指责段之临时政府,“既不受国会监督,又无须内阁副署,以根基薄弱之政府,运广漠无限之特权”,而且抨击善后会议中“所余者仅军阀官僚代表而已,等于往者之督军团会议,于人民何与?安能解决国事!”[51]再者,根据段祺瑞的计划,善后会议闭幕后,将召开国民代表会议,而其条例由善后会议制定。对此,非常会议在宣言中指出:“国民会议组织法应由代表民意机关妥为制定,不应由含有官僚性质之善后会议产生。将来制定宪法及一切建设大计,皆须由约法赋予固有的民意机关起草,不能由政府或政府指定之别种机关起草。”[52]非常会议的这些言论,坚持了民主共和的政治立场,宣扬了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与正在蓬勃展开的国民会议运动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
毋庸讳言,在积极参与非常会议活动的这些议员中,部分人不免掺杂有谋取个人地位与利益的成分(注:时有论者将参与非常国会活动的议员分为三类,其中一类为“无活动能力,又无一定主张者”,“只求保全其衣食与地位,别无他志”(《聚讼一时之国会问题》,《大公报》1924年12月13日)。信矣。);当中国历史的脚步走到1924-1925年之交,仍希冀以国会非常会议解决中国面临的政治问题,也已不免显得有些落伍。但非常会议坚持民主共和的政治立场和与军阀政权抗争的精神,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