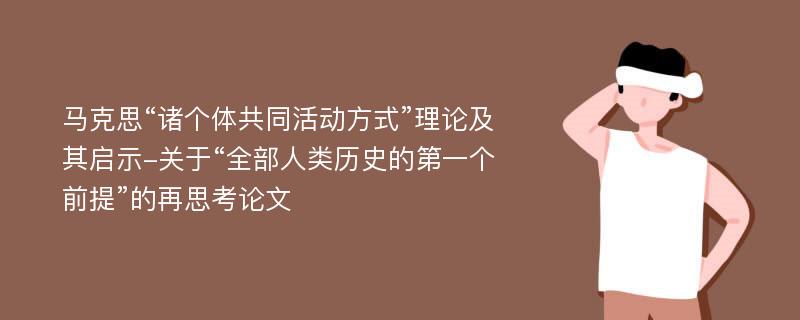
马克思“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理论及其启示
——关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再思考
沈湘平,赵 婧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 摘要] 人们以往对马克思“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理解大多侧重于其开启的物质生产逻辑。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诸个体(Individuen)的存在,直接凸显的是诸个体的共在,即以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存在。作为诸个体间联动的社会关系模式,这种具有原初性质的共同活动方式先于生产关系而不能简单归结于生产关系。人类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是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历史。“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理论的揭明,对于澄清或构建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一是有助于澄清对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的误解,凸显人们非经济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地位与功能;二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之谜的解答”,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正是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真理;三是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提供理论“接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可以理解为以人类美好生活为旨归的关于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哲学;四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形成合理有效的人类共同活动方式——包括诸民族、国家的共同活动方式和超越民族、国家的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而后者更具前瞻意义。
[ 关键词]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社会关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标志其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了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个人”,并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前提的理解着重于人类何以维持生命并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强调全部历史得以延续的基础是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继而在人类劳动发展史中找寻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无疑,这一理解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也由于对某些细节的忽略而遗漏了一些重要问题,遮蔽了马克思在讨论生产关系之前对个体存在状态的前定论述,由此导致一度将社会生活囿于经济生活的问题。对马克思关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再思考,有助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点,并获得构建社会关系的有益启示。
一、“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本质上是诸个体的共在
面对“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6页,注释1。 的现实,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历史科学的整体视野开启了使人类史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的理论征程。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的讨论是有前提的,但这个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确认”,“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个现实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然而,以往被我们忽视,如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谈“现实的个人”时,“个人”用的是复数形式(Individuen)——目前的翻译中已在“现实的个人”之前加了“一些”,紧接着的指称也是复数“他们的”(ihre);“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中的“个人”也用的是复数(Individuen)而不是单数(individuum),后续的指称中使用了复数的“人们”(Menschen)。其实,单数的“个人”(individuum)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施蒂纳用以反对“类”的、作为“唯一者”的“个体”,马克思使用复数的个人决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旨趣与理论价值。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出现的“个人”(Individuen)和“现实的个人”(wirkliche Individuen),翻译为“诸个人”“现实的诸个人”或“诸个体”“现实的诸个体”似乎更为精准;“Die erste Voraussetzung aller Menschengeschichte ist natürlich die Existenz lebendiger menschlicher Individuen”一句,翻译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诸个体(Individuen)的存在”也更为恰当。
该类型街道晚高峰拥堵状况明显差于早高峰,早高峰拥堵现象不显著,晚高峰开始较早且拥堵状态的持续时间较长,在14:30开始交通指数开始明显上升,晚高峰开始于16:00,结束于19:30,持续时间3.5 h,最拥堵时段出现于18:00—18:30. 此类模式下的街道用地类型多以办公、商场为主,集中在东城区,例如建国门街道、朝阳门街道、东四街道,区域内有工人体育馆、东单商圈、东直门商圈、朝阳门商圈等,晚高峰交通出行需求以休闲娱乐为主.
值得玩味的是,马克思在讲完“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之后,本有一句关于“第一个历史行动”的论述,结果被删去了。这句论述是:“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6页,注释2。 删去之后紧接着的是:“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4)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6、147页。 而删去的这一段的大意在论述完“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之后却有相似的表达:“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③也就是说,马克思在阐释我们熟知的生产逻辑时作了一个停顿,补充了一个展开生产逻辑的重要事实前提,即“有生命”首先意味着肉体组织受到自然的制约,“存在”首先意味着“生活”。故而,从一开始,所谓的生产不过是为了生活的生产,直接是生产人们的生活资料。
这一思想在后文中有了更为完整的表述:“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8页。也有学者结合广松涉的研究认为,这段论述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一段是过程稿中的两次不同写法,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定稿中。参见姜海波、王海洋:《论〈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编连》,韩立新:《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158页。 。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前提是人的生存、生活,第一个历史活动或历史行动是生产,生产是为了生产人们的生活本身,使生活持续成为可能。当然,这里的生活是指维系人们自然肉体存在的物质生活。
四是提升国有农场统一经营管理及服务职能。加强产业集团对农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集团与国有农场的利益联结机制,把农场培育为产业集团的生产基地。加快培育农场特色种养业,重点发展红江橙、茶叶、菠萝、蔬菜等特色产业,设立特色产业专业化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建立完善以效益为核心的经营考核制度,强化农场企业定位,制定农场三年扭亏增盈方案,将三年扭亏增盈指标纳入考核。
在最初的社会形式中,诸个体的共同活动方式总体上是自发的、狭隘的、被动的。追溯古代历史,诸个体被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天然连结,自出生起就处于家庭、氏族部落、帝国或行会等共同体中。虽然诸个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自始至终“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3页。 。也就是说,在这种共同活动方式下的诸个体,其本质和身份是先验的,是本质先于存在;诸个体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以依附于某个群体的方式被动地发生联系。
二、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内涵
诸个体的共在及其持续成为可能归根到底依赖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而人们的生产总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这种生产方式又由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构成。但是,就每一个现实的具体个人而言,在绝对的意义上存在是先于生产的。他首先得存在,然后才能进行生产。不过,人们的存在即共在首先是肉体生命的存在,但决不止是动物式的肉体存在,而是结成某种形式的共同体,进行着一些非生产性的共同活动。“生产本身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8)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7、340页。 ;“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②
天津大学和道达公司联合开发的新型一体化海上风电测风塔也利用吸力式基础进行辅助下沉和调平施工,如图5所示。测风塔架-浮体结构-吸力式裙板基础结构为一体的海上测风塔组合结构体系已应用于江苏和海南等8个海上风电场的测风工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最远拖航距离为350 n mile(启东—连云港)。
对上述思想内涵的挖掘,学界已有所研究,但尚未形成共识。有学者从生产力的宏观层次进行理解,认为通过“共同活动方式”可以由个人生产力生成“社会”生产力,希冀通过对共同活动方式的调整实现集体力的涌现(11) 邹吉忠、董建:《论“共同活动方式”与“集体力”——马克思社会生产力思想新探》,《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有学者将“共同活动”理解为“劳动者以分工协作的方式进行的实践活动”,并认为“共同活动方式是生产力的思想,具有公共性意蕴”(12) 孙淑桥、杜昌建:《马克思论“共同活动方式”的生产力意义——马克思社会公共性思想初探》,《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日本学者广松涉将“共同活动”译作“协动”,并谈到“生产”不过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历史的协动的对象性活动”,还将其看作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社会观及其世界观所定位的视域”。在他看来,有关“共同活动”的论述展示了马克思对“社会”的把握方法,是沿着亚里士多德城邦动物这个主张,对“人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动物”思想的挖掘与深化(13) 〔日〕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邓习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5页。 。在借鉴广松涉相关思想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是区别于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社会关系模式,其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14) 张聪卿:《马克思“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概念探析》,《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复有学者认为,人们共在于世是与“现实的个人”等价的人类历史前提,“共同活动方式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基础,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成为可能的社会关系模式”。(15) 沈湘平:《唯一的历史科学——马克思学说的自我规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206页。
在重溯马克思关于“共同活动方式”的原初论述,吸收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1)目前汉语翻译的“个人的共同活动”令人费解,不若“诸个体的共同活动”更贴近原意、更为精准。(2)“共同活动”不是指生产活动,而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关系性质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交往活动。(3)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是诸个体间联动的社会关系模式,“共同活动方式”不能与“生产方式”简单等同。(4)虽然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但一开始就等价于社会关系的“诸个体的共同活动”具有更原初的性质。从人类历史前提的角度看,诸个体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是生产得以可能的前提。(5)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直接表现为展现诸个体生命存在特质的各种“个人间的联系”,更为宏观地体现为一定的政治、文化、社会的制度规范,而这些都会产生一种社会力量,即有别于一般经济意义、物质生产意义上的扩大了的生产力。(6)现实的诸个体的本质就在其“共同活动方式”之中,也就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5、203页。 。同时,诸个体能动地认识、创造着社会,从而推动了社会不断向前发展。(7)“共同活动方式”是与诸个体求得解放、创造历史的过程同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共同活动方式”,人类历史也是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发展的历史。(8)“共同活动方式”的矛盾运动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共同活动方式”的合法性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前景及方向,更是一个社会维持繁荣稳定的重要指标。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18)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247页。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即“唯一的”“历史科学”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④。现实的人即有生命的诸个体,其历史发展构成社会历史的核心线索,这一精神体现在整个唯物史观之中。马克思在《1857—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则进行了最为直接的揭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该著中从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角度划分了三大社会形式,最初的社会形式是“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第二大形式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大形式则是“建立在诸个体(Individuen)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译文有修改。 。毫无疑问,生产力发展与交往形式变更是三个社会形式划分的基础,但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⑥。这种与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活动的变更,更直接地体现于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他们的社会关系模式的变更。
三、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历史发展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有个著名论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无疑,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生活是总体性概念,就包括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狭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四个方面——这正是今日所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最早表达。与“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比较起来,学界以往对马克思狭义的“社会生活”的关注并不够。事实上,社会生活是人们生活状态最直接的体现,“共同活动方式”首先就是诸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从公元前21世纪大禹创行了沟洫制度,有遂、沟、洫、浍排水蓄洪,从而进入农主牧辅的农耕时代。又过了1 300多年,到后汉、魏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317年),兴建了很多陂、堨、塘、湖等蓄水工程灌溉农田,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坑塘建设进入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新时期。
这样一来,我们发现,一方面,作为历史前提和主体的现实的人不是单个人,从一开始就是诸个体(Individuen);另一方面,作为现实的人的诸个体必须都是有生命的存在,首先都“必须能够生活”,肉体需要得到一定满足,这是存在的基础之维。两者合起来,现实的个人不仅仅是有肉体生命的人,而且是处于复数状态中的人,抽象、孤立的个体无法存在——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4页。 。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规定其实等价于作为复数的个人的共同存在或共在(Koexistenz),即“有生命的诸个体的存在”本质上是诸个体的共在。个人的存在一定是与其他个人的共在,这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而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是不以人为转移的”(7)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是个人存在的非此不可的方式和结构。这一思想隐含在马克思的论述之中,但目前的中文翻译并没有很好地体现、指引出来。由此可见,共在在逻辑上是先于生产的,生产是为了使共在持续成为可能。
在第二大社会形式中,诸个体的共同活动方式是表现为主动、实质上被动的。随着生产力、交往的发展,诸个体的共同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现实关系也日益复杂和丰富,人们突破原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很大程度上获得身份选择自由,实现了存在先于本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2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12页。 。个体因物的利益关系与毫不相关的其他个体建立社会联系。诸个体看似独立、随心所欲地“自由”活动,但实质上不能驾驭他们的共同活动。随着诸个体活动突破地域性局限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就形成了“诸个体(Individuen)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9页,译文有修改。 。在这种共同活动方式之下,诸个体共同活动受到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物的力量的支配和驾驭,而不是他们自主控制、自觉驾驭他们的共同活动。
在第三大社会形式中,诸个体的共同活动方式才是真正自由自觉的。在这一形式中,诸个体不仅不屈从于地域性、民族性的活动范围,而且其分工也不再受束缚,诸个体真正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③。共同体是自由诸个体的联合体,共同活动方式是诸个体自由、自觉、自愿、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他们选择的正是他们共同的社会关系。此时,诸个体的共同活动就表现为诸个体生命的自由活动。这便是理想的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实现,它是自由全面发展的诸个体进行的自我规定。
四、“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的“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理论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甚至陷入“隐而不现”的遮蔽状态。揭明和阐发马克思的“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理论,不仅对相关文本、思想的解读大有裨益,而且对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澄清、构建很有帮助。
一个人在与陌生人交往时,第一印象的作用较大,而与熟人进行交往时,近因效应的作用则较为明显。受近因效应的影响,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往往改变原有看法,做出错误判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种现象就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过分严格要求。教育者熟知受教育者的秉性,一旦受教育者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与平时的表现不一致,教育者就会给予多方面关注,甚至超出必要的度,认为受教育者受到了外界的干扰,甚至对其进行系统的教育[2]。
一是有助于澄清对“经济决定论”的误解。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之谜的解答”的问题——解答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也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28)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189页。 。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并未完全成熟,但寻求历史之谜的解答正是其一生奋斗的目标,也成为理解他整个理论体系的直接线索。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对唯物史观一直存在所谓“经济决定论”的误解。来自19世纪90年代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的攻击最为著名,也最具典型意义。他认为唯物史观只承认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是一种“经济唯物主义”、“技术经济史观”。有意思的是,巴尔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来自对马克思文本的直接阅读,而是来自自认为是马克思思想的继承者、捍卫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所宣传的唯物史观。更为引人深思的是,面对巴尔特的攻击,当时总体上还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竟然也宣称:“我决不想对巴尔特所用的‘经济史观’这一名称感到愤怒,而是不管怎样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23) 《伯恩施坦文选》,殷叙彝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可见,关于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的误解是多么根深蒂固。
在马克思的原著文本中,如果不加细致考察,确实容易找到一些经济决定论的证据。例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就明确说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即看似把社会关系等同于生产关系。但是,一方面,必须注意这里所指的“社会关系”明确是狭义的,是“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24)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0、327页。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该文的写作前提正是“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⑥。恩格斯在晚年也谈到,出于反驳论敌的需要,他和马克思“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因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和马克思是“应当负责的”(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6页。 。
然而,这样一种因为论战需要的“不得不强调”在列宁那里得到更为坚决的“强调”。列宁在阐述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时,提出了唯物史观“两个划分”、“两个归结”的著名论断:“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26)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9页。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人们对列宁这一思想一度作了绝对化的理解,也一度加深了对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的误解。
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经济决定只具有“归根到底”的意义,“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将经济因素说成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是对他们思想的歪曲(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4-606页。 。事实上,对马克思“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理论的开掘就是对“经济决定论”的有力驳斥。一如前述,一方面,等价于社会关系的“诸个体的共同活动”和生产关系比较起来,具有更原初的性质,它是一切现实生产得以可能的前提;另一方面,与生产方式相区分的诸个体的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若将生产这一“历史活动”等同于有生命的诸个体这一“历史前提”,遮蔽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就会忽视作为行为主体的诸个体受自然制约的“生命”及其“生活”的全部内容,甚至将社会生活缩小为经济生活,抹杀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因此,正如我们今天高度重视与经济建设相对的社会建设一样,我们必须从唯物史观的根基处充分重视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相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独特意义,从而凸显人们非经济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地位与功能。
二是更好地理解“历史之谜的解答”。
县级以下水利普查工作机构形成的需归档文件材料,应在完成收集、整理工作后,及时向县级水利普查机构归档。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将应归档文件材料据为己有,或拒绝归档。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就诸个体的共同活动及方式作出如下论述:“人们(Menschen)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ihr)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bestimmte Weise)来进行。”(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注释1。 而“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诸个体(Individuen)的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Weise des Zusammenwirkens)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译文有修改。据张一兵先生考证,马克思对“共同活动”(Zusam menwirken)这一概念的使用及其与“生产力”关系的判断受到了赫斯的影响。参见张一兵:《白开水与浓汤的辩证法》,《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14日,第9版。 。
另一种情况则是,在某一个词的现成的意义基础上,通过改变用法,比如扩大或缩小某一个意义的使用范围或者使用条件,使其产生一种新的借代用法,并在语言中稳定地传承下来,成为词义中的一种特定类型——借代意义。相对于词和词的原义而言,借代意义是后起的。例如:
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的矛盾根源在于私有制,但也与资本主义社会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有关,其矛盾的最终解决也是整个历史之谜的解答,不仅需要扬弃私有制,而且要实现一种全新的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箴言式地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0页。 “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事实上是两种不同的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以“市民”社会这一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使得个体与类以及历史之谜其他方面的矛盾凸显出来,而“历史之谜的解答”走向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不是哲学抽象、政治解放的结果,而是诸个体共同实践活动推进社会解放的历史产物。所谓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既不是简单地否定个体感性存在,也不是简单地肯定类存在,而是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两者的辩证统一和超越。或者说,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乃是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真理。
三是提供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理论接口。
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诸个体,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故马克思研究人类史就是研究现实的诸个体及其活动。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此岸世界,历史之谜的解答聚焦到个体与类的矛盾——马克思一度称为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的矛盾,因为只有“现实的个体的人”实现自身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的统一,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④。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有无、内容、性质的讨论很多,亟需回到政治哲学的根基之处加以廓清。重溯原初或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我们将发现:(1)政治是人们为超越复数的个人,实现共同存在而创造出来的,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美好生活如何可能;(2)政治哲学是正向建构而非解构的,解构自身不构成严格、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哲学;(3)政治哲学是常规(顺守)而不是非常规(逆取)的;(4)在中国探讨政治哲学事实上不自觉地有一个与其他政治哲学进行比较的维度,那就是要思考什么是好的政治哲学。好的政治哲学是既要能够与其他政治哲学共享沟通,又要能够超越其他政治哲学范式。以此观照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显然,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理论及马克思早期有关政治哲学方面的思想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唯有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的阐释中,不仅为我们所理解的政治哲学提供了原则、方法,而且留下了独特规定性的理论“接口”,这个接口就是长期被我们忽视的“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可以理解为以人类美好生活为旨归的关于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哲学。
诸个体的共同活动方式超越了作为复数的个人,探讨现实的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矛盾及其理想共同活动方式何以可能,这使得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其基础处和其他的政治哲学可以沟通,从而确立了彼此对话的可能基础。同时,在其本质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其他政治哲学是有差异的,最基本的差异是其理论立足点不同。其他的现代政治哲学即资本主义政治哲学本质上都是立足于“市民”社会的,是一种民族、国家的政治哲学。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以人类解放为旨归,从而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视野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格局。一如前述,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乃是基于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立基于此,我们对美好生活如何可能要作一种历史性形成的人类的总体理解,所有政治、政治哲学概念都必须从存在的历史性深度、人类的整体高度来重新把握。
具体来看,马克思至少从三个层面直接运用诸个体共同活动及其方式理论谈及其政治、社会理论。第一,从政治国家的产生来看,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诸个体(Individuen),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诸个体(Individuen)的生活过程中产生。”(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1页,译文有修改。 第二,在分析资本的产生与运动时,马克思确认:“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 第三,就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而言,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6页。 而体现这种理想政治生活属性的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乃是“人民的自我规定”(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
(4)加强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立法规划。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超出法律实践,需要在理论上加强研究,及时跟进。人工智能的立法既涉及对人工智能本身的认识,包括社会伦理问题,也涉及具体应用问题,还涉及数据、算法等技术问题,不同的问题归属不同的立法范畴。这就需要从总体上加以规划,在人工智能总体立法尚不成熟时,具体应用领域立法不应停滞,应成熟一项、出台一项,先易后难,逐步形成体系。对人工智能风险的管控,目前还主要在弱人工智能领域,今后强人工智能也可能突破,这方面更需要在理论研究上先期投入,为制定一个通用性的人工智能法律奠定基础。
四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现实的个人从来是诸个体以某种共同活动方式共在着的。从空间上看,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的历史也是一个共在共同体不断扩展的过程。在古代,人们虽然有过天下一家的文化想象,但从未使其成为现实。在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后的今天,诸个体逐渐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诸个体的共在真正拓展为整个人类的共在,即人类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当我们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是有生命的诸个体的存在时,就等同于说,人类必须以某种共同活动方式来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可能以及持续成为可能。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过是对人类共在这一客观事实的真理性反映和使这一事实能够可持续的积极筹划;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可能以及如何持续可能的关键就在于找寻到合理有效的人类共同活动方式。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愈发凸显,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构成对人类的基本生存的重大挑战。这就要求作为诸个体集合单元的各个民族、国家,共同合作以应对世界问题,自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反思性的行动,构建就意味着一种规范。于是,什么样的共同活动方式才是合理有效的问题突显出来,而这也正是当今世界诸大国博弈、自我辩护的焦点所在。我们认为,以作为复数的诸文明为前提,开启基于共在的反思并展开文明对话和公共性批判,从而无限逼近人类向好共在的“公共利益”,是探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唯一合理方式,而任何一种反思、公共性批判的结果都应该落实到人类共同活动方式的规范上,否则就失去意义。
物联网的技术架构分为3层: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如图1所示。其中,感知层实现物联网全面智能化感知,网络层将实现接入信息管理和由计算机网络及通信网络构成的承载网络,应用层实现应用支撑服务和用户应用服务。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我们所理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来“共商共筑共享”的。然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的追问,不仅关涉以集合体形式存在的民族、国家,更关涉全人类的诸个体。尽管在现实社会中,诸个体间特别是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诸个体间的直接联合还大大受制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状况,但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诸个体层面追问,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更具前瞻意义。一方面,一如马克思“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理论所启示的,由世界历史性诸个体相互联系直接构成的整体,才是真正社会化的人类、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当代,个体与人类之间的敏感依赖关系,个体活动的全球性、人类性影响已经逐渐成为客观现实。因此,从整个人类命运的高度反思诸个体共同活动方式而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的共同活动方式将越来越迫切;同时,只有始终确保有生命的诸个体存在,全部人类历史才得以可能,人类才有可持续的未来。
Karl Marx ’s Theory on “The Cooperation Mode of Individuals ”and Its Enlightenment :Rethinking about “the first premise of the whole human history ”
SHEN Xiangping, ZHAO J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s “the first premise of the whole human history” in previous studies mostly focused on the logic of starting material production it revealed. And in fact, in Marx’s view, the first premise is the existence of the living human individuals, which directly highlights coexistence of all individuals in a certain mode of cooperation. As a model of social relations among individuals, this primitive mode of cooperation precedes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whereas it cannot be simply attributed to the relations. Human history is not only the history of human activities, but also that of the cooperation mode of individuals. Understanding the theory of “the cooperation mode of individuals” is prominent in clarifying or constructing a serie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s. Firstly, it contributes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ghlighting the connotation, status and function of non-economic social life. Secondly, it leads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nswer to “riddle of history”, and reveals the truth that human society or social humanity exists in the mode of cooperation among individuals. Thirdly,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interface” to the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operation mode of individuals in the light of wellbeing of human. Fourthly, it offers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lies in the formation of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mode of human including the cooperation for individuals within or beyond the same nations and states, and the latter is more of forward-look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 :Karl Marx; individuals in reality; individuals; the cooperation mode; social relations
[ 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9)06-0103-08
[ 收稿日期] 2019-08-23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武晓阳 宋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