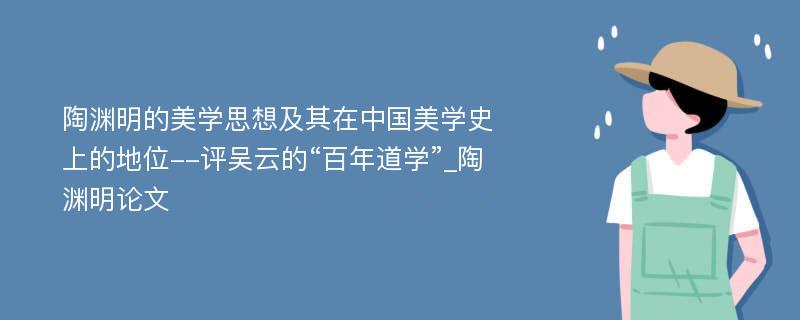
陶渊明美学思想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兼答吴云《陶学一百年》的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史上论文,中国论文,一百年论文,陶渊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审美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文学艺术家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撇开现实的利害关系,以超功利的态度同对象世界发生审美关系。陶渊明的审美与他的人生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沈约最早指出陶渊明“真率”的人格;昭明太子进一步肯定其“颖脱不羁、任真自得”的品性和“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的艺术风格,初步揭示陶渊明以“真”为核心的人生——美学观。
陶渊明的一生,确实是以“任真”自期自许、自高自傲地走过来的。他的“真率”甚至达到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程度。他直言不讳地声称出仕就是因为“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喝起酒来,更是抛却碌碌尘寰,“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任真自得,乐而忘忧;甚而忘记俗世一切繁文缛礼:“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萧统《陶渊明传》)对朋友总是那么一往情深:“物新人唯旧,弱毫多所宜。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无论是待人接物,日常生活琐事,还是关乎经世济时、出处进退大事,皆一任自然、泰然处之。诚如东坡所见,“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
文如其人,陶渊明在创作上也处处出之以“真”。“如逸鹤任风,闲欧忘海”一任情之所至,意到笔随,无不成其真切自然的妙文,仿佛晴空中的彩云,舒卷自如。诗人善于运用审美的眼光观察客观事物,特别是田园风光,发现它们都有一种创造生物的美。只要不息的生命之泉在于不断流淌,它就是天地间至美之景,无须修饰,陶诗之所以被朱熹称之为皆“出于自然”,并肯定“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其道理正在于此。他的喜怒、爱憎、理想、希望,都无所掩饰地写入他的作品。就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而言,陶渊明始终是一个封建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但在倾吐心曲、抒情写志上,却绝无一般士大夫的矫揉造作,反而象一个纯真的孩童,把自己一片赤子之心捧献给读者。这种真率自然的风格,正是他的诗文最能震人心弦的奥妙所在。元人陈绎曾称赞他的作品是“情真、景真、事真、意真”,不为虚美之辞。千百年来,陶渊明的诗文获得各种不同出身、不同地位、不同思想的众多读者的喜爱,关键也是这个“真”。这个真是他做人的准则,也是他做诗的准则。他的诗文达到了“真”的极高境界。
艺术的生命,既包含“真”,又包含“善”,缺一不可。陶渊明在追求“真”的同时,更不忘真与善的紧密联系:“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视真和善为一体,作为自身崇高的人生追求目标,既表现了自我精神的享受、思想领悟和道德升华,又使客观对象达到高级的审美层次。“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他对善的追求已不再局限于儒家传统观念,只求个人的自我完善,而且将文学创作的目的建立在分清善恶的基础上,因此他所理解的“立言”的不朽也就是美德和正义的永存。
魏晋时期,美学领域内重美轻善的思想倾向日益明显,这种强调艺术自身独立价值的审美思潮,既有突破儒家传统礼教束缚、促进“人”的觉醒和推动“文”的自觉的“思想解放”的进步意义;同时也为封建门阀士族的“及时行乐”打开了“绿灯”,为封建士大夫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风的抬头提供了条件。对此,陶渊明独异流俗,在处理美与善、美与真的问题上,坚持真、善、美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观点,正是他大大超过封建时代很多进步诗人之处。艺术与哲学,粗看似乎一在追求真美,一在追求至善,但就实质而言,二者密不可分。哲学是艺术家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而美学观则是哲学观在艺术创作上的具体运用,是艺术家美学观的物化,艺术之美必须以“善”为其核心和灵魂;而哲学之善亦离不开美,有必要以“美”为其表征和风韵。故艺术与哲学若能彼此交融相辅相成,确实可以净化生命,拓展心灵,提升人生层次。陶渊明笔下塑造的一系列光辉艺术形象,如“桃花源”的理想境界,就是融真、善、美于一炉的不朽典范,其所蕴藏的深厚内涵,永远折射出不灭的美学光芒。
陶渊明美学观的形成,有的论者归之于他的心理气质与凡人不同:“大文学家、真文学家和我们不同的就在这一点。他的神经极锐敏,别人的不感觉的苦痛,他会感觉;他的情绪极热烈,别人受苦痛搁得住,他却搁不住。渊明在官场里混那几年,象一位‘人生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强逼着去倚门卖笑。那种惭耻悲痛,真是深刻入骨。一直到摆脱过后,才算得着精神上解放。”(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对陶渊明内心世界的洞察可谓细腻,但只强调陶渊明性格上孤芳自赏、柔弱多惭的一面,对其耿介不阿、刚强不屈的一面则充耳不闻,未免失之片面。同时,离开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仅从天赋禀性方面探讨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更是以往学者研究历史的片面表现。
我们认为,陶渊明的美学观,与他的生活环境、家庭教养和前代美学思想的影响,都有密切的关系。陶渊明自幼在山水自然的怀抱中成长,“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对大自然具有铭心刻骨的浓厚感情,故乡的山山水水陶冶、培养了诗人的审美追求,他也最能赏识大自然的真美,最能表现大自然的真美;“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诗人通过对孤松的审美感受,更坚定了自己超凡脱俗的重自然、重“真意”的人生信念和审美观念。家庭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关于音乐美的见解,也对陶渊明的美学观有着直接影响。有一次桓温向孟嘉提出一个问题:“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认为弦乐不如管乐,管乐又比不上歌唱的道理就在于:弦乐用手,远于自然;管乐用口,较近自然;歌唱用喉,最近自然。音乐和文学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四言诗发展到五言诗,与音乐发展是分不开的。“四言诗大部分是鼓的音节,五言诗就渐渐由鼓发展到丝竹,由节奏渐渐发展到旋律。”(闻一多:《论诗与音乐》)陶渊明的一生,与音乐可算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学琴书”、“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中年更是“乐琴书以消忧”,晚年仍旧“载弹载咏”、“和以七弦”,对音乐的爱好从未衰退。陶渊明弹弄无弦琴的故事,更传为千古佳话。他曾经“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隐逸传》)可见陶渊明接受孟嘉以自然之义解释音乐,十分欣赏音乐的“自然”美。音乐的美学价值正在于它最能体现自然之性,琴弦只是表现自然之音的工具,与自然本身并无必然联系,所以在陶渊明的心目的中,无论是有弦的琴,还是无弦的琴,都能借以“寄意”,作为寄托和抒写情意的手段。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极大地强调主体的审美感受或审美态度的重要作用,表现他所追求的不是形式,而是体现自然本性的、想象中的境界,即那种自然的、艺术的、和谐的美的意境。陶渊明在诗文里多次提到“真想”、“真意”、“真风”,都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美的意境。“自然”、“真”、“淳”都是指事物的真性和本来面目,与它相对立的就是矫饰、巧伪。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的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也可以说是来源于孟嘉的美学观,并对后世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陶渊明的美学思想,与当时社会上老庄之学的流行亦颇有关系。老子主张万物“复归于朴”,追求真率自然;老子“大音希声”(于无声中方能品出无可穷尽的声音)更直接启迪了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借无弦琴“以寄其意”的审美情趣,在“无言”、“无声”中方能领略、品味无尽的情意和绝妙的神韵,获得最佳的、自由的审美解悟。言辞和有声反而固定和限制了人的无限的想象空间,障碍人与天地同和的真趣。陶渊明关于“真意”忘言、“无弦”寄意的见解,正是他委任自然的审美解悟所能充分表达的美学高度,而且是陶诗的艺术造诣后人难以企及的关键所在。庄子同样主张“无道无为而自然”。这一思想反映到文艺思想上来,就是主张自然美,反对雕琢文饰,“言隐于荣华”。如果语言被过分华美的辞藻蒙蔽了,华美的文饰妨害了语言的表达能力,那是庄子所不取的。所以在表现感情上特别强调“真”和自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渔父篇》)
从陶渊明一生来看,他是绝不做那种“强哭”、“强怒”、“强亲”的人的,自然更不会做这种“强哭”、“强怒”、“强亲”的诗或文。精诚与矫励、真与伪是对立的。艺术作品要取得“动人”的效果,必须出之以“真”。艺术作品的“美”与其所表现的事物的“真”是统一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下;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所描绘的这片自然景色,充满了“真意”,他整个心灵都陶醉到这一真实的自然图画里,形诸笔墨,给后人留下了传诵千古的艺术珍品。严羽评论诗歌创作时指出:“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后,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沧浪诗话》)自然真趣,确实是陶诗高于晋宋诗的重要原因。
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思想史上居何地位?在历史上将自然美作为独立的欣赏对象和艺术表现对象,从严格的意义上而言,应该认为是从晋宋之交的陶渊明开始的。陶渊明的艺术作品是中华古典自然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名言,初步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自然审美观的重要特色,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成为中华美学的古老传统,但先秦儒家尚未曾将自然美作为独立的欣赏对象和艺术表现对象。魏晋开始,人们美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陶渊明最早将自然界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将自然美作为自己个性的载体,使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达到了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的完美境界。在魏晋南北朝美学发展过程中,陶渊明是嵇康重自然的美学观到钟嵘追求“真美”和刘勰肯定“自然之趣”的美学思想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承上启下,理当给予充分肯定与适度评价。
至今所见各种文学理论批评史、美学史著作,自正绐至齐梁二百多年却是一片空白,仿佛重自然的美学思想发展线索中断似的。嵇康从“元气陶铄,众生禀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政治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人生上追求“顺天和以自然”、“任自然以托身”,在美学观上突出强调自然之义,这是他多次提及的:“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冲静得自然,荣华安足为”等,其归依自然之旨正是陶渊明“质性自然”、“复得返自然”思想之先驱;其所倡导的“至乐”乃“无声之乐”,没有钟鼓也可以有至乐,更为陶渊明抚无弦琴以寄意提供了理论依据,两者声息相通,何其相似乃尔;嵇康提倡“保性养真”、“真性无为”,痛斥“天性丧真,季世陵迟”,与陶渊明赞美“抱朴含真”,“真想初在襟”,“此中有真意”,痛斥“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前后一脉相承的轨迹亦十分明显。
钟嵘珍重“自然”的美学观在一定意义上说,则是对陶渊明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痛心疾首地感叹齐梁文坛上“自然英旨,罕值其人”,批评永明诗坛过分讲究宫商声病,以至“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也就是损害诗歌自然之美,提倡创作上“清浊通流,口吻调利”的自然的音律;钟嵘称许陶诗“文体省殆,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宛惬”,正有见于渊明创作实践符合他所提倡的“真美”、“自然”的创作理论,他赞扬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谢灵运诗“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之尘沙”、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似落似依草”等,皆属于上述考虑。刘勰同样强调“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刻,而曲写毫芥”,赞赏“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若探讨钟嵘、刘勰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的渊源,舍渊明而上溯,显然是跳过了一个重要环节,与历史本相相悖。
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在当时不为时人所称许,但对后代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反对绮靡的文风,推崇天真自然:“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认为“雕虫丧天真”是不可取的。他的文这思想和陶渊明重自然、重真率的思想是相通的。唐代以王维、韦应物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更深受陶渊明崇尚自然的美学观的熏陶,着力描绘大自然的真美,饱和着自然万物的情性,合乎“顺物自然”的艺术规律。陶渊明崇尚真美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创作,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也具有意义。我国当代文论研究功夫多倾注在刘勰、钟嵘等著名古代文论家身上,对其他一些不以文论名家的诗人、散文家的美学观、文学观,往往来不及兼顾或不屑于兼顾,陶渊明更是一个被众多的文论家和美学史家共同遗忘了的伟大诗人。这种倾向亟待扭转,以便更加充实、丰富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史,使之更为完备、多采。文学批评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既有奇峰突起,又有丘陵起伏,此乃客观历史的本来面目。
笔者新近读到吴云《陶学一百年》一文(刊《九江师专学报》1998年增刊),对1981年出版的拙著《陶渊明论集》的批评,借此略陈己见,以就正于陶学同仁。
首先,关于王国维、梁启超、 朱光潜等对陶学研究的杰出贡献,1991年出版的《陶学史话》已有详尽评述;即将杀青的《陶学发展史》还有进一步的充实,笔者并非“视而不见”。吴乐未曾读过《陶学史话》而轻下论断,似乎有欠慎重。
其次,在1998年的今天,若有论者大发“雅兴”,致力于在八十年代初的出版物中寻觅极左思潮影响的例证, 尽可不费吹灰之力。 吴氏1981年出版的《陶渊明论稿》中就不乏其例,诸如断言陶渊明“他的言行,包括诗篇,无不打上阶级的略印”(该书第14页,重点是笔者所加);吴书对千百年来众多的陶渊明研究者连“学者”之名也不愿恩赐,而蔑之为“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文人和近代资产阶级文人,认为这是陶诗中精华所在”、“这是出于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与情趣,把陶诗中某些消极的东西来欣赏与吸食。对此种观点与态度,我们应该采取批判态度。”(第110 页)联系吴文对《陶渊明论集》称梁启超为“资产阶级学者”而深表不满来看,不难发现其责人与律己运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把尺子和两种价值取向。吴书还称“《桃花源记》在当时虽然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今天,这种空想却只能是消极的了”(第145页)等等, 难道不都保留“文革”大批判的基调吗?笔者治学数十年,学术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发展,却从未曾产生过在他人旧作中挑三拣四的“雅兴”,故初读吴氏大作确有意料所不及。
再次,关于用《陶渊明论集》中的一句:“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前人尚无系统论述,是我们研究陶渊明思想的一个新的课题”,以此证明“钟书还轻易否定前贤和今人的已有的成就,往往把自己放到首创的位置上”云云,这同样是强词夺理的曲解。至今我仍坚持上述观点,即: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前贤关于陶公美学思想的探讨是不系统的,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对其美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是历史赋予八十年代以后崛起的新的一代陶学同仁的共同使命,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天才学者所能独力完成的新的课题。是耶?非耶?陶坛同仁可以心平气和地开展学术讨论,排除一切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让陶学研究健康地、持久地得以正常进行。
第四,吴文关于钟书“在哲学思想上对他影响最深的当首推司马迁”之说“未得到陶学界的认同”的判断,似有欠商量处。从吴文对魏正申《陶渊明评传》的评述看,他是细读过魏著的,而魏书明确指出钟氏“提出了对陶渊明‘影响最深的当首推司马迁’的著名论断,解决了一千多年来歧见叠出的一系列问题, 为陶学研究开启了新思路”(第121页)、“笔者在钟先生陶学理论的启迪下”(第124页)云云, 对此吴氏仍得出钟说“未得到陶学界的认同”的结论,照此逻辑推论,吴文显然将魏正申先生划在“陶学界”同仁之外去了,这种结论岂能令人信服?又如李华先生亦有“渊明以名‘名’的看法,还深受司马迁、曹丕的影响”(《九江师专学报》1998年增刊《陶渊明对“名”的看法》)的说法,不知吴氏又作何解释?
第五,关于对朱光潜“静穆”说的评价,吴文称“朱光潜四十年AI写作的《陶渊明》问世后,再批他的‘静穆’说就欠妥了。令人遗憾的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仍有极少数研陶者对朱先生的‘静穆’说,或批判或批评”,此论亦值得商榷。一则所谓“极少数”的估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实则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评陶者批朱氏“静穆”说者不是“极少数”,而是“大多数”;二则即使承认“极少数”的估计可以成立,那么这“极少数研陶者”中也包括吴氏本人在内,试看其《陶渊明论略》对“静穆”说的批评:“后世有的读者往往被后一面所迷惑,以为他只是个浑身静穆、悠然避世的田园诗人,与现实生活完全绝缘了。实际上,正如鲁迅说,陶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第27 页)这段文字清楚表明八十年代初吴著对“静穆”说的评估与1998年吴文对“静穆”说的评估的巨大反差;三则尚须补充说明的是,对朱光潜三、四十年代文艺思想的批判或批评,不但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存在,九十年代亦复继续进行,如《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邵伯周著,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书明确指出:“朱光潜的文章,在理论主张方面代表了自由主义的文学思潮”、“那就是要求文艺家不要介入现实的政治斗争,不要为政治家所规定的‘方向’所束缚,而应该抱‘中立’、‘超然’的态度,强调‘纯正文学’,强调文学要表现人性。这就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第669页), 并揭示这种文学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自由主义者,既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们受到美国政府所鼓励的所谓‘第三种力量’这一政策的影响,便以‘中立’的姿态出现,在政治上鼓吹‘中国路线’。与此同时,在文艺领域内也就出现了一股自由主义的文学思潮。”(第659 页)这种联系历史背景评析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思潮,是否存在“欠妥”或“完全失去了它的学术价值”(吴文语)?笔者认为不会。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一书才能获得“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员会”的评审通过,获得资助,使书稿及时出版问世。笔者囿于见闻,多年来从未曾发现有论者从该书中找到极“左”思潮的影响而表示“遗憾”的报导。
收稿日期:1998—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