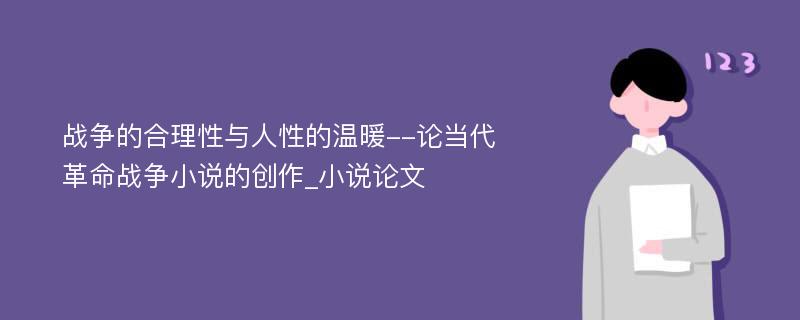
在战争理性与人性温情之间——当代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战争论文,温情论文,题材论文,当代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889(2000)02-0097-04
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指的是反映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新中国的风雨历程的作品。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在广大民众的支援下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战,这不仅是我们后人不能忘怀的过去,同时也为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作家们以属于自己时代的不同视角观察思考同样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作为当代文学小说创作的一种,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了变化和发展:从50年代激动人心的英雄主义,到90年代发人深省的心灵诉说,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人民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而精神追求日益淡化的状况下,不少作家渴望通过塑造艺术的形象唤起国人关于英雄的记忆,强调信仰和理念对于人生的重要影响,这使得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再度受到关注。我们回眸建国50周年来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便可以发现其中创作主体清晰的情感渐变——在战争理性与人性温情之间。
虽然战争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当代作家们一直没有停止用文学创作反映前辈们的征战历程。50年代的作家中,不少人从枪林弹雨中走来,他们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和平,追忆着战友们英勇献身的壮举,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拿起手中的笔,讴歌英雄、赞美英雄、升华英雄。作家们热情地书写,评论家们认可忽略英雄性格上的瑕疵,读者们更是怀着无比的崇敬之情把英雄看成是完美的化身:黄新的一篮咸菜和一块银圆无言地昭示着共产党员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王愿坚《党费》);交通员小陈一家前仆后继,用生命的代价不辱党交给的护送同志的使命(峻青《黎明的河边》);延安保卫战役中,我党高级军事指挥者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杜鹏程《保卫延安》);沈振新带领部队转战南北,以孟良崮战役的大捷体现人民军队的战无不胜(吴强《红日》)。综观50—70年代的战争题材小说创作,让英雄更加完美是作家和评论家共同遵循的法则,当然,英雄不见得就是伟人,他可以是指挥员、领导者,同样也可以是炊事员、村干部,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具有优秀的思想和优秀的品德,即使写到他们的缺点,也大多只是写行动卤莽,遇事不冷静或些许由于小农思想影响而残留的私心,并且这些“可爱的缺点”还会在革命大熔炉的锻炼中逐渐改过。由于时代的背景和作者、读者、评者三方面的合力,从60年代以后,战争题材小说中英雄人物高、大、全的弊端日渐显现,英雄被赋予了某种神性而高高置于普通人之上,人们礼赞英雄的善良愿望某种意义上却成为了阻碍战争题材小说创作走向健康发展之路的因素。
80年代之后,这种对战争和英雄的理解方式受到了质疑,作家们开始思考,战争岁月留给我们的,不应当只有胜利的辉煌,它同样也有失败的悲怆,革命的激情不可能冲淡战争的残酷,相反,写出战争本来的面貌不但不会使英雄黯然失色,而且还会让读者愈加感受到和平与安宁的弥足珍贵。比照起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我们发现过去战争题材小说缺乏的是对苦难的认识,作家们常常以革命的浪漫主义回避对战争苦难的描写,以英雄主义、大无畏的气概来淡化作为个体的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创伤。“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是干粮”,可在长征路上,游击战中,有多少战士因为弹尽粮绝而倒下;无产阶级的战士应当做到蔑视困难,战胜困难,可作为形态各异的人,谁又能说在生死的考验面前只会演绎同一种人生?而在过去,写革命屡遭挫折尚且有悲观主义的嫌疑,更何况写革命的失利?不是作家们缺少描写战争生活的才能,而是当时的文艺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手脚。新时期文学中,乔良的《灵旗》让我们第一次正视了红军在长征途中遭到的最为惨烈的杀戮,周立波的《湘江一夜》也同样扣人心弦,老作家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更是从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我军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幕: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当然是造成数千新四军将士遇难的主要原因,但也不能排除新四军内部领导层的不团结,以及领导者个人(如项英)性格上的缺陷和指挥上失误的因素。如果说从乔良和周立波起始,我们的战争题材小说开始放弃单纯的乐观主义,代之以客观、真实地描写战争的苦难和残酷,那么,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则可以看作是战争题材小说创作中重新反思对英雄形象塑造的一个标志。我们逐渐认识到,原来,英雄也不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对英雄的定位应该在“人”而不是在“神”,如果说有的人在特定的地点、时间和状态下成为了英雄,在他的身上,也同样不乏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不乏普通人的甚至是卑微的愿望。过去小说中那些政治素质优秀,作战经验丰富,个人品德高尚,无论身处逆境还是形势大好,都从不动摇革命意志,也从不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英雄们,虽然一时满足了人们在特定阶段对完美的追求,但由于缺乏现实的土壤,他们成了让人们无从师法,甚至敬而远之的神秘群体,人们看到的是他们闪光的一面,却无法了解他们的苦闷、彷徨、伤感和恐惧,今天的读者,谁还会为一个在潜意识中已经归入另类的人所感动?当英雄被提纯到了完美无暇的地步,或许也就成为了英雄主义在当代文坛迅速丧失领地的一个原由。
90年代,我们从战争题材的小说里品到了另一番滋味。90年代致力于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的湖北作家邓一光曾说:“父亲箱中有‘红星、独立自由、解放’等名称的勋章,我对那些沉甸甸的勋章很感兴趣,但后来我的兴趣变了,我很想知道父亲身上那些伤疤的来历。我想,那些伤疤,有时候比勋章更有意义。”[1]从军功章到伤疤, 从身上的伤疤到心灵的伤疤,这就是邓一光创作视角的转变,这个转变不是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他所在的一代人。邓一光是军人的后代,他将军人看作是“人类最优秀的群体之一”[1],从小就崇拜他们,仰慕他们。 在军营和干休所里长大,耳濡目染之下,邓一光对革命战争的历史和人民军队的历史比他的同龄人有着更多的了解,但与以往创作同类题材的作家不同,他既没有亲身体验后难以平静的激动,也没有历经磨难者冷峻的沉思,作为生长在和平时代的年轻人,他对父辈们的赫赫功业充满景仰,但更愿意探究的则是英雄和普通人之间的互动。于是,描写英雄的普通性和普通人的英雄壮举就成了邓一光战争题材小说创作追求的两个方面,而作为对既往英雄形象塑造的一种补充和纠正,他更倾向于表现后者,表现普通人对战争的贡献和他们为战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不应当把邓一光的创作看作是纯粹的写实笔法,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我”为四爷这活着的逝者洒下的那一掬苦涩的泪水(《远离稼穑》),无法体会“我”跪在大妈的坟前听到的,从黄土下传来的“恍如隔世的叹息”(《大妈》),事实上,正是这包含情感的书写体现了90年代作家在战争题材小说创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史积淀,在接受了新时期文学以来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洗礼之后,我们的作家懂得了文坛需要塑造真实的英雄,描写战争中真实的人生,特别是表现经历苦难的人们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和平年代的人们对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的理解和宽容。著名的革命者,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写道:“今天终将成为过去,人们将谈论伟大的时代和那些创造了历史的无名英雄们。我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他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所受的痛苦并不少于那些名垂千古的伟人。”[2]的确,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成为伟人的条件和机缘, 但“微不足道的人们”所承受的战争创伤并不也是微不足道,邓一光及90年代其他作家战争题材小说(如赵琪《苍茫组歌》等)的着眼点也就在这里:他们的作品带给读者的特别感受就是那一缕深厚的人性的温情,仿佛盐被溶化在水中,虽然没有在小说中尽情渲染,却让读者感到自始至终有一股淡淡的滋味涌往心头。
论及当代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不能忽略,那就是前苏联的战争文学。前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文学艺术上都曾经是我国学习和效仿的唯一榜样。前苏联在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击退了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平息了多次的国内叛乱,长达6 年的卫国战争更是让大多数年轻人走上了前线,许多作家亲身经历了战争,他们的创作对我国作家的影响长期而深远。早在20—30年代,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等作品就是左翼作家们经常诵读的名篇;50年代,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更是感染了几代新中国青年。建国之初,我国的文艺政策与前苏联的斯大林时期有许多相近之处,在战争题材小说方面同样强调英雄人物的塑造,炮火连天的战场,生死攸关的时刻,英雄应当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英勇善战、不畏艰险的具有强烈感召力的卡里斯马典型;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前苏联作家们深受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熏陶,强调对人与人道的关怀,而只把英雄主义看作是战争小说主题的一种,从进入战争小说创作开始,他们就有意识地用现实主义的,冷峻的写实风格来处理战争的残酷性和英雄人物的缺陷等问题,努力把握在各种复杂情况下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富尔曼诺夫在写作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前曾认真思考:“是如实描写恰巴耶夫,连他的一些细节,一些过失,以及整个人的五脏六腑都写出来呢,还是像通常写作那样,创造一个虚构的人物,也就是说,虽然形象还鲜明,但是把许多方面都割弃掉呢?我倾向于前者。”[3] 前苏联作家们在创作中正视英雄的不完美之处,拉近了英雄与普通人的距离,而这不但没有辱没主人公的形象,反而使读者,其中也包括广大的中国读者更加体味到艺术创造的魅力。而我国在向前苏联学习时,大都只片面地撷取了其中对英雄的颂歌,把英雄主义定义为战争题材小说唯一被认可的旋律,使得两国文学在同一题材创作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例如,早在20年代,前苏联作家拉浦列涅夫就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写了红军女战士玛琉特卡与她的俘虏,白军军官荒岛上的爱情(拉浦列涅夫《第四十一个》),这逾规的爱情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而在我国,描写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那朦胧而纯真的感情却受到了围剿(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绥拉菲摩维奇对充满苦难,损失惨重的行军浓抹重彩(绥拉菲摩维奇《铁流》),而刘真只借主人公之口说出“打仗二字是血写的”便受到批判(刘真《英雄的乐章》)。另外,前苏联战争小说作品中有英雄的传奇,但更多的是对在战争中默默牺牲、奉献的无名战士的关注。“在战争中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取得插旗子的光荣的,大多数人都是默默无闻地作战。虽然他们都有姓名,也不比别人差,也不比别人缺乏勇敢。”[4] 作家们为这些被历史的尘烟所淹没的“永远19岁”的战场未归人真诚凭吊,从一个开满鲜花的弹坑,一具寂寞荒野的白骨开始,追溯他们曾经是活生生的存在,曾经是年轻热情的生命。
我国当代前期的战争题材小说注重表现英雄藐视困难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有意回避或冲淡英雄对战争苦难和残酷性的客观认知,而在前苏联文学中,战争苦难与英雄主义恰恰是紧密相连的,换言之,他们把苦难当作了考验英雄品质的最佳标尺。前苏联评论家鲍恰耶夫指出:“一个人,当他在恶和战争面前,在不可避免的厄运面前,在悲剧结局面前,有力量战胜自己的弱点,获得勇气,克服恐惧,他就成为真正的人。”[5]应当看到, 战争中有许多人经受住了血与火的洗礼而成为了“真正的人”,但确实也存在有不能战胜人性弱点的群体,毕竟作为人,谁都有求生的本能,都有对死亡的恐惧,谁能对战争的残酷性无动于衷?60—70年代前苏联的“战壕真实派”作家及其以后的作家正是以他们充满对战争中人性的思考的创作在文坛引起了广泛反响,邦达列夫的《热的雪》、贝科夫的《方尖碑》等一大批作品相继获奖,这标志着前苏联的战争题材小说创作在反映战争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前进了一大步。而在我国,“战壕真实派”的创作被认为是宣扬“叛徒哲学”的修正主义作品而遭到全盘否定,这种粗暴的批判使得我们当代的战争题材小说创作失去了有益的参照,在前苏联战争文学向“全景式”、“局部式”掘进时,我们的同一题材创作却因为观念上的偏执而走进了死胡同。80年代以来,我国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伴随着文艺界“人性与人道”问题的讨论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作家们消退了英雄人物头上闪烁的光环,赋予他们普通人的休戚与悲欢;90年代,作家们又为这一题材的创作进行了重新定位:在呼唤英雄的时代里塑造英雄,在缺乏崇高的境遇里再现崇高——只不过,英雄和崇高都已经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内涵。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前苏联,革命战争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其现实的影响力,然而,任何历史都具有当代性,对历史的描述也折射着当代人对战争关注的兴奋点,从对英雄的崇拜到客观评估英雄,从颂扬英雄主义到对苦难的认识和表现,从写人物的英雄行为到展示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标志着当代人对战争的重新理解和估价。对历史的阐释是没有穷尽的,80年代,从未经历战争的前苏联女作家斯卡特兰娜还以《战争中没有女性》轰动文坛,拓展了女性的战争创伤这一严肃的主题;我国当代的报告文学创作作品《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志愿军战俘纪事》等为读者展现了革命战争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一幕,所以说,如何重拾被蔽弃、遮掩了的历史真实,在宏大的叙事背后正视普通人的生命轨迹,探讨战争与人的关系,在这一领域仍留有作家们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
回顾5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我们相信,战争作为非常时期,它会让原本复杂的人性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多样化,而文学也只有反映出了战时人生的丰富才能真正打动读者的心灵。因为对于历史,攻城拔寨抑或全军覆没都只是一个结果,可对于战争中的任何一个个体,被尘封或湮没的就是他的全部人生。其实,倘若他能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他所具有的情感和举止与今天的读者并没有什么两样,是战争改变了他,毁灭了他,或者锻造了他。考察我国当代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作家们的创作态度从战争理性到人性温情的变化不是一个随时间改变的流程,而是与当代文坛对人和人性关怀同步的跨越。我们曾经有相当一段时日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发现英雄,不是不需要英雄,而是需要真实的英雄。也许今天,我们在用理性和温情与小说中那些有名或无名的英雄进行心灵对话之后,就会深深感叹,这里还有一方文学的富矿。
收稿日期:1999-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