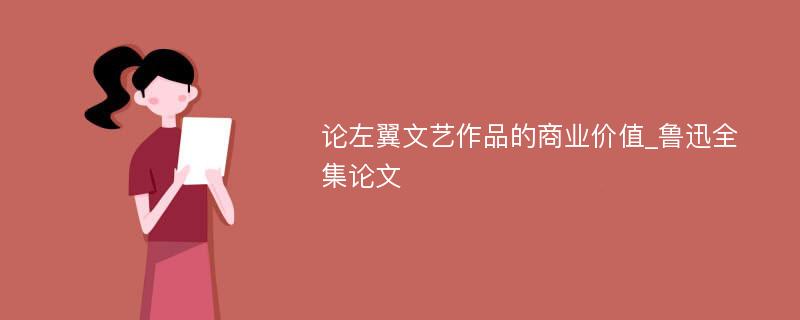
论左翼文艺作品的商业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商业价值论文,文艺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2-0107-06
本文所探讨的左翼文艺作品的商业价值,主要指的是“左联”作家在进行左翼意识形态宣传时,作品因为被读者所喜爱,而在有意无意之间获得的一种“商业价值”。正因为此,左翼文艺作品才被资本家冒着政治的危险出版、发行。资本家的目的是借左翼文艺作品来创高额利润;而左翼文坛则是希望通过公开出版的读物和公开放映的电影传播左翼话语,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商业资本的介入,使得“左联”文学在检查制度盛行的时代得以传播,保证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连续与有效,而书商和影片公司经理则相应地得到了投资所带来的丰厚利润。这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 (一)这些作品必须是左翼的、同时又有商业价值;(二)投资人进行了投资,把可能的商业利润变成了现实的商业利润;(三)投资人总会通过各种手段让这些作品得以传播,以便赚取高额的利润。
一、左翼文艺作品的商业价值
对于20世纪30年代读者的阅读兴趣,当时便有人作了调查。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些调查结果时,可以对30年代左翼文学受欢迎的程度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30年代,一位叫大卫·威拉德·莱昂的外国人曾对中国人的读书情况作了一个调查,发现“许多人都要读新一代俄罗斯作家作品,尽管这种作品大多数被查禁,只能在朋友之间偷偷传阅一些残旧的本子。奥格涅夫的《一本共产党学生的日记》、柯龙太夫人的《赤恋》、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以及伊凡诺夫和皮涅克的作品流行得最为广泛。1928-1929年间,在左翼文艺运动正式开始的时候,大约有一百种俄罗斯作品被译成中文。普列汉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文艺批评家”,“在十一种借阅最多的一般书籍中,有六部是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其中包括布哈林、恩格斯、马克思、及研究俄国五年计划的著作,其他五种为:C.安德鲁《甘地传》,M.比尔《古代社会斗争》,《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十九人委员会关于中日纠纷调查报告》及《田中奏折》”①。新文艺读物和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向导》、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共产主义ABC以及其他关于社会运动和国际运动的书籍一起畅销②。“关于翻译专号,我们当时随刊物向读者发了一个征求意见的表格,提出了九个问题。后来我们收到了六百二十份答复,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般倾向。例如多数读者认为现在质量高的创作太少;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相比,多数喜欢读外国文学;翻译的文艺书中以喜读俄国文学的为多;多半不能直接读外文文学书;半数以上的读者读译本的兴味高于读创作;对于翻译专号中的译文,最喜欢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三四一人),最不喜欢《法国象征派诗选》(二五人)。”③
在创作领域,一些出自革命作家手笔的作品,如蒋光慈继《少年漂泊者》之后的《鸭绿江上》、《短裤党》和《冲出云围的月亮》在青年学生中简直风靡一时④。 1928-1930年间,蒋光慈的作品一版再版,一年之内就重印了好几次。他的书被改头换面不断盗版,别人的作品也会因印上蒋光慈的大名而畅销。比如,邹枋的短篇小说集《一对爱人儿》出版不到一年,就被换上蒋光慈的名字出版;甚至茅盾出版于1929年7月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的作品,1930年1月也被包装成蒋光慈的创作,以《一个女性》为名出版。蒋光慈的作品确实写出了当时青年人的苦闷,陈荒煤曾这样谈到他青年时代读蒋光慈作品时的感受:“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使我感动得落下泪来”⑤。蒋光慈作品的热销似乎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郁达夫在《光慈的晚年》中说:“在1928、1929年以后,普罗文坛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慈的读者崇拜者,也在两年里突然增加起来了”,“同时他那部《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出版的当年,就重版到了6次”,“蒋光慈的小说,接连又出了五六种之多,销路的迅速,依旧和1929年末期一样”⑥。与蒋光慈在一段时间内热得发紫不同,鲁迅作品的销量一直很可观,这些情况我们可以从鲁迅的书信中得知一二:《准风月谈》最初是“几个小伙计私印的”,但很快“一千本已将售完”⑦;“新出的一本,在书店的已售完,来问者尚多,未知再版何时可出”;⑧《二心集》“出版后,得到读者欢迎,旋即告罄。同年11月再版,又销售一空,历年一月又出第3版,8月又出第4版”⑨。鲁迅作品被广大读者的喜爱,使得许多不法商贩常常通过翻印来谋取利润,对于这种情况,鲁迅不但不以为意,而且还持欢迎的态度。“《准风月谈》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错字少,于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调集》也有翻版。”⑩“《南北集》翻本,静兄已寄我一本,是照相石印的,所以略无错字,纸虽坏,定价却廉,当此买书不易之时,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功德,而且足见有些文字,是不能用强力遏制。”(11)销量一直居高不下的还有茅盾的作品,“《子夜》出版后3个月内,重版4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为五千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在《子夜》遭删后,更有进步华侨以“救国出版社”名义,“特搜求未遭删削的《子夜》原本,从新翻印”(12)。在有些读者眼中,《山雨》、《子夜》“这两部作品都是足以显示30年代初期革命文艺的创作成果的”,它们因“反映当时农村和城市的斗争生活”而“成为我们一些青年读者议论的中心”。(13)
左翼文艺有如此巨大的商业潜力,使得以出售左翼文艺作品为主的小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街头出现。—位作者在谈到这些小书店兴盛的原因时说:“‘后期文化运动’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发展就在最近的将来,我很希望这几家新生的书店能够在人才经济方面确定它们的基础。”(14)在《国民党〈文艺宣传会议录〉》中提到,“共产党所利用的书店,计有湖风、现代、光华三家”;“至于国家主义派所利用之出版机构,唯一中华书局耳”;“开明书局除出版教科书外”,“出版茅盾(沈雁冰)之著作也,计有《蚀》(包括《动摇》、《幻灭》、《追求》三种)、《虹》、《三人行》、《子夜》等,销路甚佳”;“北新书局靠鲁迅发财由五百元之小资本,发展成五万元之大商店”;现代书局“其书籍一般在水平线下,唯郭沫若偶像已成,其书籍销路殊佳,而现代亦赖以维持”。(15)一部作品,只有具有了广大的“读者群”,才能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只要具备了商业价值,出版商就会冒着政治风险而进行投资。在30年代,出版者经常面对的商业风险往往来自于政治的压力。为了赢取丰厚的利润,出版者往往会和“左翼”作家结成同盟,共同“欺骗”文艺检查机关的“把关人”。
二、投资人:利润追求与社会正义之间
在30年代,不仅左翼刊物刊登左翼作家的作品,就是后来那些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刊物,也经常刊发“左联”作家的作品,这一方面反映出“自由主义者”在文艺上的“宽容”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左翼作家的作品对读者的强大吸引力。施蛰存就曾经谈到过发表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时的情形:
当时拿到这篇文章后,要不要用?能不能用?有些踌躇,自己委决不下,给书局老板张静庐看了,他也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主要是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但还是担心文章发表后,国民党当局会来找麻烦,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他们倒没有来找麻烦。(16)
再以《申报·自由谈》为例,在改版之后,最初是向张资平约稿的,但在连载《时代与爱的歧路》的过程中,读者来信“表示倦意”,使得编者最后下定了决心不再登载,这就是后来弄得沸沸扬扬的“腰斩张资平”事件。这说明,在30年代,风花雪月的东西已经不再受到大部分读者的欢迎。改版后的《自由谈》在许多人看来,是以鲁迅和茅盾为“两大台柱”的,销量甚佳,以致有人撰文在《社会新闻》上予以攻击,“自从鲁迅与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17)。与之相仿的是《大公报》和《现代》。《大公报》为了扩大销路,开始用一些观点与官方对立的文章,虽然因此而受到官方的警告,但也带来了销售量的增加。(18)施蛰存、杜衡、戴望舒等人创刊的《现代》,则被国民党检查机关敏感地嗅出其背景乃是“半普罗”的。(19)在30年代,出版“左联”作家的书籍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但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却实在是有利可图的事情。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在编“一角丛书”时,约了“大批‘左联’、‘社联’、‘剧联’的作家,陆续给丛书写稿。1932年下半年续出30种,总数销到50万册;1933年又续出30种”(20);“因为这次的成功,于是很快便策划出版了《中篇创作新集》丛书,作者为清一色的左联青年作家”(21)。“许多书店为了在表面上显示自己前进起见,大概都愿意印几本这一类书;这种风气,竟也打动了一向专出碑版书话的神州国光社,肯出一种收罗新俄文艺作品的丛书了。”(22)
30年代杂志和“五四”时期的杂志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五四”时期的杂志多是同人性质,而30年代杂志则倾向于商业性。施蛰存说:“‘五四’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为了扩大销路,众多刊物在编辑上极尽翻新出奇之能事,但是由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文学的商业性在当时更容易与政治和意识形态达成同盟,而不像太平盛世那样易于与娱乐、消遣结缘。这样,恰逢其时的左翼文艺作品广泛地赢得读者并在一个时期里成为畅销文化的同义语,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一些在政治倾向上靠近国民党的书店这时也开始出版有关革命文学的书籍。根据徐懋庸的回忆,当时上海的出版机构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是真正同情共产党而出版进步书刊的,如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等。第二,是商人为了投机牟利而出版进步书刊的,如光华书店、光明书店之类。第三,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伪装进步、先把读者争取过去然后施以反动影响的,这是走曲线的道路。新生命书局即属此类。与此同时,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一些刊物越是被封禁,其影响反而越大,也愈受群众的支持。那些投机商人办的书店,则采取‘游击’式的办法,即在一个时期,约一些‘左倾’的作家,编一个进步刊物,销行一下,大捞一笔,出几期就停刊。”(23)
在电影界,有关左翼意识形态的电影也受到观众的欢迎。在30年代以前,电影院上映的一些影片,如《火烧红莲寺》、《呆婿祝寿》、《得头彩》、《猛回头》、《拾遗记》等,宣扬的更多的是—种封建传统观念。但在进入30年代以后,电影公司必须去面对的现实是,当年忠孝节义、才子佳人、因果报应的那一套开始越来越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了;而且,这种影片也被国民党当局视为有伤风化,也在被审查的范围内。既然同样要被审查,甚至被禁演,为什么不拍摄更有社会正义感更有商业价值的影片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左翼电影因为反映了底层民众的心声,成为—种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的象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公司开始与左翼文坛进行试探性的接触。
电影界的试探性接触得到了左联的回应。在当时,“左联”正在走“大众化路线”,而电影是最为“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在一次由瞿秋白主持的会议上,“左联”“对电影界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会议决定由阿英、郑伯奇和夏衍三人一起参加明星公司,担任编辑顾问”(24);“秋白同志要我们记住当时所处的环境,假如我们的剧本不卖钱,或在审查时通不过,那么资本家就不会采用我们的剧本,所以要学会和资本家合作,这在白色恐怖严重和我们的创作主动权很少的情况下,便不能不这样做的”(25)。从这段回忆我们可以看出,“左联”这一决定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传播意识。在“左联”看来,这是其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必要的手段和策略,这次成功的合作因此而被当事人所津津乐道,“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十分得体、恰当,稍过一点,就会适得其反”(26)。这是—种双向的利用,双方对于这种利用也心知肚明,始自1932年的这场影片合作就是如此地带有商业的味道:“我们一方面替资本家赚钱,一方面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剧本和帮助导演修改剧本在资本家拍摄的影片中加进一点进步和爱国的内容。”(27)
这种合作马上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成为左翼电影的先声,正如当时的读者所指出:“《狂流》的题材和以前轰动一时的《人道》颇相类似,而作者的态度则和《人道》恰恰相反。《人道》是一部旧伦理的说教;《狂流》却是新时代动向的写照。《人道》替权力辩护,硬说荒旱是天灾;《狂流》却站在勤劳大众的立场,指明水灾是人祸。《人道》拥护封建社会,捏造出‘琴瑟式’的节妇来骗大众的眼泪;《狂流》却暴露封建余孽的罪恶,描画农民斗争的苦况,指出大众应该争取的出路。”(28)接着《铁板红泪路》、《盐潮》、《母性之光》、《香草美人》、《上海二十四小时》等左翼影片相继问世。1933年,影坛老将郑正秋也开始改变作风,他“向左转”的新片《姊妹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影片前后在内陆18个省、53个城市和香港、南洋群岛10个城市上演,票房价值达20万元,创下了当时的最高记录。“这部片子神话一般,扭转了明星公司危在旦夕的命运。”(29)正因如此,明星电影公司在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强大压力时,表面上解除了夏衍、阿英、郑伯奇三人的编辑顾问职务,但私下里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随后拍摄的《时代儿女》、《压岁钱》又为明星电影公司创造了高额的票房价值,这使得电影公司对左翼作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商业依赖。风潮所及,其他影片公司,如联华、新华等亦吸纳了不少左翼影人,大量投拍左翼影片。对投资者来说,与左翼作家合作、以各种手段躲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制度,目的无非是赚取高额利润,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但正是在这种不自觉中,中国电影完成了与“革命文学”的融合。“以这样的方式不仅解决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同时也以大众艺术的载体和操作方式充分地表达了现代艺术文化精神”;“既有利于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品位的提高,又有利于精英艺术走出万分困窘的境地,也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表达”(30)。可以这样说,左翼文学的兴起固然有重要的政治原因,而发达的商业社会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兴盛同样都是不可忽略的历史背景。这种历史背景孕育出了新型的文化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大众既是左翼文艺家“动员”的对象,也是商业投资者眼中的潜在“消费者”。
三、投资者和“把关人”(31)的博弈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对于左翼文艺家来说,主要的“把关人”来自于这样三个方面:编辑、投资方、政府审查机构。投资者为左翼文艺作品通过“把关人”的审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1929年1月10日《宣传品审查条例》中,国民党把下列作品列为反动宣传品:“一、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二、宣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主义而攻击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三、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四、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五、妄造谣言,以淆乱观听者。”(32)并且相继颁布了《出版条例原则》、《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等。在出版物的审查上,国民党也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用力不可谓不勤,下面是1933年11月-1934年1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关于改组电影检查委员会以加强影片检查的文电》(33),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审查制度的进展状况。
片名 出口公司 修剪部分
备注
《压迫》 明星公司 大资本家作交易所压迫小85公尺
资本家一段,寅生被资本
家迫赴茶楼卖妻一段
《姊姊的悲剧》明星公司 (一)地主扣押佃户117公尺
(二)豪绅靶打黄包车夫
(三)幼麟被刺
《挣扎》 天一公司 (一)劣绅压迫一段剪去18公尺
改摄
(二)劣绅杀人,法院审判
情形一段剪去后改摄
《铁板红泪录》明星公司 (一)团丁枪击团总一段6公尺
(二)加一字幕“国民革命
军到来一切痛苦均告改
除。”
《三岔路口》 天北公司
“这些高房子都是我们穷人的血汗和
生命,也是吃人的老虎”一字幕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审查过程中删去的主要是能显示出阶级差别的东西,这往往也是影片和作品中最为当时的读者所喜欢的部分,即所谓的“卖点”。正是因为宣传左翼意识形态,即所谓阶级话语,同时也是资本家能够借此盈利的“卖点”,作家、编辑和资本投资者在无形中结成了“同盟”,来对付掌握最终决定权的“把关人”——政府审查官。在许多“左联”作家的回忆录当中,都无形中夸大了自己在与政府审查官员进行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资本投资者在这当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这里仅举一例:
1934年2月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令,“查上海各书局出版共产党及作家之文艺作品,为数仍多。兹今调查,其内容鼓吹阶级斗争者,计一百四十九种。为此特印送该项反动刊物目录一份,即希严行查禁,并勒令缴毁各刊物底板,以绝依据”(34)。当时这种查禁对“左联”作家的影响很大,“因为当时我们这些人都以‘卖文为生’,所以乱禁一通,总还是可以使左翼文人在生活上受到折磨的”(35);“对于那些没有版税收入的年轻的新进作家,辛辛苦苦写出一篇东西,却被检查老爷任意抽调了,却意味着要勒紧几天裤带!”(36)因为禁书多,牵涉的书店也多,各书店就联名请愿“体恤商艰”。这次请愿,由开明书店领衔。因为其他大书店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被查禁的书才三两本,对请愿并不热心;而禁书最多的现代、光华、湖风等书店,又是众所周知的左倾小书店,说出话去没有分量。开明书店则不同,这里引用一段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内部工作报告中对它的“评价”便知端底:“开明书店从小说起家,今则贯注全神于教科书——尤其是中等学校用之教科书,其编辑人员,如夏丏尊、叶绍钧、丰子恺等。其学识经验较之世界、大东之三十元四十元一月请来之编辑,实不可同日语,故其出品,亦较优胜而销路亦殊不恶,在新书业中,俨然成为后起之秀,今在四马路租有月费一千两之巨厦,居然硬与商务、中华,争一日之长矣。该局由出版教科书外,其可述者,即为出版茅盾(沈雁冰)之著作也,计有《蚀》(包括《动摇》、《幼灭》、《追求》三种)、《虹》、《三人行》、《子夜》等,销路甚佳。”更为重要的是,开明书店的董事长是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据说,正是看在邵力子的面子上,政府放宽了“禁书”尺度,对一部分书籍允许删改后重新出版。
一般来说,这些投资者都具有良好的社会背景,比较接近或者直接来自于社会上层。这种背景,使他们在和政府打交道时常常游刃有余。很多情况下,政府往往对他们“法外开恩”,让他们得到切实的好处。比方说,明星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就与国民党的关系很密切,1933年4月,他曾奉命率领摄影队去江西摄制反共的纪录片;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是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与以后的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方觉慧有同乡、老友之谊,袁殊用这层关系办起了《文艺新闻》,并且因为这一层关系,在“左联五烈士”的消息被封锁时,《文艺新闻》却敢刊登《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这是新闻界、文艺界最早披露“左联五烈士”的消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可以这样说,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杂志要躲过图书审查,很可能属于以下三种情况:(一)刊物与“赤化”无关;(二)投资者有权力背景支持,比如说开明书局;(三)有强大的财力作为后盾,如明星公司。在30年代的中国,“钱”与“权”足以让“把门人”打开理应紧闭着的门。这里举一个并非文艺作品的例子:1931年4月和6月,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被捕,中共中央因此被迫转移到了江西的中央苏区。当时,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或被杀,也有为数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向国民党的警察机关自首。尽管如此,花钱摆脱困境也并非不可能。例如,柳宁只花60元钱,就让人销毁了自己的档案,并从监狱里放了出来。(37)“钱”与“权”充分结合所产生的效力在袁殊身上得到了更好的体现。1935年5月发生的“怪西人”事件,使得袁殊同时被捕,但是在日本的压力和袁殊的父亲以“老同志”的资格写信请陈立夫关照的影响之下,一年之后袁殊便被释放。在“权”与“钱”的共同作用下,一个“政治犯”可以逃脱“惩罚”,一份刊物同样也不例外。判定一份刊物是否违禁是很复杂的,一旦拥有“钱”与“权”的结合便会放宽很多。
以鲁迅和茅盾所办的文学期刊作一比较。鲁迅所办的系列文学期刊一般为同人刊物,其初衷之一就是摆脱商人的影响。在徐懋庸要替光华书局编辑《自由谈半月刊》时,鲁迅曾这样写信进行语重心长的劝告:“光华忽用算盘,忽用苦求,也就是忽讲买卖,忽讲友情,只要有利于己的,什么方法都肯用,这正是流氓行为的模范标本。我倒并不‘动火’,但劝你也不要‘苦闷’了,打算一下,如果以发表为重,就明知吃亏,还是给它;否则,斩钉截铁的走开,无论如何苦求,都不理。单是苦闷,是自己更加吃亏的。”《译文》停刊表面上是鲁迅和生活书店未能就主编问题达成一致,其深层的问题在于生活书店要求更换编辑,提高发行量,但鲁迅对他们只顾商业利益的做法显然十分不满,于是发生了拂袖而去的一幕。相比之下,茅盾的系列文学期刊则存活的时间明显比较长,这主要与茅盾主编的文学期刊一般都依托某一强大的出版书局有关。《小说月报》的后台出版商是商务印书馆,《文学》创刊所依托的生活书店就“不同于那些随时面临着被国民党查封危险的‘红色’小书店,而有个可靠的背景——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事实证明,投资方是否有雄厚的资金、广泛而可靠的人际关系,是否有才干和魄力,对于期刊的存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此依托,编辑者可以不必为资金预支、联络作家、广告开支,尤其是应对发行审查而大伤脑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编辑也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制约,而不得不对自己的编辑理念作出调整。
结语
20世纪30年代,租界的存在,军阀割据局面的刚刚结束,国民党政权的极权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实行统治的呼声日趋高涨,并出台了许多的统治政策。为什么这些政策难以落到实处呢?原因在于,在社会灾难深重、贫富差距悬殊的年代,“发挥穷的现象”往往体现着一种“正义”,左翼意识形态的“阶级”话语变成流行话语是在所难免的;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阶级”话语的压制,则完全把自己放到了历史的反面。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忽略了这种被压抑的声音所具有的巨大的商业价值,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资金投入。商业社会的特点在于,对于具有商业卖点的产品,会聚集社会大量的物力财力,而自发地形成社会化的规模大生产。在30年代,虽然由于政府的阻挠,社会化的规模生产没有形成,但资本投入者却对左翼文化的保护和推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也可以说得上是政治和市场的一种奇妙的结合:一方面是市场和反对党的意识形态形成同构关系,一方面则是市场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解构。市场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解构,不像政治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解构那样,政治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解构是从外部开始的;而市场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解构则从内部和外部同时开始,这也是由资本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当时的资本家内心也许并不希望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也并不存心去宣传左翼意识形态,但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这一切变得那样自然而然。
注释:
①尼姆·威尔斯:《活的中国·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运动》,载《新文学史料》,1978(1)。
②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113-114页,上海,上海书店,1984。
③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中),第2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④王西彦:《船儿摇出大江》,载《新文学史料》,1984(2)。
⑤荒煤:《伟大的历程和片断的回忆》,载《人民文学》,1980(3)。
⑥郁达夫:《光慈的晚年》,载《现代》,1933(1)。
⑦⑩鲁迅:《350126致曹靖华》,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32、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⑧鲁迅:《350312致费慎祥》,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77页。
⑨周国伟:《略论鲁迅与书局(店)》,载《出版史料》,1987(7)。
(11)鲁迅:《340619致曹靖华》,见《鲁迅全集》,第12卷,第460-461页。
(1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234-2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3)王西彦:《回忆王统照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79(3)。
(14)汪荫桐:《小书店的发展与后期文化运动》,载《长夜》,1928(3)。
(15)转引自唐纪如:《国民党1934年〈文艺宣传会议录〉评述》,载《南京师大学报》,1986(3)。
(16)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第3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17)农:《鲁迅与沈雁冰的雄图》,载《社会新闻》,1933-03-03。
(18)萧乾:《鱼饵·论谈·阵地——记〈大众报·文艺〉1935-1939》,载《新文学史料》,1979(2)。
(19)《上海市党部宣传工作报告》,见《左翼文艺运动史料》,第319页,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
(20)赵家璧:《我编的一部成套书》,见《编辑忆旧》,第27-2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4。
(21)赵家璧:《三十年代革命新苗——专为左联青年作家编印的〈中篇创作新集〉》,见《编辑忆旧》,第245-250页。
(22)鲁迅:《〈铁流〉编校后记》,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365页。
(23)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第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4)夏衍:《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电影集·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25)夏衍:《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一些回忆》,载《电影文化》,1980(1-2)。
(26)夏衍:《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一些回忆》,载《电影文化》,1980(1-2)。
(27)夏衍:《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电影集·序》。
(28)席耐芳:《〈狂流〉的评价》,载《上海晨报·每日电影》,1933-03-07。
(29)何秀君:《张石川和明星电影公司》(肖风整理),载《文化史料丛刊》, 1980(1)。
(30)盘剑:《革命文艺与商业文化的双向选择——论夏衍三十年代的电影文学创作》,载《文学评论》,2001(3)。
(31)笔者在这里提出的“把关人”是一个传播学的范畴。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心理学家库尔特·列文。列文在 1947年发表的《人际关系》一文中首创了“把关”(gatekeeping)一词。这是他从英文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化用而来的。所以,有的论著中也称“把门人”为“守门人”,任何传播活动都会受到一些个人或集团的控制。后来传播学家们将这一论点发展成为传播学中的“把关人”论。施拉姆对此作了这样的阐述:“在信息网络中到处都设有把关人。其中包括记者,他们确定一场法庭审判,一件事故或者一次政治示威中,究竟有哪些事实应该报道;包括编辑,他们确定通讯社发布的新闻中有哪些类型的人物和事件值得书写,什么样的人生观值得反映;包括出版公司编辑,他们确定哪些作家的作品应该出版,他们的原稿中哪些部分应该删除;包括电视、电影制片人,他们确定摄影机应该指向哪里;包括影片剪辑,他们在剪辑室内确定影片中应剪掉和保留哪些内容;包括图书管理员,他们确定应该买些什么书籍;包括教员,他们确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教科书和教科片;包括负责汇报的官员,他们确定把哪些情况向上级汇报;甚至可以包括餐桌旁的丈夫,他们确定当天在办公室发生的事件中,有哪些应该告诉妻子。”在实际传播过程中,“把关人”往往是多层次、多环节和多因素的。在书刊编辑中,一般起码要有直接编辑(或称责任编辑)、主编人(或总编辑)、一级主管部门等几层把关。
(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7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351页。
(34)《三十年代反动派压迫新文学的史料辑录》续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1)
(35)夏衍:《懒寻旧梦录》,第1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235页。
(37)柳宁:《一个工人的供诉》,第66页,转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4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标签: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艺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新文学史料论文; 读书论文; 商业论文; 鲁迅论文; 子夜论文; 狂流论文; 现代论文; 茅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