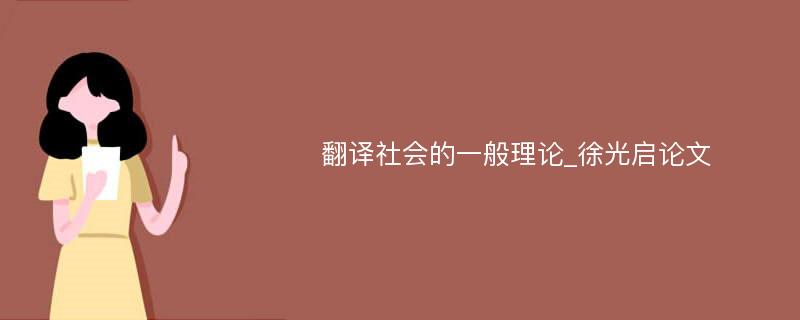
翻译会通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一谈到中国传统译论,译界就自然而然地想到“案本——求信——神似——化境”[1:19]这一体系,它代表了我国佛经翻译、西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的理论主张,是一条以“信”为核心的规定性翻译标准体系,要求译者一切以原文为中心。但这一体系遮蔽了明末徐光启开创的翻译会通思想及其大量实践。翻译会通论突破了原文中心论的藩篱,目的不是对原作表面的“信”,而是更强调把西学融入中学以求“超胜”。这一思想既承继了传统学术讲求会通的渊源,如经学、史学、子学、儒释道等的会通,又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翻译史上不乏历史回音,如清初梅文鼎的中西天文历算会通之学、洋务派张之洞的会通论、维新派严复“统新旧”“苞中外”文化观下的翻译会通、新文化运动中贺麟译介西方哲学的“和谐化合”说、钱钟书的学术“打通”论等,这些不同的会通思想与当时的西学认知、理解方式、翻译策略等密切相关,值得深入系统地研究。本文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的会通性,重点阐述“会通”和“翻译会通”的内涵,以深化中国传统译论研究。
二、从传统学术会通到翻译会通
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特点是综合性[2:41],重“学科会通”[3:144],贯穿于整个传统学术史,也是翻译会通的学术渊源和基础。
中国传统学术思潮可分为六个时期,即先秦学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之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4:总序]。先秦是中国学术的原创期,秦汉则是奠基期。秦一统六国,学术也随之一变,表现出浓厚的兼收并蓄的综合性特征。如《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4:10];《史记》“网罗天下放失遗闻,王迹所兴,见盛观衰”[4:334],以通古今之变;《春秋繁露》以“王道通三”:“上通天,下彻地,中理人”[4:8]。两汉之际,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鸿篇巨制《七略》,是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学术典籍的大汇集,共收书6大类38种,596家,13269卷,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白虎通义》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堪称儒家经学通经致用的典范。到了东汉,经学重通学,即《五经》之间的打通和今、古之间的兼容,如贾逵的《左氏传解诂》和《国语解诂》、许慎的《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马融的通学式解经方法和郑玄的通学等。
魏晋南北朝是传统学术更为突出的会通时期。儒释道“三教虽殊,劝善义一”[5:63],学者多寻求“通方之训”,以“殊途同会”[5:74]。经学方面,何晏等编撰的《论语集解》是迄今保存下来的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论语》注疏。隋唐儒释道三教继续兼容并蓄,在冲突对抗中会通融合。如天台宗慧思禅师致力于会通南北佛教,刘焯、刘炫学贯南北,开会通之风。经学方面,唐代孔颖达等人编纂的180卷《五经正义》,“融贯诸家,择善而从”[6:184]。隋唐三教会通融合的一大成就就是宋明理学的产生,达到了我国传统学术的顶峰。其中,程颐主张通经明理,“学贵于通”[7:232],郑樵倡导“总天下之大学术”[7:766]。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会通汉宋训诂与义理融合的代表作,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林的《文献通考》等体现了史学的“会通因仍之道”[7:768]。而陆九渊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悄然成了会通融合的普遍认知基础[8:324]。
明末伴随着科技翻译大潮,天主教“会通儒学”首当其冲,以适应中国传统习俗,尤其是儒家礼仪伦理。耶稣会士通过结交儒家士大夫或依附皇权,对天主教义及其宗教礼仪作适当变通,此外,还从事西方经典的汉译活动,用儒家思想或相关术语解释教义,阐明耶儒相通或同源。如利玛窦为了传教,极力地在“天主”、“上帝”与“天”,“人性论”与“仁义道德”诸方面把天主教与儒学进行揉合和会通[9:41]。中国士大夫徐光启在晚明王学会通思潮盛行、耶稣会士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自觉地反思传统文化危机,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10:374]的思想,开启了翻译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主动会通西学的先河。
徐光启的翻译思想既有深厚的传统学术会通渊源,又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翻译史上不乏历史回音,然而这一重要译论始终没有得以明确的阐释和界定。本文试图从“会通”作为传统学术范式的内涵着手,进而对“翻译会通”加以界定和剖析。
三、从会通的内涵到翻译会通的界定
“会通”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11:508]韩康伯把“会通”注疏为“会合变通”[12:84]。《周易·系辞下》又说:“变通者,趣时者也。”[11:530]“趣时”即“趋时”,可见“通”意指灵活运用,但也作“通达”、“通晓”之解[12:84],如朱熹[13:1913]说:
会是众理聚处,虽觉得有许多难易窒碍,必于其中,却得个通底道理。谓如庖丁解牛,于族处却批大却,寻大可窽,此是其筋骨丛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发于硎。且如事理间,若不于会处理会,却只见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须是于会处都理会,其间却自有个通处,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处,自然通贯得,所以可行其典礼。盖会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便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
这里,朱熹解释的“会”是“众理聚处”、“族处”、“丛聚之所”、“曲直错杂处”,里面藏有许多“窒碍”之理,有待打通;“通”则如“庖丁解牛”、“批大却,寻大可窽”,要求“通贯”而“理会”、“得个通底道理”。朱熹进一步指出,“会聚”和“通贯”这两个环节不能偏执一端,否则“便窒塞而不可行”或“便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
明清会通中西之学兴盛,“会通”又被赋予新的内涵,马涛[14:55]的有关界定目前最为全面:
会通是指主体对各家学说作融会贯通之后,进而萌生出新观念和新思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吸收各家之长,从而对客观对象及其规律性方面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中西会通则是指在明清之际随着西学的东渐,作为知识分子先进者的救世思想家们,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后所表现出的对两种文化热诚相结合的产物。
综合韩康伯、朱熹、马涛的解释,会通的核心就是会合变通或融会贯通。其中(一)“会”是指两种以上不同文化品类的“汇聚”。(二)“通”更宜于训为“变通”,或训为“同”,力求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求“通”的契合点、同一性和相互打通的可能性[12:85]。(三)会通的目的是融合众家之长以求创新。
会通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学术范式,或重“会”,或重“通”,或重会通结果的创新。重“会”,就是通过遍观博览、集大成等方式达到“通”,如元代董真卿依据朱熹的解释,作《周易会通》十四卷,于《凡例》中说:“历代诸家之说莫不究揽,故总名之曰《周易会通》。……顾名思义,则于随时变易以从道者,皆可识矣。”[15:7]由此形成了儒家五经的“会通体”疏解之书[16:245]。二重“通”,以“会”的一方观通另一方,如儒释道三教融合中,王弼以圣人“体无”观通老子“言无”,佛经翻译格义之法则“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外典佛经,递互讲说。”[17:152]三重对所“会”双方的超越和创新,如杨雄的《太玄》是《周易》与《老子》思想融合贯通的产物。纵观中国学术史,禅宗、天台宗、华严宗以及新儒家、新仁学、新宋学、新史学等,都是通过会通创新的结果。
可见,“会通”简单地说就是“融会贯通”,“变通”寓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会通”指译者通过翻译把中学和西学进行融会贯通,以求超胜。从领域来看,与传统学术会通不同的是,翻译所会通的双方是中学和西学,强调中学对西学的信任、开放、包容与接受,而非彼此的遭遇与冲突;从翻译和会通的关系来看,翻译是会通的前提和中介,既包括翻译过程中的狭义会通,又包括在译作基础上的广义会通;从策略形式来看,参照传统学术的会通范式,结合徐光启和严复①的会通实践,翻译会通也可以分为三类:会通超胜(重创新)、会而观“通”(重通)、集思广益(重会)。
(一)会通超胜,以徐光启的著译为代表。徐光启会通思想的核心是“镕彼方之材质,人大统之型模”[10:374],强调“网罗艺业之美,开廓著述之途”[18:204],以耶补儒、“会通归一”[10:374]、以求超胜等。徐光启编译《崇祯历书》,“从流溯源,因枝达干,不止集星历之大成,兼能为万务之根本。……既而法意既明,明之者自能立法,传之于人,数百年后见有违离,推明其故,因而测天改宪,此所谓今之法可更于后,后之人必胜于今者也”[10:377]。徐光启在其著译中自觉地将西方天文历算之学与中国科技传统直接融会贯通,如《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三部著译之作,“皆以明《几何原本》之用也”[18:206]。《测量法义》是徐光启根据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加以研究、整理所著,使其“法而系之义”[18:207],阐述了西方测量方法的理论依据。《测量异同》是徐光启编译完《测量法义》后,认识到西洋测量法与中国勾股测望术实质上存在着诸多类似之处,因此再运用《几何原本》中有关定理解释这种一致性,并依据西法,对传统测量之法加以补论,使之有理有据,力求超胜。《勾股义》则继续以西观中,从欧几里得几何学这一视角来对中国传统数学中的勾股数学加以阐释[19:38-39]。徐光启的翻译会通,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字句直译,而是一种“实践智慧”[20:172],充分体现了丰富的翻译目的论思想,力求裨益当世,会通超胜。
(二)会而观“通”。“会”是“通”的视角和资源,以一方解释、对比另一方,是译者选取与原语相似的译语资源以打通原文、反观译语的一种理解和诠释策略。徐光启《题测量法义》云:“泰西子之译测量诸法,……与《周髀》、《九章》之勾股测量,异乎?不异也。不异,何贵焉?亦贵其义也。”[10:82]中国数学传统之代表作《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是徐光启理解、对比西方数学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是反观的对象,进而贯通中西数学之别:西学贵“义”,中学贵“法”。在《刻同文算指序》中,徐光启以宋明理学之“理”为视角,认为西方科技“时时及于理数,其言道、言理既皆返本蹠实”,反观宋明理学则“虚玄幻妄之说”顿现[18:204]。
严复西学翻译中,中西互观互释频繁,如他以《周易》中的“易道”诠释、会通斯宾塞的天演论说。反过来,严复又明确地提出“归求反观”之说,认为“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21:49]严复运用斯宾塞普遍进化论反观中学,在《周易》中读出了丰富的进化论思想因素,进而通过中西文化会通,构建出自然、社会不断进化的新宇宙观。
(三)集思广益,严复的后案是这一翻译会通的代表。严复[22:xii]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曰: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
这里严复“集思广益”之案语实质就是他“统新旧”“苞中外”[27:127]文化观下重“会”的翻译会通,特点是通过对比异同、附以己见来会通中西,如《穆勒名学》第二节开篇对逻辑学翻译为“名学”的长篇案语:
案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罗支之为字学,唆休罗支之为群学,什可罗支之为心学,拜诃罗支之为生学是已。精而微之,则吾生最贵之一物亦名逻各斯(《天演论》下卷十三篇所谓“有物浑成字曰清净之理”,即此物也。)此如佛氏所举之阿德门,基督教所称之灵魂,老子所谓道,孟子所谓性,皆此物也。故逻各斯名义最为奥衍。而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24:2]
这里,严复从名学的起源、西中诸家类似之学到译名偏颇等,广征博引,“集思广益”,并“附以己见”,使得读者对名学、逻各斯、逻辑等得以互文见义,中西会通。
明末开启的天文历算翻译是我国引进外来文化的第二次大潮,而此前的佛经翻译是第一次。面对外来文化,前者重会通,后者更强调格义,两者多有同异。为了更好地理解翻译会通的内涵和特点,有必要把会通与格义进行对比。
四、会通与格义
格义最早见于梁朝僧人慧皎[17:152]所撰的《高僧传》,其中第四卷《晋高邑竺法雅传》中提到:
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
根据陈寅恪[25:90-116]、汤用彤[26:282-294]等人的研究,这是对“格义”做出的比较完整的解说,从中可以看出,所谓“格义”就是用中国人所熟悉的老庄哲学、《周易》等“外书”中的名词、概念去比拟或比配佛典“经中”难以理解的名词、术语等“事数”,使佛教深奥的义理易于被中国人所理解。“格义”的体例是“生解”的经典注疏形式,即大字正文下夹注小字,或谓“子注”[27:52]。
综合以上格义和前一节有关会通的论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将两者进行对比:契合与相似、拟配与贯通、生解与超胜。
格义和会通的基础都是寻找中外文化的契合点和相似性。对此,格义的重要方式是“连类”,如“……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17:152]。会通之“通”也要求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同一性”[11:85]、相似性,或基于译者认同的“选择性契合”(elective affinity)[28:398]。如徐光启认为传教士“诸陪臣之言与儒家相合”[10:434],通过长期交往,更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学说与中国古圣先贤之说在修身、事天、劝善诸多方面可以会通,甚至如出一辙[29:628]。张之洞[30:127]《劝学篇》外篇《会通》中更列举了诸多中西相似之处:
《中庸》天下至诚,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也。《周礼》土化之法,化治丝枲,饬化八材,是化学之义也。《周礼》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农学之义也。《礼运》货恶弃地,《中庸》言山之广大,终以宝藏兴焉,是开矿之义也。……
严译正文和“集思广益”的案语中也频繁地会通中西异同之论,如前文严复认为逻各斯“此如佛氏所举之阿德门,基督教所称之灵魂,老子所谓道,孟子所谓性,皆此物也。”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更广泛地运用“合观”、“连类”、“捉置一处”、“比堪”、“参印”、“相互发明”、“移笺”等方法,对中西会通的相似性策略多有启发。
如果说契合点和相似性是两者的基础,那么拟配和贯通则体现了格义和会通的差异。格义旨在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强调诠释者的主体性及其本土文化参与意识;会通则重在新意的创造,要求超越诠释主体的历史性和个人偏见,实现不同文化传统的视界融合[31:19]。
如《牟子理惑论》对“佛为何谓”的解答就是典型的格义:
佛者,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也。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32:81]
这里,牟子眼中的佛,俨然儒家经典中的三皇五帝,又似道教的神仙真人,通过“犹名”、“佛乃”等拟配标记,用儒道两家对佛教里觉悟人生的佛陀进行格义。
会通不是会同或混同,不是表层的比附,而是深层的融会贯通,强调翻译应该是通人通解。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其稿”[17:201],所以其译作“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33:7]。近代马建忠的“善译”观中,也多有比较异同,以求打通原语、意旨、神情、语气等,进而达到“心悟神解”的会通境界。有关翻译通人通解,论述最多的是钱钟书,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会通思想,包括“遍观博览”、“破执”、“破间隔而通之”、化境论等打通观,认为翻译“尤以‘通’为职志”[34:820]。
会通与格义第三个方面的区别在于两者的目的不同,即生解和超胜之别。“格义”所采取的“子注”旨在翻译正文之后对佛经相关“事数”加以注解。如安世高擅长《毗昙》学,讲经时习惯逐条分析,“取经中事数,如七法、五法、十报法、十二因缘、四谛、十四意、九十八结等,一一为之分疏。”[35:85]这种分疏是对经中“事数”进行分析和讲解。因此,“格义”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翻译方法,而是来华僧人在讲解佛典中为便于中土听众理解,借用儒道名词术语类比佛经名相,如罗什借用道家的“无”格义般若学中的“真如”[36:25]。
在对待中西文化上,会通继承传统,而“不安旧学”;译介西法,但又志求补儒,超越中西,这正是徐光启的伟大抱负,如《崇祯历书》的编译,既总结了传统天文学的成果与不足,又大量吸收了欧洲天文学的先进成果,为我所用[37:93-94]。自徐光启以后,儒家士大夫和现代文人志士的翻译会通目的非常明确,如经世、启蒙等,他们翻译策略的选择也视译文目的而定。
五、结论
“会通”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渊源和基础,作为译学范式,它指译者通过翻译把中西学进行融会贯通以求超胜。会通首先表现为对待异域文化的一种心态和认知方式,中西学的会聚体现了中学对西学的开放和包容,于异中求同;其次,会通是译者选取与原语相似的译语资源以打通原文、反观译语的一种理解和诠释策略,蕴涵着丰富的解释学内涵和对译者学贯中西、通人通解的期待;最后,会通的目的是吸取异域文化为我所用,以求超胜,这一目的突破了原文中心论的藩篱,道出了翻译的实践智慧和伦理诉求。翻译会通是传统语内会通的拓展,是我国明末以降探索济世图强的一条学术途径,是传统文化自觉和引进西学的一种文化战略。这在徐光启提出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自明末至近现代,翻译会通思想与实践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清初西学中源论下的翻译会通、洋务派中体西用论下的翻译会通、维新派翻译会通、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翻译会通。本文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不同文化观与翻译会通的不同内容、模式、目的等。
注释:
①徐光启、严复分别被称为明末、清末中西会通第一人,两人的会通思想和实践可谓各自时代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