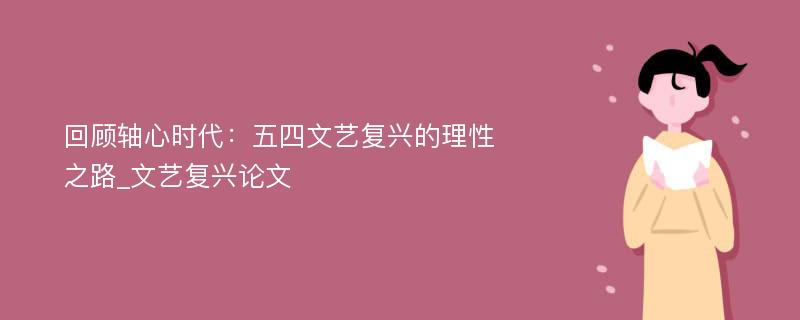
回望“轴心时代”——“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路论文,轴心论文,文艺复兴论文,时代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4-0106-08
一、“五四文艺复兴”说的历史依据
在五四后期,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出“五四文艺复兴”之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一观点体现了五四新文化人对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期盼和追寻,同时也表明他们的这样一种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诸多方面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五四文艺复兴”说一方面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五四”以来思想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理解,但另一方面也不断遭到质疑和否定。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四文艺复兴”说的历史依据是什么?换言之,新文化运动在哪些方面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关于这个问题,五四新文化人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白话文运动,另一是个性解放。1919年6月,蒋梦麟在《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中,把五四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文艺复兴的起点。他写道:“西洋人民自文运复兴时代改变生活的态度以后,一向从那方面走——从发展人类的本性和自然科学的方面走……这回五四运动就是这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1](P66)1921年7月,蔡元培在美国旧金山市的一个招待会上发表演说,也比较了中国与欧洲文化发展历程的共同点,并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看作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始。他说:“考欧洲文艺中兴之起点,群归功于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之文学。今中国之新文化运动,亦先从文学革命入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诸氏所提倡之白话文学,已震动一时。吾敢断言为中国文艺中兴之起点。”[2](P62)所谓“文运复兴”、“文艺中兴”,都是“文艺复兴”的不同译法。在这里,蒋梦麟强调的是人生态度的改变,主要是个性解放;而蔡元培的依据则是文学革命,主要是白话文运动。后来,胡适在口述自传中讲到新潮社成员看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的相同之处,也是讲这两项。[3](P171-172)
1933年7月,胡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题目为《今日中国文化的趋势》。胡适把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归结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的“相似之处”,作了比较系统的归纳。他写道:
该运动有三个突出特征,使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倡用民众使用的活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用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地反对传统文化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最后,很奇怪,这场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现代新的、历史地批判与探索方法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在所有这些方面,……被看成是预示着并指向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4](P181)
胡适一向认为,只有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来比拟,才能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而上述三点“相似之处”,就是他提出“五四文艺复兴”说的历史根据。前两点包含了蔡元培和蒋梦麟提出的根据,最后一点是他根据五四后期开展的整理国故运动而作出的补充,旨在强调这个运动领导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的批判、探索和研究的态度。胡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些方面,归结到“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的目标上来,这就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
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学者格里德曾指出:“‘一个古老民族的新生’的确是胡适所寻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不是通过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古老文明的再生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创造一种新文明来实现的。”[5](P37)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五四文艺复兴”说不断遭到人们的质疑和否认。
早在五四时期,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梁漱溟,就对新文化人的“五四文艺复兴”说提出质疑。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写道:“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1](P215)梁漱溟强调“复兴”的意义,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孔子的人生态度,中国的文艺复兴应该是孔子人生态度的复兴。
20世纪40年代,李长之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也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说:“五四所象征的时代精神是甚么呢?有人说是文艺复兴,我看并不是。这个时代还不够文艺复兴。因为,文艺复兴的意义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再生,……可是中国的五四呢?试问究竟复兴了甚么?……中国的古典时代是周秦,那文化的结晶则是孔子,试问五四时代对于孔子的真精神有认识么?”[6](P14-15)60年代,华裔美国学者周策纵在其力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写道:“欧洲文艺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古代文明兴趣的复活,是寻求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取代中世纪的思想。对这些古代文明的研究,是整个文艺复兴革命性的一个方面。而五四运动完全不是—个复辟运动。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在一个古老的国家中植入—种现代文明,并伴随着对旧文明的严厉批判。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它与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结论是相矛盾的。”[7](P469)
由上可见,人们否定“五四文艺复兴”说,最主要的理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致力于“复兴”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对古代文明的重新研究、重新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复活”;相反,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批判孔子、批判旧文明,这与文艺复兴的趋向相对立。
这里首先要指出,其实,新文化人在五四后期已改变全面反传统的态度,开展整理国故运动,致力于传统资源的开发。[8]本文要进一步论述的是,新文化人在仿效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中国文艺复兴之始,便发现先秦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媲美的“轴心时代”,发掘了久已衰落的先秦诸子之学,从而确立了“五四文艺复兴”的目标和内容。通过对“轴心时代”诸子之学及其精神传统的复兴,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本土资源与动力,这是新文化人倡导的“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
二、“轴心时代”思想资源的开发
欧洲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罗马辉煌的古典文明的发现和复兴。“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9](P444-445)曾令西方惊讶并推动欧洲文艺复兴的古代辉煌文明,并非仅仅出现在欧洲,而是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便阐述了这一历史现象。
雅斯贝斯指出,人类文化发展经历了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学技术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其中轴心时代是文明发展的突破期,人类精神领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精神文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个时期,世界的几个不同地区,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几乎同时涌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哲人和先知。他强调了轴心时代文明的巨大历史意义,认为轴心时代的哲人们对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各种问题的思考,他们所创造的元以伦比的精神财富,是以后二千多年人类不竭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他指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10](P10)
正如雅斯贝斯所指出的,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我国先秦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文化鼎盛时期。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诸子学衰落,儒学定于一尊,经学长期垄断学术。一直到了晚清,由于儒家经学无力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一些经学家开始注视和研究诸子百家,产生“通子致用”的思潮,才促成诸子学的复兴。
20世纪之初,晚清国粹派试图借助“国粹”来重铸国魂。他们仿照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发现和复兴,首先发掘了先秦时代诸子并立的文化盛况,并提出复兴周秦、古学的主张。五四新文化人与国粹派一样,也发现中国文化发展的早期,存在一个可以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媲美的辉煌时期,即先秦诸子并立、百家争鸣时代,并进而认定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文化,可以成为冲击儒学一尊的经学时代的思想武器和创造新文化的思想资源。
胡适从事学术研究,一开始便以诸子学为课题。在留学美国时,他不但写出了《先秦诸子进化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文章,而且把诸子研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内容,写了《先秦名学史》这部研究先秦诸子逻辑方法的著作。而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实际上就是一部先秦诸子哲学大纲。在这两部书中,他在章太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诸子学研究的内涵。一方面,章太炎的诸子学研究旨在打破儒学一尊的格局,而胡适则力图从非儒学派中寻找嫁接西方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章太炎把诸子学研究的内容从校勘训诂扩展到义理探求,而胡适则进一步用西方哲学作参照,致力于各家思想的融合和价值重估。
对于诸子学的研究,使胡适对先秦诸子的思想学术及其蕴涵的人文主义和理智主义传统,尤其是那个时代百家争鸣的自由精神,了然于心,十分憧憬。他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第一编“历史背景”中,曾充满激情地写道:
作为我们的研究主题的中国哲学的最初阶段(公元前600年—前210年),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和最灿烂的时代。这是老子、孔子、墨翟、孟子、惠施、公孙龙、庄子、荀子、韩非以及许多别的次要的哲学家的年代。它的气势、它的创造性、它的丰富性以及它的深远意义,使得它在哲学史上完全可以媲美于希腊哲学从诡辩派到斯多噶派这一时期所占有的地位。[11](P11)
后来,他把这个时期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古典时期”或“经典时代”。他说:“我自己对中国思想史的概念是,中国思想史上有个古典时期。这是个有创造性的时代;一个有原始性的固有思想时代。”[4](P260)“中国固有哲学思想的‘经典时代’,也就是老子、孔子、墨子和他们的弟子们的时代。”[5](P466)胡适所发现、所向往的那个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时代”,其实也就是后来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
胡适发现中国的“轴心时代”、肯定先秦诸子思想传统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为他力倡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一个像古希腊罗马那样文化发达繁荣、精神自由而又充满人文传统的经典时期,作为复兴的目标。所以,在《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胡适就明确提出了复兴“经典时代”诸子学派的主张。一方面,他主张让儒学回到它在先秦历史背景中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先秦“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的本来地位。在他看来,只要复原儒学的本来地位,不把它看作思想道德的唯一源泉,那么,儒学专制独尊的局面就可以打破。另一方面,他认为复兴那些一度与儒家学派同时盛行的非儒学派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11](P9)
当时其他新文化人与胡适一样,也发现了中国历史上那个思想闪烁的“轴心时代”,发现那个时代所积聚的思想资源。陈独秀一再说:“中国学术,隆于晚周,差比欧罗巴古之希腊。所不同者,欧罗巴学术,自希腊迄今,日进不已;近数百年,百科朋兴,益非古人所能梦见;中国之学术,则自晚周而后日就衰落耳。”[12](P372)“设全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12](P280)
1921年,蔡元培在美国旧金山市的一次演说中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有一个可以与欧洲希腊时代相比拟的辉煌时期。他对此作了具体的比较:“西历纪元前六世纪后,中国学术界,如孔子之教育,知行并重,随机启发,与苏革拉底(Socrates)相似;其言道德,尚中庸,与雅里士多德(Aristotle)相似;其大同理想,较柏拉图(Plato)所著《共和国》尤为深远。墨子之提倡数学、物理学、名学,与雅里士多德相似;其勤俭刻苦,与斯多噶派(Stoic)相似。老子、庄子之快乐论,与伊壁鸠鲁(Epikur)相似;其绝对论与柏拉图理想(Idea)相似。而且,当时周髀的算术,与欧几里得(Euclid)几何学相似。至于美术方面,如《考工记》之言建筑,言雕刻(decoration),《乐记》之言音乐,今日得自土中之古铜器,虽经过二千余年,亦尚有价值,与希腊美术相似。可以见中国古代文明与欧洲古代文明极相类似。”[3](P61)1923年10月,他在比利时沙洛王劳工大学作题为《中国的文艺中兴》的演说,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并进一步把中国诸子时代形成的思想传统,概括为平民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平均主义和信仰自由主义。[3](P340-346)
周作人在五四后期对传统文化作了重新审视,也发现了“轴心时代”文明的价值:“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13](P293)
与雅斯贝斯一样,胡适认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回归轴心时代的文化复兴运动。他曾把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复兴概括为三种:一是以唐代古文运动为代表的文学复兴,二是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哲学复兴,三是以清代考据方法为代表的学术复兴。[5](P470-471)在他看来,这些复兴都是到轴心时代寻找资源和动力,都是对轴心时代的思想观念的复活。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导言”中,胡适便指出,宋明理学“由佛家的观心,回到孔子的‘操心’,到孟子的‘尽心’、‘养心’,到《大学》的‘正心’”。[12](P6)又说:“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校勒、训诂的工夫,那些经书子书,方才勉强可以读得。这个时代,有点像欧洲的‘再生时代’。”[14](P6-7)
胡适在五四前后通过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发掘了“经典时代”的思想资源。关于这些思想资源,他后来在《中国思想史纲要》一文中,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全面的评价。他写道:
这个上古时期,不独为所有后来各时代的中国思想史确定了一个主要的模型,而且也提供了许多灵感和智慧的工具,使中国中古及近世思想家们,可以用来作凭借,去为哲学及文化的复兴而努力工作。简单说来,古典中国的理智遗产,共有三个方面:它的人文主义,它的合理主义,以及它的自由精神。[15](P515)
胡适充满激情地说:
这个古典时代三重性质的遗产,就成为后来中国各时代文化与理智生活的基础。他供给了种子,由那里就生出了后来的成长与发展。它又尽了肥沃土壤一样的使命,在那里面,许多种类的外国思想与信仰都种了下去,而且成长,开花,结果了。它给中国一个理智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及估计一切外国输入的理想与制度。而一遇到中国思想变得太迷信,太停滞,或太不人道时,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理智遗产,总归是出来救了它。[15](P518)
人文主义、合理主义和自由精神,这就是胡适所发现的中国经典时代的思想资源,也是他和其他新文化人所倡导的中国文艺复兴的力量源泉。
三、多元论与统整论之争
五四文艺复兴对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古老文明的复兴,与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旧传统的维护,有着全然不同的内涵、目的和意义。大体说来,文化保守主义者仍然尊奉孔教儒学、纲常伦理,力图维护儒学的一尊地位,试图以孔教儒学作为接纳西方文化和建造未来新文明的主体。而五四新文化人则致力于推翻儒学一尊地位,再现先秦”轴心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重新发掘历史上久已湮没的非正统文化资源,试图通过有生机传统的开发,为西方文化的移植寻找接榫,为新文明的再造寻找根基。五四时期新文化人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复兴问题上的对立,通过五四前后的几次论争集中地表现出来。其中,新文化人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论争,就是有代表性的一次。
这场论争肇始于1918年4月杜亚泉用“伧夫”的笔名在《东方杂志》发表的《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杜亚泉在文中认为,西方学说的输入导致国是的丧失、精神的破产,从而造成人心的迷乱;针对这一现状,他通过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提出“统整吾固有之文明”作为救济之道。同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以下简称“质问”)一文,对杜亚泉的这篇文章以及《东方杂志》上的另外两篇文章提出质问。接着,杜亚泉发表了《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以下简称“答辩”)一文,进行答辩和申述;陈独秀则于1919年2月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以下简称“再质问”)一文,再次予以驳斥。
杜亚泉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中写道:“论者谓国是之存在,实泥古时代,束缚思想自由之结果,而为进步停滞之原因。然进化之规范,由分化与统整二者互相调剂而成。现代思想,其发展而失其统一,就分化言,可谓之进步,就统整言,则为退步无疑。我国先民,于思想之统整一方面,最为精神所集注。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后世大儒亦大都绍述前闻,未闻独创异说;即或耽黄老之学,究释氏之典,亦皆吸收其精义,与儒术醇化。”[16](P363)又云:“救济之道,正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一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今日西洋之种种主义主张,骤闻之,似有与吾固有文明绝相凿枘者;然会而通之,则其主义主张,往往为吾固有文明之一局部扩大而精详之者也。吾固有文明之特长,即在于统整,且经数千年之久未受若何之摧毁,已示世人以文明统整之可以成功。今后果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16](P367)这两段话,反映了杜亚泉在文化观上与新文化人的尖锐对立。因而,《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发表后,便引起新文化人的质斥。
首先,杜亚泉强调文化统整,认为这是现代文明的救济之道,而这与新文化人所强调的思想自由、文化多元观点格格不入。
陈独秀在“再质问”中指出,杜亚泉所说的“分化”,当指异说争鸣之学风,“统整”当指学术思想之统一。“所谓学术思想之统一者,乃黜百家而独尊一说,如中国汉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欧洲中世独扬宗教遏抑学术,是也。……此种学术思想之统一,其为恶异好同之专制,其为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之障碍,乃现代稍有常识者之公言。”[12](P483)
1993年,王元化在为《杜亚泉文选》所写的序文中把杜亚泉归为自由主义者(其实杜亚泉并不讳言“保守”,1914年他发表文章倡言“接续主义”,便肯定其含有开进与保守两方面的意义),但也认为,“无论如何,统整说和他那自由主义思想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陈独秀对他的批评,“从文化的多元化来反对统整说,就比杜说显得优越”。[17](P57,58)
其次,杜亚泉把儒家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作为中国固有文明的基础,肯定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以儒学统整其他学说为固有文明的经验,这与新文化人对儒家纲常礼教的批判和对非儒学派等非正统文化资源的择取,以及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文化格局的追慕背道而驰。
陈独秀在“质问”中指出儒学不过中国学术的一种,批评杜亚泉以儒家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我国固有之文明与国基,且力图在共和政体下保存之,甚至用了“谋叛共和民国”这样的严厉之词。他还质问道:“我中国除儒家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以外,是否绝无他种文明?……以希望思想界统一故,独尊儒学而黜百学,是否发挥固有文明之道?”[12](P404-405)
而杜亚泉在“答辩”中则坚持己见:“所谓‘君道臣节及名教纲常诸大端’,记者确认为我国固有文明之基础。……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与现时之国体,融合而会通之,乃为统整文明之所有事。”[16](P370-371)陈独秀在“再质问”中,再次重申儒家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与现代无君臣之共和制度的对立,同时强调指出,儒家只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而非全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也只是儒学的主要部分而非全体。
对于文化统整与文化多元的不同追求,必然导致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不同认识:统整论者推崇儒学一尊的汉后文化格局,而多元论者则追慕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时代。因此,陈独秀在“质问”中又质问道:“中国学术文化之发达,果以儒家统一以后之汉、魏、唐、宋为盛乎?抑以儒家统一以前之晚周为盛乎?”[12](P403)
杜亚泉在“答辩”中称:“有分化而无统整,自不能谓之进步,中国晚周时代,及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之文明,分化虽盛,而失其统整,遂现混乱矛盾之象。以晚周与汉魏唐宋,以欧洲与中土,比较其文明,以记者之见解言之,殊不能谓其彼善于此。”[16](P370)对于杜亚泉的这种论调,陈独秀在“再质问”中称其“石破天惊,出人意表”。他反驳道:“统整(即学术思想之统一)之为害于进化也,可于中土汉后独尊儒术,欧洲中世独扬宗教征之。……夫晚周为吾国文明史上最盛时代,与欧洲近代文明之超越前世,当非余一人之私言。”[12](P483-484)
再次,杜亚泉认为西洋学说往往是中国固有文明某一局部的扩大和精详,主张以中国固有文明为主体来消融西方文化,这与新文化人对中西文化的理解以及在中国固有文明中寻找移植西方文化的接榫的意图迥异其趣。
杜亚泉在“答辩”中把现代民主主义视为中国古代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之政治原理的基础,并表白自己也主张输入和融合西洋学说。陈独秀在“再质问”中则阐述了古代民本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嘲笑杜亚泉把西洋学说看作中国固有文明某一局部的扩大和精详之“附会穿凿”,指出他关于输入和融合西洋学说的观点的种种矛盾和混乱,同时揭露其“‘不希望于自外输入西洋文明’之本怀”。[12](P486)应该说,陈独秀的指责是有根据的。杜亚泉主张输入西洋学说,目的只在于印证儒家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他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便说:“吾人之所取资于西洋者,不但在输入其学说,以明确吾人固有之道德观念而已。”[16](P350)他所说的融合西洋学说,实际上是以儒家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统整”西洋文明。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陈独秀等新文化人与杜亚泉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传统开发和文化复兴问题上的对立,作一简要归纳:杜亚泉只是要取其儒家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这一“我国固有文明之基础”,并以此“统整”西洋文明,救济中国和世界,而新文化人则是要剔除这一与共和制度不相容的“国基”,发掘传统资源中非正统的其他方面,作为移植西方文化的土壤和再造新文明的根基;杜亚泉主张文化统整,因而向往汉代之后儒学一尊的统整的文化格局,新文化人强调文化多元,因而追慕先秦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
收稿日期:2003-04-29
标签:文艺复兴论文; 胡适论文; 陈独秀论文; 儒家论文; 轴心时代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东方杂志论文; 先秦诸子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新文化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