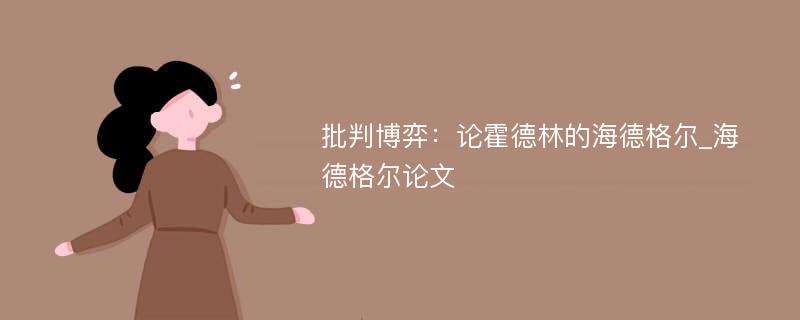
批评游戏:评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尔德论文,批评论文,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关于“诗之思”的言说迄今仍倍受现代诗学 的关注,而他的那本《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一书,则让任何关于文学批评实践的思考难 以轻易越过。如此意义上,对海德格尔关于荷尔德林诗的批评实践做出一番批评性审视 ,这对于我们眼下的文论建设无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个案。因为深入地来看,虽然海德 格尔的存在学说对于当代文论通过“语言学转向”走向“文化诗学”具有无庸置疑的意 义;但从此具体的批评实践来说,由于一种“思”对“诗”的僭妄,存在论/现象学批 评的“让诗言说”的承诺显然并未得以兑现。
这位存在论大师论荷尔德林诗究竟用意何在?曾为海德格尔思想作传的萨弗兰斯基认为 ,海德格尔的兴趣主要有三:首先是他在自己的权力-政治生涯失败后,试图通过“诗 之思”来重返权力之途;其次是借鉴荷尔德林的话语方式,通过改造“运思”的途径来 重建一种哲学品牌;再则是如作为“诗的诗人”荷尔德林那样,成为“思想本身的思想 ”,以实现古老的“哲学王”的理想。总之,“他在荷尔德林那里画了一幅自己的形象 ,一幅自己想让人看到的形象”(萨弗兰斯基382)。
《阐释》一书主要包含六篇关于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海德格尔的此番“荷尔德林之 旅”由此而体现出一种明确的批评立场,同诗人一起“运思”。这种批评实践在话语形 态上容易显得缺乏一种整体性,这是由于为了让在诗歌中纯粹的诗意创作物稍微明晰地 透露出来,阐释性的谈话势必总是支离破碎的。但以此为代价,批评却能够深入到诗作 的思想腹地并达到一种俗人难抵的境界。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任何解释最后的、但也 是最艰难的一步乃在于:随着对它的阐释而在诗歌的纯粹显露前销声匿迹”(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244)。
对话不仅仅是语言实践的一种方式,也是语言的本质性体现。因为只有通过彼此谈论 某物的方式而进行的对话,语言作为主体间思想交流的中介的功能才能得以实现。这也 就意味着,作为这种“思与诗的对话”的批评的前提,是“倾听”。因为批评之“说” 并非是批评家主体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地自说自划,而是一种让作为批评对象的诗自身 “说”。无论如何,“与诗歌相合的从诗歌而来的道说方式,只可能是诗人的道说”(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228)。但事实上,诗人本身的缺席总是使其文本处于 一种“无言”与“失语”状态。唯其如此,批评家要想实践让诗来“说”的承诺,就必 须对诗人的无声召唤做出响应。在荷尔德林的作品中,这种响应导向一条道路,即进入 那隐遁了的诸神的切近处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往意义的空间。但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条 道路呢?海德格尔认为只能通过我们对荷尔德林的诗的倾听,没有“倾听”就没有“言 说”。但倾听也就是参与到诗人之思中去,没有参与就没有倾听,而为了更好地参与诗 人之思,批评家首先得进入其生存之中。
这种“运思之说”的批评实践在话语形态上面临一个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说不 可说”。海德格尔关于艺术有一个基本观念:在艺术品中起作用的只有一样东西,即真 理,但这种真理不能被概念所捕捉,只能在具体的经验行为中被“觉知”。这就构成了 一种神秘,因为真理意味着对世界与存在的本源的贴近。“不过,我们决不能通过揭露 和分析去知道一种神秘,而是惟当我们把神秘当作神秘来守护,我们才能知道神秘。可 是,倘若我们并不认识它,我们又如何去守护它呢?”(海德格尔,《思·语言·诗》25 )荷尔德林之所以被海德格尔择选作阐释对象,不仅是这位曾表示“哲学几乎又是我惟 一的事情”的诗人也是一位“爱思者”,还因为在这位存在论者看来,荷尔德林不只是 “一位罕见的诗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位神秘的诗人”(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 释》229),从而也是一位别具一格的“诗人的诗人”。这让喜好“运思”的人们乐意将 他引为同道。海德格尔曾提出,能够用一个关键词将荷尔德林的诗一网打尽:神圣者。 这应该能够成立,因为诗人不仅曾一再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我期候着,看到了/神圣 者到来,神圣者就是我的词语”(“节日”)。而且在他的美学观里,一直将诗性与神性 相提并论,认为一切宗教按照其本质来说,皆为诗性的、创造性的。他认为在终将到来 的那个未来时代,我们完全“可以谈论多种宗教统一为一种宗教,这里每人尊敬他的神 而人人尊敬一位在诗的观念中的共同的神”(荷尔德林218)。
二
海德格尔具体实施的方案,主要是对每句诗句里的关键词通过梳理与筛选做出定位后 ,进行全面的渗透式的“串讲”。作为“倾听”的批评正是通过这种串讲得以实现,但 支配着这种串讲活动的,则是一种“命名论诗学”。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诗的本质必 得从语言之本质那里获得理解,因此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而所谓 “命名并不在于仅仅给一个事先已经熟知的东西装配上一个名字,而是由于诗人说出本 质性的词语,存在者才通过这种命名而被指说为它所是的东西”(海德格尔,《荷尔德 林诗的阐释》46)。虽然命名依赖于一个名称,而名称又来自命名活动但命名不同于名 称:名称是让人认识的。谁有一个名称,他就可以广为人知。而“命名是一种道说,亦 即一种显示,命名有所揭露,有所解蔽”,是让某种东西“得到经验的显示”(海德格 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236)。在海德格尔看来,最能体现这个诗之本质的一句诗, 是荷尔德林“如当节日的时候……”一诗的开头:“如当节日的时候;一个行走的农夫 /望着早晨的田野”;而他最为关注的一句诗则是“充满劳绩,然而人待意地/栖居在这 片大地上”。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的每部作品都由一个中心之思确立,整体不过是 这种思的一种逐渐扩展与最终的汇聚。比如“节日”可被概括为“道说着神圣者,并因 此命名着原初决断的惟一时间,而这种原决断是对于诸神和人类的未来历史的本质构造 的决断”(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92)。同样地,“追忆”一诗则被概括为: “作诗就是追忆。追忆就是创建。诗人创建着的栖居为大地之子的诗意栖居指引并且奉 献基础。一个持存者进入持存之中。追忆存在着。东北风轻轻地吹拂”(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183)。
以此而言,海德格尔式的运思批评也就是通过一种创造性的串讲活动,让被命名者得 以落实。毫无疑问,海德格尔的串讲不仅特色鲜明,而且自有一种“理趣”与“思味” 。比如对“返乡”第5小节一段诗的阐释:“是的!故乡风情如故!欣荣昌盛/在这儿生活 和相爱的一切,从未抛弃真诚/但那最美好的,在神圣和平彩虹下的发现物/却已经对少 年们和老人们隐匿起来/我在讲蠢话。这就是欢乐”。海德格尔写道:“诗人知道,如 果他把发现物称为隐匿起来的发现物,那他就说出了日常理智所反对的东西。……因此 之故,诗人在刚一说出关于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的话后,就不得不立即打断自己的话: ‘我在讲蠢话。’但他依然在讲。诗人非讲不可,因为‘这就是欢乐’”(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26)。但除此之外,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关于“追忆”一诗 的随机选择的阐释为例:1.“船夫们火热的灵魂”里的“船夫们”,被认为“就是日耳 曼的未来诗人。他们道说神圣者”;2.“榆树宛若宽大的顶峰/掩映着磨坊/但庭院中长 着一棵无花果树”,意思是“对磨坊和庭院的思念”,因为“磨坊提供谷物,并且为提 供面包而效力。为了面包之故,这位必须思天国神灵的诗人思念着人之忧心的这个作坊 ”;3.“在树荫下假寐/许是多么甜蜜”,被认为是诗人对一种无所作为的诱惑的拒绝 ,因为“诗人必须保持清醒,即便不是为了达到一种更高的沉思,首先也还必须变得更 为清醒”;4.“灵魂热爱殖民地”,意思是诗人“只是间接地、隐蔽地热爱母亲”,因 为“殖民地是归祖国所有的属地”,而“母亲是故乡的土地”。
只要我们能够暂且搁置对“权威批评”的无意识臣服心理就不难看到,如此等等的串 讲的牵强附会是无庸讳言的,经过这番阐释后的诗意的丧失殆尽也不言而喻。问题的症 结在于过于“落实”。诗人的写作活动与哲人的运思并非并行不悖,而阐释者显然将其 当作哲学文本对待了。诗毕竟是“诗”,荷尔德林对哲学之“思”虽有所偏好,并不意 味着他因此就无视“诗”与“思”之间的差异。他在给兄弟的一封信里曾如此写道:“ 将这些从诗的角度看如此微不足道的诗行放在面前,你会惊讶,我的心情何以如此奇异 。然而对当时的感受我说得甚至微乎其微。有时我就是这样,把最生动的心灵献给很平 淡的词句,以致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些词句究竟要说什么”(荷尔德林412)。没有外 人知道诗之思,其实是连诗人自己也处于一种“无意识”之中难以确定。所以有“诗无 达诂”之说:诗中之思既无从、也无须被对号入座般地予以落实。耐人寻味的是,对于 这并不是什么深刻的道理,海德格尔何以不予理睬?
萨弗兰斯基指出,海德格尔的诸如“存在存在着”与“世界世界着”这样的警句式的 言说隐藏着一种空洞的秘密;虽然他确切地指出了我们平时并没有打开直接体验的财富 ,但当他本人试图尝试做这项工作时会发现除了一些陈词滥调之外,什么也没有。他认 为海德格尔自己十分清楚那些内容生僻古怪的谈话其实“毫无意义”。所以在心情最好 的时候,“他甚至能对此持嘲讽的态度”(萨弗兰斯基418)。伊格尔顿认为海德格尔的 文本是典型的以“令人崇敬的思想”姿态出现的“神秘兮兮的胡言乱语”,这种现象“ 例示了20世纪美学在观念上的一个目的:这就是需要肆无忌惮地把自己的运作加以神秘 化”(伊格尔顿286-312)。在美国学者考夫曼看来,海德格尔的著述不断给人以一种印 象:“当揭开层层相叠的误解以后,读者会感到某些光辉的事物将要出现。可是不幸, 它总是停留在将要出现的阶段上。”当海德格尔试图为我们揭开迷底时,“黑夜似乎已 经降临,伟大的发现虽已诞生,但我们不能完全看到它”(考夫曼31)。
诚然,关于思想者们见智见仁的评论勿须大惊小怪。对于海德格尔思想在当代人文视 域中的重要影响不容低估。值得认真对待的,是试图取道于“诗之思”来完成“思的事 ”的海德格尔,他对于荷尔德林的诗的阐释看似别具一格,但不仅别有用意,更成问题 的是论者的借题发挥实在已离题万里。我们能够理解,如同英雄离不开荣誉的光环,热 衷于受人膜拜的思想法师们离不开神秘的氛围。海德格尔无疑是营造这种氛围的绝代名 家,他只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他的文本只是对一小撮词语的咏叹:存在/存在着,神 性/神圣者,遮蔽/开启,畅开/封合,隐匿/澄明,诗意/栖居,如此等等。典范的“海 德格尔式”书写可举例如下:“为诗意创作的灵魂所激励,诗人的心灵就是生气勃勃的 ,因为诗人命名着现实之物的诗意,基础并凭借其被显示的现实性才把现实之物带向‘ 本质’。诗意创作的灵魂通过生灵建立着大地之子的诗意栖居。所以,灵魂本身必须首 先在有所建基的基础中栖居。诗人的诗意栖居先行于人的诗意栖居。所以,诗意创作的 灵魂作为这样一个灵魂本来就在家里”(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109)。
这里充塞着一堆语义相近的概念与词藻:现实性/现实物,灵魂/生(心)灵,建基/基础 ,激励/生气勃勃,大地之子/诗人/人。这些词的确切的意思由于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地 被置换状态而无从着落,一种神秘也就随着这种闪烁其辞的表达粉墨登场。这让人想起 罗兰·巴特的一段话:“文本的喋喋不休,只不过是在简单的写作要求下形成的一种语 言的泡沫”(190)。但这些泡沫却能让人着迷,其中的奥妙在于能提供一种阅读快感, 这种快感来自于词语的往复回环。比如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的“返乡-致亲人”一 诗时写道:“诗人返乡,是由于诗人进入切近而达乎本源。诗人进入这种切近之中,是 由于诗人道说那达乎临近之物的切近的神秘。诗人道说这种神秘,是由于诗人诗意地创 作极乐。诗意创作并不首先为诗人作成欢乐,相反地,诗意创作本身就是欢乐,就是朗 照”(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27)。
且不说诸如“达乎临近之物的切近的神秘”,是如何清楚不过地将“海德格尔体”通 过搅混词义而实现神秘的策略展示明白。这段话语在结构上可拆析为这样一条语链:“ 诗人返乡,……诗人进入/诗人进入,……诗人道说神秘/诗人道说神秘,……诗意创作 /诗意创作,……诗意欢乐。”在这种往复回环的叙述中,一种行云流水的快感悄然滋 生,读来让人欲罢不能。尽管在这种语言的泡沫中,其实你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思想收获 。无庸讳言,与其说这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思想大师,不如讲只是一位深谙思想写作技巧 的真正高手。海德格尔的那种“欲说还休”的表述方式与“欲擒故纵”的行文风格所构 造的莫测高深之状,为自己赢得了语言魔术师与思想催眠家的桂冠。
三
事实上,与海德格尔极力让“神圣者”与“存在”攀亲带故,将诗人对于神圣性的体 验化解为关于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没有不同,荷尔德林对神性的呼吁其实是对高贵的人性 的召唤,脚踏实地的在世的人生始终不渝地是诗人视野的中心。诚然,“神”的概念在 荷尔德林诗里是个“显词”,且常被诗人用来作为人的一种对照。比如在“如当节日的 时候”一诗手稿结尾“天父的纯结光芒,并没有把它烤焦”一句的空白处,荷尔德林评 注道:“这个领域/更高,高于/人类的领域/这就是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是在张 扬一种超人类的抽象“异在”对象,而应该理解为对人的自我超越的坚信与期待。因为 对于荷尔德林,只有在通往神的过程中,人才能成为“人”。就像他的小说“许佩里翁 ”里阿邦达对许佩里翁所说:“我怎么会从生命的宇宙中走失?这里,永恒的爱对万物 一视同仁,团结所有的元素。我将存在,我不问为什么。存在,生命,这就足够了,这 是众神的光荣;为此,在神性世界中万物齐一,只要是一个生命,这个世界里没有主仆 。像相爱的人,自然的元素生活在一起;他们共同拥有一切,精神,欢乐和永恒的青春 ”(荷尔德林140)。
这里的“神”显然并非人之外的某个超然现象,而是人自身内的一种高贵品质,是人 性的复苏与提升。所以,这样的神无须人们对它顶礼膜拜,相反倒只有摆脱诸如此类的 诚惶诚恐之后才能够存在。对于以古代希腊为心灵圣地、视康德为“民族的摩西”的荷 尔德林,这样的世界也就是真正属于美的世界,因为“美更喜欢/在大地上居住,而且 无论何种精灵/都更共同地与人结伴”(“希腊”)。为此他曾欣喜地表示:“我们需要 审美的性情,我将把我的哲学书信称作《审美教育新书简》”(荷尔德林379)。所以诗 人放开心扉吟道:“家园天使,来吧!融入生命的所有血脉中/让普天同庆,分享天国的 恩赐!/让灵魂高贵!愿青春焕发!为不使人类的财富/失却欢悦,为使岁月的每个时辰都 洋溢欢悦/这样的欢乐,就像现在相爱的人们重逢之际/理所当然,也应受到神明的颂扬 ”(“返乡-致亲人”)。无可置疑地,与海德格尔笔下的那种苦大仇深地沉溺于神秘主 义冥想、没有生命喜悦而只有淡淡伤感与圣徒的苦难意识的幽灵截然不同;如同那个时 代最优秀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样,怀念着一种普天同庆的理想的荷尔德林的心是十分明朗 的,对普遍人性的呼唤与关注使他成了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分 子。“许佩里翁”里的这段话曾被反复提到:“我想不出有哪一个民族像德意志这样四 分五裂。你看到一个手工艺人,但不是人;你看到一个思想家,但不是人;你看到主人 和奴隶,青年和成年人,但不是人”(萨弗兰斯基381)。就此而言,海德格尔显然并未 按其预定的方案行事,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倾听”,而只是摆出了一种倾听的姿势,借 荷尔德林的嘴说海德格尔的话。在海德格尔的语境里,荷尔德林被置于一种“神/人” 对峙的二元结构中:“从在地出发向着天空召唤的歌,倘若没有神的声音就温声音了, 而神的声音保护着面临‘可怖之物’的人类”(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209) 。但如果我们真的倾听荷尔德林的言说那就不难意识到,对于内心深深渴望着“人”的 自立、期待着“在通往神的途中成为人”的诗人,并不需要这种“保护神”。
海德格尔热衷于对“本己之物”与“持存的东西”这样的词语,实施穷根究底的侦查 工作,而对那些抒情性相对明快的段落不感兴趣。如“追忆”里的这一小段:“但是现 在只管前行吧,去问候/美丽的加龙河/和波尔多的庭院/在那里,在陡峭的河岸/蜿蜒小 径曲折延伸/小溪跌入幽深的河流/而在小溪之上,有一对/名贵的橡树和白杨在张望” 。对此,海德格尔以“在诗意的问候中获得呈现的纯粹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就其本身来 说并不需要我们的谈论”,和“诗之言说不可漂浮于一种诗歌的风光描绘”(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116)为由,轻描淡写地将其掠过。低估海德格尔的诗学修养并 不可取,作为批评家的他并非不知道,对于一首“诗”,诸如此类的“风光描绘”与“ 纯粹的东西”并非可有可无的装饰物,而往往是诗性意味的核心所在。只有通过这些看 似“无用”的语辞所营成的节奏与旋律,才为诗情的生成提供了方便。否则,诗就不成 其为流动的“诗”而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海德格尔之所以“明知故犯”,是出于其 用从不“设防”的“诗”来解救被围困已久的“思”的需要。所以,尽管“返乡”的基 调是那么亲切明快,尽管海德格尔自己不仅承认,“我们必须用一个昭示着返‘乡’这 整首诗的词语来命名,这个词就是‘喜悦’”,而且也认为“在第二节诗中,充满了有 关‘喜悦’和‘欢乐’的谈论”(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13)。但经过他的阐 释并在其关于“深思熟虑的人和从容不迫的人首先就是忧心的人”(海德格尔,《荷尔 德林诗的阐释》32)这样的发挥之后,这首诗整个地成了一位满腹心事的圣徒的忧伤悲 怀之作。在其批评实践里,荷尔德林的诗歌文本完全成了其宣扬形而上“存在”学说的 工具,现象学所标榜的“面向事情本身”的立场因此而宣告破产。虽然海德格尔也曾承 认,“在荷尔德林的诗中,我们诗意地经验到诗歌”(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228),但在他的阐释实践中,读者已无法再去“经验”荷尔德林的诗,而只能理智地 来“认识”。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所谓“诗与思的对话”,其实是“思与思的对话” :首先以“思”为“诗”,尔后以其“思”取代诗人之“思”。这就是海德格尔以“运 思”命名的一种粗暴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实质,在其对荷尔德林诗所实施的批评实践中, 表现出的是“思”对“诗”的僭妄。
从上述分析来看海德格尔的此番“借尸还魂”式“批评游戏”,不仅不能与巴赫金对 拉伯雷的“我注六经”式研究相提并论,而且与巴特的“游戏批评”也相去甚远。这是 一桩典范的以“思”的名份对“诗”实施强暴的批评游戏。对这一个案的分析表明,有 必要对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之间的关系持一份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