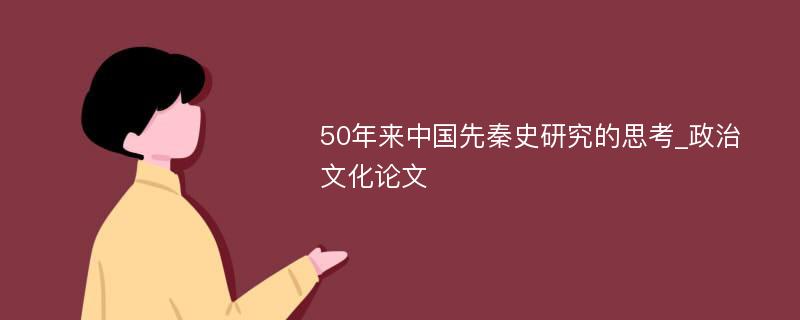
中国先秦史研究50年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学研究
本文对50年来中国大陆先秦史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如史学的功能和价值,“史学危机”,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现代西方史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郭、范诸老建构的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等问题,进行重新思索、重新认识,并对如何研究先秦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们在想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进而来认识中国的现实,把握中国的未来时,往往都把目光自然地投向先秦史的领域,因为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国文化的肇始,那里孕含着按着比例缩小了的现代中国的形影。因此,先秦史的研究在中国历史科学中一直占有较显著的地位。但是,数十年来,由于我们对先秦史研究本身还很少去进行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的批判和洗炼,致使研究的问题、研究的层次、研究的领域都未能得到纵深的拓展。并且,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动乱、历史悲剧而使得我们民族的历史意识得到了苏醒,这就更迫切地需要我们对一系列问题去重新思索、重新认识。在此,我们想就50年来中国大陆先秦史研究中有关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史学的功能和价值
在进行任何一个阶段的历史研究之前,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史学本身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功能和价值。由于我们以往并没有很深刻地去反思这一问题,致使对史学的功能和价值的认识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现象:或者是把它作为直接为所谓的革命现实服务的工具;或者是把它贬责为有嗜古癖好的人们的一种无用的摆设。由于这种模糊的、非科学的认识,使得我们的史学研究也就出现了摇摆不定的情况,什么“厚今薄古”,什么“以论带史”,什么“打破王朝体系”……这就启迪我们,对史学的功能和价值的深刻认识,有助于我们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从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本质属性来看,我们认为,史学的最大功能就是认识人类自身。哲学从人的本性、人的诸种关系来研究“人”,进而达到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认识自我。而史学则是从那已逝去的时一空场中所发生的人的活动,经过考据、论证、解释来认识人类自身。也就是说,它是通过考察我以前是个什么样子,“我”为什么会是那样的诸问题进而认识到“我”现在是什么?“我”现在又该怎样的选择,该怎样的行动?这也就是对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自身的发展历史的认识。实际上,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自身意识到的内容的历史。既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都是为了人自身的需要,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解放,满足自己那不断增长的超越自我的天性,那么,历史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以人自身的文化创造及创造活动的原因、规律来作为自己考察的对象,以此来更深入地认识那已经逝去的、但又仍包孕于现在的“我”自身中的那个“我”,使“我”在现实的未来的选择中有着更多的观照、更大的清醒和更优的决策。因为我们在选择和行动之前并不能完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种选择、行动是否符合客观规律、顺应人类自身的发展要求,因此,在选择的座标系中,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数就是:“我”原来是什么?“我”原来做过了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也就正象西方一位哲人所说的,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当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史学的这种功能时,我们就会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眼光去提出问题,论证和解释问题,进而更科学地认识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从史学的这一功能出发,我们认为,史学必须为人的现实服务,为人的未来服务,如果不是这样,史学必将失去自身存在的任何价值。但是,这种服务绝不是为所谓的政治服务,也不是为某一种实践需要加作注脚,更不是为证明某种言论的神圣性而作诠释。史学应该是,也只能是作为认识自己的中介,作为人自身解放的旗帜和启蒙的号角。
二、关于“史学危机”的问题
80年代,在我国的史学界,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里,流行着一种“史学危机”的说法。我们以为,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提法,自从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以来,它就从来没有而且以后也不会产生什么危机,这正象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不会产生危机一样。但是,仔细剖析产生这种“史学危机”说法的原因,对我们古代史的研究却有所裨益。我们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说法,大致有下列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政治干扰所致。社会是一个大系统,而政治又是经济的最集中的体现。作为文化系统一个要素的史学,当然就和政治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但是,史学毕竟是一门科学,它有着自身的认识规律和发展规律,同政治的区别也就是很明显的。然而我们在前数十年中,由于非科学地强调了突出政治、政治统帅一切,因此史学也就成了政治实践的工具,它规定着史学所研究的一切问题必须和当时的政治挂起钩来,为当时的政治实践服务。甚至不择手段地去歪曲、篡改历史,将历史变成了一个任人摆弄的侍婢。这种情况到十年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当人们从这场历史的动乱中醒悟过来后,便油然地痛感这种受到政治强行干扰、甚至成为政治附庸的史学的枯瘪。
其二,社会需求所致。我国原来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由于落后,人们最早认为要赶超西方强国,就得有他们那样的机械装备和科学技术,因而一度产生了“科技领先”的思想。目前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要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同样也需要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但是,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注意还仅局限于经、法、政一类,因此对史学的社会需求也就自然地变小,这也就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史学危机”的看法。
其三,时代发展所致。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巨大进步,为人们提供了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工具和方法,因而使得人们能够以新的思维工具和新的思维框架去重新思索、重新认识那已逝去的历史,这样也就更加不满足于传统的史学方法。英国的柯林武德就多次地将传统的史学称为剪刀加浆糊的剪贴史学。但是,目前人们又没有很好地解决如何重构史学体系的问题,因而在中外,就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危机”,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可能这种“危机”的程度要更严重些。
因此,人们所说的“史学危机”实际上是人们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新的迷惘、新的探索,产生危机的并不是史学本身而是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和需求。这种认识当然也包括我们史学工作者本身对史学的认识。由于我们认识的不成熟,以往的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诠释,成了政治实践的注脚,以致在我们的史学研究中造成了:理论的僵化,只是生硬地、教条式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言论;方法的单一,几乎以阶级斗争作为唯一的方法来探讨中国丰富的历史;内容的薄弱,数十年的史学研究只集中于几个问题,其他问题没有相应地展开研究,致使这几个集中研究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视角的狭窄,只是机械地注重从经济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层次的稀少,桠本业客观世界(自然的、社会的)具有丰富的层次,既有空间的,也有时间的,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却很少进行多层次的、立体式的展开。这种种的研究上的弊端在我们今天的历史的反思中是应该注意解决的。
三、关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现代西方史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问题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进步,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有了更加卓越的工具,建构了新颖的思维理论,诸如以系统论为代表的“老三论”和以“耗散结构”论为代表的“新三论”。现代西方史学在力图打破传统史学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立新的史学方法,形成了不少新的史学流派,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历史计量学派”、“心理历史学派”等,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这些理论和方法呢?我们认为,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一个最基本的系统——唯物主义历史观应该是,而且必将长期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因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二版,第586页)。这个原理是科学的, 它告诉了我们,非思想的物质力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物质力量往往有如海水之下的冰山,至于思想则不过是水面上浮露出来的那一小部分顶尖罢了。另外,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曲作家的一些科学的、辩证的论断也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的方法。例如,列宁就曾经精辟地指出过:“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人的认识的某些狭隘性和片面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掺杂其间。”(《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2页)
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同时,我们也并不排斥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现代西方史学中那种有价值的方法。因为作为一个发展着的人类文化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它理应吸取这些人类文明的硕果,来充实自身。并且,自然界和社会都是物质性的,它们在某些地方有着相通性,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发展规律。因而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当然也就可用来研究社会现象,如系统论的方法、统计学的方法、数学的方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方法都可运用于历史的研究,并且可运用于任何一段历史的研究。譬如先秦史,由于文献资料、数字记载的匮乏,在很多场合下就很难直接运用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来建立社会模型。当然,这并不排斥这些方法在某些细节上的运用。总之,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史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同时吸取一切对我们有价值的科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来丰富我们的史学研究。
四、关于对郭、范诸老建构起的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的看法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经过了特殊的空间途径而传播到中国来的。当时中国在坚舰利炮的撞击下,忍受着百般的屈辱,深感中国要自立,必须向西方学习,打破古老的传统,然而人们又苦于没有这种批判的武器。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便根据俄国人所理解、阐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和在自己传统思维模式、传统心理氛围的背景下来接受、宣传、普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来指导我们的史学研究,建构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体系。应该说,这种体系的建立,对人们认识中国的昨天,认识我们的祖先以及我们自己,是有着巨大作用的,因为它为我们开辟了另一条认识自己的途径。在郭沫若、范文澜诸老的体系中,他们的伟大建树主要有:他们都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历史在某种速度上有着她们的共同性,这实际上向我们正确地指出了人类所具有的共同意向以及在某一阶段上人类所具有的相同的认识发展水平;他们都认识到了物质力量的巨大作用,并力图去、解释这种物质力量对社会历史的推动和其发展的规律;他们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解释上,都有其正确或足以启迪人们认识的意义。如范老对西周社会结构的分析,郭老对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解释。但是,正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过特殊的空间途径而建立起来的,它也就不免带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其表现有:
1.思想的封闭性、排他性。认为自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凡是不合己论的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
2.研究的直觉性、同步性。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言论生硬地搬来作机械的比附。例将西方古代社会作为研究中的参照系数时也是给予简单地类比,诸如对国家形成的标志、历史阶段的过渡、商周“众”的理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现象。
3.历史的单线性、合目的性。认为历史都是严格地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单线地发展的,其间没有任何的变异、曲折,而这种发展都需要经过暴力的革命,革命又必定是最下层的劳动者和当时的先进阶级所进行的。
另外,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在中国刚刚确立以及特殊的政治环境,为了避免自己被套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因而在郭、范诸老的体系中,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政治、文化对经济的巨大的反作用。在他们的体系中,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鼎立系统往往变成了经济的独脚系统。我们对郭、范诸老史学体系的评论决不是一种贬责,因为他们的开创之功是不容抹煞的,并且他们是毫无愧疚地完成了那个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史学研究的使命,甚至可以说,没有郭、范等人的辛勤努力,就不会有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新史学。我们今天的评说只是对那个时代带有教条色彩的史学的反思,以之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充实、繁荣、完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实际上,我们的人类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地反思过程中而活生生地进展着的。
五、当前我们如何研究先秦史
上面我们在叙说对郭、范诸老的史学体系的看法时,已简单地讲了先秦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现在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说,不论是研究人员、研究机构的配置,还是研究论文、研究专著的数量,先秦史的研究规模都是不算小的。但是,由于多年来受到传统思维模式和政治干预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是有待于继续开拓的,这种开拓,不仅是对还没有或还很少涉足的领域,如人口变迁、职业制度、文化机理、区域经济等方面,并且即使我们的前哲已多次研究的问题,亦仍有待于我们重新检讨的必要,如进入文明的途径、社会的变迁、经济制度、“众”的认识、政治结构等,实际上,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史学,人们正是在对那封闭的历史遗存进行创造性的发掘中而不断地丰富着自己,人类的思想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解释过程中而向着更高的层次跃迁。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先秦史研究中,有必要:
1.打破教条的框架,切实从中国丰富而有特色的历史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考据、解释先秦历史的各种现象,并且在这种历史的认识中来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本身,而绝对不能再象以往那样把中国丰富的历史用来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言论的诠释。
2.更新治史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大系统的特点出发,吸取前哲以及今天一切有价值的史学研究方法,如陈寅恪老先生在为王国维遗书中所作的序言中提出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辨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见《金明馆丛稿》)、当今的系统论方法、丹尼尔·贝尔的“中轴结构”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等,以此来丰富我们的先秦史研究。
3.拓展透视的角度。首先应该将中国的先秦历史放在世界的舞台上,从世界这个文化背景上来鸟瞰我国古代文明在当时的位置,在当时所获得的进步,以及和当时其他地区文明的关系。其次,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认识,不仅要从经济角度,还应从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语言的多维角度去进行立体的认识。比如对晋国的“作爰田”,如果我们不仅仅从当时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对财产处置的影响,从当时人们处置财产的惯用方式及认识心理来看,也许会显得更清晰些。
4.丰富研究的内容。在前数十年中,我们先秦史的研究几乎都将全部的人力、时间投放到了几个集中的问题上,如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当然这些研究也促进了对其它许多问题的探讨,但是人们对其他问题的探讨又只是来为古史分期等研究服务,这样就显然使我们的先秦史研究内容过于单薄,也致使对古史分期等问题不能更深入地进行。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就不能再仅仅停留于以前的几个问题上,必须要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在科学的研究中,提出一个问题又往往要比解决一个问题来得更重要,史学的研究正象英国当代史学家柯林武德所说的,“每一步就都取决于提问题”的能力(《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274页)。假如我们从语言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就可能会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得到新的认识,因为语言就好象是世世代代所造成的全部知识工具和物质工具的结晶,社会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主要就是沉积在语言组织的各个层次中。比如我们对先秦时期人名、地名的分析,很可能就会更清楚地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这样也就能大大地丰富我们先秦史学的内容。
5.完善史学的体系。在前面叙述郭、范诸老所建构起的史学体系时,我们已指出在他们体系中所存在的不足。在我们今天的研究中,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补充、完善他们体系中不完整的部分,尤其要注意政治、文化、民族心理对经济巨大的反作用,具体地指出这种反作用的表现及规律,在先秦史研究中真正形成一个甚至是多个新的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史学体系,加深我们对“我”的昨天的了解,以之更切实地把握着“我”的今天,为“我”的现实和未来服务。
以上是我们就先秦史研究中有待于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实际上有的已涉及到整个史学的研究,只不过我们都是从先秦史研究的角度着眼的,故在此一并阐述。
此文得到吉林大学赵锡元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