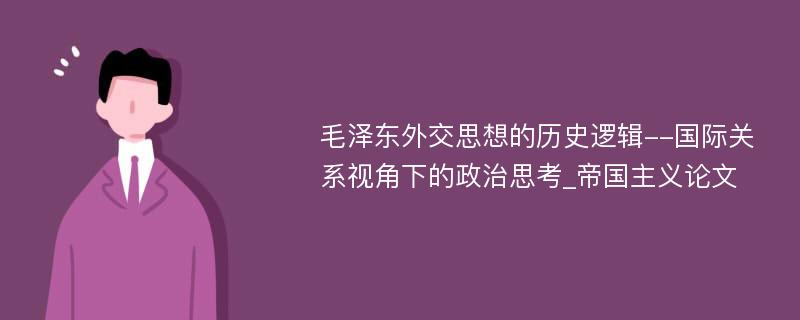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历史逻辑——基于国际关系视角的政治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视角论文,外交论文,逻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 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5)05-0092-06 将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置于近现代国际体系视域中,以历史逻辑的巨大引擎力、合力和张力进行历史追问,并赋予其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是运用唯物史观正确分析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内在要求,更是科学把握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哲学基础与逻辑前提。按照历史主义的启示,毛泽东外交思想孕育在1840年以来东西方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国际秩序之中,丰富于冷战后国际社会动荡、分化和改组的深刻的历史变革之中,是对历史时代脉动的当然反映和必然选择。在近现代外交关系中,毛泽东以主权独立、外交自主和国家安全为核心内涵和价值取向,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逻辑前提。 一、三大殖民主义外交生态与毛泽东民族国家独立的外交诉求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后,西方国家在欧洲大陆形成了相对均势状态的外交格局,并率先诞生了以平等和主权为基础的全新的区域关系外交生态。之后,这种外交现象逐渐地被新的地理意义的外交模式突破而改变——在非欧洲中心之外(例如东方世界)寻找新大陆,改变欧洲现状并占据优势——西方对东方强权政治的时代开始来临。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和秩序中,形成两个殖民外交生态体系: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殖民体系;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殖民体系。日本在为自身摆脱西方殖民困境的历史博弈中,随后也建立了对亚洲国家的新殖民体系。 这三种殖民主义体系给中国的历史命运带来了如下的影响:第一,英国的殖民运动迫使中国国家主权向欧洲“开放”。历史上,英国曾长期充当欧洲“均势”的“平衡者”。为了保持这个平衡者的国际地位,英国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东方国家寻找新大陆来作为实力支撑,以此抗衡欧洲诸国的对弈和竞争。于是,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世界殖民模式中,重商主义逐渐地占据主导地位。“重商主义政策能使国家维持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以便在海外建立专门为国家的工业生产供应原材料的殖民地。”[1]它以坚甲利器、工业资本化和不平等贸易为主要技术路线,建立西方对东方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就英国与中国关系而言,“英国的近代崛起带动的是西方欧洲霸权体系的兴起和东方中世纪华夏皇权体系的最终衰落”[2](P15-16)。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P692)“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3](P711)。第二,美国的殖民运动迫使中国国家主权向北美“开放”。在近代历史中,美国对西方和东方世界同时扮演两者角色:西方英国霸权的“掘墓人”和东方国家新殖民运动的“开拓者”。就中美关系而言,“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独立于西方殖民体系,对中国进行的新殖民运动的主要标志。此后,美国又强迫中国签署中美之间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望厦条约》标志着中美关系由鸦片走私开始的不平等贸易转化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整体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告结束。”[4]这样,美国在对传统英国殖民体制的东方控制进行反击后,实现了对中国新殖民的“交接”。第三,日本的殖民运动迫使中国国家主权向新殖民国家“开放”。在地缘政治和传统意义上,日本始终处于传统俄国和中国以及新生势力美国的夹击中,对中、美、俄的突破成为其“岛国”外交的主要使命。其后,对中国的侵略成为日本近代扩张的主要路径。日本对中国进行帝国殖民行动的秘密,在《田中奏折》中已经显露殆尽:“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5]较之英国殖民模式和美国殖民模式,日本殖民模式更多的是体现为直接的炮舰杀戮和战争掠夺。这使得中国在与国外势力的冲突中,付出了最为惨痛的历史代价。 这样,“欧洲大陆在英国的拉动下率先卷入发轫于英国的资本经济全球化,并与英国一道形成最初的资本中心国并由此形成对资本外围地区的殖民剥削和压迫。”[2](P25)美国利用欧洲诸国与英国的矛盾,通过“独立战争”和对东方国家的影响和渗透,在成为颠覆欧洲殖民体系的决定性力量的同时,也成为殖民和剥削东方国家的新的主人。而日本在成为东方国家反对和抗击前两者的新生力量的同时,又以东方社会新的“殖民领主”的身份,建立大东亚共荣殖民体系。这三大殖民主义以条约体制、文化侵略和战争手段为特征,以依靠封建势力和扶植买办集团为策应,形成了对中国的“集合式殖民模式”。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持续地成为三大殖民体系的空间聚焦之地,也成为世界矛盾向中国位移的新大陆。这种状况使得中国不得不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得不面临从未有过的民族生存力和生命力的考验,不得不被迫改变原有的自我封闭的内向型社会文明,在面对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近代外交生态中,只能进行两种选择:自主或者依附。 实际上,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诞生就是对这一时代特征的理性反映。具体而言:第一,三大殖民体系及其由此长成的中国近代主权思想,成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近现代历史上,三大殖民体系在东方中国的空间聚焦,同时升腾出巨大的民族独立革命的政治风暴。1840年是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的转折点,也是世界体系下中国由被殖民国家走向民族独立国家的历史基点。这个历史转折首先并不是中国人的主动选择,而是在面对世界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中,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裂变的情况下发生的被动性选择。正是由于这一历史被动性,强烈地激发出中国面对西方列强主导的霸权体系和殖民体系下的民族主义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开始总结近代以来的国际经验和历史教训,梳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维护国家主权为主旨,策划中国近现代外交战略。第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历史使命,构成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政治诉求。在反对殖民主义思想系中,毛泽东外交思想处于最高的历史方位之上。他首先站在“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6](P97)在“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的巨大矛盾和冲突中,对三大殖民体系进行了独立思考和外交行动[6](P101)。中国人民应当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走向独立自主外交。第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就东西方关系而言,近代全球化的本质是西方工业资本全球化和“政治文明”殖民化,以及东方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反制过程。而改变这个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实现民族国家真正独立的外交努力就是实行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这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建立民族国家外交体系的主要价值取向。在毛泽东的世界里,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百年来的屈辱外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7]这表明,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赢得国家主权和民族平等,获得国家自保和安全一直作为非常重要的动力引擎,成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缘由。 二、三大战争的东方位移与毛泽东自主外交意志的历史转舵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诞生来自于对世界战争特别是中国与世界战争互动关系的理性审视。其中,除了鸦片战争外,毛泽东所经历的三大战争是其全球史观的建立以及民族国家自主外交观念形成的动力引擎。这三大战争就是抗日战争、“冷战”和朝鲜战争。第一,抗日战争是二战期间亚洲区域国际秩序争夺的制高点,深远地影响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外交自决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是两大体系的战争。一是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体系与反法西斯体系的战争;二是亚洲范围内日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性考验:“日本对华基本方针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这是坚定的、不变的,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也是变不得的。”[8](P197)“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它一定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P205)。日本入侵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损失,“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敌。”[9](P432)“中国今天是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6](P6)“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8](P353)可以讲,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就是抗日战争所引发的关于中华民族能否存亡的大问题。第二,“冷战”是战后国际力量体制对峙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制高点,深远地影响中国在国际坐标体系中的方位判断和选择。“冷战”的实质是二战后世界秩序和体制的重新博弈。与此同时,民族独立国家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国际力量关系开始重新分化和组合,国际政治展开新的画卷。这给中国外交选择提出了严峻的课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冷战”世界提前进行了考量,首次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思想,并对国际社会呈现出的“第一种势力”(美国和前苏联)、“第二种势力”(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种势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互动和力量博弈进行了新的科学判断和考量。可以说,“冷战”背景下毛泽东的时代性判断和外交选择,对最初的共和国外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三,朝鲜战争是真正考量中国与世界强国博弈的制高点,深远地影响中国自主外交生存能力和政治意志。朝鲜战争对新中国能否实现独立自主外交,捍卫国家安全以及巩固革命胜利成果是一个全面的考验,也是对中共执政能力和外交能力的严峻考验。具体说,这场战争至少给新生的共和国带来如下的考验:一是能否具有独立应付与世界大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二是检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政治联盟关系的信任与合作的能力;三是能否具有独立于苏联社会主义体系之外,独自进行国际事务乃至进行正义战争的能力;四是能否代表民族独立国家向西方强国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宣战并获得胜利的能力;五是能否妥善处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问题的能力;六是能否有效控制和把握战争进程的能力;七是能否应付境外区域战争时维护国家稳定和政权巩固的能力;八是能否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背景下,赢得国际法理与话语权的能力;九是能否具有在东北亚地区实现与美国、苏联三角鼎力的能力;十是能否在战后新秩序生成中最大化地赢得中国国家利益的能力等等。应当说,这既是对中国自主外交生存能力严峻考验,也是对毛泽东个人不惧列强的政治意志的检验。 毛泽东自主外交思想既是对上述三大战争的积极回应,也是中华民族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后的经验总结。第一,抗日战争是毛泽东自主外交思想的实践前提。毛泽东强调,抗日战争“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6](P16)中国的外交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6](P3),“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靠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6](P3)“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9](P47)这个方向就是“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8](P353)同时,毛泽东将向日本帝国主义最后一战,同中国民族解放联系起来,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8](P474)。抗日战争为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创造了必要前提,锻炼和考验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发展进程,同时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世界体系的主体地位和自我意识[10]。可以看出,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民族自主外交思想与抗日战争带来的思考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连同对近代以来中国与外国势力持续战争的耻辱历史的印记,尤其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录,毛泽东在思考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发起的侵华战争之间的关系时,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反帝、反殖、反霸和民族独立自主的政治意志。这种政治意志甚至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影响着新中国外交的政治图谱。第二,对“冷战”形势的判断和考量,是毛泽东选择独立自主外交的主要国际动因。“冷战”的爆发使得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能否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世界大战,中国将如何选择自己的外交路径?二是美苏在世界范围的对抗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选择?三是在民族独立运动大潮中,中国是否选择完全独立的外交方略?四是前苏联的外交性质逐渐地发生变化,前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迹象愈加明朗化。面对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毛泽东开始调整“一个中间地带”思想,并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一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开始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形势的话,那么,“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诞生则预示中国外交思想将体现更大的独立发展性和创造性。“一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一度成为影响毛泽东后来观察世界形势变化,制定中国外交方略的基本理论支撑。而70年代“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最终形成都与上述理论认知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性。这几大不同时期的外交理论和策略蕴藏着一个基本的逻辑线索,就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捍卫和护持。第三,朝鲜战争深深地强化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的战略意志和政治决心。对于可能的中美军事冲突,早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已有相当的戒备。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曾强调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6](P76)也就是说,早在朝鲜战争之前的国内战争中,毛泽东就已经具有基本的估计和政治计算,这既反映出毛泽东的政治智慧,也是其长期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经验的总结的结果。实际上,与美国多年的交道,已经使毛泽东对未来共和国外交具有基本的价值取向,而朝鲜战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位开国领袖原有的独立外交意志。这表现为:一是就战争性质而言,毛泽东认为美国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美国“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中国必须“打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6](P137-138)。可以讲,毛泽东独立自主地参与战争的决心和意志来自于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知和判定。二是苏联对朝鲜战争的犹豫态度和一系列外交策略,引起毛泽东对苏联产生许多疑虑和怀疑,这成为新中国坚定独立自主外交意志和决心的主要原因之一。三是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坚定了一个信念,并深深地影响了其自主外交思想,即在两大帝国主义体系与民族解放体系的对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被欺负的”[6](P152),“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6](P152)在一定意义上讲,朝鲜战争就是中国通过战争迫使美国等帝国主义势力正视和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有决心并有能力走向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 三、三种主义的逻辑方程与毛泽东自主外交的价值取向 几个世纪以来,依靠文化意义的启示和宣扬一直是世界列强国家对外行为的“光荣传统”,从“欧洲中心论”、“美国使命论”,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都在制造一个外交逻辑:在所谓霸权文明逻辑下,以强权政治文化赢得国际话语权,以此为不平等的国际旧秩序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世界落后的民族国家始终处于被动的国际地位中,其正当的国际发展权利、民主权利无法得到基本的尊重和保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将,毛泽东外交独立思想和政治意志反映了落后国家政治领袖们力图改变世界旧秩序的政治向往。 如果按照文化范式来解构毛泽东自主外交模式及其价值取向,有三种文化历史逻辑值得深入探讨,这就是:文化主义、民族主义和伦理主义。 第一,文化主义以一种特殊的“意象”模式,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思想平台。在国际关系意义上讲,“意象”是一个国家政治领袖和国民对国际关系(包括历史、文明、战争等)本质及其特征的认知成果。当外交“意象”逐渐地变为一种价值观时,就会深度地影响外交决策者的政治意志和战略选择。事实上,毛泽东外交思想深深受到几个方面外交“意象”的影响,其中,受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在外交上更关注世界秩序中的公正与平等,以及奉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外交策略;无产阶级解放以及反对国际剥削;受中国近现代历史经历的影响,毛泽东更关注新中国的民族觉醒与国家独立;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更加关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生共和国的政权巩固与自主外交。可以讲,对上述文化与历史认知所形成的政治“意象”,影响毛泽东外交思维和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第二,民族主义以一种特殊的自强基因,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思想内核。民族主义运动主要体现为两种价值选择,一是作为民族存在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二是作为民族发展的历史使命性。这两种选择对于落后民族国家来说,在近现代都曾经历必须面对的过程。在近现代中国,在面对外部势力的侵略、掠夺、剥削和压迫中,国内曾出现了若干种不同的民族解放模式或者依附模式。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毛泽东犹如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以民族政治领袖的身份,以暴力革命和国家主权独立的方式,实现并完成了中华民族的自我救赎。 第三,伦理主义以一种特殊的文化高度,成为影响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标杆。将道德和伦理因子列入到国际政治的计算方程,是开明的政治领袖在外交世界中显示境界、智慧和能力的行为。在全球治理模式中,人道主义是国际社会全部秩序的制高点。正因如此,任何性质的国家势力和集团联盟都会希望借助这个制高点,获得其外交领域的法理资源或者“正义红利”。西方傲慢的中心主义在其推行干涉主义和霸权主义时,往往会以自由、民主和博爱的道德外衣,为帝国炮舰披上美丽的装扮;而在反击西方殖民精神和霸权意志时,落后国家也会积极地抢占这个道德制高点,尤其是领袖集团更加关注对伦理、正义等价值观的占有,以其民族道德价值监护人的身份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更重要的是在打破旧秩序和建立新世界中,占领秩序与体系的制高点,获得法理和道义支持。作为落后国家的民族政治家,毛泽东以东方人特有的世界理解力,在追求世界正义的普世价值时,树立了民族独立国家的正义原则,为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提供了道德标尺。 以文化主义、民族主义和伦理主义视角,分析和梳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动力源泉,会发现这三种“文化合力”共同影响了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文化内涵以及价值取向。 第一,毛泽东的文化价值观,成为影响外交思想长河分水岭上的一块巨石。毛泽东的文化价值观主要体现为历史文化观和国际政治文化观(革命意识形态)两个维度。就前者而言,毛泽东的历史观来自于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命运的发展启示,特别是来自于落后民族国家被殖民、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历史经历,同时也来自于东西方文明剧烈冲突的历史经历。这种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激发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抗意志和政治决心,这成为毛泽东坚决走向捍卫民族独立与尊严,选择独立自决外交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11](P20)。就后者而论,意识形态对毛泽东在国际社会划分国际力量组合关系,特别是区分敌、我、友关系并采取相应的外交策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事实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要素,意识形态是毛泽东决定选择与美国、特别是苏联关系模式及其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一段时期里,新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外交选择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恰好高度统一[12]。 第二,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外交观,成为独立自主外交主旨的思想支柱。在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既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主义者,也是一个典型的基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者。就后者而言,毛泽东认为,要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下解放中国人,必须首先解放中国人自己的思想。这是他反复强调鲁迅精神的关键所在。毛泽东以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实际上也指明了中国外交文化的方向,即民族解放与独立自强的方向。这种民族主义的诉求成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文化内驱力,也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思想引擎。 第三,毛泽东的国际伦理主义观,为中国外交思想体系进行了顶层设计。“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13],是新中国外交的两个首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除了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和投入战争外,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当然的外交选项。就后者而言,相对于国家实力和发展基础十分落后的中国来说,国际伦理意义的努力变得十分迫切。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价值维度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即在普世基本价值层面上,十分强调对主权、人权、正义、自由、安全的尊重;同时在民族国家道义上,十分突出强调对民族独立、平等、尊严和自决的价值偏好。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突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现民族解放的正义追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实践中,毛泽东以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为国际社会提出了如何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伦理命题。毛泽东秉承的道德标准是国际公正与平等、民主与人权、自由与独立,既是对国际霸权主义的限定,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界定,这个思想成为历届中国政府外交价值观的主导思想之一。”[11](P19)应当说,新世纪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其基本的国际伦理原则与毛泽东的国际伦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标签:帝国主义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美国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