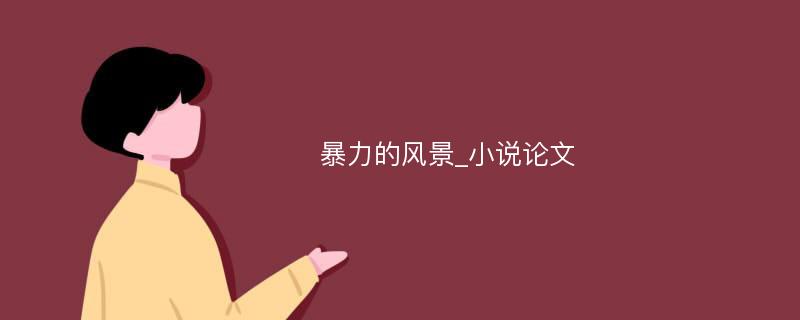
暴力的风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暴力论文,风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有所谓的第三世界文学吗?能否摆脱褊狭、不落俗套地界定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的本质特征?我以为上上之法,乃如萨义德①笔下所为,借此概念,边缘文学的多元多样、其有别于西方的特征以及民族主义的义涵,一一得到昭示。下下之法,则如所谓民族寓言说,热炒第三世界文学的概念,不过是在优雅地回避整个文学世界的丰富与复杂性。博尔赫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阿根廷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和文章,无论从什么标准说,阿根廷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但他在当今世界文学的中心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
但在这些国家,还有一种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其特出之处不在于作者所处的非中心位置,而在于他对该位置的认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种小说的特征不在于呈现非中心的问题,如“边缘”国家的社会状况(尽管秘鲁的社会问题在略萨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而在于作者如何将他自己与一个真实的或想象的创作“中心”相连,其创作艺术的主要问题都是在那里提出的。关键的一点是,作者接受自己这种游离在外的状态,虽然是此地造就其个人艺术史。这倒未必要像略萨那样,是地理意义上的游走他乡(略萨的创作生涯主要是在欧洲也即西方文明的中心度过的,而不是在秘鲁);有时也可是心理上自我强加的一种状态,作者往往因此而摆脱了所谓“影响的焦虑”。
在这种小说中,作者无需为创新问题与一个父辈或前辈形象不断对话纠缠,因为他意识到,他的题材是新鲜的,他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新的,他面对的读者也是新的,这都能使他可信可敬而自成一家。
略萨的《顶风破浪》中有一篇早期作品,评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小说《美丽的形象》。他祝贺她写了这么一部优秀的小说,没有被盛极一时的“新小说”作家弄得黯然无光。他倒认为那些作家的才华已经日渐衰竭。在年轻的略萨看来,波伏瓦这部小说最大的优点,就是“利用”了罗伯-格里耶②、娜塔莉·萨罗特③、布托④和贝克特的形式技巧和表述模式,却又带有自己的目的。
略萨在论萨特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种“利用”其他作家的哲学和技巧的概念。略萨后来发现:萨特的小说缺乏幽默感,缺少神秘感;文章虽然清晰明了,但政治上却令人困惑;艺术手法也很老套,缺乏新意。略萨年轻时信奉马克思主义,现在则后悔当时受萨特影响太深,甚至为其所惑。略萨告诉我们,他的幻灭发生在一九六四年夏天。当时,萨特接受《世界报》采访,将文学比作第三世界国家中就要饿死的孩子,暗示写小说是件奢侈的事,只有身处繁荣且正义的社会,才能问心无愧而为之。不过,略萨也承认,萨特的理性思考,萨特说文学永远不可能是游戏,这些都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安排人生道路,指引他走出文化和政治的迷宫。略萨似乎是在理性地寻找灵感,从其他作家的创作中寻找能够裨益自身的东西,而且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非中心位置,这使他的写作带有了一种纯真(略萨认为萨特缺少这种品质)和活力,不仅见于他早期的文章和书评,也见于《顶风破浪》中的其他自传性文字。
《顶风破浪》收录了略萨的随笔和书评,记录了他在过去三十年里热忱参与的文学和政治活动,读来趣味盎然。不管是谈他儿子参加拉斯特法里派⑤,谈一九八五年桑地诺主义者⑥治下的尼加拉瓜政局,还是谈一九八二年西班牙足球世界杯,略萨都写得情真意切。在文学方面,他也很推崇加缪。他说年轻时受萨特影响太深,读加缪时没能产生共鸣,但多年后秘鲁首都利马遭遇恐怖袭击,他读了加缪讨论历史上之暴力的长文《反抗者》,才意识到他更喜欢加缪而非萨特。他称赞萨特的文章直戳“要害”,这一评价也适用于《顶风破浪》中大多数文章。
对略萨来说,萨特是一个很让他纠结的人物,也许还是一个父亲般的人物。萨特欣赏约翰·多斯·帕索斯⑦并受其影响,略萨亦喜欢此人,原因也差不多,即多斯·帕索斯的作品没有无病呻吟,而多有叙事技巧的创新。后来略萨在自己的小说中运用了这些技巧(和萨特一样)。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被称赞为萨特所定义的“介入”⑧小说的绝好例证,也就是“扎根于时代的辩论、神话和暴力之中”。略萨真正感兴趣并提笔评论过的作家有乔伊斯、海明威、巴塔耶⑨等人,但最欣赏的还是福克纳,他也坦言自己受福克纳影响很深。他在谈《圣殿》的一篇文章中论及福克纳小说的形式创新,这些评论大多数也适用于他自己的小说。略萨说《圣殿》中的各个场景并非彼此衔接,而是并置在了一起,这其实更像是说他自己的小说。例如他新推出的小说《利图马在安第斯山》,就将各种声音、故事和评论并置在一起,彻底打破了延续性。
这部小说的场景放在了安第斯山脉的偏远角落。在萧敝的村落、空荡的山谷、幽僻的矿坑和崎岖的山路上,发生了一系列失踪案,大多数可能都是谋杀。政府军的军警利图马和他的副手卡列诺负责进行调查。读过略萨小说的人,自然不会对利图马的名字感到陌生。他和卡列诺四下打听,奔走乡间,讲述着各自的风流轶事,还要随时提防毛派游击队员的袭击。他们遇到的人,他们讲的事,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现实主义的秘鲁乡村全景图,展现了当今秘鲁的苦难。
秘鲁的毛派游击运动组织“光辉道路”⑩,还有当地的一对夫妇,都有嫌疑。这对行为怪异的夫妇经营着一家酒馆,有人见他们举行过仪式,很像古印加人(11)的仪式。小说描述了“光辉道路”实施的政治谋杀不可理喻的残暴,并将谋杀案的疑云引向印加人的祭祀仪式,从而形成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黑暗氛围。安第斯山暴力的风景也强化了这种氛围。书中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比秘鲁的贫困、游击战、自然环境和无望更为突出。
仿佛现代主义者略萨已经丧失了他的乐观态度,像一个真正的后现代人类学家那样,决意要探究秘鲁的非理性主义、暴力、前启蒙的价值观念和仪式。书中处处可见神话、先祖神灵、山鬼、精灵、撒旦和巫师,影影重重,也许都超出了合理的程度。“不过,想用头脑来搞懂这些杀戮,肯定是不对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道,“你压根儿就找不到合乎理性的解释。”
小说的肌理并没有受它所描述的非理性主义影响。这部小说有侦探小说的情节,自然要恪守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这是此类小说的基础;同时它又要营造非理性的氛围,以暗示暴行的隐秘根源。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并未催生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说到底,这还是一部典型的略萨作品。尽管有时显得错综复杂,但总在他的掌控之中,各种声音也调和得很好;这部小说的美与力量,就基于它紧密有序的组织。
尽管该小说竭力要避开现代主义论述“第三世界”国家的陈词滥调,但也不是《万有引力之虹》那样的后现代小说。书中到处有非理性的“他者”形象(以及与之相关的巫术、仪式、陌生的风景和暴行),但读者不会觉得这是要表现抽象的“他者”,而会觉得它是一部幽默写实的作品,其力量就在于可靠地记录了发生在秘鲁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游击队攻占小镇以及随后进行的审判,妓女与大兵之间的夸张恋情,都有报告文学般的可信度。小说中的秘鲁是一个“无人能懂的”国家,人人都在抱怨自己工资少得可怜却又不得不为之拼命。尽管略萨总在进行创作试验,却仍是拉美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家之一。
略萨的其他小说里也有主人公利图马的影子,这一点有些像巴尔扎克或福克纳的风格。利图马在《谁是凶手?》(亦是一部带侦探情节的小说)中也是主要人物,在《绿房子》中过着双重生活(该小说得名于一家妓院,《利图马在安第斯山》中也提到了它),在《胡莉娅姨妈与作家》中还是一部肥皂剧中一个令卡亚俄市黑社会闻风丧胆的虚构人物。
这个朴实的人物全心全意为军队服务,没有一丝狂热,却有一份诚实,有着强烈的生存本能和愤世嫉俗的幽默感。略萨对这个人物的处理是饱含同情的。略萨在秘鲁读过军校,写起军旅生涯来得心应手。例如,《城市与狗》中写年轻的军校生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竞争,《潘达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极为幽默地讽刺了军队里的官僚习气和性生活。他擅长描写男性之间的微妙情谊,写大男子汉的脆弱时刻,写硬汉如何无望地爱上妓女,并善于恰到好处地用一个粗俗的笑话打断男人的多愁善感。
他的冷嘲热讽令人莞尔,但从来不是无的放矢。在其早期小说中就很明显,略萨偏爱睿智的现实主义者和愤世嫉俗的温和派,不喜欢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者和狂热分子。他写的好人尽是当兵的,但他却没有尝试着去理解“光辉道路”游击队员的内心世界,他们都被描写成完全不可理喻的家伙,邪恶得近乎荒谬。
这当然与略萨政治立场的变化有关。《顶风破浪》记录了这一转变。略萨年轻时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信奉马克思主义,崇拜古巴革命;后来变成了成熟的、有自觉意识的自由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自视为“全世界崇拜撒切尔夫人、憎恨卡斯特罗的仅有的两个作家”之一,批评君特·格拉斯(12)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观点(即拉美国家应“效仿古巴”)。《利图马在安第斯山》中对“光辉道路”游击队员的描述,与他早期的一篇文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那篇文章中用优美动人的笔调颂扬了一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员,此人是他的朋友,一九六五年“在与秘鲁政府军交战”时牺牲。难道当我们青春不再时,游击队员就不再有人性了吗?还是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朋友里就很少有游击队员了?略萨的作品引人入胜,他的信仰也极具活力,会令读者产生共鸣,即便不是赞同他所有的政治观点,至少也会同情他在表达这些观点时所具有的那种孩童般的真诚。
“在秘鲁当作家意味着什么?”他在《顶风破浪》中的一篇文章里问道。该文谈到了塞巴斯蒂安·萨拉扎·邦迪(13)的英年早逝,后者是秘鲁最成功的作家之一。年轻的略萨怒不可遏,这也不难理解。他说所有的秘鲁作家最终都会失败,不仅是因为秘鲁没有读者和出版商,更是因为那些抵制并躲避“贫穷、愚昧或敌对环境”的作家都被当成了疯子,他们要么委曲求全,要么选择流亡,没有其他出路。年轻的略萨憎恨秘鲁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愚蠢”,根本不读书;他抱怨秘鲁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太少;他梦想着到欧洲生活,对非秘鲁文学相当痴迷。这都说明略萨痛苦地意识到了他的“非中心”处境。
*本文译自《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96年6月21日。
注释:
①爱·萨义德(1935-2003),巴勒斯坦裔美国文学批评家,著有《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
②阿·罗伯-格里耶(1922-2008),法国作家,“新小说”的主要理论家,著有《橡皮》、《嫉妒》等。
③娜·萨罗特(1900-1999),法国女小说家,著有《无名氏画像》。
④米·布托(1926-),法国“新小说”作家,著有《变》。
⑤该教派起源于牙买加,崇拜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相信黑人终将获得救赎,重返非洲,并迫使白人转而为他们服务。
⑥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以民族英雄桑地诺的名字命名。
⑦多·帕索斯(1896-1970),美国小说家,著有《美国》三部曲。
⑧萨特在二战后提出“介入”的文艺理论概念,号召作家通过其作品对当代重大问题做出回答,通过“介入”来改变社会现实。《什么是文学?》中对此概念有详尽阐释。萨特后来将这种有自觉政治内容的、公开的、狭义的“介入”概念扩展到无明确政治内容的、潜在的、广义的“介入”,认为文学及其他文艺形式,其批判性就是“介入”。
⑨乔·巴塔耶(1897-1962),法国思想家、作家,重要作品有《文学与恶》、《论色情》等。
⑩该派别建立于1970年,是秘鲁共产党发生分裂时成立的,主要开展游击战和暴力活动。
(11)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12)君·格拉斯(1927-),德国作家,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3)塞·邦迪(1924-1965),秘鲁作家,著有戏剧《爱情,伟大的迷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