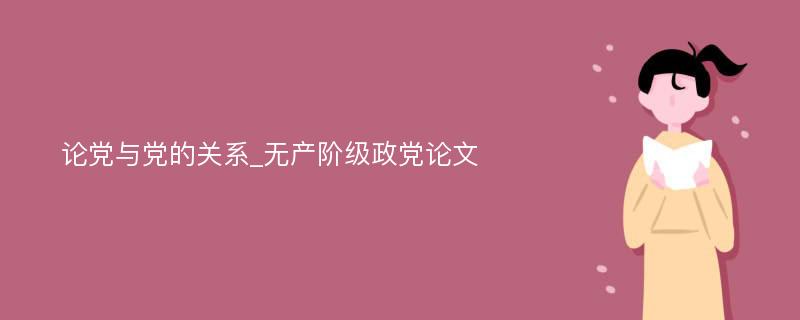
论党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论党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主义事业从本质上说是国际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登上斗争舞台,就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思想在组织上的体现,就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5个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注: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第一国际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群众组织。)。但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舞台都在本国,共产党首先必须成为本国各族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才有资格成为革命的领导者。这样,无产阶级国际政治生活中就有了一个如何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之间、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工人政党之间以及成员党与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一个半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党际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后,实践更加敦促人们对这一问题重新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庆之际,本文就党际关系中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些再思考。
一、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和空间范围
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是由资本的国际性决定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势力,在剥削和镇压各国工人问题上,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总是一致的。尽管各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竞争,但为了对付无产阶级革命它们总是会联合起来。因而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是国际性的,他们的阶级对手是国际性的,他们的解放条件也是国际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由此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就其本性来说是国际主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2页。)。根据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地位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因此,无产阶级“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9-290页。)。如果忽视这种无产阶级的兄弟联盟,那就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135页。)这就是无产阶级实现世界革命的战斗口号。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组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其宗旨和活动的目标就是要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战胜资本的国际联合。
列宁是把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的巨人,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主权国家的奠基人。列宁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不同,他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获得胜利。那么,列宁是不是因此就忽视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思想呢?是不是认为单独一国就能把社会主义持久地发展下去呢?从列宁大量的论著和实践中显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列宁思想的原意是,以一国首先胜利为契机,然后把无产阶级革命战火燃烧到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去;俄国十月革命只是拉开世界革命的一个序幕,使俄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90、91页。)。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几年中,列宁一直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寄希望于西欧革命的爆发和支持。列宁领导成立的共产国际,就是作为领导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而出现的。
从本质上说,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国际性质,但不是说它随时随地都以“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这一形式出现。这就涉及革命的空间范围问题。《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十分清楚,“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直接斗争的舞台首先是在本国。共产党首先必须成为本国各族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人也只有获得本国人民的拥护,才能站住脚,才有资格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两个著名策略口号,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前一个口号的基本精神是号召各国工农兵群众调转枪口去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一个口号的基本精神是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从而削弱反动统治阶级的实力,壮大革命力量,促使无产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国内战争取得胜利。很明显,革命斗争的舞台都在本国。
革命的范围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问题,而是关系到革命主体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力量的作用问题。这里有两点必须明确:一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可以不分国界地进行全球行动,而是本国的无产阶级首先要打倒的是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国际无产阶级可以给予道义上、物质上、力量上的支援;一个国家无产阶级胜利了,本身就是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贡献。这就是国际性的体现。二是一国无产阶级对另一个国家革命的国际援助,并不意味着越俎代疱,代替别国革命。革命的成功,总是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而且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绝对不能借口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去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恰恰相反,党与党之间要尊重各国的国情和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列宁就提出过“不能从莫斯科对各国发号施令”的警告。列宁对1920年红军在迫歼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军队时,一直打到华沙,并想以此促成波兰革命胜利的这一“善良”愿望和行动,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这与尊重主权、自主原则不相符,更何况革命不能输出,不能代替别人革命。代替的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暂时胜利了,到头来还是要以失败而告终。
如果说,在国际共运发展的历史上,过去注意得比较多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国际性的话;那么,当今在出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又强调民族化特性齐头并进的趋势时,则更应该注意国际共运的多样性,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空间范围问题。
二、历史与现实
在考察党际关系的历史演变时,人们发现有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在国际共运发展的不同时期,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组织形式有着集权和宽松不同的表现。其中有一种明显的趋向,即当国际阶级斗争激化,革命处于高潮时期,各国党之间的关系一般采取比较集中或高度集中的形式;当革命处于低潮,国际阶级斗争趋于缓和时期,党际关系一般采取宽松、自由的形式。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的建立,从总的方面说,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构想有关。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国际和情报局的建立,都处于阶级斗争激烈和革命高潮时期,它们联合的组织形式都相应地偏重于集权,所坚持的组织原则是集中制。共产国际更是在明显的革命高潮中建立的,共产国际“一大”通过的《行动纲领》强调指出:“由于无产阶级行动有协调一致的绝对必要,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和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注:库恩·贝拉:《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10页。)因此,共产国际的组织形式一直是高度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冷战开始,苏共就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必须行动一致,在国际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按照苏共的指挥行事。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产生的背景则不同。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的发展环境中编制无产阶级军队的时期,因此组织形式显得比较松散。
当前,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同时,也由于各国共产党对过分集权的弊病作过斗争,有所认识;因此,党际关系就变得宽松,主要是双边对话,比较和谐,做到了独立自主。
一个高度集中的国际组织,固然有它形成的历史背景,它在历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但历史经验表明,用一个中心集中领导处于不同情况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严格的集中制原则,并不是国际组织所必需的。服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目标和坚持各国革命道路的多样化,是不可分离的两个侧面。强调高度集中必然要损害一些国家的利益,导致党际关系的极不正常局面。组织形式上的高度集中必然会妨碍各国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且由于远距离操纵,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多,指挥时不是不及时,就是发生失误。如果某个党享有实际上的领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损害兄弟党之间的平等和独立的原则。国际组织形式比较松散,这对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有利。但如果过分强调分散,忽视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和统一,就会为机会主义的活动提供土壤;过分松散的组织形式,过分强调民族利益,有可能使民族沙文主义思潮恶性膨胀,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当今,在处理党际关系时要注意当代国际关系发展中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依存,二是各国独立自主的倾向越来越强烈。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是由生产力、现代科技革命迅速发展决定的。地球变小了,咫尺天涯,阅尽人间。人们数小时内便可跨越大洋彼岸,瞬息之间便可对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变了如指掌;加上人类所面临的战争与和平、贫困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能源等共同问题,使国家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和更加容易。独立自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不可阻挡的潮流。相互依存不是依附,每个国家都要求有自行处理自己国家内政外交的权利,反对外来干涉,争取真正的独立自主。
还要看到,当代国际关系发展中存在“一个不变”,即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的战略不变。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总战略从来就没有变过。人们没有忘记,当共产主义还是一个幽灵的时候,欧洲一切反动势力就为驱逐这个幽灵结成神圣同盟;十月革命刚胜利,帝国主义就叫嚣要把年轻的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有英美的祸水东引,后有希特勒对苏联的疯狂进攻;战后又有冷战,又有人要打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又扬言要继续“消灭共产主义残余”。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要借全球化之机把资本主义制度变为全球性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一刻也没有忘掉两种社会制度对立的现状,一刻也没有忘掉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他们推行的价值观是根本的威胁。因此,在地球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是他们不变的总战略目标。
面对上述“两个趋势”和“一个不变”的国际关系形势,我们在处理党际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时,既要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政;又要加强党与党之间的彼此交往,共同切磋,加强合作和团结。这是打掉了“指挥棒”以后当代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新课题,必须建立起彼此间的新型关系。
加强联系与合作并不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国际组织。至少在最近若干年内,重新建立国际组织没有这样的条件和必要,就是召开世界性共产党会议也没有条件和必要。因为成立国际组织或召开世界性共产党会议,免不了要形成决议之类的东西,这除了给人以束缚,损害独立自主外,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但在“两个趋势”和“一个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各国党之间处于隔绝或联系甚少的状态,大家各行其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应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合作,关键是要采取适宜的形式,遵循正确的原则。
三、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来往是一种正常的国际现象。和谐相处,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处理得不好,唇枪舌剑,甚至兵戎相见,有损于革命事业,有损于共产党的形象。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吃过“老子党”的苦头,有过切肤之痛,但中国共产党也公开承认:过去在处理与别国党的关系方面也有缺点和错误,特别是片面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估别国党的是非,对某些党曾经造成不利后果。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强烈地吸引着世界上持有各种不同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人们。大家都在思考和探索事情的是非曲直,试图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全世界共产党人在“两个趋势”和“一个不变”以及苏联、东欧剧变这个大背景下,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意义重大。根据100多年来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党际关系应该建立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
各国共产党都应当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舞台在本国。“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国情千差万别,不可能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或固定的公式进行革命和建设,一个模式不行,两个三个也不行,只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国情相结合,走符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道路必须由自己去探索,去创造。既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也不能强行推广自己的经验。因为本国共产党对自己国家的情况最了解,与本国人民的联系最密切。一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依靠本国革命条件的成熟和党的路线正确,并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出了错误,也要靠这个党自己来总结经验教训,自己纠正错误。来自外国党的指责批评,错了,十分有害;即使对了,效果也是不好的。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外国共产党“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结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即使因来自外部的错误干扰影响党犯了错误,也从不过多责怪外人,而是检讨自己的错误,因为自己对本国的情况最了解。
各国共产党是一律平等的,不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历史长的党还是历史短的党,执政的党还是没有执政的党,都不能有尊卑上下之分。在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个国家的党站在运动的“前列”,站在前列的党也没有权利以指挥者自居,自封为“领导中心”或“领导党”。即使把革命搞成功了,把建设搞成功了,也不能自认为垄断了真理,把自己的一套说成是“普遍真理”、“共同规律”,强加于人,任何党都没有凌驾于其他政党之上的特权。
各国共产党应当互相尊重。各国共产党的经历不同、处境不同,经验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对问题会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党与党之间存在分歧是难免的。要求各国党在一切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这是不现实的。对于意见分歧,只能通过互相讨论,共同切磋,友好协商来解决。有些问题一时弄不清楚,可以各自保留意见,等待实践来作出回答。切不可以势压人,强迫接受,更不可纠集几个党进行围攻。互相尊重是共产党人的美德。真正做到了相互尊重,一些问题往往容易解决。互相不尊重,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几个原则,同样也可以作为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关系的原则。中国共产党认为,虽然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差异,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分歧,但这些差异和分歧不应该妨碍发展双边友好关系,也不应该妨碍进行可能的国际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交往中奉行“超越意识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方针。发展同这些政党的友好关系,符合双方的愿望,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当今,党际关系实际上是国家关系的一部分。遵循正确的原则,处理好党际关系,是总结过去经验教训提出的要求,也是迈向21世纪的时代要求。
标签: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