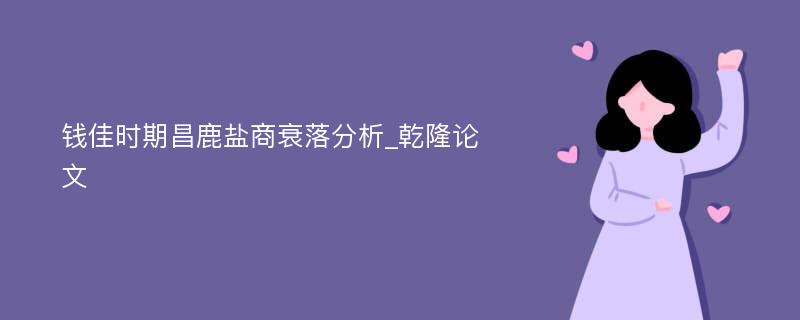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现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盐商论文,群体论文,时期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2)03—0087—08
清初,长芦盐商利用清王朝相对宽松的盐政管理体制和较轻的盐课牟取了高额的利润。康、雍两朝的天津,涌现出一批积累了巨额财富的长芦盐商,如张霖、查日乾等。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衰落过程,“乾隆时期,长芦盐商就开始从财势显赫的顶峰,急速地向下滑落。至乾隆后期,原有的盐商纷纷破产而遭参革,没有破产的盐商也大都负债累累”①。是什么导致这一时期的长芦盐商整体式微?关于这一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成果亦十分全面。导致长芦盐商走向衰落的原因目前主要指向捐输、迎幸、盐课、息银、参革五个方面②。但是,盐业运营(或专卖)是一种经济行为,压垮盐商的原因还要从经济角度寻找。
一、“饮鸩止渴”的垄断地位是各种危机的根源
关于垄断的危害,很多经济学家做过经典论述。李嘉图在谈到“殖民地贸易”时曾引用过亚当·斯密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正像重商制度其他卑鄙和恶意的手段一样,妨害其他一切国家的产业,尤其是殖民地的产业,同时不但不能增进,反而会缩减企图由此得利而建立这种制度的国家的产业。”③英国人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是近代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学术高峰期正值中国清代的乾隆时期。亚当·斯密对清政府的“垄断政策”曾进行过考查,并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又称《国富论》)中进行了论述:“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得极大的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④
结合长芦盐商的有关情况,亚当·斯密对清政府“垄断政策”的论述是中肯的。首先,世袭的“引岸专商”垄断制度⑤确实限制了长芦盐商追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的可能性。盐商们“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⑥。雍正元年(1723)八月初二日,皇帝专门下旨命各地盐政“约束商人,严行禁止。出示晓谕,谆切劝诫,使其痛自改悔,庶循礼安分,不致蹈僭越之愆”⑦。因为,除非朝廷大规模的盐政改革或强制收回,长芦盐商的引地世袭罔替,规模也不会轻易改变。盐商的利润无法作为再投资增加规模,只能被消费掉。其次,利息问题。长芦盐商为维持正常运营,曾向内务府借了大量的帑本。当时普遍认为,帑息已属较轻,内务府向盐商出借帑金很有些“皇恩浩荡”的意思。“朕惠爱黎元,屡次蠲租贷赋,不惜帑金亿千万两……况此项帑银,原系该商等自行恳请借给者,并非官派其借,出于商人勉强也。”⑧那么帑息的利率是多少呢?“且帑利只系一分起息,为数甚轻。若商人等于民间自行借贷,焉得如此轻息?是商人已受其利矣。”⑨可见,当时民间借贷的利率是要远远高于百分之十的。
盐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对食盐的垄断意味着占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津门百咏》有云:“堆积如山傍海河,河东数里尽盐坨。民间珍视同珠玉,不道此间如许多。”⑩依靠着对食盐的垄断经营,长芦盐商们取得了巨额财富,“盐筴长芦此要津,风天气色属商人。铜山金穴须臾事,大宅连云递旧新”(11)。长芦盐商们的“垄断”经营由于缺少竞争压力、发展动力和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表面风光背后,隐藏着长芦盐业绕不过去的三大危机。
(一)“有钱大家赚”,乾隆后期陋规公开化
各级官吏是食盐垄断经营体制的管理者和保护者,也是朝廷盐务政策的执行者,手中握有盐政管理和武装缉私的权力。盐区各级官吏直接从盐商经营利润中坐地分肥。雍正皇帝已经觉察到官吏加派陋规的危害,“贵卖夹带,弊之在商者尤小,加派陋规,弊之在官者更大。若不彻底澄清,势必致商人失业,国帑常亏。夫以一引之课渐添至数倍有余,官无论大小,职无论文武,皆视为利薮,照引分肥,商家安得而不重困?赔累日深则配引日少,配引日少则官盐不得不贵,而私盐得以横行”(12)。但是陋规现象并没有因为雍正的“清醒”而发生改变,反而愈演愈烈,“自设立长商以来,各省官绅士庶皆视盐务为利薮。或借口办公巧为侵蚀,或受人请托曲为通融,他若陋规黑费之类不可枚举。且课项则有□展缓,而陋规则无处减轻”(13)。“每引规费烦重,竟需成本五两有奇。所卖岸价,不过制钱八九千文,以钱易银,约每引亏银七八钱不等,商何以堪?”(14)清中叶以后,陋规现象公开化,各级官吏更加肆无忌惮。王守基的《长芦盐法议略》记载:“杂课多系相沿陋规,盐政运使衙门动辄数万,故膺盐差者回京以后,例有呈献,谓之‘当差’。振古如兹,不以为非。”(15)
据关文斌的统计,乾隆五十八年(1793)接受长芦盐商养廉银和其他津贴的政府官员包括盐政、运使与副使、直隶总督、奉天将军、天津道、天津镇、天津知府、天津知县,以及内阁、都察院、翰林院等部门的官员,还有书吏、笔帖式和护军校等等。其中,最高的为盐政养廉银,每年20000两,最低的为天津县养廉银,每年400两。大多数盐商的引地并不在天津附近,他们还需要满足引地所在地官吏的需索。这部分规费包括给盐引地知县、捕厅和都司的规费、节礼、寿礼,还有给衙门各署的规费。这些数据都是来自《长芦盐运使司档》、《大清会典》、《清盐法志》等官方正式记载,可见清乾隆时期陋规公开化已经非常明显(16)。当然,非盐区的官吏也可以从长芦盐业利润中“利益均沾”。“雍正五年正月二十日,大学士富宁安等奏议给奉天、宁古塔、黑龙江三处将军养廉银两,奉旨:尔等议称不便给予参票等语,所议甚是。此等养廉之项,应动用盈余银两,著将长芦盐课盈余银两内动用六千两,给与三处将军分用。”(17)
(二)“最大的陋规”——报效
皇帝,是国家各项盐务政策的最终决策者,他的喜好直接关系到盐商们的身家安危。商人为四民之末,虽腰缠万贯,也怕“天威难测”,各种报效成了盐商们“邀宠”的重要手段。“津门跨沧海之胜,逼近京邑。巡幸所至,首先驻跸。行宫、船坞岁资经费动辄钜万。若夫翠华涖止,情殷瞻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至过大庆典、大军需,淮商捐输或数百万,芦东亦以百万为率,其余寻常捐输,难以枚举。”(18)
根据嘉庆《长芦盐法志》的记载推测,盐商报效之例始于乾隆帝用兵大金川之时。乾隆十九年,“长芦盐政普福奏芦东众商情愿捐银三十万两,稍充军营赏需之用,且援金川之例为请”(19),结果遭到了乾隆皇帝的申饬。他认为用兵大金川时,“两淮、芦、东、浙、闽等处各商之急公捐输者,不便阻其报效之忱,俯允所请。其实于军需所费何裨万一!方国家全盛,府库充实”(20)。总之,他拒绝了盐商们的援例报效的“热心”。乾隆二十四年,皇帝的态度发生变化,“长芦、山东众商呈称,屯田塞上,中外一家,情愿公输银三十万两,稍备屯饷之需,不敢仰邀议叙”,乾隆皇帝称赞芦东盐商“办课素属急公,今复吁请捐输,情词肫恳,著允所请”(21)。乾隆三十六年,大金川联络小金川再次反叛。三十八年,“大兵进剿金川,各商志切同仇,末自有效。今长芦商众情愿捐银六十万两,山东商众情愿捐银三十万两”(22)。乾隆皇帝全部笑纳。乾隆五十二年,长芦商人捐银三十万两备造拨船,实际用去二十八万二百五十两(23)。嘉庆四年(1799)三月十九日,芦东商人江公源等呈称,“目下川楚教匪指日可除,惟安抚善后事尚需繁费,长芦商人情愿捐银六十六万两,山东商人情愿捐银三十四万两,共捐银一百万两,稍抒忱悃”,嘉庆皇帝以“芦东商力素称拮据”为由,“著各交十分之六”(24)。
报效表面上都是自愿的,有时候还可能被皇帝驳回,但是如果报效不积极,后果是很严重的。嘉庆五年,长芦盐政观豫奏请芦东盐斤加价,嘉庆皇帝以“昨两淮、浙江、广东各商俱吁恳报效,而长芦商人并未呈请出资助饷,更无可借口”(25)为由,拒绝了芦东盐斤加价的请求。嘉庆皇帝可能有些“健忘”,就在不到一年前,长芦商人刚刚捐银三十九万六千两助饷剿灭川楚教匪。
(三)靠加价维持各方利益,私盐乘虚而入
垄断行业的显著特点是缺少市场竞争,商品定价的主观性较强。以食盐为例,它的定价包括商品成本、官吏的陋规、对皇帝的报效、帑息等等,除此之外,还要确保盐商的期望利润。要保证如此之多的利润,加价销售就成了盐商的不二法门。据《长芦盐法志》的记载,清代长芦官盐加价始于雍正年间,“雍正九年六月,户部议覆,直属销卖盐价,长芦商人运本消乏,运行日艰,嗣后每盐一斤酌加大制钱一文”(26)。乾隆年间尤其是中叶以后是官盐加价的高峰期。乾隆二十九年,“准长芦盐政高诚请增芦盐价值,与原定价外,每斤加价一文”(27)。乾隆三十五年,巡盐御史李质颖“请于见行盐价外每斤酌增钱二分,以补钱价之不足,则商无亏本之虑,民无淡食之虞矣。下部议行”(28)。“乾隆三十六年,特旨加恩,每斤再暂加一文,以降旨之日为始”(29)。“乾隆四十七年,巡盐御史征瑞、总督郑大进奏,盐穰、运脚、绳席、人工较前加倍,请每斤酌增制钱二文。下部议行。”(30)
靠盐斤加价的办法来确保利润,表面上看是最简单的也是最直接的手段。但它不是“免费的午餐”,官盐加价后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是私盐横行。雍正皇帝曾对其有所预料。雍正元年,皇帝两次在谕旨中论及加价的危害,“上下各官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诛求无已,穷商力竭,不得不那(挪)新补旧,上亏国课,高抬盐价,下累小民。至于官盐腾贵,贫民贩卖私盐,捕役斗殴,株连人命,流弊无穷”(31),“赔累日深则配引日少,配引日少则官盐不得不贵,而私盐得以横行。故逐年之课难以奏销,连岁之引尽皆壅滞”(32)。雍正初年,长芦一带贩私盐的现象已非常严重,“雍正元年八月,奉上谕:长芦一带,兴贩私盐者甚多,或百十成群,手执器械”(33)。乾隆元年三月,“风闻直省四恶皆微露其端倪,即如天津一带,私盐横行无忌,恐其他类此者相继而起”(34)。
“不涨白不涨”虽然为盐商带来了巨额财富,为官吏带来了不菲的额外收入,为皇帝补充了小金库。但它最终损害的是盐业运营的根基,损害的是盐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也给国课造成巨额亏空。盐商和各级官吏获得了额外利益,皇帝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嘉庆五年,嘉庆皇帝驳回了长芦盐政观豫的《请芦东盐斤加价》折,且饬之“私盐本因官盐过昂而起,今再议加价,则私盐自必更为充斥,官引堕销愈多……况盐价既增之后,即不能复减,累民宁有已时?”(35)“明末长芦盐的运销量达二十三万九千八百多引”,当时每引为六百五十斤(36),共计15587多万斤。“以嘉庆五年奏销册计之,(长芦)共行正盐九十六万六千四十六引,每引行盐三百斤”,(37)共计约28981万斤。明代全国人口仅数千万,长芦盐区的行盐量却并不算少。乾隆六十年,全国人口已增至296968968人(38)。至清嘉庆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何止数倍,但是清代长芦行盐总量比明末增加却不到一倍,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势头。可以推测,到清朝中叶,相当多的人在食用私盐。咸丰三年(1853),清王朝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纳课之多寡以销盐之多寡为凭,销盐之多寡以食盐户口之多寡为断。自国家定课以后至于今,生齿之繁,户口之增,岂啻倍蓰。乃食盐之人日见其增,销盐之路日见其广,而行盐之引地反多滞而少畅,以致正杂之课额亦有绌而无盈”(39)。
二、“银贵钱贱”与“杰科布定律”
通过查阅盐法志、地方志等材料,笔者发现“银贵钱贱”问题一直困扰着清中叶包括长芦盐商在内的各地盐商。盐商行盐以引为单位,每引都在数百斤,所以盐商支付国课和食盐成本都是以银两为结算单位,而食盐的零售多以斤为单位,每斤售价几文至二十几文不等。因为“银贵钱贱”,买卖之间,盐商利益本身已经折损不少,交纳国课时,又有很大一部分利润被销蚀掉了。盐商们凭空“蒸发”的巨额利润,实在有些“莫名其妙”。
(一)由来已久的“银贵钱贱”
传统观点认为,“持续半个世纪以上的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了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了“银价高涨、钱价下跌”(40)。其实,“银贵钱贱”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一直无声无息地侵蚀着商业的根基,困扰着包括盐商在内的商人群体。已有很多学者注意到,我国的“银贵钱贱”问题早在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造成“银贵钱贱”的原因主要来自国内,包括货币质量不一、国家重银政策、小钱盛行等等(41)。包括鸦片贸易在内的上述原因充其量加重了“银贵钱贱”的程度。除操作层面的原因外,乾、嘉时期“银贵钱贱”现象愈演愈烈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与长芦盐业有关的“银贵钱贱”现象最早见于雍正九年的上谕。“奉上谕,前据长芦盐政郑禅宝奏称,康熙二十七年间,经抚臣等议定盐价,每觔(同斤)价银一分三四釐不等。彼时每银一两只换小制钱一千四五百文,是以每盐以觔定为十六文之价。迨后,钱价渐平,现今每两合钱可至两千文,而盐价仍是十六文。将钱易银,不敷原数,以致商运消乏,欠课难楚。”(42)乾、嘉年间,“银贵钱贱”的情况愈演愈烈。乾隆“三十五年,又议准长芦盐斤售卖所收均系钱文,近年钱贱银贵商人易银完课,有亏成本。”(43)“乾隆五十三年,巡盐御史穆腾额奏,各商运脚等费,百物昂贵,更兼钱价日贱,商赀益就消耗”,嘉庆元年九月五日,“第念商人资本微薄,各处钱价过贱,易银交课不免亏折,尚属实在情形”,“嘉庆元年,巡盐御史方维甸奏,芦东商人节年疲乏,成本加增,钱价过贱,办运交课亏折较重”,“嘉庆二年,巡盐御史征瑞奏,芦东商人,近因钱价赔累过多,资本消乏”,“嘉庆五年,巡盐御史观豫奏,芦东商人,近年因钱价亏折,赔累难支”(44)。《清史稿》中也记载,乾、嘉时期,“银价翔贵,(长芦)商亏弥钜”(45)。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曾因“银贵钱贱、芦商赔累”的事由出奏(46)。“银贵钱贱”问题几乎与清王朝的“盛世”相始终,从雍正到同治各个时期,在长芦盐业上都有表现,尤以乾、嘉时期为盛。可见,该问题并不能简单的归因于鸦片贸易等原因。
(二)“盛世”的困惑与“杰科布定律”
雍、乾、嘉三朝属于清代的“鼎盛”时期,人民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生口日繁;物产丰富,商业繁荣;当时国家也并无太多的“内忧外患”,为什么“银贵钱贱”现象在这段时期出现并愈演愈烈?笔者在查阅清代史料时,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盛世”的物价要远远高于“乱世”。清代从顺治朝开始,物价水平就已经高于明朝末年。据清初叶梦珠的亲身经历,“物价之不齐也,自古而然。不意三十余年来,一物而价或至于倍蓰”,“先父大人尝叹息,为予述隆、万间物价之贱,民俗熙□,迄今五十余年,而物价悬绝,一至于此”(47)。而繁华盛世造成的“物价腾贵”与“银贵钱贱”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嘉庆四年四月的一份上谕:“朕闻盐价颇昂,民虞淡食,汝应如何调剂,据实覆奏。奏查长芦盐价,一由物价腾贵,一由钱贱赔折。”(48)
笔者有个固有的印象,“乱世”民不聊生,物价应该昂贵;“盛世”时百姓乐业,物产丰富,物价就应该平抑。所以,笔者一直不解,为什么在盛世物价会大幅度上扬,“银贵钱贱”现象会出现,直到看到“杰科布定律”。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宏斌教授在其《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一文中,介绍了杰科布及“杰科布定律”。关于“银贵钱贱”问题,疑惑的何止林则徐一人,笔者相信,一代代皇帝和世代业盐的长芦盐商们也一直在疑惑:为什么朝廷“每钱一千,直银一两”(49)的定制就是不管用?为什么转手之间,成千上万两的银子就能无声无息的消失?杰科布(Jacob William,1762-1851)是一位英国商业家,著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50)。“杰科布定律”具体表述为,“在动荡不安的时期,特别在内乱外患时期,金银器皿急速变成货币;而在太平繁荣时期,货币就变成食品用具和首饰。”(51)结合1841年在开封、1846年在陕西及1853年在安庆发生的三次“银贱钱贵”事件,王宏斌教授对该定律进行了解读。“在和平年代,由于政治稳定,社会生活安定和商品经济比较繁荣,金属货币的购买力较强,人们总是努力购买和贮藏金银器皿、首饰与珠宝等奢侈品。这种做法特别在东方民族(例如中国、印度和日本)中盛行。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是在内乱外患较为严重时期,在遭受自然灾害袭击之后,商品经济陷入严重混乱时期,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战争和自然灾荒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首饰和珠宝变成货币,将贮藏的金银取出来以便招募兵员和换取救命的粮食和衣物,这样一来,加入货币流通之渠的贵金属就会突然增多,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52)简言之,“盛世”时,银子赚到手之后,多被商人、地主囤积起来,不再进入流通领域。市面上的银子越来越少,兑换一两白银所需的铜钱也就越来越多。当然,诞生于二百余年前的理论有其适用范围,对于金属货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它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三)官方和盐商的一些应对措施
有清一代,“定制每钱一千,直银一两”。实际上,情况最严重的时候,一两银子可换制钱两千文(53)。官方与民间的银钱兑换比率相差如此巨大,买卖之间,盐商利益遭受巨大损失,以致有亏国课。盐商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国家和各级官吏也在思考应对之策,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曾考虑将官盐改为银两交易。“乾隆五十九年,巡盐御史征瑞、直隶总督梁肯堂奏,芦东商人因钱价过贱,以钱易银不无赔折,应交正杂引课,并帑本、帑利、运费等项,商力实属难支,请将盐价暂改卖银。”最终,乾隆皇帝没有同意该提议。直到咸丰四年(1854),该建议被打折后执行,盐商交纳国课的方式改为一半交银一半交钱。“至芦商疲敝,亦系实在情形,嗣后应交各款酌照端华等所议,准其五成交银五成以制钱二千作银一两交纳”(54)。二是收缴小钱。乾隆五十九年,长芦盐政征瑞于天津关设立收缴小钱局,晓谕过往客商赴关呈缴。乾隆皇帝将征瑞的做法在全国推广。“前因各省小钱充斥,曾经降旨通饬查禁,实力收缴,并令各关口一体留心查验,俾私贩咸知儆畏。第思此等奸徒贩卖,整千累百,捆载远行,必不肯由陆路贩运携带,多糜运脚,致有亏折,总由水路行走,便于装载。惟在责成各关津隘实力稽查,一体收缴,小钱方可净尽。著传谕各关监督于关津要隘处所,仿照征瑞办法,留心查验,并设立收缴小钱之局,一律查收,晓谕各商等赴关尽数呈缴,以清钱法而绝弊源。”(54)
三、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的群体衰落属于阶段性调整
乾隆时期,长芦商人报效、迎幸花费动辄数十万。传统的“专商”垄断经营与持续的“银贵钱贱”损害了盐业经营的根基。其实,从乾隆后期开始,长芦盐商就开始进入了群体衰落期,一个极具转折性的标志就是腰缠万贯的盐商开始借帑账了。乾隆五十年,长芦商人在捐银三十万两之后,破天荒的“请赏借库项,各商按引均摊,分限十年归款”(56)。进入嘉庆年间,盐商们的衰败越来越严重。据嘉庆五年六月十五日上谕,“长芦盐务素称疲乏,今于捐挑运盐河道需费不过一万余两,已须分限二年完纳,可见该处商力疲乏已极。著传谕观豫,嗣后惟当悉心调剂,以期商力渐臻饶裕,不可再有苦累为要。”(57)这次衰落是明显的,但对长芦盐商群体来说,只是一次阶段性衰落,属于经济规律对传统“引岸专商”垄断制度和“银贵钱贱”现象的自然调整。各方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回避这一“阵痛期”的到来。朝廷改盐商以五成交银五成交钱的方式交纳国课,在全国各关推广天津收缴小钱局的做法;盐商们则一方面“贿通”工部和户部,加重“掣盐砝码”,行盐时暗地里增加每引斤数,另一方面,销售时“死价活卖”,“盐商们和地方官达成了默契:1斤盐被定为14.5两”(58),试图将损失最终转嫁到国家和消费者身上;当然,消费者也有的选择,要么“淡食”,要么“食私”。“阵痛期”不可避免的到来了,长芦盐商破产的破产、被参革的参革,最终收不回来的是国课和帑本、帑息。为重新振兴盐务,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上《淮北试行票盐设局收税章程折》,拉开了清政府盐制改革的序幕(59)。在传统“引岸专商”垄断制度和国家不健全的货币政策等因素的打击下,以张氏、查氏为代表的旧盐商倒下了,以张锦文为代表的长芦新盐商走上了历史舞台。
注释:
①②芮和林.浅析乾隆时期长芦盐商走向衰落的原因[J].盐业史研究,1994,(4):22.
③[英]彼得·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289.
④[英]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87-88.
⑤徐景星.长芦盐务与天津盐商[J].天津社会科学,1983,(1):52-58.
⑥⑦(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一·谕旨一·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上谕[Z].
⑧⑨(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乾隆五十九年上谕[Z].
⑩(11)(清)崔旭.津门百咏·盐坨[Z].
(12)(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一·谕旨一·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上谕[Z].
(13)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盐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9.
(14)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盐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39.
(15)(18)王守基.长芦盐法议略(收录于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盐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35.
(16)关文斌.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247-248.
(17)(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一·谕旨一·雍正五年正月二十日上谕[Z].
(19)(20)(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上谕[Z].
(21)(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上谕[Z].
(22)(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初四日上谕[Z].
(23)(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上谕[Z].
(24)(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嘉庆四年三月十九日上谕[Z].
(25)(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嘉庆五年三月初六日上谕[Z].
(26)(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一·谕旨一·雍正九年六月上谕[Z].
(27)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盐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390.
(28)(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十·转运下·乾隆三十五年[Z].
(29)(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十·转运下·乾隆三十六年[Z].
(30)(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六·优恤·乾隆五十三年[Z].
(31)(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一·谕旨一·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上谕[Z].
(32)(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一·谕旨一·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上谕[Z].
(33)(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一·谕旨一·雍正元年八月上谕[Z].
(34)(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乾隆元年三月上谕[Z].
(35)(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嘉庆五年三月初六日上谕[Z].
(36)来新夏.天津近代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5-6.
(37)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盐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21.
(38)(清)法式善.陶庐杂录[Z].北京:中华书局,1959:23.
(39)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盐法·邸钞[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9.
(40)周育民.银贵钱贱对中国外贸的影响[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2):130-136.
(41)许立新.略论鸦片战争前后银贵钱贱的原因[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5):15.
(42)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盐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381.
(43)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盐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391.
(44)(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六·优恤[Z]:95-96.
(45)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三·志九十八·食货四·盐法[Z].
(46)(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三十二·盐法[Z].
(47)(清)叶梦珠.阅世编[Z].北京:中华书局,2007:174.
(48)(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嘉庆四年四月上谕[Z].
(49)(清)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卷十九[Z].(转引自:王宏斌.乾嘉时期银贵钱贱问题探源[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2):86.)
(50)(51)王宏斌.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J].史学月刊,2006,(9):35-41.
(52)王宏斌.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J].史学月刊,2006,(9):35-41.
(53)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盐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27.
(54)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盐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27.
(55)(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Z].
(56)(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乾隆五十年九月初四日上谕[Z].
(57)(清)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二·谕旨二·嘉庆五年六月十五日上谕[Z].
(58)关文斌.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60.
(59)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盐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