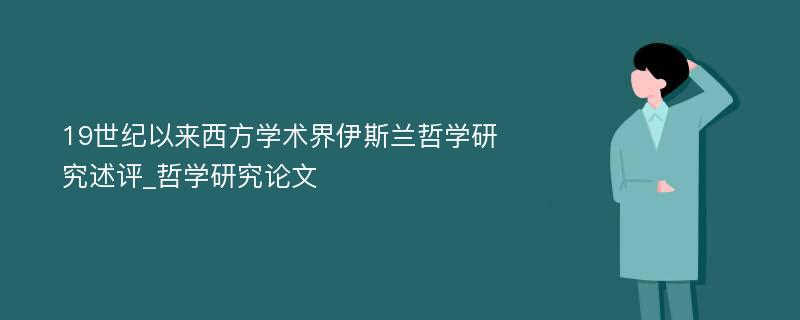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学界伊斯兰哲学研究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学界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0)01-0132-10
对伊斯兰哲学的研究不仅在伊斯兰世界,而且在西方也有很长的一段历史。在西方,伊斯兰哲学研究传统已近千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是中世纪时期对阿拉伯文著作的翻译、分析和研究;在中世纪成果的基础上,文艺复兴时期掀起了翻译和研究的第二次浪潮;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对伊斯兰哲学的研究,真正始于19世纪,并延续至今。在这段很长的历史中存在着某种连续性,而且这三个阶段之间是相互连接的,但是其中也有中断。本文主要关注最后一个阶段。此外,我们将“哲学”理解为具有传统伊斯兰根源的哲学(al-falsafah)或神圣智慧(alikmat alilāhiyyah,神授智慧),而非现代欧洲语言中“哲学”(philosophy)的一般意义,哲学(al-falsafah)或神圣智慧可以扩展到经注学(Quranic commentary,tafsīr and ta'wīl)①、宗教原理(principles of religion,usūl al-dīn)、法学原理(principles of jurisprudence,uūl al-fiqh)、苏非之道(Sufism)、自然科学、语言学等其他许多传统伊斯兰学科之中。
在欧洲语言的一般用法中,“哲学”(philosophy)让我们想起的是与普遍原则相关的某种东西,它对推理规则、概念定义、事物的起源、目的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智慧进行规定,而且我们不仅可以讨论纯粹哲学,也可以讨论艺术哲学、宗教哲学或者科学哲学。但是,在古典伊斯兰语言中,哲学(al-falsafah)是指一些特殊的学科,以及逍遥学派(Peripatetic,mashshā’ī)、光照学派(Illuminationist,ishrāqī)等一些独特的学派,恰恰不是指那些含有“哲学的”(philosophical)观念的思想派别。此外,在此后的伊斯兰历史中,神圣智慧一词在伊斯兰世界的东部地区广为人知,实际上与哲学(al-falsafah)同义,而在伊斯兰世界的西部地区,哲学(al-falsafah)这个古词还继续被用来指称“哲学家”(philosopher)的活动。但是,无论在哪个地区,这些词语总是被用来称谓某种特定类型的思想活动,穆斯林将这些思想活动与哲学或者与伊斯兰世界的西部地区翻译过来的另外一个词“神智学”(theosophy)②等同起来,而在伊斯兰文明中得以孕育,具有明显西方“哲学”(philosophy)意义的哲学因素的其他学科,却无法归入伊斯兰古典历史时期的哲学(al-falsafah)或神圣智慧中。必须加以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将此处的讨论限制为古典意义上的哲学(falsafah),但一定不要忘记它与苏非之道、教义学(theology,kālam)、法学、自然科学、数学、语言学等领域的关系。不过,这里我们将不会讨论这些学科本身或者这些学科中所包含的西方意义上的哲学。
在伊斯兰文明的语境中,哲学虽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学科,但它既与科学又与苏非之道、教义学密切相关,同时,它也在处理人类生活实践方面的领域中,尤其是在政治学和法学领域中有其分支。前期伊斯兰哲学家(主要是追随亚里士多德)以古典方式将“诸知识科学”(intellectual sciences)也就是哲学划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前者包括形而上学、自然哲学(physics)、数学和逻辑学,后者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古典意义上的),这揭示了哲学与不同学科领域以及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某些分类中,科学甚至包括教义学、经注学以及法学原理这些宗教学科。这些领域不仅像通常所理解的哲学那样,拥有其自身的“哲学”(philosophy)——哈里·A·沃尔夫逊(Harry A.Wolfson)在凯拉姆哲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③,而且,falsafah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对于这些学科在诸多方面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正是这第二个特征——任何关于伊斯兰哲学研究的完整论述都具有这个特征——需要一种跨学科的进路,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取得丰硕的成果。
19世纪以来,在西方学界的伊斯兰哲学研究史中,有几个学派引人注目。首先要指出的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在西方学界的各种进路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天主教学者培育的基督教学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特别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Vatican Ⅱ)之前,这些学者在托马斯主义或新托马斯主义的基体(matrix)内依然延续着中世纪的伊斯兰哲学研究,而在梵二会议之后,托马斯主义研究本身在许多天主教研究圈子里也已日薄西山。其中艾蒂安·吉尔松(Etienne Gilson)、莫里斯·德·伍尔夫(Maurice De Wulf)等一些学者,主要依靠的是拉丁文译本的伊斯兰著作,而且他们只关注伊斯兰哲学在拉丁经院哲学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路易斯·玛西侬(Louis Massignon)、高松(A.M.Goichon)和路易斯·加迪(Louis Gardet)等学者则非常熟悉阿拉伯文资料和伊斯兰思想的一般框架④。此外,西班牙有一支比较特殊的天主教学者,他们将某种意义上的“西班牙式身份”和对天主教神学的依托结合在一起。这个学派有米格尔·阿辛·帕拉西奥斯(Miguel Asín Palacios)、米格尔·克鲁兹·赫尔南德兹(Miguel Cruz Hernāndez)、冈萨雷斯·帕伦西亚(Gonzales Palencia)等许多知名学者,他们对伊斯兰哲学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具有创见的思想和研究主要限于西班牙和马格里布地区。伊斯兰科学思想史家米拉斯·瓦里克罗萨(Millās-Vallicrosa)、胡安·维内特(Juan Vernet)由于其西班牙出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一群体,尽管他们与天主教思想的关系并不密切。
在天主教学派的漫长历史中,可以与其相提并论又出于同一类型学术背景的学派是犹太教学派,此学派直接或间接地具有拉比训练(rabbinical training)和中世纪犹太教经院哲学的根基,其中又间或混有西方人文主义学派的因素。这个学派在19世纪产生了莫瑞茨·斯泰因施耐德(Moritz Steinschneider)、索罗门·蒙克(Salomo Munk)等著名学者,并在20世纪早期继续涌现出依格纳兹·高登兹赫(Ignaz Goldziher)、文森克(A.J.Wensinck)、扫罗·霍洛维茨(Saul Horovitz)、哈里·沃尔夫逊、欧文·I。 J·罗森塔尔(Erwin I.J.Rosenthal)、乔治·维亚达(Georges Vajda)、西蒙·范·德尔·贝格(Simon van der Bergh)、施洛莫·皮内斯(Shlomo Pines)、保罗·克劳斯(Paul Kraus)和理查德·瓦尔泽(Richard Walzer)等一批非常有名的伊斯兰哲学研究者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伊斯兰思想研究者。但是,巴勒斯坦分治带来的政治动乱,改变了许多(但不是全部)具有这类背景的学者对伊斯兰哲学和传统犹太教思想的态度,他们在解释传统形式的伊斯兰思想时,鲜有同感和共鸣。
上述这两个群体的学者的研究进路有着重要的相似性,这是因为传统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哲学和神学方面本身就具有许多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它们与伊斯兰思想具有某些基本的共同特征。与这两个群体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学者群出现在19世纪后期的舞台上。他们的思想背景不是基督教或者犹太教的经院哲学,而是现代欧洲哲学,他们试图用那个时代西方所通行的各个流派的思想来理解伊斯兰哲学的内容。先是恩斯特·勒南(Ernst Renan),然后是利昂·高德(Léon Gauthier)——他的目的是让伊本·路世德(Ibn Rushd)成为理性主义之父,接着是亨利·科宾(Henry Corbin)——他利用现象学的洞见以及西方思想中较富隐秘性的(esoteric)潮流而进入伊斯兰哲学的内在意义,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将伊斯兰哲学看成是浸蕴在当时西方各个不同派别的哲学潮流和现代学术方法之中的思想家和学者,而不是那些受过中世纪哲学学术训练的著述者或者人物。不过,科宾确实非同一般,他除了对德国哲学特别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稔熟于心外,还受教于吉尔松门下,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方面极为渊博。勒南这一类的学者则受到了当时世俗论哲学的影响,这些哲学思想成为他们研究伊斯兰哲学的背景,这里也不能不提到20世纪前苏联以及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学者,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内写出了不少伊斯兰哲学的研究著作。
与这些群体不同,西方自19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东方学派,这些学者主要接受的是语言学而不是神学或者哲学方面的训练,他们从文本和语言意义上来研究伊斯兰哲学,但缺乏哲学和神学维度上的深层次理解。这个群体对许多重要文本的编纂认真细致,而在义理阐释方面却乏善可陈。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社会科学训练对语言学和历史学训练有所补益,而且有一定数量的著作是从西方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角度来讨论伊斯兰哲学的。但许多这类作品主要是与政治哲学而非纯粹哲学相关,尽管在伊斯兰思想中,政治哲学与纯粹哲学不能截然分开。
二战之后,西方逐渐认识到,这个世界上除了西方思想传统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思想传统。因此,以比较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学派开始崭露头角。在远东和印度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研究领域中,这种进路是相对成功的,有些学者也随之开始转向,他们是在同西方思想传统,有时是在同东方其他思想传统进行比较的语境中来研究伊斯兰哲学的。井筒俊彦(Toshihiko Izutsu)、牛田典子(Noriko Ushida)等以英文写作的亚洲学者以及亨利·科宾、加迪等人的著作,标志着这个极富潜力的研究领域的开端⑤。
最后,同样是在20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一个学派,开始将伊斯兰哲学当作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学派,而不是当作一种单纯与历史兴趣相关的东西来进行研究。西方人对东方传统中“关于存在”的新知识的内在需求,使得不少探索者在伊斯兰哲学传统中来解答现代世界在思想层面上所提出的种种问题。20世纪早期,伯纳德·卡拉·德·沃克斯(Bernard Carra de Vaux)、马克斯·霍尔滕(Max Horten)及其他少数几位学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伊斯兰哲学的智慧性内容。今天,这类研究逐渐增多,西方的科宾、加迪、吉尔伯特·杜兰德(Gilbert Durand),以及东方的纳斯尔、井筒俊彦、马赫迪·穆哈黑(Mehdi Mohaghegh)、纳库伊布·阿塔斯(Naquib al-Attas)等人对伊斯兰哲学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但又无损其学术特征的研究,对于那些觉察到西方文明的深刻思想危机,并致力于寻找西方文明之外的真正哲学知识的当代人来说,这类研究可以直接满足他们对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渴求。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发生了很多事件,揭开了西方学界伊斯兰哲学研究史和研究方法新的篇章。梵二会议的结果之一是托马斯主义在许多天主教研究圈子里日渐式微,从而让那些既植根于托马斯主义,又关注伊斯兰哲学的早期天主教学者的研究进路较为少见,尽管还有一些具有这种背景的重要学者,继续在伊斯兰哲学研究领域作出颇具意义的贡献,如戴维·伯勒尔(David Burrell)所做的工作。同样,早期一些受过老式拉比训练的犹太学者所进行的伊斯兰哲学研究也日渐稀少,虽然勒恩·古德曼(Lenn Goodman)、奥利弗·李曼(Oliver Leaman)等懂得希伯莱文和犹太哲学传统的犹太学者们在继续作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伊斯兰早期哲学研究方面。
同样在这几十年里,欧洲大陆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哲学舞台开始分道扬镳,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在欧洲大陆,分析哲学在英美、加拿大分别占据统治地位,而解构主义也出现在20世纪后期的舞台上,但这两个世界的哲学思想对解构主义的解释也各有不同。此外,西方新一代的伊斯兰哲学研究者开始出现,严格说来他们不是哲学家,但由于思想背景和教育训练的缘故,他们受到了各种思潮的影响。也是在同一时期,由于科宾、井筒俊彦、纳斯尔等人前期的努力,伊斯兰哲学成为新一代西方研究者们的关注课题。
另外,在这几十年中,进行伊斯兰哲学研究并用欧洲语言写作的穆斯林学者急剧增加。穆欣·马赫迪(Muhsin Mahdi)、法兹勒·拉赫曼(Fazlur Rahman)、贾瓦德·法拉图里(Jawād Falatūrī)、马赫迪·海里·亚兹迪(MahdīHā’irī Yazdī)、纳斯尔等人执教于西方大学,门下穆斯林学生和非穆斯林学生无数。纳库伊布·阿塔斯等人则返回了伊斯兰世界,但主要还是用英文写作。此外,一批西方学生来到伊斯兰世界,对哲学及相关学科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学习,赫尔曼·兰杜特(Herman Landolt)、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威廉姆·柴提克(William Chittick)、约翰·库珀(John Cooper)等人在一般意义上的伊斯兰思想领域和具体意义上的伊斯兰哲学领域内成为众所周知的权威。事实上,上述这些学者和老一代的穆斯林学者以及侯赛因·孜艾(Hossein Ziai)、马赫迪·阿敏拉扎维(Mehdi Aminrazavi)等新一代学者,在西方学界的伊斯兰哲学研究领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对伊斯兰世界内部也产生了影响。今天,阿拉伯地区、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及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学生来到西方,师从于这些学者,在这个过程中,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尤为突出。因此,西方学界的伊斯兰哲学研究工作同伊斯兰世界自身的伊斯兰哲学的生命力是紧密相关的。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同样见证了具有生命力的伊斯兰哲学传统向西方哲学的渗透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法国尤其明显,这从克里斯蒂安·贾贝特(Christian Jambet)等年轻一代法国哲学家的著述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这又是科宾的影响所致。但现在我们也可以在伊安·奈顿(Ian Netton)、奥利弗·李曼的著作中看到,伊斯兰哲学与分析哲学⑥、符号学之间逐渐产生了相互影响。这些倾向导致英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研究中心,它不仅致力于伊斯兰哲学——特别是后期伊斯兰哲学的传播,也致力于伊斯兰哲学与西方哲学——特别是与分析哲学的互动。这个中心在伊斯兰青年哲学家戈拉姆·阿里·萨法维(Gholam Ali Safavi)的主持下,出版了刊物《超越哲学》(Transcendent Philosophy),由一批西方穆斯林青年学者构成作者群,他们对作为哲学的伊斯兰哲学和真正的比较研究都非常关注。
因此,西方学界的伊斯兰哲学研究领域比起20世纪前几十年来说有了极大的拓展。参考前述汉斯·戴贝尔的长篇文献目录就足以看到,每年都有大量用欧洲语言撰写的伊斯兰哲学方面的著作面世,其作者既有西方学者也有穆斯林学者,足以看到这一领域的学术活动在几乎所有的欧洲主要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都得到了拓展。但是,在伊斯兰哲学的学术研究中,是将伊斯兰哲学作为思想史并从西方的视角进行研究,还是将伊斯兰哲学看做具有生命力的哲学,这两种观点依然存在着巨大分歧;在对伊斯兰哲学传统的理解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是从这种传统的内部来进行考虑,还是像多数西方学者那样,仍然致力于将不断变化的西方哲学思潮中所产生的范畴,应用于这种在天启之国培育的传统之中,而且这种传统所关注的真理是超越并高于一时一瞬之潮流的。
事实上,我们在所有形式的传统哲学——它们是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不同表达——与各种现代哲学思潮的比较中都能够看到这种巨大分歧。20世纪永恒哲学的传统阐释者们,特别是勒内·格农(René Guénon)、阿南达·K·库玛拉斯旺米(Ananda.K.Coomaraswamy)、弗瑞斯约夫·舒昂(Frithjof Schuon)都坚持认为,在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⑦。他们对现代思想的批判和对居于永恒哲学核心之处的传统形而上学与宇宙论的阐释,引导许多年轻一代的学者去从事真正的伊斯兰哲学研究,但是传统学派的学者们还无法彻底根除心灵的失真和对智性和知识本性的错误预设,而这种失真和预设让很多进行伊斯兰哲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无法掌握伊斯兰哲学——一种觉知到天启之实在的哲学——的真正本质和意义。
许多西方学者所坚持的理论视角,是不会被那些归属于伊斯兰思想传统并生活在这种思想传统框架之内的人所接受的,但除此以外,从事伊斯兰哲学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对这一研究领域作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贡献。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他们对东西方的许多图书馆进行编目,发现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伊斯兰哲学手稿。今天,几乎所有西方的重要图书馆都做了很好的编目,只有少数例外,例如梵蒂冈图书馆的若干部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期望在这类图书馆里会有伊斯兰哲学手稿方面的重大发现,尽管这种可能性也一直存在。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几乎每年都会发现新的重要手稿,伊朗和土耳其的藏书编目甚至比其他多数伊斯兰国家做得更好。如果印度、巴基斯坦、叙利亚、也门、马里及其他国家的图书馆——更不用说遍及伊斯兰世界的私人藏书——能得到更好的编目,那就很有可能在哲学手稿方面有更多地发现⑧。西方学者已经在手稿编目的学术方法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这些方法不仅为他们自己所用,也被福阿德·塞兹金(Fu’ād Sezgin)、穆罕默德·塔奇·达尼施帕朱赫(Muhammad Tāqī Dānishpazhūh)等穆斯林专家,在更大的范围用来编辑手稿。这类学术活动虽然经常为哲学研究者所忽略,但它在为伊斯兰哲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提供基础性文本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与此密切相关的领域是对手稿修订本的校正与处理。在传统伊斯兰世界中,通常传授给学生的伊斯兰哲学的重要文本,如伊本·西那(Ibn Sīnā)的《治疗论》(Healing,shifā’)或者穆拉·萨德拉(Mullā Sadrā)和阿西尔·丁·阿布海里(Athīr alDīn Abharī)的《指南注》(commentary upon the Guidance,Sharh al-hidāyah)等,在教师讲授的过程中就得到了修订,在传授书写文本时,总是要涉及现存的口授传统。印刷术在伊斯兰世界出现后,受过伊斯兰哲学传统训练的学者们用石版印刷了一些文本,后来还用现代方法进行了印刷。但是,也有大量瑕疵本开始以印刷形式出现,现在情况仍然如此。
从19世纪后期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开始修编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哲学文本,亨利·科宾所指导的弗兰克—伊朗研究所(Institut Franco-Iranien)的《伊朗文库》(Bibliothèque Iranienne)系列就是一个例证。通过与西方学者的长期合作,穆斯林学者们学会了如何修编文本,在口授传统日益少见的情况下,这些工作更显必要。这项工作现在主要是由阿拉伯、波斯、土耳其以及其他穆斯林学者来完成,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对这些著作进行修订的重要意义。可惜,直至今日,还没有对任何一位重要伊斯兰哲学家,在其已知全部手稿的基础上,出版过其所有著作的修订本。毋庸赘言,这个缺陷需要早日克服。同时,那些经过修订并且可信的伊斯兰哲学著作的印刷本之所以得以面世,要感谢西方学者在这个领域所做的直接或间接的正作。
如果不把一些基本著作译为欧洲语言,伊斯兰哲学知识就不可能从通晓伊斯兰语言的学者的小圈子里传播出去。不少西方学者为此作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在过去50年中,许多精通一门或者多门欧洲语言的穆斯林学者也加入了这项工作。但是同印度教或者佛教的著作进行对比,能够为西方读者所用的伊斯兰哲学文本的译作非常匮乏。具体就英文译作而言,不仅数量有限,而且一些基本的伊斯兰哲学著作也不完整,例如伊本·西那的《治疗论》和《指要与诠明书》(The Book of Directives and Remarks,al-Ishārāt wa’l-tanbīhāt)、纳绥尔·丁·图西(Nasīr al-Dīn al-Tusī)的《〈指要与诠明书〉注疏》(Sharh al-ishārāt)、穆拉·萨德拉的《四旅程》(The Four Journeys,al-Asfār al-arba‘ah)⑨。当然西方学者也有很多优秀译作,西蒙·范·德尔·贝格翻译的《矛盾的矛盾》(The Incoherence of the Incoherence,Tahāfut al-tahāfut)在很多方面可供效仿。其他可信的英文译作包括:阿尔弗雷德·艾维瑞(Alfred Ivry)翻译的肯迪(al-Kindī)的《形而上学》,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Vladimir Ivanow)和保罗·沃克尔(Paul Walker)翻译的伊斯玛仪派的若干哲学思想著作,理查德·瓦尔泽和弗里茨·W.齐默曼(Fritz W Zimmerman)翻译的几部法拉比(al-Fārābī)的著作,亚瑟·J·阿尔伯瑞(Arthur J.Arberry)翻译的拉齐(alRāzī)的《灵魂医典》(The Spiritual Physick)和《哲学本性》(The Philosophical Life),埃弗雷特·K·罗逊(Everett K.Rowson)翻译的阿卜杜拉·哈桑·艾米里(Abu’I-Hasan al-ā‘mirī)的《灵魂及其命运》(On the Soul and Its Fate,Al-Amad ‘ala’ l-abad),威廉姆·E·高尔曼(William E.Gohlmann)的《伊本·西那生平》(The Life of Ibn Sīnā)和亚瑟·J·阿尔伯瑞编辑的《伊本·西那哲学教义学文集》(selections of Ibn Sīnā’s philosophical theology),勒恩·古德曼翻译的精诚兄弟社的长篇书信集(a long epistle of the Ikhwān al-Safā’)以及伊本·图菲利(Ibn Tufayl)的《哈伊·本·叶格赞》(Living Son ofthe Awake,Hayy ibn Yaqzān)⑩,惠勤·萨克斯顿(Wheeler Thackston)翻译的苏赫拉瓦迪(Suhrawardī)的《奥秘集》(The Mystical Treatises),欧文·I·J·罗森塔尔翻译的《阿维罗伊注柏拉图〈理想国〉》(Averroes’ Commentary on Plato’s “Republic”),查尔斯·吉内库安德(Charles Genequand)翻译的伊本·路世德的《形而上学》,库兰德(S.Kurland)、哈里·布鲁姆伯格(Harry Blumberg)、希尔伯特·戴维逊(Herbert Davidson)、查尔斯·巴特沃尔斯(Charles Butterworth)翻译的伊本·路世德的逻辑学著作以及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疏,巴特沃尔斯还翻译了伊本·路世德的《决断集》(The Decisive Treatise,Fasl al-maqāl)(11),威廉姆·柴提克翻译的阿富达尔·丁·卡善尼(Afdal al-Dīn Kashānī)的译作选集,弗兰茨·罗森塔尔(Franz Rosenthal)翻译的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的《绪论》(Prolegomena,Muqaddimah)(12),詹姆斯·莫里斯翻译的穆拉·萨德拉的《宝座的智慧》(Wisdom of the Throne,al-Hikmat al-‘arshiyyah),柴提克翻译的穆拉·萨德拉的《灵知者的灵丹妙药》(The Elixir of the Gnostics,Iksīr al-‘ārifīn)(13),玛西亚·赫尔曼森(Marcia Hermansen)翻译的德里的谢赫·瓦里·阿拉(Shāh Walī Allāh of Delhi)的《关于真主的最终论证》(The Conclusive Argument from God,Hujjat Allāh al-bālighah)。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可信译作,以上书单仅起示例作用,并不完全(14)。此外还有很多以其他欧洲语言,特别是法文(15)、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俄文译出的作品。还有无数与伊斯兰哲学直接相关的哲学教义学和苏非学说的译作尚未在此引出。
如前所述,许多伊斯兰学者和阿拉伯基督徒在过去几十年中参与了伊斯兰哲学著作的英译工作。就英文而言,我们一定要提到穆欣·马赫迪,他是法拉比著作的编辑、注疏和翻译的重要权威,此外还有乔治·侯拉尼(George Hourani)、迈克尔·马穆拉(Michael Marmura)、马吉德·法赫里(Majid Fakhry)、赛里木·卡马尔(Selim Kamal)、卡罕(M.S.Khan)、法齐·纳贾尔(Fawzī al-Najjār)、沙姆斯·伊纳提(Shams Inati)、侯赛因·孜艾[有时与约翰·沃布里奇(John Walbridge)合作]、派瑞斯·毛维奇(Parviz Morewedge),这里提到的只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学者。还有不少具有伊斯兰背景的学者进行了重要的法译和德译工作(16)。
这些工作使得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哲学资源被译为欧洲语言,但是,如果不懂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就无法从深度上理解伊斯兰哲学。这个领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又被很多因素所牵制:许多重要原始文本缺乏修订编辑,缺乏哲学词典(17),最重要的是需要一批学者承担重任,译出令人满意的译作。最后这个因素又被这个事实所恶化:许多西方大学在考虑青年学者学术晋职的时候,甚至不把哲学译作这项时常需要胆识的工作当作学术性著作来看待。
对伊斯兰哲学来说,需要像洛布丛书(Loeb Library)整理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那样对著作进行编辑,一面印的是原文,对应一面印的是英文翻译。令人欣慰的是,过去几中年里,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着手出版了这样一套丛书,其中有少量伊斯兰哲学著作(18)。其他一些美国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这类著作(19)。为了让西方那些关注哲学的人在研究中用好伊斯兰哲学的主要文献,无论如何都要更加仔细和谨慎地进行翻译。此外,在为翻译专业性哲学术语选词时,一定要反映这个特点:伊斯兰哲学是与显现于天启之国的现实融合在一起的,它没有理性主义或者怀疑主义的特征,但是,很多从事艰苦翻译工作的人的头脑中却有这种倾向。不然,那句意大利谚语“翻译者即背叛者”(traduttore traditore)就会成为现实,而我们在许多伊斯兰研究领域(包括哲学在内)的大量译作中也确实看到了这一点。
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紧随某些哲学的发展而兴起于19世纪的西方,特别是德国。但是,古典时期的穆斯林学者很早就开始撰写有关伊斯兰思想家(包括哲学家在内)生平和作品的著作了。这包括巴格达迪(al-Bāghdādī)、伊本·哈兹姆(Ibn Hazm)、沙赫拉斯塔尼(al-Shahrastānī)等人撰写的al-Milal wa’l-nihal,意为真正的教派和思想或哲学学派,也包括伊本·纳迪姆(Ibn al-Nadīm)、伊本·阿比·伍赛比赫(Ibn Abī Usaybi‘ah)、伊本·齐弗提(Ibn alQiftī)、伊本·赫勒坎(Ibn Khallakān)、哈吉·哈里法(Hājjī Khalīfah)等人撰写的关于哲学家、科学家、教义学家以及其他名称的著作。此外,穆罕默德·沙姆斯·丁·沙赫拉祖里(Muhammad Shams al 姆·Dīn Shahrazūrī)⒇、古图布·丁·阿什克瓦里(Qutb al-Dīn Ashkiwarī)、穆罕默德·图纳卡布里(Muhammad Tunakābunī)等人的一些古典作品是专述哲学家的,包括前伊斯兰时期的哲学家。这些文献通常表现了前期伊斯兰著作中的知识,包括伊本·法提克(Ibn Fātik)、阿布·苏莱曼·斯基斯坦尼(Abū Sulaymān al-Sijistānī)等人所著的希腊和穆斯林哲学家的言论集,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包括了希腊作品,例如西奥佛雷特斯(Theophrastus)、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和盖伦(Galen)等人所著的希腊哲学家言论集。
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以上大多数传统伊斯兰哲学史著作,确认和强调了哲学最初是与天启相关联的,而且肯定了智慧(hikmah)是从赫尔墨思(Hermes)那里开始的,而他与先知伊德里斯(Idrīs)同为一人(21)。但是西方自19世纪以来撰写的伊斯兰哲学的研究著作却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前提和方法为基础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实证的历史主义,而且在哲学史方面几乎完全忽视了传统的伊斯兰理解方式。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学者开始撰写伊斯兰哲学史,他们经常称之为“阿拉伯”哲学,这是对中世纪的用法的沿袭(22)。从奥古斯塔斯·施莫德勒斯(Augustus Schmdlders)和索罗门·蒙克的开创性著作开始,伯纳德·卡拉·德·沃克斯、米格尔·克鲁兹·赫尔南德兹、德·莱斯·奥里尔瑞(De Lacy O’Leary)、古斯塔夫·杜盖特(Gustave Dugat)、利昂·高德、戈弗雷多·夸德里(Goffredo Quadri)等人以各种欧洲语言,撰写了大量闻名遐迩的伊斯兰哲学史著作(23)。其中在伊斯兰世界中影响力最大的著作是特吉茨·德·波尔的伊斯兰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m Islam)(24),这本书的英文版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是巴基斯坦和印度许多大学的标准教材,直到最近在某些地区仍然如此。
这些著作一般具有学术性质,但总是在其自身哲学传承的基础上,从现代欧洲的角度来审视伊斯兰哲学。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13世纪之后的伊斯兰哲学,好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大多数著作将它们所了解的伊斯兰哲学,甚至是前期伊斯兰哲学,即mashshā’ī或伊斯兰逍遥学派的哲学家们,视为中世纪欧洲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过渡,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价值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伊斯兰哲学同《古兰经》启示之间的关系,无视伊斯兰哲学自身与天启的渊源关系。
在20世纪的前60年到70年中,对哲学史的西方式进路有所了解的许多穆斯林也撰写了一些伊斯兰哲学史著作,但主要还是以当时的西方研究模式为基础的。其中一些著作对伊斯兰哲学与教义学、伊斯兰哲学与《古兰经》启示的关系的讨论,比他们的西方同行要多一些。一些阿拉伯文作品还提供了很多阿拉伯原始文本的信息,而这在西方的伊斯兰哲学史著作中是没有的。这一时期,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穆斯林学者都是阿拉伯人,例如穆斯塔法·阿布德·拉奇格(Mustafā ‘Abd al-Rāziq)、欧斯曼·阿敏(‘Uthmān Amīn)、易卜拉欣·马德库(Ibrāhīm Madhkūr)、胡萨姆·阿鲁斯(Husām al-ālūsī)、阿里·萨米·纳贾尔(‘Alī Sāmī al-Najjār),还有著述颇丰的阿布德·拉赫曼·巴达维(‘Abd al-Rahmān Badawī),他同时以法文与阿拉伯文进行写作。在这个群体中,阿卜杜拉·哈里姆·马赫穆德(‘Abd alHalīm Mahmūd)由于非常熟悉哲学(falsafah)与伊斯兰内在教义的关系,而尤显突出。有些撰写伊斯兰哲学史的著名学者是阿拉伯基督徒而非阿拉伯穆斯林。这个群体的学者有乔治·阿纳瓦提(George Anawati)、汉娜·法胡里(Hannā al-Fākhūrī)、哈利勒·加(Khalīl al-Jurr)等人。以阿拉伯文写作的伊斯兰哲学史经常包含着许多在欧洲学者的著作中无法找到的洞见和解析,但是大多数此类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无法摆脱西方学者的模式。特别是他们将伊本·路世德看做伊斯兰哲学的终结,伊本·赫勒敦只是被作为一个后记而添加上去的。这些作品其实和西方同类作品一样,忽视了整个伊斯兰哲学传统的后期。因此,它们也根本不会重视具有生命力的伊斯兰哲学传统。
20世纪60年代,伊斯兰哲学史的撰写发生了重要转折。亨利·科宾是第一个发现整个后期伊斯兰哲学领域的西方学者,他强烈反对出自19世纪欧洲哲学的历史主义,首先是他请我和一位长于苏非教义和哲学的叙利亚专家欧斯曼·叶赫亚(Osman Yahya)与他合作,为广受欢迎的《七星百科全书》(encyclopedic collection Pléiades)撰写一部伊斯兰哲学的历史。这项合作的成果就是《伊斯兰哲学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islamique)(25),很快被翻译为很多欧洲语言和伊斯兰语言,并极受欢迎。虽然这部著作只是我们计划中的第一卷,而且还终结于伊本·路世德的生平,但与其他以欧洲语言写成的伊斯兰哲学和伊斯兰哲学史完全不同,这部著作充分考虑到了哲学思辨与启示在伊斯兰之中的和谐关系。叶赫亚和我都没有时间去完成这项计划;所以科宾以一种相对简要的方式完成了这项工作,而且全本被译为英文(26)。
就在这本《伊斯兰哲学史》出版前两年,我在哈佛大学主持了关于伊本·西那、苏赫拉瓦迪和伊本·阿拉比(Ibn‘ Arabī)的三个系列讲座,在这些讲座中,我试图将这些伊斯兰的观点结合起来:哲学真理是无历史的,在伊斯兰的历史中,真正重要的是智性的观点(intellectual perspectives),而不是利用西方资源和伊斯兰资源所进行的缜密的历史性学术工作中研究的那些个人。我的讲座实际上是从伊斯兰哲学传统的内部,对西方的伊斯兰哲学编史学(historiography)的一种回应。这些讲座后来以《穆斯林三贤哲》(Three Muslim Sages)为题成书(27)。并被译为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乌尔都文、孟加拉文及其他多种文字,直到今天它还是许多伊斯兰大学和西方大学的研究文本,这部著作代表了具有生命力的伊斯兰思想传统与西方的伊斯兰哲学史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政府创立了一个由米安·穆罕默德·谢里夫(Mian Muhammad Sharif)主持的研究中心,由东西方学者合作编纂一部伊斯兰哲学史的巨著。这部著作最初打算沿袭西方的伊斯兰哲学史著作的做法,再增加关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艺术以及近期发展等篇章。1960年左右,我开始与谢里夫进行合作,并建议他增加后期伊斯兰哲学的篇章,他接受了这个建议,但要求由我来撰写这个部分。虽然这部著作在后来几十年里都是一部标准的参考书(28),并被译为多种文字,但相对来说,它还是一部拼凑而成的著作,而且在传统伊斯兰理解方式中的伊斯兰哲学与西方编史学中的伊斯兰哲学之间,没有作到一种令人满意的整合。
自20世纪60年代的关键几年之后,西方学者出版的大量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注意到了伊斯兰哲学传统的完整性。这类著作有米格尔·克鲁兹·赫尔南德兹的《世界伊斯兰思想史》(Historia delpensamiento en el mundo islámico)(29)和伊安·奈顿的《超越的真主》(Allāh Transcendent)(30)。但是这一时期在这方面最受欢迎并以英文独著的作品是马吉德·法赫里的《伊斯兰哲学史》(31),这部著作的初版仍然沿袭了以前欧洲和阿拉伯著作的特征,将伊斯兰哲学仅仅限制在某几个学派和伊斯兰思想的早期阶段。但是修订版已经连续将更大范围内的后期伊斯兰哲学传统包括于其中,尽管这部著作在有关波斯和印度的伊斯兰哲学晚近学派的章节上还略有欠缺。
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劳特利奇出版社请我和奥利弗·李曼主编一套两卷本的伊斯兰哲学史著作,其中也包括作为哲学史系列一部分的犹太教哲学一章。这项工作打算以历史方法和形态学方法为基础对研究主题进行处理,并对伊斯兰哲学同伊斯兰启示以及整个伊斯兰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的论述。我们又邀请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学者,基本上所有的工作都有大量不同背景的学者参与,也导致了一些不同的,有时是相冲突的观点。但是这部于1996年面世的题为《伊斯兰哲学史》的著作,现在也许是在这个主题方面被应用最广的书籍。在这部著作中,西方学者和伊斯兰学者共同合作,在彼此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在西方学术研究中,很少有哪个领域能像伊斯兰哲学史研究一样,对伊斯兰世界的哲学活动产生如此的影响。西方在这方面的著作一直影响着穆斯林,也一直在影响穆斯林对自己思想传统的看法。穆斯林所面临的危险是:哲学的意义的缺失和哲学与天启之间关系的断裂。一部全面的伊斯兰哲学史应该包括伊斯兰哲学的所有时期和所有思想学派,这些时期和学派应有伊斯兰哲学的维度,而且充分意识到哲学与天启之间的纽带关系,而这样的哲学史必须要对尚未充分予以认识的人物和时代进行更加专门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至少伊斯兰哲学史研究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它深深地植根于伊斯兰的本质及其思想传统之中。西方也开始以一种与以往不甚相同的方式来审视这个主题,更多地与伊斯兰的观点相符合。无论如何,西方对穆斯林如何理解自身思想传统所提出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穆斯林的回应之中颇具重要意义,而这种回应在深度和广度上又同未来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本文译自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自始至今的伊斯兰哲学:天启之国的哲学》(Islamic Philosophy from its Origin to the Present:Philosophy in the Land of Prophecy),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年版,第13—30页。限于篇幅,翻译时对原文有所删节。特此说明。
注释:
①文中凡是与英文并列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拉丁转化,均以斜体标出。
②theosophy,又译“神知学”、“通灵学”、“通神学”等。
③参见哈里·A.沃尔夫逊的《凯拉姆哲学》(The Philosophy of Kalam),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年。
④关于本章所提及的这些人物和后面一些人物的较为全面的文献信息见汉斯·戴贝尔(Hans Daiber)的《伊斯兰哲学文献目录》(Bibliography of Islamic Philosophy),2卷本,莱顿:布瑞尔(Leiden:Brill),1999年;伊斯兰哲学研究方面的参考文献和资料指南,见奥利弗·李曼(Oliver Leaman)的《文献来源导引》(A Guide to Bibliographical Sources),载于纳斯尔和李曼主编的《伊斯兰哲学史》(History of Islamic Philosophy),纽约:劳特利奇(New York:Routledge),2001年,第1173-1176页。
⑤如果比较哲学研究要取得成果并富有价值,而且这种研究还要同时涉及某种传统形式的哲学和后中世纪时期(postmedieval)的西方哲学这两个方面的话,那就必须要避开一些极为危险的隐患,并牢牢记住一些基本的原则。见S.H.纳斯尔的《伊斯兰与现代人的困境》(Islam and the Plight of Modern Man),芝加哥:ABC国际集团(Chicago:ABC International Group),2001年,第二部分《比较研究方法和西方对伊斯兰思想遗产的研究》(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the Study of the Islamic Intellectual Heritage in the West),第39-68页。关于比较哲学研究中经常发生的混乱状况,哈里·欧德米多夫(Harry Oldmeadow)写道:“这种混乱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无法理解某种关键的区别:一方面是作为一种神圣知识(scientia sacra)的形而上学,它同直接的精神体验结合在一起,并辅之以被启示的宗教教义,而另一方面,‘哲学’在现代西方通常意味着对一套论点和问题所进行的那种独立的、本质上是理性的和分析的探究。”《游历东方:西方宗教传统与东方宗教传统在二十世纪的相遇》(Journeys East: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Eastern Religious Traditions),布卢明顿:世界智慧书局(Bloomington:World Wisdom Books),2003年,第338页。尽管欧德米多夫在这本书里所讲的“东方”不包括伊斯兰世界,但是在比较哲学研究中涉及伊斯兰思想传统时,他的评述与此极为相关,并可进行替换。
⑥伊斯兰哲学与分析哲学在真正意义上的相遇的根源,应主要归于马赫迪·海里·亚兹迪的开创性著作,其中一些被译为英文。见他的《伊斯兰哲学的认识论原理:体会的知识》(Principles of Epistemology in Islamic Philosophy:Knowledge by Presence),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⑦这些学者在传播传统学说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对西方更好地理解伊斯兰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重要作用。见纳斯尔的《知识与神圣》(Knowledge and the Sacred),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0页及以下。
⑧由谢赫·艾哈迈德·扎基·亚曼尼(Shaykh Ahmad Zakī Yamānī)在英国温布尔登创立的准则基金会(alFurqan Foundation)是西方致力于保护、编辑、出版伊斯兰手稿的一流机构。尽管没有专门致力于伊斯兰哲学,但自20世纪80年代努力开展活动以来,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它对许多图书馆编目工作的支持,已经让很多哲学手稿为世人所知。
⑨又译为《精神旅行四程》。
⑩又译为《活生生的觉醒者之子》或《哈伊·本·叶格赞论东方哲理的奥秘》。
(11)又译为《宗教与哲学相契论》。
(12)又译为《历史绪论》。
(13)又译为《灵智者的哲人石》。
(14)关于被译为欧洲语言的著作的更为完全的信息,参见前引戴贝尔著作,书中随处可见。
(15)就译著而言,在伊斯兰哲学的某些领域中,法文甚至比英文的更为丰富。包括伊本·西那和苏赫拉瓦迪等重要人物。
(16)参见前引戴贝尔著作,其译作均载于文献信息人名之下。
(17)事实上,没有一部与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相对应的英文哲学词典是令人满意的。这类著作中唯一可用的就是苏海勒·阿富南(Suhail Afnan)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哲学词典》(A Philosophical Lexicon in Persian and Arabic),贝鲁特:东方家园(Beirut:Dar el-Mashreq),1969年。但是,这部词典的词汇根本不够,特别是涉及后期伊斯兰哲学学派的一些专门词汇。
(18)目前面世的著作有:安萨里(al-Ghazzālī)的《哲学家的矛盾》(The Incoherence of the Philosophers),迈克尔·马穆拉(Michael Marmura)翻译,普罗沃:杨百翰大学出版社(Provo: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ess),1997年;安萨里的《光之壁龛》(The Niche of Light),戴维·布克曼(David Buckman)翻译,1998年;苏赫拉瓦迪的《光照智慧》(The Philosophy of Illumination),侯赛因·孜艾翻译。
(19)参见侯赛因·孜艾翻译的苏赫拉瓦迪的《光芒集》(The Book of Radiance,Partawnāmah),加州科斯拉梅萨:马兹达(Costa Mesa,CA:Mazda),1998年。还有大量的法文、德文本的双语著作,以及少量多年前被译为英文而以阿拉伯文出版的著作。其中最为有名的也许是理查德·瓦尔泽翻译的《法拉比论〈理想国〉》(Al-Farabi on the Perfect State,al-Frābī’s alMadīnat al-fādilah),牛津:克拉兰顿(Oxford:Clarendon),1985年。马赫迪和其他人在同时阅读部分阿拉伯文原作和瓦尔泽的某些译文后,对其提出了批评。但它仍然是一部重要的双语本。伦敦的伊斯玛仪研究所(Ismaili Institute)也着手出版了一系列主要与伊斯玛仪哲学有关的双语著作。
(20)参见穆罕默德·沙姆斯·丁·沙赫拉祖里的《神游乐园记》(Nuzhat al-arwāhwa rawdat al-afrāh),马克苏德·阿里·塔布里兹(Maqsūd‘ Alī Tabrīzī)翻译,穆罕默德·塔奇·达尼施帕朱赫和穆罕默德·萨瓦尔·马乌拉依(Muhammad Sarwar Mawlā’ī)编辑,德黑兰:科学文化出版社(Tehran:Shirkat-i Intishārāt-i ‘Ilmī wa Farjangī),伊历1365年。达尼施帕朱赫的长篇引论娴熟地讨论了古典伊斯兰文明中的伊斯兰哲学史的长期写作传统。
(21)参见《赫尔墨思与伊斯兰世界的隐秘写作》(Hermes and Hermetic Writings in the Islamic World),载于纳斯尔《伊斯兰的生活与思想》(Islamic Life and Thought),芝加哥,ABC国际集团,2001年,第九章,第102-119页。
(22)出于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关的非学术原因,这种习惯后来被从事哲学史研究的阿拉伯学者所采用。过去几十年间,穆斯林学者和一些西方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讨论这个主题时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伊斯兰哲学,但阿拉伯哲学这个词语在某些圈子里仍有市场,这主要是政治原因所致。
(23)这些著作的细节见前引戴贝尔著作。
(24)爱德华·R.琼斯将其从德文译为英文版《伊斯兰哲学史》,版本无数(首印于伦敦,1903年)。
(25)最早由伽利玛(Gallimard)于1964年在巴黎出版。
(26)由菲利普·谢拉德(Philip Sherrard)翻译,伦敦:克根·保罗国际(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3年。
(27)最早由剑桥的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现由纽约德尔玛(Delmar)的卡拉万书局(Caravan Books)出版。
(28)最早于1963至1966年由威斯巴登(Wiesbaden)的奥托·哈拉索威兹(Otto Harrassowitz)出版社以两卷本出版。
(29)两卷本,马德里:联盟大学著作(Madrid:Alianza Universidad Textos),1981年。
(30)伦敦,纽约:劳特利奇,1989年。
(31)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