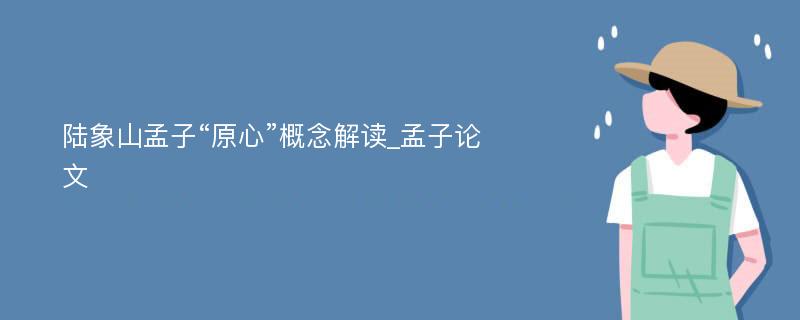
陸象山對孟子“本心”概念的詮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象山论文,本心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孟子》中,“本心”這個概念僅一見,(《孟子·告子上》“捨生取義”章)而論“心”之語則頗多,但本心即道德的本心,亦即仁義之心,故陸象山得以將之升舉爲其心學中的核心概念,乃至本體論的根源性範疇,並將孟子關于“心”的說法收攝于其中而一以貫之,對“本心”概念作豐富的詮釋。論及對孟子的繼承,象山自稱其學是:“因讀《孟子》而自得之。”①牟宗三先生說:“試觀象山論學書札,其所徵引幾全是《孟子》語句,其全幅生命幾全是一孟子生命。其讀《孟子》之熟,可謂已到深造自得,左右逢源之境。”②論及推進,陸象山自信地說:“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③且視伊洛諸公尤有不足,所謂:“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到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④“大段光明”具體何謂,這是本文要嘗試探討的。 另外,說到“自得”,這確實不是唯讀經典文本便可做到的,這需要在文本之外的實踐工夫,能够下學而上達的真儒,無不如此。孟子則早就說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離婁下》)明道亦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⑤象山就不用說了,陽明龍場悟道亦是如此。牟宗三先生說:“古人無不自幼而熟讀四書五經。然習焉而不察,不必能瞭解其中之實義。一個道德之實得于心須賴自己之獨悟。當其一旦獨悟而自得之時,其前所素習者好像不相干然。惟由于獨悟纔是一生中之大事。此中國往賢所以常常說實理所在,千聖同契,不是經由研究某某人而得也。然其所素習者亦不能說默默中無影響。故一經獨悟而實得,事後一經反省,便覺與往聖所說無不符契,就良知而言,便自然合于《孟子》也。”⑥順此,我們還可以稍微談談陸象山那個著名的“六經注我”說。 象山說:“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脚。”⑦這句話的獨特處,可以通過與程伊川的一句相似的話來比較顯示。伊川說:“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⑧伊川注重經典文本,不如象山究竟。在象山,心即是理,心具衆理;存得此心,明得此理,自然“六經皆我注脚”。扣實了說,六經皆此心之注脚。杜維明先生說:“在象山的心學裏,‘六經注我’有一定的存有論(本體論)基礎:‘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具是心,心皆具是理’。”⑨學者彭啓福亦說,“心即理”是心學詮釋學的理解根據論,它的核心在于“人一人”之間的共同性,它不同于聖經詮釋學中的“神一人”溝通,而近于强調對人類精神之理解的近現代西方詮釋學。⑩同時,我們認爲“六經注我”背後還有踐履工夫的前提,即“學苟知本”。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將“六經注我”簡單歸爲一種唯我論的詮釋方法——這正是象山所反對的:“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于其間,傷其本旨,乃爲善解書。”(11)當然,從它的基礎與前提也看到了它的適用範圍,即心性之學。又,“六經注我”說在孟子那兒其實是有傳統的,此即孟子所說的:“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中的“我”並非一般意義的我,它既是本體上的“真我”,也是工夫上明理後的我。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陸象山詮釋《孟子》的一個總體特點,即不只是停留在文本的傳注上,而是站在生命的相契、存在的呼應之基礎上進行創造性詮釋,這也是爲什麽象山能够“仿佛是別開生面”地啓動大家都熟悉的文本《孟子》,賦予它嶄新的意義。 二、“四端”與“本心” 象山講本心常常是大量引用《孟子》原話,並在後面綴上自己的評斷,從而使《孟子》文本全盤皆活,他自己就是“六經注我”的一個極佳典範。我們先來看象山是怎麽講“四端”與“本心”的,《象山年譜》載: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12) 起初,象山舉孟子“四端之心”來解釋“本心”,這已是“直截了當的正面說明”(13),但楊敬仲認爲這只不過是重複孟子的話,並没有增加自己對“本心”的認識。象山可謂善教,藉“扇訟是非”當機指點,使本心由一個抽象的概念轉而爲一個具體的體驗,而楊敬仲也當下便有覺。然而象山就其發用處或具體呈現處來指示“本心”,這與孟子以“怵惕惻隱之心”來指示“不忍人之心”並無不同,只差當下與否。面對相同的文本,象山的理解與楊敬仲的理解差別竟然如此大,看來在真生命上,象山必有與孟子相呼應的地方,用黄信二先生的話說,這纔使得象山能够透過文字概念的限隔,進入存在自身。(14)象山之所以能够如此親切、明白無誤地說出來,乃工夫自得使然。 試再看《象山語録》云:“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于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弃。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温柔,自寬裕温柔;當發强剛毅,自發强剛毅。所謂‘溥博源泉,而時出之’。”(15)很顯然,象山對《孟子》之“本心”的詮釋並非停留在“四端”字面上,而是已進入“主體實有”(16)的價值世界,“四端”是“本心”所發,而“本心”所發者又非只此四端,所以他又說:“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17)“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18)在象山看來,四端皆是本心所發,而本心則是道德情感本身,同時,它也是德性之基、行爲價值之源。 三、心即理 在象山看來,孟子的本心除有道德情感的維度外,也有道德法則的面向,故得以以仁義法則指稱“本心”:“道塞宇宙,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19)如果說從孟子的“仁,人心也”、“仁,人之安宅也”到象山的四端即本心,象山對“本心”的詮釋不至讓當時的學者産生什麽疑問或詫异感,那麽,以仁義直指本心,乃至說“心即理”,絶對是個具有震撼力的命題!然而,“心即理”說實已藴含在其《孟子》中,象山的獨特處在其畫龍點睛的本領。這一命題的正式提出是在《與李宰》書中完成的: “吾何容心”之說,即無心之說也,故“無心”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于五官最尊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20) 上面一段話幾乎全從《孟子》來,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一句乃象山的論斷。此真所謂《孟子》注象山、注“本心”,補出一段《孟子》心之諸說。按說象山所引《孟子》中的這幾句話確乎並没有什麽特別之處,大家都耳熟能詳,千五百年來無數學者讀及此等處並未覺得有何不妥,更不可能得出象山式的結論。主“性即理”的伊川與朱子,面對此數句自有不同于象山的解讀,象山之所以爲象山就在于他有這種領悟,洞見人之所不能洞見。如前所說,這種洞見並非完全是文本問題,而是還有讀者自身的緣由。 就文本而言,牟宗三先生以爲,象山“心即理”說“本于孟子之言‘仁義內在’以及‘心之所同然’乃至‘理義悅心’等。”(21)就直接的文本徵引來說,並不能說象山“心即理”說有取于“仁義內在”,儘管它與“心皆具是理”意思一樣。除了象山此處未摘引“仁義內在”一語外,牟先生本人也談到,象山之所以勸學生不要强思辨,“恐力量未到,反惑亂精神”,恐怕連象山自己也講不清楚這“生之謂性”。(22)象山没有把握恰如其分地剖析清楚“仁義內在”說相關章節所講的意思,因而也没有引用相關章節的討論文本。 就讀者自身而言,象山是自得者,能讓《孟子》文本“血脉自流通”(23),使之活躍于吾人眼前。象山說: 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24) 象山所說之此心與此理,都是根源性的。四端皆是此理之體現,在前面引文中象山還說“四端者,即此心也”,可見根源性的此理即本心自身。而理有根源性的與派生性之別,此理是根源性的,仁義禮智是派生性的。象山講理,講四端,常常是不分情與理的,蓋兩者皆是本心之呈現而可指稱本心,理是就本心之規定我們的行事方向而言的,情是就本心之應物時的自我體驗而言的,兩者共同根源于此心。 綜上所述,象山“心即理”的命題完全是對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與“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孟子·告子上》)等命題的發明,到象山方說出“心即理”這一命題,與其說這是他所引之話與所作之推論使然,毋寧說是“從胸中流出者也”。 四、本心之靈明與超越性 象山說:“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25)又說:“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禀所蒙,習尚所梏,俗論邪說所蔽,則非加剖剥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26)孟子那裏尚未有以靈明來形容本心的說法,只有先知先覺、良知良能的說法,以靈明、覺照來形容本心,是理學家們的特殊講法,象山明確以靈明言本心,陽明亦言之:“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灾祥?”(27)這個靈明乃是一個主宰力,象山說:“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28)本心乃是一明覺而非只是一性理之居所,如伊川、朱子所說的那樣,理只是心之德而具于心者,在象山,心與性並無區別,此靈明或明覺亦非一“知覺運動”之爲經驗的生理之心。 象山承《孟子》而自得的本心不但有道德情感、價值、法則、明覺的性格,而且也是一個超越的(transcendental)而非經驗的或生理的本心。象山說:“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29)凡此,皆是順《孟子》而講本心之先驗性(a priori)或超越性,是良知良能,是天之所與而我固有者,並無新說法。又,象山尚有著名的“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的同心說、大心說。他說:“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30)可見,本心之非時空性,亦即非經驗性,乃是一超越的存在。同此,象山還說:“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容私而已。”(31)又說:“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32)如此等等。 綜上,象山以“心即理”簡約地將《孟子》中所有相關說法一以貫之,可謂至矣,此非真自得者不能也。孟子只說“仁,人心也”,“仁,人之安宅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象山則直說“心即理”。“心”在孟子那裏,其作爲道德法則之根源的地位雖然已有相當凸顯,但若非真相契者、真自得者,如象山,便不能直說“心即理也”。“心”到了象山這裏,直接明瞭地與仁、安宅等同,其作爲道德法則之根源的地位纔完全凸顯,由此,象山爲其心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本心的存有論意義 由上面的討論而來,陸象山說:“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33)本心不但是超越的,而且也是存有論的,此即盡心則知天、同天所顯示的。又,陸象山說:“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34)本心不但是道德的、超越的,也是存有論的,此由“萬物皆備于我矣”一語所彰顯。 對于孟子“本心”所藴含的存有論意義,象山有更明晰的發揮:“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35)“森然”者,秩序之謂也,此一句明確道出“道德秩序”即“宇宙秩序”(36),此爲孟子所未明言而象山盛言之者;且象山是直接從本心的道德意義充其極而言其存有論的意義,孟子則是心性與天道“遙契”者。這樣,本心在象山那裏不但是道德實踐的根據,也是宇宙生化的本體,此兩者是一本。 對此一體之兩面,象山有充分發揮:“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缺。當惻隱是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温柔時自然寬裕温柔,當發强剛毅時自然發强剛毅。”(37)朗現的本心,原是道德實踐與宇宙生化不分的,此時的萬物不是現象意義上的對象,乃是以物自身的姿態出現的萬物,是“道德主體透過其自由意識所開顯的價值界域”。(38)又《象山年譜》十三歲條載:“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39)在本心之靈明朗照之中,宇宙與本心融爲一體,已不再是與我相對的僅具有物質結構身份的宇宙,而是道德的宇宙。(40)牟宗三先生說:“在圓教下,道德創造與宇宙生化是一,一是皆在明覺之感應中一體朗現。是故象山云:‘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此全物從事也,而事彰物亦彰。明道云:‘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離此個別有天地之化。’此全事從物也,而物彰事亦彰。”(41)化即是事,事便是化,此是象山“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之意。 綜上,象山將《孟子》中的本心概念凸顯爲一個本體宇宙論的根源性範疇,這是孟子所未明言、盛言者,而亦是象山心學之所以爲心學的關鍵所在,此非見道之明者不能至,非本《孟子》立說者不能至。 六、簡單的哲學史考察 爲了對陸象山的詮釋進行立體考察,凸顯其殊特性,我們有必要通過與部份相關學者進行簡單的比較研究——這裏我們選取理學家中的三位有代表性的詮釋者,即程明道、朱子與王陽明。陸學宗本《孟子》,而其大背景則是理學,由前者可以見出他作爲理學家的特殊處,由後者可以見出他對孟子學的創造性繼承處。 (一)與明道比較 一般來說,象山雖然不是繼承明道而來,但大體上又都承認他們之間有較大的親緣性,這種親緣性可以通過象山自己的話證實。象山于諸子分判得明白,他說: 讀《論語·學而》,即疑有子三章。及看《孟子》,到曾子不肯師事有子,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等語,因嘆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如此。又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云:“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蓋生而清明,有如此者。(42) 孔門惟顔、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顔、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從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43)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卻疏通。(44)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卻存,伊川已失此意。(45) 由此亦可看出,他不但與明道有親緣性,而且因見道之明而成爲第一個明確分判二程的理學家,從而開啓了狹義的理學與心學之分野,而這是明道自己也没有意識到的。儘管如此,明道與象山立說畢竟不同,試看明道論本心之語:“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46)又說:“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47)又說:“心與理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48)又,“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49)鵝湖之會上,陸氏兄弟有相互和詩,象山之兄復齋“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朋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50)與象山之兄相比,明道告神宗語到更加接近象山之體會:“明道告神宗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异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51)又《朱子語類》載:“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52)最後一條更像是象山與楊敬仲師徒倆的對話啓發。凡此皆說明程明道對本心的體會已相當接近象山,即對本心的道德意義與存有論的意義皆有說明,乃至簡易工夫論也與象山相近。惟不似象山那麽專本《孟子》、純由本心立說之凸顯,從而未能如象山之將本心之存有論的意義與道德的意義飽滿地撑開,所言本心的分量亦不如象山之多,故“草創未爲光明”之說並非毫無道理。但象山亦有不及明道者,即其“客觀一面不甚挺立”,未免“有虛歉之感”。(53)這是因爲“他是專以《孟子》爲主,其他經典乃是貫通而涉及者。自此而言,他與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五峰、朱子皆不同。此六子者,在立體方面,大體以《中庸》、《易傳》爲主”。(54) (二)與朱子、陽明比較 我們再來看看象山與朱子、陽明有何不同。朱子解釋《孟子》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55)又說:“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見性者略相似……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不异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56)在朱子,“心”雖是氣之靈,但另一方面只是一個儲存“理”的場所和一個形而下的知覺運動者,理與心的關係是:“仁固是心之德,但心之具此德並不是本心之必然地具與分析地具(本心之創發地具),而是綜合地具與關聯地具。”(57)朱子區分道德情感與道德法則,區分情與性,這使得他對心與性的關係的界定與象山大异其趣,象山說:“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事物,言偶不同耳。”(58)在朱子,心與理不真能爲一,這不但异于象山,也异于明道。 王陽明心學繼承的雖然也是孟子精神,但是他的自得經歷與象山不一樣,他是經由朱子之曲折而回歸孟子者。與陽明相比,象山的不足之處在其未能隨時代之需要,予以重新分解立義(59),如就心即性即理、知行本體等問題進行闡明,象山皆不如王陽明直接明晰。陽明言“心即理”云:“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60)這樣講比象山就表述得更加清晰明白了。然而,陽明不似象山專本《孟子》話語體系立說,陽明舍本心而言良知,將“良知”冒出來收攝四端,言良知之天理。陽明講良知亦是道德的意義與存有論的意義雙向撑開:“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61)又說:“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62)凡此,皆與象山的體會一樣,而更加顯豁。 通過上面的比較,我們的結論是:與明道相比,象山是專本《孟子》立說者,是純由本心而伸展至道德的形上學者,亦的確如他自己所說,更加光明、顯豁;與朱子相比,象山是心與理、心與性真能爲一者;與陽明相比,仍可見出他是專本《孟子》立說者,但其隨時代之需要而分解立義有所不足,義理闡明方面不如陽明清晰,陽明也可以說“孟子之學,至是而又一光”。 由前面的討論,我們比較清楚地展示了陸象山對《孟子》的繼承與創新處,現在再簡單地概括下。陸象山的本心是由孟子的四端之心、仁義之心而來,並且將之升舉爲一個本體宇宙論的概念,使之同時具有道德的意義與存有論的意義,後者雖然爲《孟子》所藴含,然而孟子並未明言,至象山,本心的存有論意義纔全部彰顯。牟宗三先生說:“然不得已,仍隨時代之所需,方便較量,象山亦有超過孟子者。然此超過亦是孔孟之教之所涵,未能背離之也。此超過者何?曰:即是‘心即理’之達其絶對普遍性而‘充塞宇宙’也。”(63)又說:“然孟子亦云‘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已涵及此義。孔子踐仁知天,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仁與天,心性與天,似有距離,然已含藴著仁與天之合一,心性與天之合一。此蓋時孔孟之教之本質,宋明儒者之共同意識。”(64)由此,我們可以說陸象山的創新是對《孟子》的調適上遂,充其極的發展,這就是“大段光明”的實義。綜上,孟子談本心以道德實踐爲主,其存有論的意義不甚顯豁;象山心學則是道德實踐與宇宙本體在其本心概念中一齊彰顯、飽滿撑開。 自二程而後,“天理”、“理”在宋儒那裏就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本體範疇,在理學背景下,象山須就“理”與本心之綜合關係作一說明。自此而言,“心即理”一命題,亦可謂隨時代之需要而重新“分解立義”者。在這個命題中,“心”與“理”皆有來自孟子的一面,這是其繼承性,但它們也有來自象山所處的時代的一面,這是其創新性。在孟子那裏,理或理義、仁義禮智等都是道德意義上的,尚不是存有論意義上的,至少這一點孟子没有明言。但在理學家這裏,“理”這個範疇所藴含的已超過“義”在孟子那裏的內涵,而具有存有論的意義。象山說:“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遁隱,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65)又說:“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凡此皆可見象山對《孟子》的發明。此外,象山與孟子所側重的亦不同,《孟子》中道德的形上學部份相對來說重視覺潤、生化,如言“養浩然之氣”、“睟面盎背”、“過化存神”,而象山論本心之存有論的意義則重視其秩序義,所謂“萬象森然于方寸之間”,這也是一個明顯的不同。另一個不同是,象山心學中的天人之際的距離或張力不如孟子强,導致天道尊嚴不顯。雖然,孟子學至象山而始光明天下。 ①陸九淵撰,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卷三十五《語録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71頁。 ②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8頁。 ③《陸九淵集》卷十《與路彥彬》,第134頁。 ④同上,卷三十五《語録下》,第436頁。 ⑤程顥、程頤撰,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上),《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24頁。 ⑥《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155頁。 ⑦《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録上》,第395頁。 ⑧《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第322頁。 ⑨杜維明撰,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卷五,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年,第130頁。 ⑩彭啓福:《陸九淵心學詮釋學思想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11届博士學位論文,第17頁。 (11)《陸九淵集》卷三十六《年譜》,第503頁。 (12)同上,卷三十六《年譜》,第487頁。 (13)郭齊勇編:《中國哲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92頁。 (14)黄信二:《陸象山哲學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9年,第223~224頁。 (15)《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録上》,第396頁。 (16)勞思光語,相關論述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三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86~289頁。 (17)《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録上》,第423頁。 (18)同上,卷一《與曾宅之》,第5頁。 (19)同上,卷一《與趙監》,第9頁。 (20)同上,卷十一《與李宰》,第149頁。 (21)《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2頁。 (22)牟宗三:《圓善論》,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第10頁。 (23)《陸九淵集》卷七《與彭子壽》,第91頁。 (24)同上,卷一《與曾宅之》,第4~5頁。 (25)同上,卷二十二《雜說》,第273頁。 (26)同上,卷十《與劉志甫》,第137頁。 (27)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卷三,《傳習録》(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1頁。 (28)《陸九淵集》卷一《與曾宅之》,第4頁。 (29)《陸九淵集》卷一《與曾宅之》,第5頁。 (30)同上,卷二十二《雜說》,第273頁。 (31)同上,卷十五《與唐司法》,第196頁。 (32)同上,卷二十五《詩》、《鵝湖和教授兄韻》,第301頁。 (33)同上,卷三十五《語録下》,第444頁。 (34)同上,卷一《與曾宅之》,第5頁。 (35)同上,卷三十四《語録上》,第423頁。 (36)關于“道德秩序”即“宇宙秩序”,牟宗三先生多次都有講到。這裏僅舉一例,即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14頁。 (37)《陸九淵集》卷三十五《語録下》,第455~456頁。 (38)李明輝:《牟宗三哲學中“物自身”概念》,見氏著《當代儒學的自我轉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36~37頁。 (39)《陸九淵集》卷三十六《年譜》,第483頁。 (40)郭齊勇編:《中國哲學史》,第294頁。 (41)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1册《現象與物自身》,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第460頁。 (42)《陸九淵集》卷三十六《年譜》,第481~482頁。 (43)同上,卷三十五《語録下》,第443頁。 (44)同上,卷三十四《語録上》,第413頁。 (45)同上,第401頁。 (46)《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王孝魚點校,第17頁。 (47)同上,第15頁。 (48)同上,第76頁。 (49)同上,第149頁。 (50)《陸九淵集》卷三十五《語録上》,第427頁。 (51)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第一册)第十三卷《明道學案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60頁。 (52)朱熹:《朱子全書》(第15册),《朱子語類》卷五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76頁。 (53)《牟宗三先生全集》第5册《心體與性體》(一),第51頁。 (54)《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2頁。 (5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39頁。 (56)《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一,第326頁。 (57)《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83頁。 (58)《陸九淵集》卷三十五《語録下》,第444頁。 (59)《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14頁。 (60)《王陽明全集》(上)卷一《傳習録》(上),第3頁。 (61)同上,卷二《傳習録》(中),第95頁。 (62)同上,卷三《傳習録》(下),第119頁。 (63)《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13頁。 (64)同上,第13頁。 (65)《陸九淵集》卷十一《與朱濟道》,第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