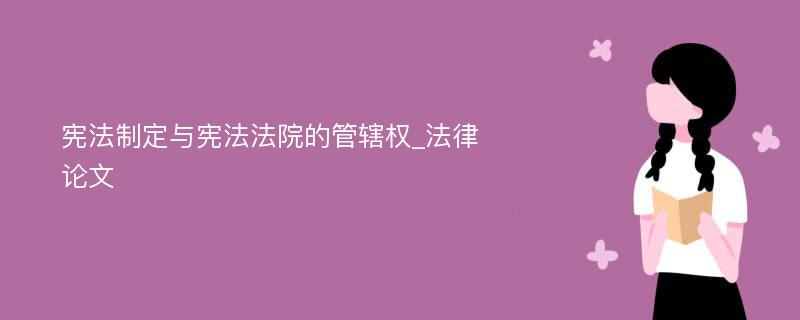
制宪与宪法法院的管辖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辖权论文,宪法论文,法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定宪法和宪法法院的管辖权”,这个题目几年前还是一个时髦的学术题目,人们可以脱离现实的日常问题喋喋不休地谈论它。但如今已不再是这种情况了。
一 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宪法法院审查联邦宪法的标准
肯定地说,很久以来,宪法制定者,更确切地说,联邦宪法的制定者(在此我仅想就他们与宪法法院的关系作一番论述)也受法律的限制(当然包括实在法上的限制,而不仅仅受自然法的限制)这已不成问题;这种限制在“宪法的基本原则”的表达中得到保证(注:关于这一点当然并非一开始就没有争论。相反,在战争时期,一些著名的专家,如鲁道夫·阿拉达尔·梅塔尔(《奥地利联邦国家法中的直接民主问题》,1930年,法律手册第245[246]页),所代表的观点是,宪法法院不能以更高一级的宪法尺度来审查联邦宪法。 而宪法法院于1948 年(汇编1607号)就作出裁决:由于联邦宪法137条至145条没有作出规定,它“无权在内容上审查依照宪法制定的各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今天,根据联邦宪法制订的法律必须经过宪法法院的审查,必要时可作为违宪被废除,这已是法律的基础知识。如果把这种(过分的)争论归咎于其法律本质,这就牵涉到对“法律”、“联邦法律”、“州法律”以及联邦宪法140条中的“违宪”这几个词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出, 梅塔尔的论点并非像今天人们一致认为的那样荒谬和没有代表性。)。由于在“正常”修宪和根据联邦宪法第44条第3 款对联邦宪法进行全面修改之间存在着宪法上的区别,所以就产生了这种情况。
(一)关于“全面修改联邦宪法”这一概念的最初解释
全面修改联邦宪法这一概念自1920年以来,在宪法解释者的理解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究其根源,可以发现,联邦宪法第44条第3 款(至1984年12月31日:第2款)明显是受瑞士联邦宪法(第20 条)“总体修改”概念的启示(注:瑞士联邦宪法的结论与此不同,但仍然需要经过某种程序,在那里对联邦宪法的任何修改都必须经过全民公决。)。但是瑞士的普遍看法把“总体修改”理解为公布新的宪法文本,原则上是对过去的宪法在内容上作重大修改,但不形成在概念上具有决定性的标准(注:见黑弗林——哈勒:《瑞士联邦国家法》1984年第272页。 关于此学说以前的情况,见施特雷:《全面修改宪法的概念》,法律公报,1935年第465(467)期。)。这符合比较宪法中典型的修宪概念而成为连贯性的宪法新文本。
凯尔森在其1922年的评论中(注:凯尔森——弗勒利希——梅尔克:《1920年10月1日的联邦宪法》(1922年)第124页。),把对奥地利“全面修改宪法”概念的不同解释视为可能解释的变种,而并未让人看出他的观点有任何优越之处。因此,在这一点上他始终坚持自己方法上的假定,即法学仅仅综合了各种正当合理的解释,而并不对其中的一种作出选择(注:凯尔森:《纯粹法学》(1960年)第353页。)。 凯尔森把一种可想像的全面修改的“物质性”概念理解为,对宪法中规定的国家制度,特别是国家形式的基础进行根本的改变,正如上下文关系所表明的(注:凯尔森——弗勒利希——梅尔克:《1920年10月1 日的联邦宪法》(1922年),第64页。),他指的是民主共和国,或“联邦国家的组织机构”。从而确立了联邦宪法(当时的)第44条和第2 款和此宪法开头两条之间的明确联系,当然由于使用了“特别是”这个词,这种联系重又失去了明确性。
(二)修宪学说的发展
以凯尔森之见,这种物质性的解释由于没有方法上的限制,可立即得到贯彻。然而,它却首先在两个方面受到了限制。其一是由于与联邦宪法前两条公告式的表述的紧密关联而产生的。按照以前的学说,联邦宪法第1条和第2条中宣告的民主共和国和联邦国家,被认为是符合受联邦宪法第44条第2款保证的宪法基本原则(在此, 我使用了一个现代术语)。但是,一项修改,即使是对此原则之一进行的重大修改,也不能被看作是“全面修改”,而只有这些原则在以下意义上的取消,即宪法经过相应的修改后,奥地利不再能视为一般国家学说意义上的共和国,民主或联邦国家(注:见厄林格:《对奥地利加入欧盟的看法》(1988年),第23页。),才可称之为“全面修改”。
当老路德维希·阿达莫维奇在其教科书(注:《奥地利宪法概论》(1947年),第70页。)的1947年第4版中, 第一次就法治国家原则加进他对民主和联邦国家原则的阐述时,与此书中关于民主共和国和联邦国家的章节不同,尚未提及全面修宪的可能。就连引用他的观点的作者,包括宪法法院(汇编1952年第2455号)也从民主共和国和联邦国家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法治国家的原则,从而使联邦宪法第44条第2 款与第1项和第2条之间在文义上的关系得到了解决。
随着与一项明显规范化的宪法基本原则联系纽带的断裂,法律想象力的障碍显然也被解除。不断有新的宪法基本原则被“发现”,以致于舍费尔(注:《奥地利的宪法解释》(1977 年), 第76 页。 )早在1971年就开始谈论“通货膨胀”。除了基本原则数量上的增加,每项原则的内容也愈来愈具体化,其后果是,不仅这些原则中的一项的取消,而且对这某一项原则的重大修改也被认为是对宪法的全面修改。
以下断言其实是很幼稚的:所有这些都已包含在1920年联邦宪法的文本中,而只不过尚未被宪法解释者们“认识到”而已。有人认为,当今达成广泛共识的这一切并未被理论以纯科学的方法所揭示,如同自然科学家揭示自然规律那样,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制定的文本被具体化了而已,而这中具体化过程隐含着极富创造性的因素。这一看法只能从一种朴素自然主义立场来加以驳斥,这种立场把语言文本与自然等同起来。贝克(注:贝克:《高水平的宪法与法治国家》,法律公报,1964年第300(301)期。)没有方法论上的顾忌,但十分中肯地触及了事情的实质。他谈到了“阿达莫维奇和宪法法院所提出的”民主、联邦国家和法治国家的三项主导基本原则。在这里,不是宪法的制定者,而首先是阿达莫维奇教授,然后是宪法法院,才能被称之为宪法主导原则的创造者。作为经验性陈述来理解,这一点决不允许出现错误。
按照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就决不能存在的格言(注:至于奥地利的国家法学在其特殊方法论前提上倾向于此,无需再证明的。人们当然不能对纯粹法学提出这样的指责,因为它的奠基人凯尔森和梅尔克恰恰清楚地看到并强调了每项法律的具体化中所包含的创造性因素。只不过他们持这样的观点:法律的具体化正因为其创造性内容,仅仅是经宪法授权的机构(法院和行政当局以及实施宪法的立法机关)的事,而不是法学的事。法学被限定在确定法律具体化的无可争议的范围之内。不管是凯尔森和梅尔克,还是他们的后继者,在他们的理论陈述中都没有严格坚持这种理论。这意味着传统法学理论的终结和我们法律体制内合理性的巨大损失,那是说,用系统论的术语来表达,它已经失去了功能性价值。有人提醒我们注意英国,美国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法学”现状,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在那里法官在整个法制内具有另一种价值,人们不能对一种法律体制的成份作孤立的比较。),我认为无视这种理论创造法律的作用是不合适的。但我认为,对理论的这一作用需要用一种同时进行的反思和公开的尺度来衡量。诚然,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还存在着某种不足。对宪法基本原则内容上的丰富更多地是以联想和纲要的形式进行的。对这种基本原则所作的深入,彻底和全面的分析——这种分析首先必须弄清各项原则之间的系统联系——迄今为止尚付之阙如。
二 宪法法院新近作出的法律裁决
宪法的基本原则尽管在内容上有了纲要式的丰富,但直到最近,它作为制宪的决定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仍停留在学术理论和学术思辩的云雾之中而没有实际的重要性。它标明了制宪最外部的界限,文明的宪法制定者无法突破的界限。在历来的语境中,对联邦宪法第44条第2款的引用, 通常不是被理解为对理智地权衡宪法补充的程序法需要的动力,即需要或不需要公民的参与,而是旨在预先阻止关于某次宪法修改的讨论。
这种情况可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当前展开的一项讨论是,几年后或许面临的修宪,即与欧共体签订一项协定,是否意味着全面修改宪法(注:厄林格对此的观点,见厄林格:《对奥地利加入欧盟的看法》(1988年),第19页。),而人们并未笼统地猜疑,持这种看法的人意在以此诋毁我国加入欧共体的行动。全面修改的概念已经失去了为制宪者划定不可超越的最外部界限的功能,而展示了必须认真考虑的可能性的前景(注:关于扩大直接民主的理由与作者所主张的全面修改宪法的理由类似,见黑格尔所著《在奥地利联邦宪法内扩大直接民主要素的可能性和界限》(1987年)。)。
更加有趣的另一种发展。近年来,在宪法法院的法律裁决中,关于可能全面修改宪法的议论越来越多(注:宪法法院1987年10月14日决议第267/86号,1988年3月3日决议第982/87号,1988年9月29 日决议第72/88号等。)。其中指责法院本身的并不常见,而更多的是指责修宪学说的,这些议论通常很少出现,几乎看不出什么学术论证的迹像。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必须成立一级法院预先对修宪学说进行研究,但如上所述,这种研究还远远不够。相反,如果批评者指责宪法法院新的“变动不居”的法律裁决方式构成了立法者和寻求法律帮助的公众感到不安的根源(注:舍费尔:《对葡萄酒的监督与联邦的间接管理》,行政管理杂志,1988年第361(372)期;另见贝希托尔德:《平等原则已陷入危机吗?》,《埃马科拉纪念文集》(1988年)第327(341)页。),那么在这一点上,人们几乎无法提出反对的意见。让我们回到将要与欧共体签订协定上来;签订这样的协定是否必须通过全民公决或根本不需要全民投票的问题,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联邦宪法第44条第3 款是否适用于国家条约(注:见厄林格:《对奥地利加入欧盟的看法》(1988年),第44页。)。每一本教科书都提到,关于这一点是有争议的。然而,在1987年10月14日就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6 条中关于公民权概念作出的著名决议中,基于欧洲人权法院对这一概念所作的扩展性解释,以近乎戏剧性的方式预示了全面修改联邦宪法的可能性。但法院并没有就国家条约进行全民投票问题作出解释。由于宪法法院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感到陌生,我从这一段文字中得出结论,它已经在考虑联邦宪法第44条第3款对国家条约是否适用。 作为一名建议对这一观念进行学术论证的学者,我虽然为此感到高兴,但也理解政治对法院作出明确说明的需要。
此外,在宪法法院的有关说明中还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之处,例如,按照在斯特拉斯堡施行的裁决实践,为全面修改联邦宪法而拟定的程序究竟怎样才能得到执行的问题。此外, 就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6条的文字举行全民公决,如同就这一公约的第4 条(涉及法院自身)进行公决一样是不合适的,然而,宪法法院却在斯特拉斯堡法院对这项规定所作的法律连续性的解释中看到了全面修宪的可能性,而这种解释按照条约文本和签约双方的意图是毫无根据的。正因为如此,宪法法院的上述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是含义模糊的,不利于法律的稳定。
不过,另外两项裁决,或更确切地说,两项综合裁决,对我的课题来说更加重要。在此,我只能对它们作简单的描述,好在它们已众所周知。
1.关于“汽车驾驶者讯问”的裁决
这项综合裁决涉及汽车驾驶条例关于“驾驶者讯问”的规定第 103条第2款。宪法法院于1984年和1985年分两步(见汇编9950和10394号)废除了这一规定(注:这种理由基本上是以联邦宪法第90条第2 款为依据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大胆。(关于宪法法院新近裁决中理由构思的“大胆”,见阿达莫维奇:《宪法法院的管辖权与权力分割》,《蔡德勒纪念文集》[1987年]第281[291]页)。这种理由实际上相当于创造一种新的不成文的基本权利——一种不必自责的权利。这使人们记起瑞士联邦法院关于“不成文的基本权利”的法律裁决。这家法院把宪法法院的功能理解为民主、法治和联邦国家根本秩序的保障者,并从这一理解出发,自认为被授权来建立和发展这种基本权利。见约尔格·米勒,《德国国家法教师联合会年刊》第39期(1981年),第67页。)。立法者显然对此并未作出积极的反应,而从根本上恢复了这项规定并且附加了一项宪法规定,以确保这一条例的实施(注:联邦法律公报1986年第106号,另见行政法院行政管理杂志1988年第4期,第1455页。)。尽管如此,宪法法院最近还是因公务原因,对汽车驾驶条例第103条第2款重新进行了审议。审议以不予终止(此项规定)并驳回行政法院的提案而告终(注:宪法法院1988年9月29日公报第72/88号。)。 宪法法院最终尊重宪法制定者在汽车驾驶条例第103条第2款最后一句中明确表达的意图,但对此有很大保留。关于这些保留,我下面还会提到。
2.关于出租车营业许可证的裁决
第二个综合裁决与出租车营业许可证有关。1986年,宪法法院终止了对临时交通法是否需要的审查,因为这种审查与自由就业权(见宪法第6条(注:宪法法院1986年10月第932号判决。))相冲突。这虽然不是对宪法第6条的第一次裁决, 但却是重新解释这一条的首批裁决之一,大约也是带来一系列后果的司法变革之一(注:见施托尔茨莱西纳:《经济法的宪法柜架及其通过宪法裁决的具体化》,《奥地利经济法杂志》1987年,第33页;另见诺瓦克:《相对性禁令与基本权利的保护》,《温克勒纪念文集》(1989年)第39页。),尽管它仅仅引发了事实上广泛得多的司法变革,特别是关于基本权利的司法变革的高潮。婉转地说,立法者对这项裁决的反应同样是迷惑不解的。联邦立法者是如此“处理”第一次取消有关法律(废料控制法第6条第1款)(注:宪法法院的裁决,1984年第10、179号。)的案例的, 以至于今后“取消”(注:联邦法律公报1985年第270号。 )某项法律变得不可避免(注:宪法法院1988年3月1日法规第79/87号,另见格里勒:《废料控制是违宪的吗?》,《奥地利经济法杂志》,1985年,第65期。)。与取消废料控制法时的做法一样,立法者再次试图以通过一项宪法规定的办法来废除临时交通法第5条(注:见联邦法律公报1987年第125号。)。
这项宪法规定(临时交通法第10条第2款第2段)授予州长规定在一个区里发放出租车营业许可证最高限额的权力,其方式是,现有停车位的数量(此数量根据规定是有限制的(注:《道路交通规则》第96条第4款。 ))与规定中所拟定的比例数相乘(注:经营许可证的这种发放形式与需求审查的结果完全相同(见冯克:《关于出租车经营许可证的发放或如何取消宪法?》,维也纳公报1987年第182(184)页。)。毫无疑问,这样一来宪法法院作出的裁决会流于一纸空文(注:邦联法律公报1985年第270号。诺瓦克的文章,《温克勒纪念文集》第68页。)。然而事实并不强调这一点,而是竭力掩盖事实上与宪法法院发生的冲突(注:见梅利夏尔:《宪法法院关于营利就业法需求审查的法律裁决》,《罗森茨威格纪念文集》(1988年)373(381)页。这使人想起了国民议会在对第二个国有化和赔偿法第12条进行“权威解释”(联邦法律公报1960年第3号)时的态度, 科恩和梅利夏尔曾指责这种态度是“在宪法决定的幌子下为所欲为”。)。宪法法院当然不得不承认事实,要求对宪法规定作出限制性解释,但这种解释实际上往往与宪法制定者的意图相去甚远。在本质上,这种解释的理由是,关于有人怀有限制宪法法院审查法律的职权和破坏基本法律秩序的意图的假定,将可能导致联邦宪法的全面修改,因此是不能接受的。这种理由巧妙地回避了与联邦宪法制定者发生公开冲突,但事实上,这种冲突并未因此而消失。
3.作为对宪法法院的反应,新近制定宪法的其他案例
宪法制定者对宪法法院裁决的另一种反应也许是完全失败的。我指的是关于限制最高机关退休金的那项联邦宪法法律(注:联邦法律公报1987年第281号。),该法律旨在纠正宪法法院关于政治家退休金(注:宪法法院1987年3月18日法规第255/86号;另见同日法规第253号, 第256/86号和第270/86号。)的著名裁决所产生的后果。这项联邦宪法法律全文如下:关于向受联邦或州的收入法规定管辖的机构发放的退休金或养老金,在得到审计庭监管的地方性实体或机构额外资助的情况下,最多只能以最高限额予以发放的规定有效。
宪法法院对此根本没有反驳,甚至明确地表示容许。但是,这类规定都是按照平等的原则(当然是一种很固执的解释)(注:见诺瓦克:《对候补资格免受宪法制订者干预的宪法保护》,《劳动社会法杂志》,1988年第109页。)来制订的。 而这项联邦宪法也并没有禁止它这样做。因此,在不改变裁决的前提下,法院尽管有联邦宪法的约束,在类似的情况下几乎无法作出与1987年不同的裁决(注:格罗夫——拉姆绍尔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见《奥地利法学家报》,1987年第705(710)期。)。这里根本不像在出租车营业许可证或汽车驾驶者讯问案例中那样,需要大胆的或甚至矫揉造作的思维方式。
第二个国有化法的修正法(联邦法律公报1987年第321 号)是制定联邦宪法的另一个极其有问题的举动。它不是对宪法法院行将作出的裁决的反应,而是对该裁决的预测:人们有理由相信,它有意抢在法律审议的前面。至于这一举动是否成功,人们当然已经表示了怀疑(注:林巴赫:《1987年修改后第2个国有化法的宪法问题》, 《行政管理杂志》,1988年,第577(585)期。关于制定宪法失败的另一个例子,见厄林格:《支持跨州的住宅建设,制定宪法的一个错误案例》,《奥地利经济法杂志》,1988年第33期。)。
三 制定宪法与宪法法院之间的界线
用宪法规定对宪法法院的裁决作出反应,在宪法政策上无疑是很成问题的。然而,决定性的法律问题是:这仅仅是一种不良的作风(纠正这种作风不是宪法法院的事),还是藐视宪法,即违反宪法的?
在前面提到的一些裁决中,人们的看法概括地说就是:这些宪法规定剥夺了宪法法院的审查权,而这是对宪法基本原则的侵犯(注:对此人们想起,宪法法院1978年(汇编8457号)是如何裁判的:“没有一条宪法规定禁止立法者按照其法律政策的目标制订新的规则,即使他们以此使最高法院对迄今为止的规则作出的裁判变得多余。即使新的规定导致了对最高法院法律裁决的修正,那么,立法者也有这种制定规则的自由”。见贝希托尔德最近发表的对此表示同意的文章,《埃马科拉纪念文集》第346页。 而对此持反对态度的有梅利夏尔, 《公法杂志》, 1961年第431页。)。
(一)宪法法院的管辖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此种看法不过把一个很复杂的题目简单化了。仅仅以下问题,即宪法法院审查各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权限,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宪法基本原则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相当复杂的,复杂到对此只能做出暗示。如果1920年向谁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人们肯定会根据那时我们对当时全面修改概念的理解,同时根据当时对宪法法院的管辖权的理解,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显然,当时人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人们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其中有问题。1920年的宪法制定者(国民制宪会议的成员)在考虑这一问题并将其记录在案(这种情况极为少见)时,将宪法法院的法律审查权视为在联邦和各州之间起一种仲裁作用的东西,即使不是作为联邦对州监督的工具(注:关于这一点详见厄林格:《宪法法院的管辖权与议会民主》,载《梅利夏尔文集》, 1983 年第125 (135)页。), 也是作为对“联邦法高于州法”的惯例的补充(注:在一篇刊登在1920年2月17日的《新自由报(由埃马科拉出版社印刷),题为《联邦宪法的诞生》的文章中,曾出现过一种观点,施密茨在《汉斯·凯尔森的指责赞同奥地利联邦宪法》中将这一观点归咎于凯尔森,并将其称作“一位奥地利法学家的立场”。这一立场也特别强调了联邦制——更确切地说——反联邦制的功能。》)。这在适用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最初提案权中已体现得很明显。凯尔森要求把通过官方途径对法律进行审查(这一表达比较笼统,不大精确,但核心是正确的)写入联邦宪法的文本,而政治家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补充将要产生的影响(注:埃马科拉(出版者)《关于奥地利宪法的起源》,1920年第 445页。另见凯尔森——弗勒利希——梅尔克,第259页。)。 然而对各项法律进行审查作为法治国家的功能,却植根于宪法法院对运用到别的场合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的权力之中。还在1930年前后便出现了一些声音,认为按照基本权利的标准对联邦法律或州法律进行内容上的审查,完全不符合法律中表达的民意,并主张将宪法法院的权力严格限制在划分联邦立法与州立法权限领域的范围之内(注:奥斯特利茨(1920至1930年为宪法法院成员):《审查宪法法院!斗争》,1930年第115 页。)。随着1929年的修正法把提案权扩大到行政法院和最高法院,宪法法院的这种权力当然也得到了明确的限定。但与今天的情况相比,宪法法院所作的法律审查工作事实上直至1933年都是微不足道的。从1919年至1933年,只有3项联邦法律和9项州法律被废除(注:罗森茨威格:《宪法法院与立法者——关于政治与司法之间的界限》,载联邦宪法60年萨尔茨堡研讨会论文集,1980年第100(106)页。)。这个数字低于1947年以后每一年平均废除的法律数,更远远低于近些年来的数字:1984年有19项联邦法律和9项州法律被彻销,1985年有19 项联邦法律和14项州法律被废除。
可以肯定地看出,根据人们对宪法的最初理解,宪法法院的法律审查权并未在联邦宪法第44条第2款(以及现在的第3款)的意义上成为宪法的主导原则。这样便出现了一个问题:随着提案权的扩大和其中体现出的宪法法院管辖功能的变化,法律审查权是否已被宪法的基本原则所确认。早在1929年或1975年以来,随着提案权的再次扩大以及其他一些重大变化(注:联邦法律公报,1975年第302号。), 这一点也许可以得到肯定。可是,如何将它与今后的修宪学说——这种学说原则上不接受宪法悄无声息的变化,并因此而要求为制订一项新的基本原则举行全民投票(注:瓦尔特:奥地利法学家报,1967年第2期,第54页。 )——协调起来呢?这些难题需要进行仔细的分析。
(二)宪法制定者“中止宪法法院”
何时以制宪行动“中止”宪法法院,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在前面描述过的案例中,这无疑是法律动议和决定法律是否能获得通过的和国民议会(法定)多数的明确意图。然而,这一行动与修改宪法(通过修改宪法,宪法文本中由于宪法法院的法律裁决而暴露出来的不足可以被清除)的客观区别在哪里?作为例子,我回忆起联邦宪法法院1964年关于确认根据宪法修改国家条约的义务的裁决,或1968年11月关于跨州的基本交通法的裁决(注:联邦法律公报,1969年第27号,另见梅利夏尔:《宪法法院与立法权》,《马尔奇科纪念文集》1974年第555 (562)页;又见梅利夏尔:《公法杂志》,1961年经423页。),它们都是宪法法院出人意料的判决(注:宪法法院的判决与裁定,1967 年第5521;5534号。)。最近按照宪法成立药剂师法庭的惩戒委员会, 或许可被看作是对宪法法院1987年10月14日作出的众所周知的裁决的反应(注:宪法法院1987年10月14日法规,81/86号等。),这项裁判也包含了一项宪法规定(注:联邦法律公报1989年第54号(药店法第19 条第7款)。)。在这些案例中,宪法制定者动机的纯洁性可能是没有疑问的,不过,也存在着难以判断的边缘性案例。例如,我想起将各州的法律宣布为符合宪法的具有“宪法效应的处置法”(梅利夏尔(注:梅利夏尔:《宪法法院与议会》,《加斯帕雷、 阿姆布罗西尼纪念文集》,1970年第1281(1299)页。又见梅利夏尔:《宪法法院与立法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载联邦宪法60年萨尔茨堡研讨会论文集,1980年第94(97)页:“立法机关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完全合法的”。)),尽管联邦政府赞同并公布了这项法令,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在执行它,但1963年(注:宪法法院的判决与裁定,1963年第4497号。)宪法法院仍然认定它是违反宪法的(注:联邦法律公报1964年第274号。)。由于这一修改, 宪法法院监督法律的权力明确地被取消,虽然这种取消仅限于某一方面,即公布法律的方面。
客观上说,通过每项宪法法令和每项宪法规定,作为一般立法的框架和宪法法院监督尺度的宪法权力得到了重新界定。这对于汽车驾驶法和临时交通法的宪法规定来说同样如此,这些规定又重新界定了宪法所保障的权利(总的来说比以前限制得更严)。但并不是每一项规定,即使是对一项基本权利限制性的新表述,都是对联邦宪法的全面修改。
因此,只有几个关于部分中止宪法法院权力的理论问题才意味着对联邦宪法的全面修改。为了准确地确定制定宪法与宪法法院的关系,人们的确还要进行根本性的思考。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宪法的基本原则,只有从这一原则出发,此种关系才能得到确定。而我也只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此粗略地加以阐述。
四 议会民主与司法的法律审查
(一)议会民主是宪法的指导原则
1920年的联邦宪法规定奥地利是一个议会民主的国家。1929年的修正法对这项基本决策作了修改,但并未改变其本质。这种民主的核心机构是议会。
在法国的宪法学说中,通过国民代表机构而实现的全民意愿在法律中得到体现,从而预先便赋予一项法律的几乎普遍愿望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和合法性的认定,即符合宪法,是理所当然的。正是从这种理解出发,将议会和法律理解为人民代表机构意愿的外在形式。宪法法院的管辖权在法国直到今天仍被保留着。瑞士的情况与此相似,只不过在那里根本的基准点是人民,而不是议会。在瑞典,宪法虽然赋予法院以依照宪法审查法律的权力,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家法院使用过这种权利。这不仅要用瑞典法律的质量(这些法律都是按照合理的程序制定的)来解释,而且也与法官们对法律合法性的尊重有关。当我1981年向法国宪法学家作关于奥地利宪法法院的管辖权的报告(注:厄林格:《基本权利保护的对象和范围——奥地利宪法法院》,载《欧洲宪法法院与基本权利》,1982年第335页。)并列举被废除的法律的具体数字时, 我无意中给扩大宪法委员会监督权的反对者,而不是支持者提供了论证上的帮助。当时在奥地利,人们还普遍认为,宪法法院是一个相当克制的裁决法院。
宪法法院审查法律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对纯粹议会制的限制以及对这一制度的修改。但“修改”并不意味着“废除”,尽管作了这样的修改,人们也没有必要就议会民主原则是否继续构成联邦宪法的总体结构进行严肃的辩论。因此,当问题涉及作为联邦宪法可能基本原则的宪法的法律管辖权的价值时,人们就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权力,相反,必须在宪法总的基本原则语境中来看待和评价它,换言之,它必须与议会民主的基本原则协调一致。
议会制的一个决定性衡量标准,或者,为了沿用一个与此并不完全相同,但与其涵义相近的概念,即法治国家的衡量标准。在法治国家中,议会的意志形成与理性保证的法律形式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意义上联邦宪法亦构成作为法治国家的议会民主——在于这样一个问题:谁最终拥有决定法制秩序的意义内涵的权力,是议会的立法者,抑或是法院。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存在着议会民主即法治国家,与法官国家之间的差别。
由于有了宪法法院的管辖权(在法官对法律进行审查的意义上),对宪法作出权威性解释的权力由普通立法者转移到了一家法院。如上所述,其中对议会原则有重要的限制和修改。但在修改中没有被取消的议会原则又要求,对宪法含义的最终决定权保留在议会(以宪法制定者的身份)那里(注:类似的观点见施潘纳:《奥地利法学家报》,1964年第2期,84页。)。
然而对纯粹议会制度的第二次修改,即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对宪法制定者作出的限制,也应该受到重视,它规定宪法制定者在全面修改联邦宪法时必须进行全民公决(联邦宪法第44条第3款)。 这里说的是对议会基本原则的限制,而不是取消。由此原则产生的结果是,全面修改的概念必须限制在对宪法的根本和广泛修改上,不能作为例外越出这一基本原则的精神来加以解释。否则,这种概念的延伸将使全民投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普遍的事情,使议会民主变为半直接的民主(注:里尔:《可能性》。)。根据这种考虑,近几年提出的某些关于可能全面修改联邦宪法的论点也许需要进一步审查,关于部分中止宪法法院职能的论点同样如此。
联邦宪法制定者的最终裁决权是通过对宪法法院的各项裁决作出反应,并对这些裁决定期作出更正的权力来实现的。联邦宪法制定者的这种最终裁决权构成了议会民主的精髓。因此,它的使用是以联邦宪法的构成规则为依据的,在这一方面不能与宪法的基本原则相矛盾(注:通过制宪行动;宪法裁决是可以修改的,这是奥地利宪法对法律司法审查的“重大问题”的回答(见卡佩莱蒂《司法审查的重大问题和比较分析》,载《欧洲一体化的法律问题》,97年第2页)。 这一重大问题涉及法律审查权的界限。这种权力赋予立法者以“最后决定权”,为此,立法者当然需要法定多数。宪法法院的作用被缩减到“上院”,即对“下院”作出的决定表示异议,这种决定可以被上院以一种特殊的程序来“否决”。而下院则必须对宪法法院的异议进行仔细的审议并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其最后决定权。下院在此范围内仅仅受选民和公众舆论的监督(见注释75。)。
(二)司法的法律审查是宪法基本原则的一部分
按照当今修宪学说和法律裁决的状况,人们也许会把完全废除宪法法院的法律审查权视为对宪法的全面修改(注:当然没有进一步论证,见阿达莫维奇——冯克:《奥地利宪法》第101页。)。 这个问题在人们蕴酿使法律秩序的许多部分脱离宪法法院的审查时就已经提出来了。随着问题的精确化,人们完全可以赞同已成为宪法法院裁决公式的表述:联邦宪法制定者中止法律审查权的各项规定在“效果”的积累上可能导致对联邦宪法的全面修改(注:宪法法院1988年9月29日法规,72/88号(关于汽车驾驶者讯问);1988年3月3日决议,第982/87 号(关于出租车营业许可证)。)。鉴于历史上形成的局面,这种表述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因此,仅仅强调法治国家的原则(注:阿达莫维奇——冯克:《宪法》,101页。)是不够的,因为, 在任何一种联邦宪法制定者可以依据的关于法治国家的理论纲领中,(集中的)法律审查都没有巩固的位置。相反,“奥地利宪法法院的管辖权制度”(注:卡普勒蒂:《当今世界上的司法审查》1971年第46页。)却是一种世界性的新创造,其法治国家的功能正逐渐展示出来(注:厄林格:《梅利夏尔纪念文集》第127页。),但决非一开始便确定无疑。
至于一种可能的论证将会是怎样的,我只能在给定的范围内作一些暗示。认定宪法法院的法律审查权是联邦宪法的指导原则(作为条件或全面修宪的积极的对立面),是基于一种价值,而宪法法院的这一管辖权在整体法律秩序的框架内的确可以实现这种价值。此外,对宪法法院期待的升值还因为议会的立法程序存在着缺陷,而宪法的法律管辖权可以弥补这些缺陷。在多党制和各种利益被有序地组织起来的国家里,议会并不像一种比较陈旧的完全指导着宪法制定者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由(法律上的基本权利)的保证者。社会的少数和局外人首先明白这一点(注:黑勒尔:《社会的局外人与基本权利》,载《罗森茨威格纪念文集》1988年第157页。)。 不论对宪法法院的管辖权期待增高的原因在那里,其价值在当今的法律秩序中如此之大,使得奥地利特色的法治国家的民主没有联邦宪法第140条便不复存在, 而变成另一种性质。然而,按照长久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对联邦宪法第44条第3 款的理解,这恰恰意味着对联邦宪法的全面修改。
对这种看法作理论论证肯定是困难的,因为宪法法院的管辖权在宪法的基本原则中达到了今天价值的那一点,并不能用某一特定形式的制宪行动来确定(因此对这一行动进行全面投票的要求未能实现)。但这一困难并不能成为免除进行论证的要求的借口。
五 联邦宪法制定者拥有最终的裁决权
宪法法院的法律审查权无论多么重要,议会民主的联邦宪法体制及联邦宪法制定者的最终裁决权对它都构成了限制。因此,上面描述过的那一类宪法规定是不容侵犯的。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宪法上的,而是宪法政策上的。由于联邦宪法制定者具有最终的裁决权,他们对宪法的现状也负有责任。
上述难题还涉及许多细微的方面。首先是宪法作为整体法律秩序的基础以及作为政治程序的框架的功能。二者都要求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其次是宪法的实质性内容,特别是作为个人自由保障的基本权利(注:见阿达莫维奇:《民主与法治国家》,《罗森茨威格纪念文集》,1988年第27(39)页。)(注:当然宪法法院也有权用它的职权,即按照宪法基本原则的标准来审查按照宪法制定的法律的权力,对宪法的本质负责。而最终应负责的则是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他只有在全面修政宪法时才受到全联邦人民的赞同与否的约束。所以并不是每一项轻浮草率地作出的与宪法形式有关的行为都是对联邦宪法的全面修改。反对的观点将抹杀议会民主中的责任关系。这一观点所带来的后果也对自己作了驳斥;把每一项在法律政策上有问题的宪法规定(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案例表明的那样)都认定为是对宪法的全面修改,这在实践中无异于阻止全面修改。从法律上来看,这意味着只能受全民公决的约束。至于这是否是保障宪法本质的合适工具,从法律政策上看是值得怀疑的。而在法律上起决定作用的是,这种间接民主形式恰恰与联邦宪法的议会原则思想相矛盾。)。此外还涉及与“宪法意识”概念有关的内容。这种宪法意识作为对宪法的确认与内在化(不仅存在于宪法专家的头脑里),是宪法作为一项法律同样起作用的前提。如果一部宪法没有得到广泛的赞同,其法律上的约束力便会成问题。遗憾的是,1933年和1934年的经验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前面列举的宪法行为虽然没有摧毁宪法意识,但却损害了它(注:马克:《维也纳公报》,1987年182页, 另见:黑姆佩尔:《联邦立法者对宪法的忠实程度如何?”这是题目的思考》,《奥地利律师报》,1987年第371页。》)。 这些行为——集累起来(宪法法院的用语(注:黑格尔:《社会的局外人与基本权利》,载《罗森茨威格纪念文集》1988年第157页。))——作为对基本权利的干预, 掏空了宪法的本质性基础并导致了一种“对宪法的不知不觉的全面修改”。另一方面,在上述一些案例中,不仅法学家的反应(注:梅利夏尔的证明:《罗森茨威格纪念文集》1988年第373(382)页。),而且舆论的反应也表明(注:当然对宪法法院关于政治家退休金的判决抗议呼声很高(格罗夫——拉姆绍尔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见《奥地利法学家报》, 1987 年第705(710)期。);另见贝尔希托尔德对此的看法,《埃马科拉纪念文集》第343页。 ), 奥地利的宪法意识不仅与战争期间相比, 而且与1946年至1966年之间的大联合时期相比,都有了很大的加强(在这一时期有一系列这样的宪法规定并未受到舆论的特别关注)(注:见梅利夏尔的证明(联邦法律公报1989年第54号(药店法第19条第7款)。 和厄林格:《基本权利保护的对象和范围——奥地利宪法法院》,载《欧洲宪法法院与基本权利》,1982年第335页。)。)。 如同在此谈到的宪法法院的解释一样,这应该是对宪法制定者的一个提醒,提醒他们要更加谨慎地对待宪法的宝贵财富。
我意识到,我的阐述并未穷尽“宪法制定者与宪法法院的管辖权”这个题目。如果我能成功地引起一场理智的、没有情绪负担或甚至没有前几年所听到的那种令人不快的声音的讨论,那我就十分满意了。
由谁来监督监督者自己呢?这是一个人们经常向宪法法院提出的问题。曼弗雷德·韦兰对此的回答是(注:佩林卡—韦兰:《奥地利的民主与宪法》1971年第239页。):“监督者监督他自己”。 我觉得对一个民主社会(这也是一个宪法概念(注:见宪法对此的法律保留,《关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8页。))来说, 科林内克的回答更加恰当,他稍稍改变了彼得·黑贝勒的提法,使人注意“宪法解释者的开放的社会(注:科里内克:《德国国家法教师联合会年刊》,第39、49页。)”。这个原则说来任何公民都可以进入的“宪法解释者的开放社会”,在民主制度中也是对宪法制定者的最后监督者。而我则要用我今天所作的考虑来取得我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要求既不多也不少。
标签:法律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法院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联邦论文;
